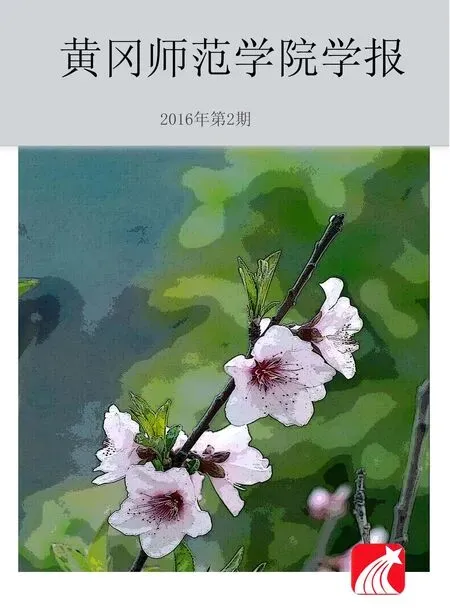浅谈莫言、王小波小说刑罚暴力叙述的根源及差异
刘梓晗
(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湖北黄冈438000)
浅谈莫言、王小波小说刑罚暴力叙述的根源及差异
刘梓晗
(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湖北黄冈438000)
莫言、王小波是新时期几乎同时出现的大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刑罚暴力叙述是他们作品引人关注的特征之一。当前学术界针对他们二人的这个特征出现了一些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并没有将他们二人的暴力叙述的特点放在一起做一个系统的比较。通过对现有的文献进行整理和对比研究,来阐述莫言、王小波刑罚暴力叙述的根源、不同点等问题。
莫言;王小波;刑罚暴力叙述;根源;差异
1980年以来,中国文坛出现的刑罚暴力描写越来越多,甚至形成一种“暴力奇观”[1],其中莫言和王小波就特别出色。他们用新的文学理念来写刑罚暴力场面,采用独特的艺术手法,以尖锐冷峻的笔触叙述刑罚暴力,使他们的作品迥异于以前的写作风貌。
一、莫言、王小波刑罚暴力叙述产生的根源
莫言、王小波的作品中刑罚暴力叙述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具体来说主要源自人生的遭际、创新意识的推动和西方文学的影响。
(一)人生遭际的影响 莫言、王小波在成长阶段经历了“文革”,在这个特殊的年代所有的暴力行为都以正当的名义获得解放,不需要借用文字来得到满足。“文革”泛滥的暴力让作家们感受到了历史的荒谬和人性的黑暗,暴力的历史只有通过暴力的叙述才能接近历史的真相。
莫言的童年生活在东北高密农村,那个年代的农村社会都普遍贫困,他家又因为成分不好,连救济粮都领不到。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歧视给他的少年生活留下了惨痛的记忆。另一方面,在农村莫言得以亲近大自然和丰富的民间文化,这培养了他强大的想象力。“文革”对莫言的性格、精神、思维方式、人生道路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莫言曾说“我对那片土地充满了仇恨”,“假如有一天我能离开这片土地,我绝不再回来”。[2](P305)正是莫言这些经历和在农村的生活使其感受到现实的压抑和无奈,从而产生了敏感内向的性格和强烈的逆反心理,这也促使了他日后将刑罚暴力作为其叙述的主题之一。并在刑罚暴力叙事中充分发挥了想象力,展示了他独特的创作才华。
与莫言有着惊人相似经历的王小波也生活在一个贫困家庭,“三反”运动期间家庭突遭变故,这对年幼的王小波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1966年“文革”开始,十六岁的王小波被送到云南兵团劳动,就是这段在农村艰苦劳作的日子里王小波开始尝试写作,这段经历也成为了《黄金时代》的写作背景。王小波曾说:“不幸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你别无选择,假如能够选择我也不愿生活在此时此地”。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留给王小波的是“创伤”的记忆,正是这些“创伤”为他日后的刑罚暴力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创新意识的推动 莫言、王小波都有很强的创新意识。他们不墨守成规,勇于在文学的丛林中开辟属于自己的地带。刑罚暴力在生活和文学上都是具有禁忌意味的话题,少有作家将此过程的展示作为叙事的焦点,莫言、王小波敢于直面这个过程并大书特书,肯定是有创新求变的意图的。
莫言曾说过,我一直希望创新,不重复旧作,一直把变化作为自己的追求。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勇敢和鲜明的创新态度,正是在这种创作观的指导下,他才会消解理性、崇高和主流话语的丑恶血腥,还原人性和历史中被遮蔽的一面。
王小波也曾说过,我们的民族总是有着许多理由钳制思想,封锁知识,而我能这么想,就说明我是个幸存者。所以在创作上王小波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冲破固有模式的钳制,寻求自我创新贯穿于其整个创作历程中。
莫言、王小波在对刑罚暴力这种富有禁忌性的文学叙述中不随波逐流,不躲不绕,敢于直面,这种勇气使他们在文坛上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三)西方文学的影响 莫言深受川端康成、马尔克斯、卡夫卡、福克纳等作家的影响。其文本的暴力叙述具有川端康成的细腻,马尔克斯式的魔幻,卡夫卡的荒诞变形及福克纳对潜意识和非理性的挖掘。
莫言在看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深受启发,他明白了,作家不仅可以虚构人物,还可以虚构故事。而他也可以写自己的故乡,这就像打开了一道时光闸门,他童年的记忆都被激活了。
王小波很多次的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提到萧伯纳、罗素、福柯等人对自己文学创作的影响。其中有一个人备受他的推崇,就是法国的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他多次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到杜拉斯,在《我对小说的看法中》中他说:“我对现代小说的看法,是被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固定下来的。”王小波不只是说说而已,在他自己的创作当中,也不断地向杜拉斯学习,在他们二人的作品中可以发现很多相似的地方。
二、莫言、王小波刑罚暴力叙述的差异
刑罚暴力叙述是莫言、王小波作品中的常用质素。作为一种文学表现手法,刑罚暴力叙述在小说的整体叙述中主要是表现主题和塑造艺术形象的功能。只有不哗众取宠,不为了描写暴力而暴力,不游离于作品之外的刑罚暴力描写才能成为有效的叙事手段和策略。
(一)莫言对行刑过程的描写极尽惨烈之美,而王小波则以游戏化的手法来表现 莫言的《檀香刑》可以说是描写刑罚暴力的集大成之作,是一部成功的中国式的暴力刑罚小说。小说总共演示了五种刑术,叙述了六次行刑的具体过程。场面血腥至极,《檀香刑》中的刑罚一次比一次时间长,一次比一次精细,一次比一次血腥可怖,让受刑者饱受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
我们来看《檀香刑》中一小段关于刑罚的细致描写。“其实,这道‘阎王闩’的精彩之处,全在那犯人的一双眼睛上。你爹我的身体往后仰着,仰着,感觉到小虫子的哆嗦通过那条牛皮绳子传到了胳膊上。可惜了一对俊眼啊,那两只会说话的、能把大闺女小媳妇的魂儿勾走的眼睛,从‘阎王闩’的洞眼里缓缓的鼓凸出来。黑的,白的,还渗出一丝丝红的。越鼓越大,如鸡蛋慢慢地从母鸡腚里往外钻,钻,钻……噗嗤一声,紧接着又是噗嗤一声,小虫子的两个眼珠子,就悬挂在‘阎王闩’上了。”[3](P36)
在这段暴力叙述中,通过“小虫子”遭受酷刑时眼睛的声、色、形的勾勒,集中表现出受刑者极度的精神痛苦。莫言通过调动语言的视觉功能,对行刑的每一个细节和过程都描写的客观和冷静,以此来达到真实的残酷刑罚展示。
莫言作品中的刑罚暴力描写充满了可怖又残忍的血腥气息,甚至还充斥着一种狂欢式的享受,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暴力刑罚中的受罚对象在肉体的非人折磨中慢慢地死去。作品中的刑罚暴力叙述浓墨重彩地表现刑罚暴力所带来的惨烈之美。
那么莫言如此详尽的描写刑罚暴力的目的是什么呢?当我们通过对那些血淋淋的刑罚场面描写的解读之后就会发现,作者想要表达给读者的是暴力刑罚背后所隐藏着的人性。
莫言以这种极端形式告诉我们暴戾、嗜血、凶恶是人的本能,是人性的真实存在。人们往往不敢或不愿直面这些,而用道德的口号,价值伦理等文化因素制造一个遮蔽自我,装饰现实的面具,莫言则以对暴力、血腥的展现无情地撕下了这个面具。另外,莫言的刑罚暴力叙述还颠覆了温文尔雅的历史表述,使权力、秩序和现实的荒谬性、虚假性昭然若揭。
而王小波则以“有趣”来作为自己的美学原则,正如他在《红拂夜奔》的序言里说的那样:“这本书里将要谈到的是有趣。其实每一本书都应该有趣,对于一些书来说,有趣是它存在的理由;对另一些书来说有趣是它应达到的标准。我能记住自己读过的每一本有趣的书,而无趣的书则连书名都不会记得。”[4](P268)
因此与莫言相比,王小波笔下的刑罚暴力叙述则不再具有那种精细的惨烈之美,而是用戏谑的游戏化的手法来写刑罚暴力。
在《红拂夜奔》中,王小波用调侃的语气叙述着红拂在受刑过程中的种种看似合情合理和正常的行刑过程,其实却可笑又不合逻辑,从而让整个故事具有强烈的讽刺和幽默效果。
到了《万寿寺》中,死亡描写的客体已经不再是死亡本身,而是在玩弄叙述,就更没有任何庄严可言了。刺客的死刑中,连受刑人都变得模糊不清,砍下的人头竟会说话,杀人变成了一种游戏。在王小波的这些刑罚描写中都有大量夸张、想象的成分。用这样戏谑的游戏的笔调来描写死亡,最终效果就是让死亡变成了游戏、悲剧变成了喜剧,从观众到受刑者本人好像都加入了死亡的娱乐之中。
在这种死亡的娱乐化描写、悲剧的喜剧化描写中,我们也能体会到犀利的反讽意味。无论是刑罚还是自杀,背后都是权力在起作用,将权力所具有的神圣色彩与不可对抗性完全颠覆,表达出作者对集权的憎恶。
王小波笔下的刑罚暴力用游戏化的手法来表现,虽然给人的第一感觉是荒诞,不可信,但是如果深入体会,这种游戏化的描写就会像印象派画作一样,变得越来越真实,越来越具有震撼力。
(二)莫言笔下的刑场充满了狂欢节气氛,而王小波的则充满了黑色幽默 《檀香刑》中描写行刑的过程无疑是一场盛大的狂欢。莫言将刑场变成众人狂欢的剧场,在这个剧场里有着不同的表演者:受刑人孙丙高声唱着哀绝人寰的猫腔,刽子手赵甲精湛行刑技艺的展示,看客们则聚精会神地看着这场表演。在执行檀香刑的刑场上,所有的人都沉浸在迷乱和疯狂之中,置生死于度外。于是,一场暴力行刑仪式就变成为一场众人狂欢的大典,在这场“狂欢节”般的气氛中所有事情都以一种可笑的姿态出现。行刑时如果受刑者显得怕死,下面的看客们就会鼓励他们;如果刽子手在行刑过程中失误了,看客们就会喝倒彩。人们害怕受刑,却又非常热衷观赏他人被折磨被行刑的过程,这是一种变态的心理。刑场上万众狂欢的是一场虚构的戏,一场充满病态和癫狂的戏。
王小波在《红拂夜奔》中的刑场描写也充满着狂欢的气氛,但与莫言不同的是王小波更多的则是黑色幽默。王小波认为幽默是一部优质小说的必备特质,而这个幽默则是他在《红拂夜奔》中的序言里所说的有趣。他的作品中想表达的就是一种超越无趣现实生活的一种幽默,所以体现在他的作品中的语言是夸张、戏谑、幽默和调侃的。在他的作品中摒弃了传统小说的叙述情节、环境、人物的原则,采用了他所擅长的黑色幽默进行了大胆的创造和天马行空的想象,摆脱了以“真实”为原则的传统小说的叙事理论的束缚,摆脱了传统文化对文本的约束。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人物大都可笑滑稽,故事情节怪诞散乱,语言幽默睿智。王小波笔下的刑场是暴力、专制,无趣世界的一个缩影,受刑人以一种幽默有趣的语言和笑声将这种无趣颠覆了,在这种笑声和辱骂声中所透露出来的则是这个世界的残酷、血腥和荒诞,更折射出一种深深的悲哀。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莫言和王小波小说中的刑罚暴力叙述隐含着对人生荒谬感的体验,对被伦理道德所充斥的人们的精神世界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在他们二人的作品中,不同的艺术因子相互糅合、碰撞,构成一个富有张力的文学世界。优美与丑陋、高雅与粗俗,理性与感性的掺和对立,是他们暴力叙述的重要特征。将死亡、暴力、血腥这些在传统文学中被认为是丑恶的事物掺入优美、崇高、诗意、力图造成奇幻的复合的审美境界。无论是莫言的血腥叙述还是王小波的黑色幽默,刑罚暴力在他们的作品中都是实现他们写作意图的一种手段。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是小说必备的质素,但这些故作惊人之语的背后所蕴藏的则是人道热肠,刑罚暴力叙述因此在小说的整体中获得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1]王德威.伤痕即景暴力奇观[J].读书,1998,(5).
[2]王金城.理性处方:莫言小说的文化心理诊脉[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3]莫言.檀香刑[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
[4]王小波.青铜时代[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 张吉兵
I206.7
A
1003-8078(2016)02-0051-03
2016-03-08
10.3969/j.issn.1003-8078.2016.02.14
刘梓晗(1990-),女,湖北黄冈人,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教育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