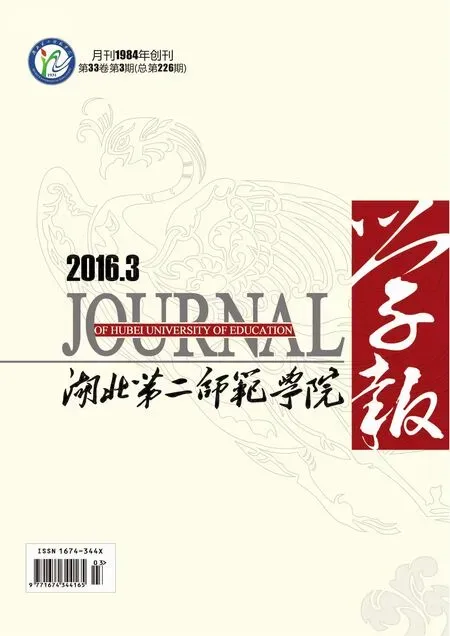语境维度论关照下《鸿门宴》英译语用规则研究
赵文婷
(辽宁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9)
语境维度论关照下《鸿门宴》英译语用规则研究
赵文婷
(辽宁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9)
摘要:本文以哈蒂姆和梅森在《话语与译者》中对语篇语境的多维关照为视角,从交际、语用和符号三个语境维度论述《鸿门宴》中部分篇章英译,探讨原文与译文意义转化背后的语用规则差异。并提出在进行汉语典籍英译时,应多维剖析原文语境,挖掘原文篇章语言形式背后的隐含义,并按照英语文化中的语用规则重构语境,再现原文含义。
关键词:语境维度;《鸿门宴》;英译;语用规则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纷纷把语篇语言学(也叫话语分析)理论引进翻译研究领域(Baker,1992),他们意识到语篇分析和语用意义的重要性,认为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原文和译文两种语言体系,还包括“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和“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张美芳,黄国文,2002)。豪斯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理论为基础提出翻译质量评估模式,贝克在篇章和语用层面的分析拓宽翻译研究视野,在此基础上,哈蒂姆和梅森又进一步拓展到语境和语篇的意符层次上,其中从交际、语用和符号三个语境维度来探讨翻译的观念得到认可。本文拟在这一视角的关照下,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鸿门宴》及其英译试做分析,综合多维度语篇语境,对英汉语用规则差异进行对比,探讨原文及译文多维语境下意义传达的得失。
二、语境维度与语用规则
(一)哈蒂姆和梅森的语境分析模式
哈蒂姆和梅森作为微观翻译功能的语篇分析派以语域分析模式为基础,结合语用学和符号学的有关知识构建了一个新的语境分析模式,包括交际、语用、符号三个层面,被称作语境维度论。
语境维度中的交际层面也称作语域层面,理论来源于韩礼德的话语分析模式。韩礼德(Hanliday,M.A.K and R.Hansan:1985)的话语分析模式重视语言的交际功能,他提出通过语域(语篇所处的动态情境)以及语域的三个可变元素语界、语旨、语式来进行话语分析。
翻译中,译者需要对原文和译文进行双语语域分析,用译语构建与原文相契合的语域环境,由此哈蒂姆和梅森(Hatim.B & Mason:1990)提出了篇章语境的语域(交际)维度。但篇章语境绝不可能仅仅是三个情景变量的累加,他们又着眼于微观语言层面上的动态情形,提出语境的语用维度,具体指的是“借用语言行事”的能力。根据语用学的基本精神,句子具有因实施行为(perform action)和超越词义(sense)而产生某种交际目的的能力(杜洪峰,2008)。篇章词句是作者为交际目的的实现做出的导向性选择,词句整合后有超越字面的含义,起到语境效果。同时符号系统之下的语言系统还带有符号的特性。译者应时刻关注语言的符号性并保留语言作为符号使用的诸种特征。比如对隐喻翻译时要考虑其联想义所带来的语境变化。至此,对语篇翻译进行交际、语用和符号三层面的语境分析模式才具有有效性。
(二)语用规则与篇章语境
人们在交际中不仅要正确使用语言的语音、语法和词汇,为交际顺畅还要正确使用语用规则,语用规则制约着语言形式,包括在对待冲突或矛盾、提出请求、表示拒绝和异议的具体言语行为和事件。某种语言的语用规则往往是约定俗成的,是一种潜在于语言使用者深层意识中的特殊的也是重要的组合规律(周树江,王玉新:2007)。在同一语言和文化中,语用规则和篇章语境是相互影响、辩证统一。读者可以通过语境预测或判定篇章结构及词语语序的选择和表达;又能依据潜意识语用规则形式化语言表达,建构出一定的篇章语境。但不同语言有不同的语用规则,符合某语言语用规则的礼貌表达在另一语言中可能很粗鲁,在语篇体裁和情景语境确定的情况下,语言意义的分析和传达还分别受两种语言语用规则的制约。跨文化语用对比研究也证明,不同语言文化传达和推理含义的方式也不尽一致(张新红,何自然:2001)。这些文化背景和推理习惯都应看做语言使用者的语用规则。
某语言的语用规则对于用这种语言创作的作者来说是一种背景语境,而译者必须具有双语背景语境。翻译时,译者应先作为原文读者,解读源语篇章语境,看到潜藏在句子、篇章等表面内容之下的不易察觉的语言习惯,并对原文语言形式下的语义潜势进行挖掘。之后,再用符合译入语语用规则的表达形式重构语境、使意义再生。
三、多维语境下《鸿门宴》英译的语用规则关照
《鸿门宴》是《史记·项羽本纪》中的一部分,内容是项羽想在鸿门宴斩杀刘邦却没有成功。本文采用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用语境维度论对《鸿门宴》原文及英译进行分析,讨论译者是否并怎样做到再现原文篇章含义,以及意义再现的语言形式在理解习惯、推理习惯、表达习惯上是否符合译语的语用规则。
(一)译文导向译语理解习惯
项羽得知刘邦想在咸阳城内称帝时,勃然大怒欲马上讨伐刘邦,范增对项羽说道:“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杨宪益、戴乃迭(2002:11-83)译文为:“When the Lord of Pei was in the east,he hankered after wealth and beautiful women,but since entering the Pass he was taken no loot nor women. This shows he has great ambitions. I told a man to watch his halo,and it takes the shape of many-colored dragons and tigers-the halo of an emperor.You must lose no time in attacking him!”
对原文进行语域分析结果如下:语场:范增向项羽进谏除掉刘邦;语旨:军师范增向项王冷静分析刘邦的行为和气质;语式:范增对话项羽,对比刘邦行为,引入理据得出结论。原文语境的语用维度分析为:语篇行为意图在于告诫项羽和读者刘邦有成为天子的潜力。原文语境的符号层面分析为:“志不在小”、“天子气”等符号说明刘邦志为天子;范增话语的排列顺序也是符号的体现,先通过刘邦自身行为变化判定其胸怀大志,又通过刘邦外部气质变化强调其大有成为天子的潜力,先讲内因后讲外因双重揭示刘邦称帝野心,而范增本身并不希望刘邦成为天子,其目的在于警告项羽下定决心、及击勿失。
对译文进行分析,发现语域维度上与原文基本一致。但在语用层面,译文忽略了范增急切警示项羽的语境义,笔者认为最后一句译作“You must lose no time in attacking him or I am afraid he will steal your crown.”更贴切原文目的,便于译语读者理解。在符号层面,“天子气”译为“the halo of an emperor.”会使英语读者产生疑问,对此,译者加了注释,把“望气”行为解释为“The ancient Chinese believed that over the heads of famous men there sometimes appeared a vapor or halo,which astrologers could detect”。这不仅是对汉文化的补充,原文表达意图也易于识别,且古汉语中观云气测灾祸的语用规则也会给译文读者留下印象。
杨戴的译文多数采用了异化手法进行直译,且按原文顺序翻译原文,这利于向西方读者传达汉语使用习惯。但英语读者说话、阅读时,更愿意开门见山,先得结论后解释理据,因此杨戴的译文不能说符合英语的语用规则。对于云气的符号性,英语读者可能不了解传统中国对封建迷信的崇拜,不易推测出这是范增欲加强理据的心理色彩。对于这种文化差异,杨戴增加了注释,弥补了译文读者对原文的理解落差。
(二)译文依照译语表达习惯
项羽的左尹项伯和刘邦的军师张良交好,项羽攻打刘邦在即,项伯私见张良劝他离开刘邦,项伯对张良说:“勿从俱死也。”张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杨戴的译文为:“Otherwise you will perish”,he warned him.But Zhang Liang replied,”The King of Han sent me here with the Lord of Pei. It would not be right to leave him in this emergency. I must tell him”
原文进行语域分析结果如下:语场:项伯劝张良离开,张良仍要帮助刘邦;语旨:项伯和张良俩友人讨论去留;语式:通过项伯与张良的对话表现各自的想法。对原文语境的语用维度分析为:语篇的行为意图在于张良想坚守仁义、继续帮助刘邦。对原文语境的符号层面分析为:“臣”、“王”、“公”称呼符号对比使用,加强其重视身份、等级的理念;而究其不愿逃走的根本原因,正是一个“义”字。“亡去不义”的价值观深深植入张良心中,这是每个义士追求的品格,也是统治者统治人心的工具。“义”字代表的符号显示了儒家道德观念。
杨戴忠实的译文在语域维度上基本与原文一致,但在翻译“臣为韩王送沛公”这一句时,对文言文理解有误,不是张良被韩王送给沛公,实际意义应为张良替韩王护送刘邦(入关)。这在语用层面有重要意义,因为“替”韩王“护送”沛公比“被”韩王“送给”沛公更能体现张良“不与俱去”“不能不语”的使命性。因此译文应该改作“The King of Han sent me here to make sure the Lord of Pei’s successfully entering of the gate.”张良把护送沛公当做使命更显示其大义,不仅增强了语气,还使得上下文语义连贯。在符号层面,因为英语中缺少“臣”这个谦词的对应词,译者在译文中转换了句式,把“臣(我)”由主语转化为宾语,以此避免英汉称谓中的不对称现象。对于“义”的翻译,译者巧妙地转化为“be right to do”的形式,清晰地再现了张良的价值观,达到了原文意义再现的目的。
在对原文语境综合分析后,汉语使用者潜意识的使用规则也就显而易见了,表现为:朋友之间拒绝对方时必然解释原因;君臣有利益矛盾时以大局为重;儒家文化是文人义士的说话和行为准则。在语用规则方面英语和汉语有相同的部分,英语使用者在拒绝时也会考虑到礼貌的解释原因,也会遵从统治者的权威,但他们没有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可能有更强的自我意识,因此译文中强调张良的忠心品质也就极为必要。
(三)译文符合译语推理习惯
刘邦赴宴而来,向项羽表明自己绝无反逆之心,项羽请沛公入席,此时范增数目项王,举所配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杨戴翻译为“Fan Zeng shot Xiang Yu several glances,and raised his jade pendant three times as a signal,but Xiang Yu paid no attention.”对原文进行语域分析结果如下:语场:范增举起玉玦三次示意项羽下决心斩杀刘邦;语旨:作为军师的范增举玉玦示意项王;语式:采用叙事手法对人物进行动作描写。对原文语境的语用维度分析为:范增的这段话形成的语篇其行为意图在于暗示项羽早下决心杀刘邦,而项王犹豫不决、沉默不应。对原文语境的符号层面分析为:范增的一系列动作是向项羽传递信息,以“玦”代决,示意项王当机立决、斩杀刘邦。且范增举玉玦示之者三,其中“三”为表示次数之多的符号,更加显示范增催促项王之意,以及项王优柔寡断之态。“玦”与“决”同音,汉语读者可以联想到范增举玉玦之意。“玦”字以音表意,这种表现手法也应该理解为汉语常用的语用规则之一。但在翻译为英语时,因为译文读者与汉语读者已有知识的差异,不能由玉玦联想为下决心的意思,会对范增举玦的动作有疑问。杨戴采用直译的手法译出“举玉玦以示之者三”,译文读者恐怕难以理解其中深意,笔者认为可改为“raised his jade pendant several times which means a signal of encouraging Xiang Yu to make up his mind in killing Liu Bei”,举玉玦作为范增向项羽传递的杀人符号,就容易被译文读者结合上下文语境解读了。
在语用维度层面,译文不能直接表达范增举玉佩数目项王的目的,译为“raised his jade pendant three times as a signal”也只是在直译原文,不容易让译文读者推理出范增急切督促项王下决心斩杀刘邦之意。因此在译文中也应做到符合语用目的,有必要把范增举玉佩的目的阐述明白。与此同时,从符号维度来看,“玉玦”在汉语中音、形、意的结合使得翻译困难,译文难以达到三者统一的效果,这时为了弥补语篇符号意义的缺失,应该按照译文推理习惯予以补充,那么针对汉语中以音表意或以形表意的符号,在译文中就可以通过转换或补充来达到原文效果。
四、结语
哈蒂姆和梅森的语境维度论拓展了前人的视野,多维度多层次的论述使得语境功能得以全面展示。翻译作为一种交际行为是在语境的制约下进行,而翻译中意义的交流和传达也是在源语语境分析和译语语境重构中实现的,因此语境对翻译具有重要的意义。除此,翻译的顺利进行还要对双语语用规则分别进行剖析和转化。源语语言形式需要通过语用规则挖掘深层含义,原文篇章含义也需要通过语境分析渐渐明晰,至此,原文的表层、深层、微观、宏观含义才能全面呈现。译者用译入语进行意义重构时,还要考虑到译入语语用规则下的语境重构,使译文含义符合译入语语言表达。
参考文献:
[1]Baker.M. In Other Words-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M]. London: Routledge, 1992.
[2]Munday J.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72-110.
[3]Hanliday,M.A.K and R.Hansan.Language,Context and Text:Aspect of language in a Social-Semantic Perspective[M].Victoria:Deakin University Press,1985.
[4]Hatim.B&Mason.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ion[M].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90.
[5]司马迁著,凌受举今译,杨宪益等英译.史记选[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
[6]周树江,王玉新.论语言的组合规则之语用规则[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7,(4).
[7]张美芳,黄国文. 语篇语言学与翻译研究[J]. 中国翻译,2002,(3):3-4.
[8]张新红,何自然. 语用翻译:语用学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J]. 现代外语,2001,(3):291.
[9]杜洪峰. 哈蒂姆与梅森的语境维度论对英汉篇章翻译的启示[J].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8,(6):119-122.
责任编辑:陈君丹
The Pragmatic Rules i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HongMenYa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xtual Dimensions
ZHAO Wen-t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029, China)
Abstract: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context which was proposed by Hatim &Mason in their work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 the paper will analyze several parts of Hong Men Yan and the English version of it from communicative, pragmatic and semiotic perspectives. There are discussions about the differences of pragmatic rules beyond the meaning transfer from source text to target text. This paper proposed that translators should analyze multidimensional contexts while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s into English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mplied meanings behind the text. Furthermore, the contexts should be rebuilt in English according to their pragmatic rules in English Culture to successfully transfer the meaning.
Key words:Contextual Dimensions; Chinese classics Hong Men Yan; Chinese to English translation;pragmatic rules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44X(2016)03-0124-04
作者简介:赵文婷(1992-),女,山东济宁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翻译学、认知语言学。
收稿日期:2016-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