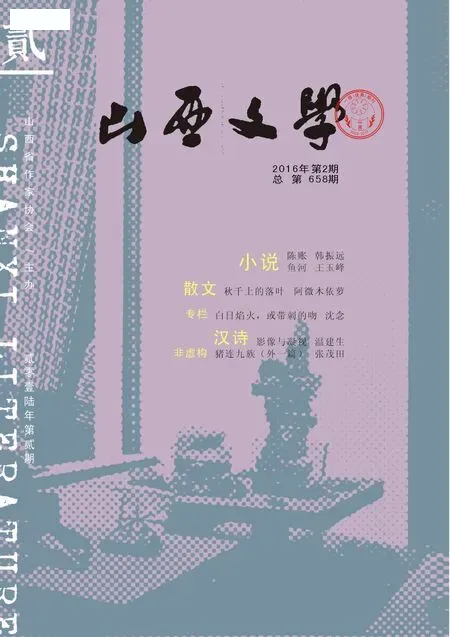白日焰火,或带刺的吻
沈 念
白日焰火,或带刺的吻
沈 念

多年前在那个小县城停留的夜晚,诗人朋友邀我分享他刚借到的影碟《日瓦戈医生》。那是个激动的夜里,诗人和我在观影结束后争相叙说着冰天雪地的壮美风光,动荡革命年代里知识分子的跌宕际遇和文学中的经典爱情唱挽。当谈到同名小说作者、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斯捷尔纳克时,深受苏俄文学影响的诗人从满墙的书堆里精准地挑出一本《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然后精准地翻到茨维塔耶娃的诗章,说,是这个唯一能同阿赫马托娃媲美的俄罗斯天才女诗人催生了老帕的“日瓦戈医生”。
这次访友的意外收获,让我第一次把目光聚焦到俄罗斯广袤丛林中这棵被遮蔽的白桦树上。茨维塔耶娃是帕斯捷尔纳克的爱慕者,他们年纪相仿,同一国度,同一爱好,互相称对方是“俄罗斯当下活着的最好的诗人”。她经常在纸上世界与他相遇对话,在交往甚密的十三年时间里两人通信二百五十多封,充满柔情蜜意。当有人提到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时,她会条件反射般答道:“这是我最亲近的人。”但两人因政治上的分歧终归分道扬镳,她捍卫自己的人生原则,对心仪的爱人也不敷衍放弃。这场分离起初并未在帕斯捷尔纳克心中引起多大的震动,直到茨维塔耶娃自杀。他对茨维塔耶娃自我践踏生命的做法有着无法言说的负罪感。纵然她的死并非他一手造成,但他在内心认定自己是那一时代里个人悲剧的推动者之一。战争结束后他埋首写作,最终写出了带来显赫声名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
捍卫荣誉?复仇的写作?一切不幸来自个体的局限性与绝对性。茨维塔耶娃恰好就是这两者的合体。让人郁结的悲剧结局是这样的——
1941年8月31日,茨维塔耶娃回到僻远的叶拉布加镇上,因战争爆发被遣散至此的她,为了儿子的学业想迁到作协所在地奇斯托波尔市,并申请到即将营业的文学基金会食堂做洗碗工,这些请求遭到委婉拒绝。她走回租住屋内,茫然环顾空洞的四周,坐到简陋窄小的木桌前写信,这是与儿子穆尔的最后一次交谈。她给很多自己爱过的人写信,但过去的那些激情、甜蜜或忧伤荡然无存。她显得从未有过的清醒和充满力量。她像搬一块块巨石一般写下活在人世的最后见证,然后找来一根结实的绳带自缢。
小镇上没人惊讶她的死,因为大家对这位异乡女诗人很陌生,只有房东大婶在叹息:“她的口粮还没有吃完呢,吃完再上吊也来得及啊!”茨维塔耶娃被草草埋葬在叶拉布加的一座山丘上,没有立下任何标志的墓碑。死亡酝酿由来已久,只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推门而入。在她贴身的口袋里,人们看到了她留给儿子的信:“小穆尔!原谅我,然而越往后越糟。我病得很重,这已经不是我了。我爱你爱得发狂。你应当明白,我无法再活下去。转告爸爸和阿利娅——如果你能见到他们——我爱他们直到生命最后一息,并向他们解释,我已陷入绝境。”
这个“绝境”,不正是她在国外流亡的日子里夜不能寐的“远方”吗?“远远近近,无论到哪里,/我总要把它携带在身。”“我纵然断去这只手,/哪怕一双,也定用唇作手,/写在断头台:那揪心的住所——/我的骄傲,我的祖国!”茨维塔耶娃1932年写下的这首《祖国》,道出的是她在战争与政治动乱年代对祖国无法割裂的思念之情。但这个她所热爱的国家,以怎样的方式迎接流亡归来的茨维塔耶娃全家呢?
现实的冷酷在她生前与死后都是叫人绝望的。大概是两年前,她带着穆尔从国外回来,找不到工作,没有一个老朋友与她来往,多数苏联读者不知其名,熟悉她的老作家也绝口不提,在那个惊弓之鸟、人人自危的年代,谁敢提到这位流亡国外十七年之久的“白军眷属”呢?她死去的这一年,苏德公开宣战。丈夫谢尔盖·艾伏隆被当局抓捕羁押,一个半月后被秘密枪决。女儿阿莉雅德娜此前流放“古拉格”,穆尔应征入伍并很快战死沙场。孤独的生活,爱的流散,被全世界抛弃,活着的意义一次次被自我否定,茨维塔耶娃是真正绝望了。她以极端的自杀方式投入祖国怀抱,不正是帮她完成一次热爱的表达吗?
阿里阿德娜曾说:“妈妈两次因为父亲毁掉自己的生活。第一次是离开俄罗斯寻找他,第二次是与他返回俄罗斯。”
但谁能拒绝祖国、故乡在每个人心中梦寐萦怀的呼唤呢?
茨维塔耶娃出身于富足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大学教授、著名艺术家,普希金国家造型艺术馆的创始人。有德国和波兰血统的母亲是音乐家,精通多国语言,弹拨一手好琴。艺术的熏染,让茨维塔耶娃很早就开始了诗歌艺术的启蒙,但母亲的早逝,无人管束任其自由发展的家庭环境,又养成了她极端的性格。在她成长的日历里,害怕孤独,耽于幻想,她渴求遇见的每一个人都是精神上的知己。她一生痴恋过多位谋面或未曾谋面的心灵知己,但上天难遂人愿,那些想念和激情在心中燃烧没多久,就很快被生活的洪流扑灭。知己成异己,希望变绝望,她唯一的解脱是抒写一行行或悲怆或广阔的心灵诗歌。
在茨维塔耶娃的精神伊甸园里,那些她曾爱过的男士们的名字,是“眼睛上的吻”“幽蓝冰结的泉眼”。俄国出版商维奇尼亚克,评论家亚历山大·巴克拉赫,青年男子阿那托利·斯坦格,丈夫的好友贡斯坦丁·罗德茨维奇,青年诗人施泰格尔……她开始一次次爱情冒险,情人关系一经虚构,立即刮起“感情风暴”。她特别钟情那些会写诗或喜爱诗的年轻男子,她并不需要对此人有多少了解,甚至故意推远相识的机会。她只需要一次邂逅,一封表达倾慕的来信,她其实是在与想象中的完美的人恋爱。但这些多是她单方面付出的爱,总是不了了之。在茨维塔耶娃的爱情观念中知己灵魂的融合永远占据首位,坠入情网成了她生活中的家常便饭,但她经历和迎来的始终都是不幸不圆满。“绝望风暴”随后掀起,为从中解脱,她疯狂写下许多流动着爱恨交织的情诗。恋爱成了激发她创作灵感的源泉,也是她的爱情诗格外打动人的重要原因。每首诗都有对象所指,每段情感都有可触可抚的细节。但年岁增长,她爱得越来越少,妆容不整,心情苦涩,白发丛生,那终究要关闭的情感之门突然坍塌,因为爱情带给她的只有痛苦和伤害。
多情的证据链,还可以延伸到茨维塔耶娃的一次同性恋情,虽然这段恋情被研究者们避讳不谈。她这次热恋上的女诗人帕尔诺克本身是位同性恋者,持续一年半之久的同性恋给她的性格留下烙印。“因为我们的生活——/在道路的黑暗中各不相同,/因为您充满灵感的诱惑”,茨维塔耶娃在诗作《女友》《少年诗篇》和《致女骑手》中倾诉心中的欢乐,也向人们供认出她为同性吸引带来的恋情。这段热恋关系在1915年底破裂,因为这时又一位异性倾慕者闯入了她的视线。
而在茨维塔耶娃生命中另当别论的两个重量级男人,是里尔克和帕斯捷尔纳克。这两位优秀的诗人在她的情感之路上被她撞遇。她与里尔克的交往发生在1926年的夏季,短暂地延续了四个月。他们书信往来,互寄作品,茨维塔耶娃几度想去见见这个“活生生的、呼吸着的、在某个地方居住的爱人”,当她还在信中试探里尔克同意与否时,里尔克因病去世。在他们通信的过程中,里尔克因每况愈下的身体而无奈的冷淡回应,以及他对婚姻家庭的抵制、对孤独的享受,几次让茨维塔耶娃气恼不已,她在信中明白地表达浓密的爱意,“吻到你的心”,“直至灵魂(咽喉)深处——这就是我的吻”。里尔克固然欣赏异国女诗人的才华,却似乎并不想和她有更密切的事情发生。他明白清楚地在其法文诗集《果园》中用诗题回复:他保持着诗人之间的关系,他对男女之间的关系保持沉默。这“沉默”遭到茨维塔耶娃对改变两人关系性质的反对,但反对无效,里尔克以死亡的方式保持了他们的“诗人关系”。
与帕斯捷尔纳克之间的暧昧则持续了很长时间。他们从1918年开始交往,直到茨维塔耶娃去世,通信多达数百封。他们互相在作品中书写对方,以灵魂上的兄弟姐妹相称,但现实生活中的几次会面计划,都因帕斯捷尔纳克的两次婚姻、茨维塔耶娃的几次精神出轨而没能实现。直到1935年帕斯捷尔纳克应苏维埃当局邀请参加一个在巴黎举行的反法西斯国际作家代表大会,两位诗人有了一次不成功的会面。前者要逛遍巴黎的大小商店为心爱的第二任妻子买礼物,后者没有丝毫情绪去陪他完成这一任务,在她心中,她不屑与任何不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女人竞争。当然,在他们的分歧中,更多因为文学观念的差异及政治立场上的鸿沟。茨维塔耶娃知道她遵循的是真的法则,艺术的自主,永远也不会加入到歌颂的大合唱之中。帕斯捷尔纳克则以更接近人性的犯错和不完美,频频站到革命胜利者的阵营,尤其是献身集体农庄式的农业合作的歌功颂德中而受到女诗人的斥责。
饥饿与战争一同而至。十月革命之后,红军与白军疯狂内战,农业被毁,粮食告急,革命露出一张饥饿的嘴脸。人们在教堂里听到这样一封主教的信:“腐肉成了饥饿的人民首选的美餐,连这样的美餐也很难觅得。”伴随茨维塔耶娃的富足生活也被时代这个莽夫剥去温暖的“外套”,丈夫身在军营,独自支撑这个家庭的她逼迫之下把两个孩子送到孤儿院,因为听说那里可以吃得好一点,但女儿很快在那里生病,饥饿、脏乱、疾病侵袭,她刚把阿里阿德娜接回家,二女儿伊琳娜就死在了孤儿院。这个刻骨铭心的伤痛,让身为母亲的她自责不已。她要和革命前那个曾经充满幻想的年轻女子决裂,决裂加剧了她对政治的远离,对那些政治狂热分子的回避。
茨维塔耶娃把自己的第二部诗集《神奇的路灯》题献给一见钟情而结合的丈夫艾伏隆,他们起初感情很好,但妻子经常性的“出轨”,尤其是那场让人嗤笑的同性恋情,对艾伏隆造成了看不见的伤害。懊恼的艾伏隆只有逃避,结果是行军入伍,这一步决定了他以及一家未来的不幸命运。他先是坚决反对沙皇专制政体,一个偶然转机又成为了沙皇的捍卫者。艾伏隆从1917年入伍后,便杳无音讯。后来得知丈夫跟随溃败的白军流亡到布拉格的消息后,她托尽关系出国团聚。正如同她女儿的评述一样,这次出国虽然家庭团圆,但让茨维塔耶娃的生活和创作陷入到因政治所设下的“未来陷阱”。
通往陷阱之路与艾伏隆的政治立场和身份发生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起初以反苏维埃的白俄身份出现的艾伏隆,为了重新取得一张故国的护照,在巴黎主持了一个苏维埃机构,还招募成了苏维埃政治警察机构的秘密成员,他转身就滑向了苏维埃立场,洗“白”成“红”。艾伏隆还参加了苏联契卡在国外设立的公开组织“祖国之友同盟”活动,该同盟的宗旨是动员俄侨归国或在国外协助他们工作,并冒险去暗杀拒绝返回苏联的契卡成员。他的这一转变给自己也给整个家庭带来“血”的教训。一直拒绝任何政治派别“邀请”的茨维塔耶娃,越来越不堪忍受丈夫对物质现实的热衷,过去的共同语言远离他们的生活。这让“渴望成为她自己而不是其他什么人”的她苦恼,离开与否这个问题纠缠于心,但她下不了决心离开。“我生命的一半”,她的孩子的相继出生,她满怀深情地记录着孩子们的一言一行。在那段丈夫不在身边的可怕革命岁月里,她与孩子相依为命,远离故土流亡他乡,这些在茨维塔耶娃的心里又烙下一个信念——“如果我现在就要死了,我更多的是会为孩子们感到痛苦,因而——从人性的角度,我首先是母亲。”
诗人让位于母亲,但母亲却与长大的孩子在政治之间的纠纷越来越对立。辍学在家料理家务照顾弟弟的阿里阿德娜,为了挣脱母亲把她束缚在锅碗瓢盆的家庭妇女式生活,尝试过一次自杀,后离家出走,并独自回到莫斯科。穆尔到前线打仗,战死沙场。茨维塔耶娃的死,不如说是对爱的绝望,在那段身处异国他乡以及回到国内的日子里,没有了朋友,没有了可以爱的对象(除了亲人)。著名翻译家蓝英年谈到茨维塔耶娃时曾作一个假设,她没发生同性恋、艾伏隆未因此入伍,她不一次次掀起感情波涛,不蔑视巴黎俄侨界舆论,不与持不同政见的作家朋友对立,家庭未陷入困境,而是贤淑的妻子、慈祥的母亲、稿酬丰厚的作家,她的命运又将如何呢?当然任何假设都是枉然,她的个性成就了她的文学影响力,也把她置于现实的悲惨境地。有的艺术家总是很难讨得现实的欢心,但时间长河的下一站,我们就能看到,毁灭她的又成全了她。像茨维塔耶娃的诗歌(文学),把她从容易腐朽的肉身群体中单独提取出来,供到更高的艺术神位。
当宽广无边的俄罗斯平原的冰雪融化,茨维塔耶娃已被“苏俄时代的伐木工”砍伐倒地。她短暂的个体生命虽如白日焰火,但闪耀的每一瞬间都是伴随欢呼尖叫的永恒。
沈念,1979年生,湖南岳阳人。曾在《十月》《大家》《天涯》《芙蓉》《山花》《青年文学》等文学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80余万字。出版有《时间里的事物》《鱼乐少年远足记》。曾获湖南省青年文学奖等奖项。
责任编辑/鲁顺民 sxwx2001@163.com
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