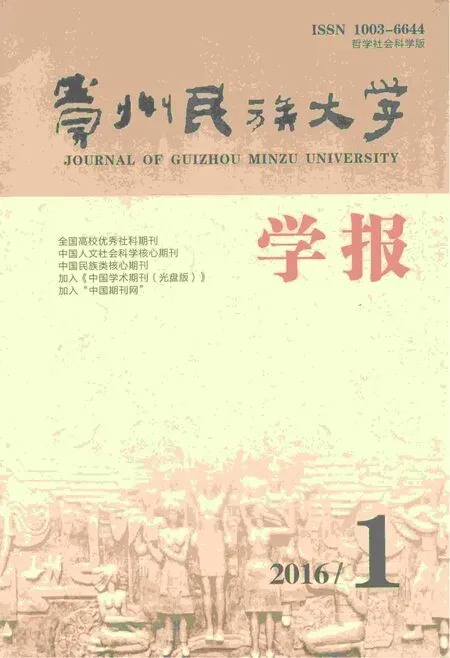达马斯卡证据法理论中三个程序支柱的相互关系*
陆 而 启
达马斯卡证据法理论中三个程序支柱的相互关系*
陆 而 启
达马斯卡在《漂移的证据法》一书中提出“支撑英美证据法大厦的三根支柱”为原型审判法庭、集中式程序和对抗制。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在细致检讨其程序支柱与证据规则的相互衍生和支撑关系之前,甚至首先是检讨这三个支柱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与不同观点的相互比较以及对英美法系诉讼文化背景的考察,这三个支柱之间的确存在着独立性、充分性、关联性和层次性的关系,这三个支柱不独可以解释证据法的过去,还可以因应程序的变化而预测证据法的未来。
达马斯卡;程序支柱;普通法证据;相互关系
作者陆而启,男,汉族,安徽长丰人,博士,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福建 厦门 361005)。
一、引言
经验描述往往比理论论证更富有贴近真相,但是任何经验往往又是在一定理论视角下的主观描述。对在人类证据法发展史上独具一格的英美证据法产生原因的深层背景的追问,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把历史考证置身于理性思辨之中,因而每个人的结论都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一个证据制度历史起源上的因果关系可能证明规则的正当性,但也有支持某个证据规则和惯例的有说服力的理由并没有历史起源上蛛丝马迹。而达马斯卡在其《漂移的证据法》一书中认为有二元的法官-陪审团制度、程序的时间集中制和当事人主导的对抗制这三个因素对英美法系证据法的产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而称之为“支撑英美证据法大厦的三根支柱”。[1]达马斯卡的分析一石激起千层浪,虽然其以文化作为其制度基石,但是分析的内容主要还是集中于一些制度特征层面,还是受到了来自Friedman对证据制度进行价值解释方面的批评。[2]P1921-1967其实,制度本身就是文化的组成的部分,承载着价值观念,但是不是制度围绕着价值转。制度除了有纵向的历史流变之外,还存在横向的比较差异。从我国学者汤维建对达马斯卡该书内容的梳理之中,[3]可以看出三个支柱的相互关系。
二、三个支柱的独立性
有学者认为达马斯卡对英美证据法的三大特征分别开来加以探讨,在分析上存在着问题或缺陷。[4]P1493欧洲大陆以一个专业法官的纠问制度来填补英诺森三世禁止神裁留下的空白,而在英格兰则出现了以12个外行的地主邻居组成的陪审团来行使审判权。有关陪审团的神话,雅典、罗马、英国《大宪章》(1215年约翰王与贵族叛军间签订的停火协议)都曾被视为该制度的创始者。事实上,陪审团审判与它们之间并无联系。其有迹可循的是,几个世纪以来,英国统治者总会召集一群宣誓者,然后再提供资讯给他们,而早在西元879年,在阿尔弗雷德大帝和丹麦国王古斯鲁签署和平协议的时候,就可以看出这十二个宣誓者与审判的关系。该协议里规定,在任一统治者的领土上的杀人犯,如果想要洗刷罪名的话,可以要求由十二名宣誓者进行审判(如果他敢的话)。只要一个简单的想象步骤,就可以把共誓涤罪的仪式转型为陪审团审判。[5]P91-有学者指出,罗马帝国的消亡使得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陪审制度“嫩芽”没能生长起来。普通法的故乡英国成为由“征服者威廉”从欧洲大陆带到不列颠群岛的陪审制度的“苗圃”*参见何家弘:《陪审制度纵横论》,《法学家》1999年第3期。关于现代的陪审制度由法入英的观点,参见Origin of the jury : The Frankish inquest, at Pollock & Maitland,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 Vol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rchive, 1968, pp.140-143;还有更多的学者认为,陪审制度实际上起源于英国。转引自王利明:《我国陪审制度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范·卡内冈教授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逐次批驳了陪审制英格兰本土起源和北欧起源的学说,肯定了布伦纳的观点,即陪审制起源于加洛林王室,后传入诺曼底并由诺曼人引入英格兰。参见[英]卡内冈编著:《英国普通法的诞生》(第二版),李红海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译者序第11页。因此,达马斯卡指出,从历史经验上看,非专业人员的裁决或者陪审团审判与技术性的证据法并没有必然联系。古罗马的平民法官、古代英国非专业治安法官以及专业法官和非专业法官组成的混合式法庭,可以循日常生活和个人事务中采用的习惯方法和策略进行事实认定,而不需要技术性的证据法。这更突出了作者所要论证的,之所以需要证据制度,突出的不是外行人员的素质缺陷而是法官与陪审团的二元分权。
达马斯卡认为,“普通法历史上一些偶然因素导致这种时间集中式法律程序依赖于使用非专业事实裁判者”[6]P6,因为“业余裁判者都有其他事务,倘若审判分为一个个独立的阶段,则很难在开庭时将他们召集起来”[7]P83。倾向于“一审终结”的集中式审判产生后,并不是如影随形于陪审团审判,而可以对证据制度和证据规则的形成和建构起着独立的影响作用。例如,受举证时限制度的限定而排除迟延提交的证据,是集中制审判所产生的直接结果,与实行陪审制不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不过,一种二分地看,一些证据法则和惯例可能只适用于准备粗略(无专业侦查机构)而且时间节制(无常规上诉机制)的诉讼程序,因此,一方面,在当前可能“旷日持久”的典型或者假定诉讼模式之中就不具有意义,甚至当下的陪审团审判更为复杂;另一方面,即使一些保存下为“当庭诉辩式” (day-in-court) 审判所需要的证据法则和惯例在当下也需要重新检讨。
在到底对抗制还是陪审制对英美证据制度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达马斯卡似乎更青睐对抗制的作用。对抗制是指一种程序活动由当事人控制的裁判制度,而裁判者则基本上保持被动。达马斯卡指出:“以这种方式来界定,对抗制显然与法院组织结构的各种形式以及诉讼程序的时间安排无关。当事人之间的争斗既可由专职法官来裁决,也可由业余法官来定夺;当事人可以在当庭诉辩式审判的单一轮回中对抗,也可以在分段审理的若干回合中较量”。[8]P103从历史发展来看,英国陪审制逐步式微,但是其对抗制势头不减,甚至从庭审延展到庭前程序;而大陆法国家的民事诉讼采用对抗制程序模式,而其审判组织是参审制的。可见,对抗制也可以离开陪审制而存在,并且在不同的诉讼阶段上延展或者滑动,正是对抗制而不是陪审制是普通法的核心观念。
三、三个支柱的充分性
在达马斯卡所提出的英美证据法的三个支柱之外,还有人认为,陪审团、宣誓(oath)和普通法的程序对抗制很大程度上是构成证据法的排除特征的三个因素,尤其是与开示规则相联系,成本现在也可以加上去。[9]P2这里提出了宣誓的要素,宣誓昭示了一种证明制度的历史文化背景或者宣誓审判的当代转化。宣誓是证人作证的一个前提,未经宣誓的证据形式——属于要排除的传闻不得进入法庭调查领域。在英美国家出庭证人的宣誓是一种在尊崇宗教信仰基础上的内心规训,具有一定的预防作用,甚至是追究证人伪证责任后果的机制前提,汤维建认为,宣誓仅是从作证人的视角而非从诉讼程序中的主要角色(“诉讼主体”)来看待问题,因此有点边缘和偏离重心。其实,在古罗马和中世纪日耳曼国家盛行的誓审恰恰是原告或被告单方或双方的宣誓为主,尽管在中世纪的日耳曼法中,宣誓神判除了“誓证法”(compurgation)还有有人到庭助誓的“辅助宣誓”(oath-help)制度,当代英美的刑事诉讼制度同样赋予了被告人的选择宣誓作证的权利。另外,兰博约将对律师的司法控制等因素归入其支柱性因素。对律师的司法控制也对证据法的形成起了作用。[10]对律师的司法控制则体现了对抗式诉讼制度的过度律师化及其矫正。还有人将之归因于试图获得公正对判决的可接受性而不论判决正确与否。[11]
笔者以为,首先,不论是宣誓还是对律师的控制,都将法律看作是一种限制权利的手段,更准确地说是出于对为或者代表当事人而伪造证据的一种担心,而不是约束权力的命令。证据法产生的这种归因不管是出于防止证人作伪证还是控制律师这些都使得证据法带上了“治民”的色彩。或许在现代证据法应该转换为“限权”视角通过对事实审理者进行约束来确立其规则的合法性;甚至现代证据法也突破了传统的强调对客观事实进行准确认识的视角而转向了诉讼主体的沟通共识,因而作为诉讼主体的控辩双方可能不仅仅局限于准确的证据提供而突出其畅通的意见表达渠道。其次,基于其他因素所产生的证据规则还是可以被解释为达马斯卡的三种要素之内。传闻证据规则所产生的原因可以归结为陪审团审判和对抗制模式,前者防止不可靠的传闻混淆陪审团的视听,后者要求证人出庭以保障当事人有效地对证人实施交叉询问,宣誓作为一种宗教文化因素并非证据法的主要原因,因为宗教强调的信仰而不是真实。此外,意见证据规则、品格证据规则等其他一些规则也难觅对“宣誓”的依赖成分。对律师进行控制的因素其实也属于对对抗式审判的矫正;作为开示规则所考虑的“成本”因素,也是对集中审理制度的矫正;所谓裁判可接受度的后果或者价值评判往往也通过对抗式的意见宣泄或者表达制度渠道来实现。
可以说,旧证据规则更多的考虑是证据的资格问题,因此侧重于一种外来的规范限制,而现代证据制度则更突出对证明程度的判断和推理问题,侧重于对法官自由裁量的内在限制。当然,对证据法的程序支柱的分析并不是意味着规则就一成不变,恰恰是为了在程序变动之中把握其可能的相应规则转型。
四、三个支柱的关联性
(一)正关联
概而言之,集中审理包含了举证质证集中和认证裁决集中。一方面,在英美法系庭审举证质证活动都落在了双方当事人身上,由此庭审体现了强烈的对抗式特征;另一方面,事实认定活动由陪审团来承担,由于陪审团审判有人多、分布分散、陪审员兼职参审的非职业性和非营利性等特殊性,要求其能持续性并且能最好一次性地进行,因而,陪审团审判延伸出集中审判的要求。陪审团审判与集中制审判几乎是一对孪生兄弟。集中式的诉讼程序的运作样式比较适合陪审团审判,换句话来说,陪审团审判就是通过“集会”一样的方式来决定案件,而开一次会要一次聚齐12个人都不容易,所以,庭审连续不间断的集中审判制度是陪审团审判的一个内在要求。“英美法倾向于集中解决与提交给事实认定者的证据有关的问题”,达马斯卡“则将晦涩的陪审团裁决与英美法的这种倾向联系在一起了。”[12]P61所以,集中制对证据规则的影响,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陪审制对证据规则的影响。在英美司法制度发展历史上陪审制和集中制同步实行。汤维建指出,我国集中审判制度推行,也同样带动了证据制度的变化,如证据失权制度、证据交换制度、当庭质证制度以及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等等,一定意义上都与集中制的推行有内在关联。[13]
当然,从历史上看,陪审制的实行也有助于对抗制诉讼机制的形成。最早的陪审员“就是”证人,而他们“说出的真话”,是唯一需要的证词。随着知情陪审团审判向非知情陪审团制度转变演化,作为发现案件真相的模式,也相应地发生了由“告知真理”向“发现真理”的转变。[14]P12其审判的过程是:“在法庭上,每方当事人自己或者通过其律师首先向陪审团讲述案件争议问题和他们将要提出的证据,以便使法庭得知争议问题的事实真相;然后他们就让其证人出庭作证;每个证人都要先宣誓,然后就其知晓的案件争议问题提供证据”。*William Andrew Noye: Evidence: Its History and Policies. (1991) p20.转引自汤维建《英美证据法学的理性主义传统》,载[美]约翰·W.斯特龙(Hohn W.Strong)主编,[美]肯尼斯·S.布荣(Kenneth S.Broun)等编著:《麦考密克论证据》第5版,汤维建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该文又收录到汤维建著:《民事证据立法的理论立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双方当事人在横向上的信息交换和观点交锋要以法官作为法律的看门人做出指示在纵向上传递给12名负责裁决的陪审员,陪审团审判最后的参与者。然而,英国学者萨达卡特·卡德里(Sadakat Kadri)依然断言,陪审团裁决的最重要特征绝不是理据,而是裁决的存在。[15]P336-337因此,离开陪审制而依然可能成立的对抗制,在具体的运作方式上,尤其在证据规则和证据制度的内容上,会发生一定程度上的变化。
(二)负关联
在陪审团逐渐淡出诉讼舞台以后,法官从法律的守门员转变为独揽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大权的单一主体,而正是为了准确适用法律刺激了法官探求事实真相的冲动。法官积极参与和介入事实认定过程,遏制了当事人双方试图激发陪审团审判感情用事的积极性,导致了对抗制一定程度上的弱化。可见,陪审制的弱化引发了对抗制弱化的连带反应。[16]
传闻规则甚至都可以集中体现陪审制(防止误导陪审员)、集中制(防止诉讼拖延)和对抗制(对质询问)三根支柱的支撑作用。如果不实行陪审团审判,也只能得出结论说该特定的证据规则在有效性上被弱化了,而不能在逻辑上得出结论认为该证据规则就要消失了。如果其他两根支柱依然存在,那么,该证据规则仍然会发挥其作用。[17]P23
因为庭前准备程序对法庭诉讼行为留下的长长的影子,对非专业事实认定者的信赖与以审判为中心不再形影不离,历史上牢不可破的普通法中证据法之基础理论的基体已经解体。不过,因为当事人双方律师材料丰富、漫无目的的审前准备,这种证据资料的增加,在拖垮对方当事人的时候,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和无序性既模糊了事实真相,又激化了庭审的对抗性。自从这种准备模式成为当代对抗制程序的一个方面后,作为普通法证据理论基础的集中制就已独立于其对抗制了。“虽然陪审团审判和时间被紧缩的诉讼已经衰落,但是各种诉讼的当事人仍然求助律师以帮助其解除所涉责任”。[18]P188
五、三个支柱的层次性
追问证据制度产生的理论基础和本质原因,这种追根溯源可以使我们深入了解一些复杂的证据制度的来龙去脉,也可以对表面现象穿针引线。达马斯卡一开始就把这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一种较老观点认为,英美的证据法是“陪审团之子”,以此防止陪审团的认知弱点。其代表人物有赛耶(James Bradley Thayer),[19]P266威格莫尔(John Henry Wigmore)等。另一种更近观点认为,英美的证据法是“对抗制之子”,以保证提供公平机会获得公正或者克服对抗式对真相的扭曲,其代表人物有摩根,[20]/[21]P156南西。[22]/[23]耶鲁大学著名教授约翰·兰博约(John H. Langbein)虽然不认同米特兰和威格莫尔等人的观点,即中世纪的知情陪审团(self-informing juries)作为积极的邻里调查者转换到被动听审者需求证人出庭和形成法庭指示模式而产生证据法,他自己从御座法院首席法官达德利·赖德爵士的审判笔记之中总结认为其中蕴含的前现代证据法关注书证真实性和证人资格,而至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才产生以口头证据为核心的现代证据法为避免陪审团成员无力评估证据而采传闻规则等,也认为现代证据法恰恰是克服陪审团的内在弱点而存在和发展的[24]P1168-1202。汤维建认为,集中制审判相对于陪审制以及对抗制来说,其对证据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并不具有主流意义和决定性作用。那么,在陪审制和对抗制两个主要因素(即两个主要理论)中,究竟是哪一个因素处在更高的层次从而具有根本性?必须要作一个选择性的回答。克劳斯认为两者理论并不排斥,有时被交叉在一起。
在这三大支柱中,对抗制最为根深蒂固。但是,陪审制与对抗制在美国证据制度形成中的作用如何?通说认为是陪审制的推行产生了证据制度。因此,证据制度是陪审制之子。达马斯卡提出一个疑问,12世纪形成了陪审制,到17、18世纪才正式地、大规模地形成的证据制度,而这之间存在12-17世纪之间只有陪审团而无证据规则的“断档”现象。因此,达马斯卡认为,证据规则的产生与实行陪审团审判没有必然联系,而与将审判法庭作出内在职能的划分有必然的联系。证据规则是用来规范二元化法庭关系的调节器。甚至认为,只要审判组织分化为两个部分,哪怕二者都是专业的审判者,也同样需要证据法的调整。[25]P35克服陪审团的认知缺陷仅仅是证据法产生的不太重要的因素,而陪审团集体决策和秘密评议以及审判法庭分为非专业和专业两部分的二元化审判组织制度,才是形成证据法的根本原因。然而,陪审团审判对证据制度的需求,一方面不是以法定证据制度为弥补事实认定者的认知缺陷或者限制事实认定者的过分自由来寻求事实认定正确,而是以事先的程序监督实现陪审团裁判结果的正当化;另一个方面是体现了职业法官以证据规则来控制外行法官实现二者的衡平。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陪审团制度的出现,本来就是对职业法官不予信任的产物;证据规则的出现,则成为对陪审团不予信任的产物。
针对于陪审团对英美法系证据规则支撑作用的程度如何,随着陪审团审判的衰落,传统的、现在仍有法律效力的证据规则是否依旧在发挥作用呢?进而言之,历史上,哪些证据规则因陪审团制度产生,而由陪审团制度起着支撑作用?这些证据规则中哪些因为陪审团制度的抽离而完全失效,哪些可能仅仅是摆设,哪些还可以继续发挥作用?达马斯卡认为陪审团审判与证据规则并无必然关联。对此,达马斯卡给出了几点理由:第一,证据规则的产生与陪审团的产生不同步,并且远远落后于陪审团的产生,恰恰是专业人士发展出了技术性的证据规则。第二,陪审团制度历史早期向美国的传播以及18世纪末在法国的移植,更突出的是将陪审员设想为人民主权的代表以制约专业法官的滥权擅断,可见,陪审团审判并没有成为技术性证据法的发源地,反倒便利了抵制罗马教会证据法的渗透,同时产生了自由心证制度。[26]P34-36由此存在第三个问题,既然陪审团事实裁决方式本身是不需要复杂的证据规则,那么,不正好可以用证据法来矫正陪审团可能具有的认知缺陷吗?然而,达马斯卡将陪审团与证据法的关联推翻之后再踏上一只脚,认为,以技术性证据法来规范陪审团是与陪审团具有认知缺陷的假定相互矛盾的,这就接近了中国成语“对牛弹琴”的意味。然而,笔者以为,达马斯卡还是看到了证据法所具有的约束和控制非专业人士的认知倾向的目的,甚至他也看到了证据排除规则更多的是由职业法官掌握,但是他对这种程序目的和实行机制提供了另一套解说,也就是“二元分化的法庭”,然而,我必须认识到之所以存在二元分化,恰恰是人为理性和自然理性两种认识论互补的结果,并且将这两种思维模式分别极化为法官和陪审团两种组织元素,由此可见,英美证据法的形成还是与陪审制脱不了干系。
对于对抗制和陪审制对英美证据制度的形塑作用那个更甚?美国学者兰博约提出了刑事诉讼的律师化而导致对抗式诉讼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命题,同样,就证据制度的发展而言,他认为:“自18世纪中期证据法的形成多少与刑事审判中的律师化机制登场存在联系,因此,我的观点是,证据法真正的历史上的活动由陪审团控制并不多于由律师控制”。[27]P306正是因为律师控制的口头审判方式与证人分类、排除传闻、举证责任、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沉默权、不被迫自证其罪等证据法或者程序法原则密切相关。这个观点也得到了达马斯卡的赞同。因此,对抗制与英美的证据法具有最为紧密的联系,对抗制一旦崩溃,英美的证据法也就完全失去了存在的空间。
六、结论
综上可见,对证据法程序支柱的考察既意图追根溯源地解释过去,又意图有根有据地预测未来。通过对英美法系证据法的程序支柱相互关系的考察,大体可见,英美法系证据法主要是在陪审团审判和对抗式审判之中有其用武之地,这两种程序上的特别之处决定了证据法的特别之处,由此,可能会影响到所谓的英美证据法排除规则的普适性,将之移植到诉讼制度文化与之不同的国家可能会造成水土不服。对证据法的支柱的不同归因,如所谓的陪审团、宣誓、对抗式、集中式、成本、裁决可接受性等整体而言可能对证据法产生这样的影响,一部分是关注证人资格、证据真假的注重证据客观性防止法庭受到伪证和捏造证据影响的传统证据法,另一部分关注诉讼主体在庭审之中以口头证据为基础的证据提出、交叉询问以及意见表达的现代证据法。证据法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主要有这样一些体现:从限制权利注重后果责任转向保障权利注重程序参与,从信任知情的事实裁决者和事实的主动调查的情境裁量转向怀疑法官以及怀疑陪审团而设置一系列预防法官受偏见信息干扰的程序机制、从自然理性和人为理性的事实认知方式相互独立分离转向以职业法官依排除规则审查证据资格和非职业法官自由裁量证据证明力等权力分工合作。当下,随着诉讼模式的多元化以及诉讼程序的科学化,证据法的程序支柱自身也不断变化,当然,受程序规则影响的证据法也随之变革。但是,总体而言,不论何种证据法,不论何种事实认定模式,都必然逐步体现出限制公权力滥用以及保障人权的制度设置,尽管真相不是可有可无的。结合当下的中国实际而言,有必要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当下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取向必然对证据法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冲击作用,突出的变化是意图让卷宗笔录确认程序逐步转变为以交叉询问为主体的口头审理程序,而这种“从分段式审理到集中式审理”的提倡已经与传统的集中式审理在案件事实认定思维模式上有着巨大的差别,更加突出法律职业精英对程序技术的操控,因此,一方面要法律职业群体自身的素质能够适应庭审中心的要求,另一方面为防止专业垄断所引发的技术支配和权力滥用反而要通过重构法庭组织而引入普通民众的自然化认识。
第二,与之相同步的是刑事速裁程序的试点和推广,这以被告人认罪为前提的程序多元化探索完全抽离了诉讼的对抗精神,由此证据法也从传统的注重对证据资格的审查转为法院对被告人认诺的明知性和明智性的审查,诉讼主体多方合意下裁判的可接受性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之中大有超越“对抗求证”的传统意味。当然,速裁案件更大的特点是真相先于裁决而不是通过裁决来决定真相,因此,“集中审理”更突出体现为一种当庭裁判,并且控诉方和审判方也有一种集约化组织方式行使职权,在所谓的“简程序而不减权利”的口号下,律师不是以辩护人而是以提供法律咨询意见的值班律师来参与程序,并且律师的参与在庭审程序之外而不是参与到庭审程序之中。
[1][6][7][8][12][18][25][26][美]达马斯卡.漂移的证据法[M].李学军,刘晓丹,姚永吉,刘为军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2]Richard D. Friedman,. Anchors and Flotsam: Is Evidence Law "Adrift"? Evidence Law Adrift by Mirjan R. Damaška[J]. The Yale Law Journal, Vol. 107, 1998, (6).
[3]汤维建.达马斯卡证据法思想初探——读达马斯卡《漂移的证据法》[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5,(3).
[4]Park.An outsiders's view of Common Law Evidence[J].Vol.96 Mich. L. Rev.1998,(6).
[5][15][英]萨达卡特·卡德里.审判的历史:从苏格拉底到辛普森[M].台北:商周出版,2007.
[9]Colin Tapper. Cross & Tapper on Evidence (12 edition)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0][27]Langbein. The Criminal Trial before the Lawyers[J]. Vol.45, U.Chi.L.Rev. 1978, (2).
[11]Charles Nesson. The Evidence or the Event? On Judicial Proof and the Acceptability of Verdicts[J]. Vol.98, HARV. L. REV,1985,(7).
[13][16][17]汤维建.达马斯卡证据法思想初探——读达马斯卡《漂移的证据法》[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5,(3).
[14]何家弘.西方证据法的历史沿革 (代序),载何家弘,张卫平主编.外国证据法选译[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
[19]James Bradley Thayer. A Preliminary Treatise on Evidence at the Common Law[M].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Elibron Classics edition, 1898.
[20]Edmund M. Morgan. The Jury and the Exclusionary Rules of Evidence[J]. Vol. 4 U. CHI. L. REV,1937,(2).
[21]张卫平主编.外国民事证据制度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22]Dale A. Nance. The Best Evidence Principle[J]. Vol. 73 IOWA L. REV,1988.
[23]吴洪淇.英美证据法的程序性解构—以陪审团和对抗制为主线[J].证据科学,2012,(5).
[24]John H. Langbein, Historical Foundations of the Law of Evidence:A view from the Ryder sources[J].Vol. 96, Columbia Law Review, 1996,(5).
责任编辑:杨正万
Damaška’sEvidenceLawAdrift:MutualRelationshipbetweenThreeProceduralPillars
LU Erqi
In the book “Evidence Law Adrift”, Damaška proposes “three pillars for British and American evidence law mansion”, namely trial court, concentrated procedures and opposition system. It is argued that we should examine their mutual impact and suppor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ir independence, fullness, relevance and layers, and to further know the change of responding procedures and the future of evidence law.
Damaška; procedural pillar; common law evidence; mutual relationship
D915.3
A
1003-6644(2016)01-0176-09
* 2014年度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刑事诉讼的律师化研究”[项目编号:2014B235];福建省法学会2015年度法学研究重点课题“特洛伊木马:品格证据的价值检视与制度构建”[编号:FLS(2015)A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