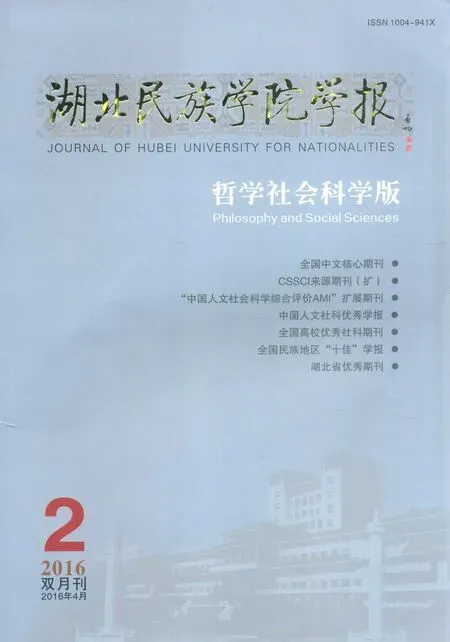种族创伤与性别创伤
——《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历史叙事
王霞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种族创伤与性别创伤
——《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历史叙事
王霞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创伤性的事件或者经验能够以文学的方式进行再现。在种族/性别创伤理论中,弗朗兹·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是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斯托夫人对美国奴隶制下的黑人所承受的种族创伤与性别创伤进行了文学建构,生动地再现了历史真实。
《汤姆叔叔的小屋》;种族创伤;性别创伤;《黑皮肤、白面具》;历史真实
一、《汤姆叔叔的小屋》与创伤理论
《汤姆叔叔的小屋》是美国作家哈丽特·伊丽莎白·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1811-1896)的代表作,1852年首次以单行本出版,并获得巨大的成功,该书深刻地抨击了美国的奴隶制,曾影响了美国的历史,斯托夫人被林肯总统称为是“写了一本引起一场伟大战争的书的小妇人”[1]。国内学界从不同的视角对《汤姆叔叔的小屋》进行了研究,比如,程巍研究了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与美国的南北方问题,认为这本书使南北战争成为解放黑奴的圣战,但在北方胜利后,小说就失去了其原本的价值[2]。郑丽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对《汤姆叔叔的小屋》进行分析,认为这本书表现了斯托夫人对黑人奴隶的同情和奴隶制的愤慨,但她无意识中对黑人形象的他者化显示了潜在的白人优越感和殖民意识[3]。肖淑芬运用互文性理论,将《汤姆叔叔的小屋》与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1931-)的《宠儿》进行比较研究,认为这两部作品存在明显的互文关系,主要表现在故事的起步、核心、关键、线索等四个层面上[4]。崔娃从伦理学批评的角度对《汤姆叔叔的小屋》中体现的家庭伦理进行解读,认为作品表现夫妻伦理、亲子伦理、兄弟伦理、主仆伦理等四种伦理关系和伦理秩序[5]。上述研究丰富了我们对《汤姆叔叔的小屋》的认识和理解。然而,稍感遗憾的是,很少有评论者从创伤理论的视角对这一作品进行阐释。因此,有必要对这一作品进行重读,探究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如何对种族创伤与性别创伤进行历史叙事。
创伤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原意指“伤”,既指外部力量造成的身体创伤,也指心理创伤。创伤作为医学、病理学研究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歇斯底里症研究,20世纪90年代逐渐发展成为涉及历史、哲学、心理学、文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内容的跨学科研究。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理论为创伤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创伤研究也由心理研究层面转向关注创伤的文化和伦理内涵。林庆新认为,创伤是指“由灾难性事件导致的、在心理发展过程中造成持续和深远影响甚至可能导致精神失常的心理伤害”[6]。陶家俊对创伤的分类、发展阶段等进行了阐述,认为创伤理论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其发展经历了弗洛伊德心理创伤理论、后弗洛伊德心理创伤理论、种族/性别创伤理论和创伤文化理论四个阶段[7]。安妮·怀特海德在《创伤小说》一书中指出:“‘创伤小说’一词描述了一种自相矛盾或冲突的事物:如果创伤包含着一种令人不知所措并抗拒语言或表达的事件或经验的话,那么它怎么能够在小说中被叙述?”[8]也就是说,创伤性的事件或者经验如何通过文学的方式进行表达,就《汤姆叔叔的小屋》来说,斯托夫人如何对种族创伤与性别创伤进行话语建构,同时,这种创伤性的叙事与历史真实性之间是何种关系?
二、种族创伤
在种族/性别创伤理论中,弗朗兹·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是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在《黑皮肤、白面具》一书中,法农指出,白人确立了一种与黑人的对立关系,在这种二元对立中,白人具有从身体到精神的优越感,而黑人则感觉到自卑,因而,当一个黑人与另一个黑人在一起时,其表现将不同于他与一个白人在一起,原因就在于欧洲白人在印证自身文明的同时也在宣告非洲黑人的落后与野蛮。为了控制这种自卑感,黑人会通过穿欧洲服装、模仿欧洲人的外表、用欧洲的语言或表达方法等来达到一种与欧洲人及其生活方式相近似的平等感觉。“一切被殖民的民族——即一切由于地方文化的独创性进入坟墓而内部产生自卑感的民族——都面对开化民族的语言,即面对宗主国的文化。被殖民者尤其因为把宗主国的文化价值变为自己的而更要逃离他的穷乡僻壤了。他越是抛弃自己的黑肤色、自己的穷乡僻壤,便越是白人。”[9]9法农认为,语言与身份认同有着密切关系,起到文化工具的作用,讲述一种语言就意味着自觉地接受一个世界和一种文化,对于那些想当白人的黑人来说,只有接受并学习白种人的语言才能表现得更像白人,并以成为白人的复制品而骄傲。
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斯托夫人刻画了一些滑稽可笑的黑人形象,他们想通过模仿白人的言谈举止来接近白人世界,比如圣克莱尔的黑人奴仆阿道尔夫,长期以来费尽心思地模仿主人圣克莱尔的风度和才艺,偷穿偷用圣克莱尔的衣服、麻纱手帕,大量地使用香水,想以此改变自己的卑下地位,“最后弄得他误认为自己真的成了老爷”[10]171。阿道尔夫除了擅自使用圣克莱尔的东西之外,还经常使用他的姓氏和地址,“他在新奥尔良黑人圈内活动时,使用的称谓就是‘圣克莱尔先生’”[10]210。斯托夫人还描述了具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统的女仆为了舞会而不停地摆弄着一对闪闪发亮的珊瑚耳坠,目的是为了吸引注意力,获得认同。对此,另一个女仆黛娜讽刺地说:“我才不稀罕你们这些浅皮肤的舞会呢,招摇作态,假装自己是白人。其实你们跟我一样都是黑鬼。”[10]211在此,斯托夫人多次强调她的四分之一的黑人血统,也就是说,她是有别于纯黑人血统的女仆。而混血儿之所以如此爱好虚伪、炫耀自己,原因就在于她们在肤色上与白人是接近的,而且有可能从奴隶的行列上升到主人的行列。此外,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许多黑人奴隶都自愿地接受基督教。第一代混血青年乔治曾愤怒地指责基督教国家的法律庇护白人对黑人的妻子进行拍卖,将黑人的儿女送到奴隶贩子手中,残暴地鞭打年迈的黑人老母亲,但是,他在听了《圣经·旧约》的《诗篇》后,所有的愤怒、疲惫、焦虑、抗争都化成了温和与顺从。基督教作为西方文明的精神支柱,对西方人的生活态度、思维方式等起着重要的作用和影响。黑人奴隶对基督教的接受,其实是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并以此区别于那些没有接受基督教信仰的黑人,显示出自身对于西方文化的靠拢,更接近于文明、高尚、有修养之人。“因为黑人属于一个‘低等’的种族,他试图与高等种族相似。”[9]170
黑人之所以要学习白人的语言,模仿他们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接受他们的宗教信仰,认同他们的文化,是因为对自身与自身文化的自卑。问题在于,是什么造成了这种自卑感?法农指出,黑人土著的自卑感与欧洲人的优越感有关,正是种族主义者制造出了这种自卑感。白人对黑人的歧视,使得黑人成为白人世界的寄生物,失去自身存在的价值与独创性,因而黑人必须尽可能地遵守白人世界的规则与秩序,并为自己不是个白人而痛苦,“于是我十分简单地变成白人,就是说我迫使白人承认我的人性”[9]74。也就是说,如果一个黑人想完全变成白人,那是由于他生活的社会环境造成的,正是自以为是优等人种的白人社会造就了所谓劣等人种的黑人的自卑情结。“在当了白人的奴隶之后,他自我奴隶制化。黑人从一切词义上来说,是白人文明的牺牲品。”[9]150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白人是文明的、高贵的、美好的、善意的、公平的、正直的。在白人看来,黑人面貌丑陋、性格低劣、野蛮愚昧、强壮、残暴,是牲口、邪恶的坏人。黑人之所以代表邪恶,是因为他的肤色黑。与之相对应,白色则象征着公正、美德、贞洁。白与黑这两种颜色,分别对应着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等二元对立的现象。“刽子手是黑肤色人,撒旦的皮肤是黑色的,人们谈到愚昧黑暗,如果人脏了那他就是黑色的,——这一点适用于身体肮脏或精神肮脏。如果有人费神把大量使黑人变成罪孽的表达法集中起来,人们会大吃一惊的。在欧洲,黑人或具体地或象征地代表性格不好的一面。”[9]147正因为如此,白人敌视、贬低黑人。
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黑利作为一个黑奴贩子,十分冷酷无情,他认为黑人不像白人那样有教养,因而可以将黑人母亲的孩子卖掉,将黑人夫妻分离。圣克莱尔的妻子玛丽认为,黑人是不可规劝与教化的,是低等人种,跟猪差不多,而且永远如此,无法改变与教育。圣克莱尔曾指出奴隶制的弊端,在白人看来,黑人无知而软弱,白人则聪明又强壮;所有的脏活、累活都由黑人去做;白人不喜欢晒太阳,黑人就要呆在太阳底下,黑人挣钱,白人花钱;黑人要躺在泥水坑里,免得白人走路时把鞋弄湿了,总之,黑人完全没有自由意志,要按照白人的意志去做事,而当黑人被白人剥削、压榨完,有没有机会进天堂,也要看白人是否愿意。“我遇到的每一个残暴、可憎、卑鄙、粗俗的家伙,只要能骗到、偷到或赌博赢到钱,买到多少男人、女人和儿童,法律就允许他们成为统治这些人的暴君。”[10]219奴隶主雷格里非常残忍、冷酷,他强迫黑奴进行超负荷的繁重劳动,还经常折磨黑奴,把黑奴当成是动物、野兽对待,为了防止黑奴逃跑,他养了几条受过专门训练的恶狗,并将汤姆打得遍体鳞伤终至死去。正是因为白人社会如此认识和界定黑人,黑人被当成货物被拍卖,被当成牲口一样驱使、鞭打。
法农指出,白人之所以要确立白与黑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目的在于通过对黑人这个他者的描述,来彰显自身的优越。正是黑人的黑映照出白人的白,正是黑人的软弱映照出白人的勇敢,正是黑人的坏与丑映照出白人的好与美。“问题总是在于主体而毫不顾及客体。……作为个人和自由的客体是被否认的。客体是个工具。他应该能使我实现我主观的安全。我冒充自己完整无缺(想要完满)且不承认任何分裂。另一人进入舞台来布置舞台。主角则是我。”[9]166法国学者达尼埃尔·亨利·巴柔曾指出,人们在描述和界定他者的时候,他者的形象总是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对他者的否定,重要的不是他者的形象本身,而是通过他者的形象来反衬和映照出自我的形象,在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关系中,自我是主体,他者只是一个用来言说和映照自己优越性的工具,作为主体的自我通过对作为客体的他者的否定而肯定了自己,“我想言说他者(最常见的是由于专断和复杂的原因),但在言说他者时,我却否认了他,而言说了自我”[11]。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托普西与伊娃这两个孩子分别代表着社会的两极,白人是高贵的、文明的、支配他人的种族,黑人则是缺乏教养的、野蛮的、受压迫的种族。斯托夫人描写了托普西的伶俐、顽皮,但是她粗野、说谎、偷东西,挨打挨惯了,不打就不干活,而且总是炫耀自己的恶劣行为,自认为是个坏人,“我想,就是他们把我的头发一绺一绺都揪光了也没用——我太坏了!天哪!我不过是个黑鬼,没有用的!”[10]277托普西之所以总在强调自己的肤色,自暴自弃,原因就在于内心根深蒂固的自卑感,她经常被白人主人打骂,从来就没有父母的疼爱,生活在一种痛苦的生活处境中,而她又无力改变这种处境,因为她知道,在白人的社会,黑人怎么努力都不会得到白人的认可,黑人是没有任何话语权的。要改变这种处境,惟一的办法就是变白,成为一个白人。当伊娃劝说托普西努力学好的时候,托普西说:“再好也没用,我只不过是个黑鬼。要是我的皮能剥掉,变成白人,那我就会争取。”[10]278
与托普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圣克莱尔的女儿伊娃。在斯托夫人的笔下,托普西和伊娃不论是外表还是心灵性格都形成了截然的对立,托普西是黑人里最黑的孩子,脸上的表情是精明和狡黠的混合,穿着又脏又破的衣服,偷丝带、手套,把房间弄得乱七八糟,把床单、床罩挥舞得满屋都是,内心充满了自卑;而伊娃的容貌是超凡脱俗的,眉清目秀,天真清纯,金黄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像一个可爱的小天使,是真、善、美的化身,她能够以平等和怜悯之心去对待黑奴,温和而高尚。“两个孩子站在那儿,分别代表着社会的两极。一个孩子出身高贵,白皮肤,金头发,眼睛深陷,额头高雅,富有灵气;她身边的这一个则是黑皮肤,狡黠、形容猥琐,然而却很机敏。她们代表各自的种族。一个是撒克逊种族,世世代代生活在文明、支配他人、享受教育和优越的物质、精神生活的环境里;另一个是非洲种族,世世代代生活在受压迫、卑顺、愚昧、劳苦和罪恶的环境之中。”[10]241斯托夫人以托普西和伊娃这两个孩子为代表,描述了黑人与白人的巨大差异,而造成黑人的自卑、自弃的一个重要原因却是白人,是白人的种族主义造成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白人的种族歧视、奴隶贸易给黑人造成了严重的创伤。法农通过搜集黑人的古代历史资料指出15世纪就存在黑人文明,证明黑人不是原始人,更不是牲口,而是一个有着历史与文明的与白人一样平等的种族,并且提出:“我想要是个人,仅仅想要是个人。”[9]85-86钦努阿·阿契贝也指出,欧洲应该去除欧洲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思想,去除对非洲黑人的偏见、歧视与歪曲,不再将其当作原始之地,将黑人作为“人”来看待。[12]
三、性别创伤
在当时美国的奴隶制社会,如果说黑人没有话语权,承受着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身体与精神创伤,那么,黑人女性更是不能言说与表达自己。一方面,黑人女性受到白人的种族压迫,另一方面,她们也受到男性的性别压迫,因而,黑人女性同时承受着种族创伤与性别创伤。首先,黑人女性的孩子经常被无情地卖掉,母子分离,她们常常充当生育机器,生孩子满足市场需要。黑人女性在奴隶贸易中所受的创伤是不可愈合的,她们的孩子经常会强行夺走并被拍卖,有些女性在失去孩子后痛苦地哭叫,有些被关起来并疯了或死了。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汤姆·洛克这样的奴隶贩子对待黑人十分残忍,当他贩卖的黑人妇女哭闹的时候,他会猛击她们的头、冷酷地虐待她们。而自以为比汤姆·洛克仁慈的黑利,则会在卖黑人小孩之前先把母亲支开。在奴隶贩子看来,黑人女性并不具备和白人女性一样的情感,他们无法理解失去孩子的黑人母亲内心的痛苦,甚至觉得她们的哭泣是可笑的。黑利买过一个黑人女性,她有一个很可爱的孩子,可是那孩子看不见,于是黑利就用孩子换了一小桶威士忌。当买主准备把孩子带走时,母亲和孩子一起跳河自杀了。这样深受奴隶贸易毒害的女性不计其数,为此,斯托夫人曾评论道,奴隶贩子已经对失去孩子的黑人女性眼中彻底的绝望习以为常,“所以奴隶贩子把他看见的那张黑面孔上表现出的巨大的痛苦、那攥紧的双手和急促的呼吸仅仅当做这一行当难以避免的事情,他只是考虑她是否会尖声哭叫,在船上引起纷乱,因为就像我们这奇特制度的其他支持者一样,他是绝对不喜欢骚动和混乱的。”[10]126
一个叫蒲露的黑人女仆,经常偷主人的钱喝得醉醺醺的,如果主人发现了,她就会被打得半死。尽管如此,她还是要喝酒,没有酒她就没法活,生不如死,喝酒可以忘掉痛苦。那么,蒲露为什么如此痛苦,是什么造成了她的痛苦?蒲露的老家在肯塔基,她被一个男人养着,让她生孩子供应市场,孩子一长大就会马上被卖掉。后来,蒲露被卖给了她现在的主人,又生了一个孩子,非常漂亮可爱,可是她去服侍生病的女主人时被传染,也生病了,没有奶水,女主人不愿意买牛奶喂孩子,孩子瘦得皮包骨头,总是哭。而女主人不仅嫌孩子烦,还不让蒲露带孩子睡,让孩子自己在一个小阁楼上,最后活活地哭死了。“后来我就喝起了酒,这样就听不见孩子的哭声了!真的,我就要喝!假如我真的要下地狱,我也要喝!老爷说我死后要下地狱,我对他说我现在已经在地狱里了!”[10]212善良的汤姆曾经劝蒲露戒酒,向她宣传上帝之爱。蒲露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看起来像进天堂的人吗?天堂不是白人去的地方吗?你想他们会让我待在那儿吗?我宁肯下地狱,和老爷太太离远点。”[10]213最后蒲露喝醉后被打,关进地窖里死去。蒲露的命运是无数黑人女性命运的写照,充当生育机器,孩子被卖掉或者死去,她们无力反抗也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在人世间如此的苦难与不可愈合的创伤面前,基督教的教义显得苍白,事实上,基督教国家的法律支持的正是罪恶的奴隶贸易,许多基督徒对奴隶贸易的残酷抱着冷漠的态度,对让人惊骇的社会的不公正行为视而不见,他们根本不愿意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去为整个黑奴阶层做些什么。乔治曾悲愤地指出,《圣经》是为白人说话的,白人健康、富有、快乐,拥有话语权,指望着进天国,而同样信仰上帝的黑人基督徒却被白人踩在脚下,“他们把他们卖来卖去,拿他们的生命、呻吟和眼泪做交易,而上帝却允许他们这样做”[10]187。基督教号召人道、爱心、慈善,宣扬人人平等,然而,白种人与黑种人的区分与不平等却是事实,正如法农所指出的:“在欧洲,即在所有的文明和开化的国家里,黑人象征罪孽。黑人代表道德标准低下的原型。”[9]148“仁慈善良的上帝不可能是黑皮肤的,他是位双颊红润的白人。”[9]36
其次,在白人的眼中,黑人女性是不值得尊重、不值得爱的。白人男人是主人,黑人女性是奴隶,前者处于支配地位,后者处于被支配地位。两者之间不存在平等关系。在奴隶贸易中,谁花钱买了黑人女性,不管他如何卑鄙如何邪恶冷酷,谁就可以占有她。苏珊和爱默琳母女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苏珊眼睁睁地看着美丽的女儿爱默琳被卑鄙龌龊的雷格里买走而无能为力。凯茜的命运更为悲惨,她被多次卖掉,沦为雷格里的性奴。根据凯茜对汤姆的讲述,她与其他黑人女性不同,从小在无忧无虑的富贵环境中长大,还在修道院学习音乐、法语和刺绣等科目,外表美丽,举止高雅。然而,她父亲突然去世,且资不抵债。凯茜的母亲是奴隶,所以债主们也将凯茜列入财产清单,被一个声称爱她的年轻人以两千块钱的价格买下,成为他的财产。凯茜住进漂亮的大房子,家里有仆人、马车、家具、衣服等等,她的生活很宽裕,并爱上了这个年轻人。后来凯茜救过他的命,还为他生了两个漂亮可爱的孩子,但他仍没有与凯茜结婚,并被表兄引诱出去玩乐、赌博、移情别恋,甚至卖掉凯茜和两个孩子来还赌债。之后,两个孩子被再次卖掉,作为母亲的凯茜非常痛苦,“我觉得似乎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弃我而去了。我又骂又叫,大声诅咒,诅咒上帝,诅咒人”[10]362。正是因为凯茜深深地体会到孩子被卖掉、被鞭打时难以言说的创伤,所以当她被卖给一个船长并生下一个男孩时,她决定不让孩子活下去长大成人,“我把两星期大的小家伙抱在怀里,一边吻他一边哭,然后给他喂了鸦片酊,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他就这样睡着死去了。我为他哭得多么伤心啊!……可是这却是少数几件现在仍然让我感到高兴的事情之一。直到今天,我仍然不感到后悔,他至少已经脱离苦海了。除了死我还能给他什么更好的东西呢?”[10]363船长死后,凯茜又被卖掉,经过多次转手,最后被丑恶、卑鄙的雷格里买下,成为他的性奴。经历了生活沉重的苦难,凯茜的内心千疮百孔,当汤姆劝说她信仰上帝时,她对上帝的存在表示怀疑,因为对于生活在底层的黑人奴隶来说,到处都是罪孽和漫无止境的绝望,根本不存在救赎的希望。事实上,凯茜是当时无数黑人女性悲惨境遇的代表,她们的孩子被卖掉、被鞭打、被折磨,她们自己也被多次卖掉,成为男人的性奴,她们不可能得到与男人平等的尊重与爱。法农指出,黑人、混血儿等有色种族的女性,从来也得不到白人的尊重,即使这个白人爱她,“似乎对于她来说白人和黑人代表世界的两极,永远在斗争的两极:真正的善恶二元论的世界观”,“我是白人,就是说我具有美色和美德,黑人从不具备这两样东西”。[9]31
由上可见,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黑人女性的创伤无处不在,构成了小说中浓郁的创伤叙事氛围。黑人女性承受的既有种族创伤,又有性别创伤,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性别主义歧视并非奴隶制的产物,它是父权社会普遍存在的毒瘤。即使是在美国社会中遭受残酷种族压迫的黑人男性,也同样具有男权至上的思想。”[13]
斯托夫人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对黑人所承受的种族创伤与性别创伤进行了历史再现。1850年,美国颁布了《逃奴法案》,允许奴隶主到自由州去追回他们的逃奴。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斯托夫人以文学的方式生动地阐释了历史,形成了文学与历史的互动与对话。她曾指出,这部小说中的具体细节大部分确有其事,许多人物形象都来源于现实生活,“书中介绍的人物的原型几乎都是作者和她的亲友见过的,这些人物说的话有许多就是作者亲耳听见或别人告诉她的一字不差的原话”[10]440。在这个意义上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中所描写的种族创伤与性别创伤是对当时历史现状的真实再现。
[1]林玉鹏.译者序[M]//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林玉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1.
[2]程巍.《汤姆叔叔的小屋》与南北方问题[J].外国文学,2004 (1):72-84.
[3]郑丽.从对黑人无意识的他者化看斯托夫人潜在的殖民意识——《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后殖民主义解读[J].外国语言文学,2009(1):64-70.
[4]肖淑芬.《宠儿》与《汤姆大伯的小屋》的互文性及其启示[J].武汉大学学报,2011(2):99-103.
[5]崔娃.《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家庭伦理解读[J].社会科学战线,2012(3):238-240.
[6]林庆新.创伤叙事与“不及物写作”[J].国外文学,2008(4):23 -31.
[7]陶家俊.创伤[J].外国文学,2011(4):117-125.
[8]安妮·怀特海德.创伤小说[M].李敏,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3.
[9]弗朗兹·法农.黑皮肤、白面具[M].万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10]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M].林玉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11]达尼埃尔·亨利·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M]//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23-124.
[12]钦努阿·阿契贝.非洲形象之一种:康拉德的《黑暗的心》中的种族主义[M]//约瑟夫·康拉德.黑暗的心·吉姆爷.黄雨石,熊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461.
[13]刘戈.《汤姆叔叔的小屋》与美国文学中的性别歧视[J].郑州大学学报,2008(3):89-93.
责任编辑:毕曼
I106.4
A
1004-941(2016)02-0112-05
2015-09-20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XKJS201508)。
王霞(1981-),女,江苏赣榆人,文学博士,硕导,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文学与文艺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