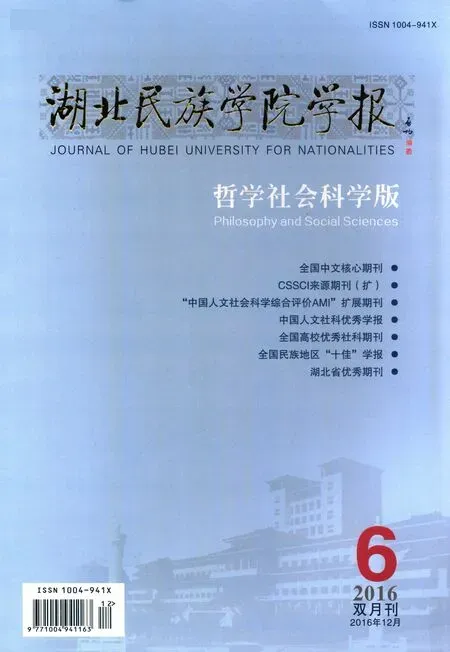空间的形而下境构
——以大卫·哈维的空间伦理思想为进路
吴红涛
(上饶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江西 上饶 334001)
空间的形而下境构
——以大卫·哈维的空间伦理思想为进路
吴红涛
(上饶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江西 上饶 334001)
传统空间哲学将“空间”作为一种形而上对象来考察,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空间作为某种“空”之先验场域的特点,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把空间认知推向了某种抽象乃至虚空的境地,使得空间缺乏本有的人情伦理温度。哈维认为在哲学思辨之外,还应从现实语境出发,对空间进行形而下境构,积极将其融贯到人类社会和现实生活中,以之来反观人类的现实世界。哈维对资本空间、城市空间和自然空间等空间形态的形而下探讨,深刻映射了人类现代社会的伦理症候,空间被哈维上升为一种伦理表征。在各类空间问题日益严峻的当下,哈维的空间伦理思想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空间;大卫·哈维;空间伦理;形而上学
“空间”是一个复杂且充满争议的问题式,哲学史上有诸多围绕其而展开的思想论争。众所周知,“在传统哲学里,空间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1]29,而在以“形而上”为主导的传统哲学范式中,“空间”似乎一直被归结为某种抽象和先验概念,对之进行的阐释也大都因为过于推崇思辨与玄想而显得模糊化,其与人类生活世界的空间认识之关系更是相对有限。因而海德格尔在反思过往的空间哲学史时,坚定地认为“空间存在的阐释工作直到今天还始终处于窘境”,这种“窘境”的缘由并非出于空间本身内容的匮乏,而在于“缺乏通过存在论概念进行的阐释”[2]。换句话说,海德格尔认为,以往空间哲学未能在“空间”与人之“存在”的问题之间架构起一条有效途径,这就使得“空间”被抛入了一个“无在”的境地。如何化解这个症结?海德格尔给出了一个方向:将空间从“粗糙”和“狭隘”的概念论述中解放出来,转而“着眼于现象本身以及种种现象上的空间性”[1]131。海德格尔的意思很明确,空间认识论必须营构在各种各样实存的“现象”之上,对于“人”来说,空间更是“现实世界最为基本的构成元素”[3]。遗憾的是,海德格尔虽认识到了问题所在,但其并未尝试解决这些问题。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对于时间的兴趣依然要大于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代美国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空间思想显得尤其富含价值。在哈维的诸多空间论著中,其不仅反思了传统空间哲学的形而上思辨之弊病,同时也很好地回应了海德格尔提出的构思,对空间问题予以系统深入的形而下境构,将“空间”与现代世界中的社会、文化、道德、环境等“现象”进行深度融合,从而营构起一种更为符合现实情境与人类状况的空间伦理学。本文将尝试讨论哈维对空间所进行的形而下境构,分析其空间伦理思想的缘由、语境与内容逻辑分层,以及其所蕴含的现实意义。
一、空间哲学与空间研究的形而上体征
尽管哲学史上留有不少专门针对空间的论述,但稍显尴尬的是,“空间”究竟为何的解释却一直未有定论。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无法在学理上为“空间”做出一个明确的概念判断,造成这种境况的缘由包括多个方面,但最为关键的无疑还是源自“空间”概念自身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英国学者弗兰克斯·彭茨等人主编的《空间》一书形象地印证了这个问题,该书讨论了“内空间”、“语言空间”、“建筑空间”等八种完全不同的空间形态,最终得出结论认为:“什么是空间?没有哪个定义能做到一言以蔽之,因为空间是复杂多元的。从以往的资料可以看到,有多少种不同的尺度、方法与文化,就会有多少种空间以及在空间中展开的人类活动。”[4]国内学者关洪也提出:“空间这个名词,有多种不同的意义。它可以指一个物体之中或者多个物体之间的空缺、罅隙或者间隔;可以指自然物或者人造物内外的空旷所在;也可以指我们生活着的地球表面之上的空域。”[5]换句话说,“空间”具有诸多不同内涵,可以在多个意义上被讨论与使用,其是一个永远处于流动与建构中的概念。无疑,此种对于空间多义性的判断,为空间概念赋予了活力与开放性,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空间概念的模糊性。与此同时,在现实语境中,空间也倾向于被视为一种存在但不可见、成立但无形式的元素,其无法引起人们实在的关注与兴趣,正如跨文化传播学之父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说过的那样:“我们对空间的态度有点象对待性问题的态度,它尽管存在,但我们却不谈论它。如果确实谈论它,那肯定不希望专门或正经地谈论它。”
正是由于空间概念这种难以把握的特质,使得其在哲学意义上内化了某种抽象与形而上的意味。列斐伏尔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甚至认为“空间”在哲学上是一直被贬抑和弱化的,在其为《空间的生产》一书所做的序言中如是谈到,在哲学上,“空间遭受了极大的蔑视,它被视为不过是诸多范畴之一罢了(如康德所论,它是一种先验范畴,一种组织感性现象的方式)。有时候,空间又被看做是充满着形形色色的幻觉和谬误:偏离轨道的欲望与行为,‘自我’的堂奥,进而也是迈向一种异化的和倦怠的、正在分裂或已经分裂的(透过语言和类似语言的——柏格森)心理学意义上的生活。”[6]显然,列斐伏尔不满以往哲学对待空间的方式,认为其过于推崇先验形式的形而上思维将空间演绎成了某种“幻觉”和“谬误”,而在这种“幻觉”和“谬误”中,空间的其它重要属性被忽略了。正如国内学者冯雷所指出的:“哲学非但没有对空间进行恰当的重建,反而贬低空间,使空间一度淡出论域。”[1]33哈维认同前辈列斐伏尔的洞见,提出空间过去常常被视为包括了“无经验性的内容”,尤其是包括了“虚无”、“无限”等此类的概念[7]234,这样导致的问题是“要确定空间概念如何产生,以及这样的概念对于可能的充分形式的表达如何变得清晰,是极为困难的”[7]232,空间因此进入了一个无所依托的形而上范畴。哈维认为,这种哲学上的空间认知,深刻影响了人们对待空间的方式,其鲜明地体现在物理学领域中,正如其所言,“关于空间性质的哲学思索因而时常影响物理学理论的发展”,由此形成了两种意义上的物理空间观:其一是“把空间看做物质世界中物体或事件的位置的质量”,其二是“把空间看做所有物质实体的容器”[7]236,前者被称之为“相对空间”,后者是一种“绝对空间”。哈维认为,“绝对空间”在以往的空间哲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其倾向于将“空间”视为一个绝对的“物自体”,认为在空间中,“每一点都是永恒不变的”[8],用它的主要倡导者牛顿的话来说,空间只不过是“抽象的、三维的、僵死的、欧几里德式的‘方格’,它永远都不会发生什么变化”[9]。可以看到,空间在这里被阐释成了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而由于“它永远都不会发生什么变化”,因此它是绝对的先验范畴,哈维将这种空间观称之为“空间的形而上学”。
将“空间”纳入到形而上的范畴,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空间作为某种“空”之场域的特点,但与此同时也把对空间的认知推向了某种抽象乃至虚无的境地,使得空间缺乏本有的人情温度。众所周知,在传统的哲学视阈中,“空间”的地位远远不及“时间”,最大原因便在于“时间”往往被理解为更具有“人性”的元素,其连接着人的过去与未来,连接着人的生老死别,对于人而言它具有更强的冲击力。相比之下,空间的存在被忽略了,用多琳·马西的话来说,空间被概念化为“一种事后想起的东西,一种时间的剩余物”,它在哲学上是“去优先化”(deprioritisation)的[10]。对此,哈维深有同感,他指出“空间”时常被“当作一种自然事实来对待”[11]253,其能够被阐释的张力被严重压缩。难怪乎法国哲学家德·塞托感慨,人们虽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空间中,然而“对此他们的认识如同对性的认识那样盲目”。[12]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哈维认为传统形而上的空间哲学给空间认识论造成了极大盲区,尽管“哲学致力于超越人类行为和局部知识的各种不同领域”,但在哈维的印象里,“那些试图为空间的定义谋求某种毫无争议的出发点的哲学家之间,已经产生了足够大的分歧和混乱”[13]46。因此,如果说形而上的空间认识论在古典时期还能够回避诸多隐蔽的空间问题,那么在现代性视野中,愈多且愈发明显的现实空间困境则宣告了:对于“空间”的理解只停留在哲学形而上的思辨层面上,完全是不可行的,因为“没有一个研究领域是和其他领域完全分离的”[14],故而我们还必须从现实语境出发,将“空间”进行形而下境构,以此融入到人类社会和现实生活中去,以之来反观我们的现实世界。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哈维深信,我们在理论问题中如何表达空间,会影响到我们和其他人“如何解释世界、然后如何对待这世界采取行动”[11]256。所以有学者指出,哈维的空间思想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对于哈维来说,空间是在特定时代和社会中被产生、形成、塑形和使用的。”[15]
二、空间现代性与空间的形而下之界
将空间认识论进行形而下境构,必须要对“空间”以往的基本属性进行重新判定。由于哈维曾接受过严格的地理学知识训练,早年以地理学身份出道的他,对于“空间”的认识似乎要比其他学者显得更为敏感。哈维认为,对于空间的理解不应只局限于“绝对”或“相对”之间,这无疑会令空间认识论陷入到“非此即彼”的漩涡中。在他的著作《希望的空间》中,哈维对看待问题中的“非此即彼”(either-or)模式提出了严厉批评,与之相对的是,他倡导“既又”(both-and)的辩证视点。站在这种“既又”辩证法的基点上,哈维认为空间应是融合了各种“关系式”的存在,也即是说,我们能够在空间中发现各种关系的建构,如哈维所言:“只有范畴之间的辩证关系才会真正起作用。”[13]55需要说明的是,指出空间是关系性的,并非等同于莱布尼茨所倡导的“关系空间”(relational space),实际上,莱布尼茨只是借此来反对牛顿神学式的绝对时空观,但他并未真正重视和明确空间本身的“关系”问题,其也只是将空间内嵌于“过程”之中来简单地看待。“过程”带有时间性,换句话说,莱布尼茨的关系空间很大程度上是意指“空间”与“时间”的关系,而不是针对空间本体论所生发的关系图式。
作为马克思辩证精神的继承者,哈维并未拥护以往任何的一种空间观,无论是绝对空间、相对空间和关系空间。在他看来,这些古典空间观将“空间”打上了形而上的烙印,置身于现代性之中,这些形而上空间观已经无法回应现实中的问题。尽管哈维曾尝试为空间划分了一个超越列斐伏尔的三元矩阵(即空间是绝对—相对—关系的三体结合),但究其根本,哈维对空间所进行的形而下境构,其聚焦点依然还是源于对“关系”的重新审视。在哈维那里,“空间”并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存在物,而是关系的聚合所,在空间中,我们能够度量各种真实世界中的关系。为了便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这种关系,哈维曾举过一例:他在一个房间里演讲,下面坐满了听众,“房间”这个空间将演讲者与倾听者联系在了一起。在这个空间里,听众与演讲者可以进行交流,听众与听众之间也可进行交流,而这些交流背后蕴含着不同身份者的不同文化背景和知识结构,因此也就使得正在演讲的这个空间有着独特的文化关系式,要理解这个空间,就必须要对这些关系进行解读[13]51。从这个意义上看,不同的关系,形构了不同的空间,比如上面提到的演讲空间,和人们居住休息的家宅空间,其不同之处除了物质结构之外,更为本质的正是其各自所包含的关系。
空间于是成为了某种超越其自身的隐喻,内嵌了关系的符码。要对现实世界的空间进行解码,就必须从真实存在的关系入手。当然,作为一名人文学者,哈维并没有对所有空间都进行包揽解读的野心;毋宁说,哈维所关注的空间是有特定的情境指向的。近年来,有不少研究哈维的学者都尝试明确哈维空间思想中的这种特定情境,如资本的运作(Alex Callinicos, 2006)、城市的演进(Sharon Zukin, 2003)、权力的操控(Marcus Doel, 2006)等。诚然,资本、城市、权力等与空间的关系,的确都是哈维分别重点考察过的议题,但其并不能全然概括哈维全部的空间语境。那么,这种特定的语境指向究竟是什么呢?我们认为,纵观哈维的空间著述,其所涵盖的面与点非常之多,但提取其共同症候可以发现,“现代性”是其背后贯穿始终的统一情境。正如哈维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借用马歇尔·鲍曼的思想明确指出,现代性等同于体验空间和时间的某种方式[11]251。作为一名批判型人文知识分子,哈维几乎将他所有的空间考察都建立在现代性视野之下,这种视野赋予哈维空间思想更多活力与更充足的现实感,这也是为何其能够引起诸多关注的缘由所在。
哈维之所以以“现代性”作为其空间思想的基础情境,主要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哈维敏感地意识到了现代性对于空间所造成的多维影响,这种影响深切改变了空间的体验形式与存在品格,且悄无声息地以各种方式潜入人们的生活之流。因而哈维认为,要剖析当前的空间症候,理解现代空间发生变化的原因、过程与结果,就必须溯源至“现代性”这个根本情境之中,将“空间”与“现代性”并置在一起考察。其二,“现代性”意味着一种转型,解析空间现代性的种种问题,不仅可为认识现代世界展现一个新视阈,更可借此来反观前现代空间的不同之处*哈维曾重点以俄罗斯学者古列维奇的著作《中世纪文化范畴》来考察前现代的空间体验形式,指出其不可分割地与宗教和道德概念联系在一起,而这种特征在“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淡”的现代性空间中是渐次缺席的。,进而为反思和解决当今诸多空间困境提供更富含张力的参照。其三,融入“现代性”这个情境,能够将空间问题推向一个更为广阔和更为深刻的境地,使得哈维的空间思想既源于具体的“空间”又得以超越“空间”,最终回归其背后更为本质的命题所在。从这个意义上看,近年来,哈维的空间思想之所以被众多不同领域的学者广为引用*据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统计,2007年,哈维成为了人文社会科学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学者之一,排名第18位。参见:“Most cited authors of books in the humanities, 2007”,in Times Higher Educational, Retrieved 5 March 2012。,有很大部分原因正是源于其并没有一味地局限于空间问题本身。
20世纪70年代末,已值晚年的列斐伏尔用其独有的创见宣告了:现代社会中,“空间”是不断地被“生产”着的。稍显遗憾的是,列斐伏尔的哲学体系过于庞杂,在《空间的生产》这本书中,依然显示他想要为“空间”进行形而上理论建构的努力。而哈维则在列斐伏尔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将“空间”与“现代性”转向了更为具体和实际的形而下讨论。正如现实所印证的那样,伴随着现代性一同到来的,还有现代世界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空间焦虑感,这种焦虑感连接了人类社会的伦理病症,映射着人类社会的伦理符码。哈维意识到了这种空间焦虑感,因此他对空间问题所进行的形而下探讨,毋宁说是对现代社会伦理症候的问诊。如哈维所说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人权理想已变成政治和伦理中心的时代。”[16]3在2014年出版的新著《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里,哈维也指出,现实世界中诸多空间景观的涌现和消逝,其危机并不在于这些空间景观本身,“危机的重心并不在于景观的大幅改变,而是思想和理解方式、机制和主流意识形态、政治忠诚和过程、政治主观性、科技和组织形态、社会关系,以及彰显日常生活的文化习俗和品味的大幅改变”[17]。“空间”在哈维那里于是上升为了一种伦理表征,从这个意义上看,哈维的空间思想无疑是聚焦在“空间伦理”这个主题式之下的。
三、哈维空间伦理思想的内容构境
哈维空间思想所涵盖的知识面极广,无论是其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批判,还是对当代城市空间和建筑空间的探寻,亦或是对社会空间及生态空间的隐忧式讨论,哈维均进行了集中且系统的论述*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批判,可参考哈维的《希望的空间》与《资本的空间》两本著作;对城市空间的探寻,可参考哈维的《社会正义与城市》、《巴黎城记》、《反叛的城市》三本著作;对建筑空间的隐忧,可参见哈维的《后现代的状况》与《希望的空间》两本著作;对生态空间的讨论,可参见哈维的《自然、正义和差异地理学》一书。。因此,“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人本主义地理学”、“现代城市社会学”、“后现代文化地理学”等这些曾被诸多学者赋予哈维空间思想的修饰词,都不能完整地概括其内容的全部指向。而从伦理学尤其是实践伦理学的视角切入,以“空间伦理”来反观哈维的空间思想,似乎要显得更为贴切,也更具有代表性与概括性,这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首先,从内容上看,空间伦理能够将哈维的空间思想有效地串联起来。事实上,“空间”在哈维的学术体系中,一直是以批判性姿态出现的(除早年的实证地理学之外),从资本空间到建筑空间,从城市空间到自然空间,莫不如是。毋庸置疑,哈维要批判的当然不只是空间本身,而是隐藏于空间背后的操控之手,它们其实都共同指向了哈维对现代社会中的伦理式发问,也显示了哈维对人类生活的伦理式关心。如哈维所说的,空间实践在社会事务中“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它们始终都表现了某种阶级的或者其他的社会内容,并且往往成为剧烈的社会斗争的焦点”[11]299。其次,从方法上看,空间伦理将“空间”与“伦理”结合起来,避免了传统空间哲学的形而上弊病,进而将“空间”带入了一个更符合现实情境和道德图景的形而下情境。同时,以伦理判断来解读空间,也能够为解决现实空间问题提供真正富含价值的参照,因为“伦理判断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指导实践”[18]。所以,运用“空间伦理”的方法来介入哈维的空间研究,追踪哈维空间思想背后的伦理命题,无疑是可行且极具阐释空间的。再次,从哈维本人来看,“空间伦理”更符合他在学术研究中所推崇的伦理诉求。正如哈维所认为的那样,“科学方法的各项原则(不论是什么),是规范性而非事实性的陈述,因此,这些原则不能以科学本身的方法来验证和赋予正当性,而必须诉诸科学以外的其它方式。”[19]同样的道理在美国分析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那里也经常被重申:“不仅科学领域有合理性问题,而且科学之外也有合理性问题”,而这种“合理性”的内核就在于“一种真的道德”[20]。而哈维之所以会从一个讲究逻辑实证主义的地理科学家,转向成为一个具有现实关怀和人文德性的人文学者,其根本原因正在于其内心被现实伦理所驱动,正如哈维所说的:“身为地理学者,我们所提供的可能有限,但身为学者和知识分子,在更大范围的各种议题上,我们却可以有更多的贡献。”[21]那么,哈维的空间伦理思想主要体现为哪些方面的内容?归纳起来,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区分为以下几个主要类别:
其一,资本空间与他者之痛。众所周知,作为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性人物,哈维在很多方面都延续了马克思的思想遗产,他甚至曾经认为,要恰当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似乎只有回到马克思才是正确的和恰当的”[22]3。而哈维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最为突出的便体现在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系统反思和猛烈批判。但和马克思所不同的是,哈维更加集中地突出了资本的空间之维,如其所说:“资本积累向来就是一个深刻的地理事件。”[22]24通过对资本积累的空间性分析,哈维揭露了资本的形态和本质,也阐释了资本主义发展对于空间的极度改造和利用。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哈维对资本主义的所有批判,并不意味着哈维和马克思一样,要为资本主义替换一个全新的制度体系,纵观哈维所有著述,可发现其并未在这方面做出理论上的努力。因而有必要指出,在批判资本的空间性之外,哈维的目的其实还指向了批判其背后对于无数个他者所造成的诸多苦痛。哈维认为,资本主义对于空间的利用,造成了全世界广泛存在的“不平衡地理”,这种“不平衡地理”以资本生产之名,极大的剥夺了不同他者在身体、情感及文化上所享有的应有权利。譬如资本积累初期,殖民者霸占他国空间,对殖民地民众进行屠戮与剥削;譬如在追求资本剩余价值的工厂空间里,劳动者的身体经常被过度使用,使得他们的身心健康遭到极大的破坏。哈维对这些资本空间背后不同他者的关注,具有鲜明的伦理性,而这种回归个体的伦理性关怀,在以往的哈维研究中往往是被忽略的。
其二,城市空间与社会正义。“城市”在哈维的空间思想谱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从早期细致深入地探讨城市的分配正义问题(见哈维:《社会正义与城市》),到20世纪末期考察现代城市中的等级区隔现象(见哈维:《希望的空间》),再到21世纪后不懈倡导列斐伏尔提出的“城市权利说”(见哈维:《叛逆的城市:从城市权利到城市革命》),我们都能够看到城市问题贯穿了哈维的全部学术生涯。难能可贵的是,哈维对城市空间的认识,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学和建筑学范畴,而将之带入到伦理学的命题意义中。对此,哈维曾经开宗明义地谈到:“在我们回答我们要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城市里这样一个问题时,就不能不回答以下这类问题:我们究竟要做什么样的人?我们寻求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我们与我们钟爱的自然处于何种关系?我们希望以何种生活方式来生活?”[16]4熟悉伦理学学科的便知,哈维所提及的这些问题,都是伦理学领域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在1960年代末期,哈维的学术兴趣之所以从自然地理学转向了带有鲜明伦理特征的城市社会学,其中尤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哈维受当时美国城市中的学生运动所启发:“我在1968年完成并将那本所谓的‘巨著’(即《地理学中的解释》)交付给出版社的时候,却发现那时候整个政治氛围都发生了改变,这叫我感到万分尴尬。……美国国内正值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如火如荼之际,我却刚写完一部立场中立的著作,不管怎么说,这的确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我知道,该是重新反思1960年代我所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的时候了。”[23]也正是在内心的这种伦理意识的呼唤下,哈维随即写作了一本与之前著作主题截然不同的《社会正义与城市》。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一个纲领,可以说,哈维之后所有对城市问题的关注,包括巴黎、马里兰、巴尔的摩、纽约、首尔等著名城市,都共同指向了其与“正义”这个伦理问题的内在联系。因此,与其说哈维关注的是“城市正义”,不如说他是想借由“城市”来触及“社会正义”的问题,并以此来反观现代人的生活及关系形态,以及对未来人类生活的某种期许。
其三,自然空间与人之异变。正如上文所强调的,哈维早期是一名讲究逻辑实证主义的自然地理学者,这就意味着哈维对于“自然”本身就具有先天的敏感意识。但和他早期追求客观、科学和实证的自然研究不同,后期哈维对于自然空间的关注,具有强烈的伦理属性,其直接同构了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的环境问题。哈维谈到:“当我们一方面关注对自然的责任,另一方面又关注对人类的责任时,有多重矛盾需要解决。”[22]217这种“多重矛盾”的出现,便是源自自然空间自身所不断内含的伦理情境。带着这个问题,哈维首先以一种“知识考古学”的方式,逐步考察了自然空间在前现代、启蒙时代、现代以及后现代等各个时期的表现。哈维认为,自启蒙理性出现以来,人类为了不断满足自己的欲求,其与自然的关系从“合理使用”慢慢变为了“强势统治”,这种统治性关系的转变,“隐含在现代科学特别是工具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价值之中”[24]138。自此,前现代社会中自然赋予人的神秘感和宗教感逐渐退隐,人类开始大肆利用乃至破坏自然。而随之现代社会里,自然空间也已被资本、权力、商业等操控,成为货币和利润的工具。这种境况的持续恶化,导致了自然空间在后现代社会中的解构,不仅自然环境被不断遭到“创造性的破坏”,人类的生存空间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与此同时,人类自身本应具有的自然性也开始淡化,“自然人”显得愈发稀缺,取而代之的,是“工业人”、“游戏人”、“电子人”及“机器人”等新型人类的陆续涌现。从这个意义上看,“回归自然”似乎已成为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境。哈维对自然空间的考察,正寄寓着他对人类道德及文化异变的焦虑与担忧,在他看来,“自然界为人类建造普遍的和永恒的价值大厦提供了丰富的、多样性的和永恒的选择,从而引导着人类的行动”[24]178。而当自然空间不断发生着异变,其根本原因正是源自人类本身在道德模式、文化心理及生活理念等方面的异变。
当然,除了资本空间、城市空间与自然空间这几种主要空间形态之外,哈维还广泛涉猎了性别空间、建筑空间、文化空间、身体空间及艺术空间等空间样式的多重分析,只不过未能像前三种那样系统和详尽,但其中所蕴含的伦理症候,依然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值得一提的是,近些年来,哈维对各种空间形态的分析,已逐渐引起了政治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重点关注,这与哈维对空间思想中的伦理性同样密切相关。
四、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哈维对于空间问题的论述,并不是建立在传统形而上的哲学范式上,也不刻意追求空间阐释的陌生化、抽象化与绝对化。相反,哈维所论述的空间往往是具体的、形象的、实在的和流动的,是对人类社会中空间问题的一种形而下境构。哈维之所以要将“空间”从以往的形而上讨论带入形而下考察,正是基于他意识到空间问题背后所蕴含的丰富伦理情境,这些空间问题的伦理情境深刻连接着人们的生命、生存与生活。
诚然,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人类现实社会中必将遭遇更多更严峻的空间问题,而像哈维一样从伦理视角切入,以构建“好生活”和“好世界”的伦理情怀来审视和探讨这些空间问题,显得尤为必要。因此,对于未来的空间研究来说,“空间伦理学”无疑是一个极其适时且必需的构建方向。相比于空间理论、空间哲学等空间研究范式,空间伦理学更为突出空间问题的现实情境、道德图景与人伦情感。以空间伦理学的视角来看待空间,将有益于人们树立更加健康的空间意识,以英国学者多琳·马西所说的“保卫空间”的姿态,为构建人类社会的“和谐空间”和“健康空间”而不断努力。
[1] 冯雷.理解空间[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2]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杰,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131.
[3] Yi-Fu Tuan.Space and Place[M].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1:3.
[4] (英)弗兰克斯·彭茨,等.空间[M].马光亭,章邵增,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2.
[5] 关洪.空间:从相对论到M理论的历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
[6] Henri Lefebvre:key writings,edit.by Stuart Elden, Elizabeth Lebas & Eleonore Kofman[M].New York:Continuum,2003:206.
[7] (美)哈维.地理学中的解释[M].高泳源,刘立华,蔡运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8] Bertrand Russell.Human Knowledge:Its Scope and Limits[M].New York:Clarion Books,1948:277.
[9] Isaac Newton.“De Gravitatione”,in Unpublished Papers of Isaac Newton[M].Trans. by A. R. Hall and M. B. Hal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123.
[10] (英)多琳·马西.保卫空间[M].王爱松,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25.
[11] (美)哈维.后现代的状况[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2] (法)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M].方琳琳,黄春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169.
[13] (美)哈维.作为关键词的空间[M]//陶东风,周宪.文化研究(第10辑).付清松,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14] (美)戴安娜·克兰.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M].刘珺珺,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12.
[15] Andrzej J L Zieleniec,Space and Social Theory[M].SAGE,2007:99.
[16] (美)哈维.叛逆的城市[M].叶齐茂,倪晓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17] (美)哈维.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M].李隆生,张逸安,许瑞宋,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4:5-6.
[18] (澳)彼得·辛格.实践伦理学[M].刘莘,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2.
[19] David Harvey,.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the ideology of science[J].In Economic Geography,1974,50(3):256-277.
[20] (美)希拉里·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M].童世骏,李光程,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21] David Harvey.What Kind of Geography for What Kind of Public Policy[J].in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1974(63):18-24.
[22] (美)哈维.希望的空间[M].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3] David Harvey.Reinventing geography (interviewer:Perry Anderson)[J].in New Left Review,2000(4):75-97.
[24] (美)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M].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刘伦文
2016-08-17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大卫·哈维与空间伦理研究”(项目编号:15CZX034)。
吴红涛(1984- ),男,江西鄱阳县人,哲学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伦理美学及空间文化批评。
B82-058
A
1004-941(2016)06-013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