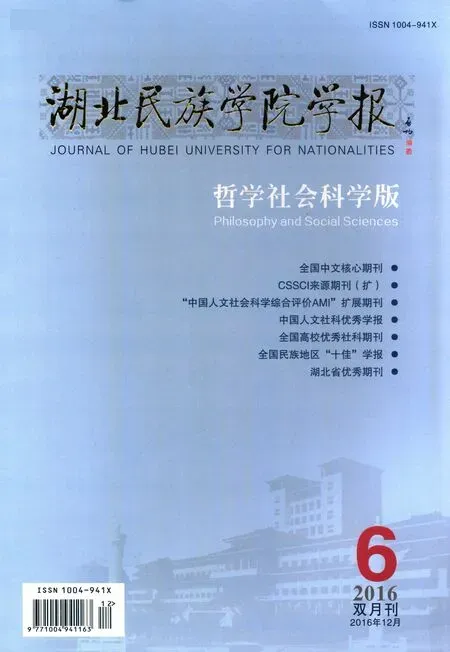历史创伤、文学再现与社会记忆
——方方的《软埋》及其他
谢文芳,陈国和
(1.湖北科技学院 人文与传媒学院,湖北 咸宁 437100;2.湖北科技学院 学报编辑部,湖北 咸宁 437100)
历史创伤、文学再现与社会记忆
——方方的《软埋》及其他
谢文芳1,陈国和2
(1.湖北科技学院 人文与传媒学院,湖北 咸宁 437100;2.湖北科技学院 学报编辑部,湖北 咸宁 437100)
作家总是通过文学的形式表达对世界的认识,参与社会记忆的传承、建构和控制。在没有档案可查,无法还原当时历史的情况下,文学以艺术方式再现历史,进行社会记忆再生产。方方的长篇小说《软埋》书写了土地改革这一历史运动对人们造成的心理创伤,同时展示了不同代际的人面对历史的不同立场和态度,再现了历史和生活的复杂。
历史创伤;社会记忆;方方;《软埋》
近几年,方方因和柳忠秧的官司四处出击,倍受媒体关注。其实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诸多知识分子都适应了鸵鸟的生活习性,大家在明哲保身、利益共享或者说同流合污中远离了良知,更不关注后人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在这种情绪下方方写了短篇小说《云淡风轻》(《长江文艺》2015年12期)揭露了庸人之恶,也创作了长篇小说《软埋》(《人民文学》2016年第2期)呈现小人物被大时代挫伤的悲剧,重现历史创伤,丰富社会记忆。
一、历史创伤
创伤主要指生理、心理等遭受的突然的、未曾预料的伤害,“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1]216土地改革不仅仅是乡村文化秩序的重组,更主要的是人们心灵世界的重建。当代中国作家如何从个人的角度深刻反思历史,并且通过文学来再现历史创伤是一个重要的命题。选择哪些记忆被保存,选择哪些记忆被遗忘,书写历史是构建自我存在的一种有效方法。《软埋》主要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儿子吴青林的家族“探秘”,另一条则是母亲丁子桃的回忆。这两条线索并行推进,同时切入建国初发生在川东陆晓村的土地改革运动,悬念迭起、环环相扣,呈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家族血泪史和国家的“痛”史。
故事的主人公之一丁子桃(同时也是历史中的胡黛云),当年是川东大户陆子樵家的儿媳妇,因为土改,陆家害怕被批斗后活不下去,决定集体以“软埋”的方式自杀。胡黛云受命“软埋”家人,并为照顾年幼的孩子,从密道中逃出陆家。坐船时家里的长工富童为了胡黛云的丫头小茶弃船而去,胡黛云和儿子落入水中,儿子丧命,胡黛云被人救起后失忆,有了新名字丁子桃。这个过程里,她遇到了有相似经历的部队医生吴家名,历经波折,两人几年后组成家庭,并生下了儿子青林。
青林是作品中的线索性人物。文中各种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正是通过他的寻根活动穿珠成链,形成了一个严密的叙事网络。青林很小的时候,吴家名遇车祸身亡,丁子桃一直靠给别人当保姆,辛苦把青林养大。青林后来到南方工作,赚钱买了别墅给母亲住,可丁子桃住进别墅的第一天就陷入人事不知的状态。实质上,丁子桃的失忆是陷入了自己的过去。她多年来一直想不起或不愿想起的惨痛记忆,因为一些刺激而重新复活,并且是以从十八层地狱一层一层向上走向光明的方式复活。丁子桃这条线索通过她的“不在现世”的灵魂,以倒叙的方式讲述了当年两个川东地主家族覆灭的故事。
丁子桃刚进自家的别墅,不是开心,而是忧虑,担心“分浮财”,担心农会“会找上门来”,并因此失忆。丁子桃失忆后,口中断断续续蹦出一些词语:枪托、三知堂、且忍庐、谢眺的诗。丁子桃独处时,莫名的恐惧就会卷土重来,隔三差五地袭击她,如潜伏在暗河中的魔鬼待机给她致命一击。丁子桃感觉到历史创伤“那些东西便在她的身后追逐”,即使“拼命地逃避”,也“始终尾随着”,“漂浮和移动,甚至挑逗、勾引”。土改的时间并不长,但是,这一政治运动影响了整个社会的生态,特别是乡村。很多人因为土地而改变了命运。成千上万的人在这场运动中遭遇了惨烈的伤痛。很多人不愿意回忆,更不想述说。这些创伤的经历者总是选择遗忘,保持沉默,甚至不允许自己的后代去探寻这段历史,不想让后代继续背负着沉重的包袱。于是,这些历史创伤的在场者埋名隐姓,永远沉默。历史的踪迹也就无从探访。
“软埋”是指“如果一个人带怒含冤而死,不想有来世,就会选择软埋。”“软埋”这个题目具有隐喻性,一方面指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了断,另一方面也指对来世和希望彻底绝望,因为“软埋”之后不得转世。陆子樵及家人含着极大的创伤放弃这一世的生命,同时也放弃有可能的下一世的生命。丁子桃、吴家名等活着的人,也选择忘记过去,忘却自己,尘封往事,拒绝回忆。这种下意识的拒绝历史创伤其实就是一种时间的软埋。遮蔽历史事件,就是软埋自己的一种有效方式。它从一个死亡的悲剧,变成了遗忘的悲剧。事实上,不需刻意遗忘,人们经常身处于历史遗物的旁边,却毫不自知,就像丁子桃作为保姆在刘小川家里那么多年,他们从来不知道她就是胡黛云。
那些具体的伤痕和梦魇或许已经远离,但是,记忆深处的阴魂却死而不僵。往往在多年以后,它会死而复生,被重新撕裂,唤醒,成为迟到的悲剧以及预想的创伤。创伤造成的鬼魅如影随形地追逐着丁子桃,伴随着她的一生。美国著名创伤理论家卡西·卡如斯(Cathy Caruth)说:“在创伤中存活下来未必是一种摆脱暴力事件的幸运路径,比起说这条路径经常被暴力的回忆扰乱,倒不如说对暴力重复固有的必须性最终或将会导致毁灭。……受创伤个人的历史正是毁灭性事件毫不犹疑的反复重复。”[2]62-63暴行和暴力并不是在受辱的时刻完成,事实上很多时候离开原始创伤的具体时空,暴力那种精神性、经历性的重复反而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实践和重复是相关的,即使是强迫性的重复——重复的趋势往往是强迫性的。这在经历过创伤的人身上尤其明显。他们往往喜欢重温过去,被那些过往的鬼魅影响,似乎他们还活在过去,和那些创伤毫无距离一样。”[3]142-143
在方方的故事中,历史摘掉了它呆板的教科书面具,不再只是具有年份与事件的文字。它更加生动、具体。那些曾经的历史亲历者,那些被正史的铅字忽略的“人”,正从那副冰冷的面具之后向人们徐徐展开,为我们讲述着那些属于他们的专属记忆。人在自然的场景和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颗尘埃。无论该与不该记忆的事情,都只能选择遗忘。
二、文学再现
作家总是通过文学的形式来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参与社会记忆的传承、建构和控制。当人们对物欲横流的社会无奈的时候,当人们对“庸人之恶”几乎绝望的时候,当人们对精神失血的文学表达失望的时候,方方用《云淡风轻》进入人精神的存在,洞察孤独个体灵魂深处的幽微和褶皱;用《软埋》进入历史的现场,拒绝“软埋”,探析时间淹没的历史河床的面貌和时间的真相。方方通过这样的故事,展示出了不同代际的人面对历史的不同立场和态度。比如,以丁子桃为代表的曾经的地主阶级、以刘晋源为代表的革命者和政府工作者、以吴青林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和以龙忠勇为代表的人文学者,甚至还有以刘晋源的孙子为代表的“90后”,面对过去,他们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看待、进入和叙述的方式。但这部小说并非要表现一种历史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而是要通过这些人物来呈现历史的复杂性,或者说,是把历史事件放在“历史的语境”与“历史的动态”中来考察。
上文我们已经论述了丁子桃对暴力土改的叙述和态度。暂且忍让,且忍庐上巨大的“忍”和“耐”字,包含了多少生存哲学和无可奈何的选择呢?而作为革命者的刘晋源则是另外一种立场和叙述方式。刘晋源“打了半辈子仗,挨了多少枪子。这红色江山,有我的血呀。‘文革’了,居然抓了我去坐牢,说我是反革命。我革命一辈子,居然成了反革命。邪不?”因此,他进一步感叹很多历史“提不得”。但是,刘晋源作为“正史”的叙述者,认为在国家利益面前,个人无法逃避自己的责任。“参加革命,就是想过好日子,不受地主的气。”“打走日本鬼人,回家过好日子。后来又说,消灭土匪,回家过好日子。再后来说,打垮国民党,回家过好日子。一直到朝鲜,还是说,赶走美国佬,回家过好日子。结果,好日子过上了,爹走了,娘没了,二老不在了,连家也都不想回了。”作为新中国的革命者和缔造者,刘晋源心中的历史非常实在,是自己和战友拿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他对青林说“你们现在的日子,是我们年轻的时候一仗一仗打出来的,是拿命换来的。那时候我们出了门,根本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因此,为了保证红色江山永固,一切牺牲都值得。正因为这种家国情怀,当他的回忆再次触及川东土改运动时,即便他承认其中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处,却依然坚信这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无可厚非。“矫枉必须过正”。“当年并没有人出来分析,穷人为什么会穷,穷人中有没有地痞流氓。更没有人说,哪些富人是好富人,哪些是坏富人。所有的一切,都是现学。而且打完仗剿完土,杀心还没有褪尽,就觉得镇压是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只要是穷人,不管活在哪个社会,你让他去把富人的财富变成自家的,把地主的土地变成自己的,只要允许,哪个不会积极去干?天下人心都是一样的。”显然,对于刘晋源来说,个人价值在国家正义面前显得非常渺小。
作为土地改革的围观群众马老头也有自己的民间认识:“基层农民激情万丈,一下子失控了。工作组也都发了昏,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处理,结果跟着农民走,都失控了。”“以现在的眼光看,你们当年会觉得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可是当年的社会状况又险恶又混乱。……打仗我们打过多少年,可谁也没干过土改。也不懂法治,当然也没人跟你说过,万事应该法治。大家开会,说这个人该杀,就杀了。或者是,土改组长听到反映,说某人很坏,该杀,也就决定杀了。基层的执政者,自己也不懂什么,政策水平很低,光想着要为穷人说话办事,并没有多想想,穷人这样做对不对。”陈思和在《土改中的小说与小说中的土改》一文中指出,在暴力“土改”中出现的迫害现象,主要通过乡村的痞子和掌权的干部两类人物得以不断再现。而在文学中不断出现的痞子形象中,最接近“土改运动”中真实的痞子的是鲁迅笔下的阿Q[4]339-340。阿Q这类赤贫的农民是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乡村及其不平的财富分配和土地兼并的产物。这类农民往往身无长物,一无所有,是真正的赤贫无产者。他们视任何一次政治运动为改变命运和“翻身”的机会。因此,这些人内在的“恶魔性”很容易激发出来,无视道德和法律的约束。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恶魔性”因素是人类原始的动力,它一旦释放出来就会对世界造成巨大的破坏。这些人被动员、组织起来就成为社会上最具有革命性的力量,成为各种暴力运动的直接执行者和推动者。也就是说,在历次政府主导的政治运动中,那些暴力行为往往由那些无名无姓的普通者执行。因为这种暴行并非由政府人员执行,而是由这些普通的底层农村犯下的,因此,不会留下正式的法律文本记录以供后世查考和研究。
以青林为代表的后来人不像刘晋源亲自率领剿匪部队,亲自杀死土匪头目。他对当年的川东剿匪一无所知,对过往的战争也只是通过电影、书本了解一二。青林认为暴力土改其实没有必要这么残酷,“如果理智地来做这些事,应该还有更好的办法。”因此,刘晋源关于战争的叙述充满了“愤慨、感叹和悲伤”。当青林听到刘晋源的叙述时脑中努力还原当年的战场和战士的情谊,并且被无名地感动。特别是当刘晋源退休以后,淡薄了名利,这种情谊就越显得尤为重要。人文学者龙忠勇认为:“改朝换代,稳固江山,这是个必然过程。只是,我们也可以自问一下,必须要这样残酷吗?”龙忠勇因此而感叹:“人生有很多选择,有人选择好死,有人选择苟活。有人选择牢记一切,有人选择遗忘所有。没有哪一种选择是百分百正确,只有哪一种更适合自己。”“历史需要真相”。“有人选择忘记,有人选择记录,我们按照自己的选择生活,这样就很好。”世道确是无常,历史真假难辨。
暴力的发生,有一定人性基础,是内在于人类心理和生理的暴力倾向。从心理本源上看,暴力来源于人们彼此心灵上的隔绝以及对社会现状的恐惧。不过,不同程度的文明环境,在化解和消除人类暴力基因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同。有的社会条件有利于抑制暴力动机,有的社会条件则可能诱发暴力。事实上,所有的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都可能产生暴力行为。在没有档案可查,无法还原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如何再现历史,怎样进行社会记忆再生产?我们唯有依靠作家对当时情景进行描述和再现。
三、社会记忆
丁帆通过对比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认为,这类小说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写作实践,“它从来都不以追求‘生活的表面真实’为目的,它们要将自己的写作,与党的政策,实际的‘土改’运动构成一个整体,来推动国家的改造,推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尽管这一改造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与遗憾,但不可否认它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尤其是农村社会。因为正统的‘土改’叙事,承担并实际发挥了社会改造的真实话语作用。”[5]225《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这类正统的土改小说有着历史合理性。但是,由于这类小说的政治性追求,自然而然也就抹杀了对生活丰富性和历史复杂性的进一步描写。“小说家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预言家,他是存在的勘探者。”[6]43这种勘探只有拒绝任何的预设才有发现的惊喜,只有执念于当下才有真正的发现。
新时期以来,诸多作家关注土改题材,如乔良的《灵旗》、张炜的《古船》、尤凤伟的《诺言》《合欢》《小灯》,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苏童的《枫杨树故事》、池莉的《预谋杀人》、莫言的《生死疲劳》等。值得肯定的是,经过了“文革”的浩劫,作家们的眼光早已超越了对土改事件本身的关注。这些优秀的作家续接了鲁迅批判国民性的思路,挖掘民族传统中的缺失,聚焦人类暴力的起源和人性问题。这种创伤书写的策略使得文学与历史的意义截然分开。历史学家往往通过一系列数据的列举与分析,推断土改运动的是非功过。而文学创作则超越历史表象,直逼人性,将那些无法在历史档案中保留下来的民间暴行通过艺术的形式再现出来。
如果说张炜的《古船》“超越了政党与政治的斗争”,“把暴力视为人性异化的结果”,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把土改中的暴力“放在人性的聚光灯下加以解剖和考察”[4]334。那么,《软埋》则是在历史创伤的记忆和遗忘的叙述中进行社会记忆再生产,从而呈现了历史的复杂性。青林对历史真相的回避,刘晋源对当年革命运动的解释,龙忠勇对大户人家变迁的探寻等,其实并不是要去穷尽历史的真相,而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历史进行阐述,丰富社会记忆的内容。丁子桃作为亲历者,从主观的角度复述当时的场景;刘晋源作为胜利者,以胜利的姿态解释历史的运动;青林则作为新世代、后来者的身份,以旁观的视角选择性地探析历史。但是,他继承了父亲功利主义的生存哲学,关注当下世俗生活,尝试忘记自己不能承受的历史创伤。信奉“平庸者不对抗”、认为“人生低调而顺其自然才能保其长久。”对暴力的回避,至少表现了叙事者对如何处理过去的创伤心存犹疑。而龙忠勇作为一名人文学者则采取类似客观的视角,直面和记录历史。因为“历史需要真相”,“有人选择忘记,有人选择记录。我们都按自己的选择生活。”这些叙述和记忆的并置与交错,历史的复杂性自然而然得以呈现。
不同的人物对同一历史事件不同阐述。其实如同社会群体、国家政权一样,出自各自的现实需要和利益诉求,自觉不自觉地延续和传承社会记忆。这种传承、建构和控制的过程就是社会记忆再生产的过程。同时社会记忆再生产不同于物质再生产,其后续的延续、传承、建构是对原初记忆的加工行为或复活过程,“这些记忆不停地再现,通过它们,就像是通过一种连续的关系,我们的认同感得以终生长存。”[7]82丁子桃、刘晋源、龙忠勇以及青林都是出自各自的现实需要和利益诉求进行社会记忆的再生产。方方通过这种虚构的形式、想象的方法和审美的特点,保留一份真实的社会历史档案。在历史的沉默与激荡处极端地书写历史暴力,见证历史的喧嚣与创伤。
[1] (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 Cathy Caruth.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 history[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
[3]LaCapra,Dominick. Writing history,Writing Trauma.Baltimore[M].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
[4] 陈思和.土改中的小说与小说中的土改[M]//思和文存:第三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
[5]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 (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孟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7] (法)莫里斯·哈布尔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毕 曼
2016-05-23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乡村小说视域下的当代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书写研究”(项目编号:11YJC751008);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从资源到产业:新世纪乡村文化的重构——以湖北省为例”(项目编号:14D067)。
谢文芳(1971- ),湖北嘉鱼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和当代文学批评;陈国和(1973- ),湖北通山人,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媒介文化。
I207.67
A
1004-941(2016)06-013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