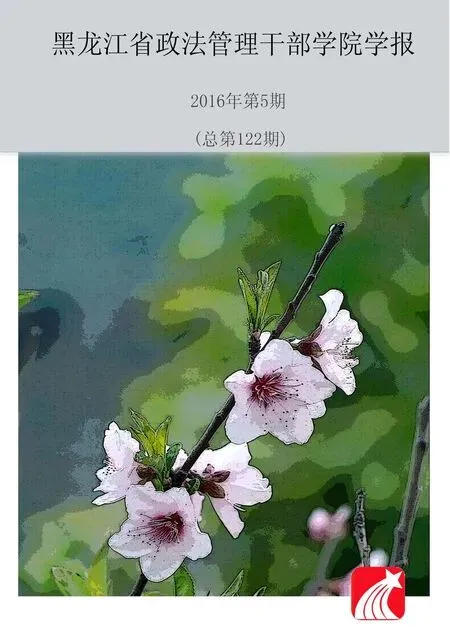论不法侵害始点的判断标准
——预备最后阶段说之提倡
张 宝
(河南科技大学 法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论不法侵害始点的判断标准
——预备最后阶段说之提倡
张宝
(河南科技大学 法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在不法侵害何时开始的判断上,传统刑法理论主张存在无法克服的弊端,难以实现理论自洽,因此有必要对其认定标准进行重构。预备最后阶段说不仅有利于实现正当防卫制度的刑事政策目的,而且有利于防止防卫权利滥用,无疑是这一问题的最佳理论选择。
不法侵害;理论选择;预备最后阶段
在正当防卫构成要件中,对防卫紧迫性要件,即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认定通常而言较无问题,但究竟具备什么条件才能认定不法侵害已经开始则仍然存在较大分歧。基于此,本文将主要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论述,并试图在对相关理论争议进行梳理与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些许浅见。
一、不法侵害始点认定的理论争议
关于不法侵害何时开始,目前我国学界主要存在进入现场说、着手说、面临危险说、区别说及有效说等理论主张。(1)进入现场说主张,不法侵害开始以行为人进入现场为主要标志[1]。(2)着手说认为,不法侵害必须达到着手程度,即进入未遂判断程度,才能进行正当防卫。因为某一侵害行为只有在达到着手后,才能有所谓的不法侵害评价。在行为者着手以前,刑法不仅不能而且也不应该加以评价,否则即有违反罪刑法定主义的嫌疑[2]。(3)折中说,又称合并说或面临危险说,认为一般而言实行行为的着手应该是不法侵害开始的标准,但在例外的场合,尽管不法侵害尚未着手,但其给法益造成的急迫性危险却已经毫无争议地呈现出来,如果不及时实行防卫反击就会丧失防卫机会,该种情形下也应允许实施正当防卫。换言之,当不法侵害尚未实施,但不法侵害者的行为已经对合法权益形成现实的紧迫性危害,即不法侵害转入实施阶段后防卫者即立刻丧失有效防卫可能性的条件下,应当认为防卫行为符合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3]。(4)区别说认为,由于不法侵害的手段、强度、不法侵害者主观罪过,以及侵害法益的性质等各不相同,因此判断不法侵害何时开始也不可能存在统一标准,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判断开始实施正当防卫的适当时机。如有学者认为,对于故意实施的不法侵害,不法侵害行为人开始实施预备行为时,就已经足以彰显其不法侵害意图,应当认定不法侵害已经开始;而对于无责任能力人实施的不法侵害及过失实施的不法侵害,只有在侵害行为已经实施并且即将损害国家、社会、个人合法权益时,才能认定不法侵害已经开始[4]。(5)有效说从防卫是否有效的观点出发,认为侵害行为客观上业已达到防卫者得以有效行使防卫之时间终点,如超过此一时间点,防卫者即无法达到防卫目的,或必须承担风险或付出不应承担的代价,即应认定不法侵害已经开始[5],至于最后有效防卫的时间点则不以未遂程度未必要,即便着手前的预备阶段,也可以认定不法侵害已经开始[6]。
二、当前理论分歧的评述与检讨
就基本内容而言,以上诸说都是对不法侵害始点判断的有益探索,但客观而论又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当之处,难以实现理论自洽。
进入现场说的问题在于:第一,对现场概念存在误读。实践中,认定某一场所是不是侵害现场,通常只有根据不法侵害行为的实际发生状况才能判断,不可能首先事先确定好一个侵害场所,然后再以行为人是否实际进入该场所来判断不法侵害是否开始[7],否则即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第二,导致不法侵害外延过于宽泛。因为进入场所与不法侵害开始之间并不具有必然的等同性,很多情形下,行为人虽然进入到某场所,但并不能由此便说明其有不法侵害意图,更不能说明行为人已经开始实施不法侵害。依照进入现场说观点,往往会对实际进入到某场所但并不具有不法侵害意图的行为人造成不当评价,继而导致不法侵害外延过于宽泛。第三,对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认定形成障碍。由于可能存在行为人虽然进入到某场所但尚未开始实施不法侵害行为的状况,因此,依据进入现场说往往会导致防卫者、第三人或司法机关无法对不法侵害的强度做出准确判断,进而不能判断防卫行为是否符合正当防卫的限度要件[4]。
着手说的问题在于:第一,将犯罪行为的着手与不法侵害的开始等同起来显然并不科学。依照通说,着手是特指开始实施刑法分则规范里具体犯罪构成要件中的犯罪行为,而不法侵害开始则不仅指开始实施犯罪行为,而且包括开始实施一般违法行为,着手说将两者等同起来,显然混淆了两者质的不同。第二,容易导致防卫时间过分迟延,实际增大被侵害人的防卫风险。对于盗窃等非暴力性犯罪而言,由于侵害法益与损害法益之间的不对等性,一般而言依照实行行为的着手可以认定不法侵害的开始,但是对于暴力性犯罪,由于危害结果往往直接伴随着实施行为而产生,因此,如果将防卫行为的始点限定在实行行为的着手,往往导致防卫行为人无力实行防卫[8]。正如有学者指出,基于法治国原则,未遂犯着手的认定当然应尽可能接近正犯犯罪的完成,如此才不至于动摇刑罚以构成要件的完成为要件。但以未遂犯的着手认定正当防卫之不法侵害的开始,则将彻底使防卫行为变得毫无意义,因为等到着手这一刹那,行为人才能施以防卫措施的可能性已经太慢或几乎太慢了[9]。德国刑法理论通说也认为,不法侵害开始的始点不能等同于未遂的着手点,因为着手的基准往往逼使防卫者错过了有效的防卫时点,这样就可能把侵害风险转嫁给被害的防卫者[10]。第三,容易倒逼防卫行为人实施过分防卫,导致防卫过当频繁高发。在故意犯罪的发展阶段上,由于未遂已经是几乎接近既遂的程度,因此,如果要求防卫者必须等到侵害行为的着手才能实施正当防卫,由于侵害越接近完成阶段,防卫者越担心难以达到防卫目的,因此,相对较早可行的防卫而言,其总是可能做出较重的反击,如此一来,便极易超过必要的限度要求,构成防卫过当。第四,将某些虽未着手但实际已使法益直接面临被侵害危险的侵害行为视为尚未开始的不法侵害也不尽合理。因为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不法侵害行为在尚未着手阶段便已经对法益构成了急迫性危险,从正当防卫的刑事政策目的出发,完全应当允许被侵害人对其实施正当防卫,如若非要等到其着手才允许进行防卫,那么多数情形下都已为时已晚。从这一角度出发,着手说也不尽科学。第五,虽然有学者不断对着手概念提出修订与完善,力图通过这种方式维持着手在不法侵害开始认定上的标准地位,如张小虎教授提出着手应当涵盖使法益直接面临被侵害的危险的意义,存在形式内容与实质内容。形式上,着手是指开始实施刑法分则规范规定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中犯罪行为;实质则是对刑法所保护的客体造成损害或形成直接威胁,其中着手的实质意义较为抽象,而形式意义较为具体,就二者关系而言,应坚持形式意义为主,实质意义为辅[1]。但根本而言,这种主张也存在问题。因为着手首先是严格的规范概念,认定刑法中的着手首先必须严格立足构成要件立场,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因此,行为纵然对法益造成了一定的侵害或危险,但只要没有充足具体犯罪构成要件实行行为,或多少实行了该构成要件行为,就不得以着手概念加以框定。而且,客观而言,客观主义的基本立场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并未得到很好贯彻,这样的背景下,为了满足打击犯罪,防卫社会的需求,实践中,形式意义为主、实质意义为辅很容易便悄无声息地演变成实质意义为主、形式意义为辅,即在所谓形式意义的掩饰下,进行超规范的实质意义的盘算,对于罪刑法定原则而言,这无疑是一场灾难。
折中说的问题在于:第一,在不法侵害认定的时点上,折中说原则上仍以实行行为着手为标准,因此,当然存在前述着手说同样的问题与不足。第二,折中说认为某些不法侵害虽尚未着手实行,但已经对法益构成了严重威胁,来不及向有关机关报告,如果不实施防卫,势必发生严重性后果,因此应当允许进行正当防卫。在此,无意中折中说已经将“不得已”作为了正当防卫的基本要件[4]。但是从现代各国刑事立法来看,绝大数国家并未将“不得已”作为正当防卫要件,我国刑法第20条也没有规定正当防卫必须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实施,由此可见,折中说主张不仅与现代普适的刑法理论不符,也与当前我国有关正当防卫基本立法相互冲突,其科学性难免让人质疑。第三,实践中的案件总是纷繁复杂,因此在折中说看来,绝大多数不法侵害是否开始总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是在判断主体素养是否良好、判断标准是否明确、判断素材是否全面等问题尚未明确之前,这种委由个案判断的主张固然可收到简便及因地制宜之效,但最终却可能导致不法侵害的认定毫无标准可言,基于此,应当说折中说主张也未必适当。
区分说的问题在于:第一,单纯以预备行为为故意实施的不法侵害的始点,容易造成防卫行为的失控。因为预备行为的方式具有多样性,距离实行行为的远近也不尽相同。例如甲欲杀乙的预备行为,既可以表现为准备刀具,也可以表现为持刀奔向乙家。张三意欲入室盗窃的预备行为,既可以表现为在家苦练配钥匙技术,也可以表现为携带作案工具潜伏目标现场。现实中,如果只是在家磨刀或在家练习配钥匙,便不宜认定不法侵害已经开始,因为这些行为都只是一般性预备行为,尚未对法益构成急迫性侵害或危险,一旦允许对其进行防卫,实践中便会造成防卫行为的把控过于宽松。第二,为什么过失不法侵害与无责任能力者实施的不法侵害具有相同的始点,区分说没有做出进一步合理解释。事实上,从不法侵害的客观属性及对法益造成的侵害或危险的最终结果上看,过失不法侵害与无责任能力者实施的不法侵害并无本质不同,仅有的区别只在于前者的着眼点在于不法侵害行为人的主观心理,而后者则立足不法侵害行为人的具体类型。第三,区分说对故意不法侵害与过失不法侵害的始点进行了明确划分,同时对无责任能力者实施的不法侵害与过失不法侵害在开始时间上又坚持统一标准,那么问题是,当无责任能力者故意实施不法侵害时,究竟依照故意不法侵害开始的标准,还是适用过失不法侵害开始的标准进行认定呢?如果适用前者,则显然与区分说论者的主张相互矛盾,而如果适用后者则显然要面临解释的难题,即为什么认定故意不法侵害的开始,反要适用过失不法侵害的认定标准呢?对此,可能也是区分说主张的理论盲点。
有效说的问题在于:第一,以“有效理论”作为不法侵害“现在性”时点的认定标准,有时难免造成防卫时点过度前移,以至于一个正处于计划当中或仅仅处于一般性预备阶段的攻击行为,都可能被认定具有“现在性”而得以对其进行正当防卫,如此无疑于过度扩充正当防卫权的合理界限[11]。第二,究竟是否有效的判断主体及标准也不甚明确,如果以防卫行为人的自身判断为标准,那么“允许人们把这种大胆的紧急防卫权使用于如此广泛的防卫性目的,也会与社会的和平秩序和国家的管辖垄断权发生矛盾”[12],毕竟,对于有计划的侵害行为的事前防卫,无论如何属于国家的任务。国家对于有计划的侵害行为进行防范尚且需要严格遵照法定程序,而如果公民个人只需依照自身的判断标准,从防卫个人权益的有效性出发便可实施防卫,并无如同国家那样受到层层限制,如此反而容易造成防卫权滥用之势[11]。第三,有效说以防卫是否有效作为不法侵害开始的认定标准,着眼于公民个人防卫权的严格保护,基本立场固然值得称道,但从全面保护法益的立场出发,难免又有“护短”之嫌,即过分重视被侵害者权益保护,而漠视不法侵害者权益保障。不法侵害者故意或过失实施侵害行为,给他人或社会合法权益造成侵害或危险,固然值得谴责,但其基本权益却仍应受到法律的合理保护,正所谓法律的阳光照耀好人,也照耀坏人,但在有效说的理论框架内,不法侵害行为人显然难以寻见丝毫的亮光。
三、预备最后阶段说之提倡
鉴于以上诸说的理论缺陷,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不法侵害始点的认定标准进行重构。由于正当防卫既要保护合法权益免受不法侵害,又要防止过度损害不法侵害者的利益,因此,在构建不法侵害始点的认定标准中,以下两种因素便必须着重考虑:一是如何有利于实现正当防卫制度的刑事政策目的;二是如何有利于防止正当防卫权利滥用。基于前者考虑,不法侵害始点认定不宜过晚,否则将使正当防卫的制度目的落空;基于后者考虑,不法侵害始点认定又不宜过早,否则则可能造成防卫权利滥用。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不法侵害始点的认定标准上,较为妥当的做法,毋宁采取一种比较折中的方案,亦即在不法侵害开始的认定上,既然着手说的判断时点过于滞后,可能把侵害风险转嫁给被侵害的防卫者;而有效说的判断时点又过于前置,容易造成正当防卫权滥用,那么,为了克服这种困难,完全可以将不法侵害开始的时点设定在两者中间,即从“预备的最后阶段”至“着手”之间这样的阶段上。对此,罗克辛教授 (Roxin)也曾深刻论述到,“正确的界限应当处于两个极端之间(即未遂阶段与有效阶段——笔者注),对于正在发生的攻击,人们除了未遂之外,仅仅应允许算上直接位于未遂阶段开始之前的那个狭长的预备结束阶段。在这个已经为紧急防卫提供基础的与未遂紧密相连的预备的领域中,涉及了对攻击的直接着手(与才进行的准备的攻击不同,那还不是正在进行的;并且与实行行为构成的直接着手也不同,那已经表现了一种未遂)”[13]。为了表达上的简洁,对于这样一种折中的设想,笔者称之为“预备最后阶段说”,采取这种标准,不仅能够有效克服传统刑法理论主张的固有缺陷,最大限度实现正当防卫的刑事政策目的,而且也能够根本上防止防卫权利滥用,对于不法侵害始点的准确认定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第一,符合目的性思考原理。刑法之所以设立正当防卫制度,根本目的就在于赋予不法侵害被害人或第三人以正当防卫权利,借以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所以某种程度上才说,“问题的重点已经不是侵害行为与防卫行为之间的绝对的时间数字的问题,而是被侵害者或第三人如何可以有效保护自己或第三人利益问题”[14]。据此,如前所述,依照着手说的主张,显然容易造成防卫行为的过于滞后,让防卫行为人过多地承担防卫风险,不仅不利于防卫行为人及第三人权益保护,也与正当防卫制度的刑事政策目的背道而驰。而预备最后阶段说将防卫行为的时点提前至接近着手的狭长的预备阶段上,只要不法侵害人的侵害行为逾越一般性预备行为而又接近未遂的着手,防卫行为人即可实施正当防卫,其着眼点显然更加有利于防卫权的充分行使,根本上契合正当防卫制度的刑事政策目的。
第二,有利于构建不法侵害始点认定的统一标准。鉴于不法侵害行为的现实复杂性,在不法侵害开始的认定上,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越发成为有力主张。有学者甚至旗帜鲜明地提出,不法侵害的现在性本身就是一个没有绝对标准的概念,因此,我们必须结合正当防卫法律概念的目的具体分析[14]。但在笔者看来,不法侵害何时开始无论如何应当有一个统一标准,或至少有个相对统一的标准,如果将不法侵害的时点寄希望于具体的个案审查,在当前自由裁量权运行不规范,法官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的背景下,必然会导致认定上的混乱。而坚持预备最后阶段说,以接近着手的预备行为为不法侵害开始的时点,则不仅能够有效克服这一问题,而且有利于实现认定标准的统一。当然,在具体案件中,对于什么样的行为才真正称得上最后阶段的预备行为也需要结合案件事实具体判断,但由于这是在坚持统一标准下的具体个案分析,因此与前述纯粹意义上的个案判断已有本质的不同。
第三,实践中有利于对不法侵害认定进行更加准确的定位。通过“预备最后阶段说”的折中,既可以将所谓现在的不法侵害适度扩张至包含“预备的最后阶段”,即接近着手的准备阶段,使不法侵害的认定不至于太过靠后,同时再辅以有效说中有效防卫的时点进行限缩,又可使认定时点不至于太过靠前,如此以来,不法侵害的认定便可获得更为准确的定位。例如,通过“预备最后阶段说”的扩张与限缩,不仅一种刚刚预先计划的或者还没有靠近未遂的预备性攻击行为不能为紧急防卫提供基础;而且当侵害一种法益的意志还没有向外部成为现实时,也不能认定不法侵害具有现在性。
值得提出的是,尽管“预备最后阶段说”在不法侵害始点的判断上具有前述一系列理论优势,但在解释论上难免也要面对究竟如何才能判断某一行为事实上已经到达预备的最后阶段,而不是一般性预备行为的质问。对此,笔者认为,可以结合主、客观两个方面进行判断。首先,从主观上看,只有当预备行为明确无误地征表不法侵害行为人的侵害意图时,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预备行为。否则,“在侵害一种法益的意志,还没有向外部成为现实时,就是缺乏一种正在进行的攻击(甚至缺乏一种攻击),应当加以拒绝(即不能认为存在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进而为正当防卫提供基础——笔者注)[13]。其次,从客观上看,只有已经与着手形成密切关系的预备行为才是进入最后阶段的预备行为,即该预备行为已具有显著的急迫性,如果不加以制止,则可能立即转变成现实的法益侵害。从防卫行为人角度看,如果不及时实施正当防卫,则将使防卫变得不可能,或形成重大困难,或使行为人陷入更大风险[6]。最后,从主客观相统一上看,最后阶段的预备行为必须同时满足:(1)预备行为能够明确地反映出不法侵害者的侵害意图;(2)行为人实施不法侵害的心理可以通过这一行为得到明确的确证;(3)该预备行为除了表明不法侵害外不能做出其他任何合理解释。基于此,前述为实施盗窃在家练习配钥匙尽管也是一种准备行为,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预备盗窃的最后阶段行为,因为该预备行为本身并不能明确表明行为人必然具有实施某具体不法侵害的目的,且客观上也未对法益形成急迫性侵害的危险。但是当行为人甲将手伸向口袋打算掏出手枪射杀乙时,该伸手拿枪行为虽然也是杀人的预备行为,但甲的杀人意图无疑已在该行为中得到确证,且乙的生命法益也因此而陷入了急迫的危险境地,如果不允许乙实施防卫,则乙极可能在刹那间即被甲射杀,因此,应当认定甲伸手掏枪行为已经进入到故意杀人行为的最后预备阶段,应当允许对其实施正当防卫。再如,某日傍晚,甲、乙、丙三个男人在人烟稀少的乡村公路上见丁女貌美如花,于是强行将其拉上面包车,意图劫持到郊外实施强奸,就基本犯罪构成而言,强拉丁女上车虽然不是刑法分则规定的强奸罪的实行行为,而只是为实施强奸创造条件,但考虑到人烟稀少的客观环境、面包车内封闭的犯罪场景及三男对一女的力量悬殊,完全有理由认为丁女已经切实面临遭受性侵的现实危险,甲乙丙三人强拉丁女上车的行为除了表明即刻就要对丁女实施强奸外已经不能再做出其他任何解释,因此,该种情形下,也应当认定甲乙丙行为已经进入到强奸行为的最后预备阶段,如果丁女实施反抗,进而造成甲乙丙三人伤害,也应当认定成立正当防卫。对此,尽管也有学者提出不同见解,认为虽然将丁女拖入车内时,甲乙丙已有强奸故意,但依照三人计划尚须等到郊外才开始实施强奸行为,因此,此时应当认为对丁女性自由之法益尚未形成直接、现实的侵害危险,而仅仅是间接之危险罢了,所以,一旦认定可以实施防卫,就可能造成实行行为着手判断过于提前[15]。但在笔者看来,作为危险判断对象的行为人意思内容,显然应当是行为人的故意而非行为人的计划,基于此,当甲乙丙基于强奸的故意将丁女强行拉上车辆,且基于案发当时特定的犯罪场景,应当足以认定其行为具有迫切的侵害法益的现实危险性,由此认定成为强奸行为最后预备阶段并无不当。
最后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坚持预备最后阶段说主张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这样的情况,即相对某特定犯罪而言,有些行为是预备行为,但如果相对于其他犯罪而言,其又成了着手的实行行为,该种情形下,相对于后者则应肯认不法侵害的现在性,允许对其实施防卫反击[16]。例如,为了杀人而侵入他人住宅,侵入住宅伊始就应当允许受害人实施防卫行为,只不过不是针对杀人这种不法侵害行为而已。
[1]张小虎.犯罪论的比较与建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28.
[2]柯耀程.正当防卫界限之认定[J].月旦法学杂志,2005,(60).
[3]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五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32-133.
[4]王政勋.正当行为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141-143.
[5]黄翰义.刑法总则新论[M].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0:173.
[6]王皇玉.正当防卫的始点[J].月旦法学教室,2011,(105).
[7]郑泽善.刑法总论争议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14.
[8]孙国祥.刑法基本问题[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283.
[9]黄惠婷.正当防卫之现在不法侵害[J].台湾本土法学,2001,(23).
[10]林钰雄.新刑法总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88.
[11]王皇玉.窃盗被害人之赃物追回权与正当防卫权——评最高法院九十一年度台上字第四00三号判决[J].月旦法学杂志,2004,(107).
[12]贾济东.外国刑法学原理(大陆法系)[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234.
[13][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总论(第1卷)[M].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432-433.
[14]黄荣坚.刑罚的极限[M].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9:90-93.
[15]陈子平.刑法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68.
[16]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95.
[责任编辑:范禹宁]
2016-06-01
张宝(1978-),男,河南驻马店人,讲师,刑法学博士。
D924.1
A
1008-7966(2016)05-01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