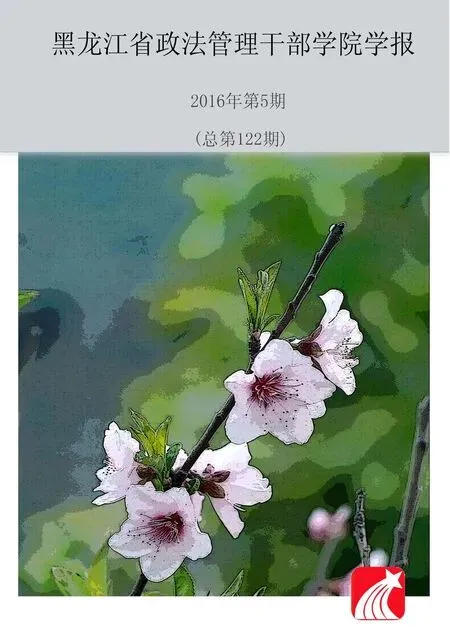政府权力清单规制行政权行使的困境和出路
——以行政法治的形成为视角
王 军
(山东师范大学 法学院,济南 250358)
政府权力清单规制行政权行使的困境和出路
——以行政法治的形成为视角
王军
(山东师范大学 法学院,济南 250358)
政府权力清单提出的目的是规制行政权的行使,在本质上仍然是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作为对行政权的控制工具。然而政府权力清单的构建,无法协调和处理好其所涉及的行政法相关关系,陷入了作为行政自制规则与法律的界限模糊、行政规则与行政裁量之间的失衡、弱化了司法有限审查原则的效力、行政公权对社会私领域造成了消极影响等多方面的困境。所以,以行政法治的形成为视角,结合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未来设想,规制行政权行使的出路在于:将政府权力清单仅仅定义为具有政府信息公开性质的,对各项公共权力进行统计的“明细单”,并通过权力清单的相关实践,为日后《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提供经验上的参考和方法上的铺垫。
权力清单;行政权行使;行政法治
一、政府权力清单释义
随着现代科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社会管理事务日益复杂,与之相适应的是政府行政权急剧扩张,几乎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行政职能不断强化,行政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明显提高,这一现象称之为“行政国家”。在行政国家中,政府或者行政组织的行政职权很可能会被滥用,成为权力腐败和效率低下滋生的温床,从而对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造成威胁。在行政国家时代,尤其对于我国而言,对行政权行使进行规范和控制是一个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的课题。因此,作为对我国行政“法治”实践进行总结的政府权力清单应运而生。
从法律属性上看,权力清单的权力内容具有强烈的实体性,作为能对行政相对人物质和精神利益造成实质性影响的政府权力清单,应该是一种具有行政自制性质的规范性文件。它是指有权主体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制定出来的,有关权力的种类、数量、适应条件、运行程序、行使边界的,具有内部和外部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
二、政府权力清单规制行政权行使的困境分析
要想使政府权力清单具有法律层面上的规范性和现实的约束力,必须协调和处理好行政法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其他国家机关、行政主体、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但这并不是权力清单本身所能完成的任务。政府权力清单作为具有行政自制性质的规范性文件为规制行政权行使,对法律规定的行政权进行重新分配和调整,触及与立法、执法、司法、社会私领域的权力边界问题,远远超出了它所承受的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拥有行政权,即可自由分配和调整”的设想很可能会陷入多方面的困境。
(一)作为行政自制规则与法律的界线模糊
行政自制规则是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基于自律,根据法律规定的程序制定避免行政权滥用、保障授权法目的实现的一般规则,具有法律的规范性和外部的约束效力。大陆法系国家的通行观点认为:行政自制规则具有法律的规范性和外部的约束效力的根据是行政惯例和平等原则,它通过在具体行政事项中长期稳定的适用而确立了同等对待的行政惯例,实质上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据此约束行政机关本身[1]。
根据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并由政府权力清单编制主体所处的层次可以看出,权力清单作为行政自制规则在法律效力上至多算是一个规章,是法律和法规的下位概念。初看起来,政府权力清单对“权力清单”的构建只是依法行事,但事实上它的编制依然取代了法律的地位和作用,造成了与法律的界线模糊。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权力清单的编制涉及相关行政权的增减、强化、弱化等内容,不论行政权力发生怎样的变化,无疑都是对体现立法者意志的行政权力法定化设置进行重新分配和调整,权力清单实际上修改和废止了相关法律,取代了原有法律的地位;第二,依据科学确权、清权厘权的原则对行政权行使的边界进行重新划定,也必然涉及对行政权的来源——法律进行本属于权力机关职权范围的解释的问题,事实上也变通了法律的规定;第三,对行政权的权力边界进行重新划定,必然会对行政相对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进一步会影响到法律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变通和修改了原有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法律的作用;第四,政府权力清单奉行“清单之外无权力”的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法律的适用,以权力清单作为行政权行使的相关依据。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作为行政自制规则的政府权力清单突破了与法律之间的界线,造成了两者界线的模糊,具有行政越权的可能性,从长远看来,这对我国行政法治的实现和相对人利益的保护是非常不利的。实际上,尽管在现代法治国家行政机关具有一定独立的权力场域,但这绝对不意味着行政机关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去修改或者变通法律的规定,对行政权进行配置,而突破自身与法律之间的界线。行政权的配置主要从以下视角得以体现:“一是基于宪法的视角,行政权的第一次配置即宏观配置是由宪法来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行政权的配置属于制宪权的范畴;二是基于法律的视角,是由宪法所完成的行政权力宏观配置在法律作用下实现的第二次分配,在这个层面上行政权的配置本质上属于立法权的范畴,其主体是立法机关”[2]。法律界限的严格性体现在制定主体的明确与一致性上。法律是由专门的立法机关通过严格的“立项、起草、审查、决定、公布”的程序制定,这样的法律才具有极大的权威性,由此而形成的法治秩序必须遵守,不得擅自违反或破坏。因为,法治即便不是最正确的选择,但对一个社会的稳定和持久存续而言,却是最好的选择。
(二)行政规则与行政裁量之间的失衡
在行政法理上,可以将行政裁量定义为:“所谓行政裁量,是指行政主体在适用法律规范裁断个案时,由于法律规范与案件事实之间的永恒张力而享有的由类推法律要件、补充法律要件进而确定法律效果的自由”[3]。而在法律规范层面上,行政裁量则意味着行政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内,根据具体行政事项的不同,对行政行为的实施有一定的选择空间。
作为行政规则的政府权力清单合法性的困境在于对行政权行使方式进行了过度细则化的规定,尤其是行政裁量行为。如果说行政裁量基准制度已经消解了自身的理论悖论,其存在还算合理的话,而在裁量基准基础之上,对行政裁量进一步细化和量化的政府权力清单,难免有狗尾续貂之意。
过度细则化的政府权力清单,一方面违反了授权法的规定;另一方面也不符合行政权行使的客观规律。从授权法的角度看,由于现代社会已经从自由主义时代的规则化和非人格化的形式正义转为以目的性法律推理为特征的实质正义。所以,立法者之所以授权给行政机关一定幅度的裁量权,乃是确保执法者能够根据行政具体情况的不同,运用裁量权作出相应的行政行为,以实现法定的利益和目标,达到个案正义和实质正义。而它的现实基础在于:其一,根据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意义上人类理性的有限性,立法者不可能穷尽所有细节对行政事项作出规定;其二,现代社会发展迅速,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社会管理的事务都与法律制定的初期有着很大的不同,法律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其三,行政主体拥有丰富的行政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相关经验,且具备实时的执法信息条件。对于行政机关而言,它具有怎样行使裁量的权力,但是绝对不享有取消、剥夺或限制自身自由裁量的权力,必须根据法律的授权目的行使行政裁量权,遵守法律的裁量权限,而过度细则化的政府权力清单明显违背了这一点。
从行政权行使的客观规律上来看,一方面“在没有行政裁量的情况下,法律相关规则本身根本无法应对现代社会和正义的复杂问题,裁量是法律和政府创造性的主要来源”[4];另一方面,裁量行为是行政权行使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占据了行政执法的所有领域,对每一行政事务都可能需要相应的裁量。行政事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必须赋予行政主体一定的裁量权。
行政事务的多样性表现在,随着现代“行政国家”的出现,行政权几乎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小到邮件运输、垃圾处理,大到建设工程许可审批、将人送上月球,无一不需要行政主体的管理。而行政事务的复杂性表现在,行政主体需要根据行政事务的具体情况做出相应裁量。就每一起行政案件而言,都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受制于多种因素发生的。行政主体进行行政裁量时,以行政事务具体情况为基础,至少应进行四个方面的判断:决定是否实施行政行为;决定实施何种行为;决定何时实施相应行为;决定怎样实施相应行为。第一,决定是否实施行政行为。对于有关违法进行生产经营的企业,行政主体应根据现场违法情况的不同,决定是否实施查封、扣押行政行为,还是仅仅进行一定的检查即可,对此行政主体有相应的裁量权。第二,决定实施何种行为。行政主体如何选择《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必须行使和运用裁量权,否则就会导致严重的不公。第三,决定何时实施相应行为。行政主体即便已经决定了要采取相应行政行为,但对何时采取行政行为,也必须进行裁量,否则在实现行政目标的同时,也可能会对行政相对人造成过多的不必要的损害。近期,为相应国家政府权力清单建设,海关总署于2016年4月7日发布《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清单》,将对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进行“正面清单”管理,而吊诡的是,文件正式发布距离正式实施的时间居然只有不到三个小时。此清单一出,舆论哗然,社会普遍认为海关总署应该提前告知将要出台“正面清单”,或者让清单的施行具有一定的缓冲期,否则将会造成电商进口的业务混乱。最倒霉的是已经在各大电商平台做好排期的供货商,很多货已经到达保税仓,就是进不去也退不出来,损失很大;同时有专家指出,政策突变背后最终埋单的仍然是普通消费者。第四,决定怎样实施相应行为。对于相对人的违法行为是秘密调查,还是公开进行?还是在实施行政处罚之前,召开必要的听证会?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这些行政执法方式,法律并不会做出明确的规定,而让行政主体根据具体违法情况的不同进行一定的裁量。
实际上,既然立法机关已经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赋予行政机关一定的裁量权,它就不可能再会对其授权处置的事务作进一步的具体规定,也就更不可能允许行政机关逾越或缩小立法机关确定的裁量边界,去对行政裁量进行规则化的细化和量化,否则就会违背立法机关赋予行政机关行政裁量的本意,行政裁量的空间就会大为压缩,甚至不复存在,行政裁量就无裁量可言。
(三)弱化了司法有限审查原则的效力
司法有限审查原则是指,为保证正义与效率的平衡,实现权力分立与制约的目的,司法机关对于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具有一定限度的审查权的原则。行政权的行使方式分为羁束行为和裁量行为,裁量行为又分为羁束裁量和自由裁量。在我国的行政法中存在羁束行为和裁量行为的区分,但不再对裁量行为进行细化。不过,羁束行为在行政行为中占的比重非常小,除此之外都是裁量行为,对自由度具有很大区别的羁束裁量和自由裁量进行区分还是有很大意义的,行政裁量与司法审查具有紧密的联系,有利于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权力场域进行判断,并决定是否给予司法审查。
在传统大陆行政法学中,要件裁量说和效果裁量说是对羁束裁量和自由裁量进行区分的基础理论学说,其中要件裁量说肯定行政机关在认定有待适用的法律要件时享有判断的空间,当然这里的“认定”必须是在真实发生的行政情境中才能进行,因为认定的法律要件不是一般性的,而是具有高度抽象性、具有终极目的的公益性内容。政府权力清单对公益性的法律要件进行规则化的解释和设定,实际上构成了对行政机关要件裁量的否定,否定要件裁量则意味着原本属于行政裁量的行为要全部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弱化了司法有限审查原则的效力,违背了授权法的目的和行政权行使的客观规律。
(四)行政公权对社会私领域造成了消极的影响
在法哲学意义上,政府权力清单在对行政权力进行重新梳理、调整和分配的过程中,事实上也同时触及了公权力领域与由行政相对人和对行政纠纷没有利害关系的其他社会主体共同构成的社会私领域的边界问题,并对社会私领域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具体体现在:首先,行政主体在具体的行政执法实践中,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判断才能体现立法者意志的权力行使行为,却在作为规范性文件的政府权力清单中提前设定,本质上构成了对社会私领域的侵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谁会成为行政相对人,以及行政相对人是否真正违法、以何种方式违法皆处在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之中,而立法者因知识和理性的有限性对此判断保持了沉默,通过赋予行政主体在行政违法事项发生时,有侵害他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可能时,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决定是否采取行政行为。在社会私领域,法无禁止即自由,并不需要效力远低于法律之下的政府权力清单对私领域的内容进行规范上的提前预设。法律只会是人类对自身进行驾驭的缰绳,而绝不可能是禁锢自由和权利的枷锁,在外部规则性的生活之外,人类还需要个体性的具有一定选择的私人领域,舍此,生活的意义又在哪里呢[5]?其次,将不宜规定在权力清单中的行政事项排除在前者之外,根据“清单之外无权力”的原则,行政主体不能对该事项进行管理,则社会因“权力的真空”而面临失序的危险,私领域的界限得到了不适当地扩大。2015年4月,河北邯郸市政府制定权力清单时宣布,除了依法需要保密的,如果哪项权力没经清理,就视为放弃,结果却陷入了“证明虽精简了,办事仍不省心”的困境,违背了权力清单制定的初衷。
三、政府权力清单规制行政权行使的出路探讨——以行政法治的形成为视角
(一)行政法治的核心内容
到底什么是行政法治呢?行政法治意味着社会存在一种稳定的、一致的、可以预测的秩序。这种秩序的关键在于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职权法定、依法立法、依法行政和依法裁判四个方面的要求是行政法治的核心内容。职权法定体现了法律与行政的基本关系,行政职权应以法律的规定为限,不得擅自扩大或缩小自己的权力界限;后三条则反映了行政机关应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制定规范性文件、行使行政职权和裁判行政纠纷。
(二)政府权力清单规制行政权行使的出路
在中国行政法的学术脉络中,对行政权行使进行规制的方法基本上分为两种:一是以杨海坤、杨建顺教授为代表的立法、行政及司法三重控制论的方法;二是章志远教授所认识和深化的作为规则之治的行政裁量基准的方法。实践已经证明,在中国特殊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境遇里,理想主义的三重控制模式难以奏效。而行政裁量基准规则和原则的匹配、实体和程序的融合,都凸显了基准作为核心控制术的地位,对此相关学者已有相当精辟的分析和论述。故本文不再对上述方法进行探讨,对行政权行使的规制应该另寻他路。
通过分析政府权力清单对行政权行使的规制所陷入的困境,以行政法治的形成为视角,应结合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未来设想,探讨其规制行政权的行使的出路。因政府权力清单问题的根源在于自身作为具有“法”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对法律规定的权力进行重新分配和调整,超出了自身所承受的能力。所以应将政府权力清单定义为一种对各项公共权力进行统计的明细单,仅仅是一个“清单”,赋予其政府信息公开的性质,并不具有规范性文件的效力。通过政府权力清单的相关实践,为日后《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提供经验上的参考和方法上的铺垫。
[1][德]哈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M].高家伟,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88.
[2]汪国华.中国行政法(总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84.
[3]王贵松.行政裁量的内在构造[J].法学家,2009,(2).
[4][美]戴维斯.裁量正义——项初步的研究[M].毕洪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89.
[5]谭志福.法律作为社会治理工具的正当性依据及其限度[J].山东社会科学,2011,(6).
[责任编辑:郑男]
2016-05-12
王军(1989-),男,山东诸城人,2014级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D922.1
A
1008-7966(2016)05-00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