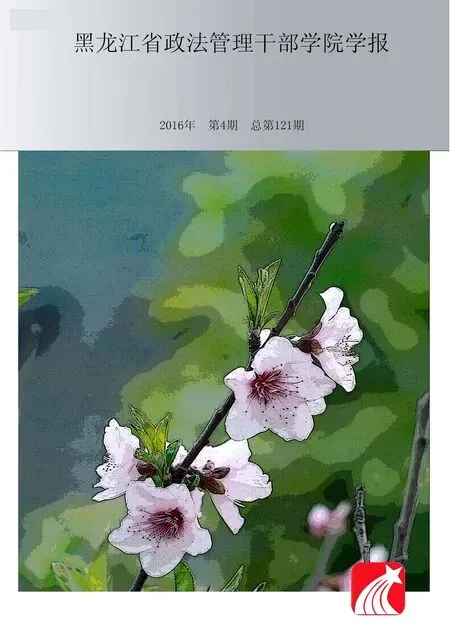论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公共安全的界限
程云欣(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上海200042)
论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公共安全的界限
程云欣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上海200042)
对于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公共安全的界定意义不仅在于理论体系的完善,也是指导司法实践的必然要求,为正确定罪量刑奠定坚定的理论基础。公共安全是指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以及重大公私安全,“公共”一词的本质是不特定,包括对象的不特定性和结果的不特定性,对“不特定性”的理解和把握是关键所在。
危害公共安全罪;公共;安全;不特定性
《刑法》将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规定在第二章,根据犯罪构成四要件的理论,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所侵害的犯罪客体为“公共安全”,而如何在司法实践中正确地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定罪量刑,区分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其他罪名,则需要我们对“公共安全”作出明确界定。
一、关于“公共安全”的学说
关于“公共安全”,学界一般将其分为“公共”和“安全”两个概念分别进行解释,笔者将其概括为哪些对象的哪些权利可以组合成为“公共安全”从而成为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客体。
(一)公共
理论上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论集中在特定、不特定、多数人和少数人四个观点上,而将前两个词和后两个词分别进行组合可以得出四个不同概念。传统的理论观点一般认为不特定多数人是公共安全含义内的。而特定少数人是明显可以排除出公共安全的范围的,这也是危害公共安全罪独自列为一章的意义所在,因此,学界的争议主要集中在特定多数人和不特定少数人是否能成为“公共”一词所划出的圈中的一员。在这种排列组合之下,学界形成了四种基本的观点:第一种作为传统理论通说认为公共安全指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1];第二种是指特定或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安全,而特定与不特定是一个对合性概念,这一观点应当是指当一行为威胁到多数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时,就构成了危害公共安全方面的犯罪[2];第三种是指不特定或者多数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的安全,在这一范围划分中,特定的少数人是唯一被排除在“公共”概念之外的;第四种观点认为范围限于不特定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财产的安全[3],这一观点将不特定作为必要要件,将特定的少数人和特定的多数人都排除在“公共”的范围之外。
分析以上几种观点,其中第三种观点所包含的范围最为广泛,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其他三种观点从各方面缩小了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范围。这一观点承认“特定性”的体系地位,否认了“不特定性”作为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根本特征。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则是类似观点的支持者。
在特定少数人必然被排除在“公共”范围以及不特定多数人必然被包含在“公共”范围内的情况下,笔者将针对特定多数人和不特定少数人列出学说以及笔者的观点。
1.特定的多数
针对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身体和财产是否能成为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客体这个争论,通常学者会举出下面这个例子:张某与王某有仇,计划杀害王某一家七口,某晚进入王某家中放置炸弹,最后炸弹将王某一家炸死。张某针对的是特定的王某一家七口,符合“特定多数人”这一概念,而他采取的行为是使用炸弹炸死他们一家,这个时候对张某是定故意杀人罪还是爆炸罪则需要具体分析。如果王某一家住在荒郊野外,张某明确清楚地知道使用炸弹不会威胁到其他人的生命、身体和财产安全等,那么定为故意杀人罪则符合《刑法》的规定;若王某一家住在闹市区,那么即使在最后只炸死了王某一家,也符合爆炸罪的特征。而这里困惑我们的是,行为人行为的定性为何会因为被害人的家庭住址而有所改变,借此笔者所要提出的观点是,通说中的不特定性不仅是表面上所侵害对象的范围是否特定,它还蕴含在行为人的行为当中。
如上述的例子,行为人针对的侵害对象是特定的,但是它采取的爆炸的手段,蕴含着侵害范围的不特定,如果是在闹市区,行为人对于其采取的爆炸手段所侵害的范围是不可控的,手段本身蕴含着不特定性。而与此相反的是,张某没有特定的侵害对象,在公共场所见人拿刀就砍,最后伤亡多人。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过这样的例子,同样的案例法院作出了不同的判决。笔者认为这里行为人应当被判故意杀人罪。尽管行为人在公共场所针对多数人进行了砍杀行为,但是他的砍杀行为是可控的,他的手段决定了他侵害的对象是特定的,而不是超出其控制范围的,会危及公共安全的。
关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不特定性,陈兴良教授认为它有两种表现形式,既包括对象不特定,也包括结果不特定。他还认为,特定与不特定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不特定性,并不绝对排除特定性因素的存在[4]。在仔细研读之后,我发现我所认为的特定性与不特定性是对合性概念与陈兴良教授的上述观点并不是冲突的。笔者认为特定性与不特定性是对合性概念是基于界定“公共”的概念上,而陈兴良教授所认为的特定性和不特定性是指行为人在行为过程中因素的定性,两种因素相互依赖,同时并存,也可以相互转化。
所以,利用陈兴良教授和黄振中教授的观点还可以解决的一个争论是,在电影院的一个放映厅放置炸弹以炸死自己的仇人,这种特定多数人的界定。这种行为以爆炸罪这一明显的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是否就意味着特定多数人应当被纳入到“公共”的概念当中?笔者认为不尽然,尽管此放映厅的人数是确定的,但是爆炸这一手段所带来的后果却无法确定,侵害的范围大小是不特定的,数量多少也是不特定的,笔者认为,可以用特定中的不特定来界定这一概念,即在表面上看,放映厅是一个特定的范围,人数也是特定的,但这仅仅是上限可以确定的不特定多数,并不能因此就认为特定多数人也是在“公共”的概念所涵盖的范围之中。
由此,笔者认为考察行为的性质,不能仅从表象上分析其针对的对象,还应考察行为本身的性质,即行为本身也蕴含着特定性和不特定性,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上都应当结合这两者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考察和界定,避免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2.不特定的少数
与特定的多数一样在学界引起广泛争议的则是不特定的少数是否能成为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客体中的元素之一。笔者认为不特定的少数这个概念本身就包含着行为人的行为不可能造成大范围的伤害,如在公共场所的石凳上放置不明显利器,谁坐上去谁就是侵害对象,范围不可能继续扩大,在此种情况下,受到侵害的对象为一个人,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定罪则不合适。
因此,笔者认为,不特定的少数不应当纳入到“公共”所涵盖的范围当中,否则违背了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本质内涵。
(二)安全
在上文提到的四种观点中,可以发现统一的是不特定的多数的生命、健康安全都是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客体,而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种观点提到其他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是否能包含于“安全”的范围之中。
首先,公共财产一般属于国家或者集体,对于公共财产的侵害则不免侵犯到多数人的利益,而这里的公共财产是否要限定为不特定的少数的公共财产则引起了争议。笔者认为公共财产不应限定为不特定的少数的公共财产,因为公共财产的性质决定了它本身应当成为公共安全的内在性质。而针对重大私有财产,有学者认为也不应当限定为不特定的多数的重大私有财产。他们认为决定其是否能成为公共安全内容的因素不在于财产所有人人数的多少,而在于价值是否重大,如果是重大财产,则不应以财产所有人人数少而将其排除在公共安全内容之外。而笔者认为无论是否重大,如果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无论是否重大,都应当以侵害私有财产类罪中的个罪进行适用。
另一个不同点是,有学者认为“公共生产、工作和生活的安全”也应当属于“安全”的应有之义。这些学者通过总结刑法分则当中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中所列罪名,认为如果不将其列入范围当中,那么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当中的有些罪名则“名不正”。笔者认为,对重大公私财产的解释不能过于狭隘。例如,行为人破坏了公用电信设施中的一个关键部件,尽管这个部件本身的价值不大,但问题不能孤立地被看待。破坏关键部位必然造成公用电信设施的崩溃,因此有理由认为该行为所侵犯的财产也属于重大公私财产的范围,而不能仅取决于其本身的价值。而且,笔者认为“重大公私财产”的含义可以囊括“公共生产、工作和生活的安全”,没有必要纳入到“公共安全”当中进行保护。
二、“不特定性”的认定
学界通说认为不特定性是危害公共安全罪名的最核心、最本质的特征,笔者在上文中也阐述了认为不特定的多数才是“公共”的核心内涵,因此,要判断某一行为是否能被以危害公共安全罪所评价,首先需要对不特定性的存在进行认定。
对“不特定性”的界定,我国刑法学界较为权威的观点认为“……不特定是一种客观的判断,不依行为人主观有无确定的侵犯对象为转移……”[5]与陈兴良教授的观点相似,他们同样认为“公共安全”包含不确定对象和不确定结果两方面的内容,陈兴良教授将其表述为对象的不特定性以及结果的不特定性。
在行为人的行为发生造成危害结果或足以造成危害结果的时候,我们一般可以看出受到侵害的对象,尤其是在已经造成危害结果的犯罪发生的时候,然而,我们要讨论的并不是受到侵害的对象是否特定,而是在行为人行为发生当时其所侵害的对象涵盖的范围,必须明确的是这不是一种现实性,而仅仅是一种预测可能性。下面笔者将通过对象的不特定性和结果的不特定性两个方面对“不特定性”进行分析。
(一)对象的不特定性
在解读对象的不特性的时候,我们通常会以行为人的行为对象为角度对此作出解读,并没有清晰地区分犯罪对象和行为对象,笔者认为区分行为对象和犯罪对象对解读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对象的不特定性是有帮助的。
学界的一个较有力的观点是“行为对象是指界定构成要件行为所要求的,行为直接指向的具体人或物,而犯罪对象是指能够表明犯罪客体存在形式的客观事物,是犯罪客体的现象形态,是犯罪客体要件中的构成要素,在犯罪构成中处于共同要素的地位”[6]。两者在我们研究某一犯罪构成的时候经常会发生重合的状况,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将行为对象和犯罪对象同一看待。
在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一章中,将各罪名按照行为对象可以划分为几类: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恐怖性质的犯罪;违反枪支、弹药、爆炸物、核材料管理的犯罪;破坏特定对象的犯罪以及重大责任事故犯罪。在这五类犯罪中,我们可以找到特定的行为对象,这也是在司法实践中判断对象是否特定的一个误区所在,所有行为都会指定一个潜在的特定的对象,而这里的对象是指行为对象,不是犯罪对象,我们需要明确的是预测可能性。行为人实施行为的时候,必定会侵害《刑法》所保护的某个特定的客体,而犯罪客体的载体及犯罪对象则是不特定的,这种犯罪对象的不特定成为了犯罪结果的不特定性的直接原因。
而犯罪对象的不特定性在实践中又呈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状况,这是由行为人的主观所决定的。一种是行为人主观上有特定的侵害对象,而在行为过程中由于其他客观因素的影响使得这种特定成为不可能从而呈现出不特定性[4],也就是上文中笔者所提到的行为人的行为中所蕴含的不特定性,将特定侵害对象的这个“特定”因素涵盖了,而使行为人的行为以及结果显示出不特定性;另一种是行为人的主观上不存在特定的对象,行为和结果则同样显示出不特定性。
(二)结果的不特定性
在对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不特定性进行探究时,最直接、最主要的表现莫过于结果的不特定性,其与对象不特定性并不是互相分离的,对象的不特定性可以通过结果的不特定性表现出来。
总之,不特定性是指一种预测可能性而非现实性,判别标准在于行为中是否包含不特定可能性的充分根据,而这种“充分”排斥抽象的、虚无缥缈的可能性[4]。同样,对危害结果的预测也不能局限于已然发生的结果,否则则会产生危害结果是确定的、特定的错误结论。无论是《刑法》当中规定的“已经造成了危害”还是“足以造成……”,都蕴含了行为本身具有的不特定性的共同特征,“足以造成危害”更能直接地凸显行为发展中有难以确定的不特定的结果的发生,而“已经造成危害’也包含有从结果中溯推行为之不特定可能性的内涵。
三、“公共安全”一元论
学界定义“公共安全”有通说,同时也有更多的不同的争论,然而学者们对“公共安全”的定义都是一元的,即学者们定义的背后都默认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这一章中所有的罪名所侵害的公共安全都分享着同一个内涵。
认为对“公共安全”应当作多元规范内涵的学者认为“一元论”在解释公共内涵时本身就产生了一个困境,学界争论的特定与不特定、多数人与少数人是忽略了此困境的。持此观点的学者否认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的很多罪名侵犯的是不特定人的权利,其论据是某些犯罪发生于特定的场所之中,这些特定场所只允许特定人员出入,针对此种空间场所或人员的犯罪侵犯的只是特定人员的安全,比如《刑法》第134条规定的重大责任事故罪和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第135条规定的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等。
持此观点的学者的第二个论点是并非所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都侵犯了多数人的安全,支持此观点的论据是《刑法》对交通肇事罪的规定,侵犯了一人的生命则构成交通肇事罪,明显说明该罪的成立并不以侵犯了多数人的安全为必要。
笔者对以上两个观点均持不赞同意见。首先,针对第一种观点即在特定空间场所犯罪不具有不特定性,笔者认为这属于上限确定的不特定性,即使能证明侵害的范围只可能限定在某一个范围内,也不能说明侵害的范围和结果就是特定的,如果这个观点成立的话,那么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的个罪在现实生活中,都侵犯的是某一个“特定”范围内的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如上文中所举的爆炸罪,若行为人选择在某一个特定小区安置炸弹,那么这个小区就是特定的范围,如此说来针对的也是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了。笔者认为持此观点的学者尚没有真正认识到不特定性的本质,以浅层面的特定和不特定对此进行定义,从而得出了荒谬的结论。
针对第二个论点,即并不是所有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都针对的是多数人。此论点的论据是交通肇事罪侵犯的可能是个别人的生命、健康安全。如在寒冬的午夜,整个公共道路系统中只有甲和乙二人,甲开车闯红灯过失撞死路人乙,本案中,甲构成交通肇事罪,但甲违章驾驶的行为只给路人乙一人造成了危险[7]。
笔者认为在这个案例中,即使是在寒冬的深夜,甲在公共道路上行驶也不能排除公共道路上还有乙以外的其他行人,这与在空无一人中的沙漠中行驶是不一样的,因为是公共道路系统,即使最后发现这个街道上真的只有乙一个人,也不能排除其违章行为可能造成结果的不特定性。
因此,笔者赞同统一的“公共安全”的内涵囊括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中的所有罪名,真正理解“不特定性”,在解释“公共”的时候是不会产生持“多元论”观点的学者所说的困境的。
[1]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338.
[2]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601.
[3]刘艳红.刑法各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49.
[4]蔡士良.对刑法中“公共安全”含义的探讨[J].湖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5).
[5]叶高峰.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定罪与量刑[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4.
[6]何秉松.犯罪构成系统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181.
[7]邹兵建.论刑法公共安全的多元性[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12).
[责任编辑:范禹宁]
程云欣(1994-),女,安徽宣城人,2014级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D924.32
A
1008-7966(2016)04-0045-03
2016-0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