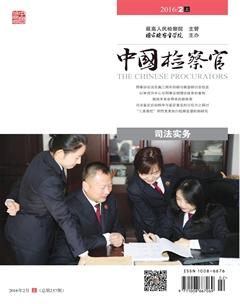中国刑事印证理论批判
2016-03-10 07:30:44周洪波
中国检察官·司法务实 2016年2期
周洪波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围绕“印证”来研究我国的刑事证明方法模式,这些研究造成的突出理论印象是:“印证”这一概念工具,在实证上能够较为具体地呈现中国特色刑事证明方法的类型特征;在规范上也能作为事实认定的具体判断标准发挥作用,尽管还应适当借鉴西方的自由心证方法。这导致“印证”一词在刑事司法实务中日益流行,且有泛滥之势。
刑事印证理论大致包括关于我国刑事证明方法的实证描述、对证明方法模式的归因解释和反思性规范立场的阐明等三个方面的内容。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我国刑事证明方法的整体特征的理解,刑事印证理论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第一,似是而非的模式标识。刑事印证理论对印证没有一个清晰的表述,其理解不符合常识见解。即便将印证理解为依据多个具有相同证明指向的证据综合判断认定事实,“印证”一词似乎能够标明我国刑事证明存在着“孤证不能定案”这种基本规范,但实际上这种规范要求也是似是而非的。并且对于什么是印证证明的完成状态,以及在都是依据多个证据判案时,在哪些情况下我国比西方国家对证据的要求更高,刑事印证理论更加说不清楚。第二,难以成立的归因解释。刑事印证理论对证明方法之成因的分析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第三,模糊不清的反思性规范立场。印证理论关于对印证模式的反思性规范立场的普遍共识是:在坚持我国刑事证明方法的规范传统的前提下,在不断加强程序制度建设的同时,逐步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的刑事证明方法,以及实现查证和认证方式从“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的转型。这种大而化之的共识缺乏实际意义。因此,学界仍需寻找替代性的模式理论来说明我国刑事证明方法所面临的转型问题。
(摘自《法学研究》,2015年第6期,第136-155页。)
*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610064]
猜你喜欢
青年文摘(彩版)(2023年15期)2023-11-20 15:26:47
中学生数理化·七年级数学人教版(2022年6期)2022-06-05 06:50:52
数学学习与研究(2022年2期)2022-05-10 00:05:46
甘肃教育(2020年6期)2020-09-11 07:45:38
武术研究(2020年3期)2020-04-21 08:36:54
北京心理卫生协会学校心理卫生委员会学术年会论文集(2018年1期)2018-05-10 09:49:08
新课程·下旬(2017年11期)2018-01-22 08:54:49
数学大世界(2017年31期)2017-12-19 12:29:42
继续教育研究(2014年1期)2014-02-27 16:10:18
法律方法(2013年1期)2013-10-27 02:2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