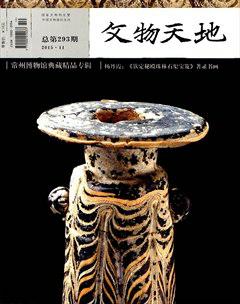杨丹霞:《钦定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著录书画

《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是以康雍乾三朝的宫廷收藏为基础的著录书,说白了就是一个宫廷收藏书画的帐本。
《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从乾隆到嘉庆时期,一共编了三次。本次讲座主要介绍关于它收藏的书画来源、著录书画的编撰体例、收藏书画的概貌,以及围绕着它著录的书画,乾隆和他的臣工们进行艺术鉴赏和书画创作等等情况。当然也包括嘉、道之后,特别是溥仪时期,《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向民间、向海外流失甚至散佚的情况。
清代内府收藏书画集大成的体现,就是这套《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的编撰。内府收藏法书名画到了乾隆晚期到达了高峰,从其搜罗的丰富,涵盖时代的悠长,它所收集的书画品质的精良,还有它著录的详实,著录书的水平之高,都是超越前代的。
《秘殿珠林》主要著录的是清代皇帝、清代臣工及历朝历代的书画家宗教题材内容的书画、缂丝线绣书画,也就是说道教和佛教的。在道教和佛教大类中,再分别时代、作者、装裱形式著录。而《石渠宝笈》著录的则是除了宗教题材之外的皇帝御笔、清代臣工的书画,还有历代书法绘画名迹,其他则有拓本、刻本、织绣品等。
这三次编撰,初衷与涵义各不相同。用我们现在时髦的话说,“初编”是清代建国百年以来较重要的一个文化艺术工程。从乾隆八年开始编《秘殿珠林》,乾隆九年开始编《石渠宝笈》,整个“初编”完成是在乾隆十年。“续编”完成于乾隆五十八年,是乾隆退休之前用了十来年的时间对自己收藏的全面总结。“三编”主要是他的第十五子顒琰即嘉庆帝,将他继位后陆续收集的民间的收藏,以及整理的在乾隆生前没有录到《石渠宝笈》“续编”和《秘殿珠林》“续编”的一些作品,本来就是在宫里的,比如说好多清三代皇帝的御笔等,当时乾隆没有编人“续编”,在嘉庆二十一年完成“三编”的时候,就入到了“三编”里面,这是嘉庆对他父亲的鉴赏方式的效仿、致敬。
不管怎样,无论是乾隆还是嘉庆的三次编撰,有一个主题是不变的,即一切的编纂、鉴赏活动都是在乾隆的主导下,即便在他死后,也是在他的鉴藏理念的指导下进行的。乾隆对于书画鉴藏、创作的兴趣爱好,伴随了他一生,也主导和决定了《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的拣选、编撰。
由皇帝主导和参与的《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其十几人的编撰队伍的名单中,《秘殿珠林》“初编”和《石渠宝笈》“初编”的人员是有重合的,核心的人物是张照,梁诗正、励宗万、董邦达、张若霭。他们首先是皇帝身边进士出身的的文学侍从,即“词臣”;其次,他们都有收藏,有的就是收藏家,而且他们或能写,或能画,或书画兼能。比如说张照、梁诗正,他们都是在康熙末年即已成名的书法家;张若霭、董邦达则是著名的画家,能作花鸟、山水,自成一格。这些“主编”自己都有收藏。特别是张照,出身名门世家,又是著名的大鉴藏家高士奇的外孙女婿。高士奇在嫁出外孙女的时候,很多重要藏品都被外孙女带到了张照家,这就特别像近现代中大家耳熟能详的书画家、鉴藏家吴湖帆及其夫人的那种情形。
“续编”的编者有王杰、董诰、彭元瑞等。其中董诰是书画家,董邦达之子,是乾隆晚期到嘉庆时期重要的词臣书画家,受到两代皇帝的恩宠。阮元,著名的金石学家,收藏家,把他自己参与《石渠宝笈》“续编”编撰的所见所闻记录在《渠随笔》里。彭元瑞则写得一手好书法,也有很不错的收藏。
“三编”的编者,主要是活跃在嘉道时期的一些词臣书画家。其中有收藏家英和,擅鉴赏,富收藏,有大量的古籍善本和书画文玩,在当时是重臣圈里的收藏翘楚。道光时因为皇后陵寝的事被抄家、流戍,藏品也进了宫廷。安徽的山水画家黄钺,也是一个鉴定家,眼力很好。从这些名字可以看出,这里集中了朝中的文学艺术精英。
两部内府书画著录的特点
通读《石渠宝笈》和《秘殿珠林》这两部内府书画著录,它具有什么和其他收藏家、前代皇帝不同的特点?我觉得有两点:
第一是分区储放。它的特色有三个:场所多、形式美、取用便。场所多就不用说了,皇帝的家足够大,宫内各处和多达数十处的行宫、苑囿,乾、嘉两帝有着无论是一般私人藏家还是前朝的古代帝王都无法比肩的藏品储藏场所。形式美是指大量的书画作品分区张挂陈设,除了那些宫殿集中存放书画的如乾清官、养心殿等处外,分区存放使书画构成了宫苑装饰的一部分,具备了与宫院的建筑园林、内部装饰格调融合互补、浑然一体的特色,是乾隆皇帝生活品味的象征和体现。利用便,因为它按宫殿区分布,将各处书画分区登记、著录,各区之内再按御笔宸翰、列朝名人、本朝臣工分类。“初编”在每个小类里面再对藏品的真赝优劣进行等级划分,所以它能够做到条理清晰、查找便利,满足了皇帝随时随地鉴赏、把玩的需要。
通过研究内府书画的分区储放,我们还可以了解书画的储放规律、皇帝在官苑中活动的一些特点。仅以《石渠宝笈》“续编”中的乾隆御笔为例,在不同的宫殿苑囿中,比如圆明园、宁寿宫、乾清官和重华官等处,是数量较多的。其中重华宫148件,这是他当亲王时候生活的地方;圆明园133件,则是每年春节最初几天在皇宫过完之后,元宵节之前就已经到了圆明园。所以,他春秋两季的时间是在圆明园等处行官度过的。从这些存放地点就可以看出他的生活和鉴赏,包括艺术创作的轨迹。
石渠著录书画的另一特色就是主题收藏。在很多宫廷苑囿当中,乾隆有意识地选择某些场所确立了一些收藏的主题。当某一个主题确立之后,会围绕一件作品或一组作品,展开对主题的再丰富、再创造。也就是说,他会率领他的臣工不断地围绕这个主题展开鉴赏、临摹等活动,使这个主题收藏在以古代名迹为核心的基础上更为丰富,而且也让这个主题更具他的个人特色。同时,主题收藏还会结合园林的营建,比如说狮子林、寒山别墅、竹炉山房,通过对书画名迹和江南名园形式多样的模仿再造,成为他继承先贤艺术余脉、流芳后世的载体。他做这些事时绝对是有“想法”的,并非像他自己说的什么“几暇怡情”而已。所以我们说这种主题收藏,不仅体现出乾隆颇具自信的鉴别能力,也反映了他的确是一位好古之心极重的皇帝收藏家,显示出他既讲政治又懂生活的个人色彩。
另外,乾隆也希望自己不仅是庞大帝国的统治者,也想要作为一个以儒家道统为中心的开明的、儒雅的、博学的仁君为后世所敬仰。因为作为一个异族的统治者,相对于中原传统的文化艺术,特别是中国书画,江南文人自宋元以来构筑起来的这种评判体系,他可能觉得自己不如那些士大夫们那么深入,但是他一定要做一个集大成者,他要以这种身份,来使他的收藏以及著录其藏品的《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更具权威性。
乾隆的很多主题收藏,都是因为得到某一件或一组作品而来。三希堂就是因为收藏了王羲之、王献之和王珣的《快雪时晴帖》《中秋帖》《伯远帖》三件晋人书法而得名。他还亲自撰写了《三希堂记》,敕命董邦达配图,图中不仅有他撰的记,还通过山水人物画的形式,体现他万机余暇优游山水林木之间,欣赏古人名迹的闲情逸致。
春耦斋在中南海的瀛台,就是后来慈禧太后关押光绪皇帝的地方。这里收藏了很多以农耕题材为主的历代画家作品,比如唐代韩滉的《五牛图》,明代项圣谟《临韩滉五牛图》,清代康熙时期重要的词臣画家蒋廷锡《临项圣谟临韩混五牛图》等三个《五牛图》,都在这里。但八国联军来了之后,这些《五牛图》和瀛台收藏的其他珍品就都散落在民间了。韩混《五牛图》是解放后政府花钱从香港购买回来的。
三友轩在延春阁,这里是因收藏了许多宋元以来以松、竹、梅“岁寒三友”为主题的作品而命名的。这些藏品包括元人《君子林图卷》,宋元人《梅花合卷》、曹知白《十八公图》,还有乾隆皇帝自己画的《岁寒三益图》、写的《三友轩诗》等等。而且这里的宫殿内外的装修,都是围绕着松竹梅的主题来设计的,各种陈设、屋外的绿植,都体现松竹梅这个主题。
学诗堂是因为贮藏了马和之画《诗经图》、宋高宗书诗经一共将近20卷而得名。乾隆把原来分散在养心殿、御书房等等地方各处存放的马和之画宋高宗书集中在学诗堂,亲自考订,分别真赝。也就是说他对这些书画的收集和鉴别,不满足于仅仅是搜罗,而是要研究。通过对于各卷的诗文考定、绘风判断,他共确认了真迹14件,其余的都是明人托名为马和之的伪作。之后,他再把这些作品统一样式,重新装裱,因为它们很多都是册页,他则把所有诗经图都裱成长卷并且固定了一种格式:前面有他御笔题四个字的引首,然后前后格水都盖上他的大印,每一段图原来都有号称宋高宗书写的诗经原文,遇有缺诗文内容的,乾隆自己还进行了补写。经过这么一番鉴别审定之后,他在作品上加盖了“石渠继鉴”这方印。大家要明白,“石渠继鉴”这方印,可不属于我们通常所说的《石渠宝笈》著录,什么“五玺全”、“八玺全”,不是的。这个印只是明确在《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初编”完成之后,乾隆进一步对部分书画进行再鉴定的成果,这印表明,他再一次鉴定,确认了。除了鉴别考订,当然还要发挥,他自己也尝试和词臣们共同临摹这些古代名品,比如,他和董邦达合画《豳风图》册,虽然画里的大部分都是董及宫廷画师来完成的,但是在题款时,皇帝一点也不客气。
避暑山庄中的婉娈草堂,则是因为收藏了董其昌的《婉娈草堂图》命名的。
还有著名的苏州狮子林,乾隆在北京和承德分头仿了两处,一处在圆明三园里的长春园,一处在承德避暑山庄。他还四次仿画石渠著录的所谓倪瓒画的《狮子林图》,五次南巡就拿这个画,到苏州狮子林去比对、吟诗、题画。故宫现藏狮子林主题的文物,一共有36件,有书法,有绘画,有的是石渠著录的,有的并不是,但石渠的藏品对园林建设的启发,对乾隆君臣、嘉庆君臣这种主题性的鉴藏、创作活动的带动,毫无疑问地丰富、拓展了收藏活动的内涵,并使得以皇帝为核心的鉴赏除了在藏品数量、质量无可比拟的“霸气”之外,也增添了不少文人雅趣。
虽非处处都是主题性的,但这种情形还有不少,如竹炉山房,如三处画禅室等。这个特色,是前代任何官方或私人藏家不具备的,加之藏品与园林建设、与创作活动的完美、有效的结合,构成了乾隆皇帝独特的睥睨千古的鉴藏方式,可以肯定,这是他对书画鉴藏史的贡献。
收录书画的数量
《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收录了多少书画呢?我们的前辈专家对于这两套书有一个统计:
历代名家书画6561笔(含缂丝、绣画290笔)、清代诸帝书画4232笔、清帝与臣工合作书画147笔、清代臣工书画2745笔,另外有历代碑帖拓本626笔、历代版本书籍850笔,以上合计13685笔。为何这里用“笔”来表述,而非简单的“件”呢?主要是三方面原因:一是石渠著录的特点决定的,二是石渠计件方式与现今博物馆计件方式不同,三是文物散佚严重。
《石渠宝笈》中许多藏品,是以一笔一笔的类似记账的方式著录的,而非现代博物馆保管意义上的件。现在博物馆的计件仅以书画作品为例,立轴、手卷每轴计一件,册页每册中的每开计一件。而石渠中很多藏品是组合,其中有的就是一件立轴或手卷,在著录中算一笔,但也有许多是数件组合,也算一笔。比如说“兰亭八柱”,包含八件作品,但是它在石渠中录为一件,也就是一笔。若按博物馆计件方式,那就是八件了。所以古今人计件方式是有差异的。
另外大量的散佚造成了计件的差误,特别是册页的散佚。在《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中对册页并非按开数而是按每册或每一组,记为一笔。组册,有的是四本的,有的多达十六本一组,也都算一笔。但是有不少册页都散失、分拆或残损了,比如周文矩《文苑图卷》,倪瓒《幽涧寒松图轴》,原本都是失群的册页,后来被改装成卷或小立轴,原来是一组或一本册页中的一开,但现在它们各自就算一件。
另外,手卷也有被拆分的情况。比如《元人君子林图卷》、王就《书颍川诗词帖》等。《元人君子林图卷》在解放后回到故宫,经过专家们考证,除了起首的李衍《墨竹图》和最后这一段元末明初王紱《墨竹图》,这一头一尾是真的之外,其余的这五段像柯九思什么的,都是明代人作假掺进去的,为了名头齐,多卖钱。古玩商卖东西时会跟买主说,这个时期能画竹子的大名头都在这了,多多给钱吧您呐。为了向公众展示方便,专家们决定,把起首的李衎的真迹保持不动,后面那些假也不碰它。最后一段王绂的真迹切出来单裱成卷。这么一来,就改变了石渠装裱的原貌,一件变成了两件,而石渠著录的“五玺”也就被分散在这两个卷里了,就是前面部分有四个印,后面王绂这卷有一个印。
王詵《行书自作颍川诗词帖》后面有苏轼、蔡襄和黄庭坚三家题跋,本来苏、黄的书法是真的,只不过不是题王就此件作品的,应是后代好事者从别处移来以增其价的,蔡襄的则是明人无款字被添加蔡款。结果乾隆一棍子把三个人的全定成伪作了,说“三跋皆伪”。因为三人题有真有假,且本就与王詵此卷无涉,故而此卷回宫后,专家们决定将王就卷后三家跋分别切出装成册页,这就成了一拆四了。
所以,这种一组一册变一开、一卷变几件的情形,按照现今的计件方式,肯定会与石渠产生抵牾,它要求我们一方面掌握石渠著录的具体情况,一方面也要明了石渠著录书画的现存状态,然后加以逐一排查核对,才可说清究竟有多少被著录书画散失了,又有多少被保存传承下来了。否则,简单、急切地见一个算一件,岂不知此件非彼件,那样计算出的数据是不可靠的。
除了数据,还有一种观点说,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没啥好东西,好的都让国民党运走了。我要说,这是无知。我想问问说这话的人,宫里的书画珍品是溥仪先挑的,还是国民党先挑的呢?溥仪偷盗出宫的东西陆续回到了故宫。除了没被偷盗、运走的,1949年之后,大量的石渠著录作品回归到故宫。比如王殉《伯远帖》、王献之(传)《中秋帖》、展子虔《游春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黄筌《写生珍禽图》、王就《渔村小雪图))、苏轼题林逋的《书法合卷》等等名迹。
当然,清代内府收藏的积累也有一个过程。从顺治一直到雍正,这些清代早期的皇帝,他们在书画方面的造诣一点不比乾隆差,清皇族成员的汉化是非常迅速的。顺治、康熙、雍正三位皇帝,不仅为乾隆的稳固江山打下了坚实基础,在文化艺术方面,也承袭了明末以来由大书画家、鉴藏家董其昌倡导的帖学书法、摹古风格绘画的“正宗”道路,这不仅体现在顺治的山水画的构图、笔墨上,也体现在康熙、雍正大量临帖书法作品上。清代历朝皇帝数万件书画作品,基本上都留存在北京故宫了,不但使我们可以窥见清帝书画的全貌以及内府收藏的线索,而且也能从他们的创作中深入探寻其创作与鉴藏的联系,尤其是乾隆。
内府收藏书画的来源
内府收藏书画的来源,不管是哪个朝代,无外乎以下几个途径:前朝旧藏、官员献纳、皇帝购买、抄家罚没。
顺治作为满族人关后第一代皇帝,接手了明内府的旧藏,今天现存的如宋徽宗《四禽图》、宋人《勘书图》以及米芾《行书三札》等,都源于明代宫廷的旧藏。康熙时,虽然未对宫廷收藏作系统梳理,但已注重对书画史、鉴藏史文献进行归纳总结。康熙四十四年,王原祁奉命任总裁,编修了《佩文斋书画谱》,书中对历代书画著录书进行了整理,对一些珍贵书画作品加以简要评述,但并未如《石渠宝笈》那样对书画作详细著录。雍正时期,已经注意对前朝皇帝御笔书法的搜集整理,但毕竟在位时间太短,只留下了少量的刻帖。但这些皇帝的积累,以及对后代继承者的教育、涵养,得以在乾隆时期光大,在藏品、研究和著录方面成就了集大成的辉煌。
与接手前朝旧藏相比,私人藏家的藏品构成了清内府书画庋藏的主要源泉。
明末清初的动荡,宫廷收藏向民间的流散,使一批有实力、有眼光的大藏家脱颖而出,异常活跃,如耿昭忠父子、宋荦、梁清标、孙承泽、安岐、高士奇、纳兰性德、博尔都等,他们的私藏最后都归了乾隆内府,另外还有许许多多知名的、没留下姓名的藏家,他们有的是被指定献纳,还有客气点的叫酌情价购,名义上是买,其实和白给也分别不大。比如像安岐,是当时的大藏家,因为他是大盐商,收藏的都是精品,从隋唐到两宋的早期的绘画就有680件套。这些东西,通过诗人沈德潜在中间斡旋,最后都以低廉的价格进入到了乾隆内府。
从顺康雍三朝的零碎搜罗,到乾隆晚期的大规模集中,不断地通过献纳、收购、罚没等方式,民间的收藏陆陆续续又从明代晚期的从宫廷向民间分散,逐渐运动的方向又反过来了,迅速从民间集中到了内府中,所以乾隆晚期,编“石渠续编”的时候,宫廷书画收藏达到了鼎盛。到了嘉庆年间,对于书画的收集,已远远比不上乾隆时期。一是由于那时民间收藏的好东西数量很少了,即使有个别好的,也都散落在皇帝无从寻找的那些人手里,秘而不宣,所以很难发现。二是即便像毕沅这样号称巨眼的大藏家,算是嘉道时期顶尖的了,抄他家的时候,得到的一些宋元名迹,也远远不能跟安岐、梁清标、高士奇这样的人比了,整体的数量、质量都比不上了。
明末清初有哪些大家的哪些藏品现存而且入了石渠著录的大致隋形如下:
耿昭忠父子: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马远《水图卷》;
张应甲:晋人《曹娥诔辞》;
王时敏祖孙:王羲之《寒切帖))、朱熹《城南唱和诗》;
梁清标:赵昌《写生蛱蝶图》、赵佶《柳鸦芦雁图》、王蒙《太白山图》;
高士奇:阮郜《阆苑女仙图》、赵孟頫《草书千文》;
顾复:黄庭坚《松风阁诗》、倪瓒《六君子图》;
孙承泽;
宋荦:郑思肖《墨兰图》、赵孟頫《红衣罗汉图>;
卞永誉:董源《潇湘图》、张即之《报本庵记》、王宠《草书离骚卷》。
这些从私人手中进入内府的珍品,经历了战乱、偷盗,其归宿各自不同,比如顾复旧藏的黄庭坚《松风阁诗》、倪瓒《六君子图》现藏台北故宫,宋荦的赵孟頫《红衣罗汉图》现藏辽博,而卞永誉的董源《潇湘图》则辗转流落到张大千手中,最后由政府购买使其回到故宫。
另外还有很多文化名流、贵族的收藏也进了内府,比如纳兰性德的藏品,赵孟頫《水村图》、赵孟頫《鹊华秋色图》、苏轼《黄州寒食诗》、朱芾《芦洲聚雁图》、董其昌《临古帖三种》等等,这还仅仅是入了石渠著录的。
另外,藏家中比较特殊的人物还有康熙皇帝最依赖的大臣高士奇。这位真是个奇葩,虽然康熙皇帝待他恩宠有加,但他献给康熙皇帝的没什么好玩意。属于他的著录书有两个,《江邨销夏录》和《江邨书画目》,前者记录了包括他鉴赏过别人的以及他自藏的名迹,后者则是他的私密账本。其中“进”字号的,是送给皇帝的,一共有51件,都挺便宜,而且有31件他自己就注明了是赝品,真的只有4件,其余的很多还没有说明。编书的时候有些东西已经进宫了。而且这一类书画最贵的才20两,和他标注要子子孙孙永保的那些动辄就几百两的,简直是天壤之别。比如《石渠宝笈初编》著录的文徵明《存菊图》卷在高士奇《江邨书画目》中注明“好而不真,三两”,属“进”字号书画。又如“石渠续编”著录为“兰亭八柱”之一的唐柳公权书《兰亭诗》卷,则注明“绿绢本,真上上神品。一百两”,这不是进的,后来归了他的外孙女婿张照,但是张照死了之后,他的后人没能守住这个宝贝,流入到了宫廷。高士奇的这个秘密帐本在20世纪初被罗振玉发现。
除了献纳、购买,还有就是抄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就是嘉庆四年抄湖广总督毕沅家的东西。
其实,皇帝自己也是一个私人藏家。在他在当宝亲王时,就已开始了书画收藏,他五岁开始写字,十九岁开始画画,因而对书画一道关注尤甚。他年轻时期的藏品不多,进入石渠的藏品有:唐寅《山静日长图》、王原祁《山村雨景图》,
还有一组巨册叫《绘事罗珍》十八册,每册十二对开一字一画,这一组十八本在《石渠宝笈》中计为一笔。从慎郡王允禧以下几十位,都是在雍正时期最著名的贵族、官僚、画家,诗人,各擅胜场。他皇子时期收藏的作品都有“乐善堂图书记”印,而这个印,也为我们了解和阐释乾隆对于古人传统的崇尚,对搜集整理书画以及编纂《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的准备和积累等提供了可能,把编纂石渠看做是他筹备已久的文化工程,也是不为过的。
编纂体例
《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作为著录书,体例是非常完备的,它主要参照了《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和高士奇的《江邨销夏录》等前人的详尽客观的优点。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编纂体例和三次编纂体例的异同:
“秘殿初编”和“石渠初编”相似。“秘”是最先编的,按当时书画贮存处所分类别收录,如乾清官、养心殿、御书房等处。藏品则依类排次,先后为四朝宸翰、历代名人、历代无名氏、古代缂丝及绣织书画几类。作者则各按朝代以千字文编号。每类之内分式排次,按书册、画册、书画合册,书卷、画卷、书画合卷,书轴、画轴、书画合轴进行排列,每一装裱形式中,再按时代早晚编排。“石渠初编”体例的排列次序为顺康雍乾四朝宸翰、历代书画则以列朝、无名、本朝;再依次为册、卷、轴、书画合璧。按上等、次等以周兴嗣千文中一字编号,依照《秘殿珠林》体例。
初编中藏品皆鉴别等次,分上等、次等,每个等次按装裱形式归类。上等为确系真迹、笔墨至佳者。纸绢、尺寸及跋语、鉴藏图章全部载入。次等为虽系真迹而神韵稍逊,笔墨颇佳而未能确辨真鹰者,只载款识及题跋人姓氏,余不全录。特殊的则有三种:数本相同者,真迹俱入上等;不能确辨真脱而笔墨并佳,入上等待考;确为后人摹本,但果能曲肖,亦人次等。
凡是顺康雍乾四朝皇帝宸翰,则以册卷轴分类,其中标题典重者居首,临摹古人的作品,则按照所临古迹早晚为序。皇帝继位前的作品,附在宸翰之后,不以编年为序。有康熙、乾隆皇帝书写题签、题跋的作品,录在各项著录之后,不与其他人题跋等同一例。
各朝书画家依其朝代、生卒早晚录入。清代的以作者年岁先后录入,不以作者的官僚、隐逸、女史等身份分类。凡遇到那类旧传失款、无款书画,有名人鉴跋无疑为某人者,则以无款或未署款书之,归在列朝有名人书画一类。名人鉴跋不可信的,则分别时代,归入无名氏一类。
被定为上等的作品,除了题跋者印章之外有文必录,包括要记录本幅尺寸和题跋全文,跋者只署别号、印章的,必要考订出其姓名;无可考证者则录题句云、跋语云,直录其题跋之词,而不妄断附会,以待存考。次等品,只记作者题识,不录印章。有御笔题跋者要详录;其他人题跋只记录“某题一”、“某跋一”,不录全文,不录尺寸。
具体到一件作品的著录,顺序按照先本幅,记录它的质地、书体、画之色墨、本人款印、本幅上他人题跋和藏印;然后录册页前后副页和尾纸(或手卷前后隔水、引首、尾纸;轴的裱边、诗塘)题跋印章等。作品的题跋、印章,按照其所据位置依次记录。前代内府印录为“某玺”;名人印章录为“某印”。
“秘殿”和“石渠续编”抛弃了“初编”分上下等次和用千字文编号的方式,不管什么作品,都是有文必录,并且把参与编纂的臣工们的鉴定意见以题跋形式附录于每件书画之后,对于书画现状逐件如实记载,每件收录的书画加盖的“续编”所用内府诸印玺也一一录入。
“三编”除上述部分宫殿外,大都收录延春阁的贮藏,并收入热河行宫避暑山庄以及皇家庭园等处的贮藏。
“秘殿”和“石渠”的用印是有规律和规矩的,俗称的“五玺全”、“八玺全”的就是指曾经秘殿或石渠著录书画上的用印规格。一般而言,各编用印的规律是以下这样的:
《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初编”著录书画的印记:1.“乾隆御览之宝”朱文宽边大方印(或“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2.“石渠宝笈”朱文长方印(或“秘殿珠林”朱文长方印);3.“三希堂精鉴玺”朱文长方;4.“宜子孙”白文方印;5.“乾隆鉴赏”白文圆印。以上称初编“五玺”。另外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印,即6.“XX宫(殿)鉴藏宝”或白文或朱文印,用以显示该件书画的收藏处所,俗称“殿座章”。以上加在一起统共是六枚印章。
“续编”用印则在“初编”的基础上增加“石渠定鉴”朱文圆印、“宝笈重编”白文方印。另外“殿座章”会相应更改为如“宁寿官续入石渠宝笈”等。“三编”因为是嘉庆年间收录的,所以会钤盖效仿乾隆的那套形制的嘉庆内府鉴藏印:“嘉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嘉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其中“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特别像乾隆的那套,但要仔细分辨,在字形、篆刻的细节上还是有不同的。要注意的是,现在皇帝御笔在市场上很热,《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各编中收录的清代各朝皇帝御笔书画,是不钤盖“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等印玺的,只钤盖“石渠宝笈所藏”或“宝笈三编”等朱文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