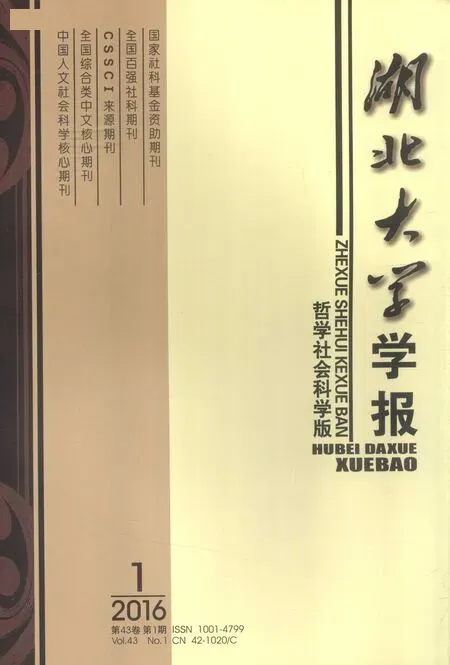顾炎武与函可之比较研究
陈友乔(惠州学院政治法律系,广东惠州516008)
顾炎武与函可之比较研究
陈友乔
(惠州学院政治法律系,广东惠州516008)
[摘要]顾炎武和函可是明清之际著名的遗民,他们颇多可资比较的事实。就个人遭际而言,两人都经历了天崩地坼的鼎革剧变和多舛的人生忧患;就入清后的身份而言,两人都是著名的遗民,一为志在恢复的铁杆遗民,一为眷怀故国的遗民僧;就人格风范而言,两人人格俊伟,一为整峻端方的“人师”,一为宽厚慤诚的方外僧;就文化取向而言,顾炎武严厉批判王学空谈心性的空疏并及于禅学,视佛禅为杨墨异端,函可则主张儒佛相融相济,既无本质的区别,又不必水火相仇。两人青年时期颇多交集可能,因机缘错失,无由晤面。此外,不同地域的经济、文化,对两人人格、思想的影响颇巨。
[关键词]顾炎武;函可;人生经历;人格风范;遗民立场;文化取向
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自署蒋山佣,学者尊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函可(1611~1659),俗名韩宗騋,字犹龙,广东博罗人。二人虽一生于江南,一生于岭南,一为僧,一为俗,但作为同时代人,他们极具可比性:其一,就个人遭际而言,两人都经历了天崩地坼的鼎革剧变和多舛的人生忧患;其二,就入清后的身份而言,两人都是著名的遗民,一为志在恢复的铁杆遗民,一为眷怀故国的遗民僧;其三,就人格而言,两人人格俊伟,一属整峻端方的“人师”①梁启超指出:“我生平最佩服亭林先生为人,……但我深信他不仅是经师,而且是人师。”(参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0页。),一属宽厚慤诚的方外僧;其四,就文化取向而言,顾炎武严厉批判王学空谈心性的空疏并及于禅学,视佛禅为杨墨异端,函可则主张儒佛相融相济,既无本质的区别,又不必水火相仇。
一、多舛的人生经历
顾炎武与函可均以富家公子经历了天崩地坼的鼎革剧变和多舛的人生忧患,并对其人生产生重大影响。两人均有良好的家世。顾炎武出身于江东巨族。高祖顾济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曾任行人、刑科给事中等职;曾祖顾章志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担任过按察使、应天府尹、兵部侍郎等职;祖父顾绍芳万历五年(1577)进士,历官翰林院检讨、知制诰等;嗣祖顾绍芾虽仅为监生,但才识过人,家富藏书,对顾炎武为人为学影响最大;本生父顾同应两中乡试副榜;胞兄顾缃崇祯六年(1633)举于乡,“以诗文为海内所宗”[1] 164。函可出身于岭南世家大族。高祖韩孟魁嘉靖七年(1528)举于乡,官户部主事;曾祖韩俦岁贡,任福建邵武府学训导;祖父韩鸣凤,万历元年(1573)举于乡,初任高邮州知州,改任沅州知州;父韩日缵,万历三十五年(1607)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谥文恪;叔祖韩鸣金、韩鸣銮、韩鸣雷、从父韩晟、韩晃(均系鸣金子)、从兄韩如璜、韩如琰(均系韩晟子)、弟宗驎为举人。“文恪公立朝二十年,德业声施在天下,门下多名儒巨人,故师得把臂论交”。这些是顾炎武所无法比拟的。
两人均家境优裕,并有着美人香草、诗酒流连的经历。顾氏尽管“嘉靖间,家道中落”[2] 29,但仍不失为殷实之家。崇祯末年,顾炎武一次就“以遗田八百亩典叶公子”[3] 232,足见其时经济状况之一斑。顾炎武十七岁参加复社,俨然一副名士风流的做派。他后来回忆,“未登弱冠之年,即与斯文之会。随厨俊之后尘,步杨班之逸躅”[2] 56。函可青少年时期生长富贵。韩日缵曾购义田赡养族人,“祖法文正公之义举,以宦囊
所积,建附郭腴田若干亩”(《博罗韩氏族谱》第八册,光绪丙申重修大宗祠藏版)。此外,还建有韩氏义塾、书院“文蔚堂”等。陪侍其父期间,十六岁的函可即与南都党社胜流如顾与治、杜浚、余怀、邢昉等在秦淮河畔一起饮酒、赋诗。对于这段风雅的生活,函可在流放辽沈期间仍念兹在兹。他在《怀江南》中有句:“多情最是秦淮鼓,梦里声声到海滨”[4] 364。
两人均经历了鼎革剧变。清军南下,铁蹄所至,激起了江南士民的激烈反抗。这场浩劫,给顾炎武留下了终身难以抚平的创伤。昆山城破之时,清军屠城,生母何夫人被砍断右臂致残,胞弟顾缵、顾绳遇难。常熟失陷后,嗣母王夫人绝粒而死。函可经历了明清鼎革的家国兴亡。在鼎革丧乱中,函可家族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其弟驎、騄、骊以抗节,叔父日钦、从兄如琰、从子子见、子亢以战败,寡姊以城陷,妹以救母,騄妇以不食,骊妇以饮刃,皆死。即仆从婢媵,亦多视死如归者”[5] 352。
除了国变之外,顾炎武先后经历了家难、陆恩案、黄培诗案等祸患。缘于宗祧继嗣制度下财产继承的矛盾,觊觎家产的从叔顾墅、从兄顾维等一伙族人屡构家难。构难者“先是纵火,继之以抢劫,再就是买通官府打官司,最后是暗杀,企图置顾炎武于死地”[6] 89。顾炎武“一家三十余口,风飞雹散,孑然一身,无所容趾”,“欲求破屋数间而已亦不可得”[2] 193。
陆恩案与家难相联系。族人的攘夺,令顾炎武“百忧熏心”[2] 225,不得已将田产八百亩典于里豪叶方恒。叶氏乘人之危,不仅压价,而且迟迟不肯支付;在顾炎武多次催讨之后才给了十分之六的价款,拒绝支付余款。入清后,叶氏见顾家势衰,便与顾氏世仆陆恩勾结,企图以“通海”的罪名借清廷之手除掉顾炎武,谋夺其田产。顾炎武获悉二人阴谋后,率人将陆恩沉水而死。叶氏“执宁人囚诸奴家,胁令自裁”。在朋友的帮助下,顾炎武得以移交松江府审理。最后,松江府“坐宁人杀有罪奴,拟杖而已”。叶氏不甘心,一面派人行刺顾炎武,使其“伤首坠驴,会救得免”;一面唆使陆恩遗属“乘间动宁人家,尽其累世之传以去”[3] 232~233。
北游期间,顾炎武因黄培诗案而第二次身陷囹圄。姜元衡(清翰林,历官直隶提督学政)为山东莱州原明兵部尚书黄嘉善的家仆黄宽之孙、黄瓒之子,为翻主仆名分,告发黄培(黄嘉善之孙、明锦衣卫都指挥使)及其从弟黄坦(现任浦江知县)、从侄黄贞麟(现任凤阳府推官)等十四人“逆诗”一案。该案最初并没有涉及顾炎武。后来,把大桑家田产抵押给顾炎武的章丘人谢长吉为夺回田产,与姜元衡勾结,以顾炎武与黄家结络刊刻“逆书”为由,将顾氏告上公堂。后来结案,黄培被判绞刑,顾炎武在亲友的帮助下保释出狱①参见鲁海:《顾炎武山东入狱考》,《清史研究》1994年第2期;许苏民:《顾炎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146页;陈祖武:《顾炎武评传》,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115页。。受此次文祸的牵连,顾炎武吃了不少苦头,几乎丢掉了性命。
函可则经历了“私携逆书”案等两次文祸。“私携逆书”案是清代的第一宗文字狱。顺治四年(1647)九月,函可拟从南京返粤。他持招抚江南总督军务大学士洪承畴所发印牌过城门时,被守城军士发现携有《再变记》及弘光帝答阮大铖书稿等有碍物品。驻防江宁的满人昂邦章京巴山与洪承畴有隙。他立即对函可刑讯逼供,想罗织罪名,借机排挤洪氏。函可忍死不吐,巴山不得已将函可交由洪承畴审理。洪氏为避嫌疑,将该案移送北京。最后定案,将函可流放沈阳,令于慈恩寺“焚修”②参见张玉兴:《函可》,《辽海历史名人传》,辽宁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382-392页;杨权:《岭南明遗民僧函可“私携逆书”案述析》,《学术研究》2006年第2期。。此后,函可在砂碛苦寒的恶劣生存环境下度过了长达十二年的流人生涯。
更令函可没有料到的是,他生前因文字罹祸,身后也在劫难逃。乾隆四十年(1775),即函可逝后116年,清廷查缴禁书,大兴文字狱,“凡函可住过的寺庙及双峰寺所遗碑塔,尽行拆毁,连《盛京通志》中所载事迹也逐一删除。所著《千山诗集》、《千山语录》被列入禁书”[7] 210。
二、共同的遗民立场
遗民是中国历史上一种重要的政治、文化现象,在明清易代的大背景下尤为瞩目,重要的原因在于,“其中的杰出人物,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所提供的深度;他们将‘遗民’作为现象的重要性大大地增强了”[8] 216。在易代之际激烈的儒佛之争的背景下③赵园分析了明清之际士大夫对佛教的优容、禁绝、会通等三种主要态度。(参见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256页。),顾炎武和函可虽一主辟佛,一主儒释会通,但他们
有着共同的遗民立场。
顾炎武和函可都参加过抗清斗争。清军南下,顾炎武和同时代很多士人一样投身如火如荼的抗清斗争。他用诗歌描绘了这一动人的历史场景:“戈矛连海外,文檄动江东”[2] 265。他还先后接受弘光政权、隆武政权的任命,有着“从军于苏”[2] 113的战斗经历。函可虽没有像顾炎武一样“出入戎行”[2] 162,但其忠行义举没有丝毫逊色。甲申之难后,函可不惮艰险,往返于广东、南京之间,似有“为当时粤桂反清运动奔走游说”[9] 960的意图。南都沦陷时,函可以大义激发士大夫起而相抗,“当是时,金陵初下,诸朝士荐绅阖户不出。师服缟练衣,持拄杖,痛哭其门,大呼曰:‘志不可降,时不可失!’闻而感激殉节者十数人”(丁澎《扶荔堂文集》,康熙十九年刻本)。因“私携逆书”案被流放辽沈,函可诗以明志,“博浪偶不中,甘心东海尘”[4] 38。
在交接这一遗民生存方式的大关目上,顾炎武和函可持身较严。
顾炎武拒绝与清廷合作,态度决绝。康熙十年(1671),翰林院掌院学士熊赐履邀请顾炎武修《明史》。顾炎武“答以果有此举,不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矣”[2] 196。康熙十七年,清廷开博学鸿儒特科,令地方督抚举荐“学行兼优,文辞卓越之人”,由皇帝“亲试录用”[10]。由于鼎贵之甥——徐乾学、徐元文居间劝阻,顾炎武未上荐牍。为避免被清廷网罗,顾炎武从此绝迹不入都门。史馆重开之后,顾炎武听说史局有延揽之意,立即致书当道,以母命“无仕异代”峻辞,“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并严正声明,“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2] 53。顾炎武坚持决不仕清的底线,但他广交仕清之人,“是为了谋求同清朝官员的某种形式的合作,以实现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11] 179。流放辽沈期间,函可也有限地与仕清之人进行了交往。在交往中,函可遵循道义原则。与函可过从甚密的海城县王令,不仅勤政爱民,“天明野外劝农回,又向城头辟旧莱”;而且品格高雅,“一局残棋一卷书”,“未见便知非俗吏”。函可还与王令“更欲论诗情未慊,几回骑马入深山”[4] 334~335。而对于为清廷鹰犬的辽阳知府张某的到来,函可则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闲话无过四五句,寒泉连递两三杯”[4] 264。
此外,顾炎武和函可通过眷怀故国旧君、表彰遗民节士来抒发离黍之悲,进而表达对新朝的拒斥和对故国的认同。
顾炎武不顾南来北往的舟车劳顿,频谒明陵。“问君何事三千里,春谒长陵秋孝陵?”[2] 348顾炎武还以诗歌表达对故国旧君的缅怀。“下痛万赤子,上呼十四皇。哭帝帝不闻,籲天天无常”[2] 342。“悲号煤山缢,泣血思陵葬”[2] 335。作为思想家,顾炎武的深刻之处在于,他通过明代政治措置得失的探讨来曲折地表达其系心故国的情怀。在《朱子斗诗序》中,顾炎武指出,明代在对待宗人上存在着严重的失误,“庸疏舍戚,内羁而外亲”,以至于“举天子之宗,无一人焉任国家之事,……宁以四海之大,宗祧之重,畀之非族者而不恤”。一旦面临农民起义和满族入侵的严峻局势,“繇国家向日裁抑过度,无有强宗大豪如南阳诸刘,得以挠新莽之威而保先人之祚者也”[2] 34~35。
函可眷怀宗国,不惜履险蹈危。顺治二年(1645)五月,南都沦陷。函可将这段悲壮的历史记录下来,并以歌咏发抒国殇之痛。“和尚亲见诸死事臣,某遇难,某自裁,纪为《再变记》一书。复黯然形诸歌咏,时人多危之,和尚为之自若”[12] 14。函可缺乏顾炎武那样的思想深度,但君国之念已然根植于其心理的深层①函可在《答李居士书》中直陈出九死获一生的衷曲:“罪秃之心不过求所以为是人,庶几无愧于吾亲,庶几无愧于吾君,即无愧于孔孟,即无愧于佛祖。”(参见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子部第35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700页。)。在他的诗歌中,眷怀故国旧君一类的诗句触目皆是。“君父恩罔极,死生苦不辞”[4] 166、“先皇岁月余今夕,故国风光忆去年”[4] 172、“半壁久添亡国恨,翠华难系老臣心”[4] 173。
顾炎武和函可还大量表彰遗民节士。顾炎武一方面大力表彰遗民节士。在众多的表彰者中,其中有曾为东宫伴读、后隐于华山的宦官范养民。顾炎武嘉许其既有“伯夷、叔齐之所采薇而饿”的节操,又有“介子推从晋公子,既反国而隐焉”[2] 105~106的志向。顾炎武还表彰了吴其沆、陈子龙、夏允彝、顾咸正等一批慷慨死节的江南旧友。
函可表彰的遗民节士主要有三类:一是著名的忠义,如黄道周等。黄氏为韩日缵门生,抗清失败,被俘殉国。函可誉之为匡扶汉室的邓禹和虽为楚囚心系故国的钟仪,“邓禹几能扶汉室,钟仪终不改南冠”[4] 418。二是韩氏宗亲,如韩如琰等。甲申之变后,如琰谋起兵。张家玉东莞建义,如琰率五千人与其合力攻克博罗、归善二县。顺治四年(1647)博罗再陷,如琰不支,单骑走避园头镇姻亲家。举人朱庚龙将执以
献,如琰等赴水死。函可闻讯后,诗以哭之,表彰其忠义精神:“到死不知仁义尽,入江翻见发肤存。竟使崖门多气色,始看融县有儿孙”[4] 257。三是岭南旧游,如陈子壮、张家玉、黎遂球等。陈子龙,号秋涛,曾为永历朝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起兵攻广州,兵败被俘,不屈而死。函可将其比作誓不降元而死的宋臣李若水、陈文龙,“若水挝唇无二日,文龙指腹定千秋。忍将礼乐随身去,尽把心肝报主休”[4] 185。
在遗民生死的大关目上,顾炎武和函可都没有采取杀身死节的极端做法。顾炎武识见极为明通,并没有迂执于“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的道德律令。他反对轻率地捐生,主张留有用之身来承担儒者救世的使命①顾炎武的生死观,与他接受了江南“爱身”、“恋财”的市民意识有关,并由此发展为治生、经世观念。(参见周可真:《明清之际新仁学——顾炎武思想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41页。)。顾炎武在《与李中孚书》中指出,“天下之事,有杀身成仁者,有可以死,可以无死,而死之不足以成我仁者”。“时止则止,时行则行,而不胶于一”,“苟执一不移,则为荀息之忠,尾生之信”[2] 82。因此,在其诗文中,很少有祈死一类的遗民表达。相较而言,函可显得有些游移。一方面,他不赞成杀身以殉的做法。函可强调,后死肩负着文化薪传的使命。他在《得石云居诗文》中揭橥后死的意义:“尚论贵只眼,平生于此深。共传迁史笔,谁谅许衡心。后死亦无恨。斯文未丧今。遥怜孤子意,山水有知音。”[4] 143另一方面,函可承袭了以“不死”为耻的遗民心理。“罪深”、“罪大”、“罪秃”一类表达,在其诗文中触目皆是。“我忧不独在乡国,我罪当诛复何说”[4] 94。“罪大心方死,病多力渐微”[4] 144。“早知一世心归梦,恨不当年革裹尸”[4] 205。“罪过弥天予作俑,饥寒到死汝为邻”[4] 232。
三、高标的人格风范
除了共同的遗民立场之外,顾炎武和函可还以其高贵的行谊、崇峻的人格耀熠于历史的天空。就公德而言,他们都表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在国家危亡时挺身而出,希图以一己之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就私德而言,顾炎武表现出力行方正的狷介之性,函可则表现出宽厚悫诚的豪阔之性。
顾炎武与函可都具有源于仁的悲悯情怀。顾炎武是实学经世、博施济众的儒者,函可则是慈航普度、仁爱济世的佛子。
顾炎武有强烈的救世之心。他强调,明道是救世的途径和手段,救世是明道的目的和归宿。“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救世也”[2] 98。而士君子救世有两种方式,“救民以事,此达而在上位者之责也;救民以言,此亦穷而在下位者之责也”[13] 1084。易代之际,顾炎武有着与义经历。随着抗清事业的渐趋销沉,他“由原来比较积极地或明或暗参与南明抗清斗争,逐渐转换成消极对抗清朝的遗民活动”[11] 145。顾炎武并没有局限于一姓之兴亡,而是以更广阔的视域关注天下。北游期间,他历览山川,周游边塞,引古筹今,究明典章制度沿革,做有益于天下的学问。顾炎武的殷殷救世之情,老而弥笃。去世前几个月,他抱病建议当局,在陕西境内田赋征收实物,待青黄不接时再卖给百姓。这样一举而数得,百姓可免折价征银的额外负担,国课又不至出现亏空,还可以防止高利盘剥②参见顾炎武:《病起与蓟门当事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9页。。
函可也有着儒者的救世之仁。在国破家亡之际,函可“以忠孝作佛事”,九死一生,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大夫等”[14] 699。函可身上沉重的君国之思的道德包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天下意识的确立与展开③顾炎武具有自觉的“天下意识”,他明确地判划“亡国”与“亡天下”,但他并没有局限于狭隘的家国视域,而是以更广阔的视野关注天下兴亡,并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相对而言,函可基本上没有走出君国苑囿。这一差别,乃是地域文化、家庭背景、个人经历等诸多因素使然。(参见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正始”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56页。),但这并不妨碍他对生民疾苦的关怀。基于儒家的仁爱济世和佛教的普渡众生,函可以诗歌表达了对苍生的悲悯以及对清统治者的批判。《老人行》表达了八旗官庄喂马奴仆欲脱奴籍而不可得的痛苦:“儿孙丧尽亲戚死,剩此零星干枯骸”,“生守官园喂官马,死作泥土填官街”[4] 94~95。
顾炎武高扬“行己有耻”的大纛,以为立身处世的根本。他指出,廉耻是“立人之大节”,“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13] 772。顾炎武在立身处世的原则性问题上立场坚定,决不依违两可。不同于顾炎武的严苛狷介,函可则宽厚豁达,如其所云,“责躬宜独厚,责人宜用宽”[4] 302。
顾炎武坚持“能文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2] 97的原则,不登坛,不授徒。顾炎武痛切于王学末流空疏之弊,不管天塌地陷,只顾立坛招徒,一以讲学为事,终致国是日非,政权易手。为此,顾炎武奋不顾流俗,力辟讲学之风。“然欲使之效曩者二三先生招门徒,立名誉,以光显于世,则私心有所不愿也”[2] 47,终
其一生,顾炎武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58岁时,顾炎武应友人之邀,在德州讲《易》,这是他一生唯一一次公开讲学①张维华指出:“亭林是坚决反对讲学的……而这次在德州讲学,可以说是破格之举。也或许在讲学的形式上,不是招徒聚众,而是约集几个同好,共同讨论,而以亭林为主。”(参见张维华:《顾炎武在山东的学术活动及其与李焕章辩论山东古地理问题的一桩公案》,《山东大学学报》1962年第4期。)。作为博极群书、六艺该通的命世大儒,顾炎武的及门弟子寥寥可数②顾炎武的门生除潘耒之外,还有李云霑与毛锦衔(又名景岩)。(参见王广成:《顾亭林先生和他的门人》,《昆山文化研究》2014年第2期。),与黄宗羲的桃李灿然适成强烈的反差。
顾炎武不仅律己甚严,而且“与人过严”[15] 61。徐乾学在太湖开设书局,延揽人才,学生潘耒也在征召之列。顾炎武力劝不可,“在次耕今日食贫居约,而获游于权要之门,常人之情,鲜不愿者。然事世风日下,人情日谄。彼官弥贵,客弥多,便佞者留,刚正者题。今且欲延一二学问之士,以盖其群丑,不知薰莸不同器而藏也”[2] 167。
顾炎武不仅坚持为人之道,而且恪守为文之旨。顾炎武强调“有益于天下”的为文之旨:“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13] 1079。为此,他主张,“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2] 91。为此,顾炎武“悬牌在室”,“绝应酬文字”[2] 96,虽知交故友也不例外。如王山史所云:“行谊甚高,而与人过严。诗文矜重,心所不欲,虽百计求之,终不可得。或以是致怨,亭林弗顾也。”[15] 61
函可慷慨好义,待人以忠。在弃俗归缁前,函可“性好义,豪快疏阔”。有“贫士冤狱,自分死,师密白得免”。贫士最初以为是有司“廉断”而感激不已,“久而知韩公子所为”[4] 10。函可忠于友谊。顾与治是其江南旧友,在“私携逆书”案中,也受到了牵连。函可与其同生死,共患难,决不卖友求生。“与治与剩和尚生死周旋,白刃交颈,人鬼呼吸,无变色,无悔词”[16] 582。函可不仅笃于身前,而且忠于死后。山东莱阳左氏、明末抗清殉国左懋第之兄左懋泰,顺治六年(1649)流放铁岭。函可与其交游唱和,甚为相得。顺治十三年,左懋泰病逝。函可在雨中与众僧为左氏持诵经咒,寄托哀思。“梵呗鱼声混是泪,悲凉岂独自于今?”[4] 251函可还为左氏遗孤托钵,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帮助解决其生计问题,尽后死之责。其在《为左氏诸孤托钵》中云:
见说遗经那可凭,敝籝残帙恨层层。修文独取多愁客,乞食还馀未死僧。众口共餐朋友泪,游魂孤照法王灯。明知一粒须弥重,坐视饥号总不能。
函可坚忍弘毅,豁达从容。不同于那些“以佛门为逋逃薮”[8] 246的遗民僧,函可皈依佛门,不仅超然地面对苦难,而且积极地寻求人生的价值,智慧地安顿生命。系狱江宁时,函可以强大的佛性度越人间苦厄。“当事疑有徒党,拷掠至数百,绝而复甦者屡,但曰:‘某一人自为。’夹木再折,血淋没趾,无二语。观者皆惊顾咋指,叹为有道”[17] 283。函可并不消极避世,而是以积极的姿态弘扬佛法。初到沈阳,函可限于慈恩寺焚修。后应普济寺住持吾上人之邀前往“阅藏”,并为僧众“演《楞严》、《园觉》”两经,结果“四辈皆倾”[4] 15。此后,函可往来于沈阳、千山等地,“自普济,历广德、大宁、永安、慈航、接引、向阳,凡七座大刹,会下各五七百众”[4] 12。
四、各异的文化取向
顾炎武是旷世大儒,函可则是禅门高僧,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做出了不同的文化贡献。两人不同的文化创造,与其不同的文化取向密切相关。大体言之,顾炎武批判王学空谈心性而流于禅学,视佛禅为杨墨异端;函可则主张儒佛相融相济,既无本质的区别,又不必水火相仇。
顾炎武以“明道救世”为鹄的,力践“博学于文”之旨,追求“实际、实物、实效之学”[18] 33,摒弃“注虫鱼”、“命草木”的雕虫末技以及徒事记诵的“语录”之学③顾炎武在《与人书三》中指出:“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鱼、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语此也。”(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1页。)他在《与人书二十五》中指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8页。)他在《与施愚山书》中指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又曰:‘论语,圣人之语录也。’舍圣人之语录,而从事于后入,此之谓不知本也。”(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8页。)。为此,顾炎武主张回归经学传统,“以济理学之穷”[19]。一如清初的其他几大思想家,顾炎武将明亡责任归为王学末流的空疏,并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
判。“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流风所及,“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13] 402顾炎武还指斥心学禅学化的离经叛道。他引《黄氏日钞》指出,“孔门未有专用心于内之说也,用心于内”,不过“近世禅学之说耳”,“皆外人之学,非孔子之真”。为此,顾炎武对佛教大张挞伐:“而佛氏晚入中国,其所言清净慈祥之说,适有以动乎世人之慕向者。六朝君子从而衍之,由清净自在之说而极之,以至于不生不死入于涅槃,则杨氏之为我也。由慈悲利物之说而极之,以至于普度众生,超拔苦海,则墨氏之兼爱也。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而佛氏兼之矣。”从纯正儒学以及救王学空疏之弊的立场出发,顾炎武主张对那些将佛法奉为“內典”的“左道惑众之徒”进行严厉制裁,“先王所必诛而不以听者”[13] 1046~1047。顾炎武的辟佛,是建立在学术根柢之上,“顾炎武以考据手段辟佛,考‘体’‘用’二字在经传中的运用,证明释氏之窃吾儒;辨析‘内’、‘外’,指已成常谈的‘內典’的说法为非”[8] 251~252。这种治学路径表明,顾炎武“在绝境中也不放弃其儒者身份与使命感”[8] 255。
不同于顾炎武的视儒佛为水火之论,函可主张儒佛兼融①函可的这种姿态和论见,并非其独有。如有学者指出:“‘会通儒释’乃至‘三教’,作为一种思想、学术取向,由来已久,有明诸高僧多取这种姿态。”(参见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页。)。在函可看来,佛道与儒道一样,不离日用常行,极为平实。他教导徒众,探求佛法“不用远求,但向你平常日用中体究”。那种“教人瞅光看影、听天鼓、觅虚声”,不过是“一种无知外道”[14] 628。佛法是一种生存智慧,达到了出世与入世的一体圆融之境,“你若向现前日用中彻见得,佛法、世法打成一片。所谓入得世间、出得世间,出得世间、入得世间,又何儒佛之分不分耶?”[14] 629他还指出,佛道与儒道一样,也讲求忠君孝亲,经世致用。“学到彻头,文亦在其中,武亦在其中,事亦在其中,理亦在其中,忠义孝道乃至治身治人、安国安邦之术无有不在其中者”[14] 699。函可强调,儒佛的会通之处在于仁:作为佛道之旨的“自利利他,自他等利,正所谓仁也”;佛儒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儒佛异,而所以为人则同也”,佛家“虽不言仁义,然而与子言必止于孝,与君言必止于忠,未尝坏世间相而谈实相”,“何止六经皆仁注脚,三藏十二部皆仁注脚”。儒佛之争,究其根本,“是皆胸中无主,或恃己见,或徇他辞,以至同异纷然,戈矛遍界”[14] 697~698。函可进而主张儒佛相济,“但为真儒,即为真佛;必为真佛,始为真儒。文章、风节、学问、经济,无不在此”[5] 683。
五、余论
顾炎武和函可可资比较的事实缕析于前,但还有两个问题,似有申说的必要。
一是关于两人的交集。作为一时人杰,顾炎武和函可因机缘错失而未能谋面。两人在青年时期发生交集的可能极大:论年龄,两人年相若,函可长顾炎武两岁;论性格,两人都染有美人香草、诗酒流连的名士之性;论机缘,函可客游金陵时,“声名倾动一时,海内名人以不获交韩长公騋为耻”[4] 10,并结交了顾与治、余怀、夏允彝、徐枋等一批江南名士,其中的顾与治、夏允彝、徐枋等是两人共同的朋友。可以推断,两人应该是互有耳闻,只是缘吝一面。流放期间,函可虽与江南旧友鱼雁不断,但其行止被限于辽沈一隅,而顾炎武北游足迹最远也不出燕赵之地,两人更无晤面之机。此外,函可寿命不永,也是重要原因。法侄今种(屈大均)曾东出榆关访函可未得。康熙五年(1666),屈大均游雁门、代州时结识顾炎武。此时,距函可圆寂已经七年了。倘天假以年,函可得以生还入关,二人把臂论交,亦未可知。
二是不同地域的经济、文化对两人人格、思想的影响。顾炎武出生的江南,是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浓厚的商业气息,使当地人养成了重利精明的习性,这对于顾炎武形成人皆有“爱身”、“恋财”之心的自私自利观念起着基础性的决定作用②参见周可真:《明清之际新仁学——顾炎武思想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41页。。顾炎武经历的家难、陆恩案、黄培诗案等几次有性命之虞的祸患,都与其“所爱者身也,所恋者田宅货财也”[2] 193的价值观深有关系。这种自私自利之性,内在地包含着几乎贯穿于其人生过程之始终的追求人格独立与个性自由的人文精神,并通过治生表现出来③参见周可真:《明清之际新仁学——顾炎武思想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46页。。他的大至商业、田庄经营,小至私人借贷,都表现出斤斤于利害得失的计较。原因在于,“在他看来,只有经济上无求于人,才能保持人格上的独立”[20]。江南“锥刀之末将尽争之”[2] 141的重利之习,加之令士大夫闻之色变的奴变风潮④顾炎武经历的陆恩案、黄培诗案,均与奴变相关。在他看来,奴变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关乎政治、伦理。顾炎武系心于此,“人奴之多,吴中为甚。其专恣横暴,亦惟吴中为甚”。(参见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奴仆”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800页。),使得顾炎武对江南“心存偏见,而钟情于北方,尤其是西北,至死也不肯回故里昆山”[21]。
并且,由自私自利所显豁的强烈治生意识,为实证验印之学开辟了道路。由此,顾炎武崇实黜虚,“学尚‘渊综’、‘会通’,追求阔大的学术以至人生境界,学而经世,学而事功,学而待后王”[8] 366。就函可出生的岭南而言,白沙之学“神秘主义儒学传统与岭南地域的巫蛮之风有一种地缘交融关系,而与南禅宗的神秘传统直接相接”[22] 261,它与“浙宗”“在明清两代主导着岭南知识群体的意识形态”[22] 262。这样,使得岭南知识群体出入儒禅,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景①岭南儒学的禅学化,白沙之学即有明显的表现。屈大均记白沙高弟湛若水讲学,“甘泉先生尝开礼舍僧寺,……甘泉之学,务求自得者也。世之未能知,其知者且疑其为禅”。(参见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08页。)易代之际,岭南逃禅之风盛行。函可的师友中出入佛禅者不少,如函罡(曾起莘)、函机(梁朝钟)、函美(黎遂球)、澹归(金堡)、今种(屈大均)等,或为著名的忠义,或有“与义”经历,或弘扬佛法,导引遗民。。浸淫佛禅的函可,走上了不同于顾炎武学而经世的道路,即弘扬佛法,不立文字。此外,岭南奴变的程度要轻于江南②傅衣凌认为在珠江流域发生的奴变运动,是当时中国南方地区人民反抗运动的一个支流,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参见傅衣凌:《明清之际的奴变与佃农解放运动》,《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04页。)吴建新指出,在清人文集、笔记中极少记载奴变,只是在一些家谱、族谱发现。(参见吴建新:《介绍几篇家谱、族谱中的广东奴变史料》,《岭南文史》1988年第1期。)。函可没有经历奴变③函可的情形与顾炎武迥然有别。他家中两仆,“录用执役先子几三十年,道广亦不下十余年,生性淳朴,以故郭内外遗产皆其管理”。鼎革丧乱后,在函可“诸弟相继尽节,当事执二人迫其产”的情况下,二人私相语曰:“二三孤幼在,将何所存活?”因誓死不言,同毙于狱。(参见释函可、张春:《遥哭录用、道广二仆》,《千山诗集·不二歌集》,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8页。),他的乡国之思淀入骨髓,也就没有如顾炎武一样疏离祖居地,而对客居地产生认同感。
[参考文献]
[1]周可真.顾炎武年谱[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
[2]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归庄.归庄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4]释函可,张春.千山诗集·不二歌集[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5]屈大均.广东新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许苏民.顾炎武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7]罗志欢.岭南历史文献[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
[8]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9]陈寅恪.柳如是别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10]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11]周可真.明清之际新仁学——顾炎武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
[12]汪宗衍.明末剩人和尚年谱[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3]顾炎武.日知录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14]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第35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15]王弘.山志: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99.
[16]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四库禁毁书丛刊:子部第116册[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17]莞城图书馆.胜朝粤东遗民录·宋东莞遗民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8]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9]陈祖武.高尚之人格,不朽之学术——纪念顾炎武亭林先生四百年冥诞[J].文史哲,2014,(2).
[20]陈友乔.顾炎武北游期间的经济生活[J].兰州学刊,2009,(7).
[21]陈友乔.顾炎武北游不归的地域倾向性探析[J].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报,2008,(4).
[22]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责任编辑:李严成]
[作者简介]陈友乔(1972-),男,湖北仙桃人,惠州学院政治法律系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收稿日期]2015-08-13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6)01-009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