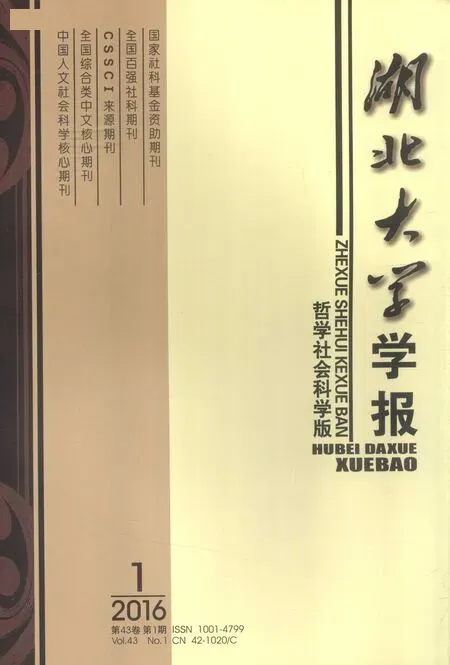品种·招魂·家园——在上海文汇讲堂的讲话
贾平凹
品种·招魂·家园——在上海文汇讲堂的讲话
贾平凹
原谅我用陕西话。陕西话可能有人不能完全听得清楚,不清楚其实对我是好事,可以遮掩我讲的不好。本来我是来上海开一个会的,没想被拉来做这场演讲。我是一生有两件事不自信,不自信了大半生,一是我的个头它总不长,二是在广众中讲话,年轻时人一多讲话就脸红,前言不搭后语,现在人老了,脸红已看不出来,要讲必须得有个讲稿。说到讲稿,首先是题目,李念先生当时来电话说你先出个题目,我胡乱说了个“品种、招魂、家园”。过后一想,这个题目怎么讲呀,我根本无法讲清,真是自己给自己下了套。为什么就定下这个题目?是我那时情绪很差,好多事正让我痛苦,看什么都不顺眼。给李念先生说了这个题目后,有人劝我去终南山修行一阵吧。终南山在西安城南,并不远,双休日西安很多人都去那里游玩。终南山却是中国很有名的山,有一个成语——终南捷径,就指的是那里的故事。终南山历来是佛道修行之地,现在仍有各种寺、庙、观、庵上千处,仍有近三千人在那里,或挂单,或自己居洞搭棚修行。我的一位老师就曾在那里学佛。这位老师在七十三岁时想到离八十只有七年了,离九十只有十七年了,生命快要结束了,就慌恐不安,夜里睡不稳,常会惊得出一身冷汗。他意识到要解决关于死的问题,要消除恐惧,建立新的生死观,就去了终南山学佛修行。我是去了终南山,那里有许多修行人我都认识,但我没有去学佛学道,我的尘缘还深重,而是在那里转悠了几天。大自然会疗治许多病的,许多病不是体质上的,也不是外来邪气侵害,而是心理上的,大自然会让你放松,让你沉静,我的情绪也就慢慢好起来。
有人说,人生是悲苦的,还举了例子,说人一生下来首先就是哭,又说你看看周边的人,谁一生顺顺
当当过?这观点的确影响到我,在生活中、工作中、写作上一受到挫折,一受到打击和不如意的事,就容易悲观。这种悲观情绪伤害过我的写作,老写不出满意的作品,伤害过我的身体,曾十多年一直病病蔫蔫。人是最易受暗示的,一旦受到暗示,就产生心理阴影,进而影响到身体,算卦是这样,诅咒也是这样。好多人就是看电视,电视里的人流泪他也流泪,好多人不能看惊悚片和关于鬼关于蛇的画面。我更是敏感体质,看电视里有炒菜,我就能闻见味道。有一个成语是“望梅止渴”,我真有感受。我有个亲戚,有一天来告诉我,他去陵园看他爹的坟了,发现对面的一个坟前新砌了一块石碑,这石碑会影响他爹的坟,心里不舒服,听说要在他爹坟前放一块石头可以抵消这种不利的,来问我放不放一块石头。我说,你已经有心理阴影了,那你就放,而且要尽快去放。人生是悲苦的这个观念,影响了我几十年。在我五十岁后,我想到另一个问题,就是:人生如果是悲苦的,来受罪的,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来世上呢?全地球五十多亿人,都是甘愿来受苦受罪吗?为什么活着都不愿意死呢?人到世上其实是来爱的。人来自哪里?来自爱,每个人都是在父母的做爱中产生的。活在这个世上,你所发生的一切,比如见到什么人,遇到什么事,都是对你有意义的。你见到花儿的时候,你心生喜悦,很爱花,其实花也一样喜悦,花也爱你。人是向往着美好来的,只是人来得太多,虽然太阳是无私的,它不因高低贵贱男女老少都照耀,但地方有限,食物有限,这才产生了竞争,有了恶和下贱的东西。同时太阳照耀了你也给了你阴影,你收获了麦子同时收获到麦草。人来到世上怎么在世上生活,有的很快适应,有的为了自保而伤害同类,有的遭遇了许多事变,这就是命运。大多数的人之所以称芸芸众生,就是顺波逐澜,糊糊涂涂过了一生;有的则坚持自己意念,这种人不论其好其坏,都是要成就一番大事业的。我一直坚信,有一些人是上天派下来给人群作指导的,历史上那些各个领域里的伟大人物都是这样。我说过,凡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集团,只要它能存在,其中必有一批人全心全意为这个国家、政党、集团做事的,他们绝不自私,绝不贪财,绝不好色。这如同一座房子有一根梁和四根柱子。我们称这样的人有雄才大略,是受命于天的,政治家有,军事家有,经济学家有,文学和艺术家也有。还有一种人,虽然不成就大事业,但做什么也是非常专注,成绩斐然,这就是人才。说到这儿,我有个认识,我觉得什么是好男人,一是要厚重,二是要耐烦,机巧和不全神贯注的男人都信赖不住。什么是好女人,一是长得干净,二是性情安静,长得干净就是漂亮,性情安静就能入得厨房进得厅堂。佛家有一种说法,说长酒窝的或脖子上有痣的人要善待,这些人仁慈,用情专一,能靠得住。因为人上世时都喝忘情水的,要忘掉前世情景,而这些人不喝,宁肯在冰河里浸泡多少次,在火海里烧烤多少次才上世的。张爱玲说过蝴蝶的前身应是花,所以蝴蝶一生都在恋花。世上的一生,都在问着我是谁呢?我从哪里来?我又将要去哪里呢?表现出来又都是蚂蚁在不停地搬动谷子草叶,草长着长着它就开花,天在周而复始地春夏秋冬,人不厌其烦地吃喝拉撒。常有这样一句话:八百年修得同船渡。这就是说,我认识你,你认识他,大家是一块来到世上的,坐的是一个船。所以,苏东坡才说,在他眼里,上至皇帝老儿下至护院乞丐没一个不是好人。大家的年龄都差不多,都在这个船上,如果风平浪静,就是逢上了好岁月。如果这船遇到了风浪,摇晃颠簸,有人呕吐,有人扯住别人要保持不倒,有人为了船的平衡要把别人推下去,这就是说,你遇到了一个不好的渡船期,你就没逢上好岁月。逢上了不好的岁月,人的缺点就暴露了,社会就有了黑暗、丑恶、恐惧和痛苦。反过来,在如此的环境里,人也就变了,一日是佛,一日是魔,你看镜子,镜子看你,人人都可以起焰,人人又都可以冒烟。我在《老生》后记里说,风刮风很累,花开花也疼。十几年前我在一个镇上采风,看到两个人吵架,吵得特别凶,旁边一个老人说,那两个人都有肝火病,那不是他们在吵,是两个肝在发炎。人活在这个世上,其实神也在人中,常说聚精会神,神是一般看不见的,凝聚精力才能见到神,当神不在其位,离人疏远,人就变成了一堆性器官和消化器官。当神在的时候,人冒出的烟,烟升到空中也会成为云。
那么,我们说我们身处的年代吧。这个年代,汪峰在唱:这是个最好的年代,这是个最坏的年代。为什么如此呢?因为社会正经历大转型,一方面社会为每个人提供了奋斗的平台,一方面社会又是让每个人焦虑、恐惧和疯狂。我们的船在掉头,在拐弯,又遇上了风,船肯定要倾斜。船上什么事就全发生了,而你正好在这船上。你在这船上,你当然有希望,有惊恐,你头晕呕吐,你得警觉着被人伤害,你也可能伤害别人。这就形成了你的特质。如同有各种土地,有肥沃的,有瘠贫的,有水田有旱田,水田里能长稻禾,旱地里则长荞麦。稻禾长上来就得不断灌水,有蛙鸣,生各种虫,在扬花时怕风,成熟时怕倒伏。荞麦就耐旱,
苗杆发红,开紫花,但鸟会来吃籽,野猪来吃苗。同样是饲养的,狗能看门下不了蛋,而鸡吃石子吃草叶也得下蛋,不下蛋就憋得慌。在青藏高原上,民歌是宗教的、蓝色的,而秦晋北部的民歌是身体的、黄色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以前是贫穷,运动不断,吃不饱肚子,又政治高压,很有秩序但没自由;现在市场经济了,富裕了,有了自由空间,也知道了什么是自由民主富强尊严,反倒更不满足了,追逐权力和金钱,道德沦丧,风气败坏,社会不安的危险度增高。我们就生活在这两种环境中,构成了我们的命运,在命运中生成了我们的品种。这品种在目下发展中的国家里都有,中国尤其典型。所以我们一些所作所想,欧美人不理解,其实欧美人以前也经历过,只是这一代人不知道罢了。就拿雾霾来讲,过去伦敦是著名雾城。这好比,欧美是把房子已装修过了,而我们正在装修,装修中当然一切混乱,尘土飞扬,电锯声聒耳,油漆味刺鼻,引起四邻不满。在这转型社会期,人人都在骂,怎么形成的呢?其实每个人都参与了,风气的形成,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这就说到文学,我们的文学也就是这品种。它要写生活,写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里面肯定就充满了改革、奋进,同时有阴暗、丑恶、肮脏和荒唐。这个时代似乎没有史诗,到处是猥琐、破碎,是一地鸡毛,是贴在墙上的标语无法揭下,揭下就是纸屑。似乎没有崇高,一切都在消解,似乎没有纯净,而是混沌一片。人人都在叫苦的时候,其实苦已经过去。世上真正的好东西是没人感恩的,甚至不作理会,这如同空气,人每时每刻都在一呼一吸,但你感觉这一切似乎不存在。真正有用的东西其实都不用,如原子弹,现在造了那么多,没见用过。对于今天中国发生的事情,有说是文化的原因。人的种类不同,所处的地方不同,形成了文化不同,文化又影响制约了人的思维和行为。我常想,世界就像一座山,在这条沟岔里住着一群大动物,如狮子、老虎,在另一个沟岔里住着牛呀猪呀兔子呀羚羊呀的,又在另另一个沟岔里聚集了一些小动物和鸟类。欧美人如同那些老虎狮子,体格大,食肉,喜欢独来独往,平时不作声,发声就咆哮。中国人是一群小动物和鸟,繁殖快,爱吵吵闹闹。大动物是掠食者,有力量、能攻击。小动物则机警、灵活,为了逃生会伪装,身上都有毒。我们就是一群小动物,鸟类,有心机,不安静,为了逃生和为了有吃有住有名有地位,竞争起来各使一技之长,使强用狠。如果我们的文化决定了我们的思维和行为,我们就得明白我们的长在哪里短在哪里,需要继承什么改进什么。
荣格说过:文学的根本是表达社会集体无意识,作家需要去抓寻那些原始的具象。新时期文学三十年来,我们既然是这样的品种,这品种好不好、行不行,又是值得掂量的。我们到底写得怎样,这些作品能不能行之久远,五十年后一百年后还有没有人去读去说呢?如“伤痕”、“寻根”、“改革”、“先锋”、“新写实”等等,这些思潮无可置疑是对推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繁荣起过极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思潮都是在思想观念上和文章写法上的一些革命。我们惯用的作品深刻性,总是以政治的社会的价值判断;惯用的时代性,总是以阶段的主流意识要求的。对于文学本身的内部规律的讨论却并不多。荣格的话说得早了,而且我们以前也说过类似的话,如写人人心中有的但没有说出来的东西。回想一下中外那些典型作品,如《唐·吉诃德》、《老人与海》、《尤利西斯》、《红楼梦》、《西厢记》、《阿Q正传》,这些作品都是表达着集体无意识,而我们没有写出来。当代的文学,难道仍是写出了生活气息,有了几个形象丰满的人物就是好作品吗?难道作品就是歌颂或揭露批判就是好作品吗?经典作品都是有超越了这些的大维度,在这个大维度里观照的是整个世界和世界中的人。如《山海经》中的大荒。《红楼梦》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泪是社会的、人生的,荒唐是语言的、文学的。当我们生活在这个喧嚣的琐碎的日子里,我们了解了它也了解了自己,认知了它也认知了自己,看透了,也看到了本来,从此获得写作的自由自在,如灵魂逃离了身体又观察身体,那么,文学的境界就自然而然与以前不一样了。观音菩萨是观音观世观自在,这里有个观,文学也是个观,所以王国维把他的书房叫观堂。
现在的作品,写得最多的是百年以来中国的历史,怎样写好这一段生活?陈思和先生最早提出过历史要归化于文学的话题。李敬泽先生也讲过只有历史不再是历史,当记忆不再只是个人记忆,而变成了经验、直觉和梦幻的时候,才有文学。这两位先生既是师生关系,又是当今超一流评论家,这些话都曾是针对我的《古炉》、《老生》说的。这些话反倒让我的朦胧变得清晰。我小时候听长辈人说古经,就是讲以前的陈年旧事,讲得非常有意思,讲得使我们做孩子的上了瘾,经常是为了听古经去给人家推磨子、剥包谷。所以,我后来觉得,当历史成了古经,成了一种故事,把这故事写出来就是文学。三十年来,我们有太
多的关于百年历史的叙写,在这些作品里,多有那些丑恶的残暴的恐惧的内容,揭露和批判是这一类作品的核心所在,这是必然和必需的。但我又有了一些怀疑,就是,如果事过境迁,后人阅读,仅仅是一种社会记录呢还是能受到文学的滋养?拿我们现在阅读前人作品的需求而推断后人阅读我们的态度,确实让我们不敢得意。对待历史,要真实去看,真诚去想,要表现出其重,又怎样在这重中变轻,如李敬泽说的,只有重才会碰到地面,只有轻才能通上天。这确实需要我们深思了再深思。
在文学叙写这个转型时代和社会的时候,摆脱不了这个时代社会的复杂、丑陋,但文学的目的并不是呈现这些复杂、丑陋,它不是让人类绝望和自杀,而是让人更好地生活。文学在这个时候,说简单一些,从某个角度讲,就是说公道话,这种公道话是在思考,是在批判那些丑恶,是美好。当一个人吃了饭后,牙上粘着韭菜,你就要告诉他,你把牙上的韭菜擦一擦,这样的话可能使牙上沾韭菜的人觉得难堪,但擦了韭菜却保持了他的好的形象。《内经》上讲,五脏得了病,那就是有鬼的原因。失去阳气的地方容易有鬼,鬼把人的经穴当作了房子和床。平日那地方充塞阳气,阳气一失,鬼去了,人也就病了。阳气是什么?就是魂魄,就是神气。过去民间招魂的方式很多,我小时候就被招过魂,夜里哭,不睡觉,家人在村中树上贴过招魂帖。三十多岁时,得了病,久治不愈,家人请了法师给我禳治过,我母亲到处给我求神。现在在陕西北部农村,我去采风时,仍看到有这种招魂的仪式,尤其普遍的是用黄表纸剪些小纸人,病人睡在床上,小纸人就放在被子上、枕头下。这个年代需要招魂,文学也在招魂,整个社会有了病,文学应该是治疗之一种,而文学开不了药方,却可以招魂。屈原的《离骚》就是招魂,司马迁的《史记》就是招魂,《红楼梦》也算是招魂。招魂也存在着什么人招、怎么招的问题。在我接触的陕西北部农村的一些剪纸艺人,老一辈的艺人实际上就是巫,他们从事这种工作久了,神就附了体,他们的招魂就起作用。而这些老艺人去世后,新的艺人也剪纸,可剪出来的东西怎么看都不是那么回事。老艺人剪纸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所剪的内容是他们对天地自然的认识,投入了巨大的真诚。新艺人剪纸只是为了美好环境,再就是借此出名或挣钱,剪出的东西一般人看了都没有冲击感,那鬼还怕吗?现在的乡下常重新修寺庙,在寺庙里塑神像。古人塑的神像你进去后就有森然感,让你不敢大声喧哗,不敢胡乱走动,你心身都收缩起来,而新庙里塑的神像,你只觉得那是个人物雕像,没有神气。在青海、西藏,寺外有许多玛尼石,就是在石上刻佛像,那简直是极高的艺术品,而且有了神性,可以让人敬礼膜拜。为什么呢?是刻石人在刻的时候十分虔诚,他把他对佛的虔诚贯注到了石头上。文学也是这样,文学取决于作家的格,取决于文字背后的声音和灵魂。如果作家襟怀鄙陋,作品的境界必然逼仄,不管你是要歌颂或是要批判,全都没有作用。当好的作品在写的时候,许多作家都有过一种情况,就是你在写作时会忘掉自己,你为你笔下的流畅和出彩感到惊讶,以为这不是你写的,是什么附了体,是谁在借你的手在写,你的浑身被什么充满,鼓鼓的。我想,这种情况,就是作品诞生了神气,生命在蓬蓬勃勃形成。真情投入,投入得专注,神自然就会归来。没有大的关怀,没有真诚,自己的品格低下、境界逼仄,你即便说是要招魂,你招不了,反倒招来的是邪气。我读过一篇写足球世界杯的文章,文章对一些球员这样不满,那样不满,这都可以发泄,写着写着却冒出一句,说你挣那么多钱,娶那么漂亮的老婆(因为现场转播时有看台上那些球员老婆的镜头),你这样踢球?!这就暴露了作者的心态。你写足球,写球员,你管人家老婆干啥?完全的嫉妒,好色么。文学里常有的调侃、戏谑、轻薄的腔调,也和这个文章是一样的。招魂的目的是回家,身有家,心也有家。尤其心要有家,心若没家,身就等于没家。这个社会,人人都在路上,都心里空虚,都恐惧,做任何事都是在找神寻家。
我还能讲些什么呢?我无法讲了。许多问题我能意识到,但我讲不清。我在写这个稿子时,写到这儿突然觉得我写的没意思了,就不写了。那我也就在这里结束我的讲话,把更多时间给陈思和先生讲。他每次讲话,我都喜欢听,肯定大家也喜欢听。谢谢。
[责任编辑:熊显长]
——为被日寇屠杀的30万南京军民招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