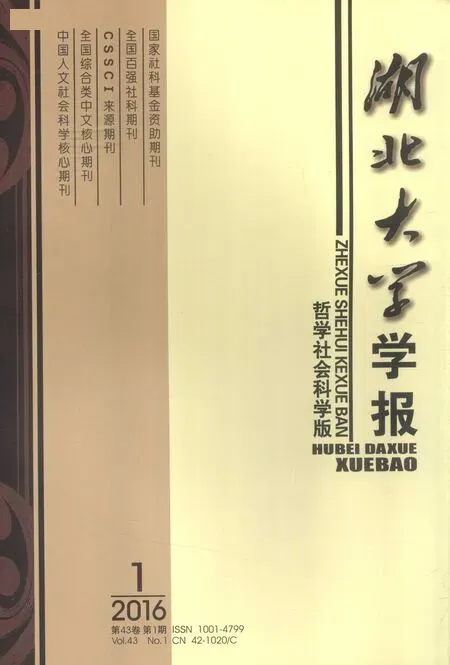从上博楚简看早期儒家对君权合法性及相关问题的阐释
丁四新,邹啸宇(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从上博楚简看早期儒家对君权合法性及相关问题的阐释
丁四新,邹啸宇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从上博楚简来看,早期儒家对君权合法性及相关问题的主要看法有:君权来源于天与民,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天下为公”的德治理想,即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使人人都能安身立命、成就自我,所以君权本质上就是源于万民并为了万民的公器;君权的合法性基础在于天命、民意与德能,这三者具有内在一致性,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为君权的合法性奠基,其中道德因素最为根本;“仁以得之,仁以守之”是君权的获得与维系之道,执政者既须修身立德、率先垂范,又须依仁治民、导民向善,如此才能顺应天命、合乎民心,从而取得统治的合法性。
[关键词]上博楚简;早期儒家;君权;公器;合法性;仁道
上博楚简中的《缁衣》、《民之父母》、《子羔》、《从政》、《容成氏》、《仲弓》、《季康子问于孔子》、《武王践阼》和《颜渊问于孔子》等儒家文献蕴含着颇为丰富的政治思想,其中许多内容皆不同程度地触及到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中十分重要的君权问题。目前学界虽有不少关于上博楚简的研究成果,但对于其中所涉及的早期儒家的君权思想尚缺乏专门、深入的考察①此前,我们曾就禅让问题探讨了上博楚简的政治哲学。参见丁四新:《楚简〈容成氏〉“禅让”观念论析》,载刘大钧主编《简帛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邹啸宇:《禅让制中政治权位转移的影响因素探析——以上博楚简〈容成氏〉与〈子羔〉为中心》,载丁四新主编《楚地简帛思想研究》第5辑,岳麓书社2014年版。。有鉴于此,本文将从君权的性质、君权的合法性基础,以及君权的获得与维系之道等方面,对上博楚简中所见早期儒家的君权观作一探究。
一、君权的性质:源于“天”、“民”并服务天下百姓的公器
从上博楚简来看,早期儒家对君权的性质虽然没有系统的论述,但无疑有其十分深刻的思考。在他们看来,君权作为最高政治权力,乃是源于天下百姓并最终为了天下百姓的公器,它在本质上具有大公至正的特征。这样一种君权观主要蕴含在其“天民一体”的君权来源说和“天下为公”的君权目的论之中。
(一)君权的来源:天民一体
对于君权的来源问题,早期儒家是站在天民一体的立场上来阐释的②陈来先生将“天民合一”视为中国早期政治哲学的三大主题之一。参见陈来:《中国早期政治哲学的三个主题》,《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他们既将君权的来源归于“天”,同时又认为“天”即代表着天下人民的意志。所以对他们而言,君权的产生是即“天授”即“民予”的,“天”与“民”共同构成君权的来源。楚简《容成氏》曰:
昔尧处于丹府与藋陵之间,尧贱施而时是著,不劝而民力,不刑杀而无盗贼,甚缓而民服。于是乎方百里之中率,天下之人就,奉而立之以为天子。于是乎方圆千里,于是乎持板正位,四向绥和,怀以来天下之民。是以视贤,履地戴天,笃义与信,会兹天地之间,而包兹四海之内,毕能其事,而立为天子……尧以天下让于贤者,天下之贤者莫之能受也……于是乎天下之人,以尧为善兴贤,而卒立
之。[1] 119①本文所引上博楚简的释文皆从宽式。本文所引《容成氏》篇参考了夏世华的竹简编联及释文。
从简文来看,尧以前居处于丹府与藋陵之间,可能出身贫贱,因其有大德大功,所以被天下之人拥戴为“天子”。他十分重视贤才,通过“视贤”、“让贤”的政治活动择取真正的贤人立为“天子”。在这里,“‘天子’一名的真正含义不在于所辖面积的广窄,而在于人君与‘天’是否具有真实的关联,只要真实地得到‘天’的命令、许可,他就是‘天子’”[2] 198。正因为尧是“天子”,所以才能获得并行使君权。这就可以确证,君权是“天”所赋予的,“天”是君权产生的根源。同时,简文又反复指出,尧是被“天下之人”奉立为“天子”的。据此可知,尧之能成为“天子”离不开广大人民的拥戴。这表明,民心向背也是判定君权合法性的重要理据,只有得民心者才能禀受天命而成为“天子”。尧作为“天子”,既是天之所命,又是民之所立,而天所命者即是民所立者,足见天、民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就在于:民心即是天命的体现,天命借民心来表达;而天赋君权即是民赋君权,君权根源于天也就是根源于民。由于君权的存在本于天命、民心(即公意),所以它就是平治天下、造福全民的公器,而统治者运行君权以治理天下就必须出于公心。简言之,君权理当具有大公至正的本质,而绝不是由个人意欲支配的。
(二)君权存在的根本目的:实现“天下为公”的德治理想
在早期儒家的观念中,君权是为天下人的安身立命和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而设置的,其存在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天下为公”的德治理想。在楚简《容成氏》中,作者通过对禅让制所达至的政治效果的描绘表达了“天下为公”的德治理想。这一政治理想的确立既指明了君权存在的目的和意义,也规定了君权的公共性本质。
先来看《容成氏》对帝尧的论述。上引简文指出,尧为政治国达到了极高的理想状态,他主张施行简易、宽和的为政之道,倡导以仁政来治理人民,乃至他被诸侯、百姓推戴为“天子”。该篇简文还说:
舜听政三年,山陵不处,水潦不湝,乃立禹以为司工……天下之民居定,乃饬食,乃立后稷以为田……五年乃穰。民有余食,无求不得,民乃愆,骄态始作,乃立臯陶以为李……三年而天下之人无讼狱者,天下大和均。[1] 128~129
第一段文本叙述了舜治理天下的情况。首先,他命禹担任司空以治理水灾,使人民得以安居;其次,命后稷为农官以治理农事,让人民丰衣足食;最后,命臯陶担任法官以治理狱讼之事,构建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可见,舜执政始终以天下人民的福祉为本,通过他的治理,整个天下呈现出一片生生不息、和谐稳定的气象。第二段文本叙述了禹治理天下的事迹。禹执政三年,不制造兵革,不踏勘田地,不滥用民力,不收苛捐杂税,不行繁苛政令。其一切举措皆根据广大人民的需求和意愿而定,乃至天下百姓都诚心归服。显然,禹治国理政,仍是以万民的福祉为依归,实行简易、宽和的为政之道,轻徭薄赋,爱恤民命,使得整个社会都安定和谐、繁荣兴盛。
归纳起来,尧、舜、禹三位君王治理天下有两个共同特点:第一,他们都是本于救济天下、造福百姓的公心来为政治国的,其执政是为了建构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使人人都能安身立命、实现自我价值;第二,他们都主张通过施行仁政来成就天下为公、天下和合的理想。从简文的叙述来看,在德治理念的指引下,尧、舜、禹三圣王无疑都实现了公天下、和天下的政治理想。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都是德才兼备的贤者,并且获得了君权,从而有资格治理天下。可见,对早期儒家而言,君权的存在是为人民大众的利益服务的,而绝非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利、私欲。既然如此,君权在根本上就是服务天下人、成就天下人的公器,绝不可私自为用。尧、舜、禹三圣正因为对君权大公至正的本质有着深切的体认,所以才没有陷溺于权力欲,而是始终秉公执政以治理天下,积极推动天下为公、万邦和合的最高政治理想的实现。
二、君权的合法性基础:天命、民意与德能
所谓“君权的合法性基础”,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背景之下,个人或集团获得并维系君权的正当理据或根本条件。从上博楚简来看,早期儒家主要以天命、民意与德能作为君权合法性的
三大基础。这三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它们相涵互摄、相依互成,共同为君权的合法性奠基①欧阳祯人在《先秦儒家的君权合法性论证浅析》一文中,从君权的天命支撑、道德支撑和制横措施三方面对先秦儒家的君权合法性理论进行了考察,但他并未讨论君权的民意基础(参见《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5期);杨松禄在《中国古代君权合法性探源》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君权合法性理论是以天命、道德、民意为支撑,但他对这三者之间的内在关联缺乏论析,也没有把政治才能这一因素纳入其中加以探讨(参见《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一)顺应天命:君权合法性的形上基础
在早期儒家看来,天是君权的最终来源,天命或天道是君权合法性的终极依据,只有领受天命、保有天命的人,才能获得并行使君权,也才能维系君权。如楚简《孔子诗论》云:
〔“帝谓文王,予〕怀尔明德”,曷?诚谓之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诚命之也。信矣!孔子曰:“此命也夫!文王虽欲也,得乎?此命也。”[3]②此处参考了李学勤的竹简编联及释文。
据此可知,文王凭借其美德而受命于天,又正因为得到了天命,所以才取得统治的合法性,从而得以兴建和发展周邦。如果没有获得天命,文王即使有伐商兴周之志,那也是无法实现的。可见,文王伐商兴周最终是由客观的、超越的天命所决定,而并不以其主观的意志为转移。也就是说,文王握持君权以统治周邦,是以禀受天命为前提和根据的。这种“受命为王”的观念亦见之于楚竹书《子羔》篇,该篇曰:“舜其可谓受命之民矣。舜,人子也,〔而〕三天子事之。”[4] 180③本文所引《子羔》篇参考了夏世华的竹简编联及释文。这深刻地表明,受命为王并非贵族阶级才能享有的特权,普通民众也可以禀受天命而成为君王。由此可知,不论君王的出身如何,欲“为王”就必须先“受命”,一旦“受命”便可获得“为王”的资格,即取得执掌君权的合法性。这就意味着,天命是君权合法性的终极依据和形上根基。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谓“天命”作为至上人格神的意志或命令,同时蕴含着天道的意义④梁启超说:“前此谓有一有感觉有情绪有意志之天直接指挥人事者,既而此感觉情绪意志,化成为人类生活之理法,名之曰天道,公认为政治所从出而应守,若此者,吾名之曰抽象的天意政治。”参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天道内在于人伦日用之中,乃是万事万物存在及运行的根本法则、一切价值和意义之根源。由于舜与文王受命的根据主要在于其具有大德,所以道德伦理便构成了“天命”的重要内涵。就此而言,“天命”当具有天道(普遍法则与价值根源)的意蕴。早期儒家认为,唯有得道者才能获得并维系君权,失道者则反之。据《容成氏》所说,武王伐灭商纣,就是奉行天道的结果。由此表明,顺应天命或天道才是取得执政合法性的终极理据。
(二)合乎民心:君权合法性的民意基础
在早期儒家的观念中,作为君权合法性之终极依据的“天命”实际上是通过“民意”与君王的“德能”来体现的,唯有具备大德大能进而赢得民心者才能受命为王。因此,民众的意愿和君王的道德、才能也是决定君权合法性的根本因素。
首先来看“民意”对君权合法性建构的作用和意义。民心向背无疑是判定君权合法性的重要依据。从楚简《民之父母》篇来看,民心所向者也就是真正可以作为“民之父母”者。“民之父母”的观念蕴涵着丰富的政治哲学意义⑤参见荆雨:《德与民:中国古代政权合法性之根据》,《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6期;《从政治正当性视角看儒家“民之父母”思想的内涵及其当代意义》,《古代文明》2012年第1期。,它直接表明君权合法性的存在必须以民意为基础。竹简《民之父母》云:
〔子〕夏问于孔子:“……敢问何如而可谓民之父母?”孔子答曰:“民〔之〕父母乎,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致‘五至’,以行‘三无’,以横于天下。四方有败,必先知之,其〔可〕谓民之父母矣。”[5] 154~158⑥本文所引《民之父母》篇,以濮茅左的竹简编联及释文为基础,同时参考了庞朴、季旭升、廖名春、陈剑等人的意见。
这段文本主要在探讨“何如而可谓民之父母”的问题,即具备何种条件的人才有资格执掌君权以治理天下。孔子的答语指出,唯有通达礼乐之本原(即仁道)者,方能称得上是“民之父母”。即是说,为民父母者必当满怀仁德、爱民如子,其仁心大德充塞于整个天下,以至于四方有难,皆能先知先觉。这就要求统治者必须心系人民、心怀天下,始终以广大民众的福祉为依归,能够倾听民声、体察民情、满足民欲,以至于使天下之人皆有所安顿、有所成就。唯有如此,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与支持,从而成为“民之父
母”意义上的理想君主,亦即真正保有执政合法性的统治者。
可见,在早期儒家看来,民心所向是君权合法性的基本保障。这一点在楚简《缁衣》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其简文云:“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好则体安之〕,君好则民欲之。故心以体废,君以民亡。”[6] 87①本文所引《缁衣》篇参考了邹濬智和虞万里的竹简编联及释文。这里把君与民的关系比作心与身的关系,意在表明,君、民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撑而不可分割的。民既可以立君,亦可以废君。若君爱民、重民,则民必拥君、尊君;若君虐民、残民,则民必反君、废君。因此,唯有仁民爱众,才能赢得民心,从而取得统治的合法性;反之,则必将丧失统治的合法性,以致被人民推翻。这就充分表明,君权合法性的获得与维系依赖于民意的支持。
(三)拥有大德大能:君权合法性的德能基础
既然民意是君权合法性的决定性因素,那么什么人才可以获得民心呢?早期儒家认为,只有道德高尚、能力超群的贤者才能得到万民的拥戴。这一点可从楚简《容成氏》对尧的叙述中窥见端倪。尧因为“善兴贤”而最终被天下人拥立为天子,这就直接体现出人民百姓对尧“善兴贤”这一举动的充分肯定,也反映出当时人民对“兴贤”的积极态度,而根本上则表明天下人对“贤”及“贤者”的认可。此即意味着,贤者能够赢得民心、顺应民意,因而具备受命为王的资格。
“贤”是《容成氏》篇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它蕴含着执政者获得与维系君权的根本要求,决定着执政者能否取得统治的合法性。换言之,“贤”也是判定君权合法性的重要依据。根据《容成氏》的叙述,尧、舜、禹三位君王无一不是贤者,且他们都“不以其子为后”,而是择取真正的贤者立为天子,主张“以天下让于贤者”。由此表明,唯有贤者才配居“天子”之位,才有资格执掌君权。究竟何谓“贤”或“贤者”?《容成氏》说:“其德欲清而尚,其政治而不赏,官而不爵,无劢于民,而治乱不倦,故曰贤。”[1] 113竹简认为,上古帝王德行高尚,倡导无为而治,好尚施惠于民;其政治才智高超,不用奖赏而事物得治,不加封爵位而臣下尽职,不勉励督促而民能自觉努力,不用劳倦而天下大治。这就表明,上古帝王具有大德大智,由此才被视之为“贤”。可见,“贤”在这里就是对上古帝王之高尚道德与非凡才智的综合评价。对于“贤”的义涵,我们也可从尧纳贤的标准中来把握。尧择贤的标准是:“履地戴天,笃义与信,会兹天地之间,而包兹四海之内,毕能其事。”[1] 119其中“履地戴天,笃义与信”是指贤者当具备正直刚健、重义守信的德行,这是对贤者德行方面的要求;“会兹天地之间,而包兹四海之内,毕能其事”则指贤者当具有经纬天地、统御四海的才能,这是对贤者政治能力方面的要求。由此可知,只有德才兼备的人才可称之为贤者。当然,就“贤”的内在规定而言,早期儒家更为重视其中的道德义涵。如《容成氏》中记述:尧因舜“孝养父母,以善其亲,乃及邦子”[1] 119~120而“美其行”,并“三从舜于畎亩之中”[1] 120,以至最终立舜为继位者,这充分说明道德在尧的择贤标准中具有优先性。《子羔》篇则指出:“尧见舜之德贤,故让之”、“舜之德其诚贤矣,由诸畎亩之中而使,君天下而称”[4] 180,这就更加清楚地表明,“德”才是“贤”的本质内涵,是人们受命为王的根本依据。
显然,在早期儒家的观念中,执政者既须拥有贤德,又须具备贤能,二者缺一不可。就此而言,个人的德行与才能无疑也是影响君权合法性的重要因素②陈来先生指出:“从早期禅让的政治文化传统,到夏商两代,在君权神授观念的同时,也都传留了一种由君主领袖的美德和才智来建立政治合法性的传统。事实上,这种从才和德方面建构统治的合法性的意识,不仅为君主和民众共同接受,而且在氏族部落禅让制度中更是必然如此的。”参见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93页。。因此,统治者必须具备贤德贤能,才能为执政的合法性奠立坚实的根基。当然,对于早期儒家而言,道德因素在君权合法性的建构中无疑具有更为根本性的作用。
总之,天命是君权合法性的终极依据,禀受天命者才能执掌君权、治理天下;而天命通过民意来表达,视民心而定,赢得民心者才能禀受天命;又因民心归向于贤者,所以具有贤德贤能的人才能赢得民心。显然,天命、民意与德能三位一体,为君权合法性的建构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三、君权的获得与维系之道:“仁以得之,仁以守之”
早期儒家既以天命、民意与德能三者一体作为君权合法性的基础,这就要求执政者必须具备大德大能,由此才能合乎民心、顺应天命,从而取得统治的合法性。由于道德因素对君权合法性的建构具有最终决定作用,所以早期儒家强调以“仁”为君权的获得与维系之道。楚简《武王践阼》甲篇云:
〔武〕王问于师尚父曰:“不知黄帝、颛顼、尧、舜之道存乎?意微茫不可得而睹乎?”师尚父曰:“在
丹书,王如欲观之,盍斋乎?将以书见。”……师尚父奉书,道书之言曰:“怠胜义则丧,义胜怠则长;义胜欲则从,欲胜义则凶。仁以得之,仁以守之,其运百〔世〕;不仁以得之,仁以守之,其运十世;不仁以得之,不仁以守之,及于身。”[7]①本文所引《武王践阼》篇参考了杨华的竹简编联及释文。
周武王灭商后即天子之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汲汲于谋求为政治国之道,于是向太师尚父(吕望)请教,尚父以丹书所言开示之,他指出:为人君者治国理政,若怠惰胜过大义则会导致国家灭亡,而大义胜过怠惰就能长治久安;若大义胜过私欲便会吉顺,而私欲胜过大义就会有凶险。若以仁道得天下、守天下,则其国运可以持续百世;若以不仁之道得天下,而以仁道来守天下,则其国运可以持续十世;若以不仁之道得天下、守天下,则其国运只能止于当时。由此可知,一国之存亡实依赖于执政者是否具有仁德以及能否实行仁道。也就是说,统治者能否正当合理地获得并维系政权,关键在于其仁与不仁。“仁以得之,仁以守之”才是获取君权与维持君权的根本之道。这就要求执政者既当以修身立德为本,先正己以做好表率;同时又须坚持以仁治民,导民兴德向善。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唯有兼重并修,才能将仁道真正贯彻落实,从而顺天应人,赢得执政的合法性。
(一)修身立德,率先垂范
早期儒家十分重视执政者的道德表率作用,他们认为,执政者应当以修德正己为本,唯有做到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人民才会心悦诚服地归顺,并随之而向善。据楚简《颜渊问于孔子》所载,颜渊向孔子请教化民之道,孔子曰:“修身以先,则民莫不从矣;前〔之〕以博爱,则民莫遗亲矣;导之以俭,则民知足矣;前之以让,则民不争矣。”[8]②本文所引《颜渊问于孔子》简文,以复旦吉大古文字专业研究生联合读书会的编联及释文为基础,并参考了陈伟、黄人二、赵思木等学者的意见。即是说,君上能先修身立德,则民皆自然顺服;君上博爱,则民皆仁厚;君上节俭,则民皆易于知足;君上谦和有礼,则民皆好让不争。可见,在孔子看来,执政者欲化民成俗,就必先修身以正己,己身正然后才能使民得正。若执政者自身品行端正,则无须教令,人民自会由之而行;若自身品行不正,则纵使三令五申,人民也不会服从。这正如楚简《缁衣》所云:“子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以命,而从其所行。’”[6] 88可见,真正能让万民诚服的并非政令、刑罚等强制性手段,而是执政者的美德善行。因此,统治者必须以修身立德为本。
从上博楚简的相关文献来看,早期儒家认为执政者在道德修养上应当至少达到如下三点要求:
第一,必须具备敬、谦、信、恭、宽、惠、仁等品德。楚简《从政》甲篇云:
从政所务三:敬、谦、信。信则得众,谦则远戾,远戾所以……[9] 93③本文所引《从政》简文,以汤浅邦弘的编联及释文为基础,并参考了陈美兰、陈剑、陈伟等学者的意见。
从政,庸五德、固三制、除十怨。五德:一曰宽,二曰恭,三曰惠,四曰仁,五曰敬。君子不宽则无以容百姓,不恭则无以除辱,不惠则无以聚民,不仁则无以行政,不敬则事无成。[9] 90~91
简文中论及的“敬、谦、信、宽、恭、惠、仁”七德,是对执政者的基本德行要求。“敬”德要求执政者严肃认真、专心谨慎地治理天下事务。在早期儒家看来,执政者为人处事敬与不敬关系到国家的存亡祸福。楚简《武王践阼》乙篇曰:“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不敬则不定,弗强则枉,枉者败,而敬者万世。”[7]可见,执政者能否持敬对于国家的安危治乱、政权的得失兴替具有重大影响。因而统治者只有具备“敬”德,才能安邦定国、稳固政权。“谦”德要求执政者虚心谨慎、谦卑礼让。《颜渊问于孔子》云:“前之以让,则民不争矣。”[8]这就指出,执政者必须懂得谦让,才能使民不争、和合天下。“信”德要求执政者真诚踏实、谨守信用,如此才能得到民众的信赖与支持。《缁衣》云:“信以结之,则民不倍。”[6] 89统治者若能真心实意地对待人民,则人民自然不会叛离。所以执政者必须以诚待民,方能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宽”德要求执政者宽宏大度,这样才能安邦利民。据楚简《仲弓》篇载,孔子将“宥过赦罪”即宽恕过错、赦免罪行视为“政之始”[10]④本文所引《仲弓》简文,以陈剑的编联及释文为基础,并参考了晁福林、李锐、梁静等人的意见。,强调为政者应当宽以待民,实行宽和的政治。“恭”德要求执政者恭敬和顺地对待人民,而不能倨傲自恃、作威作福。《缁衣》云:“恭以莅之,则民有逊心。”[6] 89据此可知,执政者必须以恭敬之心待民,才能真正赢得民心。“惠”德要求执政者广施恩惠于民,以济世利民为己任。“仁”德要求执政者亲民、爱民、恤民、重民,如此才能得到万民的拥戴。《缁衣》篇谓“慈以爱之,则民有亲”[6] 89,《颜渊问于孔子》篇将“老
老而慈幼”视为君子入仕之道,并指出“老老而慈幼,所以处仁也”[8]。这些都表明,仁爱民众、保有仁德乃是统治者获得与维系政权的基本要求。
第二,必须谨言慎行、言行一致。《缁衣》云:“〔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恒以行。〕故言则虑其所终,行则稽其所蔽,则民慎于言而谨于行。’”[6] 90孔子指出,君子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引导和教化人民,他们讲话一定会考虑其可能导致的后果,行动必然会明察其可能造成的弊害,如此人民也会随之而谨言慎行。这就要求执政者应当谨慎小心自己的言行举止。谨言慎行的一个重要表现即是保持言行统一。《从政》甲篇云:“可言而不可行,君子不言;可行而不可言,君子不行。”[9] 93《缁衣》亦云:“子曰:‘可言不可行,君子弗言;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则民言不危行,行不危言。’”[6] 90此是说,对于能言而不能行者,君子不言;对于能行而不能言者,君子不行。由此,人民才会做到言行一致。这主要在于强调执政者应当慎言慎行、言行相顾,如此方能垂范天下、导化民众。
第三,必须合理控制自己的欲求。执政者身处国家政治权力的中心,其私欲能否得到合理有效地控制,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人民的安危祸福。因此,早期儒家强调执政者必须以理节欲。据《武王践阼》乙篇载,太师尚父借丹书之语向周武王指点为政之道,其开首即云:“志胜欲则昌,欲胜志则丧;志胜欲则从,欲胜志则凶。”[7] 124~125此是说,若君王的志向胜过私欲,则国家便会吉顺、昌盛;若私欲胜过志向,则国家便会凶险,甚至丧亡。这就是告诫统治者必须立德明道以遏止私欲,如此才不致因一己之私的陷溺而导致丧权亡国。周武王受教之后,在坐席的四端刻铭以警戒自己。其中杖铭曰:“恶危?危于忿戾。恶失?失道于嗜欲。恶〔忘?忘〕于贵富。”[7] 124牖铭曰:“位难得而易失,士难得而易外。”[7] 124这里指出,当人忿怒暴戾的时候就会很危险,当人深受嗜欲诱惑的时候就会丧失道义,当人富贵的时候就容易忘形。然而,权位难得却易于丢失,士人难求却易于外流。就此而言,执政者必须以道义来主宰、克制自己的情欲,才能维系其政权而勿失。对于执掌最高政权的统治者来说,权力欲的制约无疑最为关键。早期儒家基于德治的理念,非常注重统治者的德行修养,强调通过深化统治者的道德自律意识来实现权力的有效制约与规范运行[11]。他们深信,唯有如此,统治者才会真正自觉地合理用权、秉公执政,从而在根本上解决权力的规范与制约问题。所以对早期儒家而言,权力的控制主要是通过执政者以理治欲的道德修养来实现的,其关键即在于掌权者能否自我节制权力欲。因此,统治者欲维系政权,就必须懂得克己制欲。
(二)依仁治民,导民向善
早期儒家政治哲学具有内圣外王合一的特征,其修己与治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后者的开展须以前者为基础,前者亦须通过后者的展开才能充分实现。就此而言,仁道作为君权之获得与维系的根本原则,必然贯通于修己与治人两方面。这就意味着,统治者在修身立德的基础上,还必须施行仁政、以德治民,如此才能巩固其政权,才能实现仁道于天下。
在早期儒家看来,唯有本于仁道治国理民,才是执政者赢得民心、维持统治的根本。楚简《季康子问于孔子》云:
季康子问于孔子曰:“肥从有司之后,抑不知民务之焉在?……请问:君子之从事者于民之〔上,君子之大务何?”孔子曰:“仁之以〕德,此君子之大务也。”康子曰:“请问何谓仁之以德?”孔子曰:“……君子玉其言而慎其行,敬成其德以临民,民望其道而服焉,此之谓仁之以德。”[12]①本文所引《季康子问于孔子》简文,以陈剑的释文为基础,并参考了福田哲之、廖名春等人的意见。
季康子担任官吏之后,不知如何着手治理人民的事务,于是向孔子请教民务何在。孔子指出,为政治民的根本任务在于“仁之以德”。所谓“仁之以德”,是指为政者以德治民、化民,亦即修身立德,做好表率,通过德行的感召使广大民众自然诚服、驯化。《缁衣》载孔子语云:“长民者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劝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免心。”[6] 89即是说,统治者若以道德教化民众,以礼义管束民众,人民就会受到劝勉而诚心归服;若以政令管教民众,以刑罚整治民众,则人民会因求免处罚而顺从。可见,政令刑罚只能使人因惧怕刑罚而暂时免于罪过,而道德礼义则可以让民众诚心改过迁善。因此,为政治民应当以德礼为本、刑政为末。这就要求统治者施政宽和而不严苛,否则就会失去民心。《从政》甲篇云:“从政有七机:狱则衅,威则民不道,卤则失众,猛则无亲,罚则民逃……凡此七者,政之所殆也。”[9] 92这里指出了政治活动中七种危险的做法:其一,大兴刑狱致使民众产生嫌隙;其二,逞威张势则民众不会顺从;其
三,鲁莽蛮横失去民心;其四,刚猛严苛则民众不会亲附;其五,好施刑罚则民众叛离;等等。显然,这些施政行为均过于严苛、残暴,缺乏仁爱精神,以致违背了基本的人性、人情,由此必然招致人民的反对。《季康子问于孔子》所引臧文仲之言曰:“君子强则遗,威则民不导,严则失众,猛则无亲,好刑则不祥,好杀则作乱。”[12]无疑也表明了此意。执政者若一味采用严刑峻法与强制政令,或仅凭其权势来统治人民,必将导致众叛亲离、丧失政权。早期儒家对苛政、暴政的危害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大力倡导宽政、仁政。他们认为,执政者必须坚持以仁道为本,才能真正取得民心、稳固政权。
总之,早期儒家以仁道为君权之获得与维系的根本原则,认为执政者得权守位的关键即在于“仁以得之,仁以守之”。这就要求统治者既当以德修己,率先垂范;又须依仁治民,导民向善。如此才能顺天应人从而获得执政的合法性,才能实现仁道于天下。当然,作为执政者,如果徒有道德与理想,而缺乏真正的能力使之落实,则其价值理想的实现势必受阻,而政治腐败、社会混乱、民生疾苦等问题亦无法得到有效解决。所以,执政者必须具备卓越的能力,这一点毫无疑问。由《容成氏》可知,除德行之外,早期儒家也颇能正视统治者的才能对于为政治国的重大影响。只不过他们提倡德治,更为强调道德因素在政治中的重要性。
四、结语
从上博楚简来看,早期儒家君权观的要义有三:其一,早期儒家站在天民合一的立场阐释君权的来源,认为君权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天下为公”的德治理想,即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使人人都能安身立命、实现价值。此即决定君权必当是源于万民并为了万民的公器,必当具有大公至正的本质特征。其二,早期儒家以天命、民意与德能三者一体来建构君权的合法性。他们认为,君权合法性的终极依据是天命,天命通过民意来体现与落实,而民意又取决于君主的贤德与贤能,所以天命、民意与德能具有内在统一性,它们相互涵摄、相互作用,共同为君权的合法性建基。其中道德因素对于君权的合法性具有最终决定作用。其三,早期儒家以仁道作为获得君权与维系君权的根本之道,由此认为执政者既当以修身立德为本,同时还须依仁治民,导民兴德向善。如此才能将仁道实现于天下,才能取得统治的合法性。早期儒家对君权的以上认识皆源于其对仁道的体认与追求。从根本上说,君权就是将仁道贯彻于天下的工具,其存在的目的即在于实现仁道,其合法性的建构也是以仁道为本。这就决定了仁道是获得与维系君权的根本原则,只有仁者才能得民心、得天下,而不仁者必失民心、失天下。因此,对早期儒家而言,仁道是执政之基、立国之本,是一切政治的根本原则和终极追求。总之,上博楚简所见早期儒家对君权合法性及相关问题的讨论,乃是将天命、民意与德能三大要素加以融会贯通,既坚持以德为本,强调君主的道德修养及其施政行为的公正性;同时又充分肯定民众之意愿和君主之才能对于君权合法性建构的重要性。这无疑丰富了先秦儒家的君权思想,并对今天如何规范和制约政治权力的运行仍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夏世华.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容成氏》集释[M]//丁四新,夏世华.楚地简帛思想研究(四).武汉:崇文书局,2010.
[2]丁四新.楚简《容成氏》“禅让”观念论析[M]//刘大钧.简帛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李学勤.《诗论》简的编联与复原[J].中国哲学史,2002,(1).
[4]夏世华.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子羔》集释[M]//丁四新,夏世华.楚地简帛思想研究(四).武汉:崇文书局,2010.
[5]濮茅左.《民之父母》释文考释[M]//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6]邹濬智,季旭升.《缁衣》译释[M]//季旭升.《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7]杨华.上博简《武王践阼》集释(上)[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8]复旦吉大古文字专业研究生联合读书会.《上博八·颜渊问于孔子》校读[EB/OL].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592.
[9]汤浅邦弘.《从政》的竹简连接与分节[M]//战国楚简与秦简之思想史研究.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6.
[10]陈剑.上博竹书《仲弓》篇新编释文(稿)[EB/OL].http://www.bamboosilk.org/admin3/html/chenjian01.htm.
[11]孙季萍.先秦儒家政治文化中的权力制约思想[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12]陈剑.谈谈《上博(五)》的竹简分篇、拼合与编联问题[EB/OL].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04.
[责任编辑:黄文红]
[作者简介]丁四新(1969-),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先秦两汉哲学、简帛思想和周易经学研究;邹啸宇(1985-),男,湖南衡阳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资助项目:12JJD75003
[收稿日期]2015-07-12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6)01-004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