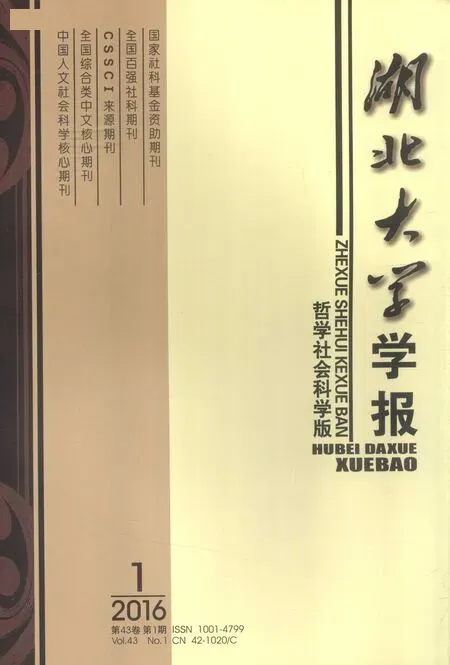贾平凹小说研究综述
叶澜涛(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贾平凹小说研究综述
叶澜涛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贾平凹是新时期三十年来重要的作家,其小说创作对于新时期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其研究也不断跟进。目前,贾平凹研究主要集中于整体研究、作品评价以及比较研究三个方面。此外,还有部分批评质疑的声音。贾平凹研究整体水平较高,涉及的面也较广泛,但仍存在不足和遗憾。通过对其研究现状的梳理和问题的发现,能够更加有效地将贾平凹小说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关键词]贾平凹;整体研究;作品评价;比较研究
贾平凹自1973年发表短篇小说《一双袜子》以来,至2014年出版长篇小说《老生》,其创作已经走过了四十多年的历史。贾平凹不同时期的创作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引起过争鸣与回响,与评论家之间产生了积极的互动。我们通过阅读贾平凹,甚至可以看到一部微缩的“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不同的评论家通过评价其作品,不断运用各自的评论武器来实践其批评理念。可以说,贾平凹小说的批评史也是新时期文学批评十分有意义的个案。
贾平凹小说评论史时间长,参与的人数多。根据中国知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的统计数据(截止至2015年3月19日),以贾平凹研究为主题的论文共有3600余篇。其中许多文章都刊载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内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例如《小说评论》165篇、《当代作家评论》109篇、《文艺争鸣》56篇、《当代文坛》50篇、《文学评论》43篇、《南方文坛》22篇。一些重要的学术期刊还以专辑的形式发表过贾平凹研究成果,例如《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3期发表的“贾平凹专号”以小说《带灯》为专题,2015年第1期又发表“《老生》评论小辑”;《文艺争鸣》2012年第10期发表“贾平凹研究专辑”;《小说评论》2013年第4期发表“贾平凹长篇小说《带灯》评论小辑”;《文学评论》2015年第1期发表“贾平凹小说评论专辑”。此外,检索中国国家图书馆官网发现,中国大陆地区以贾平凹为研究对象的书籍有40余本,此数据还没有囊括评论集或专题史中的专章专节。另有近300篇硕博士论文以贾平凹研究为标题或涉及到贾平凹作品的评论。由此可见,贾平凹研究一直处于相当活跃的状态。通过梳理后可以发现,虽然贾平凹的研究论文和评论著作很多,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贾平凹小说创作的整体研究
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已逾四十余年,对贾平凹的评论也一直在跟进。近年来,各种综述评价类的文章陆续发表,极大丰富了贾平凹研究的资料。其中张涛整理的《贾平凹创作年表简编》(载《文艺争鸣》2012年第10期)及《当代作家评论》编辑部整理的《〈当代作家评论〉发表的贾平凹评论文章目录索引》(载《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3期)具有较大的工具价值。《贾平凹创作年表简编》从1964年开始至2011年截止,将贾平凹生平较为重要的创作事件进行梳理,逐年将其创作状况进行排列,工作细致扎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另一份有价值的资料是《〈当代作家评论〉发表的贾平凹评论文章目录索引》。《当代作家评论》作为当代重要的作家作品评价阵地,从1985年起开始发表对贾平凹的评论文章,截止2013年,先后发表了90余篇各类论文,许多较为重要的总结及对谈均首刊于《当代作家评论》。
评价综述类除了资料汇总外,其余很多论文对贾平凹各个阶段的创作进行了总结式的评价。例如早期雷达的《模式与活力——贾平凹之谜》、刘建军的《贾平凹论》等,中期李遇春的《拒绝平庸的精神漫游——贾平凹小说的叙述范式的嬗变》、杨胜刚的《对贾平凹90年代四部长篇小说的整体阅读》、叶君和岳凯华的《贾平凹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心理根源》等,近期周燕芬的《贾平凹与三十年当代文学的构成关系》、陈晓明的《本土、文化与阉割美学——评从〈废都〉到〈秦腔〉的贾平凹》、程光炜的《批评对“贾平凹形象”的塑造》等均是各时期较有代表性的评论文章。
关于贾平凹的早期评论主要是以感受式为主,将不同阶段的贾平凹创作进行梳理,由于写作时间先后有别,因而对于其创作分期的划分也是各有不同。雷达的《模式与活力——贾平凹之谜》(载《读书》1986年第7期)是较早对贾平凹的创作进行概括总结的论文,它将贾平凹1978年至1985年的创作划分为三个阶段,认为贾平凹总的创作模式在于擅长描绘人物的“性”“情”,活力之处在于展现男女主人公各种心灵秘密。刘建军的《贾平凹论》(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也将贾平凹1978年至1985年的创作划分为三个阶段,但着重分析的是贾平凹在写作过程中的情绪变化,即从清新乐观到沉思孤独,却又包含喜悦自信的复杂情绪,而无论作者情绪变化如何,现实主义精神始终不变。
中期评论主要梳理的是贾平凹90年代创作的范式和心理趋向,但论述的角度和重点有所差异。李遇春的《拒绝平庸的精神漫游——贾平凹小说的叙述范式的嬗变》(载《小说评论》2003年第6期)梳理总结的时间从1980年至2002年。论者将其创作分为三个阶段,即“启蒙论”叙述阶段、“生存论”叙述阶段和“现代性反思”叙述阶段,并以这三个阶段的代表作串联起贾平凹二十余年的创作历程,认为贾平凹的创作不甘平庸、不断自我超越。杨胜刚的《对贾平凹九十年代四部长篇小说的整体阅读》(载《小说评论》1999年第4期)分析的是贾平凹90年代的四部长篇小说即《废都》、《土门》、《高老庄》、《白夜》的特色,论者认为这四部小说充满了批判意识和现实主义精神,表达了作者对于国运世风深沉的忧虑。但不足的是,小说在描写上存在观念化痕迹,人物有流于抽象之嫌。叶君、岳凯华的《贾平凹90年代长篇小说创作的心理根源》(载《中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1期)分析的也是贾平凹90年代的长篇小说,但分析的视角有所不同,主要从作家的心理轨迹进行论述。90年代的贾平凹是一个失去家园的孤独灵魂,既失去了现实家园,又失去了政治家园,精神家园也没有终极关怀而茫然失措。贾平凹在这四部长篇小说中表达了寂寞、悲凉的情绪。
近几年的贾平凹评论呈现出更加宏观和多元的视角,不仅梳理的时间段更长,而且出现了从批评史的角度来讨论批评与创作的互动关系。这也显示贾平凹的创作不断走向历史化和经典化的进程。周燕芬的《贾平凹与三十年当代文学的构成关系》(载《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5期)概括的时间从1977年至2007年,总结出贾平凹的创作有两大特色:“个人化”与“民间化”。这两大特色统一于一个总的思想原则,即“以中国传统美的方法,真实表达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我心目中的小说——贾平凹自述》,载《小说评论》2003年第6期)。程光炜的《批评对“贾平凹形象”的塑造》(载《当代文坛》2010年第6期)侧重梳理的是贾平凹小说创作的批评史,时间跨度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新世纪初。论者认为批评对“贾平凹形象”塑造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塑造、改写和修复“贾平凹形象”过程中,文学批评也裹挟了大量其他因素和信息。在这一双向互动过程中,批评家的文学观念和知识结构也发生了深刻而积极的变化。从批评史的角度来认识贾平凹的创作,显然具有“知识考古学”的价值。张博实的《以“中国之心”诠释当代中国经验——新世纪以来贾平凹创作研究述评》(载《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3期)延续上一篇的评论研究路径,也从评论史的角度总结了新世纪十年贾平凹研究的概况。新世纪十年,对于贾平凹的研究主要涉及对《废都》的重评及《秦腔》、《古炉》的评价。论者认为真性情是贾平凹的创作个性,近十年的贾平凹小说充满了厚重的“落地”之感。从语言方面对贾平凹小说进行总结性研究的论文数量不多。汪政、晓华的《“语言是第一的”——贾平凹文学语言研究札记》(载《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是其中之一。论文主要从贾平凹作品中的古语和方言研究入手,指出贾平凹对于语言的声音效果要求严格,通过对短句式的大量使用及方言、古语的插入使得其小说语言厚重精练。
在这些综述类文章中,需要重点提及的是陈晓明的《穿过“废都”,带灯夜行——试论贾平凹的创作历程》(载《东吴学术》2013年第5期)。这篇文章概述的是贾平凹1980年至2013年的创作,重点论述其
小说创作,旁及散文创作及语言风格。论文论述全面、论点精到,显示出论者扎实的研究功底和犀利的学术眼光。还有李遇春的《“说话”与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文体美学——从〈废都〉到〈带灯〉》(载《小说评论》2013年第4期)也是近年来国内贾平凹研究中的一篇颇有分量的论文。论文选取小说与“说话”之间关系的研究角度,从古今文学演变的宏观文学史视野出发,对贾平凹从《废都》到《带灯》以来的全部长篇小说创作作出了饶有新意且有深度的文体考察。论文深入地揭示了贾平凹几十年来在追求小说现代化的同时所从事的小说民族化和中国化的艺术努力,比如对中国传统“闲聊式”说话体长篇小说的创造性转化,对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中人物群像式“块茎”文本结构的艺术吸纳,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细节流”长篇小说文体的艺术开创,对中国古代文学中“史传”与“诗骚”传统的艺术融合等。
除了上述以论文形式出现的综述类文章外,还有一类整体研究属于会议和访谈类,这类论文也较为全面地总结了贾平凹不同阶段的创作特色。如会议类:《作家,是属于时代的——“贾平凹作品学术研讨会”发言摘要》(陈思和等,载《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5期);访谈类:《关于小说创作的问答》(贾平凹、韩鲁华,载《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1期)、《贾平凹与新时期文学三十年》(贾平凹、黄平,载《南方文坛》2007年第6期)、《传统暗影中的现代灵魂——贾平凹访谈录》(李遇春、贾平凹,载《小说评论》2003年第6期)、《“把作品打造成一句成语”——贾平凹先生访谈录》(邰科祥,载《文艺研究》2008年第11期)。
贾平凹整体研究主要论述的问题包括题材研究(乡土、底层题材)、心理研究(乡土理想、欲望叙事)、叙事研究(叙述范式、语言特点)等。不同的评论家都认同贾平凹是一位乡土题材的作家,通过描述城乡变迁中不同背景社会群体的情绪反应来思考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及文化命运。
二、贾平凹小说的作品评价
贾平凹的作品评价类文章数量多,这是其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贾平凹的早期研究中,丁帆的《谈贾平凹作品的描写艺术》(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和阎纲的《贾平凹和他的短篇小说》(载《光明日报》1980年2月6日)等文章较早地开始描述和总结贾平凹的小说创作特色。丁帆的《谈贾平凹作品的描写艺术》通过形象分析《麦收时节》、《美》、《进山》等,指出作品中人物具有“姿”与“韵”兼备的意境美。阎纲的《贾平凹和他的短篇小说》主要针对贾平凹早期作品《竹子和含羞草》、《满月儿》指出其创作中清新、淡雅的特点。很快,关于贾平凹小说作品的评论文章越来越多,而且这一类研究成果视角多元,极大展示了评论家的创作力和活力。其中下列论文研究视角较有特色、研究水平较高:雷达的《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载《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6期)、陈晓明的《乡土叙事的终结和开启——贾平凹的〈秦腔〉预示的新世纪的美学意义》(载《文艺争鸣》2005年第6期)、谢有顺的《尊灵魂,叹生命——贾平凹、〈秦腔〉及其写作伦理》(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5期)、吴义勤的《“贴地”与“飞翔”——读贾平凹长篇新作〈带灯〉》(载《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3期)等。
贾平凹的作品评价类论文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1)小说《废都》的褒贬评价;(2)小说《秦腔》的认知理解;(3)小说《带灯》的底层代表性。针对这三部长篇小说,不同立场的评论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对《秦腔》、《带灯》等作品的评价多持赞赏态度,而对《废都》的评价则争议较大。
1993年,《废都》的出版给文坛带来了巨大的震撼。针对这一作品,各种评论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其中大部分的批评是负面评价和情绪宣泄。雷达的《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避免了对《废都》好坏优劣的情绪化评价,认为《废都》的写作与作品特定的文化环境分不开,并且认为《废都》是当代一部重要的“世情小说”。雷达的观点对于为争议中的《废都》定调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陈晓明的《废墟上的狂欢节——评〈废都〉及其他》(载《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则较多地运用西方理论来解读这部小说。陈晓明认为,《废都》实际上是贾平凹自身镜像的反映,性在这篇小说中的地位不仅引起了读者的联想,而且通过“缺席”的性将阅读史与当下阅读体验勾连起来,从而变成一部关于性的文化稗史。这篇评论较有价值之处在于论者充分认识到《废都》的象征意义,将《废都》的出现认作是知识分子立场的消退和狂欢时代的来临。现在看来,这一观点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是相当精准和前瞻的。
《废都》的出版引起的讨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贾平凹的创作及评论界对于《废都》之后的长篇小说的认知,明显的证明就是对《高老庄》、《怀念狼》、《土门》、《白夜》等小说的评价均不是太高。对这些小说有较为详细、精彩的评论文章主要有旷新年的《从〈废都〉到〈白夜〉》(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孟繁
华的《面对今日中国的关怀与忧患——评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土门〉》(载《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1期)、丁帆的《“新汉语文学”的尝试——〈怀念狼〉阅读断想》(载《小说评论》2001年第1期)等。
这一创作和评论相对低潮的状况在《秦腔》中得到了扭转。《秦腔》出版后,立即得到一致的赞誉,并荣获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谢有顺在《尊灵魂,叹生命——贾平凹、〈秦腔〉及其写作伦理》一文中对《秦腔》作了一次文本细读式的解读,论者认为一个优秀作家的写作应该具有“文学整体观”,即:“国家·社会·历史”维度;叩问存在意义的维度;超验的维度,即与神对话的维度;自然的维度。《秦腔》体现了贾平凹的“文学整体观”。在《秦腔》中既有作家对于社会历史命运的思考,又有自然与人的意义的追索。因此,《秦腔》确实代表了贾平凹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较高水平。不仅如此,《秦腔》建构起了一套新的叙事伦理,即日常化叙事。这种将见解与看法隐藏于叙述背后的做法,实际上代表着作家对于生命原始形态的尊重及生命悲凉本质的认知。刘志荣的《缓慢的流水与惶恐的挽歌——关于贾平凹的〈秦腔〉》(载《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与谢有顺的观点一致,但对于《秦腔》中缓慢如水的叙述节奏背后体现出的作家对于乡村衰败惶恐、心酸、分裂的情感有了进一步的揭示。《秦腔》对于秦腔命运的讨论不再是作者关注的重心,而如流水般叙述的背后是作者对于不断涌现的文坛风潮的倦怠与反拨。
李星的《人文批判的深度和语言艺术的境界——评贾平凹长篇小说〈高兴〉》(载《南方文坛》2008年第2期)及徐德明的《乡下人进城的一种叙述——论贾平凹的〈高兴〉》(载《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均从农民工进城的叙述可能性的角度讨论了《高兴》的意义。李星认为《高兴》除了题材价值外,白描式的语言也是其鲜明的特点。徐德明将新世纪乡下人进城的可能性进行列举,在众多的可能性中,《高兴》与“建筑民工群体”、“拾破烂群体”、“讨饭群体”等悲情叙述不同的是,《高兴》的基调复杂,哀乐杂处、层次鲜明。李遇春的《底层叙述中的声音问题——评贾平凹的长篇新作〈高兴〉》(载《小说评论》2008年第2期)进一步指出,贾平凹在《高兴》中是想发出作者独特的声音,表达他对当下中国农民工生存境遇的另一种积极的理解,但这种理解与社会上普遍流行的底层意识之间存在着距离,由此带来了底层叙述中乐观的旋律与沉重的底色之间的声音裂隙。
《古炉》是贾平凹的一部忆旧之作,也是贾平凹目前唯一描写“文革”题材的长篇小说。王德威的《暴力叙事与抒情风格——贾平凹的〈古炉〉及其他》(载《南方文坛》2011年第4期)将《古炉》与沈从文的《长河》做比较,认为两者之间都有将暴力叙事抒情化的倾向。在论者看来,这种诗意化的处理是一种“危险的对话关系”,这种“危险的对话关系”让暴力叙事的情绪淡化,而这正体现了贾平凹对中国现代抒情传统的思考。李遇春的《作为历史修辞的“文革”叙事——〈古炉〉论》(载《小说评论》2011年第3期)从历史与记忆、历史与隐喻、历史与伦理三个层面分析了《古炉》重建的“文革叙事”特征,指出这种“文革”小说既有“历史小说”的历史性,又有“新历史小说”(作为“新写实小说”的变体)的写实性,因此有别于传统历史小说的宏大叙事。该文还重点剖析了“造反派”夜霸槽和“走资派”朱大柜的艺术形象,指出《古炉》在艺术典型形象塑造方面达到了很高成就。
《带灯》是《秦腔》之后,贾平凹长篇小说的又一座高峰。作品着眼于新世纪日益激烈的贫富差距问题,将“维稳”这一敏感话题作为题材,显示出作者直面问题的勇气及新世纪农村问题的尖锐。陈晓明的《萤火虫、幽灵化或如佛一样——评贾平凹新作〈带灯〉》(载《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3期)十分尖锐地指出,带灯的出现实际上意味着社会主义新人系列的“幽灵化”。无论是《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艳阳天》中的萧长春,还是《新星》中李向南、《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社会主义新人序列中尚未出现如带灯般如此乏力的形象。吴义勤的《“贴地”与“飞翔”——读贾平凹长篇新作〈带灯〉》(载《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3期)认为《带灯》除了延续贾平凹一贯“贴地”描写的现实主义风格外,还展现了带灯“飞翔”的一面。这种理想主义情怀既体现在与竹子的闺蜜之情上,也体现在与元天亮柏拉图式的情感中。小说结尾带灯被萤火虫包围的场景显然是“飞翔”的带灯形象的大胆升华,也是作者理想主义情怀的集中爆发。
作品评论类论文也有一部分属于会议类或访谈类。如会议类:《〈土门〉与〈土门〉之外——关于贾平凹〈土门〉的对话》(刑小利、仵埂、阎建滨、李建军、孙见喜、王永生、贾平凹,载《小说评论》1997年第3期)、《贾平凹长篇小说〈带灯〉学术研讨会发言摘要》(贾平凹、丁帆、陈思和等,载《扬子江评论》2013年第4期);访谈类:《闲谈〈高老庄〉》(贾平凹、孙见喜,载《文学自由谈》1998年第5期)、《贾平凹访谈
录——关于〈怀念狼〉》(廖增湖,载《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4期)等。
与整体关照类论文不同,作品评价类论文往往从某一部作品入手,注重文本写作特色分析及与其他类似文本的比较。许多观点闪烁着思想的光芒,例如丁帆对贾平凹早期小说的感受、雷达认为《废都》是当代重要的“世情小说”、陈晓明评价《废都》是“时代精神”的反映、谢有顺认同《秦腔》的“文学整体观”、王德威认为《古炉》有民族苦难抒情化之嫌、陈晓明认为《带灯》是“社会主义新人的幽灵化”、吴义勤将带灯形象描述为“贴地”与“飞翔”等,均是十分精确到位的判断,有力地将贾平凹小说研究引向深入。
三、贾平凹小说的比较研究
贾平凹小说研究中有一类属于比较研究,即将贾平凹小说与古今中外小说作比较。这类比较研究又可具体分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两类。
影响研究具体可分为:(1)传统文化影响,例如栾梅健的《与天为徒——论贾平凹的文学观》(载《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6期)等。(2)外国文化影响,例如姜智芹的《欧洲人视野中的贾平凹》(载《小说评论》2011年第4期)等。平行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之间的比较。例如:樊星的《民族精魂之光——汪曾祺、贾平凹比较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6期)、梁颖的《自然地理分野与精神气候差异——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比较论之一》(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等。
贾平凹的创作中有着古今中外文学影响的因素。栾梅健的《以天为徒——论贾平凹的文学观》较为全面地论述了贾平凹文学观的形成原因。该文从贾平凹论沈从文的文学观出发,总结“以天为徒”是两者之间共同的文学创作观。这一点与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相似,川端康成也认为天、地、人的和谐和合一是文学创作的核心。从这一总的理念出发,论者发现地理环境、生理条件、家庭背景均影响了贾平凹的创作。从《满月儿》到《废都》、从《高老庄》到《古炉》均体现了贾平凹“以天为徒”的创作理念。
贾平凹的创作在宗教方面受到道教的影响较多,这一点曾在胡河清的《贾平凹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6期)中得到了论述。《贾平凹论》用博学的道家知识阐释贾平凹早期创作的特色,令人耳目一新。另外,陈绪石的《论贾平凹创作中道家悲剧意识》(载《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与程亮的《道教“贵柔守雌”思想对贾平凹小说的影响》(载《宗教学研究》2008年第1期)等文也论述了贾平凹小说中的道家思想。前者通过列举贾平凹的“土匪系列”、《废都》、《白夜》等作品证明贾平凹的“人生如梦”的道家意识。后者主要分析《废都》之后的贾平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认为小说主人公充满了道教的隐士思想和“贵柔守雌”的价值立场。石杰的《贾平凹及其创作的佛教色彩》(载《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另辟蹊径,提出贾平凹小说中的淡泊超脱的人生观和“静虚思想”与佛教有直接联系,论者列举的是《三目石》、《太白山记》等作品,这样的分析也有一定的道理。
贾平凹的小说除了受宗教影响外,还有文学方面的影响。例如雷达的《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和陈晓明的《废墟上的狂欢节——评〈废都〉及其他》都提到了《金瓶梅》、《红楼梦》、《西厢记》等世情小说对《废都》创作的影响。不仅如此,李陀的《中国文学中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意识——序贾平凹著〈商州三录〉》(载《上海文学》1986年第1期)、李振声的《商州:贾平凹的小说世界》(载《上海文学》1986年第4期)等都提出“商州系列”小说明显带有明清笔记体小说的痕迹。贾平凹的小说不仅受“庙堂文学”的影响,也有民间文学的因素。张器友的《贾平凹小说中的巫鬼文化现象》(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4期)认为,贾平凹小说中不少地方涉及到民间神秘文化现象。
贾平凹的小说不仅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也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黄嗣的《贾平凹与川端康成创作心态的相关比较》(载《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从创作心态的角度比较了贾平凹与川端康成之间的相似性:童年时期的孤儿气质,走上文学道路后对于禅宗文化的迷恋浸淫,以及避世逍遥的心理。沈琳的《试析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贾平凹创作的影响》(载《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3期)着重分析了《百年孤独》与贾平凹小说之间的相似性,认为贾平凹对马尔克斯作品中孤独感的接受、拉美农村与商州农村描写存在的相似性、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现代派文学研究的兴起是其影响产生的前提和基础。
影响研究有接受影响的一面,同时也有施与影响的一面。近年来,贾平凹在欧美、日本等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大。《西方读者视角中的贾平凹》以及《欧洲人视野中的贾平凹》集中讨论了贾平凹的作品在欧美国家的传播。韦建国、户思社的《西方读者视角中的贾平凹》(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从
《浮躁》谈起,重点讨论了《浮躁》、《废都》等作品在法国的影响及评价。姜智芹的《欧洲人视野中的贾平凹》(载《小说评论》2011年第4期)讨论的视野更宽阔一些,涉及的作品也更多。文章从三个方面探讨了贾平凹作品在英语、法语世界的传播:一是国外的译介与影响;二是国外的研究;三是传播与接受的原因。国外研究论文则主要以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的中国学者写作的贾平凹论文为主。其中悉尼大学王一燕的《叙说中国:〈废都〉和贾平凹的小说世界》是其博士论文。该论文以霍米·芭芭的“国族叙述”(national narration)为理论依据,讨论了《浮躁》、《白夜》、《土门》、《高老庄》等作品。另有多伦多大学司徒祥文的《农民知识分子贾平凹的生活和早期创作的历史-文化分析》、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郑明芳(英译)的《贾平凹20世纪90年代四部小说中的悲剧意识》和方金彩(英译)的《中国当代作家张贤亮、莫言、贾平凹创作中的男性气质危机和父权制重建》等论文(以上四篇海外论文转引自姜智芹的《欧洲人视野中的贾平凹》)。随着贾平凹在国际文坛上影响力的不断增加,已经有学者开始讨论《带灯》等新作的翻译与推广问题,例如杨慧仪就在《呼唤翻译的文学:贾平凹小说〈带灯〉的可译性》(载《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5期)一文中讨论了《带灯》的翻译传播问题。除了英美国家的传播外,吴少华的《贾平凹作品在日本的译介与研究》(载《小说评论》2014年第5期)重点介绍了日本对于贾平凹作品的翻译和研究状况。
文本比较方面主要以中国现当代作家为参照评价体系,比较其创作风格上的异同。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载《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将沈从文与贾平凹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指出二者之间均具有“乡下人”意识。沿着地域文化讨论的话题,李振声的《贾平凹与李杭育:比较参证的话题》(载《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3期)将贾平凹的西部文化与李杭育的吴越文化进行对比,指出二者在“寻根文学”时期创作的代表性篇什为各自的地域文化书写作出了贡献。当我们讨论“西部作家”这一整体概念时,其实作家之间还是有一些差异和区别的。梁颖的《自然地理分野与精神气候差异——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比较论之一》(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将西部三大作家进行比较,从自然地理上的差异分析对各自创作上的影响:路遥的创作带有陕北高原的刚毅与悲凉,陈忠实的创作具有关中地区的厚重与朴实,贾平凹的创作则带有陕南地区的灵秀与清奇。
除了从地域文化差异的角度进行比较外,还有从作家心理、气质等角度进行比较的。例如樊星的《民族精魂之光——汪曾祺、贾平凹比较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6期)将汪曾祺与贾平凹进行比较,认为汪曾祺小说中呈现出的士大夫的幽远境界在贾平凹的小说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两者之间在摹写“民族魂”的角度上是统一的。张英伟的《疾病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贾平凹与史铁生比较研究》(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从疾病对作家心理状态的影响入手,分析疾病对贾平凹和史铁生两人创作的影响。论者认为在与疾病的斗争过程中,两人均表现出超强的毅力和斗志,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对于生命都有了更深的体验和感悟。
四、贾平凹小说研究中的质疑声音及其他
除了赞誉、肯定的声音,还有一类论文对贾平凹小说创作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批评。例如张志忠的《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李建军的《消极写作的典型文本——再评〈怀念狼〉兼论一种写作模式》(载《南方文坛》2002年第4期)、李建军的《私有形态的反文化写作——评〈废都〉》(载《南方文坛》2003年第3期)、吴炫的《贾平凹:个体的误区》(载《作家》1998年第11期)等文章对贾平凹创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出了批评和指责。例如吴炫就指责《废都》思想平庸和落后;张志忠批评《高老庄》有太过强烈的自我迷恋,存在明显的理念大于形象、神秘主义泛滥以及男权主义倾向明显等不足;李建军则认为《怀念狼》是“消极写作”的典型文本。这些反思和质疑性的文章为贾平凹小说价值的再评价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以上三类基本囊括了贾平凹研究的主要问题,可以看出重视宏观综述和作品分析仍是贾平凹研究的重点和着力点。研究中略显不足的是关于贾平凹小说语言研究的成果不多。另外,相比于贾平凹的小说研究,贾平凹的散文研究略显薄弱和滞后,不仅数量少,而且整体水平也有待提高。“文坛劳模”贾平凹的创作仍在不断延续,对其创作的研究也在不断延展,期待会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不断面世。
[责任编辑:熊显长]
[作者简介]叶澜涛(1980-),男,湖北黄石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3BZW11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资助项目:CCNU14Z02017
[收稿日期]2015-04-08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2016)01-002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