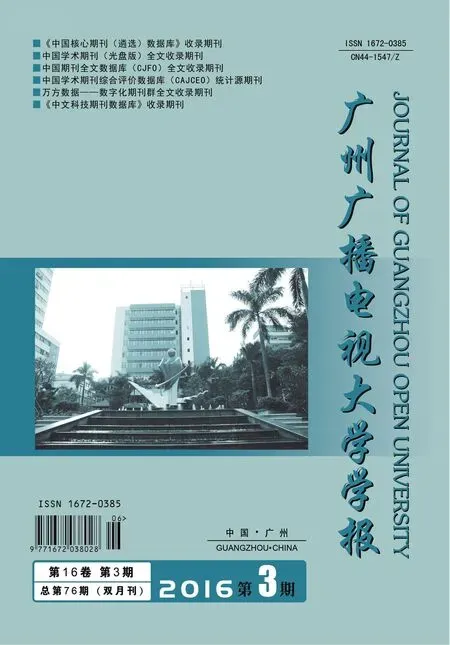艰难的涉渡之舟:曹禺早期戏剧叙事伦理*
张 亮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艰难的涉渡之舟:曹禺早期戏剧叙事伦理*
张亮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摘要:曹禺早期剧作所处理的题材常具有明显的伦理意味,时常通过塑造矛盾人物形象,从伦理角度深刻地开掘人类行为动机及其复杂后果。叙事伦理批评开创了审美和价值研究的新思路,笔者拟从叙述伦理的维度去解读早期曹禺创作中的价值取向,以期开掘出作者隐匿于文本背后的伦理取向及其功能意义。
关键词:曹禺;《雷雨》;蘩漪;《原野》;仇虎;叙事;伦理
曹禺早期剧作所处理的题材常具有明显的伦理意味,如乱伦、“三角恋”、“始乱终弃”、卖身、复仇、婆媳矛盾等。剧中人物形象虽然有若干侧面,但是读者的兴奋点常常落脚于伦理层面,而且读者对剧作中人物形象进行臧否时常借助伦理尺度。曹禺通过塑造这些人物形象,从伦理角度深刻地开掘人类行为动机及其复杂后果。因此,曹禺早期剧作的主题亦称之为“复杂的主题”,即通过描述现代人面对种种两难伦理冲突所陷入的困境,揭示伦理问题的复杂性。[1]法国著名的小说家昆德拉曾经盛赞塞万提斯的小说,这是因为在塞万提斯的“鸿篇巨帙”中,布满了生存的陷阱与雾霭,然而作者既不希冀指出一条“光明大道”,也从未故意地铺设一条“天台迷路”。人生的诸多头绪似乎总是真假莫辨,似是而非,经常令身处其间的人类不解其意,左右不是。[2]同样地,从《雷雨》诞生的那天开始,各种疑惑与争论也从未间断,尤其是文本叙事中各种伦理体系之间的交锋、更嬗,主题呈现出了深浅不一的层面、驳杂多端的内涵,这些均使得读者很难从传统的理性伦理视角作出非此即彼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简单判断。面对这样的一种两难抉择的情形,“叙事伦理”提供了一种新的维度去重新打量这样一种“两难抉择”,具体的操作方法一般是 “通过文学叙事来呈现生存的伦理状态,……是叙事的结构、形式、姿态、语调以及叙事意图、叙事功能所构建的伦理空间 ”。[3]据此,笔者拟从叙述伦理的维度去解读早期曹禺创作中的价值取向,以期开掘出作者隐匿于文本背后的伦理取向及其功能意义。
一、新旧伦理矛盾及其内在冲突
从本质上来讲,叙事伦理是希望艺术地表现人世间的善恶是非等一切关乎伦理的主题,然后为读者呈现一个个形象可感的典型人物,从而借此树立某种榜样或者是敲响某声警钟,进而承担起文学艺术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然而,曹禺并没有止步于单纯树立一个榜样或惩戒。他首先在《雷雨》中对中国传统的“伦理/乱伦”进行发难。在“暴露了大家庭的罪恶”的《雷雨》中,一系列不能两全、无法弥合的孽缘情仇撕扯着蘩漪、周朴园以及周冲、四凤、鲁侍萍等人。概括地来说,蘩漪追求幸福,合乎伦理;与继子周萍产生情愫,违背伦理;不断干扰、嘲讽周朴园的夫权,顺应了五四以来中国妇女摆脱传统伦理束缚,追求自我解放的时代潮流;阻挠周冲婚恋自由、蔑视四凤“始终是个没受过教育的下等人”的封建门第等级观念,与五四新文化破除封建等级制度,主张人人平等的文明新风格格不入。蘩漪在“理所当然”地反抗和报复周朴园和周萍的同时,却中风狂走般地伤害了四凤和鲁侍萍,甚至殃及天真无邪的周冲。不能否认,大力宣扬个性解放、婚姻自由对中国传统伦理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将其作为反对传统伦理的思想依据也在情理之中。蘩漪毫无顾忌地反叛传统伦理,却由于自身“半新不旧”的特征,一只脚迈入极端自我主义的泥淖里,一只脚又掉入传统势力的罗网中,最终在歇斯底里中走向了毁灭。剧中的蘩漪犹如行走在生存的雾霭之中,她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在面对伦理问题时灵魂深处呈现出反抗、挣扎并试图保持独立的人格姿态,但却不知如何在合乎伦理的框架内做出反抗,并在传统道德与“五四新风” 两者之间的夹缝中独善其身。除此以外,这种存活于夹缝中的窒息感也折射出任何一个处于转型期背景之下的人类,包括中国人在近现代所面临的一次又一次的“选择恐惧症”。此外,在《雷雨》中,伦理与个体冲突的模式也表现在周朴园不同人生阶段的不同选择。青年时期的周朴园在新思想的影响下,公然挑战传统伦理“门当户对”和“父母之命”的观念,与侍女鲁侍萍自由恋爱生子,可惜周朴园最后还是在父母的干涉之下渐渐走上了为封建论理代言的道路,例如他压制蘩漪的个性自由发展,逼疯蘩漪,反对周冲的人道主义做法,言行威慑使周萍懦弱等。一个人在不同阶段作出前后两种不同的伦理取向,其实是后者通过异化个体、渗透个体,从而大显传统伦理淫威的重要表征,这表明了存在于新旧伦理之间的外部矛盾的不可调和性。
诸如蘩漪、周朴园、仇虎此类具有复杂内涵的典型形象,其存在本身便意味着一种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然后往往从中可以窥见作者忽隐忽现的伦理取向。回顾《原野》一剧中的仇虎,他在伦理与个体的矛盾冲突中逐渐陷入迷狂无望的过程。在悲怆的命运之下,仇虎“值得人的高贵的同情,他代表一种被重重压迫的真人,在林中重演他遭受的不公”。整体而言,所谓“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仇虎复仇是合乎传统伦理的;面对瞎眼的焦母、懦弱的焦大星,坚持“父债子偿”便会置身于欲放弃又不甘的尴尬境地,这显然是传统伦理中值得严肃商榷的部分。而且仇虎挣脱樊篱,采取了极端的复仇方法,最终还在枪口下结束了自己生命的做法也很难说是传统伦理或新伦理所提倡的。仇虎与初恋情人花金子彼此爱慕,是合乎新伦理当中承认和尊重个体追求幸福权利的核心要求的;然而花金子是有夫之妇,情敌焦大星还是一起长大的好友,“通奸”或“婚外情”的罪名也是被传统伦理与新伦理所悬为厉禁的。于是这里便暴露出了两对矛盾:(1)传统伦理的内在矛盾;(2)新伦理的内在矛盾。由此可见,现代中国人不仅面对新旧伦理之争,尤其是还必须面对新的伦理准则体系以及传统伦理准则体系自身内在的冲突。蘩漪追求幸福却走向乱伦,仇虎为声张正义复仇却导致伤害无辜,二人最后毁灭了他们所反抗的对象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试想现代人遭遇这两对矛盾的时候所面临的重重高压,只会逼使现代人陷入更大的绝望与痛苦之中。
二、深刻而复杂的伦理意味
事实上,所谓“复杂的伦理主题”正是曹禺早期剧作令作者感到徜徉恣肆、衔华佩实的关键原因之所在,在文本中营造出深刻而复杂的伦理意味也称得上是曹禺先生戛戛独造。五四新伦理的核心是“个人本位主义”, 蘩漪和仇虎顺理成章地可以视为“个人本位主义”的亲身体验者,他们的言行举止都高扬“个人本位主义”的大旗,甚至其最终命运的指向可以看做是“五四”新伦理的“殉道者”,极度不满和鄙视传统伦理对人性的蔑视与戕害,他们为了砸碎传统伦理价值体系甚至不惜受苦乃至付出宝贵的生命去坚守自己的信仰,以上这些观点和看法都无须赘述。不过深入到他们反抗行为的细节本身时会发现,传统的伦理价值体系固然被撼动了,可惜人类伦理中还有一种重要的东西叫做“善良风俗”,它虽然不在法律条文的范畴之内,却也应该是人类文明的“大经大法”或者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金科玉条”。至于像蘩漪这样与继子周萍乱伦的行为、仇虎滥杀无辜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仅仅被视作违背社会伦理的行为,诸如此类违反社会基本伦理的行为,其实从心理机制上切入分析的话很可能是从一般个性主义滑向了极端利己主义的泥淖之中,问题更严重的还在于,这些行为难道没有曲解或者妖魔化“五四”运动所提倡的新伦理中关于“人道主义”的精神么?“五四”现代人道主义社会改造观的总原则就是“爱的哲学”观,主张以“爱”的力量,而绝不是暴力、反抗的方式去彻底解决人类问题,实现世界的大同,易言之,“勿以暴力抗恶”。蘩漪和仇虎的行为既违背旧的伦理秩序也不合新伦理的要求,虽然“事出有因”貌似“情有可原”,但“乱伦”和“杀人”却严重地践踏了“人道主义”之“爱的哲学”,极端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产生矛盾,使他们的行为产生了难以挽回的恶果——蘩漪伤害了四凤、周冲,仇虎杀害了焦大星和小黑子。
纵观曹禺早期剧作中的经典人物例如蘩漪或仇虎,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新伦理内部的那种焦灼与激撞,易言之,他们一旦行动总是会将人道主义抛诸脑后,而“义无反顾”地选择“个性主义”,坦白地讲这正是新伦理的一个可能存在的内在缺陷。梁漱溟曾指出:“人在情感中,恒只见对方而忘了自己;反之,人在欲望中,却只知为我而顾不到对方。”[4]在《雷雨》和《原野》里,曹禺对新伦理的内在缺陷有着深刻的认识,可以将蘩漪与仇虎的困窘与毁灭视作他为读者留下了一道暗语,启迪读者对新伦理的内在缺陷产生合理的怀疑,并试图考虑是否存在摆脱这种两难困局或矫正弥合这种内在缺陷的可能办法。答案也许可以从《北京人》和《家》中寻找。对比《雷雨》《原野》与《北京人》《家》发现, 一个循环往复的逻辑悖论始终萦绕在曹禺早期剧作的上空:新的伦理破坏和反对传统伦理,传统伦理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矫正、弥合新伦理的内在缺陷。简单说来,蘩漪和仇虎很大程度上崇尚自我,背弃传统;愫方和瑞珏则奉献自己、固守传统。愫方和瑞珏放弃了自己生命中最美丽的年华去陪伴和温暖两个行将枯朽的生命,而且曾文清和觉新的生命是缺乏内核价值的,可也正因如此才衬托出愫方和瑞珏的隐忍与奉献,这是她们奉为“圣经”的伦理价值,但其实这根本是不值得的。由此愫方和瑞珏的行为不免落入传统伦理的窠臼当中。但是,曹禺对这两位女性也是充满赞美和同情的,这同之前赞赏“雷雨”般性格的蘩漪和充满生命野性的仇虎显然构成了前后矛盾。虽然如此,读者依旧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是,愫方和瑞珏尽管在新伦理面前显得持守有余,不够先锋和激进,但仍旧无法轻易把她们归入祥林嫂、爱姑一样的“旧女性”甚至是焦母这样的负面形象,相反地,无论从传统还是新伦理的角度出发,她们似乎要比蘩漪、仇虎显得更高尚,读者更加激赏这种高尚中所内含的深情、坚忍与无私、克己。紧接下来的问题是,不在于是确认或否定哪一组形象身上体现的伦理准则,问题在于出现在曹禺早期剧作中的这类“摇摆不定”“模棱两可”的前后矛盾的叙事指向什么?它的功能与意义是何?
三、叙事伦理的功能指向
事实上,许多作家在处理“伦理”这样一个带有哲学思考的道德现象时,仅仅止步于形而上的思考是很难实现艺术和社会的双重功效的,而且有时候言之过甚更难令广大读者产生共鸣。相较于针对伦理问题的“皮相之谈”亦或是“高谈大论”,曹禺更擅长注意到日常生活之中处处都有闪现的伦理身影。曹禺笔下的伦理光辉是内在而坚实的,并非一些空洞的概念所能简单代替。从古至今,文学这一“万卷诗书事业”总是关乎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五四”新文学运动又再次提出文学应该是人的文学,所以叙事伦理最后指向的也应该是个人,它需得敢于直面人类生存境遇中的“模糊”地带,去抚摸和探照到那些我们习焉不察的角落里的人。从这个角度而言,叙事伦理成就了文学的重要使命,它让每一个人都确认了其存在的意义,尤其像我们这样一个被历史洪流裹挟而下的苦难民族,尊重传统与现代文明下的精神和灵魂性的事物,其实是具有非凡的意义的。曹禺虽然不是“牧师”,但却欢迎精神和灵魂性的事物进入自己的叙事当中,从而确立叙事的伦理价值取向。在曹禺的早期剧作中,他所构建的叙事伦理多着眼于新旧伦理的夹缝中,并且寓自己的多元思考于曲折的剧本故事和情节冲突之中。 面对那些恣肆或执着的剧中人物,曹禺经常会坐立不安或者扼腕兴嗟,但是却从来对公是公非未置一词。何况伦理其实根本不存在一个恒久不变的标准,它常常时移势迁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有所松动或转变。五四时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新旧不同的理念之间发生激烈的碰撞,国民的伦理价值体系历经洗礼与动荡,但是也赋予传统的伦理价值体系得以被重新打捞与清理的可能性。不过,曹禺没有追随其他作家清算传统伦理谱系、提出新伦理的步调,相反以一种超然的态度面对现实和人性的起伏变化,仿佛某种先验的体会使他觉察到新旧伦理之间的差距,并且朦胧地发现了一个事实,那便是新伦理所宣扬的“个人主义”“个性主义”在某些时候,正是造成以蘩漪为代表的那些人们悲剧的根源。有人将这种叙事姿态称之为“悖论叙事”或呈现状态,这正是曹禺早期剧作叙事伦理的核心所在。比如面对“乱伦”“始乱终弃”“男尊女卑”的题材,曹禺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究竟该作何取舍呢?对于作家而言,这些取舍问题显得略微棘手,但是这些问题到了社会学家手中就显得不是那么棘手了,因为这些人可以凭借专业知识和实证分析,然后就轻而易举地明辨黑白和计功量罪。不过即便如此,文学的意义也并不就是这样简单。叙事伦理使文学意义得以延伸具备了相当的可能性和实操性,它仿佛“探照灯”一般可以搜寻生命潮湿角落中的困惑与挣扎。质言之,叙事伦理从来不会标榜要去伪匡正或者是疗救社会,它只是将呈现生存境遇中的“尺水丈波”视为己任罢了。说到底,曹禺早期剧作大获成功就在于它搜寻到了生命潮湿角落中的困惑与挣扎,还原了伦理的相对性与不稳定性。曹禺深谙其中的奥秘,所以在关于“乱伦”“三角恋”“复仇”的处理上,文本叙事并没有停留在价值决断上,而是致力于倾听不同人物命运的喟叹与表现剧中人物进退两难的焦灼与疯狂,曹禺满怀敬畏地厘清一个事实,那就是人生是一个充满不可解决的伦理悖论的过程,这样便使得叙事走向了更为广阔的人性领域,从而诞生了《雷雨》、《原野》、《家》一系列早期剧作,让每一个观看戏剧的人遇见似曾相识的生命阵痛和人生悖论。
在五四新文学的创作队伍中,曹禺的剧作没有沉溺于展览身体性爱或者是“灵肉合一”的爱情叙事,他坚守着写作的理想与底线,乃至是整个生命的全部信仰。对于曹禺来说,戏剧既不是供人茶余饭后的消遣咀物,也不是社会革命的动员工具,而是开掘伦理价值取向的多种可能性,试图去相信每一种可能性的背后都有其合理发生的条件。假如曹禺在这部剧作中只专注于为张扬“现代”而否定“传统”,最终他还是会发现在那个时代的一切问题本来就没有表面那么简单。生活既不是提供善恶是非的道场,也不是对弈棋盘上讲究“排兵布阵”的棋子,生活中更多的是随心所欲和天马行空,即所谓的“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曹禺早期戏剧对人物命运和行为从不做普世性的价值评断,也源于此。个体生命的丰富性和张力性才得以彰显,剧作的叙事伦理的最终旨归就是这个丰富性和张力性,它为人类社会贡献了一种“伟大的力量”,支撑着脆弱而野性未泯的人类穿行于生存的雾霭之中。
结语
曹禺在剧作中没能明确给出针对伦理两难抉择症候的“药方子”,但这不能归咎于作者世界观的局限。首先,作家不是从事社会史研究的专家,他们无需强迫自己明辨社会发展的潜在规律,指引出一条通向幸福未来的康庄大道。与此同时,作家也不必向剧中人物的行为动机及造成后果进行纯伦理层面的臧否,也没必要向读者摆出一副“应病与药,令得服从”的说教架势,感染观众的戏剧永远是要诉诸情感的。其次,某种被读者或观众认为是艺术“空白”、“模糊地带”、“盲区”的东西,往往为艺术作品平添了许多意蕴层次,广大受众可以结合着自己的人生体验以及审美习惯,充分发挥自由的想象力,善于发现隐匿于作品背后的伦理价值的复杂性,这也正是艺术作品的生命力之所在。总之,叙事伦理作为一种新的批判思路和范式,为我们呈现了一种别样的审美价值评价尺度,正如西方人文修辞伦理学的观点,“叙事可以帮助塑造读者的情感、自我和生活观”。[5]如果用“生存迷舟”来比喻生活世界中所遵循的新旧伦理的话,我们需得搭载于其上来进行一次生命之旅,那么事实上每一个人的一生无异于一次艰难的涉渡,涉渡其间之艰难虽难以言表也不难想见,因为每一步所踏的很有可能正是新旧伦理的模糊地带,亦或是伦理准则评价被延期的“领地”。诚然,二十多岁的曹禺在完成早期剧作时,“没有明显地意识到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什么”,单凭“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既有异于李大钊、瞿秋白等一大批革命家提出的诸多主张,矢志要以马列主义来改造旧中国的传统价值体系,也不同于鲁迅和茅盾等社会活动家那样,可以一针见血地洞见复杂的社会现象背后的真相。但是曹禺却以青年人固有的热情也好,偏激也罢,用戏剧的形式“发泄自己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这一“叙事伦理”在整个现代文学中似乎是鲜见的,它集中出现在曹禺早期有着“复杂的主题”剧作中,为其内涵增添了整整一个深厚的充满历史感与现实意义的伦理层面。
参考文献:
[1]胡润森.曹禺悲剧中的伦理[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1).
[2]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152.
[3]杨红旗.伦理批评的一种可能性——三论小说评论中的“叙事伦理”话语[J].当代文坛,2006(5).
[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88.
[5]祝亚峰.叙事伦理文本批评的方法与途径[J].江淮论坛,2011(6).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385(2016)03-0083-05
*基金项目:南开大学2015年“知行南开”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计划(项目编号:A005)。
收稿日期:2016-05-12
作者简介:张亮,男,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