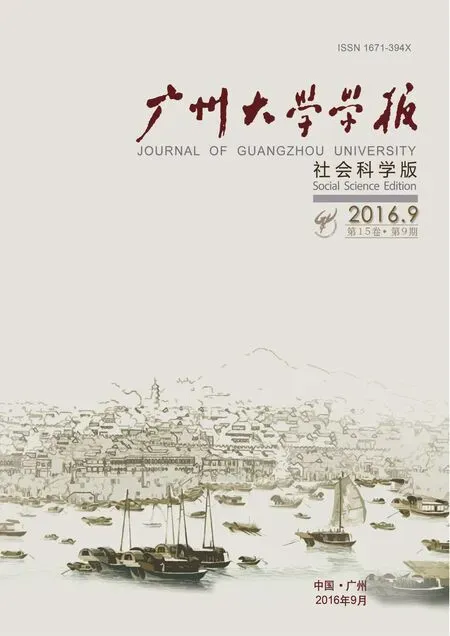论保障性住房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
车 栋
(东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论保障性住房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
车栋
(东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保障性住房政策实质上是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利益博弈,这一政策之所以在促进社会正义上功能不彰,主要原因在于与保障性住房密切相关的低收入群体无法参与到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保障性住房政策内在的公共性和福利性决定了公民参与保障性住房政策制定的价值;现代公共政策制定的民主化与科学化要求之间的张力使公民参与保障性住房政策面临参与的能力、搭便车和动力困境;而保障性住房政策公平与效率兼顾的现实需要,要求政府完善公民参与渠道,及时回应公民参与需求,实现二者在保障性住房政策制定中的良性互动。
保障性住房政策;公民参与;完善途径
引 言
住房不仅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基本生活品,而且还是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重要基础条件。早在汉代,“各安其居而乐其业”(汉书·货殖列传)就强调了住房的重要性,指出了“安居”与“乐业”之间的逻辑关系。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优胜劣汰,市场在调节住房资源分配上,必然会出现住房的数量和质量在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巨大、明显或潜在的差距。保障性住房政策便是一项为了纠正住房资源分配上的“市场失灵”,保障人们住房的基本权利得以实现,而由政府主导的一项公共和社会福利政策。
经过多年的探索,中国保障性住房政策处于不断完善中,保障性住房建设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保障性住房体系从无到有,规模不断扩大,覆盖面不断提高。”[1]“十二五”规划提出未来五年将建设3 600万套城镇保障性住房,全国城镇保障性住房覆盖率达到20%左右,基本解决了城镇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保障社会困难群众实现“安居梦”。[2]截至2013年底,已开工666万套,基本建成544万套,已全面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完成投资1.12万亿元。[3]
保障性住房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国家尤其是地方政府层面对保障政策的覆盖面和覆盖范围缺乏明确或准确的界定;设计过于烦琐和复杂,不利于实践操作和管理;尚未明确建立保障性住房运作的退出机制和封闭运行机制等问题。[4]在这些问题中,保障性住房分配的不公平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根据全国工商联房地产商会的REICO工作室在2005年对北京、太原、西安三地所做的调查显示,高达48%的经济适用房被用作商业出租,而普通商品房的比例仅20.55%。北京市受访业主中属于高收入的家庭占25.8%;属于较低收入(中等偏下)和低收入的家庭占22.3%。[5]这表明,保障性住房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偏离了既定的保障城市低收入者住房,实现社会公正的目标。
作为技术性的政策问题容易得到解决,但作为价值性的政策问题则比较棘手。保障性住房政策实质上是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利益博弈,这一政策之所以在促进社会正义上功能不彰,主要原因在于与保障性住房密切相关的低收入群体无法参与到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要实现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既定价值目标,就需要完善保障性住房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平衡机制。
一、公共性和福利性的内在价值:公民参与保障性住房政策制定的必要性
住房不仅是一项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而且也是重要的人权之一,这从根本上决定着住房政策必然涉及到每个公民,具有典型的公共性;而保障性住房则是为了纠正市场在住房资源配置中的缺陷,使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的个人或群体有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具有典型的福利性,其政策倾向于特定公民群体。这两个特性决定了相关利益群体参与保障性住房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的必要性,公民参与具有内在价值。
首先,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公共性要得以实现需要公民参与,特别是利益相关者的持续参与。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如何使政策真正具有公共性,使政策让社会每个成员都被纳入其中且受益,不同的理论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理性主义决策模型认为,一项理性的政策是获得“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政策,即政府应该选择那些使得社会效益最大程度地超过社会成本的政策。这就要求决策者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了解所有的社会价值偏好及其相对权重,了解可以获得的所有备选方案,知道每一备选方案的所有结果,计算每一备选方案的收益与成本之比,选择其中最有效的政策方案。理性主义决策模型具有明显的精英主义决策倾向,将大部分相关利益群体排斥在决策过程之外,相信精英群体的理性决策。而以林德布洛姆(C.E.Lindblom)为代表的渐进主义决策模型则认为,决策者的理性是有限的,在有限理性的条件约束下,某一政策便是对过去政策的补充和修正。之所以需要补充和修正,就在于认识到了公共政策的对象或利益相关者的反馈,这就开始突出了公民对于公共政策制定的价值。而公共选择理论则通过经济学的方法研究非市场决策,尤其是公共政策制定,认为政策是自利个人的群体选择。[6]虽然公共选择理论在政策制定模式上并不主张直接民主,而仍然坚持代议制民主,但该理论则强调了个人偏好和选择对于公共政策的价值。
现代社会使得个人和群体的选择日趋多样化,人们对于房屋的偏好必然具有多样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重要性并不仅仅表现在物质形态上,而是体现于以房屋为空间的个人、群体和社会情感,即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正如多尼森(D.V. Donnison)指出的,房屋不仅是住所,是可用来交易的商品,对于其居住者而言,更是一种作为家的情感寄托的东西。[7]既然房屋与更为复杂的情感相连,那么,作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就不可能对人们在房屋上所寄托的情感和期望有完全理性的认知。此外,由于政府信息的局限,不可能对社会每个成员的情况都有及时、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导致保障性住房政策在准入、分配、退出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保障性住房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大量信息需要利益相关者及时和全面的反馈,这样才能避免政策偏离目标。因此,保障性住房政策如何才能具有公共性,使“社会效益最大化”,必然需要以广泛的民意为基础,而畅通的公民参与则是民意得以体现最为重要的一种制度安排。
其次,保障性住房政策增进社会公正、扶助社会弱势发展的福利性也需要公民的参与。当前,中国处于全面的社会转型期,从利益关系角度看,社会转型期就是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重构的时期,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呈现什么样的形态以及是否合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益博弈主体之间的关系。在人民共和国,权力的人民性使得公共权力必然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各级政府努力将所有低收入者纳入保障性住房政策的覆盖范围。但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政策目标及其过程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变形和扭曲。因为在利益驱动和权力制约乏力的情况下,政府也是作为特殊的利益群体,会不同程度地将自身的利益与公共利益混合在一起,二者有时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离。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权力部门则会打着保障性住房的幌子谋取部门私利。如2005年至2009年,仅北京就有4 736公顷土地被作为经济适用房用地,占总供地计划指标的66%,但同期面向社会供应的经济适用房只占市场总供应量的7%左右,其余的经济适用房都“被内部”了。至于这些“被内部”的经济适用房用地划拨给了什么单位,建设了多少经济适用房,分配给了谁,都没有向社会明确公布。[8]
由于政府权力制约的乏力,保障性住房政策偏离既定目标的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不仅使原本旨在通过社会再分配促进社会公正的政策措施受到了影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影响会延续到下一代。伦德(B. Lund)认为,住房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其分配结果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公正产生密切联系,住房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可能会对居住者的受教育水平、身体健康程度等产生直接的影响,这使得他们与那些在住房资源上处于优势的富人相比,必然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而且这种情况可能会影响并延续下一代。[9]“市场失灵”并不是政府干预的充分理由,政府在实现社会公共资源的再分配过程中,也会由于权力的滥用而导致“政府失灵”。现代民主政治认为,公民参与是驯化公共权力的一种重要方式。除了以权力制约权力外,以社会权力制约公共权力也是避免“政府失灵”的必要措施。因此,社会福利权并不仅仅是被动接受,还需要公民积极参与激发政府主动承担增进社会公正的职责。
二、政策民主化与科学化之间的张力:公民参与保障性住房政策制定的困境
公民参与并不意味着任何公共政策的制定以及政策实施的每个阶段都需要所有或者大多数利益相关者的直接参与,公民参与注重的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诉求表达、相互协商以致理解和妥协,最后使票决的结果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因为在现代民族国家,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存在难以调和的现实困境,就公民参与保障性住房政策而言,这种困境也非常明显。
这种困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现代民主政治需要公共政策具有相对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公共政策具有公共性的内在价值,二者都需要公民的制度化参与;另一方面,以技术官僚和专家学者为代表的专业知识、科学知识与大众常识之间存在张力,二者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具有不对称性,通常表现为专业和科学知识取代大众常识,使公民参与趋于形式。前者主要涉及到公共政策的价值层面,而后者主要涉及到公共政策的操作和质量方面。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现实困境主要体现在后者。
对于复杂和专业的公共事务,自古以来,精英群体一直贬低大众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他们认为大众中的大多数是无知无能的,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很难有正确的时候,而政府治理是一种艺术和技能;而且由于大多数人是无知和愚蠢的,他们很容易受人蛊惑和摆布。[10]而到了现代,一般认为,公众在知识储备、信息收集和分析、问题认知能力、沟通能力、理性思考能力等方面远不及技术官僚、专家学者。就保障性住房政策制定而言,公民参与面临三个方面的困境:一是能力困境。如获取信息渠道狭窄、人际关系稀疏、对政府机构设置和办事流程不甚了解等,一般人只是被动地从媒体或他人获得保障性住房的相关信息,在保障性住房资源紧缺时,迫切需要群体难以比较顺利地向政府相关部门表达住房困难。二是搭便车困境。如果某一群体对保障性住房的建筑选址、房间格局、分配标准等不满意,那么,在信息、能力、诉求渠道、时间、财力等成本约束以及缺乏强有力的组织下,基于成本与收益的衡量,多数人都会倾向于选择搭便车行为。三是动力困境。由于能力困境和搭便车困境,必然会降低公民参与的效能。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开着好车住保障性住房,将保障性住房用于牟取私利,而本应享受保障性住房的弱势群体却无可奈何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公民在保障性住房政策中的声音越来越小,缺少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从而使保障性住房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公平正义的轨道。
在崇尚科学和专业知识的现代社会,大众常识通常被污名化为肤浅、短视、片面,甚至非理性。科学知识被过度推崇,而大众常识则被贬低或漠视。政府在制定保障性住房政策时,主要侧重于保障性住房的居住功能,注重在保障性住房选择方面吸收专家学者的参与,使保障性住房建设符合城市总体规划,能纳入快捷便利的交通网,提高土地利用空间等。却忽视了保障性住房的社会和政治功能。在现代社会,住房问题与个人的社会地位、社会处境、财富、权利等有关,在多种意义上呈交互式问题,而且,住房已成为社会阶层划分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表现。[11]如在很多大城市,保障性住房的选址就会受到土地市场价格的影响,大多数保障性住房只能选址在郊区。这些地方相应的交通、教育、医疗、市政基础设施、文化等设施比较缺乏,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保障性住房政策对象不能享受城市发展的成果,也造成了新的社会不公平。如北京公布的《北京市2008年住房建设计划》中,保障性住房主要集中在昌平、大兴、顺义等郊区,多分布于五环以外的区域。[12]上学难、出行难、治安乱等,成了保障性住房政策对象必须面对的问题。[13]
三、公平与效率兼顾的现实需要:公民参与保障性住房政策制定的政策目标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是既要有公平的价值取向,又要有政策制定过程与结果上的效率。就我国保障性住房覆盖率低、城镇化进程加快、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的现实而言,更需要做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正如所分析的,保障性住房的公共性和福利性是该政策的内在价值,决定了保障性住房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的必要性,而公共性和福利性也规定了公平是保障性住房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目标。而政策民主化与科学化之间的张力则需要对公民参与范围、程度、方式等进行规范,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实现保障性住房政策制定的效率。公平与效率相互间既存在张力,又相互影响,这种相克又相生的关系在保障性住房政策制定及建设过程中体现得比较明显。
当前,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在公平分配和效率两个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由于改革开放后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相对滞后,特别是重视建设而忽视对准入和退出的管理与监督,保障性住房建设的整个过程都有可能不同程度地存在侵害公平正义和效率的各种问题。如公职人员违规购买保障性住房现象严重,分配对象信息审查存在问题,保障性住房分配后闲置和转租转售现象突出等。[14]由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等单位支持设立的REICO工作室于2005年发布的《经济适用房政策评价》调查报告显示,很多地方的经济适用房被用作了投资。在对北京、太原、西安三地所做的调查中,经济适用房的自用率平均为70.29%,其中西安为92.1%,太原为80.25%,北京仅为51.34%,其经济适用房的出租率高达40%以上。在此次调查中还发现,北京市受访业主中属于高收入的家庭占25.8%;属于较低收入(中等偏下)和低收入的家庭占22.3%。[15]在保障性住房政策保障对象和标准不明晰、准入和退出机制等监管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就容易出现应享受住房保障的群体未被纳入保障范围,而不应该享受住房保障的高收入群体则滥用有限的资源,以及部分人通过保障性住房交易获得非法收益。在两会上,有政协委员就提醒这种不公平分配值得注意:“分配给不符合条件的家庭仅占很小的一部分。但是,正是这一小部分违规情况,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16]
保障性住房不仅仅承载着保障城市困难家庭和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而且也承担着为这些群体提供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发展成果的公平机会。但现实中,很多城市的保障性住房建设仅仅是为了完成政府社会保障的任务,而为充分认识和赋予保障性住房的其他社会功能。2010年西安市的廉租房实际保障户数已达到了16 928户,但这些住房大多处于城郊地区。[17]
保障性住房的不公平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保障性住房的使用效率不高。如对于保障性住房准入与退出机制的不完善导致对保障性住房对象群体的筛选和监管不严格,使不应享受保障性住房的人占有部分保障性住房资源,而急需受保障的群体却未被纳入保障对象。又如,保障性住房选址在郊区偏远地带、屋顶过低、房屋建设质量差、采光条件差、周边配套设置不完善、出行不方便等,既体现出保障对象在享受基本公共物品方面的不公平,同时也直接影响了保障性住房的利用率。如2007年12月,济南市建设的世纪中华城经济适用房就面临着尴尬局面,在符合申请购买的首批204户家庭中,竟有113户自动放弃选房,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地理位置偏远、周边配套不足等问题。[18]东莞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起步于2009年7月,但到2011年10月,与很多大城市保障房供不应求情况恰恰相反的是,东莞的保障房却一直面临着申请遇冷的窘境,规划目标4 852户却只有300户提出申请获得资格并成功选房。[19]因此,各地政府在制定保障性住房政策时,必须警惕因“政绩工程”而过分追求效率,这会从多个层面损害社会公平,进而使公平与效率陷入恶性循环,其结果必然导致有限资源的浪费、公共利益受损以及公民住房权与发展权无法得到保障。
因此,公平与效率必然是保障性住房政策在制定过程中必须放置首位的政策目标。李克强总理曾强调,公平分配是“保障性安居工程持续发展的生命线”,要“把确保公平分配放在更重要的位置”。[20]一般而言,保障性住房体系的运行机制和过程有四个方面:(1)供应规划体系包括供应体系和规划布局,这是保障性住房运行的前提;(2)进退管理体系包括配租体系、退出体系和管理体系,这是保障性住房运行机制的核心;(3)支持体系包括公积金体系和法律政策;(4)资金运作体系包括资金筹集和资金管理。[21]为了实现保障性住房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就需要根据保障性住房建设不同阶段的具体情况,不同程度地向公民开放,吸纳公民意见,整合公民偏好。特别是在保障性住房选址、准入和退出标准、监督管理等环节,更需要通过公民参与将保障性住房分配过程中的详细情况反馈给政府,从而使政府根据具体情况对原有保障性住房政策进行修改与完善,使之更能提高分配效率,有效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
四、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公民参与保障性住房政策制定的实现途径
保障性住房是一个涉及日常生活诸多方面的系统民生工程,这就决定了保障性住房政策制定既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又是一个涉及到社会一大部分群体的公共问题。不管哪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保障性住房政策制定的政策目标及价值取向。保障性住房政策要实现其预期目标,除一些专业知识需要由政府或专业部门单独完成外,保障性住房涉及公民日常需求的领域或环节,就必须重视公民参与,及时将公民诉求纳入与整合到政策过程。
一是加强和完善公民参与保障性住房政策制定的法律保障。当前,我国尚未制定有关保障性住房的法律,在现有的保障性住房的政策法规中,对于公民参与的规定仅限于原则性的模糊规定,而没有对公民参与进行可操作性的规定。因此,当前需要从公民的参与权利和监督权利两方面完善公民参与保障性住房政策制定的法律保障。就公民参与权利而言,相关法律的制定需要明确公民参与的主体,如哪些公民符合参与政策制定,这就涉及到是以户还是以公民为参与主体的问题;明确公民参与的程序,如公民在何时向政府相关部门提出诉求、以什么形式提出、如何获得政府相关部门的回应等。就公民监督权利而言,法律的制定需要明确公民实现监督权利的途径,如向立法机关反映,就需要从立法上明确立法机关的监督职责、范围和责任等;明确司法机关在保障性住房监督中的责任,使公民能够就权利和利益受损通过司法渠道进行维护;明确媒体在保障性住房监督中的权利,为公民监督赋权。通过多种监督渠道,切实保障公民监督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进而维护和实现自身合法权益。
二是完善和拓宽公民参与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渠道,使利益相关者的偏好和诉求能及时有效地表达出来,作为保障性住房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公民参与并不是越多越好,要提高公民参与的质量,就需要有序的公民参与渠道和机制。如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设置专门部门接待利益相关者,工作人员不能仅仅记录利益相关者的诉求,而是需要为其提供相关信息,引导其形成正确的认识。定期举行听证会,就保障性住房中的非专业领域交由政府、专家学者和利益相关者充分讨论。为保证听证会的有序、效率和质量,要提前对利益相关者的诉求进行归类,避免相同或相似意见的重复表达,也要给予利益相关者充分的表达时间。特别是保障性住房的保障范围、保障性住房保障对象的标准界定、保障对象的退出机制、保障房的分配程序、保障房的物业管理等,必须充分吸收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三是完善和加强政府相关部门及时的信息发布和政策回应。信息是公民参与的重要前提条件,信息内容的真实性与丰富性、信息发布渠道是否通畅、信息覆盖面是否广阔等,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公民参与的效果。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保障性住房不只是保障人们的居住需求,而且还与教育、就业、交通、消费、医疗、娱乐、安全等日常生活中的诸多方面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公民不能获得各方面的相关信息,那么,公民参与保障性住房政策制定就很可能出现短视、片面的情况,而看不到与保障房相关的长期规划和未来发展。这就需要各级政府根据相关法律切实做到公开保障性住房的相关信息:如政府主管部门、建筑单位的相关信息,住房保障工程规划,在建和已建保障性住房项目情况,保障性住房申请审核程序,保障对象信息,配租配售房源信息,公众参与情况(包括征询意见、投票的结果,经协商、听证后的有关会议纪要和结果)等。[22]各级政府还需要加大对保障性住房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完善政府门户网建设,将有关保障性住房的文件、政策制定过程、公民参与渠道、新闻媒介监督等相关方面的信息及时在网上公开;同时利用微信公众号、手机软件等媒介及时向公民发布各种保障性住房的相关信息等。另外,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公民参与存在着参与价值和参与实践方面的内在矛盾,要切实将利益相关者的诉求作为公共政策制定的依据,就需要完善和加强政府相关部门对公民的回应。如保障性住房在选址、保障范围、保障对象标准等方面,相关部门就需要通过设置专门服务窗口,利用媒体宣传、电话联系、网络等方式回应利益相关者的质疑;政府相关部门也需要就保障性住房的各个环节定期对利益相关者提供资料和现场讲解,等等。
四是建立特定保障区域的居民代表委员会和专家咨询委员会。居民代表委员会是基于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而建立的区域性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居民代表组织。居民代表委员会是临时性的自治组织,根据特定的程序和原则进行运作,进而将人们参差不齐的意见整合成为较为统一的利益诉求。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提高居民代表委员会整合意见的能力,政府需要向各居民代表委员会及时派出专业人员“深入当地群众,入街道,走住户,展示规划设计理念,使公众对规划设计的认知程度加深,专业人员引导公众对政府决策进行深度解读”[23]。通过这种利益表达和整合平台,有利于大众与政府就保障性住房进行利益表达、整合与互动,从而为公民参与保障性住房提供有效和有序的参与平台。专家咨询委员会是由相关专家学者组成,其功能是对公共政策中的专业性知识进行研究,为政府相关部门提供建议。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受政府委托或根据自身的研究需要及时深入社区进行广泛调研,了解相关利益者的现实需求,从而为政府保障性住房政策和建设提供专业意见。在保障性住房政策制定和实施环节,需要根据情况召开居民代表委员会和专家咨询委员会,就相关议题进行充分讨论和协商。
五是积极探索和完善多种吸纳公民参与的保障性住房建设模式。各级政府需要积极吸收、鼓励和支持市场和社会力量介入保障性住房建设。保障性住房承担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社会发展功能,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调节,因为市场机制调节也面临着“市场失灵”的困境。但“市场失灵”并不意味着政府干预的有效性。政府也面临着资金、信息、管理、监督等各方面的有限性。这就需要政府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中需要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职责和劣势,充分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弥补自身的不足。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上,政府不必只是保障性住房的唯一建设者,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实现和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如贵阳保障性住房就采取了一“建”二“买”三“收”的模式;[24]在保障性住房运营和管理上,可以采取“政府政策+市场运营”的模式,确定各自分工,吸纳多方力量参与,提高保障性住房管理过程中的效率和公平性。
[1]张占斌,李万峰,费友海,等. 中国城镇保障性住房建设研究[M]. 北京: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13: 37.
[2]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EB/OL].( 2011-03-16).http://www.gov.cn/2011lh/content_1825838.htm.
[3]赵树梅.我国保障性住房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宏观经济管理,2014(4).
[4]刘琳,罗云毅,程选,等. 我国城镇住房保障制度研究[M]. 北京: 中国计划出版社, 2011: 112-120.
[5]郑征. 经济适用房政策评价[EB/OL]. (2005-08-24).http://www.chinadwelling.com/w/Default.htm.
[6]戴伊. 理解公共政策[M]. 谢明, 译. 12版.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13-15、21.
[7]DONNISON D V. The Government of Housing[M]. Hamondsworth: Penguin, 1967: 100.
[8]杨廷文. 揭露中国“楼市”背后的“陋事”[EB/OL].(2012-05-03). http://house.yzdsb.com.cn/system/2012/05/03/011702242.shtml.
[9]LUND B. Understanding Housing Policy[M]. Bristol: Policy Press, 2006: 2.
[10]王绍光. 民主四讲[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14.
[11]ADAMS J S. The Meaning of Housing in America[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84,4: 515-526.
[12]黄兴文,蒋立红. 住房体制市场化改革: 成就、问题、展望[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9: 271.
[13]罗应光,向春玲,等. 住有所居: 中国保障性住房建设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1: 199.
[14]毛鹏, 陈小瑞. 保障性住房的社会效率和公平问题及改进建议[J]. 建筑经济, 2012(1): 37-40.
[15]北京经济适用房自用率仅五成[N]. 京华时报, 2005-08-25.
[16]李小健. 公平公正: 保障性住房“生命线”[J]. 中国人大, 2011(21): 23-24.
[17]廉租≠偏远——廉租房也应走进城市中心地带 [EB/OL].(2010-05-19). http://www.shaanxijs.gov.cn/news/info/21420.shtml.
[18]刘文波,刘成友,朱磊,等. 保障房三问[N]. 人民日报, 2011-01-22.
[19]保障房申请遇冷? 位置偏远、配套设施不完善[N]. 广州日报, 2011-10-20.
[20]李克强: 把好公平分配这个保障性安居工程发展的生命线[EB/OL].(2012-02-07).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2/07/c_111496936.htm.
[21]马智利,等. 我国保障性住房运行机制及其政策研究[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0: 129.
[22]康淑娟. 公众参与保障性住房规划设计探讨[J]. 中国房地产, 2015(34): 73-76.
[23]周庆, 韦祉含, 赵立志. 保障性住房规划设计公众参与的现状、问题及建议[J]. 特区经济, 2013(2): 74-77.
[24]孙晓蓉. 探索西部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管理经验——“贵阳模式”解析公租房保障体系建立[N]. 贵阳日报, 2011-07-04.
[责任编辑罗海丰]
Research on the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of Public Housing Policy in China
CHE Do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 China)
Public housing policy is essentially the interest game between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The reason why this policy does not have the desired function in promoting social justice mainly lies in that the low-income people who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ublic housing could not participate in the affordable housing policy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The inner public characteristics and welfare of public housing policy has decided value of the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the public housing policy.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democratization and scientization of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of modern public policy makes the citizen participation facing difficulties involved in ability, free-rider and driving force. Public housing policy requires both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It requires the government to broaden the channel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response to the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demand timely and promote the beneficial interaction between citizens and government in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of public housing policy.
the public housing policy; citizen participation; improving ways
2016- 05- 17
车栋,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外政治比较研究。
F293.3
A
1671-394X(2016)09- 0029- 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