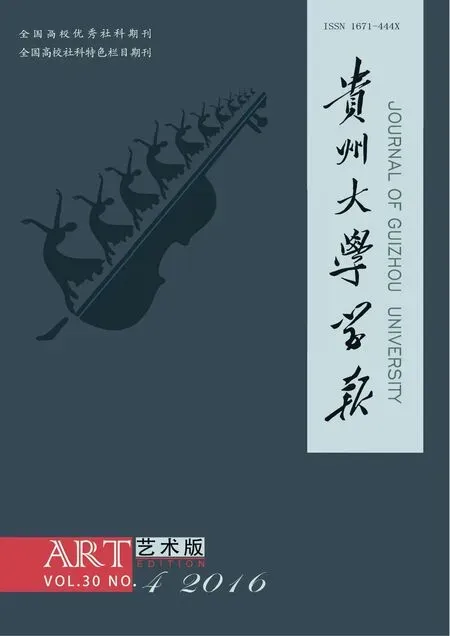行走的中国,失落的家园
——影片《消逝的星星》对中国当下社会的跨文化呈现
李 彬
(北京电影学院 电影学系,北京 100088)
·“乡土·中国”研究专题·
行走的中国,失落的家园
——影片《消逝的星星》对中国当下社会的跨文化呈现
李彬
(北京电影学院 电影学系,北京100088)
意大利影片《消逝的星星》通过一个意大利产业工人在中国的所看所思,用行走的方式,通过“他者的目光”,走马观花式地呈现了当下中国的表情和状态,阐释了当下中国现代性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并给出了批判性结论,呈现出一种对精神家园的深深失落之情。
当下中国;跨文化解读;旅途叙事
2006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有两部运用“行走中国”的旅途叙事方式呈现中国当下生活实景的电影引起瞩目,一部是后来获得金狮奖的《三峡好人》,一部是意大利导演吉安尼·阿梅利奥(Gianni Amelio)拍摄的意大利/法国/新加坡/瑞士[1]合拍影片《消逝的星星》(TheMissingStar)。
《消逝的星星》的主线索是一家意大利钢铁厂将出过事故的旧高炉卖给不知情的中国厂家,50岁的老工人文森佐担心这可能引起新的事故,便研制出新的零件,希望替换掉旧的问题零件,以解决潜在的危险。他只身来到中国,在女翻译刘华的陪伴下,跨越大江南北寻找这台机器。一路上的见闻却让他陷入深深的思索。
“影片展示了这个快速发展的国家人们的真实生活(如果不是全部,至少是部分)与社会变迁”*原文为:This movie shows real people's life (if not all, at least some) and the changing of society dur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Missing_Star.09-26-2015.。作为一名意大利导演,阿梅利奥意欲呈现当下中国的尝试,可以折射出西方电影人对中国现实社会跨文化解读的兴趣与努力。
一、行走中国与底层视角
影片导演阿梅利奥被视为第三代意大利导演的代表,并且是20世纪80年代“极端现实主义”浪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张纪录片式拍摄法,强调用自然光效和现场音响来营造环境气氛和刻画人物心理”,“继承早期的新现实主义关注人物命运和心路历程的传统,一方面最大限度地拉近电影与现实的距离,另一方面强化叙事的张力和技巧”。阿梅利奥的影片“常常喜欢用非职业演员,通过旅行过程来呈现人物的情感交流,场面调度自然流畅。这些影片既回归新现实主义传统又有所创新,既注重画面运动的技巧,更强调真实气氛的纪录。”因而,国际影评界称“极端现实主义”为“新新现实主义”,而阿梅里奥则自称是“新现实主义的儿子”。[2]86
陈卫星曾指出,新现实主义在问世之初着重于对物质匮乏所带来的苦难产生同情成为一种叙事基调,而当今的新现实主义则更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的风险社会所产生的人的命运的波折,以及由此激发的心理适应和人性尊严。[3]85
如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偷自行车的人》,《消逝的星星》也是借由一次寻找之旅来展开世纪之初的中国图景。旅途叙事最适宜展现社会人情,百态人生。有趣的是,贾樟柯的影片《三峡好人》与美国记者彼得·海斯勒2011年出版的著作《寻路中国》也同样展现的是新世纪头十年的当下中国现实。
三部作品都是旅途叙事、底层视角,关注的焦点也都是2001-2007前后的当下中国。这是21世纪的头几年,是中国社会最飞速发展,变化最巨大的几年,中国已然成为经济全球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有人说,这也是“中国现实逐渐碎片化”的几年。在作品中涉及到的这近十年中:
2000年中国与欧盟就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双边协议
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三年目标基本实现
2001年加快农村税费改革
正式成为第143个WTO成员国,迈向全球性贸易
2002年通过农村土地承包法
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启动
人民银行宣布启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制度
2006年5月20日,长江三峡大坝全线建成
200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举行*根据新华网等网站的年度大事记整理而成。
官方记载寥寥数语,但卷入其中的普通百姓生活无疑是翻天覆地的。彼得·海斯勒在《寻路中国》的前言中说:“2001年夏天,我考取了中国驾照,在此后的七年中,我驾车漫游于中国的乡村与城市。这七年也正是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期,单在北京一地,每天申领驾照的新人就有一千多,其中有好几年,乘用车销售额的年增长率超过了百分之五十。仅仅两年多的时间,中国政府在乡村所铺设的公路里程数,就超过了此前半个世纪的总量……这种由农而工而商、乡村变身城市的发展,正是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3]
《消逝的星星》主人公文森佐所见证的正是这“最重要的变化”。文森佐的寻找之旅并不顺畅,由于进行中间交易的贸易公司不负责任,文森佐无法知道钢铁厂的确切地点,他请来帮助他的女翻译刘华也因为被他弄丢了工作而冷脸相对。茫茫人海,诺大中国,幸而刘华被他的诚意打动,开始帮助他寻找。南下武汉,北上内蒙,文森佐跨越了半个中国。飞速发展中的中国社会,普通民众的生活图景在他眼前展开。
吉安尼·阿梅利奥格外青睐用旅途线索来结构叙事。阿梅利奥获得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的影片《小小偷的春天》(StolenChildren,1992,又译成《盗窃童心》)就“以公路片的结构样式再现新现实主义的社会真实性。”[3]87影片表现了一段三个主人公在意大利境内从北到南的旅行,“以旅行来结构,使得一个个事件各成段落,更鲜明地展现了外部环境对主人公的冲击和影响,以及如何造成人物意识上的一步步蜕变。”[4]
而1994年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最佳导演奖的《亚美利加》(Lamerica)表现的则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阿尔巴尼亚的移民潮。阿梅利奥谈到本片的创作缘起时提到:1991年8月,阿尔巴尼亚向意大利大批移民,“突然间,似乎整个卡拉布里亚成了装载着大批移民驶往纽约的一条大船……是什么促使那么多的人放弃了自己的家园?他们要追寻什么?我决定到他们的家乡进行一次没有偏见和疑虑的旅行。”[5]137在最终结构的故事中,也是靠旅途,“一种险象环生的旅行过程和一些偶然发生的事件”[7]141来一步步展开情节。
在欧洲现代电影创作中,“旅途叙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作形式,“流浪”是一个重要的创作内容,用来揭示人在现代社会中被挤压的状态,个体越来越孤独、无聊,找不到自我存在的依托,精神无所皈依,世界也变成了另一个漂泊无依的世界。法国学者若兹·库贝洛在《流浪的历史》(HistoryduvagabodageduMoyenAgeànosjours)中写道:“明天的不确定性使每一个小百姓都成为了一个潜在的流浪者”。[6]而在欧洲现代电影对人文主义内涵继承和发扬的历史进程中,流浪模式无疑仍是一个重要载体,作为重要的意象和主题,通过“流浪”对人的生存方式进行思考,思考旅行(流浪)与生命的关系,流浪者在沿途所遇到的事件与景观,大多为其本身的孤独疏离作了注脚。“他们在现代生活中被边缘化、孤立化,反而能以无关乎己的冷静眼光观察审视一切,观望考察社会。”[7]
旅途也是更大范围观察底层生活,进行底层叙事的最佳方式。借由旅途线索,《消逝的星星》的空间呈现非常丰富。在地域跨度上,影片从意大利来到上海,去到武汉,再到重庆,最后辗转内蒙,跨越了中国华东、华中、西南、西北四个区域,从繁华都市,到偏远乡镇,从华东街巷,到西北荒漠,渡长江,过黄河,行程可谓漫长,视野可谓广阔。一路上,主人公乘坐的交通工具有绿皮火车、游轮、长途汽车、敞篷卡车、三轮货车、简易渡船,可以说最大程度地触及到了中国社会普通民众的生活,用底层叙事构筑了影片的主线脉络。
二、他者目光与时代面孔
旅途叙事所带来的视角往往是“旁观者”视角。《三峡好人》中两个分别到三峡库区寻找妻子/丈夫的主人公来自山西。《寻路中国》的作者彼得·海斯勒则是《纽约客》的驻北京记者,中文名叫何伟。而《消逝的星星》意大利式的观察视角也很容易让人想起四十多年前的另一部意大利影片《中国》。导演安东尼奥尼在创作之初的拍摄计划中明确指出:“我将用一个来自欧洲人的眼光进行拍摄,用一个来自异域文化的他者的眼光来探寻这个神秘的国度。”[8]他在影片中也提到:“中国的人民就是这部片子的明星,我们不期望解释中国,我们只希望观察这众多的脸、动作和习惯”。影片强调了其“客观审视”的立场,展现了近半个世纪前国人的面孔和生活细节。如今,《消逝的星星》也试图用镜头掠过一张张生动的面孔,传递出中国这个庞然大国中的芸芸众生被现代化浪潮裹挟其中,随波逐流,奔涌向前的精神世界。
在《亚美利加》中,阿梅利奥的主人公因为汽车轮胎被盗而不得不使用阿尔巴尼亚的交通工具:拥挤肮脏的公共汽车和敞篷卡车。“让吉诺和菲奥雷乘汽车进入阿尔巴尼亚人流中。那些阿尔巴尼亚人要去港口乘船,要到不会遭到任何组织的边境线上去。这种持续不断的人流和坚持不懈的人群就形成了影片里许多重要画面的重要成分。”[7]142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在《消逝的星星》中同样充满了持续的人流和不懈的人群:城市街头,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和人群川流不息;大学校园,青年学子人头攒动;火车站候车厅,人群摩肩接踵;长江游轮上,也坐满了南来北往的乘客;下了游轮走向出站口,人们蜂拥着挤进硕大的索道车;还有西北小镇上夜市里吃饭唱卡拉OK的民众……影片中,为了替文森佐省钱,刘华带着他住在工人宿舍,搭乘各种敞篷卡车和三轮货车,流动的空间,涌动的人潮和质朴的面孔成为文森佐最直观的底层体验。
旅途叙事所带来的流动的景观呈现了丰富的地理地貌和建筑空间。上海过街天桥、武汉长江大桥、长江三峡两岸、西北荒漠荒山,还有茫然无尽头的滚滚黄河……空间本身是具有文化内涵的,“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9]。在上海,镜头避开了最富有“魔都”地域景观特色的摩天高楼和花园洋房,只通过宾馆窗户展示了建设中的密集楼群和高大塔吊,影片将更多的镜头对准了普通人的生活/生存空间。
建筑往往是一个时代所特有的文化符号。芬兰建筑大师尤哈尼·帕拉斯马曾阐述过对电影与建筑影像的微妙关系:“建筑和城市的精神任务是营造我们的现世感……真正的建筑是由物质建造的空间和主体精神空间之间的经验感觉和意义交流。”[10]作为产业工人,文森佐最有感情的无疑是工厂,特别是钢铁厂。
影片开篇,在濒临倒闭的意大利钢铁厂,文森佐看着拆除了高炉,空空如也的厂房,内心的情感难以名状。来到中国,在武汉找到第一个钢铁厂后,热火朝天的工作场景与意大利工厂的衰败形成鲜明对比,看得他兴奋地朝工人们挥手问候。高炉中钢水喷溅,钢花四射,看得文森佐出了神。这里是文森佐的情感空间,是沸腾的生活象征,也是他的精神故乡。
据说,影片构思来源于一部2002年的意大利小说《退役》,其作者Ermanno Rea也是本片编剧之一。他到当地钢铁厂深入生活,完成了50页的调查报告,并据此创作了小说,甫一问世便成为当年的销量亚军。小说主人公与电影主人公同名,是一名产业工人,在那不勒斯钢铁厂工作了一辈子,从普通工人一直做到高级技工,可以说,这座工厂造就了他,代表他整个的人生。然而,钢铁厂要停止运转了,主人公最后的工作就是负责设备的拆除,他希望一切细节都可以精准完美,不容忍出现丝毫瑕疵,这是他职业生涯的最后句号。“小说中拥有悠久历史的巨型钢铁厂象征着身份、团结、力量,它的拆除不仅仅是一座建筑的毁灭,还包括它所在的城市和围绕它运转的所有人的生活。这种改变是物质意义的,更是心理和文化层面的。”[11]所以,在《消逝的星星》中,支撑他来中国的目的,其实是要通过寻找完成一次“拯救”,对自己那台问题高炉的拯救,让它继续焕发生命力。
影片还着重表现了底层民众的生活空间。在山城重庆,刘华带着文森佐来到小姐妹的工厂宿舍楼。气喘吁吁爬了十几层的高楼,文森佐看到的是逼仄楼道里的拥挤住房,楼道里甚至有住家直接吆喝售卖熟食。走廊里高高低低挂着晾晒的衣物,每户人家的居住区域都非常狭小,而且往往堆满了家具、床铺以及生活用品。疲惫的青年工人半裸着蜷在床上熟睡。文森佐被带到一个大一点的房间,几个女工正在踩着缝纫机工作,工作区域与生活区域完全混杂在一起。桌子既用来裁剪衣服,也可以供孩子们在上面玩耍。
在重庆的钢铁厂,未封闭的工厂使得工人的生活空间与生产空间也是混杂在一起的。建设中的工厂施工现场,为厂区做清洗、修理的工人们没有戴安全帽就在施工现场洗衣服晾衣服,甚至吃饭带孩子,工地的工人们则抬着设备、煤气罐等危险品穿梭其中,全然无视工地上树立的“施工现场注意安全”的宣传牌。
旅途叙事也呈现了丰富的时代面孔。张同道教授曾在评论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时谈到:“每个民族、每个时代、每个人都有一种典型的表情,那种表情是心灵与特定时间、空间交汇而呈现出来的一种精神图式。”[12]安东尼奥尼试图刻画的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的不同面孔,有属于官方式的朝气蓬勃,也有属于隐秘式的迷茫困惑,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典型表情。而在《消逝的星星》中,影片也试图捕捉那些具有鲜明特征的当下中国社会的各种表情。
表情是心灵的映射。“个体表情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民族表情,国家表情,它是一种社会视觉语言符号”[13]。21世纪初期,市场机制的确立和工业结构的转型,深刻地触发了中国社会结构的重组和阶层利益的分化。“中国社会中数量最庞大的两个人群:工人和农民,他们的命运因社会转型而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工人阶级曾经是社会无可置疑的主流人群,工农联盟是由宪法规定的国家政治主体,但是他们今天却变成了大众传媒和影像中的‘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群。”[14]
2009年,美联储主席伯克南和“中国工人”同时登上《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榜,这标志着全球经济衰退背景下,中国经济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日益上升所带来的对“劳动”和“生产”的关注和承认。《时代》总编辑理查德·斯坦格尔说:“中国工人是观察中国对世界影响的一个角度,这种影响实在无法估量。”[15]
在《消逝的星星》中,中国产业工人的面孔有两种特质:一是淡漠随意的。影片开始,在意大利工厂,一个中国青年工人正在门口吸烟,文森佐示意他不能吸烟,他把手头的烟掐灭,却紧接着又从口袋掏出一支烟面无表情地吸起来;在影片结尾,文森佐终于找到了高炉所在的钢铁厂,并将置换的IC部件交给一个“识货”的工人,哪知这个工人将IC部件交给另一个工人并嘱咐其赶紧换掉后,传看的工人们却随手将之扔到了废料堆。此外,在生活与生产混杂的厂区内,安全隐患下的工人也是安之若素,全然不顾,似乎只有眼前的生计才是最重要的事。
第二种工人面孔是轻松欢乐。食堂里,青年工人远远望着文森佐这个高鼻梁深眼窝的“老外”,悄悄议论着,发出阵阵笑声。年轻的面孔上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和欢乐的神采,似乎繁重的劳动和逼仄的生活都不能消磨他们生命的活力。也许吃饭时间是工人们最放松的时候,即便是一碗面条,打饭师傅和吃饭工人也能笑呵呵地讨论半天。
孩子是导演着重强调的面孔。《小小偷的春天》就描述了在贫困的意大利南方,在被黑手党控制着的西西里和黑社会势力猖獗的拿波里,孩子首先成为罪恶的受害者。《消逝的星星》中也出现了多处孩子的镜头。过街天桥上一队幼童从文森佐面前走过;通往游轮甲板的楼梯上,一个小男孩默默坐着吃零食;拥挤的青工宿舍,一个胖嘟嘟的小男孩跑到饮水机前嘴对着出水口喝水;开放的厂区,来来往往忙碌的工人中,一个小女孩独自坐在一边静静吃着午饭;溜冰场上,不同年龄的孩子都在自如地舒展着身体滑来滑去;山村小镇,坐在门槛上哭泣的小女孩用小胖手抹了抹眼泪;还有西北理发店,扭来扭去不想剃头的孩子……影片还刻画了一个留守儿童寂寞空洞的面孔。未婚生子的刘华将儿子放到乡下由奶奶抚养。孩子有些自闭,总是愣愣地望向远方,连许久不见的妈妈都不能让他露出片刻微笑。这些面孔都将是中国的未来。
此外,影片中还有各色面孔:意大利收购设备的考察团疲倦的面孔,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到斗兽场参观;文森佐风尘仆仆来到上海找到购买设备考察团所在的公司,新任领导告诉他原来的董事长已被废弃时的权术家面孔;大学校园,即将毕业的学生在合拍毕业照时兴奋的笑脸;长江游轮,年轻人聚在一起唱歌的欢快面孔;被误会捉到警察局,面对的是警察怀疑冷漠的面孔;山村老屋,刘华奶奶布满皱纹,是沧桑的面孔;还有西北小镇,搭车司机热情的面孔,饭馆青年默默关怀帮助的面孔;内蒙古火车站,独行老汉催促文森佐赶火车的善意微笑的面孔……
这些面孔被一双来自异域他乡的眼睛所注视。这份来自他者的目光含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深情,借由长镜头的缓缓移动,传递出创作者深深的忧虑之情。影片试图展示的中国“问题”非常开阔:从轻率的设备购买,到贸易公司的不负责任,再到长江三峡工程让很多人背井离乡,还有计划生育政策,留守儿童问题……然而,也正因为这份他者的目光来自异域,所以这份悲悯的深情在解读起来,比之贾樟柯在《三峡好人》开头用缓如江水流动的长镜头,抚过船舱中每一张黝黑的面孔时所透出的生活质感和心灵震撼多了一份隔膜。
三、批判主题与失落家园
《消失的星星》是一部典型的公路片。以反叛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法国新浪潮”电影和美国“新好莱坞”公路片,最早是西方左派青年电影人批判现代性,与资本主义体制进行对抗的革命宣言。《四百下》、《筋疲力尽》、《逍遥骑士》、《粉身碎骨》莫不如是。在意大利,自从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以来,电影也一直是以意大利共产党为主的左翼社会力量的重要社会工具。[3]88安东尼奥尼的影片《扎布里基角》(ZabriskiePoint)中的“革命”主题更是淋漓尽致。影片中有一大段一群青年男女在荒野中群交嬉戏的画面,可谓赤裸裸地向主流价值观宣战,用蛮荒之爱,对抗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而在影片结尾,安东尼奥尼干脆设计了一场大爆炸,要炸毁的正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消逝的星星》的导演阿梅利奥在《小小偷的春天》中所彰显出的那种真实性,其来源正是“在于随着工业化的现代性普及过程,弱势人群所经受的命运的冲击。来自西西里的意大利人始终扮演着工业化过程中的‘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他们的生存环境和社会习惯使他们经常成为被现代性所拯救的对象,这几乎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意大利电影的常规主题。”[3]87-88《亚美利加》中,“导演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所展现的贫困、失望和怪诞的冲突、环境,以及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们的绝望与对生机的渴望,都令人震撼而且难以忘怀……同时在影片的叙述过程中又不断积累着内在的痛苦。”[7]146
在《消逝的星星》中,一路上,目睹了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面貌,文森佐的心情越来越沉重,“没想到中国是这个样子的”。如果将原小说《退役》看作《消逝的星星》的前传,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文森佐的内心世界,他的动机与他的失落。“他将一生奉献给工厂,对所有的设备充满感情,如今一切都结束了,象征钢铁厂灵魂的高炉将被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资本家隐瞒了它有缺陷的事实。作为维修工,1953年出生的他见证了这座1960年代高炉的诞生、每一次改造和维修,他必须要把它修好,为了中国工人的安全,也为了高炉的完美谢幕。”[13]但现实是,这一趟关于高炉的拯救之旅无疑是失败的,因为千辛万苦找到了购买高炉的厂家,送去解决设备隐患的关键配件却被随便扔进废料堆。文森佐本人并不知道配件的命运,完成任务的欣喜过后,他却在黄河渡船上流下难过的泪水,这个“面临贫困和现代之间的社会反差而激发出来的表情”,不由自主泄漏出“一个西方人的内心感受的复杂性”。[3]89这趟通过拯救高炉进而隐喻着拯救中国的旅行显然是失败了。
影片主题是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质疑,片名即代表导演的态度。“消逝的星星”指的是五星红旗上的星星在消失。片中借由女主人公之口指出,五星红旗上的星星指的是“诚实、耐心、正义、团结”,这可谓是导演的创造性阐释,然而,在当今中国,这些在导演看来构成社会坚定的精神基石的东西正在消逝。影片弥漫着一种哀伤、忧虑的情绪,《半个月亮爬上来》的音乐在苍茫的画面中传递着强烈的失落感。无疑,导演认为,“社会、经济和文化反差使得经济现代化运动正在某种程度上腐蚀社会理想。”[3]89
对于中国,西方左派知识分子一直有一种情结。“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让西方政治家着迷,他们甚至一致认为中国是最有可能将乌托邦的理想推向现实的国家。[16]但是,如今的中国,资本的力量统治了这个国家。
影片的开场颇耐人寻味。雨夜,濒临倒闭的钢铁厂,满载着中国收购团的大客车驶入厂区,厂区门口是围观抗议的工人们,他们高喊着“吸血鬼!吸血鬼!”工厂大门上挂着一条横幅,写着“给有钱的中国佬清仓!”旁边是一幅漫画,画着一个穿戴成清朝模样的扎辫子的人,张牙舞爪意图控制冒着烟的钢铁厂,用来指代“有钱的中国佬”前来收购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没落工业淘汰的设备。
意大利工厂的破败让做了一辈子工人的文森佐失去了精神的支柱,“出自于生活现实和心理困境的破解,必然转化为一种自主的行动——寻找,以此作为生活的希翼”[17]。表层的寻找真实的指向却是内心自我的寻找,但是,中国这个文森佐浪漫想象中的乌托邦世界却摇身一变成了资本大佬,这使得作为产业工人的文森佐的中国行由“精神回乡”而一落千丈成为迷失之旅。最终纵使任务完成,文森作内心却无比失落,潸然泪下。这是文森佐精神家园的失落和自我救赎的失败。
来中国之前,文森佐对中国是亲切的,或许,中国就是他的(同时也是导演的)精神故乡。他能说几句中文,能脱口说出邓小平的话,了解三峡工程将带来的经济利益。在武汉钢铁厂门口,高高矗立的毛泽东雕像坚定地指向前方。这应该是他耳熟能详的中国符号。但是,在流动的现代中国中穿行,看得越多,文森佐心情越沉重。他说:“这个国家到处都是钢铁厂。”作为一个国家的重工业基础,钢铁制造业一直被许多国家视为国民生产中的重要环节,曾经是世界工业化进程中最具成长性的产业之一,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工业水平的重要指标。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和消费国,国际市场占有率自2003年始快速上升,2008年更是创历史新高12.07%。[18]
钢铁是基础建设的重要部分。在影片中,中国犹如一个巨大的工地,所到之处几乎都可以看到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在上海,宾馆外的工地夜以继日,灯火通明;在武汉,江边的大楼远近错落,很多几近封顶,远远望去,高耸的塔吊正在繁忙工作;在重庆,建设中的钢铁厂,生产能力将达到300万吨;在西北荒漠,尘土飞扬的公路上,筑路工人也在紧张忙碌……
这是火热的,现代化的中国图景,身处其中的中国面孔正在经历着变革,甚至裂变。然而,在《消逝的星星》中,导演的创作出发点是要讲述“主人公文森佐的价值观因为陈旧而在今天不合时宜,这不仅仅在意大利如此,在中国也不例外。社会、经济和文化反差使得经济现代化运动正在某种程度上腐蚀社会理想。影片所期望的是中国应该从自身的智慧出发超越现代性的一般规律,能够像影片主人公那样在不知不觉地努力中走到终点。但从影片的处理来看,万里之外的阀门最后被随意地扔进废料堆。似乎作者对自己的创作意图并没与足够的自信,作为意象的中国还是福柯所说的异托邦。”[3]89-90
彼得·海斯勒在《寻路中国》中说:“这个处于世纪之交的十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之一。正是在这十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力开始增大。”“中国巨变的推动者变成了普通人——走向城市的农民、边学边干的企业家,他们的能量与决心是过去这十年中的决定因素。”[5]
《寻路中国》的时间跨度是七年,它“探讨经济,追踪发展的源头,探究个人对变革的应对……通过叙述普通中国人的经历来展现中国变革的实质。”[5]作者经常在一地连续呆上数月、甚至数年,跟踪变化。他不会仅仅听主人公自己讲述,会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的故事在面前一点点展开。虽然在彼得·海斯勒的叙事中依然是一个西方的“他者”目光,甚至偶尔透露出某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但是在这七年中,他是与他笔下的人物生活在一起。换言之,他参与到了他们的生活中,而不仅仅是个旁观者。“他把观察中国的两个点,分别放在怀柔附近的三岔村,和江南的丽水。通过乡村,何伟希望联接到中国的过去,而通过临近温州的丽水,何伟想探究中国未来的可能性。而无论是写乡村还是写城市,有一点没有改变,他始终聚焦的,是中国最广大也最普通的家庭里面最普通的人。三岔口村让人记住了魏子淇一家;而在丽水篇里,何伟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位应聘职位,开始还被排除在名单之外,最后竟然把一家三口都带进厂的小姑娘。”[19]
一本书的容量显然要比一部电影宽松得多。七年来的生活细节也足够作者游刃有余地展开中国故事。当年安东尼奥尼在中国待了22天拍成《中国》,他曾坦言:“也许,我需要在这里住上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对中国有些了解。这个国家太大了,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无法充分感知的话,想要深刻理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怕是不可能的。”[20]
受制于时间和篇幅,《消逝的星星》也是走马观花式的,印象式的,呈现式的。但导演又显然不满足于仅仅呈现,影片为当下中国做了一个批判式的结论:构成这个国家精神基础的东西正在消逝。然而,这种批判由于缺乏生动的故事细节而不免流于概念。例如,同样是关于三峡工程的反思,《三峡好人》用整整一部影片的长度和两个寻找的线索来进行集中讲述,中间穿插了众多生动的人物故事颌生活化细节,而《消逝的星星》却只用了一句“甘蔗不都是甜的,有些人必须离开自己的家园,你所看到的一切都将要淹没”就轻轻带过,缺乏故事支撑也就难以呈现出其背后的复杂性,难以产生认同,打动人心。
不过,这趟旅程也不完全是失败的。文森佐唐吉诃德式的执着赢得了女主人公刘华的支持和认同,两人的感情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男女主人公的情感变化构成了影片的另一条线索。这也是一次“拯救”,代表西方文化的文森佐从感情上拯救了代表中国的刘华。
影片开始,刘华对文森佐是冷漠的,因为他害得她丢了工作。但是,随着旅途的继续,刘华不仅开始认同文森佐的举动,还一直帮他省钱,甚至将他带到自己的“领地”中,生活里。在自己以前居住过的青年工人宿舍,疲惫的文森佐想要放弃,刘华热情地鼓励他。两人甚至有了情不自禁的肢体语言——被前男友伤害的刘华投入文森佐的怀抱哭泣。在乡下老屋,刘华带着文森佐见到了自己的奶奶,儿子,并向他讲述了自己的情感故事。更重要的是,刘华自此在文森佐面前盘起了头发。这是一个女人心有所属的象征。影片结尾,失落的文森佐在火车站见到了前来会面的刘华,说起刘华的儿子对文森佐的期盼,文森佐用了“我们”一词来指称二人,这分明已是一家人的表示。
然而,也因为这条线索的设置,使得影片的戏剧性偏移到女主人公的故事与男女主人公的情感变化上,削弱了主线的笔力,叙事也产生了游移。旅途叙事原本就是生活化,开放式,碎片式的。或许因为旅途故事中没有结构出打动人心的戏剧点,因而需要在情感线索上得以加强,却同时也暴露出了影片的西方本位主义立场。
[1]小毕.2007意大利电影回顾展——Italiana影像中的意大利[J].电影, 2007(01).
[2]陈卫星.人道主义的展示与文化的历险[J].博览群书,2007(03).
[3][美]彼得·海斯勒.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M].李雪顺,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前言.
[4]宁岱.詹尼·阿梅里奥及其新作《盗窃童心》[J].世界电影,1993(05).
[5]尹平.关于影片《亚美利加》[J].世界电影,1996(05).
[6][法]若兹·库贝洛.流浪的历史[M].曾丹红,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前言5.
[7]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张旭东,魏文生,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90.
[8]舒可.安东尼奥尼与《中国》的对话[J].三联生活周刊,2004(12):46-47.
[9][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M].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21.
[10]尤哈尼·帕拉斯玛.建筑和电影中的居住空间[A].孙炼,译. 建筑师,2008(12):125.韩佳.他者眼光与影像中国——安东尼奥尼纪录片《中国》研究[D].湘潭大学,2013:10.
[11]御用文人.一个意大利工人的中国苦旅[EB/L].https://movie.douban.com/review/1285772/.
[12]张同道.中国表情——读解安东尼奥尼与伊文思的中国影像[J].当代电影,2009(03):94.
[13]韩佳.他者眼光与影像中国——安东尼奥尼纪录片《中国》研究[D].湘潭大学,2013:8-9.
[14]吕新雨,赵月枝.中国的现代性、大众传媒与公共性的重构[A].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2010(12):1-24.罗锋.“历史的细语”:新纪录运动中的底层影像研究(1991-2010)[D].复旦大学,2011:11.
[15]李静.瓦解与重构:当代工人阶级形象的书写(1999-2011)[D].华东师范大学,2014:22.
[16]Bernard Frolic.ReflectionsontheChineseModelofDevelopment[A]. Social Forces, 1978:386. 韩佳.他者眼光与影像中国——安东尼奥尼纪录片《中国》研究[D].湘潭大学,2013:31.
[17]刘坛茹,王文敏.当代中国底层电影的寻找叙事研究[J].当代文坛,2011(04).
[18]中国报告大厅.我国钢铁行业在国际的竞争分析[EB/L].http://www.chinabgao.com/k/gangcai/12944.html,2014-9-16.
[19]孙小宁.何伟:“我觉得我还不了解中国”[N].北京晚报,2014-10-11(19).
[20]雍强.《中国》:辨别安东尼奥尼[J].电影,2005(05).
Flowing China and the Lost Home: The Missing Star as a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LI Bin
(Department of Film Studies, Beijing Film Academy, Beijing 100088)
The Italian film The Missing Star cast a glance at the contemporary China through what an Italian industrial worker had seen and thought as a road film with a “view of the Other” by representing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during the modernization in current China and reached a critical conclusion by expressing a deep regret for the lost spiritual home.
contemporary China;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travel narrative
龚艳
2016-07-15
李彬(1974—),女,山东人,博士,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副研究员,美国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电影文化,公路电影。
J905
A
1671-444X(2016)04-0012-09
学术主持人语
本期集结了三篇关于“家园”、“乡土”、“中国化”的文章,这三篇论文从某种程度上回应了今天中国影视尤其是民族影像的历史、现状、创作的思考。北京电影学院李彬老师的《行走的中国,失落的家园》,以意大利影片《消逝的星星》作为切入点,通过一个意大利产业工人“他者的目光”来看待今天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问题,是跨文化文本的研究案例。1980年代是寻根热潮时期,乡土文学、乡土电影不同层度地呈现出一种“伦理隐喻”。复旦大学的龚金平老师在论文《艰难而沉重的自我追寻之旅——中国乡土题材电影中的伦理隐喻与情爱叙事》聚焦于1980年代的中国乡土电影,文章从“礼俗文化”与“自我认同”、“静态意向”与“动态意向”、“传统儒家伦理”与“现代伦理”三个维度关注这些影片中所展现的伦理交锋或碰撞,还对2000年左右的乡土电影进行了梳理,乡土电影的时代性对比成为留给研究者的有趣话题。浙江传媒学院的袁靖华与王冰雪老师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影视尚没有完全摆脱文化上“被他者化”与产业上“被消费化”的双重困境。文章提出,以“中国梦”为价值引擎的影视创作观,为当下中国化电影的本土创作提供给了思路,“中国梦”文化内核的目标应该是追求个体幸福的同时追求社会良治,人与人包容和谐,将个体的成功与社会的完善相联结,这也是区别美国梦和欧洲梦的方向。这三篇论文所讨论的中国梦的文化价值、1980年代乡土电影与中国现代化困境遭遇,共同构成当下影视创作的本土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