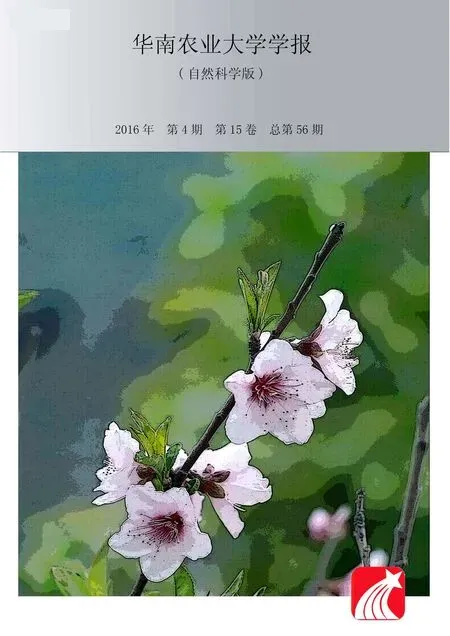当代乡贤:地方精英抑或民间权威
李晓斐
(南京理工大学 社会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94)
当代乡贤:地方精英抑或民间权威
李晓斐
(南京理工大学 社会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94)
摘要:分别梳理了地方精英与民间权威的概念与脉络,指出地方精英更强调客观支配、民间权威更侧重于本土文化建构的特征。当代乡贤的核心特质,即介于自身的客观支配力与当地人们的主观认定之间,认为乡贤具有由当地特定文化观念体系塑造与建构的特质。从乡村治理的意义上,讨论了乡贤文化与乡贤培育的真正意义,乡贤文化不仅仅是指乡贤本人的嘉言善行,更指的是能够建构或生长出乡贤的本土文化体系。培育乡贤更意味着对乡村社会本土文化观念的尊重、培育与引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形成乡贤得以生长的文化土壤。
关键词:乡贤; 地方精英; 民间权威; 客观支配; 主观认定; 本土文化体系
近年来,乡贤之于乡村建设的意义,受到从学者到官员的一致关注[1-2]。对于乡贤及其文化的强调,反映出乡村治理领域日益认识到传统文化资源的价值。然而不论从学术还是现实层面上,对于何为乡贤以及乡贤的内在意义等问题均较为模糊与笼统。在为数不多的围绕当代新乡贤的研究中,一种观点直接将乡贤视作地方上有着雄厚经济实力的老板企业家或富人[3];另一种观点则将新乡贤定义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拥有一定财富或者创业能力的,乐善好施的,在当地具有一定威望的乡村人士”[4]或“指在民间基层、本土本乡有德行、才能和声望并且深受当地民众尊敬的人”[5]。在某种程度上,前者将新乡贤等同于地方精英特别是经济精英,后者除了强调其经济精英的特点之外,同时也强调了“地方威望”即民间权威的一面。在很多研究中,地方精英与民间权威是可以混为一谈的。但是,从概念辨析的意义上,两者能否直接划等号?如果不能,有哪些区别与联系?进而,当代新乡贤到底应被视作地方精英还是民间权威,或两者兼而有之?
一、精英:从国家走向地方
在社会学的意义上,“精英”最初是高高在上的。在帕累托的精英理论中,社会分为非精英阶层和精英阶层,后者又可分为统治精英和非统治精英两个部分[6]。此时,精英不仅是一个涉及社会分层的概念范畴,更与统治地位或政治权力密切相关。精英与国家权力结构相连的观点在米尔斯的《权力精英》中得到更充分的阐述[7]。
中国研究领域亦是如此。与当代“新乡贤”提法密切相关的传统社会士绅或乡绅,即被视为精英的同义语,并与中华帝国的政治权力及科举功名密切相连[8]。而最初围绕士绅群体的研究,更被学者概括为士绅理论模式:在此模式下,作为精英的士绅群体是铁板一块的,具有基于科举考试所形成的文化同质性、与帝制国家紧密相连并深受儒家文化体系的支配等特征,其精英地位来自于帝制国家的赋予,其职能也势必是维护帝国的秩序与稳定[9]。被学界广为所知的费孝通[10]、张仲礼[11]、瞿同祖[12]、萧公权[13]等学者的研究,无疑也受到了这一理论模式的影响。值得指出的是,虽然各有侧重,但上述学者在不同程度上均看到了士绅的双重角色的特性,即:不再将士绅仅仅看作帝国秩序的维护者,而是更加强调士绅在国家与地方之间所起到的上下沟通渠道的面向,士绅将帝国官僚体系与乡村勾连在一起,并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要为地方谋利益,另一方面又充任帝国政府在地方的代理人角色。费孝通更将帝国时期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官僚统治与士绅群体自下而上自治并行的现象称为“双重轨道”的权力结构[14]。
由此,以士绅群体为代表的精英研究逐渐摆脱了高高在上的局限,日益走向地方、深入民间。特别是《中国地方精英与支配模式》的出版,更意味着对县级以下中国地方社会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精英及其在地方竞技场(arena)中的资源、策略与实践的日益关注。有学者将士绅阶层或精英群体的这一研究历程的变化概括为士绅论、乡绅论、地方精英论等不同阶段[15-16]。自此,“地方精英”甚至取代了士绅精英,成为理解地方社会的极富解释力的概念。周锡瑞(Joseph Esherick)等人将“地方精英”界定为在县级以下的地方舞台上实行支配与控制的任何个人与家族,这一界定大大扩展了士绅精英的范围,囊括了处于地方社会顶端的所有人,既包括传统的地方士绅,也包括商人、实业家、军队头目、地方长老及社区领袖等不同职业的人;并且,来自社会史、社会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们详细讨论了地方精英在职业(组成成分)上的异质性、地域空间上的异质性(包括长江三角洲、东南沿海、华北、长江中上游、外围区域和边陲区域等)、以及精英行动的复杂性和对各种不同资源的灵活运用[17]1-24。
相较于士绅群体,“地方精英”的概念不再过多强调其与国家政治权力的紧密联系,精英地位不再被视为仅仅来自国家的赋予,而是更加注重精英在地方舞台上的资源、策略、实践与结构之间的相互交织以及地方精英的持续、变迁、转型或消退的种种图景。由此,对于中国精英群体的认识经历了从国家赋予到官民中介、再到强调民间性的地方舞台具体实践的历程。
就概念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地方精英”的核心要素是对地方的“支配”(domination),其支配的来源是对网络、庇护、经纪、调解等种种策略的运用以及对物质、社会、个人或象征性资源的控制。张信也同样把地方精英界定为“无论采取何种手段在地方竞技场中行使支配的人们”[18]。当下大多学者对乡村精英的研究也是如此。贺雪峰明确指出精英属于社会分层的概念范畴,在传统社会,乡村精英指的是拥有土地、权力和声望的乡绅;建国后乡村精英大多是基于阶级与政治身份的村庄主要党员干部,以及改革开放时候的现代型或经济型精英[19]。学者们也大都根据所支配资本的不同类型,将精英分为经济精英、政治精英、社会精英等等。可以说,精英与支配相连,成为学界对于精英概念的基本认识。
二、民间权威:本土文化的建构
由于士绅研究逐渐凸显的民间性或地方性,民间权威(folk authority)的概念也日益受到学界关注。有趣的是,在权威研究的开山鼻祖马克斯·韦伯那里,与上文所讨论的精英概念一样,“权威”也是与“支配”密不可分的:支配意味着“某种特定命令被特定人群服从的可能性”,合法性的支配形式即权威[20]。而那些来源于民间的、非正式的以及非官僚制领域的合法性支配形式,即“民间权威”[21] 269。
在民间权威的研究脉络中,最初学者们同样看到了民间权威人物所扮演的官民中介的角色,并将其纳入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框架之下。甚至在共产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乡村研究中,有学者将共产党村干部比作传统社会乡绅,他们一方面把国家指令和意识形态传达给村民,另一方面作为地方利益的代表,也维护着地方的文化[22]。
与此同时,随着认识的深入,民间权威的概念日益呈现出与士绅及精英研究的不同面向,其中之一即是,更加强调民间权威的本土文化建构的特征。在此研究路径下,许多学者发现,民间宗教与仪式具有象征性权威,从而成为民间权威建构的主要方式。例如王斯福指出中国民间宗教与仪式所具有的象征性权威及其与帝国权威的相互关联[23];罗红光[24]、林益民[25]等也同样从文化象征符号体系的角度来讨论民间权威的生成过程。但是,对于中国广大乡村来说,并不是每一个乡村都存在具有强大象征性权威地位的村庙或民间宗教仪式,相反,大部分村民可能更具有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意义上的世俗性。对于这些村庄和村民来说,人们无法通过对宗教仪式等文化象征符号的控制来获得权威,那么,其权威又是如何生成或构建的呢?杜赞奇通过对华北乡村资料的分析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而乡村社会权威正是产生于由各种关系与组织中的象征与规范所构成的文化网络之中[26]。王铭铭对闽台乡村的研究也曾指出,民间权威除了来自于具有象征性权威的宗教仪式之外,同时也来源于对一套人们广为接受的权威人格的本土观念的遵守[21]298-300。
为了更好理解民间权威的本土文化建构,很有必要借助于韦伯“克里斯玛(charisma)权威”的概念。在韦伯的论述中,克里斯玛权威具有鲜明的主观性特征,艾森斯塔德对此有着明确阐释:一个人是否拥有克里斯玛权威并没有一套客观标准,它不是价值判断的,而完全取决于追随者或受众的主观认定,如果一个人能够成功向人们展示其超凡特质或达到某项使命并得到人们的承认,那么这个人就具有克里斯玛权威,相反如果他失去了让人们承认的特质,也就失去了这一权威[27]。换句话说,克里斯玛权威更多来自于人们的主观认定,又由于不同社会的人们有着不同的道德观或文化观念,因此这种主观认定又与特定社会的本土文化观念密切相关。可以说,克里斯玛权威与特定社会的本土文化观念体系相对应。只有成功满足或履行特定的文化观念,才有可能得到当地人群的普遍认可与追随,从而拥有一种克里斯玛权威。对于“民间权威”而言,不论是上文学者指出的民间权威建构所需的宗教仪式象征符号、文化网络、本土观念,还是笔者在田野调查点路村概括的以会做人、公平公正及为集体利益考虑为内容的本土观念体系[28],均是特定社会村民普遍接受的文化准则。民间权威的生成或构建,正是依靠其对上述文化准则的履行与满足。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民间权威”的概念同样具有鲜明的主观性。
同时,正是由于“民间权威”的主观性,大大扩展了民间权威人物的来源或范围。如果根据兰钦与周锡瑞对于“地方精英”并不局限于本地社会的活动跨度的讨论——即从本地社会成功进入到更高层级竞技场(arena)并且在此之后仍然与家乡保持密切联系、把外部资源带入家乡以及在不同层级竞技场中自由穿梭[17] 314,则可以看出,民间权威人物的概念大大超出了地方精英的范围,有的民间权威人物甚至不必是精英,只是普通的村民或小人物,只要其成功符合或履行了当地村民相应的本土文化观念,就能够获得声望与村民们的认可。
三、当代乡贤:客观支配与主观认定之间
如果说“地方精英”是根据其所控制的各种资源以及对地方社会的客观支配来界定的话,那么,民间权威则源自于其符合了村民们的某些期待而得到村民的主观认定。换句话说,两者的来源与侧重点是不同的,前者侧重于自上而下式的对地方社会的支配,强调的是一种客观上的权力与影响;后者则更强调自下而上式的普通民众的主观认可与主动接受,是一种主观上的价值判断与认定。正是由于这种不同,民间权威所涵盖的范围可能要比地方精英宽泛得多。也就是说,在概念分析的层面上,民间权威的概念不仅弱化了对地方社会的实际支配与控制的面向,而且可能更加突破了“地方精英”一词所具有的社会分层的限制,从而涵盖了更为广泛的对象。由此,民间权威人物既可以是控制着各类资源的种种精英,又可以是一般的普通村民或者小人物,其关键并不在于对地方的客观控制与支配,而在于他们是否能够遵守当地的核心价值体系。如果能够做到,那么即便是乡村小人物也可以获得村民的广泛称赞与主观认可,从而获得了一定的权威性;反之,即便是各类精英人物也无法让村民们内心信服与尊敬。
但是另一方面,两者的相似之处又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不论是地方精英还是民间权威人物,起码都是地方社会中有着一定影响力的重要人物。也正因为如此,贺雪峰等人将农村精英分为体制精英(治理精英)与非体制精英(非治理精英),后者即是并无国家授权却在农村社会有着一定影响力的村民[29],从而具有明显的民间权威的意涵。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从学理上理解民间权威和地方精英所共有的这种影响力呢?前些年学界围绕差序格局的概念展开了热烈讨论,其中,阎云翔强调了差序格局中的等级观念及其存在于以己为中心的社会网络之中[30];张江华则指出差序格局的核心是“社会圈子”并且居于社会圈子中心位置的个体具有克里斯玛性质[31]。这些讨论大致勾勒出乡村社会的某些面向:一、乡村社会存在具有伸缩性、边界模糊、以己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格局;二、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是中心个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潜在扩张的能力。在此意义上,或者可以说,地方精英与民间权威的影响力体现在,两者均是具有成功扩张能力从而在其社会圈子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中心个人。
那么,当代新乡贤到底应被视作地方精英还是民间权威或两者兼而有之?或者说,当代新乡贤在何种程度上体现着地方精英或民间权威的意涵?通过前文对地方精英与民间权威的分析梳理,我们可以对当代乡贤的概念大致归纳如下:
其一,与地方精英和民间权威所呈现出的共同特征相一致,乡贤也是当地社会中有影响力的核心人物。一般情况下,不论是优秀基层干部、先进典型还是普通村民,要想成为乡贤,其必然是当地社会成功的中心个人;或者说在乡土社会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的社会网络中具有潜在扩张的客观能力,从而在当地具备或大或小的影响力。
其二,也是更为重要的,在本文分析的意义上,乡贤不一定必然是精英,但一定具有民间权威的意涵,也就是说,实现对各种资源的控制以及对当地社会的权力支配,并不是成为乡贤的必要条件;相反,乡贤更多依赖于当地普通民众对他的主观认定,而这种主观认定与价值判断来自于被视为乡贤的人们对于当地某些普遍接受的核心文化观念的遵守。换句话说,乡贤并不一定必须是居于当地社会分层体系顶端的精英。能否成为乡贤,其关键因素在于他能否遵从并满足当地特定文化观念下的普通村民的普遍期待。
中宣部长刘奇葆曾指出:“从现实情况看,农村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等先进典型,成长于乡土、奉献于乡里,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正日益成为‘新乡贤’的主体。”[32]这一提法可谓把握了乡贤的特征。但本文想要说的是,乡贤之所以能够在乡民邻里间“威望高、口碑好”,并不仅仅因为是干部、模范或典型,而正是因为其满足履行了当地社会核心的本土文化观念与期待。在此意义上,乡贤可以被视为处于地方精英的客观支配与民间权威的主观认定之间,既可以来自于地方精英或基层干部,也可以来自于普通的小人物,前提是对当地文化观念的尊重与满足。
四、乡贤文化的培育与引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治理”日益成为学界探讨乡村社会秩序与发展的重要主题。纵观学界对于乡村治理的研究,大致呈现出从自上而下围绕村民自治制度及乡村基层政权的研究转为自下而上重新回归到治理本身并日益重视本土文化机制的变化趋势。换句话说,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最先关注乡村治理的学者大都从村民自治的内容、模式、机制以及基层政权的制度建构等方面展开讨论[33],随后,学界对于“治理”概念的理解逐渐深化,日益意识到治理的多元主体性及社会自主的民间性等特征[34],以及中国乡村社会本土文化机制、农民的行动逻辑与价值观念对于乡村治理的重要意义[35]。
围绕乡贤概念与内涵的分析梳理,对于乡村建设或治理究竟有何价值与意义?综合前文分析,可以明确的是,“乡贤”与当地普遍接受的核心文化观念是密不可分的,乡贤声望的获得及其对普通村民影响力的发挥均与此有关。由此,如果我们重新审视当下所谓的“乡贤文化”,就会看到,“乡贤文化”可能并不仅仅简单指的是传统士绅的历史文化资源或由道德模范、身边好人所引领垂范的“嘉言懿行”。更为重要的是,“乡贤文化”更意味着一种能够建构或“生长”出乡贤并使其深受普通村民认可与尊重的本土性文化观念体系。同时,乡村中的本土文化体系又是在不断变迁的。仅以笔者曾做过调查的路村为例,改革开放之后,在市场经济等外部因素的冲击之下,村庄原有的构建民间权威的那套本土观念体系(即会做人、公平公正和为集体利益考虑)也发生了剧烈变化,办事公平公正以及为村庄集体利益考虑等内容不再被遵守,随着原有本土观念体系约束性的日益衰退,痞子气与霸道气开始出现甚至被不断强化,其直接后果就是原有民间权威人物的日渐消退,由此,新的民间权威不仅无法在地方社会“生长”出来,反而还呈现出痞子型人物在村庄公共事务中大行其道的趋势[28]。
通过对“乡贤”的重新审视,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到,当下对于“乡贤文化”的发展与培育,不能仅仅简单地在乡村社会“寻找”某些当代新乡贤进而在民众中进行榜样式的宣传教育,更重要的是,发展乡贤文化更加意味着要对乡村社会的本土性文化观念的尊重、培育与引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形成能够“生长”出当代新乡贤的文化土壤,才有可能使当代新乡贤成为当下乡村多元治理的真正主体之一,从而充分发挥乡贤在乡村建设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刘伟,严红枫,叶辉,等.乡贤回乡,重构传统乡村文化[N].光明日报.2014-07-02(01).
[2]郭超.用乡贤文化滋养主流价值观——访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N].光明日报.2014-08-15(02).
[3]何倩倩.“乡贤治村”调查[J].决策,2015,(4):49-51.
[4]宋青宜,本刊编辑部.中国未来的脊梁:新乡绅[J].观察与思考,2010,(5):12-18.
[5]桑林峰.把乡贤文化根植乡土[J].新湘评论,2014,(22):26.
[6]帕累托.普通社会学纲要[M].田时纲,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296-298.
[7]米尔斯.权力精英[M].王崑,许荣,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2004.
[8]徐茂明.明清以来乡绅、绅士与士绅诸概念辨析[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98-101.
[9]李猛.从“士绅”到“地方精英”[J].中国书评,1995,(5):93-107.
[10]费孝通,吴晗.皇权与绅权[M].长沙:岳麓书社,2012.
[11]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M].李荣昌,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12]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M].范忠信,晏锋,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3]HSIAO K.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 century [M].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0.
[14]FEI H.Peasantry and gentry: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and its changes[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46,52(1):1-17.
[15]衷海燕.士绅、乡绅与地方精英——关于精英群体研究的回顾[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126-130.
[16]尤育号.近代士绅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史学理论研究,2011,(4):99-109.
[17]ESHERICK J. W. and RANKIN M. B. 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
[18]ZHAN X.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 the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Henan: 1900-1937 [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7.
[19]贺雪峰.村庄精英与社区记忆: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J].社会科学辑刊,2000,(4):34-40.
[20]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81,238-241.
[21]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M].北京:三联书店,1997.
[22]SHUE V. 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s[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23]FEUCHTWANG S. Historical metaphor: a study of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and recognition of authority [J].Man,1993,(28):35-49.
[24]罗红光.权力与权威——黑龙潭的符号体系与政治评论[M].王铭铭,王斯福.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333-384.
[25]ENG I, LIN Y. Religious festivities, communal rivalry, and restructuring of authority relations in rural Chaozhou, Southeast China [J].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002,61(4):1259-1285.
[26]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10-25.
[27]EISENSTADT S.N. Max Weber on charisma and institution building [M].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8:18-27.
[28]李晓斐.文化与民间权威:一个中原乡村地方政治的个案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2.
[29]仝志辉,贺雪峰.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兼论选举后村级权力的合法性[J].中国社会科学,2002,(1):158-167.
[30]阎云翔.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J].社会学研究,2006,(4):201-213.
[31]张江华.卡里斯玛、公共性与中国社会:有关“差序格局”的再思考[J].社会,2010,(5):1-24.
[32]本刊综合.创新发展乡贤文化[J].人民文摘,2014,(10):24.
[33]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4]让-皮埃尔·丹.何谓治理[M].钟震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35]贺雪峰,董磊明,陈柏峰.乡村治理研究的现状与前瞻[J].学习与实践,2007,(8):116-126.
Conceptions of Country Elite: Local Elite or Folk Authority
LI Xiao-fei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n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94, China)
Abstract:The paper sorts through the conception and research tendency of local elite and folk authority, and points out that local elite emphasizes on objective domination while folk authority pays more attention to local cultural construction. Therefore, the feature of country elite is between objective domination and subjective identity shaped by local specific cultures. In conclusion, the real sense of country elite culture and cultivation based on the rural governance is not only for good words, good actions but for the local cultural system. Besides, respect, cultivate and guide the local culture of rural society forms the culture to country elite cultivation.
Key Words:country elite; local elite; folk authority; objective domination; subjective identity; local cultural system
收稿日期:2016-03-07
DOI:10.7671/j.issn.1672-0202.2016.04.01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5CSH04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15001_04);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2SHC007)
作者简介:李晓斐(1982—),男,河南南阳人,南京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学。E-mail: lixiaofeinju@163.com
中图分类号:C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16)04-013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