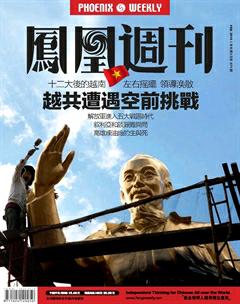医患纠纷何以成为部门斗争?

最近,中科院与北医三院因一起孕妇死亡事件来了一番“亲密接触”,并引发了各方关注:观战吐槽者有之、谴责医闹者有之、同情患者者有之,你方唱罢我登场,且事态大有不断升级之势。为什么一件民事意义上的医患纠纷,升级为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与北医三院及其背后的北京大学、教育部及卫计委等两大官办单位体系之间的纠纷?日益严重的医患冲突背后的症结又是什么?
从医患纠纷到权力角力
从正常的程序分析,出现了医患纠纷,不论错在何方,首先当由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出具事故鉴定意见;而后双方自行或通过第三方的仲裁机构进行协商,若涉及刑事问题,则警方涉入;若双方仍然对鉴定意见或调解结果不服,则起诉至法院,由法院进行裁决。然而,在此次事件中,我们看到的是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公函、北医三院的通告以及医师协会的官方声明,纠纷处理程序的说明却不见踪影。类似医患纠纷由患者所属的机构单位出面处理的情况,同样也发生在几个月前《山西日报》与山西省人民医院之间。
为什么患者及家属在医患纠纷后不选择通过法定程序解决纠纷,找事故鉴定部门、找事故仲裁机构、找法院,而要选择一些“非正常”的途径?在医患关系中,医生由于掌握的信息优势和专业优势已处于“占优”地位;但在民事关系中,二者理应是平等的。双方发生医患矛盾后,可以选择第三方仲裁机构合法处理。但是,由于公立医院隶属于政府部门,医生与公务员一样是国家干部,是“政府”的人,可以说,他们是“权力”机构的“直系亲属”。相比之下,作为个体的患者并无公权力的依靠,在庞大的公权力的对应下,自然就认为与医院、医生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在面对医院所拥有的强有力的行政支持,患者也不愿相信事故鉴定、仲裁机构能够中立、客观、公正地处理纠纷。
在面对以强大公权力为支撑的医院时,个人难以对抗,同时公平、公正的行业监管机制的缺失,又使得患者一方不得不设法寻求新的资源依靠——另一个公权力部门,来抗衡医院方背后的公权力。但对大多数患者及其家属而言,寻求另一公权力部门的帮助同样是可望不可即的,但在本次事件中,死者单位是中科院下属的正厅级事业单位理化技术研究所,而中科院则是国务院直属的正部级事业单位。北医三院来头同样不小,在业务上属于国家卫计委的“委管医院”,在人事关系上又隶属于北京大学及国家教育部。
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发声质疑中科院的中国医师协会也是一家准行政单位。由此可见,事件发展至今,已经不是当事的医院、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医疗纠纷了,而变成了两个权力机构的角力。有行政级别但无行政权力的中科院与掌握实权的卫计委和教育部间的角力,其结果可想而知。若本次事故中的患者来自卫计委、教育部或发改委,可能结果是另一个样子。
医患纠纷的发展逻辑
能够获得公权力相助的患者毕竟是少数,近年来医患之间的冲突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其根源在于行政部门的过度管制以及由此导致的医生自由执业权的缺失。
医患关系的一个本质特征是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医生天然掌握诊断和治疗的信息优势,而患者在医生面前天然处于信息劣势。从理论上讲,医生的信息优势会导致医疗领域“供给诱导需求”的现象。但是,在长期的市场实践中,医疗领域也发展了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方法。简单来说,就是在医生和患者之间形成一个长期博弈,甚至无限期博弈的关系。医生的收益依赖于他和患者之间无数次的博弈过程。在长期博弈中,实现医生和患者的激励相容,即实现患者健康就是实现医生的收益最大化。这一关系形成后,会对医生行为产生约束,使其利用信息优势为患者服务;患者也相信医生没有“欺骗”自己。若医生出现“欺骗”患者的情况,那么市场竞争也会把该医生淘汰。
上述理想状态的达成需要两个前提。一是医生是独立的、自由执业的。自由执业可以界定为医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直接责任,同时对自己的收益有直接的支配权。只有这样,医生才有动力与患者达成长期关系。第二个前提是存在医生之间的竞争,即医疗竞争性市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有“欺骗”行为的医生被市场淘汰。这也是古今中外大多数情况下医生都是自由职业者的原因。纵向看,中国历史上的医生,即所谓“郎中”,都是自由行医的;横向看,欧美发达国家以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医生也都是自由职业者。
但是,在医疗过程中出现医疗事故和纠纷是不可避免的。要保证医患之间的纠纷不至于上升为激烈的冲突,还需要一个独立于医患之间的第三方的事故鉴定和纠纷处理机构。这一“独立”的“第三方”既可以是民间组织,也可以是政府机构,但前提是:与医生、医院以及患者都没有利益关联。
上述三点,前两者保证医患之间的基本信任,减少信息不对称的危害;第三点保证在出现事故和纠纷后,有一个医患双方都认可的处理机构。但是,这三点在当前中国医疗领域都没有形成,从而导致医患矛盾凸显、医患关系恶化。
在中国,医生与医院的关系是雇佣关系,医生是医院的职工。在此情况下,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是间接的,医生的行为由雇佣他的医院来背书。中国的病人看病,找的是医院,而不是医生。如此一来,医生就失去了与患者之间建立直接关系的通道。患者与医生发生关系,需要首先通过医院挂号,由医院给患者分配医生。这样,医生也失去了与患者形成长期稳定关系的动力。不可否认,即使如此,大部分医生也还能尽职尽责,精心为患者提供服务。
但是,中国的医生又不仅属于医院。因为医院的主体是隶属于卫生行政部门的公立医院,绝大部分医生也就成为隶属于行政部门的事业单位编制人员。除了医院和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生进行管理外,人事部门负责医生的定级,财政部门负责医生的工资,发改委负责医疗服务和药物的定价,社保部门负责医生的社保,编制部门负责医生的编制,等等。医生发现他们深陷有关部门编织的管制网中,甚至连如何为患者看病也有相关规定。但是,这也不一定导致医生放弃医德,不认真为患者服务。
在此之上,相关部门又进而设定了医生获取收入的形式和水平,医生的诊疗费被设定在超低水平,医生的工资也被设定低于市场中的均衡工资。有医生说,我收入低,不干了;相关部门说,可以,但独立行医后,你所有的待遇和资格都没有了,而且只准许你们在规定的区域从事规定的医疗服务。“双规”使得医生望市场而兴叹。但是医生对比市场上其他行业的收入,心有不甘,一些医生开始不好好提供服务了。怎么办?这时医院发现虽然不能明目张胆提高医生的诊疗费和医生的收入,但可以通过卖高价药获取灰色收入。这就是以药养医。
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医生不仅在医院鼓励下卖高价药,而且还在医院默许下通过其他方式,比如高价检查等方式获取高收入。更有甚者,出现收受红包、接受药企回扣等腐败行为。这些行为使得医生的角色定位出现混乱,他们不仅看病,而且要从患者身上获得灰色收入。医生和患者的目标出现了冲突;而因为医生掌握有信息优势,冲突中受损的多是患者。
在市场竞争条件下,这样的医生一定会被市场淘汰。但是,相关部门又说了,我给你低工资、低收入,但是我同时也给你们一个垄断地位,你们可以利用此垄断地位通过其他渠道获取收入。在公立医院垄断的情况下,即使医院和医生再无良,患者也别无选择,只能在他们迈进医院的第一步就开始通过各种方式规避来自医院和医生的明枪暗箭,对医生的诊疗抱以怀疑的态度。而患者又处于信息弱势,他们没有能力对诊疗过程提出意见,如果治疗结果不符合预期,自然得出判断是医生“黑”了自己。
截至此时,虽因为医患之间的不信任产生了医患纠纷,但不一定就演变成为诸如“杀医”的极端行为。在怀疑医院和医生“黑”了自己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其他渠道,例如法律渠道、纠纷调解机构来解决。这需要对医疗事故进行鉴定。但正如上文所说,中国的医疗事故鉴定机构和公立医院都隶属于卫生行政部门,若鉴定结果对患者不利,即使在事实上鉴定结果是客观公正的,患者也难以相信。既然正常渠道不被信任,那么患者只有一途,即“闹”。雇“医闹”、拉亲戚、抢死尸、堵大门、静坐、示威等方式就成为常见的医患矛盾爆发形式。
我们已经提到,患者与医生之间没有直接关系,医生是医院的职工,医院要为医生的行为背书,因此从程序上讲患者的对立面是医院,而不是单个的医生。患者以个人之力抗衡作为组织的医院以及医院背后庞大的行政力量,除了一些能力、势力较大者外,胜算并不大。认为自己被“黑”,求告无门,闹事又无胜算,患者发泄的所有渠道看似全被堵上了。但是,患者发现还有一个发泄口,就是为自己提供诊疗服务的医生。于是,悲剧发生了……
出路:社会化办医
一个明显的对比是,“伤医”、“杀医”等“非正常”现象多发生在公立医疗机构;发生在社会办医疗机构的类似事件很少见。当前一些社会办医确实存在一些不规范的现象,一直被污名化,但是有意思的是,不管社会办医怎样不规范,我们却极少在社会办医机构见到恶劣的“杀医”事件。

这背后的原因是,在社会办医条件下,监管部门是“独立”于医方和患方的。一旦出现医疗纠纷,在监管者面前,患方和医方是平等的;监管方与社会办医机构不存在上下隶属关系,不存在天然的“利益联盟”;即使出现“相互勾结”,也是比例较少的腐败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患者不仅“投诉有门”,而且对监管者能够客观公正处理纠纷有一定的信任。
实际上,近年来监管部门对社会办医的监管水平和监管力度确实大大提高了,但是对公立机构的监管却往往流于形式。其中最为社会所诟病的药物滥用、滥开大处方,在公立医院实际发生的比例并不低,特别是大型公立医院。这些指标都是日常监管的主要内容,却少见监管机构对公立医院进行处罚,导致当前医疗卫生领域的监管“无效”。
那么,怎样才能形成“有效”监管的体制?古人尚避“瓜田李下”,类似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一个基本经验是,要形成有效监管,必须打破“裁判员”与“教练员”二者于一身的体制。
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条件是办医的社会化,卫生行政部门与医疗机构彻底脱钩。办医社会化不外两个主要路径:一是现有公立医疗机构与行政监管机构脱离隶属关系,实现法人化治理,成为独立于行政监管部门的法人。这一点在新医改文件中被称为“政事分开”和“管办分开”。医改几年来,政府下了很大功夫,一些地区也对公立医疗机构展开了大规模的法人化治理改革。但从效果看,并不明显。一些地区新成立了医管局,将所有公立医院划归医管局;但医管局仍然是行政部门下的一个机构,仍然无法实现“真正”的独立。一些地区将“管办分开不分家”作为改革思路,不过是在公立医疗机构头上再加一个“婆婆”而已,不仅不解决问题,还进一步将问题复杂化。我们说改革是“壮士断腕”,但现实告诉我们,“断腕”总是不容易的。
第二个路径就是通过促进社会办医和非公立医疗机构的发展,形成一个规模较大的独立于监管部门的医疗服务提供方,并倒逼公立医疗机构的改革。社会办医从一开始就与行政监管部门独立,不存在上下隶属关系,是实现“真正”的监管的前提条件。这一点类似于增量改革,并通过增量改革倒逼现有体制内的改革。这也是中国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