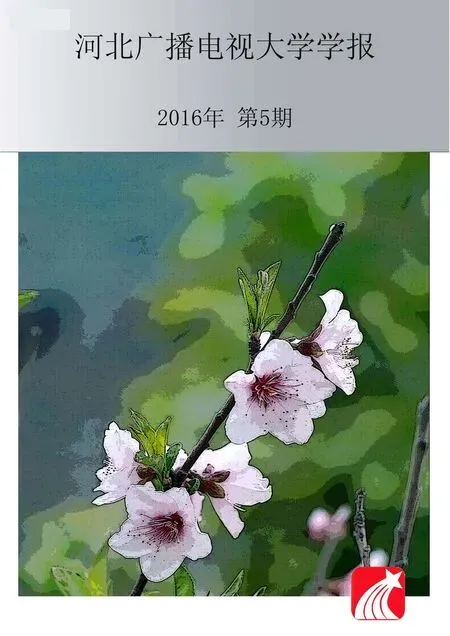“传统”与“现代”并存的艺术特色
——以林徽因小说《九十九度中》的创作为例
黄娇娇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文学·语言研究】
“传统”与“现代”并存的艺术特色
——以林徽因小说《九十九度中》的创作为例
黄娇娇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从形式到内容上,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是非常富有现代性的一篇小说。这部小说探讨了人们对幸福和自由的不懈追求,也对当时中国社会进行了批判。在传统与现代思想冲突的背景下林徽因创作了《九十九度中》,这部作品体现了作家创作中对现代性的独特见解。虽然她的作品在思想上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也以传统为主要叙述平台,但她在创作中对现代性的理解和应用也都非常特别,所以在作品中能看到其对现代性创作手法和传统思想的熟练转换,丝毫没让读者感到突兀,反而使之得到了完美的整合,这也是林徽因创作中最为新颖之处。因此研究《九十九度中》的创作,可以从“现代”与“传统”并存的创作视角作为切入点,结合波德莱尔提出的“现代性”理论对《九十九度中》文本进行全新的解读,探讨以中国和西方为代表的传统和现代对林徽因创作的影响。同时分析作家是如何通过“现代性”的创作来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的整合与创新,这不仅有助于了解作家对现代性的独特认识,还有助于理解作家的人文情怀及她对人生问题的一些思考。对文章中所使用的“现代性”作进一步的界定,并结合作品,可以探讨双重文化对林徽因创作的影响和蕴藏在作品中的独特意义。
林徽因;《九十九度中》;波德莱尔的“现代性”;现代与传统并存
林徽因从小对传统文化有着非常广泛的接触和学习,但同时也接受了完整的西方教育,所以她不仅收获了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还具备了西方的自由民主和个性解放意识,这些都是构成她创作中非常独特的重要因素。林徽因自己也承认,她是在“双重文化教养下长大的”[1](P357)。在两种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冲击下,她吸收了不同文化的特点,在创作中以过人的敏锐、独特的视角和大胆创新的开拓精神,一直勇于尝试,力求突破,也正是这种特殊的文化身份使林徽因在小说创作中,不仅收获了更为广阔的现代化视野,就连面对不同文化的冲突和矛盾都能游刃有余地做到完美整合。在对待中西方文化上,林徽因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就算她是站在西方文化的立场来观看中国的传统文化,但同样她又能客观地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去反观西方的文化。由于这种特殊的背景,林徽因的作品无论在思想见解上还是在艺术特色上都别具一格。虽然她的创作数量不多,但却不乏创新之作,尤其是《九十九度中》这部作品,不论是在现代文学史上还是在京派文学作品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学者李健吾也对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及肯定:“在我们过去短篇小说的制作中,尽有气质更伟大的,材料更真实的,然而却只有这样一篇,最富有现代性。”[2](P454)就如李健吾所说,林徽因小说创作中的艺术特点就是她能很好地将传统和现代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很完美地融为一体。因为林徽因本身有着非常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都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些特点在她的创作中都有所投射。不过,在创作技巧上林徽因还一直力求突破传统创作手法上已有的局限, 这就成为她文学创作中最为独特和最有意义之处。
本文试图探讨林徽因以传统与现代并存的视角进行创作时其特色和真正意义所在,而通过不同学者对“现代性”概念界定的梳理,本文将对文章中使用的波德莱尔提出的“现代性”概念再作进一步阐释,并分析林徽因在创作技巧上如何深受“现代性”的影响。另外,则是结合波德莱尔的“现代性”理论,来分析《九十九度中》文本在创作手法上所体现的现代性特点。最后,本文想进一步思考林徽因对“现代性”特殊的理解,这不仅能更加透彻地理解作品的意义,同时有助于把握作家的人文情怀以及作家在创作技巧中对“现代性”概念的使用等。
一、 林徽因小说创作《九十九度中》的现代性
“现代性”这个抽象的概念最先出现在拉丁语中。“modernitas”一词在11世纪末已经出现,它派生于形容词“modernus”,意思就是“现时的”,它的存在始于公元5 世纪末。[3](P18)从古至今对“现代性”的定义就模糊不清,很难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因为此概念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所以很难做到精确的理解。在过去的人文学术领域中,不同学科的学者、科学家都对此有着自己不同的见解和认识。现代性与现代化密切相关,是一个“集最相矛盾的词义与一体的十足的杂音异符混合体”[3](P13)。“现代化”*“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现象,它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在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在人类社会各个方面所发生的一系列巨大的、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体现在物质经济、制度规范、价值取向、思想意识、精神心理等所有领域,并使那种合理化的科学和工业主义精神渗透、体现于这所有领域中。”参见逢增玉:《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几个基本问题》,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概念诞生之后才产生出“现代性”*“现代性”概念,英文为modernity,是指“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在社会各个领域所出现的与现代化相适应的属性,或者说,是在现代化促动下,在社会各个领域(物质、制度、精神文化)发生全面变革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应和现代化的属性。” 参见逢增玉:《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几个基本问题》,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这个概念,而这都包括政体现代性、科技现代性、思维现代性、道德现代性、教育现代性、法律现代性、学术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等。另外,美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卡林内斯库将“现代性”概括为:“世俗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简单来说,如果我们将“现代性”具体到文学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就可以得出以下两层具体含义:“一方面,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想形式,直接表达现代性的意义,它表达现代性急迫的历史愿望,它为那些历史变革开道呐喊,当然也强化了历史断裂的鸿沟。这个也就是卡林内斯库眼中的第一种现代性,现在通常被称作为启蒙“现代性”或是“世俗现代性”。在美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卡林内斯库的观点中,他认为存在着“两种彼此冲突却又相互依存的现代性——一种从社会上讲是进步的、理性的、竞争的、技术的;另一种从文化上讲是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它致力于对前一种现代性的基本价值观念进行非神秘化”。卡林内斯库把后一种现代性称之为“审美现代性”。参见陈晓明:《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的转型》,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与启蒙现代性关注社会政治制度层面与理性主义对社会生活的制约有所不同的是,审美现代性更注重个体生命在现代生活中的处境和体验的问题。[4](P78-79)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和法国社会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对“现代性”也有着自己鲜明的见解,在此就不加以赘诉。齐美尔更是从心理学角度对“现代性”给出了新的定义,他指出现代性是“凝固的内容消解于心灵的流逝因素”[5](P204)。
波德莱尔是第一个使“现代性”这个概念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3](P41)他是从美学角度去理解“现代性”,并对“现代性”下的定义是:“现代性,就是那种短暂的、易失的、偶然的东西,是艺术的一半,它的另一半内容是永恒的、不变的。”[6](P19)本文将着重探讨的就是波德莱尔立足于现时的所有感想,是一种对事先毫无刻意安排的、简易的、容易被遗忘的零散性记忆碎片和体验。这里所谓的“现代性”正是在这两者(既是构成因素和认同力量,同时又是解构因素和异己力量)的综合作用下,伴随着自我反思、批判乃至否定,又产生了内部的张力,终于实现了其价值重构的本质。在这个复杂的过程中,“现代性”更向作家展现了一个鲜活而新奇的世界,激发了作家创作的动力,最终发展为前所未有的多种可能性。波德莱尔善于观察生活中最细微的场景,从中捕捉到了现代性的特质。如此,通过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理解的梳理,不难发现林徽因在创作《九十九度中》时同样有着对生活细节的观察,通过那特定的场景,作品中表现出现代性的特质。
《九十九度中》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创作方法上,其次是林徽因自身特殊的文化修养。阅读她的文学作品时,不难发现她对时代的觉悟,她敏锐地、勇敢地去学习西方的创作观念和思想,这也赋予了她很多创作的灵感,从而创作了与传统文学完全不同的、非常富有现代性的文学作品。从创作手法去探讨林徽因理解的“现代性”和波德莱尔所指的现代性虽然表象完全一致,但在本质上就能体会到这两者间有着一定的差异。最为简单和直接的不同点就是,文本中对于吃饭的地名、出行的交通工具、主人公的言行举止、饮食着装和消遣的娱乐等都和西方文学中传递出的“现代性”有着很大的不同。林徽因创作中的“现代性”给人传递出更多的是“静态”的和较为缓慢的一个流动,有一种淡淡的平淡感,整体感觉比较和谐内敛,画面感的冲击力也不会太大,自然“现代性”的张力也会略微显弱。这可能跟整个生活的文化意识形态有着很大的差异有关。反而,西方对“现代性”的体现是“动态”的和急速的流动,其更富有活力,画面的节奏感更加快速,空间的流动性也更大,同时也会给读者带来更多视觉上的冲击。西方对现代性的诠释更多的是不断的变化和革新,而林徽因在创作中对现代性却力求“变化中的不变”。
解读《九十九度中》时,不难发现作者把自己的一些思考寄托在文本中的主人公身上,无论是对“现代性”的思考还是对传统文化和思想方面的思考都一一投射在作品中,并借由他们来阐明自己的想法。譬如:生活在新旧时代的阿淑就是一个矛盾的纠结体,她受过新时代思想的影响,但对于生活在传统下的整个大家庭来说,她毫无勇气去为自己的幸福努力争取,更无法和传统旧式家庭的压力去抗衡,她最终还是不敢违背父母替自己做主的婚姻。即便心中有再多的不愿意,她还是在旧社会思想的压迫下妥协了,从她身上可明确认识到,“五四”新时代对自我解放的追求、对自由的渴望、对自我命运自主的掌控都显得格外奢侈,幻想也在现实中破灭,对阿淑来说自由恋爱和女性解放更多的是一种讽刺。从这个情节中,能清晰看到通过作品中对主人公充满无奈的命运和性格的塑造,林徽因想表述的真正思想。作者通过作品向读者坦诚,当时有部分女性,因受过新思想的影响,对自己不公命运已有觉悟,也试图争取,但最终还是向无奈的大环境妥协了。《九十九度中》主人公们呈现出的新时代思想或文本中出现的较为时尚和富有现代性的工具等都是比较表象的,所以在西方的现代性作品中很难读到传统的韵味,但在《九十九度中》却仍然能从比较富有“现代性”的作品里读到很浓厚的传统韵味。这种韵味并没有使文本显得突兀,反而更能使文本的创作技巧和思想内容做到很好的兼容,这也是林徽因在创作中大胆的实践所取得的突破。
除了创作方法之外,《九十九度中》还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现代社会、现代人物等,这些给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新的文学视角。当时的中国文学正处于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变时期。面对复杂多样的文艺思潮,林徽因在文学创作中积极、勇敢地进行精神探索,在创作中学习与借鉴、批判与否定、比较与选择,这些都是她惯用的思维和方法。同时,在面对思想与文化中的变化时,她选择与其他作家不同、又具有独特性的创作手法,其作品也成为富有“现代性”的文学作品。从她自身的创作中,彰显出特殊因素也有投射的痕迹,并透露出了这是多元化创作的结果。她的文化身份不断地被刷新,也不断地被重新塑造,她在创作中所想表达的正是一种文化渗透,而从中表现出她独特的文学世界。在作品中,她所表现的创作方法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思想倾向的问题,而是在特殊文化语境中演变出来的独特创作心理。由此可见,林徽因在创作手法中,一直对现代性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这也是她创作中最有特色之处。本文将在下一章节中试图对《九十九度中》文本中具体创作的思想、审美内蕴、艺术手法等现代性特征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论述。本文的论述结合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来解读《九十九度中》有一定的重要意义,同时还可以更为客观地加深对林徽因小说创作的研究。
二、波德莱尔的“现代性”在《九十九度中》创作中的体现
林徽因《九十九度中》的“现代性”体现,对生活在当下社会的大环境中也有很大的帮助,在如今物欲横流的时代中,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的矛盾与张力丝毫没有削弱,反而演变为越来越极端化。再从林徽因《九十九度中》来看,林徽因通过小说中人物和情节的现代性描写,非常直接地向读者揭示了现代人们普遍存在的孤独感,作者一直提倡的是人人都有追求自由的权利,真正符合现代人的特质。当再次认真阅读《九十九度中》作品时,不难发现林徽因对作品中“人”这一主题的关怀和探讨,描写得非常细致。作者通过《九十九度中》的创作,以成熟、富有创新的艺术形式体现了她生命内在体验的多样性和特殊的人生经历。这部作品呈现出作家独特的美学风格,从中获得特殊的现代意义。林徽因的创作风格虽是京派,但作品却并非和其他京派作家完全一致,对此,萧乾曾说:“我甚至觉得她是京派的灵魂。”[7](P1)
林徽因的小说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文坛上曾受到很大的关注,其主要原因就是她的小说在技巧上具有很大的创新。其中,《九十九度中》便是林徽因小说创作中最具“现代性”的一部作品,在创作手法上,小说采取独特的叙述方式展开,叙述时间和空间的独特构建等,都使得文本相比以往的创作显得尤为独特和创新。李健吾更是对《九十九度中》给出了极高的评价和肯定,也曾说过:这是一篇最具有现代性的小说。在《九十九度中》中,林徽因无论是对作品中人物意识的流动和挖掘,还是“现代性”技巧的运用,都使小说文本在时间和空间上展现出非凡的自由,她对西方“现代性”技巧的运用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所以在小说创作中不仅体现出浓厚的现代化和开放性的特点,还表现出掺杂在其中的传统韵味。不过,林徽因在自己的创作中并没有直接使用西方小说创作的手法,她把非常具有“现代性”的创作技巧融汇在自己创作过程的同时,也结合了自身拥有的独特传统优势进行整合创作,所以作品中现代性的体现并非只是对西方现代性的简单复制和模仿,而是创作出了非常富有特色的中国现代性作品。
《九十九度中》的创作手法明显具有现代性的特点,但小说传达的内容却保留了很多传统的因素。李健吾对《九十九度中》的“现代性”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和认识,他强调和谐美,形式和内容必须做到完美的统一,他说:“形式和内容不可析离, 犹如皮与肉之不可揭开。形式是基本的,决定的。辞藻用得恰当,增加美丽; 否则过犹不及, 傅粉涂红,名曰典雅,其实村俗。一个伟大的作家乞求的不是辞藻的效果,而是万象毕呈的完整的和谐。”[2](P454-456)李健吾关注的就是作家和作品是否和谐,从创作来看,他认为:“一部文学作品之不同于另一部,不在故事,而在故事的运用;不在情节,而在情节的支配;不在辞藻,而在作者与作品一致。”[2](P454-456)作家主观与客观、感情与理性的和谐,通过一部作品可以清晰看到作家对于人生持有的态度,基于作品中的现代性思考和深受传统层面的影响都和作家自身的成长环境有密切关系。这样一来,林徽因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她对传统文化思想的传承,这种传统和现代的融化就成为她文学创作的独特之处。
深厚的中西文化修养给林徽因带来了广阔的文化视野,这在小说中表现出强烈的“现代性”意识。《九十九度中》选取北京的几个人物一天里所经历的故事,通过描述这些小人物和他们的故事,展现出城市里不同阶级人物的真实生活和精神状态。由于篇幅的限制,在短篇小说中一般很难对相关的所有人物和故事情节交代得特别详细,但林徽因将每个人物的生活、城市的面貌、他们的内心世界和阶级问题等都展现给了读者,这是她文学创作的一个突破点。除此之外,小说更突出的特点是它在传统和现代两种不同的风格和思想中获得了完美的融合。在小说叙述的技巧和人物思想的描写中,文本都能表现出现代中的传统和传统中的现代,两者之间没有不协调,反而呈现出非常和谐的韵味,因此故事情节也变得更加符合常理。
实际上,《九十九度中》的核心思想是以传统为平台表现其“现代性”特征。这里所提出的“现代性”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解读,但笔者认为“现代性”更多体现在创作技巧和结构上,这又与作者的情感暗合。由于这些原因,在此将借用波德莱尔提出的“现代性”来结合作品作进一步细致的探讨。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理解:“从零散和细微的生活画面中,去发现和捕捉现代性特征,这些特质都是瞬间流逝的,画面中出现的往往也只是偶然和过渡而已。”[6](P19)如文本中对于老太太过寿的礼数讲究,作者把每一个准备的细节都交代得非常清楚,同时将卢二爷对饭局的犹豫选择、车夫们辛苦劳作时和闲暇时的生活状态等都清晰地勾勒出来,从这些细节中可以看到作者对生活细微的细致观察,所以才能通过文本把地方特色展现给读者,北平人对生活更多的追求可能是“吃”和“说”,同时还非常注重“体面”,可看出《九十九度中》文本都是围绕这些情节而展开的。
在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理解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分析《九十九度中》故事情节中出现的现代性体验的表象。在阅读波德莱尔的艺术现代性理论时,不难发现他提出的很多观点都和林徽因在创作中使用的技巧非常相似。波德莱尔曾认为:“人们往往以对时间的非连续性的意识——与传统的断裂、对新颖事物的感情和对逝去之物的眩晕——来表示现代性的特征”,[6](P19-21)从表象看,也许会有学者认为,两人之间对现代性理解也会存在不同,但在本质意义上却跟《九十九度中》所要表达的“现代性”意义是不吻而合的。在《九十九度中》的文本里,林徽因描述了不同人物对生命的体会,他们对美、爱和自由的追求,同时通过人物的日常生活、各种琐碎的普通社会现象,给读者提示了深刻的人生哲学。在《九十九度中》的文本里呈现出来的“现代性”最直接的就是指人们活在当下的瞬间感受,而这种感受并非刻意和长久的,只是一个瞬间的过渡,唯有发生在瞬间的当下,才是最真实的。
林徽因对“现代性”技巧的运用和波德莱尔提出的“现代性”具有一致性。如刘西渭所言:“在这样溽暑的一个北平,作者把一天的形形色色披露在我们的眼前,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而且那样多的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这是个人云亦云的通常的人生,一本原来的面目,在它全幅的活动之中,呈现出一个复杂的有机体。”[8]小说中看似错综复杂、毫无连续和凌乱散漫的结构安排恰恰是作者有意安排的叙述结构,整部小说,并非按照传统小说一样排序,没有一个完整有序的结构,逻辑和表述都是跳跃性的陈述,情节也都是零散的,作者把看似毫无关系的几个故事情节同时展现给读者。这部小说里出现了大约40个人物,但每个人物的特色都非常鲜明,所以很难去把某个人物或某个情节归类为主要或次要,他们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通过这些人物反映了当下普通人民生活真实的一面,也使她在创作中有不同的侧重点。实际上,在这部小说中,作家有意无意地向读者展示了截然不同的人生和生活的不同层面,由多个小故事贯穿起来凸显出无奈和悲剧命运的主题。无论是生活在最底层、最艰辛的“挑夫”的暴病和死亡,还是奔波的“车夫”为了债务纠纷而引发的入狱之灾,还是“卢二爷”、老太太过寿、阿淑的婚礼等,从这些情节中都能看出作者的精心塑造。
挑夫的病死看似充满“偶然性”,但这是作家的精心铺垫,由挑夫角色作为一个“过渡”,作家想带出不同阶级生活的面貌和精神状态,无论是老太太过寿的情节还是王康和杨三的打斗或是阿淑的喜事等,这些故事的细节都是在同一“短暂”的时间里迅速地完成,在故事情节中没有太多的铺垫,更没有充分的阐释,这在节奏上也给读者带来了一种急迫感。不过,正因为大部分读者没能及时跟上作家的脚步,会出现有部分读者读不懂的现象,对故事本身带有很多疑惑和不解之处,反而让读者感到更有立体的阅读空间。林徽因非常善于把握当下生活的每一个“瞬间”,这使得小说故事呈现得更为精练。并没有因为要刻意去符合传统小说格局,为人物做出过多的重复叙述,更不会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沉重。林徽因对文本中的每个故事情节、人物心理状态和语言叙事的风格,都是时刻在对“现代性”做无声的阐释。
对波德莱尔来说,现代性就是由多个“现在”的不同点构成的,并非一个连续的时间点或时间段,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人生中,永恒与现实、神圣与世俗互相接触,每个体验都是无法重复的现在。[9]波德莱尔强调,一个成功的艺术家要从自己所见所闻的千奇百怪中学会接受,在乏而无味的平淡事物中去发现它的存在意义,让它变成自己创作的奇迹。林徽因在《九十九度中》的创作中对这一观点阐释做得非常贴切,作者善于发现和挖掘,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由多个小人物组成的,而且故事情节也都是从日常中的小事件演变而来的,这些平淡无奇的故事却向读者深深地揭示了现代人们的荒诞的孤独感和憋屈无奈的生存困境。其中,逸九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他追求新的思想和新的生活方式,但婚姻爱情的不由自主依旧让他生活在极度的空虚和幻灭之中。另外,以挑夫的暴病死亡、阿淑的婚礼、老太太的过寿、卢二爷无聊的饭局和车夫因钱财纠纷的入狱之灾等都是看似毫无联系和毫无意义的小故事,作者却巧妙地将其融合在一起,使之变得趣味十足,让读者在众多小故事中看到北京各个阶层的生活面貌,从这些画面中,能让读者对阶级之分、人生无常有更多更直接的认识,这样的作品往往也向读者呈现出不同面的思考。在《九十九度中》整篇小说无论是从人物还是故事情节,很难去划分主次,多个故事在同一时间展现给读者,在阅读时充分感受到了画面的立体感,出乎预料的是,每个小故事背后都会有另一个故事作为延续或是有新的情节作为展开,但作者这样的安排丝毫没有突兀和凌乱不清,反而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仅能感受到作者创作手法的新颖之处,还能发现作者的超强逻辑和对情节独具匠心的设置。正如李健吾所说,这篇小说是“把人生看作一根合抱不来的木料”[2](P454)。人生本来就是这样,既有一定的规律和模式,又纷乱复杂,非人力所能把握。如果说艺术技巧只能是创作文本中的一个支架,那么小说的内容则是精华,只有两者之间做到和谐自然,才能使作品传递出惊人的效果。小说由一开始几个互不相关的故事场面,组成相互依赖的关系,到最后才能体会到作者对小说结构的精心安排,才明白文本中每个小的事物和人物都能贯穿整个文本的核心。
林徽因《九十九度中》的小说无论是从人物、故事情节还是结构上处处都能看到作者富有“现代性”的独特创作,每个章节环环相扣、错落有致,不仅逻辑严密,而且在看似毫无关联的人物情节背后能找到一脉相承的因果关系,作品充分展现出作者创作中的和谐之美,也非常符合作者“扩大短篇小说的表现功能,勿使其过狭窄”[10](P319)的主张。在作品中,作者通过不同视角也对人生进行了不同的思考和探讨,通过故事中人物希望的破灭、绝望、委屈、无奈和深深的孤独感,从而寻求蜕变和解放自我的追求等的描写,充分让读者意识到《九十九度中》是一部有着浓郁的“现代性”小说。
三、传统中的现代,现代中的传统
关于文学创作,林徽因认为“创作的主力固在心底”,而作家想达到“活力真诚”的创作境界则是需要“在运用文学创作的技术学问外,必须是能立在任何生活上面 ,能在主观与客观之间,感觉和了解之间,理智上进退有余,情感上横溢奔放,记忆与幻想交错相辅,到了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的程度”[11]。尤其是《九十九度中》成功地将“现代性”艺术手法与传统的写实方法相结合,把文本中每个人物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都刻画得栩栩如生。林徽因的创作似乎无法彻底抛弃传统对其创作的影响,作者因受京派影响,在作品中多多少少也向读者展现出作者对人性的关怀和批判。林徽因的小说,不仅观照生活在不同阶层的平凡人生,其故事情节也都源自最为普通的日常琐事,但她间接地展示了作品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创作手法上也有不断的创新和尝试,这也给读者带来了阅读上的新鲜感。作者在创作中一直力求创新,强调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所以小说的结构不仅显得更加完整,在阅读时也能获取更多的新鲜感,这便是林徽因创作中的新颖之处,也显示出作家独特的审美意识。
在《九十九度中》中,作家对“现代性”技巧的运用已取得了很大的突破,整体来看,该作品由多个小故事和不同的人物情节的叙述作为展开,无论是人物还是情节的安排都并非传统模式一气呵成,而是以富有现代性的创作手法,跳跃性和穿插性的叙述手法作为不同的转换,在阅读感上呈现出很强的时空立体感。
小说由小人物挑夫展开,通过对挑夫的用具和工具活灵活现的描写,瞬间让读者抓到了富有动感的画面。再从挑夫口渴的情节延续,作者又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新的叙述环境,通过新环境的诞生,又将两个故事的主人公带出来,此时将读者带到一个新的视觉场面,向读者介绍了北京的另一个不同场面,新东安市场和西门的喜宴堂,这里出现的并非只有空间的转换,同样作者也精心安排了不同主人公的经历和心灵上的变化。无论是对阿淑婚礼的描写,还是对卢二爷家长里短的描述,作者在创作上都是有意识地从不同层面上去挖掘主人公们不同的心灵对话,无论是故事情节中人物活动的场面,还是形形色色的小人物都被作者塑造得栩栩如生,场面也是热闹非凡,无论是故事创作方式还是跳跃式的叙述方法,都毫无错乱之感,相反作者都能很好地控制文本节奏,穿插组织也显得非常和谐。林徽因对小说创作一直有着非常独特的见解,她强调不能太拘于传统,要不断尝试创新,要让小说创作更具有现代性和包容接纳性。因此,作家应该“能多面地明了及尝味所见、所听、所遇, 种种不同的情景; 还得理会到人在生活上互相的关系与牵连;最后更得有自己特殊的看法及思想, 信仰或哲学”。[12]也由此可见,她提倡的是一种开放式的小说体式。而《九十九度中》之所以“最富有现代性”,“惟其这里包含有一个个别的特殊看法, 把人生看作一根合抱不来的木料,《九十九度中》正是一个人生的横切面。”[2](P454)这样的评价也是对林徽因小说创作的独特性给予的最好的阐释。小说中的跳跃式叙述和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创作手法,很少有人敢于尝试,这也是林徽因创作中最大的突破,这种毫无限制自由的开放式的小说创作方法恰恰体现了强烈的现代性创作方法。可以说,林徽因的文学创作融汇了传统与现代的因素,即传统中有现代,现代中有传统。
作为出身名门、留学西洋,“在双重文化的教养下长大的”[1](P354)林徽因虽属京派作家,但她有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知识结构和情感体验,在她创作中也仍然保留了京派作家的一些特质,作者还是和京派其他作家一样怀着共同的文学理想,同是赞美“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2],但更多还是凸显出她自身在创作中的独特性。在小说创作中,林徽因以带有北京文化氛围的都市风景为主要背景描写北平胡同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从故事情节中清晰知道作者讲述的是北京地域文化的特质,无论是老太太过寿的讲究,还是阿淑充满被动和无奈的婚姻,都能反应出生活在当下女性的命运,也是中国当时女性命运的代表,有时作者通过热闹非凡的场面向读者揭示的恰恰是更深层次的悲凉的孤独感。同样作者通过挑夫的暴病和死亡以及车夫的牢狱之灾等不同故事情节的描述,让读者强烈感受到当下人们的荒诞无奈之感,同时阶级之分、贫富差距等都展现在作品中。虽然林徽因在《九十九度中》文本创作中表现出强烈的现代性创作手法,但在文本的思想内容上,探讨的却都是传统思想和故事,这就是林徽因对现代性的独特的诠释。
林徽因的小说创作与现代性的讨论深刻地阐释了她丰富的文化思想,也拓展了林徽因文学创作及思想构成的研究。综上所述,林徽因的文学创作明显地体现了她继承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接受西方的文学创作模式,通过无数的写作和尝试的过程,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她最终获得开创性和独特性的意义。在她的文学作品中,《九十九度中》是最能把传统与现代做到完美融合和最和谐的一部作品。因此,如李键吾所言,她的作品才能被称为“最富现代性”的小说。最难能可贵的是,在林徽因为数不多的几篇小说创作中,我们仍然看到林徽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以及她对西方文化的学习热情。在创作中,她把东方女性特有的审美理想和自己的情趣、禀性都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使她的作品具有平和淡远的属于自己独特的韵味,而这是林徽因在文学及其他艺术领域上获得的非凡成就之一。
[1]林徽因.致费正清、费慰梅[M]//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文学卷)[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2]李健吾.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M].张大明,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3]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黄曼君.现代化大叙事与中国新文学传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5]王小章.经典社会理论与现代性[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6]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
[7]柯灵,编.林徽因小说:九十九度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8]刘西渭.咀华集[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9]肖伟胜.波德莱尔的审美现代性思想及其开创意义[J].学术月刊,2008(8):116-123.
[10]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12]林徽因.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M]//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文学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37-40.
Coexistence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 Artistic Features of Lin Huiyin’s NovelNinety-nineDegrees
HUANGJiaojiao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Peking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Fromtheformtothecontent,LinHuiyin’sNinety-nine Degreesturnsouttobeauniqueexampleofmodernismoftheera.Thenovelexplorespeople’srelentlesspursuitofhappinessandfreedombutalsocriticizestheChinesesocietyatthattime.Againstthebackgroundoftheconflictbetweentraditionandmodernism,LinHuiyin’swritingintheNinety-nine DegreesreflectstheuniqueviewofmodernismincontemporaryChina.AlthoughherworkswasaffectedbytraditionaleducationandcultureandbasicallystandsonplatformofChineseliteraturetradition,herunderstandingandapplicationofmodernityisveryspecial.Itcanbeseeninhernoveltheskilledconversionofmodernwritingtechniquesandtraditionalthought,whichdoesn’tmakethereaderfeelawkward,butonthecontraryhasbeentheperfectintegration.ThatisthemostoriginalfeatureofLinHuiyin’screation.Therefore,thestudyofthecreationofNinety-nine Degreescantakethecreationperspectiveofcoexistenceofmodernityandtraditionasastartingpoint.ThestudycomparesBaudelaire’s“modernity”theorywiththeNinety-nine DegreesinthenewinterpretationofthetexttoexploretheimpactoftraditionandmodernityonLinHuiyin’screationbothfromChineseandWesternculture.Atthesametime,itanalyzeshowthewriterrealizedtheintegrationandinnovationof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andartthroughthecreationof“modernity”.Thisdoesnotonlyhelptounderstandthewriter’suniqueunderstandingofmodernity,butalsohelptounderstandthewriter’shumanisticfeelingsandthinkingoflifeissues.
LinHuiyin; Ninety-nine Degrees;themodernityofBaudelaire;coexistenceoftraditionandmodernity
2016-08-07
黄娇娇(1987-),女,缅甸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46.5
A
1008-469X(2016)05-003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