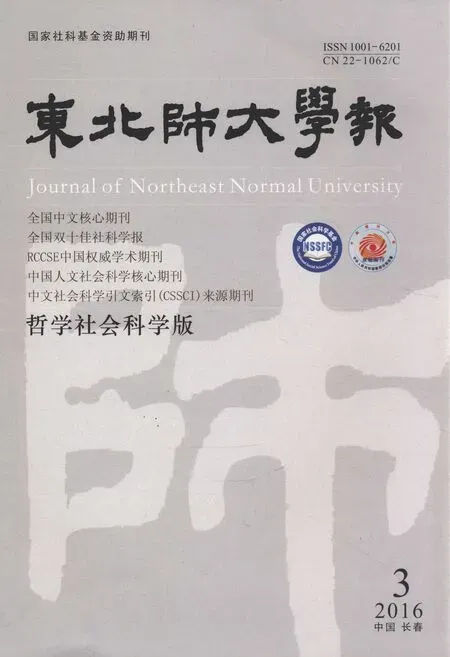中国多民族视域下的“国家认同”政治建构
杜宴林,才 圣
(吉林大学 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12)
中国多民族视域下的“国家认同”政治建构
杜宴林,才圣
(吉林大学 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并非完全一致,且往往存在着一定的张力甚至是冲突。因此,“国家认同”的政治建构就显得至关重要。作为世界多民族国家中的重要一员,中国在建构“国家认同”上历经了“同化主义”与“承认政治”的制度实践,时下亦进行着“宪法爱国主义”的理论探索。然而,这些方式和路径或在实践中遭遇困境,或自身存在着理论局限。多民族视域之下,中国“国家认同”之实质基础在于形成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其所依赖之路径是实现民族融合。
[关键词]同化主义;承认政治;宪法爱国主义;民族融合
几个世纪以来,“民族主义”思潮席卷了全球,并深刻改变了世界的政治地理,主导着世界向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基本宗旨前行,民族主义情感也成为国家认同最自然而然的来源。然而,如果我们用“政治单元与民族单元相一致”这一民族主义严格标准来检视的话就会发现,民族分布与国家疆域不一致的情况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据统计,全世界近200个主权国家中,拥有3 000个左右的民族[1]91。通常的情况是,在一个国家之内,存在着一个在人口和社会结构上占主导地位的主体民族——如俄罗斯联邦的俄罗斯人,英国的英格兰人,中国的汉族人等——与其他若干处于从属地位的少数民族,如俄罗斯联邦的车臣人,英国的苏格兰人,中国的维吾尔族人、藏族人等。
民族结构的多样性招致了主权国家之内潜在的不稳定因素。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前苏联与前南斯拉夫的解体,世界掀起了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在此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如果一国之内的各民族无法做到和谐共处,某一民族的民族认同超越了国家认同,国家的整体建构就会受到民族主义的严重挑战。时至今日,民族主义的幽灵依然困扰着许多“多民族国家”,如俄罗斯联邦的车臣问题、英国的苏格兰问题、中国的新疆问题、西藏问题等等。因此,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国家认同”的政治建构极具现实意义,这关涉到多民族国家的内部稳定与长治久安。
一、“国家认同”政治建构的传统路径:同化主义与承认政治
本质上,“同化是一个民族模式(one nationality pattern)取代另一个民族模式。一般而言,较弱或数量上处于劣势的群体不得不对自己进行修正”[2]94。同化主义曾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长期奉行的一种民族政策。此种政策的直接目标就是用主体民族的文化(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来整合其境内的少数民族,从而试图将“多民族国家”逐渐改造成为“单一民族国家”。
一般而言,在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问题上,主体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基本一致,而少数民族的认同倾向则易于在“民族”与“国家”这两端之间摇摆。从这种意义上讲,国家似乎在和少数民族“争夺”认同感,而一旦争夺失败,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就会超越国家意识,国家就会有遭受民族分裂的潜在危险。基于此,长期以来,“将多数群体的民族认同强加给少数民族一直被认为是政治稳定所必须的”[3]116。在西方,除瑞士以外的几乎所有国家都曾试图通过同化或排除其内部民族而将自己变成单一民族国家[3]116。这其中最具世界影响力的莫过于美国的“盎格鲁-萨克森一体化”和“民族熔炉”政策。1818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曾明确指出:“如果他们(来到美国的移民)不能使自己适应这个国家的文化道德、政治或物质特征,及这个国家的善与恶的补偿平衡,那么大西洋总是向他们敞开的,他们可以回到其诞生地和父母之邦去”[4]41。
此种基于同化主义的“民族熔炉”理念,在20世纪初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孙中山先生。1921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具体办法之演讲》中说道:“像美国这样的民族主义,才是积极的民族主义,这样积极的民族主义,才是本党所主张的民族主义的好榜样”;“拿汉族来做中心,使满、蒙、回、藏四族都来同化于我们…仿效美利坚民族的规模,把汉、满、蒙、回、藏五族同化成一个中华民族,组织成一个民族的国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理念,将同化主义作为“中华民国”制定民族政策的指导方针。一方面,国民政府不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的“民族”地位。例如,针对我国西北地区的回族,蒋介石只称其为:“宗教信仰不同的国民”[5]339。另一方面,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国民政府大力推行汉化。例如1929年,湖南省保靖县在“五月份政治报告”里就明文规定:“禁止苗语苗俗,责令乡主任、保董提倡汉语、禁止苗语”[5]479。
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讲,族群间同化的程度比较高,无疑可以提升社会的整合程度。列宁就曾指出:“谁没有陷入民族主义偏见的泥坑,谁就不能不看到资本主义同化民族的这一过程包含着极大的历史进步作用”[6]66。19世纪以来,同化主义政策曾在一些国家获得了相当的成功,法国即为其中一个典型例证。“法国的民族建构政策非常成功地同化了其大多数曾经都是人口众多的少数民族群体——包括巴斯克人、布列塔尼人、奥克西坦尼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等等。”[3]117。
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同化主义逐渐被看作是带有强制和歧视色彩的,进而越来越遭到世人的质疑。同时,随着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意识的广泛传播,少数民族更倾向于保留自己的语言、宗教、公共制度和祖先文化而变得难以被同化,并且更有能力去抵制同化。在此种背景下,同化主义往往会招致“反抗性民族主义”,即“少数民族会为了保护其语言、文化和自治制度而战,有时就是暴力抗争”[3]117。因而,二战之后,奉行同化主义的国家(包括中国)纷纷改头换面,转向了一种新型的政策模式,即承认政治。
承认政治,即“对差异给予政治承认,不以多数人或主流规范同化少数或边缘群体,而是保持相互的尊重”[4]155。不同于同化主义强调文化的一元论,承认政治以“多元文化”为导向,对一国之内所有民族(包括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均给予平等和公开的承认。
承认政治通常会表现为国家承认少数民族对于其地理空间的相对治理权,这具体分为两种制度模式:一种为“民族联邦制”,即以“民族”作为划分联邦单位的政治原则,从而保障少数民族自治权力。其典型代表为前苏联以及今日之俄罗斯,加拿大等。另一种为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自治”,即在中央集权下的单一制框架内,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特殊安排,赋予其一定的自治权,例如法国之科西嘉,英国之苏格兰,中国之“民族区域自治”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立即扭转了中华民国时期的“同化主义”政策,不同于国民政府的“国族主义”思维,新中国政府更愿意承认自身的“多民族格局”,将新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多民族共和国”。1950年代,新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先后正式认定了除汉族之外的55个少数民族,进而形成了现如今中国“56个民族,56枝花”的多元局面。除此之外,新中国政府还为每个少数民族都划定了各自的“民族自治地方”——即5个民族自治区、30个民族自治州、120个民族自治县(旗)。在宪法和法律的授权下,民族自治机关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民族立法权;变通执行上级国家机关决议、命令权;财政经济自主权;文化、语言文字自主权等自治权利。
可以说,20世纪中期以来,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承认政治业已成为世界的主流,同化主义实践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取代了同化主义的承认政治亦有其自身的局限:即承认政治的焦点在于确认业已存在的各民族认同,因此其自身并不足以成为一种处理认同的方法[3]118。承认政治旨在承认各民族的“民族认同”而非形塑“国家认同”,其不足以将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情感”升华为“爱国主义情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并没有随着承认政治的落实而得到妥善解决,如前苏联与前南斯拉夫的民族分裂,中国的疆独、藏独问题等等。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新疆问题和西藏问题的不断发展,许多学者都开始反思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并认为“民族成分”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划定,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并催生了少数民族的“领土意识”,不利于国家的整体建构[7]188。我们有理由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本身已不足以成为解决新疆问题和西藏问题的灵丹妙药。在“如何既尊重民族差异,又能实现国家整合”这一问题上,承认政治并不是万能的,它只解决了问题的前者(尊重差异),而无力解决问题的后者(实现整合)。
二、“国家认同”政治建构路径的新探索:培育“超民族认同”
进入21世纪以来,几乎所有多民族国家都在国家认同问题上面临着相同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忽视甚或否认少数民族特殊性的同化主义已遭人类文明所摒弃而变得难以奏效;另一方面,承认少数民族的特殊性,以“容纳差异”为目标的“承认政治”又不足以实现国家的整合。因而,多民族国家必须超越传统路径,在承认政治的基础上做出进一步的探索。而如今的一个共识是:国家应建构并推进一种超越现有民族认同多样性的、新的“超民族认同”,“一个承认自己有不同民族群体的多民族国家,只有同时培育一种各民族群体的成员都拥护并且认同的超民族认同(supranational identity)时,它才可能是稳定的”[3]118。
国家认同能否建立在一种超越民族的概念基础之上?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就曾凭借“阶级政治”,成功地培育出了一种“超民族认同”。
新中国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通过武力革命的方式取得的,而在革命过程中输入“阶级斗争”手段,则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建国的关键所在。“阶级意识”是与“民族意识”相对立的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认为人类的根本划分是横向的、以地理国界和文化传统为标志的‘民族’之间的区分,而马克思主义认为应该是纵向的、以经济地位为标志的‘阶级’之间的区别”[8]15。正是利用了这种超越民族边界的阶级划分,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中国各民族中的“底层劳苦大众”团结在了“天下穷人是一家”、“各族穷苦人民翻身解放当家做主人”的革命战斗旗帜之下,其动员能力几乎超出了当时全世界精英阶层的想象。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土地改革运动向着以新疆和西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地区推进,中国共产党将广大少数民族中的底层群众从受压迫的悲惨境地中解放出来,并将一些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与国外势力所极力渲染的“民族关系”问题巧妙地转化为了“阶级翻身”和“社会解放”问题,几乎以“阶级”的概念彻底消解了“民族”的概念。因而,不论是1958年新疆库尔班大叔骑着毛驴进北京拜见领袖毛主席,还是1959年西藏百万农奴庆贺翻身解放,都有着强烈的政治含义:即中国的政治基础由“民族”转向了“阶级”。由此,“‘共产党’所代表的劳苦大众阶层这一‘阶级’概念有效地超越了民族概念,实现了各民族之间的真正团结和统一”[9]31。
然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阶级政治开始动摇,阶级情感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神性。当那种超越在民族之上、连接各民族之间的“阶级纽带”消失之后,曾经被“阶级”概念所消解的“民族”概念却再次显现出来。在全球化与市场经济发展这一世俗化进程中,各民族(包括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宗教和文化开始复兴,各族人民的族群归属意识不断增强,民族再次成为维系人们自身认同的主要工具。也正是在此种背景下,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开始逐渐走入困境,“地域概念”和“民族概念”的结合反而给狭隘民族主义意识的传播与扩散提供了合法的政治空间。因此,汪晖先生就曾敏锐地发觉,如果说西藏“3·14事件”和新疆“7·5事件”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出现了一定危机的话,那么危机只是产生于当代条件下,而不是在更早的社会主义时期。例如在西藏,参与2008年“3·14事件”的主要不是那些经历过“农奴—土改—改革开放”的老人,而是生于70年代之后,成长在藏区,面对全球化与现代化冲击的藏族青年,旧的合法性条件对于他们而言,已经与今天的现实相去甚远[10]117。
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还能否培育出一种不同于“阶级”的新型“超民族认同”?
对此,学界普遍引进了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理论,并认为:新形势下的中国应立足于“公民个体宪政”,在此基础上重建中国今天的政治基础。“具体而言,今天中国的政治基础不是民族,也不是阶级,而是公民个人,即中国宪法中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由此,用‘公民’意识来取代‘民族’意识,强调少数民族的公民身份,从而弱化其民族身份”[9]31-32。“用公民政治来缓和、淡化与化解族群政治,将族群冲突转化为民主问题,使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转化为宪法认同”[11]70。
在民族问题纷乱复杂的今日,“宪法爱国主义”理论似乎为中国提供了一个乐观的展望:所有个体都将隐蔽自身的民族成分,以“公民”的面目来参与国家建构。“在这种政治文化之下…最重要的不是具有相同的民族背景,而是具有民主共和国的公民身份;不是学会在民族文化中生活,而是在政治文化中生活;不是去寻根问祖,而是学会如何批判地查视自己的利益以便进入理性的协商程序,这就是具有形式普遍性的民主政治文化”[12]52。
经由民主宪政机制,国家为各族公民搭建起一个表达自身利益诉求与相互沟通对话的政治平台,将族际竞争与博弈控制在宪法秩序之内,并以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来逐步取代和化解民族主义的冲动。在宪法爱国主义理论的畅想下,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未来随着中国民主宪政机制的向前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不断完善,公民权利与公民自由的逐步发展,届时,中国的国家认同就会在“公民”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成功建立起来。
纵观世界经验,瑞士也许可被视为实行宪法爱国主义而获得成功的一个典型案例。瑞士是世界公认的族群最为多样化但同时又是族群和谐程度最高的国家,其政治基础在于“公民”而非“民族”。“在瑞士的族群治理模式中,‘公民身份’具有优先性……一种建立在直接民主和严格宪法平等基础上的‘公民身份’超越了‘族群’的影响”[13]100。
然而,对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而言,宪法爱国主义这种理论探索到制度实践的创造性应用之间却还有着不短的距离,也往往遭遇现实的挑战:1995年,加拿大魁北克的独立公投中,赞同分离的民众比例高达49.4%;2014年,英国苏格兰的独立公投中,赞同分离的民众比例高达44.7%。事实上,魁北克和苏格兰出现的民族分离主义倾向,其根源并不在于加拿大和英国没有发展出一套完善健全的民主宪政机制——事实恰恰相反,加拿大和英国都是民主宪政机制较为发达的国家——而是在于,民主宪政机制本身似乎并不足以为两个(或以上的)民族共同分享一个国家提供足够充分的理由。许多魁北克人和苏格兰人都认为,自己追求的民族国家也会同样实行民主政治,并尊重公民权利,而且,他们也更希望在自己的民族国家中享受这种民主和权利。
宪法爱国主义理论贡献在于,它为多民族国家规划了一条适合于国家整体建构的民族意识表达途径——即各民族成员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通过“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的途径表达民族意识。但问题却在于,对于某些——特别是曾经有着明确政治诉求或政治记忆的少数民族而言,这绝非是表达民族意识的唯一途径与最佳途径,当这些少数民族寄希望于打破现有的国家体制,通过独自建立“民族国家”来表达民族意识时,宪法爱国主义理论就会走入困局。在宪政民主机制较为发达的加拿大和英国出现的魁北克与苏格兰公投分离危机,就是典型例证。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于某些已经有着悠久历史和意识自觉的少数民族而言,国家对个体公民权利的保障根本无法冲淡其集体的民族主义激情,比起在多民族国家的民主政治框架内,通过与其他民族协商对话来达成共识,在“民族自决”的旗帜下独立建国似乎更有感召力。因此,在这片深深扎根于民族主义的土地上,公民政治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和力度上化解族群政治,依然是值得怀疑的。
三、“国家认同”政治建构的实质基础:实现“民族融合”
在培育“超民族认同”的理论探索与制度实践中,我们不得不承认,作为人类最主要的情感依托,“民族认同”仍是一种如此自然、深刻和广泛的认同,以至于任何试图培育“超民族认同”的努力都显得力不从心。在中国,曾经消解了“民族”概念的“阶级政治”于20世纪80年代逐渐消退,而被学者们寄予厚望“公民政治”亦不足以成为淡化“族群政治”的有效路径。那么,在多民族视域之下,建构“国家认同”的基石究竟为何?
加拿大学者威尔·金里卡认为:人们是通过追问他们“认同谁”和他们感到“与谁休戚相关”,来决定他们想与谁分享一个国家的,而此种认同感实是源自于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而在多民族国家中,人们难以共享的也恰恰是这些东西[14]240。印度学者巴赫拉也曾断言:“为了使许多族群共同凝聚成为一个民族国家,非常需要从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中提炼出一个各族共享的‘共同文化’,其基础是历史中各族长期共享的社会伦理、生活方式和彼此的文化认同”[6]246。
二位学者的论述似乎指出了问题的根源,即如想使多个民族共享同一政治屋顶,其基础不仅仅在于多民族国家能够在民主宪政机制下平等保障每个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事实上,少数民族通过民族自决和独立建国亦能做到这一点——而是在于,各族成员能否共同分享一种共性的文化。
在2014年北京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即56个民族对于共同的“中华文化”的认同[15]。马戎先生曾撰文称,21世纪中国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乃是形成“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因为“凡是在历史上没有形成族群间‘共同文化’,凡是近代没有发展出以这样的‘共同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的‘多民族国家’(multinational nation-states),必然存在解体的风险”[16]29。
而纵观历史经验,如想造就多民族之间的共同文化,其路径不外乎两种:一为“民族同化”,一为“民族融合”。“民族融合”这一词汇对于中国而言并不陌生。几千年来,伴随着人口流动,商贸往来、族际通婚和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历史诗篇在中华大地上不断上演,从未停歇。正是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不断互动和交融的进程中,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中华民族文化也在不断丰富充实。不同于一些西方国家采取的军事征服、野蛮杀戮、强制迁徙等非文明行径,以“民族融合”的文化式手段来化解民族冲突的政策模式,为历代中原王朝所推崇。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民族融合”并不同于“民族同化”,二者有着质的区别。民族同化是“单向”的,而民族融合是“相互”的。民族同化通常是国家强制力推动,以主体民族的文化来整合其他少数民族,最终以少数民族丧失其原有民族特征、被迫改造成为主体民族中的一部分为结果;而民族融合则是在平等和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各族成员间的互动交流,进而逐渐融合成一个不同于任何原有民族的崭新民族。如用公式直观表达的话,民族同化模式为:汉族+少数民族=汉族;而民族融合模式为:汉族+少数民族=中华民族。不同于同化主义的是,民族融合路径以平等和自愿(而非政府强制)为前提,因此不会带有民族歧视的色彩,时至今日亦不会招致人类文明的质疑和挑战。
纵观中国境内的55个少数民族我们不难发现:那些“中华民族意识”较强的少数民族往往和其他民族(特别是主体民族汉族)之间的融合程度较高,文化共性较多,如满族、土家族等;而“中华民族意识”较弱的少数民族往往和其他民族(特别是主体民族汉族)之间的融合程度较低,文化共性较少,如维吾尔族、藏族等。笔者认为,时下中国境内的新疆问题与西藏问题之所以得不到彻底解决,其根源并非在于中国政府压制了维吾尔族和藏族的民族意识以致招来了“反抗性的民族主义”,更不在于中国宪法没有赋予维吾尔族和藏族成员平等的公民身份,而是在于:由于特殊的历史、政治和地缘等因素,维尔吾族和藏族与其他民族(特别是主体民族汉族)之间缺乏广泛与深入的互动交流,以至民族融合程度较低,文化共性较少,因此对于用来整合56个民族的“中华民族”概念存在着一定的疏离感。如果说中华民族的意识基础在于中国各族人民相互交往的历史以及在此历史进程中不断融合而产生的共同的“中华文化”,那么,我们似乎必须承认的是,时至今日,此种以民族融合为基础、能为各族人民所共享的“中华文化”还未完全形成。因此,马戎先生才会称形成“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是21世纪中国所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
而为应对这一挑战,笔者认为,时下中国必须延续和推进历史上不曾间歇的“民族融合”进程。一方面,应逐步排除阻碍民族融合进程的制度性因素。为此,我们需要慎重反思当下“板块式”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例如,在维、汉、蒙、回、哈萨克、柯尔克孜等众多民族共同生活的新疆地区,仅以‘维吾尔’赋名赋义,等于屏蔽了其他族群的存在,亦似乎剥夺了其他族群的地理合法性,同时,使得禀获赋名的族群产生“我才是这里唯一的主人”的错觉和口实,其实不利于民族团结和民族和睦[11]69。张千帆先生就曾建议,应以“地方自治”来逐步取代“民族区域自治”,即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一样,实行“藏人治藏”、“疆人治疆”,但这里的“藏”、“疆”不是一个民族概念,而是地理概念[17]255-256。比起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自治消除了一个行政区域的民族色彩,既留存了“自治”之魂,也有利于各民族成员之间的平等交流。
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在平等和自愿的前提下,以政策引导和鼓励的方式推进各民族之间(特别是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对各民族在互动交流过程中自然出现的文化融合现象,政府应给予积极的评价。值得关注的是,近些年来,新疆和西藏地区已经开始向着鼓励和促进“民族融合”的方向迈进,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民族通婚”。例如2014年6月,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在民族通婚家庭座谈会中明确表示: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积极鼓励全区各兄弟民族通婚,促进西藏各民族大团结、大融合。同年8月,新疆且末县更是出台了《关于民汉通婚家庭奖励办法(试行)》,规定凡民汉通婚的夫妇连续5年每年可以获得1万元人民币的奖励,除此而外,还享有养老、医疗、住房、子女上学等一系列的奖励和优惠措施。可见,政府已经着手以政策引导的方式,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积极创造条件和搭建平台。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实行“单一制”的“多民族”大国[18]20。未来,在推进民族融合、形成中华民族共同文化这一漫长道路上,我们还需要不断地去积极探索。可以说,唯有实现了56个民族的“民族大融合”,形成了属于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才会真正走向成熟,中国也才能从根本上化解民族主义的挑战,将“国家认同”建立在“中华民族”的概念之上并根植于各族成员的心中,为国家的内部稳定和对外竞争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参 考 文 献]
[1] 乌小花.当代世界和平进程中的民族问题[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2] [美]米尔顿·M·戈登.同化的性质.吴晓刚,译[M]//马戎.西方民族社会学经典读本——种族与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 [加]威尔·金里卡.多民族国家中的认同政治[J],刘曙辉,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2).
[4] 关凯.族群政治[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5] 李鸣.中国近代民族自治法制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
[6] 马戎.民族社会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 马戎.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的症结与出路[M]//谢立中.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8] 周传斌.论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理念及其贡献——以中国多民族国家与美国民族—国家的比较为例[J].广西民族研究,2006(2).
[9] 中华民族意识与现代国家建构学术研讨会纪要[M]//陈明,朱汉民.原道(第十七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10] 汪辉.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外二篇)[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11] 许章润.立宪共和主义族群政治进路[M]//陈明,朱汉民.原道(第十七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12] 石茂生,程雪阳.论当代中国国家认同和国家统一的基础——基于民族主义与宪法爱国主义的考量[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13] 田飞龙.瑞士族群治理模式评说——基于“宪法爱国主义”的公民联邦制[J].法学,2010(10).
[14] [加]威尔·金里卡.多元文化公民权——一种有关少数族群权利的自由主义理论[M].杨立峰,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15] 丹珠昂奔.切实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B/OL].国家民委门户网http://www.seac.gov.cn/art/2015/2/6/art_40_223723.html.
[16] 马戎.创建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应对21世纪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J].西北民族研究,2012(2).
[17] 张千帆.权利平等与地方差异——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另一种视角[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
[18] 才圣,杜宴林.地方法:中国传统“封建”政治思路的现代表达[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
[责任编辑:秦卫波]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Multi-ethnic Background of China
DU Yan-lin,CAI Sheng
(Center for Jurisprudence Research,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Abstract:In multi-ethnic countries,nationalism is not equal to patriotism.They usually have contradiction.So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s very important to multi-ethnic countries.To be an important member in multi-ethnic countries,China has practiced assimilation and admitting political.We are also exploring the 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 now.But these ways hav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or theoretical defects.The true way to construct national identity is creating the common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We need achieve the fusion of all ethnics.
Key words:Assimilation;Admitting Political;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Ethnics Fusion
[收稿日期]2015-09-11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FX015)。
[作者简介]杜宴林(1974-),男,四川广安人,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才圣(1988-),男,吉林辽源人,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16)03-0079-06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6.03.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