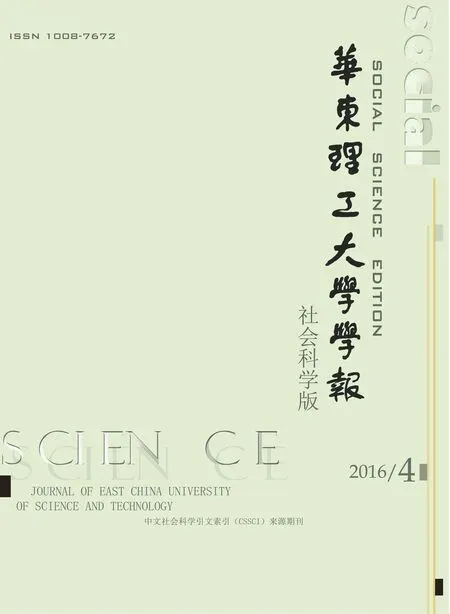国家不是艺术品?
——中西国家学的一个比较
陈迎年(华东理工大学哲学研究所,上海 200237)
哲学与文化
国家不是艺术品?
——中西国家学的一个比较
陈迎年
(华东理工大学哲学研究所,上海 200237)
国家学仍然是政治哲学的拱心石。本文在深入分析黑格尔“国家不是艺术品”命题的内在层次的基础上,比较了黑格尔的国家学与儒家的国家学:两者都强调国家具有超出个人的人性之上的神性部分,都坚持美真的分别与同一;但儒家国家学的艺术纯度更高,更容易以高涨的浪漫主义“道统纪”来实现对黑格尔“神统纪”国家学的批判和超越。因此,简单地给某种国家学标上“极权主义”、“保守主义”等标签以了事非常容易,但却可能因此而错失很多东西;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儒家国家学现代化的前提条件;现代化的儒家国家学,有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国家 艺术品 国家学 黑格尔 牟宗三 马克思
对于今天的政治哲学来说,尽管流行“共同体”概念,或者直接试图避开“国家”一词,但实际上,国家学仍然占据着确定无疑的核心位置。相应地,儒学或者被诠释为专制意识形态,或者被解释为原始自由主义,或者被导向超越了个人与极权两极对立的社群主义等,争论的焦点仍然在国家学。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中华文化的发展繁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条件,而发展繁荣中华文化则必须直面儒家的国家学。不过,由于并不存在集中、现成的儒家国家学,问题便转化为:儒家的国家学基因如何能够与当代国家学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这是一个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的思索过程。
本文以黑格尔“国家不是艺术品”命题为基本问题来展开。之所以如此,除了把复杂问题具体化以逐步扎实推进的考虑外,至少还有如下三方面的原因:首先,虽然马尔库塞、卢卡奇等人对黑格尔的“国家理想主义”进行了辩护,但人们还是如著名的罗素那样易于把这种国家至上说跟极权主义联系起来,这与儒学的境域极其相似;①郁建兴:《黑格尔的国家观》,《政治学研究》1999年第3期。其次,现代新儒家如牟宗三常借用黑格尔的国家学来讨论儒学的“外王”问题,以期有所“共喻”,来展示儒学的现代性,但同样引起了人们的广泛争论;最后,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黑格尔国家学中的庸人气味及露骨的、非批判的神秘主义,但却并非置之不理,而是通过“扬弃”让其获得了新内容从而“完成”了它。在当代,深入剖析黑格尔的国家学,不仅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也有利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这里的任务是在思索中重建,而非简单地判断“正确”或“错误”。因为,“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9页。那么,如何才能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那样入乎其内而又出乎其外,来实现重建儒家国家观的任务呢?
一、神圣国家:专制还是自由?
黑格尔国家学的突出特征,就是强调国家具有超出个人的人性之上的神性部分,且把这种神性部分的顶峰和起点具体地规定为君主。在黑格尔看来,这神性并非源自国家的“应然”,而出于对国家的“认识”。
按黑格尔的逻辑,既然国家学在于说明如何“认识”国家,那么这“神性”便以“理性”的自足面目出现,除考察“必然性”之外,别无他求。“它就是把国家作为其自身是一种理性的东西来理解和叙述的尝试,除此以外,它什么也不是。”②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3页。“国家必须被看做一个建筑学上的大建筑物,被看做显现在现实性中的那理性的象形文字。因此,一切关于纯粹功利的东西、外部的事物等等,都应该被排除在哲学探讨之外。国家是自我规定的和完全主权的意志,是自己的最后决断。”③同上,第300页。由此,“君主”与“国家”同一了:一方面,黑格尔强调,“‘国家'是存在于‘地球'上的‘神圣观念'”。④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国家是神的意志,也就是当前的、开展成为世界的现实形态和组织的地上的精神。”“神自身在地上行进,这就是国家。国家的根据就是作为意志而实现自己的理性的力量。”⑤同②,第271、259页。另一方面,道成肉身,黑格尔把君主也看成是“以神的权威为基础的东西”,即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任性”或普遍理智最难理解的“神物”。⑥同上,第301、297页。
既然国家学在于“认识”国家而非只想象国家的“应然”,那么,显现在现实性中的“非理性”的东西,那些关于纯粹功利的东西、外部的事物,怎能轻易就被排除在外呢?此种“排除”工作之后,难道不是只余留下国家的“应然”了吗?这个问题,是“国家不是艺术品”命题的核心问题,笔者留等下节再论。这里要强调的是,黑格尔国家学中的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让黑格尔以普鲁士国家的卫道士形象示人,长期背负“极权主义”的恶名。
无独有偶,在《正论》篇中,荀子曾这样描写“天子”:“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道德纯备,智惠甚明,南面而听天下”,而且“势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志无所屈,而形不劳,尊无上矣”,很懂得服饰饮食、行居坐卧等全方位的安乐恬愉,以至“居如大神,动如天帝”。⑦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31-336页。荀子的描述并非空穴来风,而是讲明了儒家的一个常识,或者说一个早在儒家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的奠基性神话。比如《尚书》一开篇,帝尧便以这种大神天帝形象出现:“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⑧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页。再比如《诗经·大雅·文王》,同样塑造了那种美德光芒四射、泽及天下百姓、受天命而王天下的“神物”。因此,有人倾向于认定,儒家将社会导向极端的王权专制,对今日之中国罪莫大焉。
非常有意味的是,黑格尔也根据中国大神天帝的“天子”而判定“中华帝国”“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是君主的专制政体”,因而虽然是“最古老的国家”,但却很不成熟,还处于国家发展的最初阶段(起点)。①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23页。相反,他却认为自己道成肉身的国家学代表着国家的高级阶段(终点)。据说这种国家学知道人类之为人类都绝对是自由的,而要真正实现这种自由,每个人必须自在自为地将自己交给“神物”。个人如果脱离国家,不接受国家的统治和管理,他就丧失了自由和作为人的种种权利。黑格尔写道,“成为国家成员是单个人的最高义务”,“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②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53-254页。
值得关注的是,现代新儒家中以中国文化为本位者如牟宗三,竟然对黑格尔的这种国家学推崇备至,也基本同意黑格尔对中国之为君主专制政体、个体自由缺乏等批评。其所争者,只在东方这个起点,也即是决定的终点:各民族国家的发展有其自身起伏隐显的节律,空间不能取代时间,过去的发展程度不代表未来的发展前景,因而过去中国的发展虽伏而不显,但却并非如黑格尔所论仅仅只是“起点”,随着中国对世界知识的学习,随着东方的觉醒和发展等,世界历史最终必然回到这片“故土”上来。③牟宗三:《历史哲学》,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65页。
现在的问题是:同为圣王国家、同样强调个人之于集团的本分义务,是什么让黑格尔判定中国的王权成就的是专制,而日耳曼的王权却是自由的绝对保障?是什么让黑格尔敢于一方面宣称东方各国是专制的只知道一个人的自由,希腊和罗马世界是贵族的只知道一部分人的自由,而日耳曼是民主的知道一切人的自由,另一方面又在讨论日耳曼的王权时把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的古代区分看成是“一种外在的差别”、“纯粹数量上的差别”,认其“完全是肤浅的”?④同②,第287页。是什么让牟宗三相信“黑氏讲国家,是从精神表现价值实现上讲,是一个道德理性上的概念,文化上的概念”,⑤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139页。而非极权独裁的国家学?是什么让牟宗三敢于借助黑格尔的国家学,来走出中国道德理性表现上的专制主义传统?
二、国家与艺术品:美真的分别与同一
上述系列问题涉及黑格尔辩证法的左右逢源。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黑格尔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处处都从各种规定的对立出发,并把这种对立加以强调”。⑥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2页。即,无论是黑格尔把精神现象学分为三大部门,第一是有灵魂、意识、心灵三环节的主观精神,第二是有法、道德、伦理三环节的客观精神(法哲学即在此层面上讲),第三是有艺术、宗教、哲学三环节的绝对精神,从而构筑了一个大环套小环环环紧相连的因陀罗网迷宫;抑或把合理性与现实性等同起来以构筑必然性,宣称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抑或处处强调国家是一个包含着各种差别的发展的有机生命整体:凡此等等,都是两头通的。这里不妨借“国家不是艺术品”这一命题来展开讨论。
一方面,美真分属,国家不是艺术品。黑格尔说:“国家本质上是尘世的和有限的,它具有特殊目的和特殊权力。”⑦同②,第281页。“国家不是艺术品;它立足于地上,从而立足在任性、偶然事件和错误等的领域中,恶劣的行为可以在许多方面破损国家的形相。但是最丑恶的人,如罪犯、病人、残废者,毕竟是个活人。”⑧同②,第259页。这里的尘世、有限、地上等,都是指国家是一种独立自主性的客观存在,因而是真的,也就是特殊的和不完美的,甚至丑恶的。相反,艺术品却是美的,也就是普遍的、无限的和自由的。这是因为,“美就是理念”,“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⑨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2页。艺术品中的感性的客观因素虽然还是客观存在,但其存在的直接性已经被取消掉了,因而才能够作为理念的感性统一物,才是美的。比如画家所画的马,不是活的真马,只取了真马所现的现象,所以虽然还是一种客观存在,但真实的存在本身的纷繁杂芜已经被取消了,真实存在所特有的规律已经被否定了,从而概念才得以在其中安身,“像在自己家里一样”。①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3页。
要而言之,在黑格尔那里,“真的东西”或者属于观念和感情(宗教中的上帝),或者属于直觉(艺术中的图画和观察),或者属于被认识和了解的思想(哲学中的概念),因为三者都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结合;但国家却是精神“在有限生存中完全实现它自己时所取的形态”,因而是所有那些主观与客观结合的“基础和中心”。作为基础和中心,国家把自己与艺术品区分了开来。②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51、55-56页。
另一方面,美真合一,国家也是艺术品。既然国家与宗教、艺术、哲学都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结合,都是“真”的,那么也可以说这四者有“同一的地位”。③同上,第52页。在这个意义上,国家也是艺术品,每一个具体的国家都是国家概念的感性显现。黑格尔说:“国家具有一个生动活泼的灵魂,使一切振奋的这个灵魂就是主观性,它制造差别,但另一方面又把它们结合在统一中。”④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81页。“根据某些原则,每个国家都可被指出是不好的,都可被找到有这种或那种缺陷,但是国家,尤其现代发达的国家,在自身中总含有它存在的本质的环节。”⑤同上,第259页。
在这里,黑格尔强调的是必然性,是绝对精神本身,因而要求排除掉一切关于纯粹功利的东西、外部的事物等等。把这些感性的东西排除掉了,剩下的就只有绝对精神本身了,国家与艺术品的区别当然随之亦无。如果再考虑到黑格尔视“社会和国家的目的在于使一切人类的潜能以及一切人的能力在一切方面和一切方向都可以得到发展的表现”,⑥同①,第59页。以及后来的海德格尔把诗的吟咏、思的谋划、翻耕的塑造、创建国邦的行动等,或者说艺术、建国、牺牲、思想和生产等,都归结为本源的艺术作品,⑦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8页;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45-46页。国家与艺术品的这种同一也就更清楚了。
如此既分属又合一,黑格尔实际上是把“时间”自由开启和闭合了。⑧同②,第75页。时间开启了,精神在时间里发展了,美真便不同,则国家不是艺术品;时间闭合了,精神回到了自身,美真便处于同一地位,则国家就是艺术品。这样,时间的自由开启和闭合,也就意味着时间的某个横截面的展显或时间的当下圆顿完成,以及两者之间的自由变通。由此,巨大的辩证法生成了。
人们往往把目光更多地投向黑格尔的这个巨大辩证法,但这里要强调的却是,能够保证辩证法生天生地巨大功能的现实环节,唯有知解力。“知解力活动是有限的,不自由的,因为它把看到的事物都假定为独立自在的”,根据这种抽象的假定,感觉对象都是实在的,人们只有克服主体作用,即首先适应、被动授受、正确了解它们,然后才能“认识”真理,然后才谈得上利用知解力工具展开“实践”,实现主体的自由。⑨同①,第144-145页。这种工具而非目的性质的知解力,即一般所谓的知性、思辨理性或工具理性等,表现在国家形态中,便是客观精神,便是法。也就是说,知解力假定建立起了客体,并帮助主体通过实践克服客体以实现自由。这意味着,知解力是自我牺牲的化身,它“知道”自己是抽象的、不自由的和有限的,同时必然也能够在“时间”中“自由”地取消掉自己的种种片面性,而回归到绝对精神的无限之中。
这样看来,正是因为发展和成就了知解力这种“假定”,有“客观精神”以为基础,黑格尔才有了底气把自己的神圣王国与中国的专制王国区别开,牟宗三才乐于在《历史哲学》、《荀学大略》等著作中借助黑格尔的国家学来重建中国道德的神圣王国。⑩陈迎年:《认识论·意识形态·存在论——牟宗三的荀子阐释批判》,《人文杂志》2013年第10期。应该说,知解力的假定和取消,它在时间中的自由开启和闭合,在黑格尔是“精神现象学”,在牟宗三是“良知坎陷”。牟宗三的“智的直觉”,也可以看成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
三、国家艺术品的纯度:神统纪与道统纪
把牟宗三的“良知坎陷”等同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关注的重点是两者之“同”。两人都把“真正的国家”视为灌注了生气的有机体,它圆满自足,是绝对的真实、实体性的真实、最高的真实、本然的真实,“就是最高的对立与矛盾的解决。在最高的真实里,自由与必然,心灵与自然,知识与对象,规律与动机等的对立都不存在了,总之,一切对立与矛盾,不管它们采取什么形式,都失其为对立与矛盾了”。①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7页;陈迎年:《牟宗三的善美学》,《文艺研究》2010年第5期。
这种境界,牟宗三在《圆善论》中名之曰“圆善”。不过,牟宗三又强调说,自己的圆善“直接从孟子讲起”,“是孟子的智慧”,而“必须顺王学之致良知教而发展至王龙溪之‘四无',再由此而回归于明道之‘一本'与胡五峰之‘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始正式显出”。②牟宗三:《圆善论》,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版,第Ⅹ页。
众所周知,对立与矛盾并非什么新鲜事物,自古以来一直都在搅扰着人类,如中国古代的性与情,或者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的对立与矛盾等。但是同样不可否认,“只有近代文化教养才把它们推演成为最尖锐最剧烈的矛盾。偏重知解力的文化教养,或则说,近代的知解力,在人心中造成了这种对立,使人成为两栖动物”。于是,“动物彼此之间以及与周围事物都和平相处,而人的心灵性却酿成两面性和分裂,他就围困在这种矛盾中”。③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6、125页。质言之,因为知解力的近代扩张,已经让它取代了道德之“觉”而成为人禽之辨的关节点。于是,“人类的第一天性便是他直接的、单纯的、动物的存在”,作为“第二天性”的道德或自由绝不是什么原始的和天然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知解力的后果,“要靠知识和意志无穷的训练,才可以找出和获得”。④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3-43页。因此,国家学首要的东西便不是“道德”,而是“抽象法”。
在已经确知并认同这种古今变化的情况下,⑤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页。牟宗三仍然要把真实的国家首先安放于孟子学,于是,牟宗三与黑格尔之“同”马上便标明了两人之“异”。
一方面,由于知解力“假定”在辩证法中的基础性地位,黑格尔的国家学必然强调事物各自的独立自在性,而表现为众多独立自在者之间,如市民社会与国家、抽象法与伦理、私利与公益、手段与目的、自由与法律、现象与本质、自由与必然、认识的心灵与实践的心灵等的普遍对立和矛盾。对立和矛盾是如此地普遍和尖锐剧烈,以至于马克思多次强调黑格尔的国家学“有意识地坚持二元论”,因而总陷入“二律背反”之中,最终成为了“木质的铁”、“雅努斯的两面头”,或者说“布利丹的驴子”。⑥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3、314、350、354、360等页。
马克思本人对这种二元论国家学虽有所批判,但却比黑格尔更加重视和坚持了知解力假定的基础性地位,强调“对现代国家制度的真正哲学的批判,不仅要揭露这种制度中实际存在的矛盾,而且要解释这些矛盾;真正哲学的批判要理解这些矛盾的根源和必然性,从它们的特殊意义上来把握它们”。⑦同上,第359页。
沿这条线发展下去,政治科学从政治哲学中渐渐分离了出来,迅速壮大,最终甚至“自视为获得政治事物真正知识的唯一方式”。⑧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知解力“假定”以为基础,牟宗三才需要借助黑格尔的国家学来重建中国道德的神圣王国的国家学,把“坎陷”出科学和民主之“新外王”当作其国家学的首要任务。培养生成知解力,开出对列格局,实现中国道德神圣王国的客观化,成为牟宗三国家学的焦点。这是《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道德的理想主义》等书所反复申说的,而为大家所熟知,这里不再赘述。
唯牟宗三还要把黑格尔国家学的“神统纪”向前再推进一步,以再造一个更加质实、现成、神圣、道德的“道统纪”。①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页。“道统纪”的国家学先跟“神统纪”的国家学一样,强调表面上的历史曲折宛转的发展不过是绝对精神、精神实体在背后荡漾的结果,然后又转进一步,把精神实体推出去,理解为个人可以当下显现的“道德的心”,或者说“现成良知”。而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在牟宗三看来,西方人(包括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等)的辩证法实际上都接触不到“真实”,都是现象层面的滚雪球,都是横冲直撞的毁灭之道,而需要让它停下来,需要有一个凝然坚住的道德心灵实体作为“起头处”而对其进行自如的收放。这便是“辩证法的辩证”,它指望和依靠中国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儒家、孟子心性之学一系,要把上帝、实体等从现象之流中拉出来,与之打成两截,超然为之基地。②陈迎年:《智的直觉与审美直觉——牟宗三美学批判》,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5-112页。
众所周知,黑格尔“神统纪”国家学的那个客观而绝对必然的上帝,开始时只是空洞无物,需要在辩证发展中来充实和厘定,然后才能获得其内容和特性,所以它必须以知解力为基础。但是,当牟宗三“道统纪”国家学在开始的时候,让人人具有凝然坚住的现成良知,本性圆满自足,则人人都已经是上帝了,根本无需知解力来充实和厘定自己。于是,牟宗三“道统记”国家学的焦点虽在知解力,但那却是假象,其中心只能是道德神心的自由呈现。所以牟宗三才敢说,自己的国家学纯粹是孟子的智慧。
按牟宗三的理解,哲学本质上就是政治的,政治附属于道德,政治科学仅仅只是大海中的一朵浪花、平地上的一个土堆,只有极其短暂、有限的意义。于是,儒家的神圣国家成为唯一的真正艺术品,即真即美即善;而一般所谓的艺术品,包括黑格尔的作为艺术品的国家,美则美矣,却都处于现象层,既不真也不善。这样,牟宗三的国家学就要比黑格尔的国家学更少杂质,美真合一的纯度更高。
四、人性问题:两头凑泊还是本体下贯?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黑格尔的国家学一分为二,即作为“体系”的国家学和作为“方法”的国家学。作为体系,黑格尔的国家学受到了无情的批判,它首先是“露骨的神秘主义”的产物,因为神圣观念既是国家的“终点”也是国家的“起点”,它使自己外化为国家,然后又在思维中和在国家的历史发展中,再返回到自身。因此,神秘的实体成了国家的主体,而国家的主体则成了某种其他的东西,成了神秘的实体的一个环节。③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59、273页。正如黑格尔所说的,“上帝统治着世界,而‘世界历史'便是上帝的实际行政,便是上帝计划的见诸实行”。④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其次,这种国家学“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是极其温和保守的,“几乎达到奴颜婢膝的地步”,它让人们看到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并承认一切现实的国家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因此“不必向自己的同时代人提出太高的实践的政治要求”。⑤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4页;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01页。
作为方法,黑格尔的国家学却得到很高的赞誉。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处处都从各种规定的对立出发,并把这种对立加以强调,因此“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完整的阐述”。⑥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9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他们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天才论述,都可以被看成是黑格尔国家学的某种延续,“他的革命方面,即辩证方法,是被当作出发点的”。①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8页。
按照这种“体系”与“方法”的区分,既然牟宗三的国家学已经让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停了下来,而且还标示出一个凝然坚住、本性圆满自足的现成良知,那么它只能作为一种体系,比黑格尔的国家学更为神秘和保守。牟宗三本人也的确常常需要为其浓厚的神秘主义和保守主义色彩而辩护。②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页;《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17页;《中国文化的省察——牟宗三讲演录》,台湾联合报社1983年版,第20页。
这特别涉及对人性的理解。恩格斯曾经表彰黑格尔的深刻:“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的思想。”③同①,第233页。所以,黑格尔一方面视国家为艺术品,强调“‘国家'是存在于‘地球'上的‘神圣观念'”,“国家乃是‘自由'的实现”,赋予国家以先天的永久性和神圣性,视其为道德、伦常、宗教虔敬、美等等之类东西的完成。④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另一方面,黑格尔却也看到了国家这种艺术品与一般所谓美的艺术的差别,即在于前者之真是赤裸裸的,有丑在焉,有恶在焉:德性和那些先天的永久性和神圣性的东西“同‘世界'和世界的创作之间就没有什么主要的关系了”,现实世界是“德性横遭宰割的屠场”,人类“个别兴趣和自私欲望”引发种种“暴行”和“腐败的常例”,绘出“一幅最为可怖的图画”,“只要一想起来,就得使我们忍受内心的苦刑,无可辩护,无可逃避”。⑤同上,第21-22页。
无论人们称这种既是艺术品又不是艺术品的国家源于“人类的非社会和社会性”,⑥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页。抑或“理性的狡计”、⑦同④,第34页。“存在游戏”、⑧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69页。“天道之权变”⑨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页。等,有一点是明确的:传统儒家对此并不陌生。这里无需指出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的背反,亦无需述说宋儒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对立等,只需听一听朱夫子的感叹即可:“千五百年之间,正坐为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⑩朱熹:《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3页。
出于对孔孟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及“儒门淡泊”等的焦虑,牟宗三的国家学最终明确放弃了黑格尔国家学中众多独立自在者之间的游斗凑泊,停止了善与恶、心与物的辩证法,而改为直觉之理的直接下贯和现成良知的自我坎陷。所谓“自我坎陷”严格说来并不是一般人所谓的辩证法,而只是一种绝对的唯心论,因为它以“心”这个绝对而岿然不动的形上实体、道德本体作为起头,本身只可以流射、放射而无所谓辩证。⑪陈迎年:《智的直觉与审美直觉——牟宗三美学批判》,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
本体下贯的国家学美则美矣,然而却是不真的艺术品。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那样,“好的最大敌人是最好”,“纯粹的光明就是纯粹的黑暗”,⑫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第226页;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8页。这种国家学以高涨的浪漫主义完成了对黑格尔的批判,但却因此比黑格尔更加发展了国家的形式主义,是一种更加可怕的首尾一贯和同义反复;因为缺乏对立面,在实践中它更有利于一个人独断独行的政治国家的形成,更易于把政治国家和物质国家都变身为奴隶。就此而言,牟宗三的庸人气味更重,江湖气味更重。
不过也需看到,浪漫主义的国家学并不足以为中国的政治国家负责,亦不意味着儒家国家学的一无事处和全面衰落。正如恩格斯所言,“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⑬同①,第254页。哲学已经终结了,学术已经终结了,问题只在于改变世界,只在于政治。套用马克思的话来来说,“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对于儒家国家学的批判一定不能只讨论其本身,而应该“集中于只用一个办法即通过实践才能解决的那些课题上去”,因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①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7、460页。就此而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儒家国家学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责任编辑:肖舟)
The State is not a Work of Art:A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State Theory
CHEN Yingnian
(School of Marxism,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China)
The state theory is still the keyston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Hegel's proposition of“the state is not a work of art”,and comparing this with those of the Confucianism. Thus it stressed:First,the words of“totalitarianism”or“conservatism”is clear enough,but it may miss a lot of things;Secondly,China's modernization is a premise condi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thirdly,modern Confucianism is helpful to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China.
state;work of art;state theory;Hegel;Mou Tsung-san;Marx
陈迎年(1974-),陕西耀州人,博士,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儒学现代化问题研究。
B035
A
1008-7672(2016)04-008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