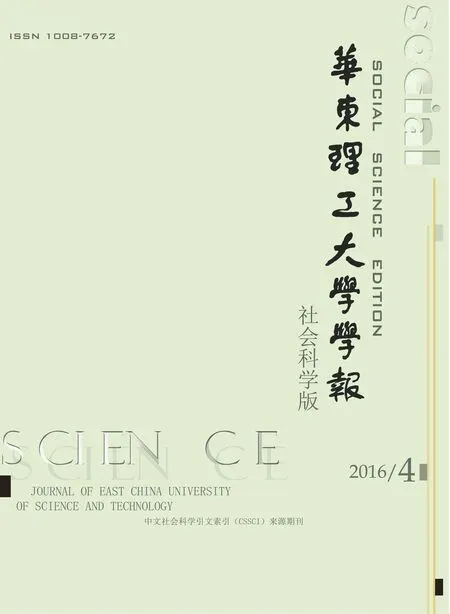抗争文化:当前农村地区抗争政治的“催化剂”
胡兵(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校团委,上海 200237)
政治与法律
抗争文化:当前农村地区抗争政治的“催化剂”
胡兵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校团委,上海 200237)
当前,中国农村地区每年都会发生诸多抗争事件,本文从地域文化中的民风民俗谈起,指出民风对农村地区的抗争环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抗争事件的发生反过来又影响了该地区的文化。从这个互动过程来看,抗争文化对农村地区的抗争政治起着“催化剂”的作用。对抗争文化进行研究,有助于厘清抗争政治发生的全过程。文章最后指出当前抗争文化的扩散趋势,直接影响了农村地区抗争政治频发的环境。
抗争文化 地域文化 抗争政治
马克思认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当人们所属的社会阶级与敌对阶级的矛盾充分发展之后,他们就会展开集体行动。就无产者而言,当资本主义把他们逼进工厂,让他们失去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同时又使他们形成了包括阶级意识和工会组织在内的集体行动资源时,他们就会开展集体行动。但问题是:为什么一个“应该”造反的群体的成员经常不去造反?为什么缺少了一部分重要成员的协作,工人运动就不能成功?为此,马克思提出了一个“虚假意识”理论,即工人之所以不能按照“历史”的要求行动,是因为他们还笼罩在阶级敌人所制造的无知的迷雾中。①转引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凤凰传媒出版集团、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5页。也就是说,工人被“骗”了,只要时间一长,工人们意识到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这个问题就能自行解决了。应该看到,马克思虽然看出集体行动的根源在于社会结构,却严重低估了从事集体行动所需要的资源。而实际上,抗争文化对于抗争政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考察抗争文化所发挥的作用,本文以Z镇为研究单位,力图呈现出抗争文化在乡域内的“抗争治理”的复杂关系。Z镇属于华中地区,地形特征以平原、河流和湖泊为主,包括若干丘陵地带。福武直曾总结过华中地区村落的特点:华中地区的农村作为形成社会集团的地域空间虽然具有一定的集团性,但是这一范围决不是充足的,与华北和华南的村落相比,华中地区的村落更加开放,更缺少自我满足性。①转引自李国庆:《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论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因此,对于处于变动中的中国社会来说,Z镇无疑是较好的研究样本。②根据学术规范以及对田野调查者隐私权的保护和尊重,文中出现的地方均为化名,文中受访者的姓名也使用了别名。下文同。
一、地域文化中的民风民俗
民风民俗反映出一个地域的文化,更反映出这个地域人们的特点。本文所研究的Z镇及所在的G县的居民非常敬重祖宗,素有正月十五“送灯”的习俗,③光山县委统战部:《信阳光山县独特的元宵节“送灯”习俗》,载《根在中原网(信阳站)》,2012-3-21正月十五这一天,人们无论身居何处,都风雨无阻地赶回家,早早吃罢团圆饭,准备给祖坟“送灯”。全家人在长辈的率领下,带着各式灯具、五彩蜡烛、纸钱祭品、烟花爆竹,悉数前往祖坟地送灯,烧纸钱、放烟花、鸣炮磕头。是夜,全县坟地一片灯光,各种烟花此起彼伏,绚丽多彩,阵阵炮声,震耳欲聋。给祖坟送灯、祭奠先人,不仅是对先人的怀念,更是尊老敬祖传统美德的传承。
Z镇及G县人素来好客,对朋友一向有好客传统,春节时请春酒或平时招待亲朋,酒席颇为丰盛。从建国初期的两荤六素八个菜,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八个凉菜、四个爆炒、四个煎炸、四个烹菜、四羹汤,桌上还摆放水果酒和白酒外加啤酒或其他饮料,随客人选用。上第一道菜时,由主人亲自端放在桌上,一一敬酒,并客套一番;筵宴中间上“圆子”菜时,主人又二次敬酒,以示热情。④光山县志编撰委员会:《光山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79页。从筵宴习俗上可以看出该地方人们的好客程度。G县人民对阶级敌人,自古以来就形成了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传统。清代末期,县境内农民不断地自发组织起来,打官府、杀豪绅,抗暴活动此起彼伏。20世纪初,G县激进的知识分子,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活动;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倡导和致力“自治运动”,中共G县支部成立后,特务队、武装便衣队、赤卫队、农民自卫军相继建立,组成新的县区乡苏维埃民主政府。⑤同上,第199页。这些可以看出G县人民爱憎分明的文化特点。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战争、交通、资源等影响和限制,G县一直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即国家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为落后。改革开放后,G县剩余农村劳动力陆续外出到沿海省市打工,农民陆续致富起来。然而正如亨廷顿所说的那样: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⑥[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8页。如果贫穷的国家或地区出现动乱,那并非是因为他们贫穷,而是因为他们想致富。在G县,经济的发展对人们之间的交往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打工”之前的农忙阶段,各村庄村民互帮互助,小孩基本上都是吃百家饭长大的,碰到在谁家玩就在谁家吃饭。然而,“打工”这种生产方式出来之后,村民之间的交往开始以利益来衡量了,农忙的时候帮忙不再是“白干”,而是以每天多少钱的方式结算。村民建房也不再是雇佣几个长工和短工,而是承包给建筑队。村民之间的传统的交往方式受到剧烈的冲击。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一批人迅速致富起来,而另一批人则没有起色,于是这种分化带给村民的心理落差迅速蔓延,村民之间不再团结一心,在他人遇到困难时,幸灾乐祸者有之,隔岸观火者有之。
Z镇魏冲村一户人家外出打工期间,房梁年久失修塌了下来,却没人告诉他,直到他打电话回来才知道房屋塌了,房屋日晒夜露1个多月,损失惨重。Z镇大余湾一户人家,堆放物品的旧房屋因连降暴雨变成危房,由于男方外出打工,女主人没法转移物品,而村子男劳力却不肯帮忙,于是只好借拆旧房屋的名义请了一支建筑队才把物品转移出去。
从上面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市场经济的发展,严重冲击着传统村庄的民风民俗,使得一些原本民风淳朴的村庄也夹杂着更多的利益成分。新时期的民风民俗尚未成型,正处于变动和待塑造的状态。在具体的抗争政治案例中,一些民风民俗被工具性地利用,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促成抗争政治,而抗争政治事件反过来又对尚处在变动之中的民风民俗产生重要的影响,甚至会打上抗争政治的印迹。媒体曾多次报道游客路过各地村庄,与村民纠纷时经常吃大亏,甚至以民风民俗被破坏来“敲诈”游客,于是,所谓“穷乡僻壤出刁民”便传了开来。显然,这是对当前村庄中民风民俗的不恰当反映,但也从另一个角度提醒人们如何看待抗争政治与民风民俗的关系?即如何塑造当前的民风民俗?
二、农村场景中的抗争政治
自古以来,不同的地方(村庄或乡镇)有着不同的民风民俗,民风乃某一区域民众的特征。有民风彪悍之地,也有民风淳朴之地。裴宜理认为,在一些地区长期存在的叛乱的传统与当地的生态环境和经济生活密切相关,而这种长期叛乱的环境作为传统文化因素又影响新的条件下农民的叛乱形式。①[美]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55-271页。比如,同样的政策执行造成一定程度的“侵权”,引起部分民众的不满,但有些地方发生抗争,而有些地方民众则以智慧来化解侵权,其区别就在于“民风”起着关键的作用。
1.民风的基础:宗族文化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中国大陆部分农村地区的村落,多为一个姓氏为主集中居住,大的宗族居住地形成村庄或集镇,很多地名源自宗族聚落,并以宗族姓氏形成地名。宗族指拥有共同祖先的人群集合,通常在同一聚居地,形成大的聚落,属于现代意义上模糊的族群概念。家族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组织,包括同一血统的几辈人。宗族是家族的泛称,不同的姓氏,代表不同的宗族;同一姓氏,但由于不是同一父系的家族,故有“同姓不同宗”的说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拍摄的电影《芙蓉镇》即在湘西永顺县王村镇拍摄的,王村便是以王姓为主的城镇。即使进入二十一世纪,远离中心城市的农村地区、山区,仍旧存在以宗族聚居为主的村落,也发生着许多以宗族为背景的村庄故事。比如发生在1980年的一次村民“械斗”,解决了大明湾、小明湾之间的水库用水问题。
械斗发生在大、小明湾的村民之间。小明湾是外迁人口村,有20多户人家。他们是从深山里外迁出来的。政府当时给他们分了部分田地,他们另外在丘陵地形上开辟了部分荒地,构成了小明湾村民土地的全部来源。小明湾水田的上方有一个水库,用于水田灌溉。水库的下方除了有小明湾的水田外,还有稍远一点的大明湾和方湾的水田。由于水库面积不大,蓄水量基本上只能满足小明湾的水田。遇到旱涝天气,大明湾的村民就会去“偷水”,即把上方小明湾的水田田埂掘个口,水便向下流了。1980年,又遇上旱涝天气,大明湾的人便偷偷给水库掘个口,一直向下放水,被发现后,两村人发生大规模的械斗,共有近30名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拿着铁锹、锄头之类农具参与械斗,受伤10余人,有2人被打晕后扔进水库,后被救醒,没有人命伤亡。械斗的结果是小明湾进一步明确了使用水库的绝对优先地位。至今大明湾仍会发生个别“偷水事件”,但总体上已经不再为水库用水产生纠纷了。
事后,村中长者回忆,幸亏制止及时,否则一旦出了人命,械斗就会变成“世仇”。这起事件在双方村子都起到一定的震撼:小明湾以不到20户的村民,与超过40户的大明湾械斗,并且赢了。当年参与械斗的年轻人,在放牛时也经常打架,时常有输有赢,但从来没有过械斗。但这次,他们明白,非这样不可,因为他们代表的是全村人的利益。
这起“分水风波”,让人想起“洪洞县广胜寺好汉宫”在晋南一带广为流传的油锅捞铜钱分水的故事。①广胜寺分水亭现存碑文“霍泉分水铁栅记”记载:“霍麓出泉,溉田行顷,唐贞观间,分南北二渠,赵城十之七,洪洞十之三。因分水不均。屡争屡讼,雍正三年乙已夏,余署府篆,诣渠相度,创制铁栅,分为十洞,界以墙,南三北七,秋九月起工,四年丙午春告竣,水均民悦,相率面清。”这就是广胜寺洪三赵七分水亭的真实历史。传说在当时赵县的一个二十岁勇敢的小伙,飞快地把手伸进油烟翻滚的油锅,捞出七枚铜钱。从此,霍泉水“赵七洪三”。小明湾村民据说也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或许村民们从这个传说中汲取了智慧,能够很好地处理“分水”的问题了。
2.民风的建设力量:乡村精英
乡村精英是指那些比其他成员能调动更多社会资源、获得更多权威性价值分配,如安全、尊重、影响力的人。②仝志辉:《农民选举参与中的精英动员》,《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1期。陈光金依据不同乡村精英在不同资本上的相对优势,把乡村精英也划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③陈光金:《20世纪末农村社区精英的“资本”积累策略》,《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中国的知名村庄一般都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乡村精英,如江苏江阴华西村的吴仁宝、河南临颍南街村的王洪彬、山东寿光三元朱村的王乐义等,他们属于政治精英。贺雪峰通过对传统村庄的研究将乡村精英分为两类,一是在任的村(组)干部,为治理精英,因为他们实权在握,自然有他们用权的地方和理由,也就有他们发挥权威的基础;二是非在任村(组)干部,他们对村(组)干部的决策和行为具有重大影响力,且对一般村民具有号召力的那部分村民。④贺雪峰:《村庄精英与社区记忆: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4期。在Z镇,一些乡村精英及由他们主导的民间组织,不仅在乡村治理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也在抗争政治的发生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例如这起因砍树发生的抗争事件。
Z镇地处丘陵地带,小山丘特别多,在小明湾、大明湾、石子岗、竹岗四个村子附近有一个小山坡,山上种满了杉树,属于陈岗村(行政村)的,有两个老党员负责看守。村民们一般都在这个小山坡上放牛。1998年,陈岗村委会突然决定砍掉山上所有的杉树,由各村小组长传达给这四个村。村民的反响基本上都很平静,“树是人家的,砍就砍呗”。直到砍树的前一天晚上,小明湾村民在纳凉时一位长者说了句,“这么多树就砍了,他们得搞到多少钱啊?我们以后就没地方放牛了”,引起了许多人的响应,都觉得村里做的不对。人们不禁义愤填膺,决定不让他们砍树,要先搞清楚砍完树后村民能得到什么好处。于是第二天一早,小明湾十几名妇女到了山上阻止砍树工人上山,后来石子岗村也有几位妇女参与进来。待陈岗村大队会计带人上山砍树时,见到这一阵势,就让工人回去了。他留下来谈判,具体结果就是砍完树后山上的土地整理以及可开荒的地全部归小明湾和石子岗,事件就此告一段落。大明湾和竹岗的村民事后后悔不已,不过也没有太闹事,原因是他们没有参与这起事件,如果再“插一杠子”就有些理亏。
在这起事件中,乡村精英起到了在关键时候与对方讨价还价以获取利益的角色。比如大明湾和竹岗在这件事中的表现,他们认为再争取利益是侵占了小明湾和石子岗的利益,他们把相邻的村子人看成是自己人,所以他们选择不去要那些小利益。而小明湾和石子岗则把村委会的人当成了“敌人”,需要把该得的部分利益讨回来。
3.民风的挑战因素:乡村混混
乡村混混,是指乡村社会中不务正业、为非作歹者,以青年人居多。作为研究对象的“乡村混混”,是一个去标签化的中性词汇。正如默顿所言,边缘基层的越轨行为来自于社会倡导的文化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合法手段之间的断裂与紧张,为了减轻这种紧张,他需要通过越轨来释放自己的失望。⑤Robert K.Merton,1Social Structure and Anomie.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38(3):PP.672-68.它是一个“地方性知识”的概念,用于表达在乡村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越轨”青年群体。华中学派的一批学者对“乡村混混”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研究。①如陈柏峰:《乡村混混与农村社会灰色化——两湖平原,1980-2008》,华中科技大学2008年社会学博士学位论文;黄海:《当代乡村的越轨行为与社会秩序——红镇“混混”研究(1981-2006年)》,华中科技大学2008年社会学博士学位论文;以及黄海:《乡村“混混”的生存土壤——对湘北H镇农村不良青年的考察》,《青年研究》2008年第11期等。他们的结论是,乡村混混是一种常态持续存在,有其特定的社会基础,只要有社会变迁中的时空差异和文化碰撞,就会有边缘人的存在,也就会有乡村混混。在Z镇,也有着这种乡村混混,他们不断挑战着“纯朴”的民风。
2002年秋天,Z镇小明湾村头的谷场突然燃起一场大火,共5个谷垛子被烧,当晚火灾即被扑灭,其中1个大面积烧毁,其余4个小面积过火,涉及4户人家。谷垛子被烧事件在Z镇掀起轩然大波,居民议论纷纷,派出所也到过现场,但最终没有查出个所以然来,案件不了了之。
谷场向来是村民们的保护重地,一般由关系好的几户人家建在靠近村边的空地上,由于收割周期较短或者可能碰到雨天,使得收割的水稻杆来不及打成稻谷,便都堆放在谷场,形成一个个谷垛,待自家所有水稻全部收割齐整后再碾打成稻谷。众多的谷垛围住谷场,在打谷的过程中,各户人家相互帮助,尤其是遇到雷阵雨天气,全村人帮助正在打谷的人家抢收稻谷。多年来,谷场成为村庄中村民自我建设的一个公共空间。谷场建设的过程便是村民巩固关系的过程,盖谷垛子、碾谷场、打谷等一系列共同劳动的农活使得村民们联系更加紧密。碰到阴雨天,谷场来不及碾平打谷的这段时间,村民们相互照看谷垛,形成一定意义上的谷场空间。
因此,谷场发生火灾非常罕见,在小明湾村民的记忆中还从未出现过。当天晚上9点多,部分村民已经准备睡觉,住在村头的罗姓村民发现谷场冒烟,便立即查看,并呼喊村民拎着水桶灭火,在救火的一个多小时过程中,来到谷场的村民越来越多,全村20余户村民每户都有人帮忙灭火。事后,村民们一致认为是故意纵火。放火者并未选择在半夜动手,而是在9点多村民快要睡觉时,可以有救火的时间不至于损失太重。由此说明,放火者并非穷凶极恶,可能与小明湾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可能跟小明湾村民有矛盾。因此,故意纵火的对象锁定在本村的一户罗姓人家和大明湾一户翁姓人家身上。当然这些分析都是基于猜测,没有任何证据,派出所也查不出原因,又不能下结论,只能不了了之。
在这起事件中,没有看到村民们的“匪气”或者“霸气”,没有誓要找出真凶的决心,对于派出所破不了案也似乎只能接受。受到损失的村民把这一切归因于自己倒霉,并未怨天尤人,而是继续生活,村庄又平静起来。在访谈时提到这件事,那户村民还说,“谷垛子被烧换来今后几年的太平也值了,人家或者真的是一时大意,要是真坐牢了,他肯定报仇啊,搞得成天提心吊胆,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被人烧了”。这就是朴实的村民的想法。他也没有对政府提出什么要求,农业税正常缴纳,尽管他本身家庭收入在村庄中算是中等偏下的水平。一切就这样风平浪静地过去了。这或许就是小明湾朴实的民风的体现。
在这个故事中,政府是缺位的,即使村民遭受到了较大的损失,政府也没有给予一定的补偿,村民也没有要求政府给予补偿。而类似的故事出现在不同空间的另外村庄,结果就不同,就有村民依据“受害者”的身份进行反复地抗争,拒交当年乃至数年的农业税并索要补偿。②申端锋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讲述了和平乡村民因麦茬着火引起了集体上访事件。参见申端锋:《治权与维权:和平乡农民上访与乡村治理1978-2008》,华中科技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其实,村庄内部是有着自身的规则的,遵守传统规则的村民们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破坏在村庄中的形象。这个互动过程,政府部门尤其是基层政府应该有所作为,对这种村庄规则给予支持,对已形成的村民文化给予培育,否则的话,村民会对基层政府大失所望,长时间之后,会在与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不遵守村庄的民俗,转而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么与政府的关系就变成纯粹的利益关系了,一旦发生冲突就难以协调和控制了。
三、抗争政治塑造地域文化
抗争政治的形成需要组织或者领袖进行有效地动员,但这个动员并不是自动生成的,必须要说服人们相信参与抗争是有意义的,地域文化便参与到抗争政治的意义塑造中,同时,抗争政治反过来又影响了地域文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文化因素开始占据集体行动理论研究的重要位置,过去被人们讳莫如深的意识形态也开始被重新重视。文化的作用在革命理论家那里,常常被替代为意识形态,革命理论家试图透过意识形态观察革命运动,或者透过革命观察意识形态。
不仅如此,周建新在《动荡的围龙屋》一书中提出了文化抗争的概念,认为文化可以贯穿抗争政治的全过程。所谓文化抗争,是指争取社会和文化生存,借助文化资源和文化力量来进行的抗争。他在书中描述了一个客家宗族的城市化遭遇以及村民面对传统文化资源被侵占所自发保护长达数十年的文化抗争事件,文化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再造,文化认同得到了新的建构。①周建新:《动荡的围龙屋——一个客家宗族的城市化遭遇与文化抗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在Z镇,一场抗争政治事件也能够影响人们的看法。在“水库用水风波”事件发生后,附近村庄都对小明湾另眼相看,觉得他们敢对超过两倍的大明湾进行挑战,并且还赢了,觉得小明湾人比较强悍。而小明湾人自己也意识到,还真可以挺起腰杆子做人了。有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在林地被砍前,附近的村民都来林地放牛。每逢暑假,放牛的基本都是初中及以下的青少年,这中间就发生了一起小孩打架事件,小明湾的3名小孩与赵湾的6名小孩发生了纠纷,最先开始是“一对一”单挑,小明湾赢了,于是赵湾一个小孩说了句“别惹小明湾的人”,然后6个人就跑了。当时周围放牛的小孩至少有20-30人,在这么多人面前认怂还真是不多见。这件事在小明湾被传为美谈,周围人对小明湾的认识也更加固化在强悍上。而小明湾自己也逐渐把强悍作为自身的特质,经常在各种公共场合发出声音,带领周围的村庄参与一些活动。可以说,正是这一起“水库用水风波”改变了小明湾人的性格,也改变了其自身的文化。
抗争政治不仅能够改变自身的行为,也改变其他人的行为。在Z镇,如果某个村庄发生了抗争政治,那么今后一段时间这个村庄就会受到格外的重视,而一些“钉子户”家庭更是重视的焦点。在奥运期间、世博期间,这些因抗争政治事件而被关注的家庭受到了重点盯防。李岗村同样由于抗争政治事件而出名,由于其村民的努力,其村庄通往主干道的公路就率先得到了修整,而其他村庄则是等到财物资源到位后才进行。Z镇其他的公共物品分配也大多遵循着这样的规律,获得公共物品的先后顺序往往与村庄的抗争文化有着密切关系。
重大抗争政治事件对村庄今后一段时间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时至今日,各村庄人都清楚地知道哪个村庄的村民具有什么特点,这些印象的形成正是基于曾经发生的抗争事件。比如Z镇曾有村庄的牛被偷,于是各村庄加强了警戒,但那些打工外出人较多的村庄依然有牛被偷,而某些强悍的村庄就不会发生这类事,治安情况也相当好。再比如大赵湾与小赵湾曾经发生了一场集体打架事件,明显地区分了两个原本相邻的村庄人的性格,大赵湾的村民个体比较擅长打架,甚至于同村的青年村民之间也经常发生打架纠纷,而小赵湾的村民则比较团结,村庄的路修得也比较好,交通较为方便。这便是抗争政治事件给村庄文化带来的影响,甚至塑造了新的地域文化。
四、抗争文化的扩散与蔓延
当前,抗争文化的负面影响已经大大扩散了,显然扩散的原因并非是抗争主体一方面的因素,其指向群体也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不可否认的是,其抗争文化扩散所遵循的标准不再是道德,而变成了利益。
Z镇大明湾某村民半夜突然身体不适,于是请方湾的一名医生上门诊治,医生也从未见过这种症状,紧急处理后送往县医院,可惜还未到县医院村民便去世了。这件事从道德上讲,谁都没有过错,然而医生却被要求赔偿2万元。理由是病未看好,需要承担过失责任。据村里的老人讲,村民半夜暴病的事在以前也发生过几起,有的救过来了,有的去世了;但从来没有说让医生赔偿的,最多是上门探望表示没能救治过来的愧疚。
诚然,对医生来讲,1948年世界医学协会《日内瓦宣言》承诺“我将要凭我的良心和尊严从事医业”,不能见死不救。但如果频繁地让医生承担能力之外的责任,这将对医生的执业准则形成挑战。长此以往,在农村地区,可能医生不愿意接纳疑难杂症了。那么,受到伤害的还是农民本身。无独有偶,方湾的一名村民病重,请同村医生来诊治,也是因为病情恶化,两户人家形成“世仇”,这名医生被迫弃医到外地打工,这件事双方还多次寻求村委会及镇政府的解决。在赵岗,一户人家小孩先天性哮喘,附近医生没有医治好,便到北京的一家大医院进行诊治,小孩哮喘稍有好转,但却没有像医院宣传的那样能够彻底根治。于是,在职业“医闹”的唆使下,这户人家要求医院按照医学事故进行赔偿,最终经过调解,医院愿意退回一半的手续费。根据对当事者的访谈,他当时听信了“医闹”的蛊惑,认为确实是医疗事故,但又不愿意对医生进行这种闹剧的“敲诈”,于是寻求医疗机构进行鉴定,结果是手术成功,并不是医疗事故。对“医闹”而言,其判断依据纯粹是利益,没有赚到钱,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根本没有道德可言。在Z镇卫生院,也多次出现村民与医院发生纠纷的事例。这种现象在当前社会中也比比皆是,显然是不正常的,需要引起人们的反思。
当前的“医患关系”以及存在的“职业医闹”,便是抗争文化负面影响扩散的突出表现。上述案例中,医院本身或许承担着宣传上的“夸大”责任,再加上某些医生可能存在的不当行为,可能让患者产生误解,再加上“职业医闹”的挑唆,容易引起纠纷和抗争事件。但如果每位医生都确实遵守《日内瓦宣言》,或许能够有效地缓解当前日益严重的“医患关系”。
这种在利益面前容易产生抗争的文化逐渐扩散到各个领域,不仅在医疗方面,在衣食住行方面也存在着。以前,在Z镇,村民种菜往往是自给自足,多余的则送给其他村民,而现在,村民多余的菜拿到集市上去卖,而缺菜的村民要到集市上去买。这种现象也使得“偷菜”成为现实,种菜的村民甚至半夜都要起床去菜园子看看,以防被人偷走。在建房子方面,这种抗争文化的扩散就更加严重了,建房之前是朋友,建房之后变成陌生人。村民往往根据建房的质量决定是否支付尾款,而在建房过程中确实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纰漏,于是成为不支付尾款的重要理由。这种对自身利益的抗争,甚至无底线的抗争方式在村庄中正在扩散,形成一股抗争文化,这种文化往往带来一些大的负面影响,一些暴力抗争政治事件可能是由这种不合理的抗争失控引起的。
五、小结:抗争政治的“催化剂”
在中国,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抗争文化,因此也造成不同区域抗争政治的不同特点。当酝酿抗争政治的因素形成之后,抗争文化决定着抗争政治是否发生以及什么时候发生。于是,不论在常规的日常活动中还是在危机时的暴力行为中,这种抗争文化即共同拥有的道德理念结构,对于何谓公正的共同观念,融入到农民行为结构之中。正是抗争文化这份道德遗产,使得农民能够不同于其他地域的人们而产生强烈的侵权认知,使得农民在抗争中选择了这些目标而不是别的目标,选择了这些策略而不是别的策略。也正是这种抗争文化,使得出于道德义愤的集体行为能够在一夜之间发生而无须事先协调。抗争文化就是“催化剂”,加快或者减慢抗争政治产生的速度。正催化能够加速抗争政治的形成,即抗争文化不断刺激抗争者采取各种抗争策略实现冲突升级,产生抗争政治甚至引发暴力冲突。负催化能够减慢甚至化解抗争政治的形成,即抗争文化不断约束抗争者全盘考虑各种因素,找出抗争政治的替代品诸如体制内的解决方式等,使得可能引发抗争政治的因素发生变化,最终延缓甚至化解了抗争政治的发生,或者在发生抗争政治时采取温和而非暴力的方式。
对于“催化剂”而言,在发生化学反应时,其自身的性质不发生改变。对于抗争文化来说,其植根于当地村民的生活方式和特征,在短时间内也不容易发生变化。改革开放初期,许多台湾人来大陆后对大陆人的印象,都会说到“爱围观”,只要有一点小事,都会有一群人聚集看热闹。鲁迅的笔下曾描写过“人血馒头”和“围观杀人”时中国人的劣根性。如今这种“爱围观”文化中的特性依然存在,如网络上的“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当发生突发事件后,第一时间就会有数量众多的群众围观,如果当事者加以煽动,就极容易转化为对抗性的行动,甚至演变成暴力冲突,这种催化作用就十分明显,也是抗争文化的负能量所在。而如果在现场对围观群众进行引导,让真实信息迅速传播,围观群众就会散去,就会瓦解抗争者所希望造成的集体行为,也就打消了其继续为了自身利益抗争的想法。
抗争文化的第一层作用是过滤掉部分村民完全不合理的抗争政治的想法,他们可能对自身侵权的认知出现了偏差,而错误地做出抗争政治的决定,那么抗争文化的正面影响就完全能够纠正这一错误想法。第二层作用是当村民完全因为集体遭受了侵权而决定进行抗争行动时,抗争文化能够将抗争政治的决定转化为行动的时间缩短或延长。如果是缩短转化时间,就加速了抗争政治的形成,迅速爆发抗争政治事件,其处理将依赖于与官方的互动,村民的诉求被官方接受或者部分接受或者完全置之不理,这一迅速的过程使得官方可能来不及应对,极有可能引起暴力冲突。众多社会泄愤事件就类似于这类突发群体事件,其社会影响往往是负面的。如果是延长了抗争政治的形成,抗争者便会缜密地准备各类抗争策略,其自身的行动是理性的,也给了与官方互动的时间,这类事件容易在双方之间进行协调和妥协,容易达到抗争者的目的。这便是抗争文化所起到的正面作用。

图1 抗争文化对抗争政治的催化作用图
总之,抗争文化这种“催化剂”是否起作用,起正面还是负面作用,取决于这是何种抗争文化,取决于当地村民的生活方式和特点。在特定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和经济结构的村庄,抗争文化在一定时间内往往是“不变”的。我们只要抓住抗争文化的特点,就能够判断出哪些地方容易发生抗争政治,而哪些地方则不易发生。做出这些判断,就有利于对村民的抗争想法形成准确的认识,进而寻求合适的方式进行治理,尽量满足村民的合理诉求,使得村民不经历抗争政治便达到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
(责任编辑:肖舟)
Protest Culture:A Catalyst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Rural Areas
HU Bing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China)
Based on the regional culture of folk customs,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folkway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rural protest environment;at the same time the resistance events in return affect the protest culture.From this interactive process,the protest culture plays a role as catalyst to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rural areas.To study the protest culture is help to clarify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contentious politics. Finally,it points out the trends of the spread of the protest culture,which directly affects the frequent contentious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rural areas.
protest culture;areal culture;contentious politics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底层抗争与基层治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胡兵主持,编号为14YJC840012)的阶段性成果、同时也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从抗争文化到治理逻辑:我国基层社会秩序的变革”(胡兵主持,编号为2015BSH005)的阶段性成果和华东理工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胡兵(1983-),男,河南信阳人,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青年研究。
C91-03
A
1008-7672(2016)04-006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