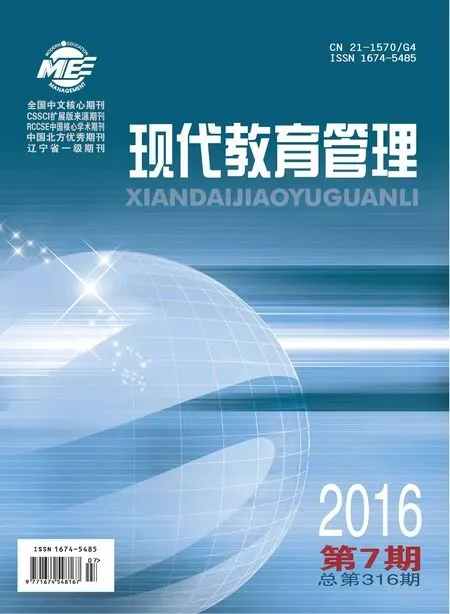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检视与重构①
罗儒国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检视与重构①
罗儒国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是观测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特征的标准或尺度。建立科学、完备的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不仅是实施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工作的重要前提,还是诊断与提升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迫切需要。然而,目前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评价指标概念界定模糊,指标类型设置不尽合理,指标数目确立较为随意,评价指标体系缺乏针对性、前瞻性等方面。为此,我们需要厘清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内涵与外延、注重研究基础与方法创新,注重“本土化”指标体系研制,加强评价指标顶层设计、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重视评价指标更新与发展,从而为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提供有效工具。
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检视;重构
一、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的检视
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是考量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特征的重要尺度,通过系统梳理与深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目前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依然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评价指标概念界定模糊,指标可操作性不强
在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研制过程中,评价指标概念界定要清晰明了,表达方式尽可能简单易懂,尤其是定性指标。定性指标选择与设计更要严格定义指标内涵,同时给出具体的评判标准,以便实现经验判断的分数转换,从而确保定性指标的可操作性。然而,当前部分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概念缺少必要的界定与说明,有的指标界定比较模糊,大多指标没有给出具体的评价标准;有的主体指标也只是简要说明应从哪些方面进行评价,但对于如何评判、标准是什么等问题没有给出详尽说明或具体标准,从而导致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缺乏可操作性、实用性也不强。另外,虽然有些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对主体指标、次级指标做了简要说明,但是不同指标体系的某些核心指标(如“工作性质”或“教学特性”、“薪酬福利”、“工作条件”等)的解释和说明却不尽一致。那么,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中的“工作性质”究竟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与其他人员的工作性质有何区别?所谓工作性质是人们所从事工作具有的特性。在哈克曼和奥尔德姆看来,工作特性包括技能多样性、任务同一性、任务重要性、自主性、反馈性等五个方面。[1]事实上,教师“工作性质”除了具备一般工作典型特性之外,还有其特殊性,需要进一步澄清、明晰。
可以说,正确认识与把握评价指标的内涵与外延是构建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的重要内容与关键环节。我们倘若对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缺少科学阐释与必要说明,就难以获取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相关信息或有效数据。有论者强调指出:“有效的指标体系需要一个明确的概念基础。在开始创建一个指标的时候,首先必须花时间思考清楚到底想要测量什么,否则很可能最终虽然得到一个指标,但它实际测量的却并非你所想要的内容。”[2]
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类型多种多样,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分为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微观指标和宏观指标等不同类型。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类型相对单一主要表现为某些指标类型的缺失以及各类指标比例设置不尽合理。
一是主观指标多,客观指标少。前者反映的是教师对工作生活整体及其各个领域的满意程度的观测指标,后者是反映教师的客观工作生活条件、状态的观测指标。从已有的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来看,大多侧重于主观指标的研制。比如,有论者将教师工作生活质量定义为教师在学校组织中,透过对工作环境的安全与健康情形、教学工作自主性、工作上的社会互动关系、进修研究与未来发展机会、薪资报酬与福利制度,以及领导管理与行政制度运作的一种经验与感受,以满足教师个人需求的程度。在此基础上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教学自主、行政运作、薪资福利、工作环境、社会关系、进修研究等六个主观指标。[3]客观指标主要是反映社会、学校提供给教师工作生活条件的充裕程度的观测指标,因而有别于那些反映教师工作生活主观经验与感受的主观指标,因而客观指标也是衡量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但此类指标并不多见。
二是微观指标多,宏观指标少。微观指标是反映特定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状况或特征的观测指标,主要是对个体层面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测评。微观指标往往借助于“主观幸福感”或“生活满意度”对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状况或特征进行衡量与评估。然而,不论是生活满意度,还是主观幸福感都是基于教师个体的认识与主观感受。从已有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来看,反映全国教育事业发展水平、全国教师队伍整体发展水平以及教师工作生活条件的宏观指标尚不多见。即便有相关指标,也仅仅是作为教育事业发展水平评估的次级指标,而未专门用于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估之中。究其原因,可能与数据、资料获得较为不易有关。在笔者看来,宏观指标主要涉及我国教师平均工资水平、教师人均办公经费与培训经费、全国教师人均办公用房面积、全国教师养老与医疗保险覆盖率等。
本文认为,如果要切实提升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的有效性与科学性,不断扬弃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存在的局限与不足,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就需要从整体的、系统的角度出发,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倘若将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理解为社会和学校为教师提供工作生活条件的充裕程度,以及教师工作生活需要满足程度的话,那么一套理想的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不仅包括反映教师工作生活体验与主观性感受的主观指标,还包括反映教师工作生活条件状况和水平的客观指标;既包括反映社会供给程度的宏观指标,也包括反映学校教师工作生活需求满足程度的微观指标。
(三)指标数目确立较随意,缺乏科学、充足依据
作为一个复杂的、多维度的、抽象化的概念和范畴,教师工作生活质量往往是由不同要素或维度构成的系统结构。然而,目前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对于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结构维度及衡量指标与数量问题并未达成有效共识。从现有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成情况来看,各个指标体系构成存在一定的差异,且指标数量不尽一致,少则三、四个,多则十几、甚至二十多个。譬如,李佩瑾构建的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包括个人期望、工作环境、工作任务、组织结构四个指标。[4]卡西欧则将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衡量指标限定在薪资、工作自豪感、工作动机与热情、工作安全、员工参与、交流、职业发展、解决问题能力等八个维度。[5]贾海薇构建的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则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即生存的需要、社会需要、自我的需要),每层次又包括不同指标(如工资收入水平、福利待遇、工作安全感、自我实现与个人成就等),共计20个次级指标。[6]另外,有的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的构建往往缺少系统、科学的理论基础或是缺乏充足的现实依据,因而其科学性、实用性水平并不高。有的评价指标往往是借助于文献分析法、频数分析法等方法建立起来的。譬如,哈特基于生活满意度量表整理出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测评指标[7],Seashore,K·L则是在借鉴企业员工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的基础上,通过综合分析建立的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8]。
事实上,评价指标的完备性和简约性是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面临的一对矛盾。一方面,如果评价指标体系过分追求全面性、完备性,评价指标数量繁多,则会影响到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实践的可行性以及教师工作生活评价指标的可操作性、实用性;另一方面,如果指标数量过少,也会因为缺少有效反映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状况或特征的足够信息,从而严重影响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如此一来,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应包括哪些指标?为什么是这些指标而不是哪些指标、评价指标选择的依据是什么?哪些指标可以作为核心指标?如何在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的简约性与完备性之间保持动态平衡?评价指标数量究竟控制在怎样的范围之内最佳?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学界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和说明,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四)指标体系针对性不强,涵盖范围过于宽泛
一般而言,由于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是教师在一定物质条件基础上对工作生活整体及其工作特性、工作报酬、工作生活条件与环境、教师培训与晋升发展、学校组织管理等各工作生活领域的主观感受,因而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的建立必然要充分反映教师工作生活(或教学生活)涵盖的主要领域与范围。然而,目前部分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内容比较庞杂,指标涵盖范围过于宽泛。比如,在有的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中,不只是涵盖了教师的专业生活质量,还涉及教师的业余生活质量。[9]依此看来,教师工作生活不仅包括专业生活,还包含业余生活,在此基础上构建的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必然包括业余生活质量与专业生活质量两个不同领域。此外,有论者运用模糊集合理论的综合评价方法初步建立了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20项次级指标,如教师工资收入水平、衣食费用比例、住房条件、福利待遇、工作休闲、工作安全感、工作对婚姻(爱情)的影响、工作对友谊的影响等。[10]此指标体系中提及的“衣食费用比例”、“住房条件”指标究竟属于日常生活质量指标,还是工作生活质量指标?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与教师日常生活质量评价指标是否存在着差别?如果有,又该如何有效区分呢?在我们看来,教师工作(或专业)生活质量不同于教师业余生活质量、精神生活质量、日常生活质量,我们不能混淆其中的差异。不论是从内容构成来看,还是从评价指标来讲,它们之间都是有所不同的、存在着较大差异。
大寻访活动已经过半,走深圳,过东莞,经广州,访厦门,到温州,看杭州,转上海。今天分赴苏州、无锡,再聚南京。问及难忘的风光景色,当然是人文,是各家企业的掌门,也就是一种“企业家精神”。
作为社会成员的教师,不仅存在着不同的类型,还有着不同的个体需求,他们的工作生活领域也往往复杂多样。因此,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就需要把握教师工作生活特点及其工作生活质量现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设计“领域专表”,尽量避免出现评价指标交叠现象,不断提高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的针对性、专门性。
(五)指标体系分类不够周全,缺乏前瞻性、动态性
一般而言,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是由主体指标、次级指标组成的。主体指标主要作为整体、综合评价之用,而次级指标通常作为主体指标的支撑。在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研制中,主体指标层次要分明,次级指标尽可能完整地表达主体指标或上级指标的含义,且各个指标间相互独立,避免出现过多的信息包含或指标内涵重叠。
从指标体系分类情况来看,当前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依然存在着评价指标分类不够科学、合理等方面问题,从而难以客观、真实而准确地反映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状况和水平。譬如,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通常被划分为个人、工作、组织三个不同层面,但不同指标体系同一层面包含的指标内容却不尽一致。有论者认为,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的“个人层面”包括“工作报酬,工作和个人基本权力的保障,工作、家庭与休闲的平衡”;工作层面涵盖“工作特性、工作量及工作压力,工作投入度、成就感及尊荣感,工作环境,工作条件,职业生涯发展”等。[11]而有的论者则持有不同观点,在其构建的评价指标中,“个人层面”包含“薪资福利(奖励升迁制度、福利、退休或休闲娱乐),成长发展(进修、生涯规划),社会支持(家人支持态度、亲师关系、社区关系)”;“工作层面”包括“工作性质(工作上专业要求、工作负荷量、自主性),工作资源(人力、经费、设备)”。[12]另外,即便是在同一评价指标体系,不同层级的评价指标之间也存在着内涵交叠现象。比如,在吴素月构建的指标体系中,“社会支持”指标中的“社区关系”与“组织层面”中的“社区互动”指标究竟是何关系,它们有无区别、如何区分?“薪资福利”指标中的“奖励升迁制度”究竟是属于“个人层面”,还是归属于“组织层面”?诸如此类的细节问题值得进一步斟酌与考量。
评价指标缺乏前瞻性、动态性是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中存在的另一突出问题。一是重视工作生活质量静态评价,忽视工作生活质量的动态评价。在现有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中,评价指标体系设计重点关心的是某一时间节点上教师对教学生活整体以及工作报酬、工作条件与环境、教师培训与晋升发展、学校组织管理等工作生活或教学生活各领域的主观感受。如此一来,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评价结果通常只能反映出现阶段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状况和水平,而难以真实反映教师工作生活质量发展变化与提升程度。二是重视现实教学生活质量评价,忽视虚拟教学生活质量评价。伴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广泛应用以及教育信息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虚拟教学生活日渐成为教师典型的、例常化的教学生活方式。作为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虚拟教学生活质量理应成为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设计考量的内容,但现有的评价指标体系并未对此做出必要的修订、更新和完善,评价指标设计缺乏一定的前瞻性、动态生成性。
此外,教师对工作生活总体以及各领域的满意度往往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发生相应变化。换句话说,在职业生涯发展各个阶段,由于教师工作生活经验日益丰富、工作能力大幅提升以及工作生活需求日趋多元,教师对工作生活的满意度也会有所不同。社会经济与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也使得社会和学校的供给程度与水平发生显著变化。如此一来,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的选择与设计既要全面考虑教师工作生活领域的拓展与变化,也要充分考虑教师工作生活条件与环境的变化发展;不仅要重视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静态分析,还要注重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动态评估。
二、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的重构
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选择与构建之所以会出现上述诸多问题和偏差,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对教师工作生活质量内涵与外延定位不明、缺乏综合式评价思路等。为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厘清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内涵与外延、注重研究基础与方法创新,注重指标体系的针对性、设计“本土化”指标体系,加强评价指标的顶层设计、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重视评价指标更新与发展、增强评价指标的适切性,从而为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提供有效工具。
(一)澄清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概念内涵,注重研究基础与方法创新
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概念的界定,除了要运用科学下定义方法之外,还要充分考虑教师工作生活特点与教师工作生活需求,以及教师工作生活现实境遇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提出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可操作性定义。本文认为,教师工作生活质量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层面来理解。从广义上来讲,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是社会和学校为教师提供工作生活条件的充裕程度,以及教师工作生活(或教学生活)需要满足程度。从狭义上来看,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是教师在一定物质条件基础上对工作生活(或教学生活)总体以及工作特性、工作报酬、工作条件与环境、教师培训与晋升发展、学校组织管理等各个工作生活领域的主观感受。[13]
构建科学、有效的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既要有基础理论支撑与指导,也需要借助科学的指标构建方法与技术。从以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来看,关于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构建理论的相关探讨并不多见。社会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学者对生活质量、工作生活质量理论基础展开了较为深入研究,具有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譬如,邢占军教授在《公共政策导向的生活质量评价研究》一书中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社会福利理论、需要层次理论、系统论等理论作为生活质量评价指标构建的理论基础。[14]杨兴坤则探讨了工作生活质量指标设计的五个基础理论,包括古典管理理论、人际关系理论、行为科学理论、人性假设理论、社会技术系统理论。[15]虽然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是生活质量或工作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也有其特殊性,究竟有哪些相关理论可以作为理论基础仍有待深入研究。此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方法也是多元的,概括起来大致有两类:一类是基于主观评判的方法,如文献分析法、头脑风暴法、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等;一类则是基于统计分析的方法,如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聚类分析法等。然而,每种方法有何优缺点、适用条件和范围是什么,究竟该选择哪种方法比较合适,指标体系构建的程序和步骤有哪些,如何确立指标权重等,这些问题都是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不容回避、且必须解答的议题。
(二)注重指标体系的针对性,构建“本土化”指标
在以往教师生活质量或工作生活质量评估中,不少学者采用的是“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量表”(WHOQOL-100)或“工作满意度量表”(TJSS)分别对不同类型学校、不同性别教师进行的调查与分析,但此类量表只涉及到教师的生理健康、心理、独立性、社会关系、环境和精神宗教等维度,因而不能较好地反映教师工作生活需要的“满足度”和社会、学校供给的“充裕度”,从而难以全面反映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状况和水平。
教师工作生活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工作生活有着共同点,但也有其特殊性,体现在教师工作生活目的、工作生活过程、工作生活环境等不同层面。正是由于教师工作生活目的、工作生活过程等方面特殊性,使得他们有着不同于其他职业生活的现实需求。教师生活在特定的学校场域中,他们对工作生活领域的主观感受及其生活体验也会有所不同。因此,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构建不能简单地套用和移植其他学科、领域有关工作生活质量评估指标与测评工具,而是要对诸如此类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系统分析,全面、深入地了解它们产生的背景及其适用条件、范围,在与相关学科进行平等对话、道德沟通的基础上,通过教育学加工与改造,结合教师工作生活特殊性以及教师工作生活现实需求,科学运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方法与技术,建立一套适合教师职业特点的专门化的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三)重视评价指标的顶层设计,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从以往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来看,存在着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单独使用、或混合使用同时并存的局面。长此以往,不仅不利于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估工作的开展,也不利于研究者之间的对话与合作,更不利于不同国家、地域之间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比较分析。如前所述,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复杂范畴,不仅包括薪酬福利水平、工作条件与环境等客观层面,还涉及到教师对工作生活整体及各工作生活领域的体验、感受等主观层面。因此,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就要从全局、整体角度出发,充分彰显“以人为本”的思想,以满足教师物质、精神、健康、心理和环境等工作生活需求为旨归,从客观与主观、宏观与微观、定性与定量、输入与输出等层面入手进行顶层设计与统筹规划。既要对教师工作生活总体进行评价,也要对教师工作生活各个领域做出评估。在周长城教授看来,在开展生活质量评价时,那些仅仅对客观物质条件的考量,或是单纯对主观满意度的评价,都会由于认识论上的偏差进而导致评价结果遗漏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16]如此一来,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需要加强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宏观指标与微观指标、输入指标与输出指标的整合,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便准确、有效地反映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状况与水平,以及教师工作生活各个层面的满意程度。
(四)加强评价指标更新与发展,增强评价指标的适切性
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构建要充分考虑到评价指标随外部环境、时空变化而变化的可能性。随着网络社会教师教学生活方式的转型以及教师工作生活条件与环境的急剧变化,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需要及时更新与发展,通过不断调整与优化,以便增强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评价指标的适切性、时效性。对此,我们不仅要深入地了解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状况,还应充分考虑信息网络社会对教师工作生活的影响,以及教师工作生活领域的不断拓展与延伸,相应地增设教师虚拟教学生活质量系列指标。虚拟教学生活质量是社会和学校为教师提供虚拟教学生活条件的充裕程度,以及教师对虚拟教学平台与环境、虚拟办公平台或虚拟教学管理平台、数字化教育教学资源平台、网络研修与学习平台等各个维度的满意程度。评价指标主要有校园网覆盖范围、带宽、安全以及泛在信息平台建设水平,数字化教室等信息设备的配置状况,数字教育教学资源库建设水平,教学管理平台、学术管理平台等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水平等。此外,如若考察某一期间教师工资福利是否有实质性增长,是否快于城镇物价增长速度,则可通过“教师平均工资指数”来考察教师工资水平变化。
[1][美]G.史密斯,迈克尔.A.希特.管理学中的伟大思想:经典理论的开发历程[M].徐飞,路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25-138.
[2][16]周长城.生活质量的指标构建及其现状评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480、20.
[3]蔡明达.国民小学教师知觉工作生活品质与组织承诺之关系研究[D].台南:国立台南大学,2012:5.
[4]李佩瑾.中小学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指标之建构[D].台北:国立台湾科技大学,2003:5.
[5]Casio,W.F.Managing Human Resources:Productivity,Quality of Work life,Profits[M].New York:McGraw-Hill,1992:14-47.
[6][10]贾海薇.高校教师工作生活质量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3):87-93.
[7]Hart,P.M.Teacher quality of work life:Integrating work experiences,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d morale[J].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1994,67(2):109-132.
[8]Seashore,K.L.Social and Community Values and the Quality of Teacher Life[R].Minnesota:University of Minnesota,1988:5-9.
[9]孙钰华.关于农村教师工作生活质量(QWL)的研究[J].教育科学,2007,23(6):58-63.
[11]毛作祥.YB县教师工作生活质量调查:西部农村若干被调查学校的管理问题与改进对策[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8:4.
[12]吴素月.工作生活品质与工作倦怠相关性之研究——以台东县特殊教育教师为例[D].高雄:义守大学,2005:5.
[13]罗儒国.教师工作生活质量概念释义与辨析[J].教师教育学报,2015,(5):29-37.
[14]邢占军.公共政策导向的生活质量评价[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11.
[15]杨兴坤.公务员工作生活质量研究[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16-37.
(责任编辑:李作章;责任校对:赵晓梅)
The Review and Reconstruction of Assessment Indicator on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Work Life
LUO Ruguo
(Wuhan University,Wuhan Hubei430072)
The assessment system on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work life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observation standards or scales of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work life.Building and improving a scientific assessment indicator system is not only a premise and foundation of carrying out the assessment of quality of work life,but also an inevitable choice of inspecting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work life.However,the current assessment system of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work life exists some problems which cannot ignored,such as unclear definition of assessment indicator,irrational setting of indicator types,arbitrary establishment of indicator number,assessment system lack of pertinence,foresight and dynamics.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connotation and extension of basic concepts,strengthen theoretical base and method researches,attach importance to update and improvement of assessment indicators,stress pertinence of indicator systems,and reinforce integration of assessment indicators,so as to provide an effective tool for the assessment of the quality of teachers' work life.
teacher;quality of work life;assessment indicator;inspection;reconstruction
G451.4
A
1674-5485(2016)07-0082-06
①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小学教师教学生活质量评价研究”(10YJC880085)。
罗儒国(1978-),男,湖南常德人,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教师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