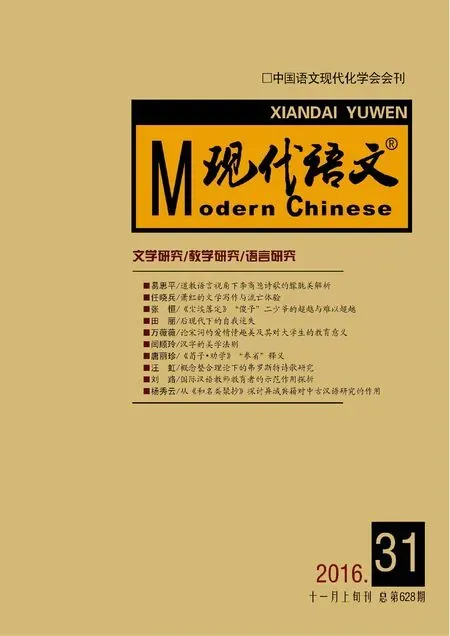《黄雀记》之后:苏童的写作困境
○董 蕾
《黄雀记》之后:苏童的写作困境
○董 蕾
苏童的写作在当代文坛自成一派,以独特的写作气质和文学意象隐喻着快速转变的文化现场。新作《黄雀记》的题目颇具古典意境和哲理感,但整体叙事在容量上和内涵上显得过于单薄,缺少长篇小说应有的厚重感和整体感,苏童的长篇创作需要等待再次突破。
苏童 意象 颓废 写作困境
苏童的写作在当代文坛中早已自成一派,他阴柔温婉的写作气质,无论将其置在先锋文学创作下,还是乡土/新历史/新写实等不同文学语境中,苏童总能置身其中,用独特的文学意象隐喻着快速转变的文化现场。从“枫杨树的故乡”到“香椿树街”,在“乡土/历史”与“城市/写实”的多重维度中,苏童建构出自己的有往日有今朝的南方世界:对历史想象性的叙述,他让人物在宿命和欲望中经历生命往复,是为别具一格的先锋派文法;对现实事态的描写,他在暴烈之中掺杂温情,将城市历史与个人记忆细细勾勒,形象地隐喻着国民经济转型期的生存状态。2015年,苏童凭借《黄雀记》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作为国内文学最高荣誉奖,获奖无疑是对苏童写作的肯定。光环之下,我们将如何评价《黄雀记》之于当代写作和对于作家苏童本人的意义,或许正如“黄雀”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特殊隐喻彰显的那样,黄雀之后呢,等待当事人的是有意义的突破还是新的困境?
一、长篇写作的困境
《黄雀记》的故事并没有我们预想中复杂,小说用将近27万字讲述了一个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一件青少年强奸案。少年、暴力、80年代,是苏童“香椿树街”系列短篇小说常设的情景元素,这也很符合读者熟悉的苏童笔法,仿佛那个在古典和先锋之间都能找到平衡点的苏童又回来了。故事开始于对祖父的叙述:“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祖父都要去拍照”[1]。祖父在七十岁之后每年都要为自己照“遗照”,这种怪异行为让他的儿媳不能容忍,终于在最后一次拍照时丢了“魂”而疯癫。少年宝润替祖父拿照片时错拿一张有着愤怒脸庞的少女相片,疯癫的祖父要求寻找在文革时期藏有祖先遗骨的手电筒,又在整个街道牵扯出挖掘祖先遗产的掘金运动。人们将祖父送到了井亭精神病院,并让其孙子保润照看。宝润发明了制服祖父的“捆人”技术,成为医院的名人,并在医院中遇见了花匠收养的弃婴,曾经错拿的照片上愤怒的少女“仙女”。故事的开端先描述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的“巧合”和并不合理的情节设置。上了年纪的祖父每年照遗照的行为被儿子儿媳过分嫌弃,祖父“必须”疯癫而走入精神病院,宝润可以不顾学业前程专心来到病院用真实的精神病院绝对不能使用的“捆绑术”照顾祖父,而在整个事件中,宝润的父母这两个角色几乎缺席,并没有起到影响叙事发展的作用。宝润在精神病院终于和相片上的少女相遇,让整个故事的开端成为宿命般的巧合。苏童的小说一直在情节上取胜,内心刻画和故事强的特点也不难解释为什么他的小说经常受到影视导演的青睐。接下来的情节其实是非常好推测的,一切似乎都在意料之中,主人公宝润对仙女产生了好感并提出和仙女约会,仙女却似乎爱慕另外一个“街道少年”柳生。后来宝润被仙女骗钱后将仙女捆在荒废的水塔上扬长而去,却被仙女诬告强暴犯入狱十年。宝润一家家破人亡,柳生深藏愧疚,仙女改名重回医院生下红脸婴儿。
表面上看,整个《黄雀记》的叙述是苏童先前“香椿树街”系列的一个延续,而这个太像故事的故事,一切都在宿命的轮回和读者想象的范围空间内。这种古典的“虚构”和“想象”,符合读者的预期,但是却离文学真实有点远了。苏童将整个事件分别通过宝润、白蓁(仙女)、柳生三个当事人不同的视角,分三大段,每部再分割成小段叙事,共同组合起来试图多角度还原叙事的真相和时代的变迁。这种结构其实我们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苏童在写作时的叙事困境:首先,被分割成若干小段的叙事方法其实又让苏童回到了他熟悉的短篇小说的方式上,并不是说一个长篇小说的样式必须怎么写,但苏童的这种小段切割法的确像把一整块木料切割成积木,静待读者去组装剪辑,因之缺少了长篇小说应有的整体感。另外,一个太巧合的故事虽然可以表现出人物在命运和时代中的成长和无奈,但这种过于“传奇”古典的叙事方式会让作品失去一些表达现代生活的能力。英国小说家威廉·特鲁弗曾说道,生活,绝大多数时候是无意义的。长篇小说模仿生活。“传奇”本身的不真实感,过多的“戏剧性”有时可能会让书写变得更加“无意义”。从《蛇为什么会飞》《碧奴》再到《河岸》和《黄雀记》,苏童以每三四年一部速度编织着自己的长篇世界,这也许出自于一个作家的理想和野心,但这些作品并不如他的短篇那样迷人。其实苏童本人也表达过自己的写作状态,在2010年召开的《苏童作品学术研讨会》上,他说道:“我对自己的短篇小说蛮自恋,我很享受。但是写短篇和长篇是两个人吗?我自己也不清楚。……越写得轻松,一气呵成的短篇小说,肯定是我最为满意的作品。这种状态不可能长久贯穿于长篇小说的创作过程,所以写好的长篇小说一直是我的野心和梦想,也是煎熬我的非常大的痛苦。”除了写作技巧上的问题,还有什么是煎熬的苏童写作的困境,也许还在于当代写作究竟应该怎样去“描写”生活。
二、“意象”之于苏童写作的意义
作家李陀很早就有感于我国当代小说出现的一种重视意象营造的现实写作,他在《意象的激流》中也谈到:“这是一些什么样的美学特征呢?那就是意象的营造,就是使小说的艺术形象从不同角度上具有意象的性质,就是从意象的营造入手试图在小说创作中建设一种充满现代意识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在写作中注重意象的营造一直是中国古典诗人熟悉的创作传统,也是中国古典美学重要的诗学范畴。在古典小说中,意象往往是触发深层隐喻的锦上之花,如《红楼梦》中贯通始终的“通灵宝玉”,现代作家笔下成熟的写作意象也非常丰富,张爱玲的“月亮”、沈从文的“渡船”、鲁迅的“人血馒头”、”戴望舒的“丁香”、闻一多的“死水”……这些意象蕴藏着丰富的文学密码,赋予作品深远的象征意义。
苏童也可谓是意象达人,《妻妾成群》《罂粟之家》《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红粉》《米》《城北地带》等小说中,苏童精心布置着各种意象,从地点到具体物象,把自己的审美理想通过这些意象成功地传达出来,塑造了“枫杨树的故乡”—“香椿树街”—“城北地带”等意象群。到了《黄雀记》中,仍然有着很多自带“阐释意义”的意象。所谓的自带阐释感,笔者指的是那种已经多次出现在各类文学作品中,被多次阐释出丰富意义的“意象”。比如祖父照遗照的疯癫行为,“疯癫”与“精神病院”在福柯的《文明与疯癫》之后,一直都在被过度阐释,照相术在中国最初流传时,就被当做是“摄魂术”而斥责为妖术。柳生的名字自带着隐隐的伤感,保润的“捆绑”行为、仙女的“失踪”和复现、“不死”的祖父以及祖父离去后的家族老屋和床下的蛇、仙女被困的“水塔”、直到最后改名为白蓁的仙女生下的红脸怒婴……再加上作品的题目“黄雀”,这些意象除了构造叙事气氛和承担隐喻功能之外,这些可供阐释的意象在其他文学作品中已有多种阐释,而在这部作品里也没有更为特殊的内涵。但它们却让作品生发出一种刻意的加工感,没有了苏童早期作品意象的深厚质感。
三、“南方”的想象与世俗的诱惑
“南方是一种腐败而充满魅力的存在。”[3]:苏童在很多年前就曾为自己的“南方”给予过一次定义。生长于苏州,长期生活在南京的他,天生就和这两座历史悠久的南方城市结缘,苏童给予他的城市和历史的想象会让人联想到诗人波德莱尔笔下的“恶之花”,而他笔下的人物也总是在城市的现代文明中颓废堕落,生发出一朵朵诡异迷离的恶之花。苏童的传奇往往是从“逃亡”开始的,早期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陈宝年开始从乡村转向城市,而到《米》中,逃荒者五龙浪荡一生众叛亲离,最终恶疾缠身,却又希望再次还乡。到《黄雀记》里,仙女在少女时期被保润的朋友柳生强暴后,拿到柳生的“封口费”也开始自己的“逃亡”之旅。仙女在第三章中以企业秘书“白小姐”的身份重新出现,改名白蓁。和苏童先前塑造的逃亡人物不同,此时仙女的逃亡只是因为“社会逻辑”的逼迫。因为在中国很多男性的逻辑中,一个被强暴的女子已经是不洁的,何况她并没有坚持真相,反而拿了施暴者的封口费而诬陷他人。按照这种逻辑,白小姐在下文中的堕落颓废似乎合乎情理,即便成为一名风尘女子都顺理成章。果然第三章的白小姐几乎堕落为“小姐”,她陪有妇之夫庞姓台商去巴黎游玩,不小心怀孕后企图报复台商,用生下孩子的方式向台商索取巨额赔偿。“她很懊丧。要么是富翁,要么是帅哥,要么服他,要么爱他,这是她选择男友的标准,为某个男人怀孕,则需要这些标准的总和。庞先生在标准之外。在她的眼里,庞先生只是一个普通的台商,矮,微胖……”[4]白小姐被塑造成一个经常在大众言情剧中出现的狗血形象。白小姐的逃亡与堕落在作者的逻辑想象中,只是一个商品经济时代堕落女性的符号而已,和先前苏童的“南方”无关,也无关任何的隐喻,她的逃亡也不具备更深刻的意义。
也许这次苏童在《黄雀记》中的写作是不太成功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黄雀记》的水塔上,少年保润将仙女捆绑以为惩罚,但没想到最终对仙女实施强暴的却是他的朋友柳生。也许柳生也不是那只黄雀,写作本来就不是一件作家完成后就终止的事件。一部作品的完成,后面可能会有无数只黄雀般的阐释者在静静等待。
注释:
[1][4]苏童:《黄雀记》,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3,第214页。
[2]李陀:《意象的激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编:《小说文体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页。
[3]苏童:《南方的堕落》,台北:远流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
(董蕾 河南郑州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4514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