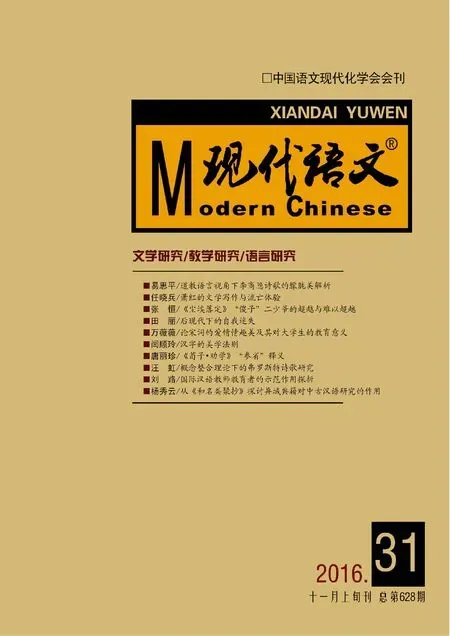试论明代白话小说对元杂剧的改写——以《断鲁郎势焰之害》改写《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为中心
○甘玉鑫
试论明代白话小说对元杂剧的改写——以《断鲁郎势焰之害》改写《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为中心
○甘玉鑫
在明代的白话小说中,有不少作品改编自元代杂剧。主要以元杂剧《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及其白话小说改本《断鲁郎势焰之害》为例进行分析。《断鲁郎势焰之害》精简和改写了原作的线索和情节;删减原作的人物数量,改写了原作人物的形象;对原作的结局和收尾也作了继承和改动。明人对元杂剧的改写与明代的社会文化密切相关。
明代白话小说 元杂剧 《包待制智斩鲁斋郎》 《断鲁郎势焰之害》 改写
元杂剧又称北杂剧、北曲、元曲,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它不仅丰富了汉民族民间传唱的故事,更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明代的公案小说《百家公案》中,就有不少的篇目改写自元杂剧,《断鲁郎势焰之害》就是其中的典型。《断鲁郎势焰之害》收录于《百家公案》的第九十二回,是据元代关汉卿的《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杂剧改写而成。《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杂剧是一部惩恶扬善的公案末本戏,小说《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对杂剧的人物、故事情节、结局等方面都进行了改写。但是,改写后的作品较原作而言,情节在篇幅上大量缩减,人物形象的刻画也略显粗糙,缺乏生气,整体艺术效果不如原作。下面试分别详述之。
一、线索与情节的改写
《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一剧共由两条线索交叉构成:一是李四之妻被鲁斋郞以“修银壶”为名所夺,李四欲告状还妻,却巧遇张珪与其妻子李氏相救,遂相识;二是讲述张珪欲替李四打抱不平,却迫于权贵不得不成为“和事佬”,让李四屈服于现实;及至后来身为“六案孔目”的张珪之妻在清明时节又被鲁斋郞夺去,却不得不向鲁斋郞低头,甘愿双手奉上妻子,造成两家悲剧。这两条线索的交错纵横使得故事情节越发精彩,同时杂剧又分别补充了包公拾得两家儿女各抚养成人,最终智斩鲁斋郞,使两家破镜重圆的情节。其间故事情节的发展一波推向一波,跌宕起伏,既符合了戏剧的基本特点,也使得整部剧作更有戏剧性。而改写之后的《断鲁郎势焰之害》则将主角张珪与李四改换成了马佑君,将故事情节设为一有夫之妇路途偶遇鲁斋郞遭殴打,向包公陈告,最终讨回公道。由于故事结构的简化,小说《断鲁郎势焰之害》在情节上也作了很大的改动。
(一)故事起因的改写
杂剧《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中在故事的开头即在交代鲁斋郎的身份地位后写道:“自离了汴梁,来到许州,因街上骑着马闲行,我见个银匠铺里一个好女子,我正要看他,那马走的快,不曾得仔细看。张龙,你曾见来么?”[1]便想着如何能够将这个女子“勾”到手,由此掀起整个故事的开端。小说《断鲁郎势焰之害》却是这样开头的:“话说景佑五年三月,东京开省院贡举天下才子。西京有一士人,姓马名一字佑君,父曾为平原县知县。一因为东京出榜招贤,遂整备行李,出去赴省。其妻李氏,年方十九,美貌端方,见夫临行垂泪,不忍别之。”[2]于是携妻子同行,这完全改写了杂剧中李四夫妻在家平淡度日,并不曾招惹是非,却凭空被鲁斋郎抢去了李四的妻子,打破了他们宁静和谐的生活。
(二)具体细节上的改写
其一,在杂剧《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中,对于鲁斋郎抢李四之妻时先是借修银壶为借口,然后设计诓李四和他的妻子喝下三钟酒,便强行带了李四的妻子往郑州去了。杂剧除了这段李四之妻被夺的剧情外,后续还有李四前往郑州告状遇见张珪一事,推进情节的发展。在张珪欲为李四打抱不平之时却迫于权贵不得不成为“和事佬”,让李四屈服于现实;后张珪之妻被夺,而其身为“六案孔目”却不得不向鲁斋郞低头,双手奉上妻子,同时杂剧又补充了包公拾得两家儿女抚养成人,最终智斩鲁斋郞,使两家破镜重圆。
而改写之后的《断鲁郎势焰之害》则将主角张珪改换成了马佑君,将故事情节设为一有夫之妇路途偶遇鲁斋郞殴打,向包公陈告,最终讨回公道。虽然情节完整,但是在情节的衔接上过于简单。同时,小说没有做任何交代便直接安排马佑君向包拯陈告一事:“便令妻直入府陈告于包拯。拯审状明白,随即差人追换鲁千郎来证”[3];马佑君告状竟如此容易?“直入府陈告”虽说包拯大开府门却也不至于并无其他阻碍,这不得不令人感到惊奇。反观《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杂剧,是这样描述这段场境的:鲁斋郞在夺得李四之妻时,鲁斋郞看出李四想要告他,便丢下一句话儿:“你的浑家,我要带往郑州去也。你不拣那个大衙门里告我去”[4];当李四往郑州上要告鲁斋郞,却从张珪口中得知鲁斋郞之势力强大,不得不自认哀哉!而当张珪之妻被鲁斋郞看上时,身为六案孔目的张珪却又不得不将妻子“双手奉上”,丝毫不敢反抗,甚至连状告的念头都没有。
其二:对于杂剧《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假借“鱼齐即”的名义向皇帝讨来圣旨,合法地斩了鲁斋郎这一环节,《断鲁郎势焰之害》在改写的过程中,却进行了别样的处理:通过自己的生日邀请各官员士子献诗贺寿,从而故褒奖鲁斋郎“足下文学优余,诗词清丽。”并设宴款待,在酒桌之上辨明是非曲直,并大怒云:“朝廷法度,尔敢故犯乎?罚铜是哪款律法?”[5]于是让公吏取长枷押送到狱中第二日还出榜声明:豪强鲁千郎已经被押解在狱,凡是受过他屈辱的,曾经致使受冤不得辩白的,现在都可以来开封府陈述其罪状。远近的人听说这条消息后都赶来为自己伸冤,后来包拯都为百姓逐一审明清楚,将鲁斋郎斩了首级,还公道于穷苦百姓。
除上述《断鲁郎势焰之害》将告状之情节精简化之外,如《当场判放曹国舅》(百家公案第四十九回)、《瓦盆子叫屈之异》(百家公案第87回)、《瓦盆子》(龙图公案第四十四则)等小说篇目均对元杂剧百姓申冤辩明之细节作了精简的处理,让文章结构稍加逊色,情节也逐渐变得简单。可见,元剧与其改写者相较,自是前者更胜一筹。
二、人物的改编
通过比勘,我们很容易发现,小说《断鲁郎势焰之害》改写《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杂剧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人物上做了很大的改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人物的删减
《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全剧共出现了鲁斋郞、银匠李四、李四之妻张氏、六案孔目张珪、张珪之妻李氏、包拯、李四一双儿女、张珪一双儿女等人构成整部戏曲,整部剧就是一个大舞台,人物生动而形象。由李四与鲁斋郎之间的矛盾冲突揭开故事的序幕,进而经过张珪的妻子被夺,一双儿女失散,将情节步步推进,而失散的儿女又正好被包拯拾得抚养成人,在包拯的撮合下两家阖家团圆,让剧本情节更加完整;而小说《断鲁郎势焰之害》将人物删减至四人:鲁千郎、马佑君夫妇与包拯。整个小说篇章就只描述了马佑君夫妇在高考途中平白受了冤,最后通过包拯明断讨回公道;整个故事情节就像规规矩矩的“正方形”,从原点出发,最后又归于平静。
其次,删去了张珪这一重要角色。《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杂剧将“六案孔目”张珪的心理刻画得淋漓尽致。他听到李四的遭遇时,本来是想为他出头的,但是在听说是鲁斋郎抢了李四的妻子时就马上泄了气,还劝李四不要再继续追究了。张珪这种自相矛盾的性格特点与心理活动在杂剧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当自己在面对鲁斋郞要夺妻子时,也只能双手将妻子奉上。面对妻子的质问时,说:“他便要我张珪的头,不怕我不就送去与他;如今只要你做个夫人,我还算好的。”[6]此时张珪的无奈、软弱、自卑的性格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像张珪等一系列的微小官吏的无奈与自卑,更映衬出当时百姓生活苦不堪言的社会现实。《断鲁郎势焰之害》将李四改成了马佑君,删去了张珪这一人物形象,不得不说小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精简了杂剧的难度,但是其塑造的人物性格却略显生硬,没有原剧那般栩栩如生,使人物缺乏固有的文学生命常态。
以上两点不单单是在杂剧《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出现,如小说《玎玎珰珰盆儿鬼》中杨国用遇上甲半仙占卜了一卦,说百日内有血光之灾,需离家千里方可化解,于是才有了后面的死于非命,包公断案等情节。不仅如此,《玎玎珰珰盆儿鬼》还在故事情节中又添加了杨国用回乡之时做的梦,梦见自己被杀;而明人改写后却直接删去了这部分,并且将主人公改成李浩,直叙其外出经商,最后再采录杂剧的基本剧情进行改写创作。使故事情节缺少复杂化,且使故事的主题变得单一化。当然,人物数量的删减并不局限于这两篇,如《拯判明合同文字》(百家公案第二十七回)、《张员外义抚螟蛉子》(初刻拍案惊奇卷33)、《赵汝州传》(情史类略)、《汴京判就胭脂记》(百家公案第62回)、《占家财狠婿妒侄,延亲脉孝女藏儿》(初刻拍案惊奇卷38)等也都对人物进行了一定的删减。
(二)人物形象的改写
1.鲁斋郎形象的改写
《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杂剧在开场时就直接交代鲁斋郞的性格:“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再没双。街市小民皆怕吾,则我是权豪势要鲁斋郞。”[7]而《断鲁郎势焰之害》对鲁千郞的描述则是放在马佑君之后,且仅用一段极为简短的文字作介绍:“有十数人在店前列,有一人紫巾黄袄,威焰烁烁,乃一豪势之家,名鲁千郎,父为现任转运。”[8]从而拉出鲁千郎这一人物,但是豪势之家却并不能说明鲁千郎就是一个无恶不作之人,也很难看出平民百姓与他的关系所在。但是杂剧却一针见血地从侧面说明鲁斋郞在市井百姓眼中早已经深恶痛绝了。同时剧本也正面显示了鲁斋郞的欺行霸市,欺男霸女。如当身为六案孔目张珪在自己的儿子被人打了之后破口大骂,但对方是鲁斋郎,故被他反骂着:“张珪,你怎敢骂我,你不认的我?觑我一觑,该死!你骂我,该甚么罪过?”[9]还与张珪耳语道:“把你媳妇明日送到我宅子里来!若来迟了,二罪俱罚。”[10]更加衬托出鲁斋郎蛮横无理,飞扬跋扈,流氓地痞无赖的性格;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鲁斋郎是官僚豪强,以权压人的社会地位。而经小说改写后的鲁千郎则完全看不到其蛮横无理,飞扬跋扈的无赖个性。
2.包拯形象的继承
无论是《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杂剧还是小说《断鲁郎势焰之害》,都充分体现了包拯的智慧。在《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杂剧中,包拯以“鱼齐即”名义,上报皇帝,斩鲁斋郞于“市曹”;小说则展示了包拯设饭局诓骗鲁千郎道出事情原委,遂直枷了鲁千郎,并张榜与鲁千郎有冤者皆可来告,逐一审明,既成案款,直斩鲁千郎。由此可见,《断鲁郎势焰之害》与《包待制智斩鲁斋郎》都体现了包拯的“智”。
值得注意的是,元杂剧及其明代白话小说改本均保留了包拯的“超自然”能力。如《玎玎珰珰盆儿鬼》杂剧及其小说改本《瓦盆子叫屈之异》,故事中的包拯备下金银纸钱,门神便放冤死的鬼魂进入公堂。作者还借张别古的口吻称赞包拯“人人说你白日断阳间,到得晚时又把阴司理。”[11]这些能表明包拯在百姓的心中已经完全神化,拥有“超自然”的能力,能够断鬼通神,连神也惧怕三分。
笔者认为,在塑造人物形象时,要赋予人物灵活生动的语言,力求做到个性化,体现出人物说话的艺术性,符合人物的性格特点。清代戏剧理论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也提到创作剧本必须要“语求肖似”“务使心曲隐微,随口唾出,说一个肖一个,勿使雷同,弗使泛泛。”[12]
如《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中张珪听说李四受了不平之冤时,有这样一段对话:“(正末云)谁欺负你来,我便着人拿去,谁不知我张珪的名儿!”[13]在李四说出是鲁斋郎时,张珪又转变了话语:“哎哟,唬杀我也!早是在我这里,若在别处,性命也送了你的。我与你些盘缠,你回许州去罢。这言语你再也休提!”[14]因此,读者也可从中揣摩出张珪有着愿意为平民百姓审明冤情的正义之心,却又有惧畏权贵,不得明哲保身的心态。正是这种人物独白与对话将张珪这一人物的双重性格鲜明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让读者对人物的身份形象有了明确的定位。而《断鲁郎势焰之害》中的马佑君在听完妻子告知其所受殴打之事时,只有一句:“此人无理太甚。”[15]便领着妻子直接到开封府包拯初告状去了。其间,对于马佑君这人物的言语太过平常,则达不到这种高超的艺术效果,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其他小说如《张员外义抚螟蛉子,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三)、《汴京判就胭脂记》(百家公案第六十二回)等,均在某些程度上对元杂剧原作的人物语言进行了改动或删减,使人物的活动性格表现也因此而缺少表现力,无法正确传达出塑造人物形象的意义。
3.结局与收尾的改写
在比勘的过程中,笔者发现白话小说改本对原作的结局作了一定的继承与改变。以《断鲁郎势焰之害》小说改写元杂剧《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为例,《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以包拯断完鲁斋郞之后,张李两家夫妻团聚,儿女欢喜姻缘次第为结局,更加符合市民百姓的主观愿望。而改写后的《断鲁郎势焰之害》只用两句话即交代了整个事件的结局:“发回佑君夫妇。后来佑君得中高第,除授同州佥判夫妇同去赴任。”[16]即两者之间都以美好团圆为结局。又如元杂剧《相国寺江孙合汗衫》最后的结局为:“您道一家骨肉再团圆,这快心儿不是浅,便待要杀羊造酒大开筵。多只是天见怜,道我个张员外人家善,也曾济贫救苦舍了偌多钱。今日个着他后人儿还贵显。”[17]被小说《苏知县罗衫再合》改写后同样是以大团圆结局收场:“苏泰历宫至坐堂都御史,夫人王氏,所生一子,将次十承继为苏雨之后,二子俱登第。”[18]当然,类似的作品还有不少,如《玎玎珰珰盆儿鬼》《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包待制陈州粜米》等数十种杂剧在改编之后也都是继承了这般结局。
无论是元杂剧还是其对应的小说改本,在结局之后,往往还有一个收尾部分。这个部分是对故事情节的一个总结。元杂剧均由地位较高的人来下断语,以此总结全剧,而小说改本则是多以一首诗来概括整个故事或者直接交代故事的结局作为结尾。如《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杂剧直接由包拯下断语:“则为鲁斋郎苦害生民,夺妻女不顾人伦。被老夫设智斩首,方表得王法无亲。你两家夫妻重会,把儿女各配为婚。今日个依然完聚。一齐的仰荷天恩。”[19]又如元杂剧《包待制智赚生金阁》的收尾,也是直接由包拯下断:“(正末云)一行人听我下断:庞衙内倚势挟权,混赖生金阁儿,强逼良人妇李氏为妻,擅杀秀才郭成,又推嬷嬷井中身死,有伤风化,押赴市曹斩首示众。嬷嬷孩儿福童,年虽幼小,能为母亲报仇,到大量才擢用。将庞衙内家私,量给福童一分为养赡之资。郭成妻身遭凌辱。不改贞心,可称节妇,封为贤德夫人。仍给庞衙内家私一分,护送还乡,侍奉公婆。郭成特赐进士出身,亦被荣名,使光幽壤。”[20]但在明人改写的白话小说当中,大多是直接以判决书结果来收束全章。如《断鲁郎势焰之害》交代为:“案款已成,遂将千郎斩了首级,号令四门。发回佑君夫妇。”[21]《张员外义抚螟蛉子,包龙图智赚合同文》等则是用一首诗:“螟蛉义父犹施德,骨肉天亲反弄奸。日后方知前数定,何如休要用机关。”[22]从而给故事情节做一个总结。
笔者认为,无论是杂剧还是小说,其收尾部分都具有明显的主观意识。但是,元杂剧体现了统治者加强对思想文化的控制。如上文提及《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中的[收江南]明确说明了贫苦百姓之所以能够沉冤得雪,主要是因为皇帝清明的功劳:“今日个依然完聚。一齐的仰荷天恩。”而明代改写后的白话小说《断鲁郎势焰之害》的收尾部分除了以判决书:“发回佑君夫妇。后来佑君得中高第,除授同州佥判,夫妇同去赴任。”说明结局之外,其他经过改写后的小说如《诉穷汉暂掌别人钱,看财奴刁买冤家主》:“想为人禀命生于世,但做事不可瞒天地。贫与富一定不可移,笑愚民枉使欺心计”[23]《张员外义抚螟蛉子,包尤图智赚合同文》“螟蛉义父犹施德,骨肉天亲反弄奸。日后方知前数定,何如休要用机关”(同注[22])等,其收尾大多是以劝谏为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教化世人,给社会传递一种向善、正义的能量。
三、影响明代白话小说改写元杂剧的因素
笔者认为,明人对元杂剧作品的改写跟当时的社会文化有很大的关系。首先,元人杂剧的繁盛,并广泛流传至明代,为明代白话小说的改写积攒了大量的原始基础素材。其次,明人重视律法的态度,也是影响明人改写元杂剧的因素之一。《大明律·吏律二》“讲读律令”条载:“凡国家律令,参酌事情轻重,定立罪名,颁行天下,永为遵守。…… 其百工技艺,诸色人等,有能熟读讲解,通晓律意者,若犯过失及因人连累致罪,不问轻重,并免一次。”[24]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杂剧中,包拯需要假借“鱼齐即”之名上报皇帝,才能将鲁斋郞斩于“市曹”,而在小说改本《断鲁郎势焰之害》中,包拯却可以光明正大地将鲁斋郎绳之于法。
再者,明朝正统到正德年间,由于王振、汪直等宦官专政,再加上英宗复辟等事件,明朝统治者放松了文化控制,虽采取“八股取士”的人才选拔方法,但政治局势仍极不稳定,卖官鬻爵等风气十分盛行。“刘吉企图结好科道官,笼络言路,遂数兴大狱,……台署为空,中外侧目。”[25]从此处可观之,这段时间内官衙内产生了许多冤假错案,许多百姓伸冤无门,生活苦不堪言,人民热切希望能够能有一个像包拯那样的清明官吏来辨明是非,为他们伸张正义,由此改写家为了能够更好的迎合当时的社会的价值观需要,满足市民的主观欲望,便将元杂剧的情节简单化,使杂剧“圆满”结局更加生活化、实际化。
与此同时,明朝商品经济的不断兴起、壮大,市民阶层开始不断扩大,人们对文学作品的需求越来越大,为了满足当时各阶层市民的需求,明作家、艺人需要不断地进行创作,但创作需要更多的时间与空间构思,根本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量,所以作家们不得不把笔尖开始伸向元代杂剧。元代杂剧数量较大,在民间广为流传,故许多创作者开始了对杂剧的改写之路,以此来满足市民阶层的市场文化需求。与此同时,当时的文学领域展开了以心学为基础的启蒙哲学运动,李贽等人兴起了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因此明代的文人志士在思想观念上脱离了封建思想的枷锁,思想得到了得到了极大地解放,审美观念也由此产生了变化。所以,文人志士阶层开始形成了一种由趋俗到入俗的风气,转而进入将杂剧改成通俗白话小说,便于以书面语言形式在民间流传。
注释:
[1][4][6][7][9][10][13][14][19]王季思:《全元戏曲》(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9页,第360页,第369页,第358页,第364页,第364页,第361页,第361页,第381页-382页。
[2][3][5][8][15][16][21][明]安遇时编集,魏同贤标点:《包龙图判百家公案》,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15页,第316页,第316页,第315页,第316页,第316页,第316页。
[11]王季思:《全元戏曲》(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0页。
[12]沈勇译注,[清]李渔著:《闲情偶寄》,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第385页。
[17]王季思:《全元戏曲》(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8页。
[18]魏同贤主编,[明]冯梦龙著:《警世通言》,《冯梦龙全集》(第二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156页。
[20]王学奇主编:《元曲选校注》,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363页。
[22][23]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354页,第381页。
[24]怀效锋点校:《大明律》,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25][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百六十八),“刘吉”条,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528页。
[1]王季思.全元戏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2]魏同贤标点,安遇时编集.包龙图判百家公案[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
[3]李建明.拙劣的改编,成功的采录——谈《判瓦盆叫屈之异》对戏曲的改写[J].南通大学学报,2010,(3).
[4]沈勇译注,[清]李渔著.闲情偶寄[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
[5]魏同贤主编,[明]冯梦龙著.冯梦龙全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6]张明明,高岩.杂剧,《鲁斋郎》中张珪人物形象论[J].绥化学院学报,2007,(4).
[7]王学奇主编.元曲选校注[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8][明]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9]怀效锋点校.大明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0][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甘玉鑫 广西玉林 广西玉林师范学院 537000)
(本文系201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明代白话小说改写元杂剧研究”,项目编号:[20151060618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元杂剧的明清改编本研究”,项目编号:[15YJC751023]。)
——包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