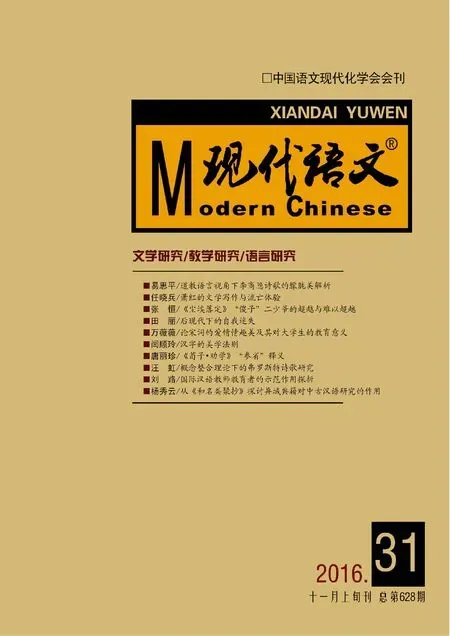道教语言视角下李商隐诗歌的朦胧美解析
○易思平
道教语言视角下李商隐诗歌的朦胧美解析
○易思平
中国道教宣扬语言文字的神秘性和神圣性,道书中的语言古奥怪谲,隐秘晦涩。作为道教信仰者,李商隐的诗歌创作深受道教语言的影响,其诗歌大量使用道教的隐语、典故及故实名词,从而呈现出别具一格的朦胧美,包括诗歌语言的模糊美、诗歌意境的迷幻美和诗歌主旨的隐晦美。
道教语言 李商隐诗歌 朦胧美
唐代大诗人李商隐,一生沉沦下僚,人生坎坷不堪,“然而他所创作的诗歌,却在百花惊艳的唐代诗歌园圃中开放出一丛绚丽夺目的奇葩,一千多年来为人们所珍视。”[1]但他的诗歌以朦胧晦涩著称,留下许多谜团,尤其是其中许多题作“无题”的诗歌至今仍众说纷纭,难以确解。究其原因,当与道教语言对他的影响有关。道教与佛教“以心传心,不立文字”之蔑视语言文字的观念不同,而是宣扬语言文字的神秘性和神圣性。正如葛兆光先生所云:道书“为了宣传神灵的灵异威严及鬼怪的可怖与凶恶,为了引起人对理想中的仙界的向往,当然也为了保证道士对于沟通人神天地的特权,它们常常需要使用一些非常独特和怪异的词语,所以它不是无文字语言以为说,而是专凭文字语言以为神。”[2]道教典籍因而常常使用一些古奥艰深的语言,以追求一种玄奥莫测的宗教宣传效果。作为一位道教信仰者,李商隐怀有浓郁的道教情结,因此他在诗歌创作中常常大量使用道教语汇,包括道教隐语、典故、故实名词等,从而使他的诗歌披上了一层朦胧美的奇异色彩,包括诗歌语言的模糊美、诗歌意境的迷幻美、诗歌主旨的隐晦美。
一、道教隐语与李商隐诗歌语言的模糊美
隐语,顾名思义,就是一种隐秘性的话语,它是诗歌最原始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古代宗教的产物。朱光潜先生曾经指出:“诗歌在起源时是人与神互通款曲的媒介。人有所颂祷,用诗歌进呈给神;神有所感示,也用诗歌传达给人。不过人说的话要明白,神说的话要不明白,才能显得他神秘玄奥。所以符谶大半是隐语。这种隐语大半是由神凭附人体说出来,所凭依者大半是主祭者或女巫。”[3]因此,隐语有点谜语的味道,就是故意把话说得含蓄、委曲甚至晦涩,让人不易索解。闻一多先生云:“隐语古人只称作隐,它的手段和喻一样,而目的完全相反。喻训晓,借另一事物把原本说不明白的说得明白些;隐训藏,借另一事物把本来可以说的明白的说得不明白。”[4]中国道教以神秘之“道”为最高追求,又宣扬神仙信仰,于是为了隐秘其修仙之术以自珍,并达到崇道的目的,便常常使用隐语来称呼某些事物或宣扬某些观念,使之显得玄远深奥。比如称炼丹的鼎器为“神宝”,称金银为“黄白”,称硝为“小玉”,称铁花为“独神”,称太阳为“炎宫”,称月亮为“银宫”,称身体为“玉山、玉都”,称面为“灵宅、尺宅”,称鼻为“神庐”,称眉为“神盖”,称口为“天关、玉池”,称足为“地关”,称心为“赤城、灵台”,称口中津液为“玉液、玉浆、玉泉、玉英、金醴、玉醴”,等等。[5]特别是由于道教宣扬阴阳雌雄观念,主张男女双修的房中术,于是为了忌讳和避俗求雅,更是常常使用隐语来指代男女两性,如以日、龙代阳性,月、虎代阴性等。不只如此,生活中的许多物象都成了指代阴阳雌雄的隐语,比如“虹、雷、岁、月、草、木、金、石之类,皆分辨雌雄”[6]。
李商隐对道教隐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他的一些隐秘情诗中。一般认为,李商隐曾与女冠发生过缠绵悱恻的恋情,但这种恋情由于有违社会道德习俗,他不敢公之于众,只好借用道教隐语言之,因此,“龙凤”“龙虎”“蟾虎”等词在他的诗歌中便频繁出现,运用自如。例如:“天泉水暖龙吟细,露畹春多凤舞迟”(《一片》)、“松篁台殿蕙香帏,龙护瑶窗凤掩扉”(《圣女祠》)、“紫凤放娇衔楚佩,赤鳞狂舞拨湘弦”(《碧城三首》之二)、“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无题·飒飒东风》),等等。而且,他进而还常用道教隐语“高唐梦”“高唐雨”“云雨梦”“梦雨”“云雨”等来指代男女性爱。如:“如何一梦高唐雨,从此无心入武关”(《岳阳楼》)、“剧馆觉来云雨梦,后门归去蕙兰丛”(《少年》其二)、“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重过圣女祠》)等。这些性爱隐语出自战国时楚国“道家文人宋玉”[7]《高唐赋》一文所写“巫山云雨”之艳遇故事。李商隐非常熟悉道教的隐语瘦词,是“赋高唐”的能手,故常常大量引用“高唐”隐语植入自己的诗歌中,隐晦其性爱本事,达到委曲朦胧、深情绵邈的抒情效果。[8]
李商隐借助道教隐语来指称自己爱恋的对象,或描写男女两性关系,一则对情爱进行诗化、美化和雅化,二则让语言含蓄蕴藉,言在此而意在彼,让人似懂非懂,难以揣摩,从而领略到一种模糊之美的语言魅力。
二、道教典故与李商隐诗歌意境的迷幻美
诗文中使用典故,可使表情达意不落俗套,出奇创新,尤其是言简意赅,有含蓄之美,如刘知己《史通·叙事》所谓“言近而旨远,辞浅而意深”。李商隐对典故十分偏爱,诗文中大量用典,尤其是道教典故,乃至惹来后人不少批评,如宋人黄彻《 溪诗话》卷十说他“好积故实”,杨亿《谈苑》说他是“獭祭鱼”,范晞文《对床夜语》卷三更讥讽他的诗是“点鬼簿”。实则李商隐喜欢在诗中使用道教典故并非要卖弄学问,故弄玄虚,而主要在于追求一种朦胧的艺术境界。因为,道教典故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其所咏之人,所写之物,所绘之景,所述之事,都具有非理性色彩,往往非虚非实,亦虚亦实,非真非幻,亦真亦幻,显得意象迷蒙,意境缥缈,给人一种迷幻感。且看他那首著名的《锦瑟》诗: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此诗让众多诗家生出“一篇《锦瑟》解人难”的慨叹。诗歌四联之间似乎毫无关联,特别是中间二联与首联、尾联之间简直断裂如崖,跳跃性极大,让人如坠云雾,不知所言。其实,中间两联是把四个独立的道教典故接在一起——“庄生梦蝶”“望帝化鹃”“珠有泪”“玉生烟”。“庄生梦蝶”出自《庄子·齐物论》,说庄周梦见自己化为蝴蝶,醒来后“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望帝化鹃”出自《华阳国志》中杜鹃啼血的故事,望帝原为古代蜀国君王杜宇,因国亡身死,其魂魄化为杜鹃,每到春天便悲鸣恨啼不止,直至出血。“珠有泪”出自唐谷神子《博物志》鲛人泣泪成珠的故事,传说鲛人是神话中的人鱼,生活在海里,珍珠就是由它们的眼泪变成的。“玉生烟”源自南北朝干宝《搜神记》,传说春秋时吴王夫差的小女儿紫玉爱慕韩重,欲嫁他为妻而不得,乃至郁闷而死,韩重游学回来后前往她的墓上哀悼,忽见紫玉原形现身,赠他明珠,并对他唱歌,韩重想抱住她,紫玉却化为一缕轻烟不见了。这四个道教典故硬接在一起,看似既无条例,又无逻辑,显得杂乱而突兀。但这四个典故却营造了一种相似的意境:迷离彷徨、忧郁凄婉、哀怆孤愁、蒙胧虚幻,从而表达了与首尾两联所云“无端”“惘然”之相似的悲情愁绪。
再看他的《圣女祠》一诗:
松篁台殿蕙香帏,龙护瑶窗凤掩扉。
无质易迷三里雾,不寒长著五铢衣。
人间定有崔罗什,天上应无刘武威。
寄问钗头双白燕,每朝珠馆几时归。
此诗首联描写圣女居处的环境,后三联则连用“三里雾”“五铢衣”“崔罗什”“刘武威”“双白燕”等五个道教典故,让人感觉乱而无章,莫名所以。“三里雾”出自《后汉书·张楷传》“(楷)性好道术,能作五里雾”;“五铢衣”出自《博异志·岑文本》“上清五铢服”,传说为古代神仙穿的一种衣服,轻而薄;“崔罗什”出自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冥迹》人神交接之故事,传说清河人崔罗什,途经长白山遇一鬼女,自称是汉末吴质之女,所云汉魏时事皆与史合,预言人事亦皆应验;“刘武威”出自五代杜光庭《神仙感遇传》:“刘子南者,乃汉冠军将军武威太守也。从道士尹公,受务成子萤火丸”,以道术而避死获生,取得战绩;“双白燕”出自东汉志怪笔记《汉武洞冥记》之“钗头白燕”故事,据传有神女赠一玉钗与汉武帝,武帝以赐赵婕妤。后传至汉昭帝元凤中,宫人欲粉碎此玉钗,结果打开匣子,“唯见白燕直升天,故宫人作玉钗,因改名玉燕钗,言其吉祥。”这五个高度浓缩的道教典故,无论是神奇的人鬼,还是诡奇的物象,都显得神秘悠远,使诗中的圣女形象多了迷蒙的仙气,传达了诗人对圣女可望不可即的企慕之情,尤其给诗歌营造了一种朦胧迷离的意境,增添了诗意朦胧的美感。
李商隐非常喜欢且擅长使用道教典故,善于捕捉道典中蕴含的各种神奇神秘的意象,诸如仙道人物、神奇物象、洞天仙境等,以此营造朦胧虚幻的诗歌意境,犹如帘外之月和水中之花,具有一种象外之意和韵外之味,传达出一种含蓄隐秘的情绪,让读者虽不甚解却在心灵上得到一种精神的愉悦。[9]
三、道教故实名词与李商隐诗歌主旨的隐晦美
李商隐诗中所用道教语言非常丰富,不仅有道教隐语、道教典故,还包括大量的道教传说故事以及名词术语,有学者统称为“故实名词”,并统计李商隐诗中常用的道教故实名词有蓬莱、方丈、瀛洲、瑶池、玉山、阆风、萼绿华、金翡翠、绣芙蓉、苑内花、紫府仙人、秦楼客、嫦娥奔月、王母下凡、青鸟西飞、偷桃窃药、萧史引凤、弄玉吹箫等,“几乎用尽道藏故事,摄取全部神天仙道的意象”[10]。这样一来,不仅使得李商隐的诗歌语言模糊,意境朦胧,更使他的诗歌意义模糊,主旨隐晦,难以确解,尤其是他的许多无题诗,就更是所谓“托意”“寓言”之作,引发了无数后人的探究兴趣。且看他的《玉山》一诗:
玉山高与阆风齐,玉水清流不贮泥。
何处更求回日驭,此中兼有上天梯。
珠容百斛龙休睡,桐拂千寻凤要栖。
闻道神仙有才子,赤箫吹罢好相携。
此诗之意,历来歧见颇多,或说求令狐绹引荐,或说怀念诗友李贺,或说悼念亡妻王氏,等等。乍一看,此诗确实有点不知所云。这是因为,短短8句诗中竟有七个道教故实名词:玉山、阆风、回日驭、龙休睡、赤箫、凤鸟、神仙等。这些道教词汇,除凤鸟、神仙二词易懂外,其余都较晦涩。玉山,指西王母所居;阆风,也叫阆风台或阆风巅,仙人所居;回日驭,谓日神羲和驾车前进,不得过,为之回车;龙休睡,出自道书《庄子·列御寇》:“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颔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成语“探骊得珠”即源于此。赤箫,指箫史,语出汉刘向《列仙传·箫史》:“箫史者,秦穆公时人也。善吹箫,能致孔雀白鹤於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凤鸣。”后来夫妇俩“皆随凤凰飞去”而成仙。理解了这些道教故实名词,诗歌旨意就迎刃而解了:开首二联写玉山之高,第三联言修仙不易,末联点名主题,“借用道教中萧史吹箫引得女子弄玉相随相去成就美满爱情故事,表达了诗人在玉山学道既登仙境又能携佳侣同游”[11]的美好愿望。
我们再来看他的《碧城·其一》:
碧城十二曲阑干,犀辟尘埃玉辟寒。
阆苑有书多附鹤,女床无树不栖鸾。
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
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对水精盘。
这首诗同样给人云里雾里的感觉,或认为咏唐时贵主事,或认为讽唐武宗李炎之作,或以为写唐明皇与杨贵妃之情事,或认为自写恋情。但倘若理解诗中“碧城”“阆苑”“鹤”“女床”“鸾”“云雨”“河源”等道教故实名词的意思,就能明白此诗乃是写女冠之风流生活。“碧城”是传说中神仙居住的地方,“阆苑”传说为西王母所居之阆风苑,“女床”亦是传说中的仙山,三者用以借指女冠居处之壮丽华贵;“鹤”和“鸾”都是传说中为仙女传书之神鸟,住在“女床”等仙山上;“雨过河源”包含“云雨”与“河源”两个道教故实,如前所述,“云雨”指男女性事,“河源”则指天河,源出南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所载西汉张骞乘木筏寻找黄河源头而居然直达天河遇见织女的故事。可见,诗歌主要写女冠与人幽会缠绵、男欢女爱之事。难怪有学者讥女冠为“半娼式的女道士”[12],看来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综上所述,李商隐的诗歌从语言到意境到主旨,都是含蓄模糊,隐晦难解。连国学大师梁启超在都在《中国韵文内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中发出感叹:“他讲的什么事,我理会不着。拆开来一句一句叫我解释,我连文义也解不出来。”但另一方面,又“觉得他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快。须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秘性的。”梁启超虽然不解诗义,但又不得不惊叹其美,这就是李商隐诗歌朦胧之美的独特魅力所在。
注释:
[1]蒋凡点校,[清]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2]葛兆光:《中国宗教与文学论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3]朱光潜:《诗论》,北京: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1页。
[4]闻一多:《说鱼》,《闻一多全集》(第一卷),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17页。
[5]冯利华:《道书隐语刍议》,北京: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第2期,第66-67页。
[6]钱钟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65页。
[7]张松辉,周晓露:《宋玉为道家文人考》,陈鼓应:《道家文化研究考》(第二十四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88页。
[8]韩大强:《试论道教对李商隐诗歌创作的影响》,新乡: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5期,第161页。
[9]李娟:《试析李商隐诗歌意境的主要特征及成因》,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4期,第50页。
[10]黄世中:《唐诗与道教》,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页。
[11]蒋振华:《唐宋道教文学思想史》,长沙: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290页。
[12]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页。
(易思平 广东深圳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518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