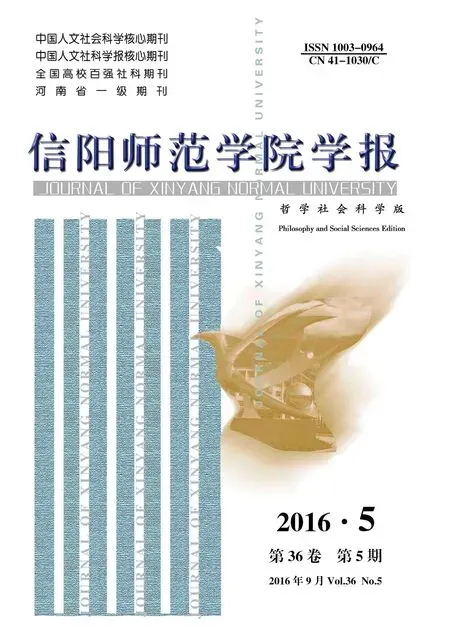灵魂的返乡之旅
——论墨白的中篇小说《民间使者》
杨文臣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河南当代文学研究·
灵魂的返乡之旅
——论墨白的中篇小说《民间使者》
杨文臣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墨白的中篇小说《民间使者》是一部充满了隐喻意味的文本,通过讲述“我”的民间艺术寻访之旅,带我们领略了民间艺术的精神和魅力,揭示了民间艺术在当下的尴尬境遇。民间艺术中存在着艺术之根,蕴含了关于生命和存在的本真之言说,就精神而言是超越时空的,“我”的民间艺术寻访之旅,因而也是一次灵魂的返乡之旅,是对失落了的艺术精神、生命精神的寻找。
墨白;《民间使者》;民间艺术;隐喻;返乡
在墨白的颍河镇系列小说中,《民间使者》是最“另类”而又不可或缺的一部。可能是多年以来社会底层的苦难经历在墨白的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对自己的故乡颍河镇似乎特别“苛刻”。早年他致力于书写底层民众那热辣而粗鄙的人生,书写贫穷和苦难结出的畸形酸涩的果实,书写淡雅古朴、旖旎如画的颍河镇风光下,掩盖的往往是愚昧、麻木和残忍。后来,墨白的笔触更多地对准了颍河镇的出走者们逃到城市后的生命和精神状态,惶惑、焦虑、孤独、沉沦、绝望……他们无家可归,因为回首来处,现代性冲击下的颍河镇正日益浑浊、破败。即便是偶尔把颍河镇作为出走者们记忆中的乐园,墨白也总是淡抹几笔。其实,在他眼中故园倒也并非如此不堪,爱之愈深,责之愈切,是悲天悯人的情怀、强烈的责任感和批判意识促使他做出了这种选择。在中长篇小说中,《民间使者》是唯一一部对民间艺术和文化精神正面施以浓墨重彩的作品,有了它,作为一个文学家园、文化地域的颍河镇才是完整的。
一
墨白有美术专业背景,1978年他考入淮阳师范学校艺术专业学习绘画,担任过11年的小学美术教师,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后,对艺术的理解和对文学的理解相促相长,加之读书的宏博,使他对艺术精神有着超出常人的理解。关于民间艺术,学界大多做一种实证式的阐释,即将其还原到特定的地域和历史时期,探讨其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情感、愿望之间的关联,鲜有人从形而上的层面关注其艺术精神。李泽厚借用克莱夫·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来阐释中国的民间艺术[1]27-28,但“意味”也是限于历史的、实证的层面,民间艺术的现代意义并没有得到关注。墨白却非常明确地意识到,虽然在现代性大潮的冲击下,传统民间艺术已声影萎缩,但其艺术精神却是永恒的,可以跨越时空与现代艺术进行对话。
在《民间使者》中,“我”倾心于超现实主义绘画,在我居住的小城中能够理解我的只有我的父亲,而他是一个民间艺术收藏者。民间艺术和超现实主义,在我们眼中有霄壤之别,在艺术史上也毫无干系,它们之间居然有什么瓜葛?在父亲的收藏室里,“我”看到有许多泥玩具,分门别类地放在一个玄色木柜的九个层面上:
第一层:(也是大柜里最底的一层)长有各种冬眠动物面相的泥猴(如蛇、蟾蜍等等)。第二层:各种因痛苦和苦难改变了五官或扭曲了身子的猴面人。第三层:长有各种水族动物面相的泥猴(如鳖、龟等等)。第四层:长有各种人类饲养的动物面相的泥猴(如牛、羊、兔等等)。第五层:一组反映生殖系列的泥猴(包括拥抱、交媾、生育等等)。第六层:各种食肉类凶残动物面相的泥猴(如虎、狮、豹等等)。第七层:长有各种飞翔的鸟类面相的泥猴(如雁、鹰等等)。第八层:长有各种想象中的多角怪兽、四不像等等面相的泥猴。第九层:想象中的神圣动物面相的泥猴(如龙、凤、九头鸟等等)。
这些泥玩具在自然界没有原型,它们是怪诞的,让我们联想到萨尔瓦多·达利。虽然有很大差别,但二者都在怪诞中表达了诸多玄奥深远的意义。从整体上看,九层泥玩具象征了整个生命创化的历程。泥玩具都是猴身,象征着所有生命存在着亲缘关系,是一个共同体,而不同面相从不同侧面既表现了生命的进化顺序,又是精神从沉睡、苏醒到飞翔的象征。九个层面从低到高的排列顺序和泥猴们代表的不同动物的生存空间恰好是对应的,如果我们把它们三三分组,会发现形成了一个“地狱/人间/天堂”的空间秩序。我们还可以从前四个层面和后四个层面分别抽象出阴、阳的范畴,中间一个层面体现阴阳的交泰相济,从而把九个层面阐释为一种道家思想支配下的宇宙图示,如同但丁的《神曲》之于基督教文化。单单着眼于某一个层面,也会引发深沉的思索,比如,第一个层面会让我们想到生命与大地、生命的死亡与潜伏之间的关联,第二个层面让我们想到苦难之于生命的意义,是生命的底色,也是生命的动力。可以说,在这些怪模怪样的泥玩具中,隐含着难以穷尽的丰富意味,关于时间、空间、肉体与精神、生命的终极意义等等。父亲年轻时从事油画创作,后来皈依了民间艺术,我最终也走上了同一条路,这表明:在民间艺术中存在着艺术之根,存在着给生命以抚慰和支撑的力量。
艺术的根或者艺术的本质是什么?海德格尔说,是对存在的真理的澄明,是“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2]256。在非本真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我们切断了与天空、大地以及其他存在者本应亲密无间的因缘关系,用功利性的眼光打量一切,于是诸神退场,大地隐匿,世界自行锁闭,我们漂浮在量化了的、机械的时间和空间之中,成为没有根基的、异化了的存在者。艺术的使命在于开拓出一个世界,并将世界置于大地之上,“我们终有一死的人就成长于这大地的涌动和生长中,我们从大地那里获得我们的根基的稳靠性”[3]200。艺术是神圣的,引我们回归本真的存在。《民间使者》中,墨白告诉我们,泥埙就是这样的艺术品。胶泥采自大地深处,水来自天空的雨露,火热的阳光使其干燥,在泥埙中,渗透着天空与大地的气息;泥埙是姥爷耗费了许多时间和心血制成的,承载着他对女儿的许诺,凝结着这个沉默的黑脸汉子的智慧、希冀和对于生命与大地的虔敬。
不知什么时候,父亲和冷姨同时听到从外面传来一种乐声。那声音仿佛来自土地的腹部,有仿佛走了很远很远的路途;那乐声如同在雨季里滑过枝头的水丝,洗涤着冬季残留的尘土,一切都在那乐声中变得清新起来。冷姨在那乐声里慢慢地稳定下来,她仰望着低矮的草庵子泪流满面,她知道那乐声来自姥爷为她做的泥埙,那种来自土地腹部的声音使她得到了力量,她在那泥埙的乐声里产下了一男婴。
泥埙吹奏出的是一种“寂静之音”,一种纯粹而又无比丰富的声音。在泥埙的吹奏声中,生命伴随着苦难降临,也是在泥埙的吹奏声中,冷姨安然赴死。
和泥埙一样,泥泥狗也是用胶泥做成。人来自尘土,终将归于尘土,胶泥这种材料相比其他材料更能引发我们关于生命本真的思考。不仅如此,泥泥狗都用桃胶做的黑色颜料作为底色,以衬托其他各种明艳的颜色。桃胶是桃树的伤口中流出的泪水,黑色是苦难的颜色。生命何尝不是如此。那些如草芥般平凡的底层民众默默地忍受着各种不期而至的屈辱、摧残、苦难,怀着对生的喜悦,对死的坦然,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在泥泥狗这种艺术形式中,蕴含着坚忍顽强的民间文化精神,是抱朴含真的生命本色。墨白曾感叹,现在的泥泥狗制作为了迎合市场把底色换成了黑漆,在阳光下能看出光泽,这样的泥泥狗已经失去了其精神本质[4]52。
还有桃雕,是艺人们用刀,也是用生命刻出来的。桃园是冷姨一家人安顿生命和灵魂的家园,是父亲和冷姨的疗伤之所,也是他们爱情生长的伊甸园。但桃园毕竟不是“桃源”,逃避不了各种外来力量的侵袭。一天,一支溃散、肮脏的军队洗劫了桃园,遍地是断枝残叶、踩得稀烂的桃子和那群魔鬼啃噬后留下的桃核。桃园的栖居者们默默把桃核淘洗干净,然后冷姨的母亲开始在上面不停地雕刻各种传说中的神话或历史人物:
她手中的刻刀走进桃核的表面,或走进桃核的内部,发出哧哧的叫声,这种艺术的语言在沉长的黑夜里慢慢地融进了冷姨和我父亲的血液。
桃核是坚硬的,一如桃园人那坚不可摧的生命意志。所有的民间艺术,虽然表现形式各有不同,都有着共同的血脉,桃园作为一个象征性场所就是它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所以,泥泥狗、泥埙、桃雕、剪纸、面人等,都来自桃园,那些民间艺人们都存在亲缘关系。通过娓娓地讲述艺术和生命的故事,墨白告诉我们,在民间艺术中,蕴含着无比深沉、崇高的文化精神和生命意识。
二
墨白非常重视文本的隐喻和象征,他的创作孜孜追求于“在叙事语言中隐含一种诗性,使整个作品隐喻着一种象征性的主题”[5]418。《民间使者》是墨白这一追求达到极致的作品,诗性气质非常浓郁,隐喻、象征几乎遍布于叙事的每个层面。
“琳的出现和父亲的死亡过程几乎是同时来到那年阴雨连绵的三月”。这是小说的开端。从叙事学的角度,这一开端根本构不成情节。我们读到这句话时,会期待这两个事件——琳的出现和父亲的死亡——之间有现实的、因果的关联,但不久就会发现,那种预期的关联并不存在。如果二者只是巧合,我们可以责备作者是在戏耍读者,故弄玄虚。但读到终篇,有鉴赏力的读者会明白,这一开端意味深长,隐喻了民间艺术极其尴尬的现代境遇,而这也是《民间使者》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父亲,一个民间艺术收藏家,一生不得志,连儿子也拒绝了他,儿子喜欢上现代西方艺术。父亲大部分时光都呆在那间幽暗的储藏室里,吹奏土埙,把玩藏品,那些东西是他精神的寄托,已融进了他的血液和灵魂。父亲的死亡象征了民间艺术的消失。当他离开时,“他漫长的人生旅途好像一片云烟从我的面前飘逝,找不到半点他所生存在这个世上的依据”。
琳是桃园的传人,她的生活不像她的父辈、祖辈那样沉郁、苦涩,琳出现时穿的是“红色”衣服,而冷姨是一身“黑衣”。琳现在的身份之一是“民间使者”,频繁到外地城市甚至国外访问,她已经有财力在颍河镇上起了一幢自己的两层楼,就要搬离寒酸简陋的桃园居所了。相比郁郁不得志的父亲,琳的境遇似乎表明民间艺术正受到重视,有了发扬光大的灿烂前景。果真如此吗?如前所说,桃园是民间艺术的精神家园,离开桃园后的民间艺术是否还能保留自己的精神实质?琳之于艺术的态度,或许并不像其先人们那样虔诚恭谨,她不知道那些悲怆的往事,而冷姨也说,好久没有听到琳剪纸的声音了。如此,小说的开端就隐喻了这样的内容:在发扬光大的喧嚣声中,民间艺术的精神正在流逝。
海德格尔告诉我们,人们总是倾向于逃避沉重的存在之思,沉沦到一种无根基的生存状态之中[6]213。父亲的收藏室让“我”恐惧,在他死后“我”轻率地毁掉了他的藏品,“这别怪我,父亲。我必须清除你的痕迹,我才能生存”。但逃避并不能令我解脱,“当最后一只泥猴滑落在地的时候,我的胸腹仿佛被掏空了一般,一种失落感深重地笼罩了我”。“我”的精神历程父亲也曾经经历过。在桃园和冷姨的父亲“泥人杨”一起劳作时,“父亲艰难而吃力地跟在黑脸汉子后面,看着黑脸宽背上的汗水在阳光下如同乌金一样闪亮,他心里就有一种压抑的感觉”。小说没有交代父亲离开桃园和冷姨的原因,或许也是出于逃避?我们知道的是,离开桃园后的父亲成了漂泊的异乡人,只能在那些藏品中排解自己的乡愁,直至郁郁而终。
我们沉沦已久,存在之光被迷雾阻断,“我不知道那些忧伤沉闷的细雨从何而来,也不知道辉煌的太阳糜烂在何方”。当“我”追寻父亲当年的足迹,满怀憧憬地登上颍河河堤时,难掩失望之情:
这就是我父亲笔下出现过无数次的颍河吗?为什么没有远航的白帆和高大的货船?为什么没有赤脚的纤夫和行船的号子?为什么没有窈窕淑女和捣衣的棒槌声?为什么没有开遍堤岸的桃花和在水中逍遥的水鸟?没有,这一切都没有,有的只是光秃秃的被水泥包裹了的岸,清清的河水被上游排放出来的废水所污染。我立在河岸上,嘈杂的人群从河底涌上来,那是一群刚刚从对岸过来的人,我听到机帆船无力地在河道里干咳。父亲当年所赞叹的就是这条河吗?
这就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诗意褪尽,气息奄奄。“满脸皱纹没有一点表情”的老汉只关心我是否买船票,对于我神圣的寻访之旅丝毫不感兴趣。当世界失却其深度,在计算性表象思维和技术的支配下沦为生命的容器的时候,生命也蜕变为肤浅的、功利化的存在,灵魂无处安放。我们必须回归,否则就会陷入虚无,焦虑和孤独将像梦魇一样困扰着我们。“我”这次寻访之旅因而意义重大,是对失落了的艺术精神、生命精神的寻找,是灵魂的返乡之旅。
三
如此,我们就明白何以墨白一直执着于“寻找”的主题。寻找并不是为了某个确定之物,那只是寻找的契机。重要的是寻找本身。寻找是一种能力,那些庸庸碌碌却又自以为是的个体是不会去寻找的,他们的目光总是满不在乎地滑过事物的表面,他们的耳朵总是充塞着各种纷纭杂沓的信息,他们的心灵已经涣散麻木,失去了对于世界的好奇和生命的激情。个体必须拥有诗意的想象,必须能够倾听召唤,才有去寻找的可能。这种想象和倾听的能力,本质上就是一种艺术的能力。或者说,唯有艺术,才能带我们的心灵踏上诗意的寻找之旅。
一张被虫蛀遍了的竹桌,在常人眼中只配扔掉,但却唤起了“我”许多的美好想象,后来“我”沿着父亲曾经走过的路途进行了一次漫长的流浪,却发现那里并不出产竹子,也没有这种竹桌,这使“我”感到迷惑。但这只竹桌的确给了“我”许多美好的想象,也给“我”提供了重走一遍父亲当年走过的路的冲动,这就是它存在的意义。不只是竹桌,父亲日记中的许多人和事都已改换容颜,或消失无踪,但寻找的意义不会因此折损。海德格尔说,追问意味着已有关于问之所问的先行领会。同样,寻找本身已经许诺给了自己以意义。
寻找必然会有所收获。墨白说:“我们要寻找某一事物,可是偏偏有许多与这一事物无关的事物扑面而来,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看上去它是那样的毫无意义,实际上它对我们十分重要。”[7]13父亲当年去颍河镇寻找老面人梁,始终没有见到,但走进了冷姨的世界;“我”错过了与琳的见面,却意外邂逅了面人梁。当“错过”这一情节重复出现时,显然就具有了隐喻意味。墨白很清醒,由于语境的差异,某些过去的艺术形式、生活方式、道德理想等等,很难在当下复现,但我们依然应该展开追寻。我们会错过目标,会陷入迷惘,但总会柳暗花明,事物会因我们执着的追寻而呈现出过去隐匿的,甚至是全新的意义,我们也许会因此而进入一个超出预期的胜境之中。所以,尽管各有曲折,父亲和我都到达了桃园。海德格尔告诉我们,思之路径隐晦幽暗,但终将拥我们入于大道之中。寻找是思的隐喻。
父亲离开的时候,淫雨霏霏,一如“我”当时纷乱迷惘的心绪;而冷姨离开的时候,“我”的生命正在关于民间艺术的思考中升华:
时间从我的思索里慢慢地滑过,黄昏慢慢地从我吹奏的泥埙的乐声里一步步地走近。当我从思考里走出来的时候,我看到月亮已挂在东方的天空,这是从雨季以来我见到的第一个月亮。月亮朦胧的光辉穿过无限的空间照进屋子里来,照在坐在门边的冷姨身上,我叫一声,冷姨。……冷姨没有回答我,她的手上仍旧握着一把刻刀。
月亮是乡愁的守护者,乡愁是之于家园的眷恋,是对栖居的倾心。尘霾弥漫而又光彩炫目的城市夜晚,我们已看不到月光,我们也不再拥有家园和本真的乡愁。我的到来,冷姨的死亡,和小说开端形成了呼应。对于父亲死亡和琳的到来,作者有意做了一种僵硬的处理,琳没有和父亲见面,她的出现莫名其妙,在窗外向我挥挥手就离开了,与此同时屋里父亲颓然倒地,这之中隐喻了精神层面上的断裂。而冷姨是在月光温柔地照抚下,土埙的吹奏声中,安然回归大地的怀抱,在场的“我”也受到召唤,“异乡人”返还“家园”。小说到此收尾:
在往后的日子里,我准备一边用木棍捶打胶泥,一边等待着琳从遥远的南方归来。
非常美好的期待:关于未来,关于爱情,关于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精神的回归和发扬……
最后,谁是民间使者?就小说而言,琳,“我”,父亲,冷姨和那些民间艺人,土埙、泥泥猴等民间艺术品,在不同的层面上都是民间使者。其实,最当之无愧的民间使者是墨白,他带我们领略了民间艺术的精神和魅力,引领了这次浪漫而深沉的灵魂之旅。
[1]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2][德]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3][德]马丁·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刘海燕.墨白研究[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
[5]墨白.梦境·幻想与记忆——墨白自选集[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
[6][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7] 墨白.爱情的面孔·代序[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韩大强)
The Return Journey of the Soul——on Mo Bai's Novel A Folk Messenger
YANG Wenche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China)
Mo Bai's novel A Folk Messenger is a text full of metaphoric. By telling protagonist's journey of searching for folk art, this work shows the spirit and charm of the folk art to us, and reveals its embarrassing condition in current. Folk art has the root of art, and contains true speech about life and existence, so it is beyond time and space in spirit level. The journey of searching for folk art is a journey of searching for the art spirit and life spirit that have been lost, a soul journey return to its home.
Mo Bai; A Folk Messenger; folk art; metaphor; return home
2016-04-21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4JJD810016);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4BKS016)
杨文臣(1980—),男,山东兖州人,文学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文学理论与批评。
I207.42
A
1003-0964(2016)05-0107-04
—— 《印象:我所认识的墨白》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