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远的乡村灵魂
渐行渐远的乡村灵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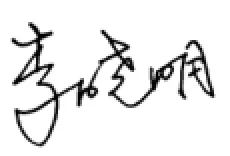

李晓明李晓明,笔名日尧月,甘肃省秦安县人,1972年6月生。长期从事散文创作,百余篇散文散见《中国散文家》《新华副刊》《时代邮刊》《散文诗》《甘肃日报》《兰州日报》等四十余种报刊。

碌碡,这一乡间上世纪80年代以前常用的风物,不知起于何时,据《金史·赤盏合喜传》“大兵用炮则不然,破大硙或碌碡为二三,皆用之”便知,我国元代就有碌碡了。从宋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诗之六“治打时稍难,唯伏日用碌碡碾”而知,宋代已常用于轧碾成熟的庄稼,脱粒粮食。
碌碡,生于石头,却高于石头。石头,本性冷漠寡言,一经石匠的凿砸雕刻,再穿上木匠的那件木框外衣,就很人性化了,也具备了人的性灵和智慧。它也知道感恩人们,为人们虔诚尽力脱粒粮食——农人一年的希冀,也焦渴和成熟庄稼这一女味很浓的女性拥抱和狂吻,展现男性的凶猛粗悍。场院里飞转的碌碡,已失去了本身的笨重,变得很轻盈灵活,它的体温也在渐次升高,思维也在慢慢活跃,心灵越来越纯,言语渐渐增多,此刻的碌碡是一个会说话会思考会感恩的圆柱形体并穿着外衣的石头了。
这一笨重的石器农具,不论是人力拉动其咯吱咯吱地在场院轧碾脱粒,还是用牲畜(驴马牛)拉动在场院转圈圈地脱粒粮食,均是很慢悠的活计。
碌碡,一年四季里大部分时间不是呆呆地站立,就是死死地沉睡在场院的某个角落,真是体现了石头的本性——冷默。唯在碾场的时刻,才会生龙活虎起来,嚯嚯滚动起来,才会具备其石头的灵性和睿智。碾场时,碌碡成为会说话的石头(咯吱咯吱),和喘着粗气冒着热汗的人们融合在一起,很乖顺,很温柔,也很雅致地跟在人或牲畜的身后,一圈一圈地由外向里转圈圈。此刻的碌碡蛮劲十足,激情充沛,却很温顺地在庄稼这一熟透端庄、女性十足的怀里撒娇,要不是人们在碾尽粮食后的停止歇缓,碌碡是绝不会罢休的,你说,碌碡一年里有几回这样的撒娇?
乡村碾场的碾轧,是一个很艰辛的慢动作,是将时间一圈一圈转完的钟摆。头上那轮鲜亮的太阳和皎洁的月亮在天上转圈圈,地上的人们和碌碡一圈一圈地转圈圈,一天就这么不停地画着圆逝去了。其实细细而想,世间哪个物种不是在画自己的圆呢?譬如大自然最具灵性的人,有的人把圆画得很像,圆上的线条很是明晰,有的人画的哪像个圆呢?都说人生是场梦,可谁又能长期沉睡做梦呢?人生与其说是一场梦,莫如说是在画一个属于自己的圆。一块冷漠的石头嬗变成一个碌碡后,都能把一个圆画得很好,但于人而言又会是怎样的呢?在社会啥都提速的今天,人们似乎不是用心灵和纯真画圆,而是用浮躁和贪欲画圆,这怎能画好一个人生的圆呢?
在物质渐次丰厚的日子里,我们要学习碌碡的慢悠转动,不要像一台粉碎机那样把时间碾磨得零零碎碎以至成为一堆面粉,还是把时间过成一片又一片吧。一个人本身就是一个很正规的圆规,我们要用自己本有的“工具”,把自己的人生之圆画得圆圆的、亮亮的。
碌碡,你是一块会说话的石头,具有灵性的石头。飞转时,你是场院中一位男性味十足的庄稼的狂吻者,又是间接体现一位农人一年希冀的飞舞者;站立时,你成为一个体型健壮的男子汉,有宽大的胸怀和顶大的力气,不嫌灰尘虫鸟的轻薄,不怕人们屁股的沉重,一律沉稳寡言气平笑纳地高高撑起。
在大雪即将封疆的西北子夜,我却格外地缅怀碌碡的性灵和慢悠,感恩和温存,耐住寂寥和随时奉承,稳稳画圆和咯吱欢唱。
场院角落的碌碡,沟渠路旁的碌碡,泥土深层中的碌碡,您还具有高于石头本身的性灵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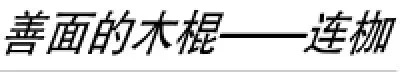
连枷,乡村人们于场院砸打谷糜小麦等成熟农作物的风物,在我国出现得很早。《国语》卷六之《齐语》记管仲对齐桓公说,“令夫农,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权节其用,耒、耜、枷、芟”,可见其春秋就有了。唐代师古的《注》说:“拂音佛,所以治禾者也,今谓之连架。”可见“连架”这个名字唐以前就出现了。
70后的我,在童年幼稚浅浅的印象中,家居陇右秦安老家,每到麦收抑或秋后,如遇响晴的天气,大人们准会在场院里老早地铺满厚厚一层带穗的庄稼茎秆,待到太阳毒辣辣的中午时,大人们一起上阵,各自手握一把连枷,相对而立,一上一下,一进一退,节奏均匀有序地拍打带穗的庄稼穗秆,让成熟饱满坚硬的粮食脱离茎秆。那一声声啪啪的声响,震动着瓷实的场院以及邻近的土院子,传播着沉闷厚重的声响,飘散得好远好远。这种原始的脱粒粮食的方法,在我的老家叫“打场”,很朴实却不俗气,很艰辛但不失望,很随意然不急促。
打场,打的是唤醒和希望,安抚和平心。这一上一下的砸打,这一啪啪的声响,是一把瓷实连枷和一株成熟庄稼的磨合和亲昵,是将沉睡的粮食抚摸而醒,是把离开泥土无根的粮食安抚,是将农人的希冀颗粒归仓。打场,是一种慢动作,急不得的农活。用力得匀称,你落它起,你进它退,哪里还需几连枷,哪里不该砸打,何时进退,几时歇缓等举止,全在眼耳和眉宇间展现,全场院除去啪啪的连枷声外,别无他声,只缘于汗流浃背的劳作辛苦,火辣辣日头的毒刺。打场,又是紧密合作的谐调活儿,不紧不慢地起落砸打,一步一步地稳健挪动,虽没半点踪迹,却很踏实沉稳。
乡村人常说:“趁热打铁,乘风扬场。”虽不常说趁热打场,打场却是在中午太阳直射的强劲有力的阳光下进行的。在酷暑时节,一场院平躺的金黄麦子再次被镀上一层太阳色,古铜色的人们头顶一顶或新或旧的草帽,连枷的长木柄和那排用牛皮扎帮的木条已被强热的光照榨干水分,紧随啪啪的声响,再热的天气也因丰收的喜悦而把啥都忘记了,一如一位铁匠,不仅感觉不到燃烧的高温,还会将这一熊熊地燃烧看得很值钱,很适合,并产生优美的联想,其翩翩浮想不亚于一位诗人的灵感莅临。
真正的诗歌在朴实艰辛的田间地头、农具起落砸打的场院……
连枷,起初为乡村脱粒粮食的农具,早在先秦就用于军事守城,《墨子·备城门》中说:“二步置连梃、长斧、长椎各一物;枪二十枚,周置二步中。”唐朝再次改良,用来守城以及马上骑兵使用,之后的宋元明清间,连枷就演变为“连枷棍”而用于武林。这是连枷的第二次生命嬗变。但不管是砸打庄稼脱粒的功效,还是用于军事武林的防守能力,均离不开连枷的本性——砸和打。正因连枷的强劲刚硬、宁折不弯、连环不息的特性,被人们在生活中应用得彻彻底底。
连枷,作为农具,是其性情慈善的一面,那啪啪的沉闷声响,仅是让一粒粒成熟粮食真正地离开母体,走向完整的粮食、闪光的粮食、个性的粮食,成为一粒实实在在的粮食。这一生命的最终嬗变,才使一粒粒粮食成为人们的眼睛、希望和心灵。单一纯洁,温馨芳香。
连枷,成为武器时,这就迫使连枷不得不显露其阴险的一面,它将赋予人的私欲贪婪,人间仇恨,那一绝响有力的砸打,不仅仅是一种防御,也是一种攻打,还是一种降服,更是一种占有。
任何事物都是一把双刃剑,均有善恶两面,就看您是用其哪一面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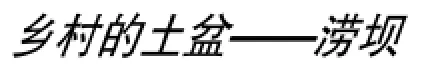
涝坝,北方乡村聚集雨水的闲置土坑,常处在村落抑或村子间的边缘,是乡村孩子夏季撒野的主要集散地。
涝坝,南方称之湖泊,聚集之水清澈,可养鱼虾,供人食;西北称之涝坝(水塘),水浑浊,散养青蛙小虫,仅为孩童贪玩之地;北方称之海子,成为草原沙漠中人的生命之源泉。不管何种称谓,均为一滩死水。南方的有着浓烈的鱼腥味,西北的有着熏天的臭气味,北方的有着清淡的咸水味。不说南北,仅说西北的涝坝,就很有风味了。
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西北乡村,人们散居山川沟壑河畔,村落间闲置的空地很多,巷道宽而长,小径繁而密,草木丛生,葳蕤荣枯,故而在乡间这些闲置的荒地上,人们常常在一个离自家较近的闲地上取土打墙建屋、填院平场、盘炕泥墙,久而久之,一个或大或小,或深或浅的土坑自然而成。一到多雨的夏秋两季,汪汪的一坑雨水自会聚集得漫漫的,多者溢出,少者聚之。常年繁忙的大人哪里有时间去打理这一闲置的水坑?只能自生自灭,自渗自枯,水坑中不知何时散居着青蛙蚯蚓、小虫微蛆、枯枝败叶,水坑周围杂草丛生、树木葱郁、引蝶招蜂,一派恬然安静的乡村美景自成。那时的孩子玩具几乎没有,作业极少,干完大人安排的活计,就可以尽情地去撒欢了。去哪里呢?孩子们最清楚,涝坝,最大的一个,水最多的一个,三五成群,一拨儿一拨儿地就聚集在涝坝旁了,呼声震天,笑声入地,脏算什么,只要玩得开心就好。
男人的童年记忆主要在夏季,女人的童年记忆却在四季。
在那个时代的乡村,孩子们最喜欢的季节就是夏季,最玩得开心的场所就在涝坝。一场骤雨过后,抑或三伏天毒辣辣的太阳能把牛晒死的中午,孩子们都会疯了一样跑到村里最大水最多的涝坝边缘,男孩们有的将裤管挽得高高的,嘻嘻呵呵地去趟水,有的高兴到了极点时还会把衣裤全然脱掉,如飞鱼,倏地从边缘跳起,一头扎进浑浊的水里,来个痛快的“蛙泳”,有的还会瞒着大人把自家本来很稀缺的玻璃小瓶拿来,眼睛不眨地在水里捉瞎眯(一种带甲壳没眼睛的虫子),还有的会将一只青蛙的某条后腿提起,倏地扔向不远处在坑旁玩耍的女孩身旁,惊起一声惨叫……
女孩子大都温雅喜净,只能在湿漉漉的坑边缘踢毽子、投沙包、捉迷藏、追蜻蜓、捂蝴蝶了。那时的男女在性别区分上还很朦胧,真是一帮“愚昧”至极的孩子,哪有你是长把的、我是没把的区分呢?
涝坝里一片混乱,呼天喊地,坑旁笑声成片,打闹成堆,有时男女混合嘻嘻哈哈的打闹,喧嚷至极,似乎能把天震塌,能把地踏漏。春季的折柳追小鸟,秋季的赤脚趟水,冬季的滑冰爬滚,涝坝成为唯一的一个聚集孩子撒欢、度过贫穷单调却很天真烂漫童年的集散地,也是那时一个贫穷孩子不能缺少的安放心灵、相互交流、打发时光、自由活动的场所。
在物质匮乏、玩具没有、大人放养的时期,谁会想到一个个乡村的孩子却能把自己的童年、少年过得完完整整紧紧凑凑纯纯真真,不仅思绪如春花自由绽放,心灵似夏花烂漫盛开;不仅把身体锻炼得一如瘦猴一样灵敏,还会把意志锤炼得如同钢铁般坚硬。
这潭或浑或浊的死水,飘满残枝枯叶的死水,虫子聚集的死水,无蛟龙盘卧,无鱼儿游荡,无大人看管,却让一个个乡村的孩子将自己的童年、少年过得充实完美、纯贞洁净。
涝坝,我在如今物质丰厚、你却被一座座院子挤跑的日子里,缅怀你,如同缅怀我自己那充满阳光般烂漫纯真的童年。
在闹市的早晨,一群群可爱天真的孩子被大人带在自行车上、汽车里、公交车里送去学校,背着鼓鼓的书包,目睹此情此景,我不由得再次想起了纯情的童年和乡村的涝坝。
邮购书目
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散文诗贺卡,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校园贺卡(塑膜套装)每套10.00元1997年、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2007年散文诗刊,2004年、2005年、2007年校园版珍藏本(每年均12期盒装)每年38.00元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散文诗刊珍藏本2008年、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校园版珍藏本每年50.00元
以上均已含挂号邮资,欲购者,款寄湖南益阳市康富南路18号散文诗杂志社发行部。邮编:413000。并请在汇单附言栏注明所订购书、刊名,款到即挂号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