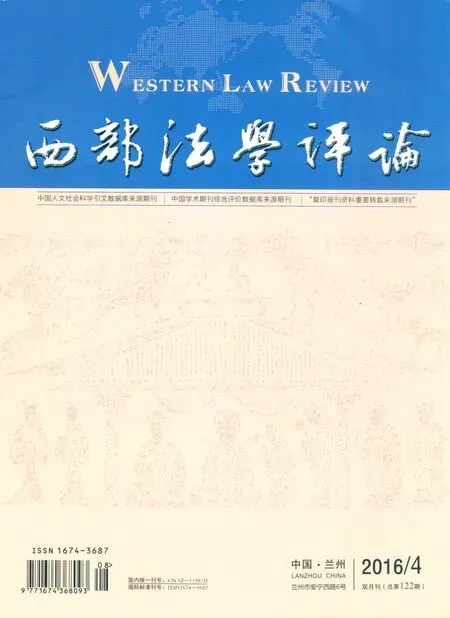作为制度体系的法:成因、主题及启示
马 斌
作为制度体系的法:成因、主题及启示
马斌
体系化既为法学方法论上的要求亦是法治原则的题中之义。但法律作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如何选择理论上的“体系化元素”,直接决定了体系化的任务与走向。以美国近现代法律思想史为观察文本,自克里斯托弗·兰德尔基于普通法构建的原则体系伊始,随着规制国的出现,法律体系在公法的影响下呈现了由规范到制度过渡的局面,并引发了体系化研究范式的根本性转变。梳理制度体系学说的发展历程并从中提炼普遍性的理论框架,对我国当下法律体系研究和法治建设能够提供新的主题和理论提示。
体系化;法律制度;规范;法律程序学派
一、导言
体系化是法学研究中的恒古议题。既然法律的意蕴和价值乃对社会生活施以秩序,那么承担此项重任的前提就是确保法律自身不能杂乱无章。同时,体系化不仅使法学知识成为可能,也会为民众及官员运用法律提供便利条件。〔1〕但法律作为复杂的社会建制,如何确定体系化的基本单位则是首先要解决的理论问题。以目前研究进路来看,我国学界大体上以“规范”和“规范的体系化”为研究重点,相关文献不胜枚举。这当然有着深刻的背景因素。在对西方学说的引介和应用进程中,法释义学(rechtsdogmatik)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最为昭著。发端于罗马法并在德国概念法学中达到巅峰,法释义学对我国民法及法学理论的影响力无需再证。英美分析实证法学自传播以来,该学派的命题和话语体系随着国内研究的成熟也基本完备。法释义学和分析法学虽然在宏观背景上迥异,但均以“规则或规范”为重心,规则是体系化当仁不让的逻辑出发点,两者都试图将实证法材料以融贯的综合体面貌呈现出来,试图完成实定法材料的无矛盾和一致性。以上背景决定了我国目前体系化研究的理路和态势。
但从本体论审视,法律体系除规则之外亦包含不同类别的制度机构,这些基本单位在规则的制定、适用和执行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功能,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实证法材料的融贯化,有序化的确是支撑法治的必要条件,但由于法释义学和分析法学有着欧洲私法传统这一共同的母体,使得担当实证法规源头的“法律制度”长期被排除在法体系的概念之外,没能成为体系建构中直接关注的对象。在法释义学和分析法学等规范主义范式的主导下,仿佛体系化无必要也不可能适用在法院,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身上,仿佛规范体系化可穷尽法律的整序工作。有鉴于此,本文以美国十九世纪末到二战后期的法律思想史为素材并完成以下任务:从实然意义上,指出法律体系学说在兰德尔和现实主义运动之后,随着公法的勃兴发生了嬗变。美国学者开始将理性与动态的目光由“规范集合”投向了法律制度,体系化的逻辑起点也由规则过渡到承担法律制定和适用的“制度”本身,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并有别于传统规范体系的理论框架。在描述意义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规范性层面提炼出一般性的制度体系学说,期望对我国当下的体系化思路提供有益启示。
二、普通法背景下的体系形式
以兰德尔(C.C.Langdell)的法律科学作为考察美国近代法律思想史的开端,这是所有学者公认的前提。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伊始,美国法已经从直接适用英国的普通法逐渐步入独具特色的轨道,确立了自身的法律原则和先例,*Neil Duxbury, Patterns of American Jurisprud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1.兰德尔的法律科学就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由于兰德尔本人并非纯粹的理论家,因此他的法学理论需要从教学法中推导出来。运用案例教学法,兰德尔力图在案例材料中,发掘并提炼出普通法针对特定的问题(cases)的规范内容。他确信,将已决案例筛选和归类后就会看到普通法原则和公理的成长过程。*C.C. Langdell, A Selection of Cases on the Law of Contracts, Little Brown, 1879, p. vii.虽然以案例材料为中心,但以普通法为宏观背景,兰德尔建构体系的单位比较清楚:法律体系是由特定的原则或公理构成并可基于逻辑发现的规范体系。以体系化的进路来看,从一般到特殊的逻辑演绎构成了兰德尔展开体系化的具体方式。
如果说兰德尔的法律体系仅仅是其案例教学的副产品,随后登场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则进一步从理论的高度奠定了普通法的规范体系,进而对兰德尔的体系设想完成了概念上的深化。初步来看,本文的上述断言有违学术界的常识,因为现实主义标志性口号即为“ 反叛形式主义”,兰德尔又恰恰是现实主义直接攻击的对象,两者间似乎不存在任何相容性。上述常规的结论固然符合历史事实,但这种泛泛的概括遮蔽了一个关键问题,也就是论及兰德尔必须要区分的两项“形式主义”内涵。兰德尔的形式主义通常被后续学者理解为由基本原则推出法律判决的三段论推理,*Thomas C. Grey, Formalism and Pragmatism in American Law, Brill, 2014, p. 50.但科学意义上的形式主义处理的是普通法原则之间的逻辑关系。与法律推理中的形式主义相对照的话,虽然都可称作由一般到特殊的逻辑演绎,但两者在适用对象和功能上却大相径庭。兰德尔的案例教学法可能间接导致了三段论的推理方式,但其主要意图是论证法学的科学性,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因此,抛开司法三段论,现实主义对兰德尔的批判也同时关涉到法学意义上的形式主义,也就是兰德尔倡导的“一元论”。 现实主义虽然鄙视脱离现实的逻辑演绎,但并不是全盘否定法学的科学本色和科学方法。*同前引〔2〕,第79页。换句话说,体系化并非现实主义清理的对象。只不过兰德尔的整理工作并非实现普通法的无矛盾性和完备性,而是把弗朗西斯·培根的真理观应用到法律上,*William P. LaPiana, Logic and Experience: The Origin of Modern American Legal Educ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55.将法律科学看成把案例归摄到以普适真理为基础的原则身上。这就导致兰德尔并不是以动态的眼光对普通法做通盘性的整理,而是将普通法简化为少数的基本原则。这样一来,由少数原则支撑的法律体系一经完成,根本没有进一步体系化的必要,这种体系化的僵化性才是现实主义反对的。因此,逻辑演绎属于“体系化”的下位概念,反对逻辑演绎并不全盘摒弃体系思维。过于注重现实主义与兰德尔的分歧,会掩盖双方在某些问题上的共同之处。
从科学意义上的形式主义出发,霍姆斯,庞德和卢埃林等人虽然认为逻辑演绎作为体系化的方式不合时宜,但没有否定体系化本身的正当性。就宏观的法律体系建构而言,现实主义者与兰德尔实质处于同一阵营,其共同的对立面是当时占据正统地位的“立法至上论”,主要以杰里米·边沁和约翰·奥斯丁(John Austin)等早期法律实证主义者为代表。举例来说,霍姆斯就指责奥斯丁的“主权命令”没能充分注意到法律的实施面向,因为命令也存在着“可执行”和“不可执行命令”之分。*G. E.White, Justice Oliver Wendell Holmes: Law and the Inner Sel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19.这种区分可视为现实主义者区别“纸上的法”与“行动中的法”的源头,但霍姆斯实质上是在凸显法官的地位。霍姆斯强调,现代社会中律师所关注的法并非主权意志所造就的,真正的法来源于那些被称为法官的主体,因为法律是经由法官也即法官的“意志”方获执行。*同前引〔7〕。法官角色在霍姆斯这里已不再是法社会学意义上的经验模型,而是法律体系逻辑上的效力顶层,法官意志与主权意志在规范体系的效力地位上是平行的。
从上述宏观背景出发,法律现实主义中隐含的体系化路数与兰德尔是大体一致的,现实主义的体系图景潜藏在法律体系的逻辑单位上,与兰德尔相比只存在技术分歧。尽管拒绝兰德尔主义抽象而形式化的规则,但是一些现实主义者暗示,可以基于经验主义的法律进路来设计一种新型的法律规则。*斯蒂芬·M·菲尔德曼:《从前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美国法律思想:一次思想航行》,李国庆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0页。接下来的问题是,何谓现实主义者宣称的“新型法律规则”呢?沿着上文提到的法律渊源转变为线索,体系单位的新面貌就会浮现出来。传统法学将法律效力的最终标准始终定位在立法机关上,而现实主义运动则调转了聚焦,将法效力的最终落脚点放置在具体的低位阶规则,也即法院的判决之上,将法官的判决置于法律体系的中心地位。*[比利时]Michel van de Kerchove and Franois Ost, Legal System: Between Order and Disorder. translated by Iain Stewa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66.按照奥斯丁和边沁的传统体系模式,法律体系作为金字塔结构由底部直接上溯到顶端的终极规范,立法机关是法律规范的唯一渊源,而现实主义者则对这套规范金字塔完成了倒砌,法律多样化的渊源最终汇集到法官的具体判决之上。在这套体系中,约翰·奇普曼·格雷(John Chipman Gray) 是最好的例证。尽管格雷与霍姆斯都强调法官的地位,但格雷对待奥斯丁的态度更加温和,这也导致了格雷的法律思想颇具体系形象。与奥斯丁相似,格雷也认为必须存在一个有形的,区别于宗教,自然和道德的法律权威机构,奥斯丁利用主权承担这一角色,格雷则诉诸于法官。虽然法官并未享有主权者所具备的无限权力,但格雷坚持法官是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最终决定者。体系结构在格雷这里也颇为明显,法官在做出的判决之际所制定的规则即为“法”本身,对于未来的案件来说,作为先例的规则仅仅是法律渊源。*同前引〔2〕,第53页。由于普通法和制定法在美国这段时期没有明显的冲突,也没有导致其它的连锁反应,且兰德尔与法律现实主义又都处在普通法阵营内,因此法体系本身也没有发生什么显著变化。从法律体系的构成单位上来看,法律现实主义者只不过把普通法的“原则”变成了综合各种因素(经济,政策考虑或法官心理因素)而生成的“判决”。
三、规范到制度:法律体系的范式转换
熟知美国法律史的学者都清楚,20世纪初至六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是极具动荡和变革的时期,法律实用主义、理性信仰,社会进步等思潮共同构成了该历史时段的宏大场景。已有的研究视角如“探寻司法的客观基础”,“法律与经济、社会的互动”*如前引〔9〕,第213,303页;以及莫顿·J·霍维茨:《美国法变迁:1780—1860》,谢鸿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虽然再现了该段历史时期的丰富内容,但却忽略了一个关键的事件:新政背景下规制国确立及公法的勃兴也恰恰是这一背景导致了法律观念以及法学研究重心潜移默化地发生了转化,为生成新的体系图景提供了土壤。
在私法传统的感染下,兰德尔认为遴选案例是法学作为科学必须重视的环节。但此番选择也同时意味着排除,因为供研究的法律材料仅限于一个来源:上诉法院二审之后的案例。兰德尔不仅刻意排除立法材料,甚至认为行政法亦无研究价值。*Rudolph J. Gerber, Lawyers, Courts and Professionalism: The Agenda for Reform, Praeger, 1989, p. 32.毫不奇怪,这套教学法导向一经提升到法学理论的客体方面,必然以普通法为体系化的基础,完全排除了立法机关等官方制度的地位。如上一节所交代,法律现实主义虽然反对兰德尔的逻辑演绎,但现实主义者也将法院及其判决结果置于中心地位。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二战前美国法学界的公法研究近乎停滞。但随着新政时期立法数量的增多以及规制国理念的确立,法院,立法机关和行政机构的权限问题便日益紧迫。随之而来的是,各政府机构在诸多法律过程中的权限分配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在这种趋势下,二战后大多数学者将理性的运作投射到法律制定和实施过程。以一般法律概念的视角观察,法律被潜移默化地看做社会规整的一系列过程,理论重心也由规范过渡到诸法律制度的结构问题。
对于该段历史时期的主题,路易斯·布兰戴斯法官曾作出经典概括:“良好的政府形式不在于其能否制定最佳的政策,而恰恰在于能否实现各机构之间相互配合,由合适的机构主体行使与之相符的权力。”*Henry M. Hart and Albert M. Sacks, The Legal Process: Basic Problems in the Making and Application of Law, W N. Eskridge and Philip Frickey eds. Foundation Press, 1994, p. lx.按照国内学界的通常习惯,本文也采取“程序学派”的译法,但为清晰性考虑,在讨论具体问题时则用“过程”一词。呼应着美国学界的主流观念:法院和立法机关在制度上应当分开,郎·富勒的“良序学(eunomics)”以及亨利·哈特,阿尔伯特·萨克斯开创的程序学派应运而生。*由于现实主义运动冲击了司法的客观性,因此凡论及法律程序学派,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都将其主旨视为对现实主义的回应,但这里明显出现了逻辑跳跃。因为捍卫司法判决客观性就算迫在眉睫,可以从原则、政策或其他方面入手论证,并无必要关注法院、立法机关、仲裁和行政机构之间的结构关系。显然,以司法客观性为主题,由现实主义径直过渡到程序学派之所以令人费解,缘于缺少公法兴盛这个环节。富勒和程序学派之间的理论传承与相互借鉴不是此处的重点,就二者的细微区别而言,美国学者达科布利正确地指出,哈特和萨克斯旨在提出一套专有的“过程”概念作为理论工具,而富勒则注重法哲学层面的分析路数。*同前引〔2〕,第233页。以本文的主题为据,需要对富勒和程序学派的文本材料再次调整:就体系单位的嬗变而言,重点应放在法律程序学派上,而富勒的相关思想比较适合法律体系的结构问题,本文在第四节会集中探讨。但这种划分不是完全绝对,就体系单位而言,民事制度在法律过程学派中的独立地位与富勒的贡献是紧密相关的。
程序学派将目光聚焦于制度权能(institutional competence)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不容忽视的是,将制度权能作为在不同法律角色(legal actors)中分派任务的基础,背后却体现了新政支持者对政府职能的独具特色的反思。*Morton J. Horwitz,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Law 1870-1960:The Crisis of Legal Orthodox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54.以一般性的理论框架来看,哈特和萨克斯一改新政前期唯普通法的惯常进路,将规制国中实定法和行政法的作用也纳入研究重点。哈特和萨克斯在论及法院时指出,普通法与制定法的关系衍生了法院与立法机构的角色安排,也就是法院和立法机关谁更适合解决相应的纠纷*同前引〔14〕,第341页。表面上看,制度权能安排处于派生地位,主题似乎应为制定法和普通法的关系而不是法律制度的结构,但实则不然。此时的“法律”不再是规则或原则等抽象之物,而是产生这些社会规范(social ordering)的制度和过程。对于程序学派的贡献,富勒曾做如下评价:“法学院常规的课程内容无一例外将重点放在社会规制的结果(results)上。尽管习惯法,实定法规,行政法和合同法在教学中略占一部分,但法学院对产生这些法律形式的社会过程却没有投入太多的时间来研究。”*Lon. Fuller, Mediation-its Forms and Functions. in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 Order Selected Essays of Lon L. Fuller, Kenneth I. Winston ed. Hart Publishing, 2002, p. 144.富勒的上述断言不经意勾勒出法律体系单位的新形态,也即不同过程中的各个参与人。详细来说,由于法律的概念不是调整权利义务关系的“法”,而是法制定和适用的过程中官方和民事制度主体,法律体系化的基本单位也不再是正统学说一贯聚焦的法律规则、原则。在这里,不妨与兰德尔和现实主义的体系模式进行对比,公法背景下体系单位的根本转变就会异常清晰。这种转变的内在理路可从以下两个步骤解剖。
第一步可概括为宏观理论焦点的转移。普通法背景使现实主义也忽略了立法和行政机构等官方制度的重要性。对于兰德尔和法律现实主义来说,私法奠基下的传统不仅导致普通法原则是权利和义务的源头,也必然使法院在普通法的体系图景中处于独占性的地位。以公法的兴盛和联邦结构问题的紧迫性为动因,程序学派虽然沿用兰德尔的案例教学法,但关注的焦点与兰德尔已有了本质区别。兰德尔建构体系的元素是普通法的原则和公理,他试图通过特定的案例材料发掘并整合背后的公理性原则,藉此通过逻辑演绎完成体系化。相形之下,哈特,萨克斯的关注焦点并非新政之前作为成品的“法律规则”,而是规则等法律形式产生、修正、解释和最终执行的一系列过程。哈特、萨克斯虽沿袭案例分析,他们关注不同机构各自的职能分配也即制度权能的合理性。*同前引〔14〕,第158页。通过强调哪个制度最适合解决什么法律问题,程序学派要求法科学生能够对法律过程中每个制度机构的位置和角色做出正确的识别和评价。自然而然,法律体系的构成部件演变为在这些线性过程中承担相应功能的制度。哈特和萨克斯认为,某些问题虽然在审判过程中出现,但法律人不仅要清醒地意识到法院的功能,还需了解立法机关甚至行政机构承担的功能是什么,甚至要厘清什么问题应留待公民自行解决,因为在法律的运作过程中,立法机构、行政机构,仲裁甚至民事主体都有可能比法院更适合解决具体争端。*同前引〔14〕,第7页。
第二步可概括为法律制度的“理论功能”发生变化,这一点更为关键但又不易察觉。兰德尔的体系路径与德国法释义学在目标方面可以类比,体系化的宗旨在于把握数量激增的案例材料,同时也减轻司法审判的压力,但司法过程本身(per se)并不是直接关注的对象。法律现实主义运动虽然将目光投向司法过程,看似拓宽了法学研究的视野,但法律体系的逻辑单位仍保持着和法释义学相同的面貌。进一步深究的话,法院是规则效力的来源,是解释法律体系的理论假设。但公法的视域下,形形色色的法律制度既是对社会问题日趋复杂以及专业分工趋势的回应,也是建构体系的逻辑对象。程序学派将法院、立法机构等制度单位置于中心地位,其结构性的思维显然也突破了现实主义唯司法论的瓶颈,因为在程序学派这里,司法机构仅仅是司法过程中的一项制度活动。*同前引〔2〕,第255页。不过,哈特和萨克斯使用的“过程”术语有些模糊。每一项过程中包含不同的官方机构,但每一项机构亦有自己的“过程”。从相关著述来看,哈特,萨克斯在强调司法过程时,其实并不是指法官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产生法律判决这项单一的司法过程,而是法院,仲裁或行政机构参与的整体过程,也即制度性纠纷解决,其中并不限于法院这个单一的职能单位。所以哈特和萨克斯所指的是社会治理的整体过程,不要与通常的“司法审判程序”相混淆。与私法视域下的体系不同,法院不再是唯一的体系单位,立法,仲裁甚至行政机构也应当一并考虑。顺理成章的问题就是:在不同制度并存的情况下“谁”适合做“什么”,这里已经出现了法律制度内部结构化的理论空间。
有必要对本节内容做一番总结。以新政前后期的体系花对象来看,诸学者选择的体系单位在本体上已发生质变,绝非规范和判决等仅在表象上存在差异的逻辑单位。在私法主导的背景下,体系化对象上的趋同导致了法律体系从兰德尔到现实主义的过渡中,未能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单纯从文本上来看,哈特,萨克斯甚至富勒本人从未以“法律体系”视角对自己的理论学说进行总结,也没有明确使用“体系单位”一词。如萨默斯所言,程序学派关注体系的生理特征(physiological),并没有从静态解刨意义上(anatomical)突出法律体系的构成元素。*Robert S. Summers, Lon L. Fuller. Edward Arnold, 1984, p. 31.此处是萨默斯针对富勒的评论。法院在富勒的良序学中被视为建构社会秩序的过程,富勒从没表示过法院是法律体系建构中的理论单位。但萨默斯的如上概括显然也同样适用在哈特和萨克斯身上,普通法国家的学者很少用欧陆的抽象思维展开论述。但基于理性的重构,体系元素由规范移到了在法律整体运作过程中的不同制度参与人,这一点异常明显。法律体系在战后美国学者的眼中已不再是狭义的“规范体系”,而是由彼此相互作用的部件构成并发挥特定功能的整体。在公法的刺激和带动下,法律体系在学理上完成了根本性的革新。
四、理论提示与实践价值
我国学界对美国二战前后的法律思想已有充分探讨,但基本聚焦于形式主义,现实主义运动等历史现象。即使对富勒的研究比较成熟,也是将目光局限在程序自然法和目的解释的方法论问题上,没能从法律体系的视角来发掘这一阶段的理论资源。这种理论空缺的原因首先源自人们的感性经验:立法、法院等制度不仅泾渭分明而且早已约定俗成,不存在体系化的问题。其次,就算提出了一套有别于规范体系的制度框架,无非是精确地描述官员实际行为的普遍性特征,也不会为后续的改良工作指出明确的路标。总之,将法律视为制度体系几乎不存在进一步操作的空间。一旦将制度体系与规范体系进行对比从而剖析制度体系中隐含的应然性主张,就会发觉上述常规的看法有失妥当,因为制度结构视域下的法从评价性维度上提出了新的要求,其理论及实践意义不容忽视。
(一)制度的识别原则
上述第一个问题关涉体系单位的确认。众所周知,在规范主义的范式下,法律体系作为规范性意义的集合,法学家需要以立法文本或先例作为材料,阐释法秩序针对特定或一系列行为方式(cases, topic)预设的规范性后果。但“规范意义”不同于表述规范的“语句”,这是规范主义领域内公认的命题。申言之,同一法条可能涵盖多个规范,反过来不同法条完全可能指涉一项规范单位。就法律体系的构成要素而言,规范本身的抽象性使其独立于立法文本和司法判决等实证法材料,因此对规范的确认构成了法教义学和分析法学的恒古难题。法律规范既然作为抽象之物,如何对抽象意义的“规范单位”进行确认(identification)和逻辑个别化(individuation)自然构成了一项关键任务,既是对法律做后续体系化工作的前提条件,*[阿根廷]Eugenio Bulygin, Legal Dogmatics and the Systematization of Law, Rechtstheorie, Beiheft 10, Duncker&Humblot, 1986, S. 199.也是进一步展开体系化或融贯化的重中之重。
基于同样道理,确定某一制度的身份也绝不是凭感官经验能够化解的问题。虽然从直观上来看,法院、立法机关、行政机构和民事契约等制度不仅轮廓鲜明且自身一体,但正如法律条文不等于法律规范,作为体系单位的“制度”并不是实体意义上的存在物,而是官方机构之间,甚至官方和民事制度之间在整个法秩序中被分配或应当承担的“角色(role)”或“功能(function)”。若实现程序学派要求的划定制度权限,也即判断待决法律问题应归属于哪个职能单位最为适恰,中间必然有一个关键环节,那就是先要明确划界这些职能单位的角色。与上述规范单位的析取相对比即可看出,如何确定角色同样是棘手的问题。诚然,法院和立法机构的功能在立宪之后即告完成,但随着社会结构的复杂和情势的变迁,从法律所承担的整体目标再到不同制度的具体功能也会变得异常繁复,在这种局面下如何调整制度单位的角色?是否存在相对科学标准?这些恰恰是制度体系衍生的关键议题。对制度角色的归属问题及其与目标之间的关联,富勒的如下断言是最为恰当的概括:“一方面要保持不同制度和官员的角色不相冲突,而另一方面每项制度和角色服务的目标又异常杂多”,*Lon L. Fuller, Anatomy of law, Frederick. A. Praeger, 1968, p. 39.足以见得制度角色在体系化过程中的难度和重要性。
从实践意义上来看,规范法学旨在提供的信息决定了规范单位逻辑结构的差异。因此,规范单位的逻辑结构为凸出义务、许可或授权等价值考量,在设计上可能存在不当。比如,某一项规范结构需要涉及不同的法律部门,导致每项规范的内容过宽而有损实务上的操作性。制度单位的身份性同样存在上述问题,其对照物就是富勒以司法为例所提出的“多中心(polycentric)倾向。”*Lon L. Fuller, Forms and Limits of Adjudication, in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 Order: Selected Essays of Lon L. Fuller, Kenneth I. Winston ed. Hart Publishing, 2002, p. 126.关键的是,制度角色定位偏差的后果相比规范来说更为严重。因为现代法治社会中每一基本制度单位都有自身的特殊形式,比如法院承担的功能决定了法院在人事资格、运作程序等方面必然有别于立法机构。同时,某一制度单位不仅以特定的目的为取向,还应当以所服务的目标为评价标准,制度角色一旦分配不当远不是理论层面上的问题。在二十世纪五、六时年代,美国官方及民众经常明里暗里诱导法院承担非司法性职能,时常基于错误的司法概念将审判程序改头换面;还造成现有的、不应与司法手段相等同的其它程序也具备了司法的特征。富勒就对这种态势十分担忧,因为错误地选择实现目标的手段不仅导致司法效率低下,还会滥用真正的司法所具备的道德优势。不仅会造成理论分析偏离正轨,甚至人们会利用诸多不相关的标准来评判司法现状的优劣。*同前引〔23〕,第96页。作为现代法治国的制度载体,法院一旦难以完成应当履行的职能,要么名存实亡,要么由于作为手段的瑕疵性而丧失普遍认同,这些问题远不是在理论上后续争辩所能修复的。总而言之,必须实现制度之间科学合理的个别化安排,既避免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同时防止各职能单位承受过多且不合理的重任。就此问题虽然无法得出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但这恰恰是亟待深入研究的对象,也是将体系化对象局限在规范身上所遮蔽的重要议题。
(二)体系化的逻辑路径
本节导言中的第二个问题关涉法律体系的应然性。完整的体系学说除了重新界定体系单位之外,必须展现体系的内部结构,从而为后续的体系化提供评价性标准,因为法律秩序乃人为的创造物,放任自流不可能效果显著。因此,必须确定体系化的展开方式,这也是描述意义上的“体系”和规范意义上的“体系化”之间的差别。在规范体系中,以逻辑演绎的一致性,无矛盾性为标杆是为了清楚地看到规范集合内部是否存在规范空缺(gap),冗余或矛盾现象,以便在保持规范性内容不变的原则下为现行规范集合提出改良方案。*同前引〔1〕,第78-79页。如果说普通法或法释义学有着形式逻辑作为支撑,一旦取代了演绎式的逻辑机理, 如何探寻制度体系的“体系性”,用什么作为体系化评判标准的替代选择?从富勒对手段-目标逻辑的深化思路中,可以对该问题做出回答。
以历史脉络来看,手段-目标推理作为工具理性逻辑的表征,在现实主义运动中就已出现,程序学派对此也有所侧重。概括来讲,法律并非规范集合体(a body of norms), 而是一套工具(a body of means),由于人类的基本需求和利益派生出种类繁多目的,法律就是服务于这些目的之工具总和。*Robert S. Summers, Instrumentalism and American Legal Theor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20.但工具理性在富勒这里有两个关键的变化。首先是富勒更为强调手段-目标推理的一般性意义。其次,富勒虽然赞同手段-目标的推理方式,但指责现实主义者忽略手段的重要性。尽管目标可能十分明确,但作为手段的法律资源却不能随意调用,对手段的选择也需要理性的审慎和考量。*Robert S. Summers, Professor Lon L. Fuller’s Jurisprudence and America’s Dominant Philosophy of Law. in Essays on the Nature of Law and Legal Reasoning, Duncker&Humblot, 1992, p. 87.由于理论旨趣所限,富勒本人没有正面讨论法律体系的结构问题。但本文认为,从富勒对手段-目标的改造中可以推出,制度体系具备了自身的内在结构,这种体系性已经不再是演绎式的逻辑结构,而是表现在目的与所需要手段之间的特殊关系之中。相对于规范体系的演绎逻辑,制度体系具有和完全不同的特色,因为在手段-目标构筑的理论框架内,法律制度集合呈现出横纵两套不同的结构,为体系化提供了清晰的路标。
首先,面对特定法律问题时不同机构的角色体现了横向的结构关系,待处理的法律纠纷作为目标,会将不同的制度机构整合在一起。解决特定的法律问题不能局限于某一项制度化过程,还需同时把握不同制度的功能及其相互关联。比如民事协议仅作为一项单位,但其中除了民事主体之外还包含立法机构、法院、仲裁甚至行政机构在内,不同单位履行着不同职能。其次,手段和目标关系还有演绎逻辑所不具备的纵向等级,那就是手段之于目标的远近程度决定了不同的制度的等级结构,具体来说,与目标相隔较远的手段要受制于接近目标的那些手段。*同前引〔10〕,第64页。这种一般性的概括非常关键,遗憾的是,在富勒的著作中并未出现。仍以上述的民事制度参与过程为例,在民事主体可以自行解决争端或提交仲裁的情况下,法院在地位序列上则退居其次;而在确实需要官方机构介入的场合,行政机构有时从信息的获取或执法程序上来看明显优先于司法机关。从理论上完全可以得出,制度体系则以工具理性支撑的“手段-目标推理”取代了逻辑演绎。
如果循此路线来审视手段-目标推理,我们会发现它同时也承担了体系化的独立评价标准。就制度体系的框架而言,由于各职能单位在功能上呈互补递进的关系,在每一个过程中,不同的法律部门构成相互作用且不可分割的整体从而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效果,这正是体系化的内在要求。但法律体系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不同的制度在功能上经常会交叉或重叠,当功能自发性的程度越高而人为审慎和有计划和创造因素越少时,这种重叠的现象就愈发明显。*Karl N. Llewellyn, Law and the Social sciences—Especially Sociology, Harvard Law Review, 62 (1949)1292.以手段和目标逻辑作为评判标尺,可以尽量压缩制度角色“自发性”的空间,进一步实现各个“法律器官”在功能上的均衡效果。通过将目光由“法律”转向法律制定和实施的过程,利用手段-目标进行评价,就会洞察到制度单位在设计层面是否存在缺失,各个职能单位在功能上是否协调,从而发现法律体系效率低下的根源。如果说规范体系旨在排除规范之间的矛盾,制度体系则通过探查不同制度背后的基本目标,发现并纠正法律体系的功能缺失或障碍。*Robert S. Summers. Form and Function in A Legal System: A General Stud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312.功能缺失意味着在法律体系的运行中,某项或几项角色没有相应的机构来承担,而功能障碍表明不同角色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冲突。手段目标推理的独立性还表现在,如果存在上述病状,凭借逻辑一致性和无矛盾性是无法呈现出来的,因为制度角色与规范之间有严格的前提性关联。虽然现代法治国强调官方机构的规范性授权,但必须先行划定官方机构之间的角色。不同权属之间应有适当的关系,以使在其基础上产生的各项规范和决定能够构成一个无冲突且有效的秩序体系。*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显然,法律规范的融贯化一定程度上要依赖于法律制度结构的合理性,也说明制度体系化并不是处于理论上的附属地位。
在法学理论层面,以手段-目标结构作为体系化的逻辑路径仍有必要澄清两个误解。其一,手段-目标不是关于法律本质的断言,并非国内学者反复抵制的“法律工具主义”,而是搭建法律体系的逻辑结构。其二,手段与目标推理也不是国内文献通常提到的“法律万能论”,即以效果为重来评价法律改良社会的能力。上述两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手段-目标逻辑的体系化功效。如果据此认为工具理性有违民主、公平和正义等价值的话,那么自概念法学成熟以来,规范体系一贯倡导的形式逻辑同样由于忽略个案正义而饱受诟病。总而言之,从积极的理论启示上关照,如果规范体系在保持原初规范意义不变的情况下,利用逻辑演绎达到法律体系的完备性和一致性,那么制度体系则利用手段-目标推理,在保证宪法确定的民主、法治等目标前提下,实现不同职能单位角色上的科学性和最优化,此为体系性思维在制度设计层面的表征,同样是法治秩序建构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五、结语
法治要求政府权力分散,但并不意味着各个机构孤立而为。法律的稳健运行需要完整自洽的制度结构,需要对制度角色进行理性安排和整序。甚至可以说,法律规范的有序化取决于不同制度单位的融贯与协调。以法律体系为主线并按照公私法为时空划分标准,可以在纷杂的历史材料中看到由规范体系到制度体系的演变之路,也呈现了美国学者将理性由加诸于实定法材料移至法律制度的建构。在应然层面上,以法律制度体系为立足点不仅拓宽了体系化展开的维度,同时也说明法律职业群体作为谋划社会秩序的担纲者,对不同制度进行审慎的安排与建构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我国规则体系已完备并进入制度设计的背景下,本文期望对中国法治建设提供理论资源和概念词汇。
马斌,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1〕[阿根廷]Carlos E. Alchourrón and Eugenio Bulygin, Normative Systems, Springer-Verlag, 1971, p. 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