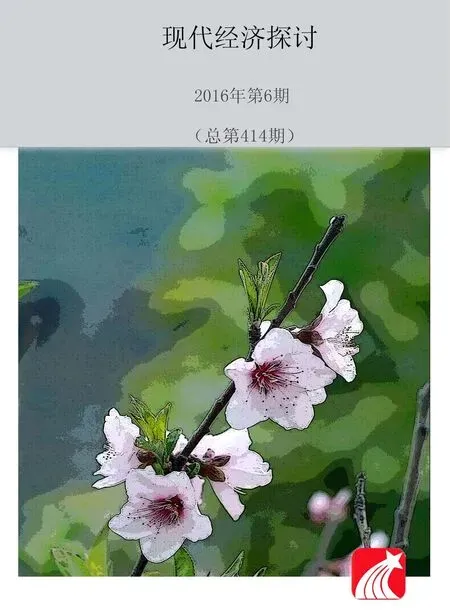论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性质
王 沁 李凤章
论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性质
王沁李凤章
内容提要:土地出让合同的性质是我国理论和实践中长期困惑的问题。我国的土地使用权出让,源于我国对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其语词源于香港的土地批租,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权力色彩,其本质上应该是行政契约而非民事契约。
出让土地使用权行政契约
关于土地出让合同的性质,在理论上存在极大争议,立法和最高法院的解释也一直摇摆。2005年6月18日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已将土地出让合同视为民事合同①我国没有区分合同和协议、契约,本文视三者为同一含义,可以互换,但在引用有关文件时,仍尊重其原有表述。。但一些地方立法却仍然坚持将土地出让合同视为行政合同。如2008年10月1日实施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93条,2012年1 月1日实施的 《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第100条等。2014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行政诉讼法修正案》,其第12条第11项规定将土地征收补偿协议视为行政协议。但该条款并没有明确指出土地出让协议的字样,土地出让协议是否构成第12条之受案范围,仍需论证。
一、举重以明轻,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是行政协议
虽然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并没有明确指出出让协议属于行政协议,但行政诉讼法的第12条明确规定了土地征收补偿协议属于行政协议。而土地征收补偿协议,本身是征收决定生效后,就补偿的数额和方式由被征收人和行政机关签署的协议。其涉及的只是货币补偿问题,仅局限于经济损失的计算,而不涉及到其他的公共利益如土地的利用方式、利用条件等。土地征收补偿协议,在过去长期以来都是按照民事协议来处理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当拆迁双方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而就补偿问题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时,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言外之意就是,如果双方达成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可以作为民事纠纷受理。实践中,也大多作为民事案件受理。现在,行政诉讼法将其明列为行政协议。如果一个单纯计算损失补偿的协议可以被认定为行政协议,那么,出让合同,其不仅涉及到经济利益,而且还涉及到土地如何利用;不仅涉及到协议双方当事人,更涉及到其他不特定主体的知情权和平等权,其更应该被视为行政协议。此谓举重以明轻②所谓“举重以明轻”,是指如依法律规定,对构成要件A应赋予法律效果R,假定法律规则的理由更适宜(与A相类似的)构成要件B的话,法律效果R更应该赋予构成要件B。。
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建立是对产权的再造
目前我国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源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探索,其制度来源是香港。
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土地国有,没有所谓的土地产权制度,更不存在市场对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土地一直都是由国家行政无偿地划拨,利用效率低下。上世纪80年代末,外商开始在国内投资建厂,必须占有、利用一定的土地,传统的无偿划拨,已经无法满足外商投资的需要。1979年7月施行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其第5条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的中资方可以将场地使用权作为出资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作为合作经营的投资,那该企业必须向政府缴纳土地使用费。至于场地使用权的性质,是债权,还是物权,并没有涉及。1980年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第12条规定,“境外客商使用经济特区土地的要交纳土地使用费。”这里仍然只是“使用”,而不是稳定的土地权利的赋予。但随着国家的日益开放,外商对稳定土地产权的需求日益强烈。特别是,随着外商在华居住的长久,他们需要购买房屋,需要较为长期的土地权利。一些立法开始采纳“土地使用权”的概念。1984年颁布的《厦门经济特区土地使用管理规定》第4条规定,特区企业需用土地,应持投资项目的批准文件和合同副本,向厦门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申请,经核配后,领取土地使用证,取得土地使用权。其第6条分别根据不同的用途,规定了不同的土地使用权的年限,比如:工交、公用事业的土地使用权年限为40年;用于商业、服务业为20年;用于金融、旅游业为30年;用于住宅的使用年限为50年;用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的土地使用权年限为60年;用于畜牧、种植、养殖业的为30年等等。当时并没有“一次性出让”的概念。但厦门的立法,已经使之成为较为稳定的产权,而非简单的合同关系。其第9条中规定特区企业或个人对经批准使用的土地没有所有权,只有使用权。而土地使用权在核定的使用期内经批准可以转让,办理过户手续后可换发土地使用证。这一规定,在内容上已经非常近似于现在的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
为什么会采纳土地使用权这一概念呢?其实,在所有权被否定的情况下,私人所能取得的占有、使用土地的权利,很自然地就被称为使用权。既然个人的土地所有权体系已经不复存在,建立在个人所有权基础上的传统用益物权体系自然也不复存在,整个传统的物权概念体系都不再适用,那么,土地占有人使用土地的权利是什么呢,最直接朴实的想法当然就是使用权。例如,1950年11月21日公布实施的《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就明确提出了土地使用权的概念。其第12条明确了废除地租,农民只需依法向国家缴纳农业税,其17条对用“国有土地使用证”来保障农民对土地使用权作了规定。
20世纪80年代末,为了适应土地有偿利用的形势要求,在所有权被禁止流转的背景下,很自然使用权就提上了日程。1988年宪法第10条第4款中除了坚持不得非法转让土地之外,还增添了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的内容。由此可见,使用权这一形态,一方面坚持了土地公有制的不变,一方面为了建立土地市场,又通过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原则,将使用权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产权形态。所以说,使用权是中国土地市场赖以建立的基础性土地财产权利,在使用权制度出台之前,土地按计划分配,被无偿划拨和使用,而使用权的出让、转让和抵押,建立了土地产权制度,使土地市场成为可能。因此,我国土地使用权绝非大陆法系的用益物权,而是“借助土地使用权实现土地的物权化、市场化配置。也就是说,在我国,土地使用权充当着基础土地物权的作用。”很早就有学者认识到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对其后转让的作用。“土地能够作为商品进入市场,起点在土地所有者出让使用权,这在我国通称一级土地市场。而另一个层面是土地经营使用者之间转让使用权,通称为二级土地市场。”到了今天,在集体土地上主要有承包经营权①承包经营权,虽然由于其发端于农村的家庭承包经营,而冠以承包经营权的名称,但其本质仍然是基于集体土地所有权而设立的基础性农地物权,所以,《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条才开宗明义地强调其立法宗旨是,为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在国有土地上主要有出让土地使用权、划拨土地使用权。
三、从“出让”一词的溯源看出让合同的性质
现有法律将出让视为一种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方式,和划拨并列。但是,划拨是一种单方的行政决定,表明的只是一方对自己财产的调配或者分配。至于这种调配或者分配,是否以及将为土地使用人创设何种权利,并不涉及。而出让,《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7条的定义,虽然存在着同义反复,但其强调的是,这一行为的结果是将土地使用权从所有权人那里拿出来,转移给了受让人,即结果是发生了物权的变动。那么,凭什么发生这种物权的变动呢?具体的行为方式是什么?这一概念并没有交代。实际上,与划拨这一行政机构的单方决定无偿授予土地使用权不同,出让强调的是国家作为所有权人和受让人通过合同方式,有偿地将土地使用权移转给受让人。而合同条款,包括价格、主体等的确定,则采取了“招拍挂”的方式。可见,所谓“出让”,从方式上讲是“招拍挂”缔约,从结果上讲是将有期限可以依法转让的土地使用权从所有权中分离让与给使用人。如果将“出让”界定为权利的移转,那么,划拨也是“出让”,只不过由于划拨没有对价,不是“招拍挂”缔约,划拨所“出让”的土地使用权具有特殊性,包括主体特定化为公共机构,权利只能服务于特定公共利益目的,因此土地使用权不可交易等。同样,在集体土地上宅基地使用权的分配也是无偿“出让”,只不过只能“出让”给本村的村民用于建造自住房,且不能转让。而承包权,也是如此。概言之,出让,作为使用权从所有权中分离的结果,强调的是使用权被让与给受让人,只不过由于不同的方式和条件,所让与的权利被赋予了不同的内容。如此,现有的土地使用权类型,就应该根据权利内容的不同加以区分和命名。例如,现有出让土地使用权,应该被叫做自由性有期限土地使用权;划拨土地使用权则因为主体特定,服务于特定主体的特定目的,可以称之为人役性土地使用权。与此类似,宅基地使用权也是服务于特定主体、特定目的,且没有时间限制的人役性土地使用权。而承包经营权,则不但具有人役性,而且,还具有时间的限制,可以称之为人役性有期限土地使用权。所有这些土地使用权的设立,都是使用权从所有权向土地使用人的“出让”。
上述分析只是在语义分析基础上的简单结论,说明“出让”作为权利变动这一结果,是国家和集体在保持公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将土地财产权以使用权的形式赋予给个人和社会组织,是对土地财产权的再造,适用于各类土地使用权。那么,这种“出让”的制度内涵是什么?还要进一步从语词溯源角度加以分析考证。
我国的土地有偿出让制度,源于对香港土地制度的继受。当时无论是深圳还是上海,具体土地出让方案的设计者都是香港专家。就深圳来说,1986年11 月17日,深圳派出了房地产改革赴港考察团,在为期10天的考察中,考察团先后拜访了当时港英当局的各相关部门;与各届专业人士进行了座谈;观摩了一次大型的官地拍卖会;现场考察了香港的诸多地产项目——最终在1986年12月28日向市委、市政府提交了一份 《深圳市房地产改革赴港考察报告》,到1987年7月,在这份考察报告的基础上由市委政策研究室、市政府基建办公室联合草拟的《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体制改革方案》提交至市委、市政府。改革方案提出了“所有用地实行有偿使用,协议、招标、公开竞投”的基本制度设想。这样,1987年9月10日,深圳市首次以协议方式有偿出让土地,从而开创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土地产权制度的先河。就上海来说,其最初的方案设计也是先到香港考察,并邀请香港的专家起草方案,最终在1987年11月29日出台了《上海市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办法》,并在1988年8月成功出让虹桥地块,打开了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新的一页。那么为什么会选择香港模式呢?按照当时负责设计方案的蒋如高的说法是港英政府的土地制度是所有权归英王,而在土地的使用受到明确限制和严格管理下,使用权可以有限地出让。而我国土地所有权也是国有的,不能转让和出卖,因此香港土地管理模式非常适合我们借鉴。参照香港模式,土地所有权国有,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不同的年期和实际用地情况,有偿使用或有偿出让。
如果明确了我国的制度源于香港,那么,对于“出让”一词,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考察其词源。首先,在英语中对应的这一词语是什么?对此,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三规定:All leases of land granted or decided upon before the entry into force of the Joint Declaration and those granted thereafter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2 or 3 of this Annex,and which extend beyond 30 June 1997,and all rights in relation to such leases shall continue to be recognized and protected under the law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①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三的中文官方表述是:《联合声明》生效前批出或决定的超越1997年6月30日年期的所有土地契约和与土地契约有关的一切权利,以及该声明生效后根据本附件第二款或第三款批出的超越1997年6月30日年期的所有土地契约和与土地契约有关的一切权利,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继续予以承认和保护。。这一类似的表述并且体现在香港基本法的第120条。可见,对于土地使用权,香港使用的语言是“leases”,“lease”即租赁,而用了“leases”复数形式,说明这一“lease”不止一种,包括了各类不同条件、不同期限的lease。但是,就支配这一权利的动词来说,都统一使用“grant”。那么,“grant leases”,在官方文本的中译又是什么?可见上述leases被翻译成土地契约,即租契。而“grant”被翻译为“批出”,并且在grant和decide upon(决定)之间使用的是“or”,而非“and”,可见,“decide”和“grant”之间,并非并列关系,更准确地说,“or”后的词语应该是对 “grant”换一种说法的解释。可见,“grant”本身即带有明确的有权力一方的决定的含义,所谓“批”,非批量之“批”,而是批准之“批”也。根据Black法律词典的解释,“grant”的含义主要是give、confer、permit或者agree、approve、warrant或者order,都含有权力者的许可、授予、批准之意。即使包含了不动产转让的意思,这种转让也强调是正式的转让,而且,其主要适用于“feoffment”,即采邑的授予。可见,“grant”,主要是国家或者上级权力者对社会成员财产权的批授。而转让则大多是平等的主体之间财产利益的完全转移。至于平等主体之间的出租,更是直接使用lease的动词形态即可。这一点,从对香港grant一词的进一步溯源和比较中,即可看出。
回归之前的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除了新界适用中国的习惯法之外,继受的是英国的普通法。作为殖民地时代香港基本宪法文件的英皇制诰(Crown letters patent),在第13节中,明确授权总督可以代表王室批授土地(保有权),并且对王室已经依法做出的土地批授或处置 (契约)予以履行①原文是“The Governor,on Our behalf,may make and execute grants and dispositions of any lands within the Colony------”。。其同样使用了“grant”一词。而根据英国普通法原则,其土地权利体系是所谓土地保有(land tenure)制度。自威廉征服以来,英国就建立了土地保有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国王拥有全部土地的所有权,而将土地保有权批授(出让)给其属下的封臣。封臣再把土地保有权向下级封臣批授,从而形成了领主和各级封臣之间土地保有权批授的金字塔体系。很多著者在表述这一制度安排时,都使用了grant一词。例如Adrian J Bradbrook在谈到保有原则时说:“The Crown retained absolute ownership of the land for himself and granted rights over the land to the grantee fulfilling particular duties and conditions.”5p187Benaiah W.Adkin也曾写道:“No absolute ownership of land was possible,except by the king.The person to whom the lands were granted by the king held under him a fee,whereby in return for their right to hold their land,they undertook to be faithful to the king and to render certain services to him.”6p8在英美法传统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国家的“出让”也使用“grant”。例如在澳大利亚South Australia殖民地,总督WM.F.Drummond Jervois曾签署1877年88号法案,明确规定:The grant in fee simple of any land in south Australia heretofore granted or hereafter to be granted shall be construed to include and to convey to the owner in fee simple for the time being of such land the absolute property in all mines and minerals。而美国联邦政府为了支持铁路建设向铁路公司出让的土地保有权(fee simple)也使用“Grant”一词。当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批授(出让)的主要是自由保有(freehold或者fee simple)不同,香港批授的主要是租赁保有,所以被简称为批租(grant leases)。
出让土地使用权,只不过是香港的批租(复数)而已,即批授对土地的租赁保有。这一点,在大陆引进制度后长期使用“批租”一词的表述上也可以看出。戚名琛指出,“土地批租制度”是英文“The land leasehold system”的香港译法,意思是“批租只涉及土地的使用权,业主取得和能转让的也只是某一块土地在一定年限内的使用权,不改变土地的所有权。田莉也认为:“大陆和香港以及英联邦的一些国家地区,采取的是同一类土地权利体系,即土地归政府所有,但政府以一定的使用年期将土地(leasehold)批租给个人和企业。”当时亲手设计操作方案的很多老人,例如1986年亲身参与了上海市土地有偿使用的决策以及第一块土地出让试点,时任上海市土地批租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蒋如高,曾任上海房地资源局副局长的殷国元等,都认为使用权出让就是批租。以至于有学者在出让制度实施多年后还慨叹:“在8年前既已被法规明确规范使用的出让一词,至今仍然被港语土地批租所取代——不仅在报刊文章里,而且还出现在政府文件里。”甚至建议恢复“批租”的使用。
另一方面,在一些地方立法中,在建立“招拍挂”制度出让土地使用权之前,也有使用“批准”设立土地使用权的。例如 《厦门经济特区土地使用管理规定》(1985)的第9条,虽然有使用权的概念,但其设立使用权的表述方式是“批准”,一般称为“经批准使用的土地”。
总之,考察“出让”一词的历史原意以及使用情况,所谓“出让”,只不过是批准让出而已,即批准将土地的使用权从所有权中分离,授予用地申请人,其本质是国家公权力的运用,而非财产权的经营。
四、结 语
综上所述,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乃是行政合同。出让不是平等主体间的财产权转移,而是权力者对其领土范围内的社会成员批授财产权。批授的主体是公共权力主体,只不过其赖以批授的基础,是其对土地的所谓“所有权”。因此,土地使用权出让,就不是地上权的设定,而是财产权从无到有的创设。从受让者的角度来说,其取得的是基础物权,就像英美法中的土地保有权一样。从出让者的角度来说,其也不是作为一般的民事主体或者一般的地主而出让土地,不能以谋取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而要考虑到作为公主体其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例如为普通公民提供基本的居住保障,以及保障财产权授予对普通社会民众的机会开放等。相应地,有关国家违反土地出让合同的救济,也就应该纳入行政诉讼,适用一般公法的救济。
1.高富平:《土地使用权的物权法定位》,《北方法学》2010年第4期。
2.戚名深、张瑜:《中国城市的土地批租》,《城市问题》1989年第3期。
3.深圳市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深圳土地革命——回顾深圳土地管理20年历程》,《国土资源通讯》2006年第19期。
4.饶斌、刁娅君:《上海第一块土地批租的前前后后——蒋如高老人的回忆》,《中国土地》2008年第3期。
5.Adrian J Bradbrook,Susan V MacCallum,Anthony P Moore,Australia Property Law,Cases and Materials,Sydney:Law book Co,2003.
6.Benaiah W.Adkin,Copyhold and other tenures of England,London:Estates Gazette ltd.,1907.
7.John Bell Sanborn,Congressional Grants of land in aid of railways(1899),The bulletin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E-conomies,political science and History series,Vol.2,No.3.
8.戚名琛、刘正山:《对土地批租制度批评意见的批判》,《中国房地信息》2006年第2期。
9.田莉:《土地有偿使用改革与中国的城市发展——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共土地批租制度的启示》,《中国土地科学》2004年第6期。
10.徐聪:《批租与出让的选择》,《中外房地产导报》1998年第8期。
11.宋亚平:《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建设》,《理论探索》2015年第1期。
12.高宏伟:《农业生态安全视角下的农村土地流转分析》,《经济问题》2015年第2期。
13.黄健元、潘付拿:《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安置的局限与出路》,《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责任编辑:吴群]
F301
A
1009-2382(2016)06-0084-05
王沁,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生;李凤章,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上海200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