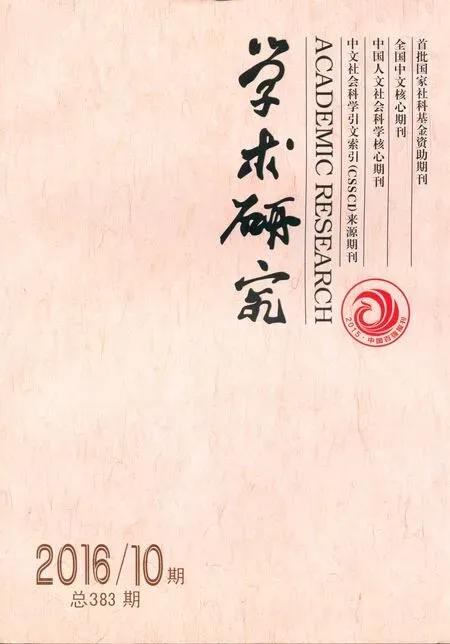汉斯·卡斯托尔普的美学教育:论成长小说《魔山》*
[德]佩德罗·卡尔德斯[文] 赵培玲[译]
历史学
汉斯·卡斯托尔普的美学教育:论成长小说《魔山》*
[德]佩德罗·卡尔德斯[文]赵培玲[译]
在本文中,笔者对托马斯·曼的《魔山》作为一部成长小说进行了批判性的思考。弗兰克·莫莱蒂(Franco Moretti)认为成长小说这种形式象征着现代性,因为正是在成长小说中青年时代被赋予现代所特有的那种活力和不稳定性,以至于成为整个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青年人的经历或许是在一战后消亡的众多事物之一,正如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其著名的《经验与贫困》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经历的显著特征就是感觉自己失去了建构意义的能力。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塑造一个像汉斯·卡斯托尔普(虽然他生活在一战前)这样一个青年角色本身已经包含着对作品形式的一种挑战。何种语言才能适合在那个特定历史时空中完成对一个青年角色的塑造呢?汉斯·卡斯托尔普有别于查尔斯·狄更斯笔下的皮普,以及巴尔扎克笔下的吕邦泼雷,因为他既没有顺从于命运也没有自我毁灭,而是愿意让自己接受美学教育,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一个成长小说的主角。
历史文化魏玛共和国成长小说托马斯·曼
驱使笔者研究托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年)所著小说《魔山》(The Magic Mountain)的原因,并不全是长久以来阅读这本书带来的快乐。坦白地说,第一次接触这部鸿篇巨著时,它没能像作者的其他作品那般吸引笔者,如《布登勃鲁克一家》、《魂断威尼斯》、《托尼奥·克律格》等。然而若干年之后,这种不冷不热的感觉却被一种激情所代替。笔者发现,如果不是读了弗兰科·莫莱蒂所写的关于19世纪欧洲成长小说的研究著作《如此世道》,[1]笔者是不会认真反思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阅读体验的。
笔者无意贬低他人的相关研究,①参考这些书目可以获得关于这个问题的更多知识:JACOBS, Jürgen. Wilhelm Meister und seine Brüder: Untersuchungen zum deutschen Bildungsroman. München: Wilhelm Fink, 1972; MAAS, Wilma Patrícia. O Cânone mínimo: O Bildungsroman na história da literatura. São Paulo: Editora UNESP, 2000; MAZZARI, Marcos Vinícius. Labirintos da aprendizagem: Pacto fáustico, romance de formação e outros temas de literatura comparada. São Paulo: Ed.34, 2010; SELBMANN, Rolf. Der Deutsche Bildungsroman. Stuttgart: Metzler, 1994, 2a.ed他们中不乏质量颇高的研究成果,但在随后阅读《魔山》的过程中,脑海里一直回响着莫莱蒂的诸多篇章和观点。重读《如此世道》时,恨不得读完书中提到的所有小说,为的是穷尽一切可能改进自己对《魔山》的阐释。
在《魔山》开篇几页被作者称为“前言”的部分中,我们已经能读到作者尝试着从美学角度对魏玛共和国危机进行阐释,①在阅读关于美学体验的演讲稿时,我意识到《魔山》开头章节中存在三种美学经验的维(按照汉斯-罗伯特·姚斯的定义),它们分别是创制(poiesis)、净化(katharsis)、感知(aisthesis)。参考汉斯-罗伯特·姚斯Pequeña apología de la experiencia estética. Barcelona: Paidós, 2002.其中创制体现在托马斯·曼采取的从战后叙事者的角度叙述战前的人物的叙事策略,感知体现在读者的理解过程,据作者称,读者需要花费至少7天,长则7个月的时间来理解这部小说,净化同样是小说的重要主题,小说在开头就指出战后的读者可能对这种故事不会产生太多兴趣,因为战争“还没有完全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详见MANN, Thomas[1924]. Der Zauberberg: Roman. Grosse kommentierte Frankfurter Ausgabe.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2002, pp.9-10.作者意识到叙事者的艰难:他是一个“用过去式喃喃自语的魔术师”;[2]当现在与过去的联系如同铜器上的铜锈一般被擦除后,出现了能让人体会到一个可怕的深刻变化的空间时,他必须勇敢面对因此所带来的历史性转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和其他倾心于揭示战争体验的作品相比,《魔山》拥有至少同等、甚至更多形式上的丰富性,很遗憾瓦尔特·本雅明没能在他几年后的著名论文《经验与贫穷》②值得注意的是,瓦尔特·本雅明在1925年4月一封给索伦·舒勒姆的信中表达了对这部小说的欣赏,尽管在此之前他对托马斯·曼怀有浓厚的敌意,参见他在一战期间写的散文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 BENJAMIN,Walter. Briefe I. Org. G. Scholem e T. W. Adorno. 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1978, p.377. apud NEUMANN, Michael. Der Zauberberg: Kommentarband. Grosse kommentierte Frankfurter Ausgabe.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2002, pp.113-114.中提到这部小说。
《魔山》的主题,正如它开头声明的那样,是“汉斯·卡斯托尔普的故事”,[3]是他“发生于很久以前”的故事,虽然按照真实时间并非如此。一个“事件从未停止过开始”[4]的时间框架能给叙事创造诸多可能性,但对角色构建提出了难题。出于这个原因笔者才特别关注一个“普通年轻人”的角色刻画,并进一步考察文学,尤其是成长小说所展示出来的“在人们的生活和意识上留下的深深的裂痕”。[5]这在《魔山》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莫莱蒂的许多洞见之中特别让笔者感兴趣的是,他将19世纪欧洲成长小说定义[6]为年轻男性主角体现的一种象征性的现代性。莫莱蒂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来定义现代性:“一个永恒的革命状态,它将传统积累的经验视为无用的负担,因此这种状态将不能由成年,更不能由老年来表现”,[7]而青年就其本质来说是短暂的,在形式上与这种定义相对应。这种青年经验清晰地在成长小说所刻画的主角的矛盾性中凸显出来。根据莫莱蒂的观点,这种矛盾性基于分辨与变形的原则。③莫莱蒂声明这些观念来自罗特曼,出自弗兰科·莫莱蒂:《如此世道:欧洲文学中的成长小说》,伦敦:沃索出版社,1987年,第7页。这样一来,成长小说的特征可以归纳为将结尾处叙事行为本身悬置,年轻的主人公终于与那个处处限制他的种种欲望的世界握手言和,将最初的狂喜与后来的幻灭折衷后形成了一个整体认识。但是成长小说也可能拒绝这种调解,在这种情况下故事的核心不在结尾,而在叙事行为本身,成长被描绘为纷繁复杂、无穷无尽的体验,作者只能以一种随心所欲的方式结尾(司汤达、普希金、巴尔扎克、福楼拜在这方面都具有代表性),且在多数情况下会毁灭他们的主角。
《魔山》的主题和成长小说的主题相吻合:对于19世纪的成长小说而言,年轻主人公的故事是标准的主题,但对于托马斯·曼而言,这个主题仍是个问题。除了对这一文学体裁形式是如何经久传世的进行学术研究之外,笔者认为研究如何以新的方式敏锐地把握历史感会更有意思:④想要了解Bildung这个词如何在小说中出现,见SCHARFSCHWERDT, Jürgen. Thomas Mann und der deutsche Bildungsroman: Eine Untersuchung zu den Problemen einer literarischen Tradition. Stuttgart; Berlin; Köln; Mainz: W. Kohlhammer, 1967, pp.146-149.关于《魔山》是否属于成长小说的问题,迈克尔·纽曼作了简要而充分的讨论,参见NEUMANN, Michael. Ein Bildungsweg in der Retorte: Hans Castorp auf dem Zauberberg. Thomas Mann Jahrbuch, Bd. 10,1997, pp.133-135.如何写一部关于生活在“开头从未终止过”的时间框架里的年轻人的小说?
重大的变化不仅仅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我们在托马斯·曼写于一战之前的这部作品里也可以发现这种重大的变革。但是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像汉斯·卡斯托尔普那样的年轻角色。在《布登勃洛克一家》中,青年一直处于缺席的状态,并且随着汉诺·布登勃洛克的早逝而被排斥在外。《殿下》中年轻的王子克劳斯·海因里希身为贵族,无须遵从中产阶级对于发展、改革和进步的要求。①Jürgen Scharfschwerdt 细致地分析了托马斯·曼和成长小说流派之间的各种关系,尽管有时候超越了托马斯·曼本人在散文书信和日记中记录的作者用意。他对成长小说的逃离疲劳,经历自我肯定,最后在模仿中重获活力的故事线索相当具有洞察力。参见SCHARFSCHWERDT, Jürgen. Thomas Mann und der deutsche Bildungsroman: Eine Untersuchung zu den Problemen einer literarischen Tradition. Stuttgart; Berlin; Köln; Mainz: W. Kohlhammer, 1967, chaps. I and III.即使在《魂断威尼斯》中,塔基欧虽然比汉斯·卡斯托尔普年轻许多,却只是一个超脱世俗之美的象征。即使在托尼奥·克律格那充满艺术气息的自负中我们也难以看到他会有朴实无华的卡斯托尔普的影子。这样一来,因为“青年是现代性的实质,是一个在未来,而不是在过去,寻找意义的世界的标志”,[8]我们不免提出疑问,《魔山》的主人公能够像19世纪成长小说的典型主角那样传达这种象征力量吗?准确地说,我们的问题是,汉斯·卡斯托尔普是否对寻求意义本身感兴趣。
一、世界
人们不仅仅以个人身份生活,而是不知不觉地与他的时代和同时代的人同呼吸,共命运。人们可能认为他生活中那些一般性的,非个人的基础已牢固地奠定,同时把它们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对它们一点儿不抱攻击、批判的态度,像善良的汉斯·卡斯托尔普那样。但有一点也是很可能的,即人们同样也察觉到时代的笔名,从而多少有损于自己道德上的完美性。个人各式各样的目的、目标、希望、前景都在眼前浮现,使他从中获得奋发向上、积极工作的动力。如果不属于他个人的,亦即他周围的生活(甚至是时代本身)外表上看来哪怕多么活跃而富有生气,而骨子里却十分空虚,没有什么希望和前景;如果他私下承认它既无希望又无前途及办法,同时对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提出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问题是人们费尽心机在最终的超乎个人至上的绝对意义上提出的)报以哑然的沉默,那么对一个较为正直的人来说,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使他趋于消极而无所作为,开始时只是表现在他的精神上和道德上,后来就一直扩展到他的生理和机体部分。在一个不能满意地回答“人生目的何在”的时代里,凡才能卓越、成就出众的人,不是道德上异常高超——这是很少见的,而且不失为英雄本色 ——,就是生命力极其旺盛。上述无论哪一种品质,汉斯·卡斯托尔普都不具备,因而他可算是个“中不溜儿”的人,尽管我们是从崇敬他的角度说这话的。[9]《魔山》中叙事者的这些字句让人想起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acs)曾将小说定义为一种超验流放的形式;但是在托马斯·曼的小说中的这段话中,读者并没有发现“个人目标、目的、希望、观点”与冷漠无情的世界之间的矛盾。对于托马斯·曼来说,“个人生活”叙事(一个由被挫败的梦想组成的内在人格的成长)并不足以建构他的主人公。这样一来,即使一个平庸的普通年轻人也会被“绝对基础”的危机所影响,即使这个角色从未尝试脱颖而出,从未尝试将他自己与这个世界和世界对他的期望区分开来以便质疑他的生活的那些显而易见的自然基础,他也至少拥有展开生活轨迹的冲动。在这部小说中,这种生活轨迹是由作者来讲述的。
故事由一段旅程开始,其起因平淡无奇,是过度劳累导致的精疲力竭。作者决定以卡斯托尔普渴望休息作为开头,因为出于某种原因,他的“身体和生理”处于非常虚弱的状态。我们接着读到一个年轻人离开他的出生地,位于德国北部的汉堡,去往瑞士阿尔卑斯山区的达沃斯,在那里他会拜访正在贝格霍夫疗养院治疗肺结核的表哥约阿希姆·齐姆森。在这段旅程中,叙事者展示了年轻人精神上的转变,“涉世未深”,[10]并且因为这个原因“可能会从书呆子和乡愚一下子变成流氓之类”。[11]于是,这部小说展现了弗兰科·莫莱蒂眼中19世纪成长小说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即角色的成长不是经过一个漫长的学徒生涯或者家庭教育完成的,而是借助于旅程、冒险和波希米亚式的生活[12]中的不确定性和危险经历,使得年轻人摆脱种种陈规陋俗而根据自己对世界的体验来构筑个人独有的视角。
然而,在效仿成长小说这种主人公角色的时候,作者做了变通,①除了Scharfschwerdt以外,曼弗雷德·瑟拉的研究也将《魔山》视为对成长小说的戏仿,参见曼弗雷德·瑟拉:Utopie und Parodie bei Musil, Broch und Thomas Mann: 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 - Die Schlafwandler - Der Zauberberg. Bonn: Bouvier, 1969.卡斯托尔普踏上旅程的动机不同于19世纪作品中主人公身上常见的对于变革的渴望。汉斯·卡斯托尔普并不想经历奇遇和危险,即使在乘坐火车从德国北部到瑞士阿尔卑斯山脉的这一段旅程中,周围环境也被描绘成越来越具有敌意。深渊和险峰在敏感的汉斯·卡斯托尔普眼前交替出现,以至于他期望一旦抵达贝格霍夫,新的环境将秩序井然,他就能毫不费力地适应。[13]最开始,地理位置的转移只是两段平静生活中的一小段插曲,一边是每日规律的劳作,另一边是单调乏味的康复疗养。他希望旅途的动荡会逐渐被后来的日常生活平复。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将旅途作为核心主题这一点与19世纪小说类似,然而出发旅行的动机却截然不同,譬如《幻灭》的主人公卢西·得·吕邦泼雷搬家到巴黎是出于自我证明的强烈愿望,而汉斯·卡斯托尔普完全没有这种改变自己生活的愿望。
他登上火车纯粹是因为已经在贝格霍夫疗养了五个月的表哥要求他前去看望,同时希望从疲劳中恢复过来。本来打算只呆三个星期,到最后却停留了七年。和向往伦敦巴黎这样的大都市的动机相比,这两个目的要朴实得多,它们也揭示了主人公的性格特点。尽管这里“极度自我的根基”难以掩盖其裂缝,主人公还是自然而然地跨过了这些裂缝。如果在19世纪的成长小说中通往过去的桥梁被烧毁了,那么汉斯·卡斯托尔普依然能通过这些桥梁,仿佛它们牢不可破。这样一来,便不难理解为何汉斯·卡斯托尔普在到达达沃斯之后受到了一个家庭成员的热烈欢迎,这让我们在主人公身上看到的不是他对原社会关系的自愿放弃,而是一种错位,这种错位得以保留汉堡与达沃斯的一缕联系。由于齐姆森是主人公的亲人,这里有必要谈谈《魔山》中主人公的家庭背景,从中我们或许能找到笼罩着角色的冷漠氛围的些许踪迹。
主人公童年经历的突出特点大约就是他年仅七岁便成为孤儿;在双亲去世后,汉斯·卡斯托尔普曾经被祖父汉斯·洛伦兹·卡斯托尔普照看过一年多的时间。但是这段短暂的时间已经足够让这位“生命力极为旺盛,不会轻易倒下去”[14]的老人,成为他连接过去的唯一的(也是腐朽的)纽带。他对老卡斯托尔普非常感兴趣,在可听见德语方言的那所老房子里,200年以来卡斯托尔普家族受洗的洗礼盆对他具有神奇的吸引力。叙事者描述了这套洗礼盆和暗淡无光的银碗,在其中可以看见过去的碎屑、时间的锈迹以及某一位祖先的象征,汉斯·卡斯托尔普对于这个人的认同超过了他对自己父母的认同。但与此同时,老人很难为孩子提供一个可供效仿的成长的榜样,因为他是一个已彻底死去的时代的残骸。当叙事者讽刺地描写[15]在过度隆重的葬礼中,一只苍蝇停留在汉斯·洛伦兹·卡斯托尔普的尸体的前额上并抖动着它的口器的时候,作者似乎在暗示早年丧失双亲是作为历史经验载体的《魔山》中主人公的重要特征。
在老人死后,汉斯·卡斯托尔普转由叔祖父天那珀尔领养,他对这个年轻孤儿的关心完全是从管理的角度出发的。天那珀尔只专注于管理卡斯托尔普家族的财产(并从中每月抽取一部分作为这项工作的酬劳),和孩子的关系一直很疏远,以至于两人之间的矛盾大到改变了汉斯人格的地步。如果说这部作品刻意避免了什么的话,那就是通过否定和代沟来建立认同的策略。天那珀尔给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唯一建议是他应该找一份工作来维持自己的体面生活。于是,年轻人决定成为一名船舶工程师,这在汉堡这样的港口城市并不奇怪(同时也源自他长时间以船只为题材进行绘画的爱好),[16]他就像马克思·韦伯描述的那种人:[17]能够镇定自若地穿梭于未知的世界,所需的技术能力(比如船舶工程学)任何人只要肯下功夫就能学会。家庭代表的过去与城市的环境对于汉斯·卡斯托尔普而言并不像一个负担:“这个有民主气息的商业城的上层统治阶级,将高度文明赐给它的孩子们,而汉斯则悠闲而不失尊严地将这种文明承载在自己的肩上。”[18]现代性一直寻求摆脱过去的重负,从这个角度来看卡斯托尔普很难说是现代性的象征。如果对于很多人来说文明是一个负担,或者一团急于甩掉的碎布片,那么卡斯托尔普既无需拒绝又无需刻意遗忘,因为文明跟他毫无瓜葛。
于是汉斯·卡斯托尔普就被描绘成“一张一尘不染的白纸”。[19]他之所以是一张白纸,是因为,如果他是一个政治人物,他既可能成为保守派(从他对祖父的认同来看),也可能成为激进派(作为一个工程师,其从事的行业与技术进步密切相关)。不仅如此,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已经23岁,却并未寻求与世界作对,也不想通过工作来获得自立,即使在没有失业的时候,他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更愿意花时间来抽自己最喜欢的牌子的香烟:“他生活中所谓的工作,只是和无忧无虑地享受一支马丽亚·曼契尼雪茄烟相距不远的一种观念罢了。”①托马斯·曼:《魔山》,第45页,关于这部小说中的主题参见:HEFTRICH, Eckhard. Zauberbergmusik: Über Thomas Mann.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75, pp.57-64.事实上,他只有在自己无所事事[20]时才觉得完全健康。因此他几乎是一个抽象的角色,读者很难对他产生任何认同和期待。这样一来,他是一个平庸的人,[21]尽管小说的叙事者暗示这个贬义词并不含有对角色的负面评价。因此, 笔者认为汉斯·卡斯托尔普既不是一个直面混乱世界[22]的怀疑者,但他也不完全遵循前代人灌输给他的价值观,对于他来说,这个世界上除了“自我实现的阻碍”之外的确还有其他东西。
二、象征
但是,汉斯·卡斯托尔普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于是,他的平庸便不仅表现在缺乏投身世界的愿望,也表现在没有面对冷漠无情的世界的能力,或者更准确地说,没有面对他实质上是个孤儿这一事实的能力。尽管在对待冒险的态度上汉斯·卡斯托尔普与威廉·迈斯特、于连·索瑞尔和卢西·得·吕邦泼雷截然不同,但他并不满足于日常工作的琐碎,在这一点上,根据莫莱蒂的观点,[23]他类似于19世纪成长小说的主人公——最终拒绝任何形式的工作。另一方面,当我们考虑到托马斯·曼曾经描写过的托马斯·布登勃洛克这个勤奋的商人的疲惫与哀伤,以及古斯塔夫·冯·奥森巴哈这个作家对自己的苛刻要求,我们会意识到作者无法以同样的方式来描写卡斯托尔普,因为他无法失去他从未拥有的东西:理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理解卡斯托尔普对奋斗的反感不仅仅是一种波西米亚式的对于劳动的批判,而且还是一种身体的病态。
从作者的语言来看,我们可以说汉斯·卡斯托尔普感受不到文明重负压肩的痛苦;在任何意义上他都不是那种因过激行为导致自我伤害的悲剧性角色。此刻,笔者回忆起莫莱蒂关于19世纪成长小说中个人成长与历史进程的分离的论述。对于他来说——此处巴尔扎克是最典型的例子——小说通过打消“个人会随同社会发展一起进步”的幻觉,从而达到其明确的批评功能,对于莫莱蒂来说,在《人间喜剧》中我们认识到变革的必然性,[24]历史进步的车轮会直接碾过那些阻挡的人。在《魔山》中读者也能感受到个人和他者之间的鸿沟,但是作品又揭示:即使对于那些无意对抗世界的人,这个鸿沟也在消弭。肺病感染不仅阻止了个人抱负的实现,还剥夺了个人身体正常活动的能力,这其中就包括了汉斯·卡斯托尔普,尽管他曾经能够在周围环境中感到自在舒适。
因为《魔山》的开头描写一个年轻人踏上寻求休憩的旅途,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强迫的停滞——这是对《浮士德》开头,“从一开始就是行动”的有趣的、颇有讽刺意味的颠倒。而汉斯·卡斯托尔普面临的停滞则来自疗养院的顾问大夫贝伦斯的诊断,[25]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是如此:在返回汉堡的前夜(计划的三个星期时间已经到了),卡斯托尔普因为发烧接受检查,随后被告知汉堡的潮湿天气会让目前的发热恶化为严重的疾病,因此即使他要返回德国,也只能去贝格霍夫。接着医生又强烈建议他在疗养院住下来,以避免病情恶化。在这种尴尬处境下,如果他离开,就必须返回旧宅。这样他还不如留下来的好。
卡斯托尔普到阿尔卑斯山的一段平淡无奇的旅行,虽然尚未能让主人公完全脱离平庸, 但也从一开始就带着某些不适应。值得思考的是:适应疗养院单调重复的日常生活对一个耐心的人[26]来说不是件难事,不出两周他就会和开始达沃思[27]旅行之前的生活分离开来。然而如上文所提到的,一种不安还是在这个平庸的青年身上体现出来:已经快要到达贝格霍夫时,汉斯·卡斯托尔普觉得不太舒服,他最爱的马丽亚·曼契尼牌香烟抽起来就像皮革一样。[28]他的不安通过身体展现出来,也正是这具身体展现出生命的脆弱性,就算是那些从未对自己的身体怀疑过,从来都是顺其自然的人也看到了这种脆弱性。卡斯托尔普内心空虚,实际上只是一具肉体,它不断加速、越来越剧烈的心跳告诉他,他对俄国女人克拉芙迪亚·肖夏[29]多么痴情。
年轻人这张白纸只是一具肉体,这与教导汉斯·卡斯托尔普[30]的意大利激进知识分子兼共济会成员鲁多维科·塞塔姆布里尼口中的人文主义概念形成了强烈对比。塞塔姆布里尼这个启蒙时期思想家奇怪的缩影,认为每个年轻人都已经是一张写满了字的纸,要靠教师来擦除错误以塑造成理想的人。在重病中,塞塔姆布里尼说年轻人处于尚未定义完全的状态,[31]因此容易受到各方面的影响。问题是,他怀着教学信念,认为年轻人还有进行建构的可能的时候,却没能意识到被潦草地涂满、等待着别人来修饰抛光的那张纸完完全全是一张空白纸,纸上没有前人的影响、没有任何传承的文化,也没有外部世界作用的痕迹。只有一具被压抑着的躯体,透过疗养院薄薄的墙壁听到了隔壁房间[32]夫妻亲热的声响,它试图掩盖自己的羞耻,也并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对。疗养院的心理分析师克罗科夫斯基博士却观察到,正是在这具压抑的身体里,“贞洁和爱情”[33]这两种力量在斗争着,且以前者的胜利告终。但胜利品却是疾病缠身,因为据分析,疾病本身就是变形的爱情。[34]这种停滞不仅仅表现在浪费了宝贵的时间,无法创造商品和财富,还表现在另一种无能:总是把自己看成是他者中的影像,无论这个他者是一个观念,一个人,还是一个轮廓。
对于卡斯托尔普这样的中产阶级①更多关于中产阶级角色的塑造问题请参考奥尔格·卢卡奇关于托马斯·曼的古典学研究(那时他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LUKÁCS, Georg. A la búsqueda del burgues. In: ______. Thomas Mann. Barcelona: Grijalbo, 1969.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他仅仅是一具皮囊,他在某种意义上和无产者类似(后者只能出卖劳动力)。即使托马斯·曼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讽刺也依然很有趣,特别是当读者注意到这个抽象的身体不同于塔基欧的理想而不可触及的身体,以及克劳斯·海因里希王子的纯粹象征性的身体,格雷姆伯格笔下的这两个角色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并感到愉悦。
不过汉斯·卡斯托尔普并不是小说中唯一的年轻角色,他的表哥约阿希姆·齐姆森,是那种我们永远无法赋予其主角的人物,与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约阿希姆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军旅生涯。除此之外,他还意识到,作为一个年轻人自己已经在阿尔卑斯山上“不得不像一池死水[35]那样凝滞不动”了五个月,而“山下的生活”[36]一直在酝酿着决定性的变化。这是一个需要证明自我的年轻人的决定:“像我们这样的年龄,[37]一年时间是多么宝贵啊”。他的表弟为了避免感染,欣然接受了贝伦斯留在贝格霍夫的建议,而齐姆森尽管身体状况差得多,却拒绝留在疗养院继续治疗,决心回到他的工作,同时也回到他的真正快乐中去,尽管他知道这会要了他的命,事实也的确如此。尽管感染了肺结核,这个年轻军人仍拥有一副具有古典美的运动员式的身体,苗条而健美,[38]这和汉斯·卡斯托尔普的身体形成了鲜明对照。并且在死亡之后(这是整本书中最感人和讽刺的场景之一),约阿希姆的尸体还展示了其体格魅力。对于齐姆森而言,身体展示了它是强壮的,比心灵更愿意去生活和工作,[39]不仅如此,在那些因为疾病而不能去享受的岁月里,他的生命的时间恰恰是在他的身体里流淌着。[40]
在死去之后,约阿希姆的脸又重获年轻的魅力,这张脸孔将拥有永恒的青春,因为它永远给自己希望,尽管死亡意味着某种形式的凝固。对于约阿希姆而言,从军不是偶然的,他穿军装时感觉良好,很像与他碰巧同名的另一个更伟大的角色——赫尔曼·布洛赫的《梦游者》三部曲中第一部中的约阿希姆·帕瑟诺,他们都只能在确定的形式中找到意义。②曼弗雷德·瑟拉对《魔山》和《梦游者》的三册书进行了有趣的比较,然而他忽视了笔者在此强调的两个约阿希姆兹之间的联系——或许帕瑟诺处于主角的位置而齐姆森不是。
在汉斯·卡斯托尔普和他的表哥之间,我们能看到一张白纸和一个穿军装的人之间的对比,一具抽象的不确定的身体与苗条健美身体的对比,胸无大志的市民与精于谋划且热衷于职业生涯的军人之间的对比,这些对比恰恰向我们展示了汉斯·卡斯托尔普的成长经历(如果这算是一种线性的不断前进的变化)并不是朝着成年人,成熟的确定的形式。更确切地说,身为一张白纸意味着它还可能成为任何事物,具有多种可能性,但同时也意味着无法忍受军服的约束。不正是因为他纯粹是一具身体,他才第一次真正地关心起某些问题,并且开始尝试为自己的经历寻找意义的吗?周围生活的都是病人,自己又不停地发着高烧,卡斯托尔普在贝格霍夫度过的第一个冬天的那些夜晚里阅读病理学和药学,为的是寻找生命的解释,更确切地说是生命开始的某个瞬间。但这仍然是一种无关自己的兴趣,他的身体既是人类的又是宇宙的,在一切复杂的生理机能中保持着抽象性。汉斯·卡斯托尔普又发现低级生物体的重要活动都显露在外,而高级生物体都会藏起他们的本质,比如他们如何起源,他们的物质又如何分裂成更小的部分:“这是生命对于‘自我认知’的一种既充满希望又徒劳无益的探索,是一种对自然的‘自我发掘’,结果却一无所获,因为凭知识既不能洞悉自然的一切,也无法窥知生命的奥秘”。[41]他在那个他无法理解的生命瞬间中看到了有限性,尽管这个瞬间的意义已经被宣告出来了,那是当他为了弄清发烧的原因拍摄了手部的X光片,从而借助疗养院的技术手段“透视了自己的坟墓”。[42]他的骨骼是一具完全被剥离了血肉的架子。唯一能辨识的地方是祖父传给他的戒指。
他对于药学的兴趣以及对于医学技术的着迷标志着他在那个瞬间突然意识到自己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医生。卡斯托尔普没有思考未来,而是想象自己如何可以拥有一个不同的过去,意识到自己仅仅是因为偶然[43]可以成为工程师。尽管这个意识源于对技术的兴趣,药学和工程学引起主人公兴趣的原因有很大不同。汉斯·卡斯托尔普知道从这一刻开始,过去毫无意义。不仅如此,这唤起了他的爱的冲动,让他渴望冲出自我,能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看待自己(无论是在X光中还是想象出来不同的过去中),让生活的轨迹不再保持静止和中立。正如他从克罗科夫斯基的演讲中学到的,爱情如果不能被接受,一直保持沉默的话,①参考托马斯·曼:Der Zauberberg.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2002, p.196. 赫夫特里希对小说中表现的爱与疾病的关系作了有趣的分析。See HEFTRICH, Eckhardt. Zauberbergmusik: Über Thomas Mann.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75, p.78.就会演变为疾病。
这样一来,身为一张白纸并不是无法矫正的缺陷。如果说最开始汉斯·卡斯托尔普无欲无求的话,那么后来他逐渐开始对于某些问题产生兴趣,尽管只局限于某个专业的学科,比如药学,但我们毕竟已经看到了求知欲。②注意约瑟夫·劳伦斯提出的简单但尖锐的问题:“如果汉斯·卡斯托尔普是哲学教育的受众,应该可以确定教给他的是什么”。见LAWRENCE, Joseph P. Transfguration in Silence: Hans Castorp´s Uncanny Awakening. In: DOWDEN,Stephen (org.). A Companion to Thomas Mann´s The Magic Mountain. Rochester: Camden House, 2002, 2a.ed, p.3.
不过他的自学更多的是关于美学而非科学,因为他感受和观察世界的方式如此多种多样,从单纯的抽烟的快乐到这部小说的核心的哲学与诗学问题:“时间是故事的要素,正如它是生活的要素一样。它必然受叙事的制约,犹如身体存在于空间一样。时间又是音乐的要素,音乐本身又对时间进行计量和分割,它不仅能娱乐,也能让时间显得宝贵。”[44]在此笔者将回到《魔山》的作者在序言中表达过的、并在结尾又回顾的那个主题:对于他来说,叙事为时间填充内容,正如音乐一样。并且因为这是一个汉斯·卡斯托尔普的故事,笔者认为故事的发展应当基于主人公对各种艺术形式的接触和审美印象进行考虑。在小说结尾处我们能发现一个显著的标志:卡斯托尔普在和他挚爱的克拉芙迪亚·肖夏的谈话中提到,他找不到一个通信的对象,甚至在汉堡的亲戚也不行。他又引用古斯塔夫·马勒的一首歌曲来描述自己的状态:他与世界失去了联系(Ich bin der Welt abhanden gekommen)。③参见 MANN, Thomas. Der Zauberberg.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2002, pp.898-899. Ich bin der Welt abhanden gekommen的歌词是弗莱德里希·胡克特的一首诗,选自《胡克特民谣》,这是20世纪头十年内写成的五首组歌,时间上在托马斯·曼写《魔山》之前。如果说世界离他而去,那是因为从某些方面来说世界对他的麻痹效果被解除了。能够用一具躯体,甚至是机器来代表自己本身就是向自我定义、勾画自己轮廓迈出的重要一步。
托马斯·曼对于古斯塔夫·马勒的仰慕之意值得关注,除此之外,汉斯·卡斯托尔普的这句话也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一个角色如何不再是一张白纸,当然他也仅是刚刚开始而已。当然这个转变不仅仅单纯地表现为对世界的联系的转变——尤其因为正如马勒的这首歌曲的题目暗示的,卡斯托尔普似乎已经向这个世界告别。在他身上没有主动的自我肯定的愿望——19世纪意义上的对自由的追求——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从绝对消极的状态中走出来,并改变自己作为白纸的状态。正如埃克哈德·海福瑞琦指出的那样,“汉斯·卡斯托尔普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的……创造性,而在于他能够使自己惊讶,并展现出好奇心,换言之,在于一种开放的态度”。[45]他没有失去着迷的能力。因为消极状态从来没有完全占据他的心,我们在小说中并没有看到救赎式的转折。或许卡斯托尔普从来都不是完全死气沉沉,这也解释了他体体面面的平庸性。最后正像赫尔曼·维甘德[46]所提及的,即使是成为船舶工程师这样一个最随波逐流的决定也展现出了他身上的某些积极因素,毕竟他从小就喜欢画帆船。
在这个漫不经心的职业选择中已经展现出一种美学倾向。他对身体的兴趣也是如此,最初是对X光片影像①卡拉·舒尔茨对《魔山》中技术细节(尤其是X光)的作用给出了有趣的分析,指出了卡斯托尔普的自我意识如何通过他对世界的技术层面的考察展现出来。不过我认为这种技术视角同时也和卡斯托尔普的美学经验有关。见SCHULTZ,Karla. Technology as Desire: X-Ray Vision in The Magic Mountain. In: DOWDEN, Stephen D. (org.). A Companion to Thomas Mann´s The Magic Mountain. Rochester: Camden House, 2002, 2nd ed.的不带感情色彩的纯粹技术意义上的观察,以及对高等生物细胞结构的解释,但另一方面他从小就注意到人的形体以及其象征意义,对祖父的画像的记忆对他而言尤其重要,后来它甚至与祖父的真实容貌[47]混淆起来。同样,在贝格霍夫他也很喜欢贝伦斯绘制的克拉芙迪亚·肖夏的画像。这个医生在照看和揶揄他的肺结核病人之余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画笔上,他向卡斯托尔普提到他十分了解这位俄国女士,但只是在生理学的层面上,他清楚她的血压、皮肤组织、淋巴组织,等等。但是这位医生又认为,事实上“表面的东西却更难掌握”。[48]汉斯·卡斯托尔普被这张画像迷住了,在医生用业余的笔触所表现的肖夏的肌肤上甚至能“连毛孔都看得出来”,[49]他从此开始狂热地阅读药学书籍。
身体不仅包含着无限复杂的生理结构,它的外表本身也具有神秘感。生理学分析不是唯一让汉斯·卡斯托尔普感兴趣的事,他读过因诺森特优三世所著《人类的悲惨处境》,这本书是从塞塔姆布里尼的对头里奥·纳夫塔那里借来的。纳夫塔既是耶稣会士又是共产主义者,既支持中世纪传统又为革命恐怖辩护,他在自己的居室里收藏了一具14世纪的耶稣塑像,虽然完全不符合客观的解剖学比例,[50]但还是让卡斯托尔普着迷。如果说身体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的话,它看起来扭曲、脆弱并且受着折磨,[51]但首先让卡斯托尔普震惊的是,和普通的弥撒相比,葬礼是宗教的象征元素,它的仪式和凝重更能熏陶灵魂。[52]
他的艺术兴趣首先体现在绘画和雕塑中的人体。[53]但各种视觉艺术在叙事中往往只出现一次,[54]戏剧则会反复出现,无论是古典的——比如在剧院中——还是通俗的——比如在电影院里[55]——都是卡斯托尔普乐趣的源泉。他常常回忆起弗雷德里希。席勒的戏剧《唐卡洛斯》代表了面对死亡时保持尊严的典范:“我觉得,不论世界和生活本身,都要求我们大家都穿起一身黑衣服,带着漂白的褶皱领,而不是你们那种军服的衣领……同时时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总会死去。”[56]艺术和约阿希姆一起引领着他去拜访疗养院中的垂死之人,“死者的舞蹈”这一章节的名字可能就由此而来;除此之外在贝伦斯的建议下,卡斯托尔普和他的表哥拜访了卡伦·卡斯特德,一个在贝格霍夫以外生活的患病女人,他们带她一起去电影院,并愉快地观看“生活被切成一片片的小块,短暂地匆匆而过,各个镜头时隐时现,闪烁不定,有时还伴随一些音乐,音乐把人们带回到往昔的景象中去”,[57]正在上映的电影②迈克尔·纽曼认为这部电影是恩斯特·刘别谦拍摄的Sumurun, Thomas Mann在 1920年看过这部电影。小说作者并没有考虑到让战前的角色观看战后电影产生的时间问题。See MANN, Thomas. Der Zauberberg - Kommentarband.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2002, p.240.的剧本探索了肉欲、裸体以及利比多。[58]但在绝大部分艺术体验中,汉斯·卡斯托尔普只能通过再现来感受身体,无论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艺术把他从近乎绝对的消极态度中引领出来:如果身体是停滞的原因,那么它同时也可以成为痴迷的对象。
三、爱
然而,这部小说在笔者看来并不是一个关于角色进化的故事。的确,卡斯托尔普离开了停滞状态与对科技和政治的失望状态,而对世界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美学兴趣,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前进方向与19世纪成长小说的主人公相反,威尔海姆·麦斯特和皮普(查尔斯·狄更斯的《远大前程》的主角)在饱受摧残之后,放弃了不可能的愿望而与那个禁锢他们理想的世界达成妥协。19世纪的年轻角色在对世界失去热情之后就消沉下来或者遭受毁灭,虽然卡斯托尔普的道路与此相反,但也并不意味着道路的尽头是救赎。他对身体和奇异形体的兴趣本身就有局限性,前者有被肢解的危险,后者则面临融解。
在“雪”那一章中,卡斯托尔普察觉到了身体的存在,这一次是他自己的身体,而不是来自书本的、雕塑、绘画或是电影的抽象知识。去阿尔卑斯滑雪的时候,我们的主人公被困在一场暴风雪中,大雪带来了死一般的沉寂和大自然冷漠无情的表现,对于来自文明的孩子[59]既可怕又吸引人。说起来有些矛盾,大雪既遮盖了一切,又向卡斯托尔普展现了他自己纯粹的身体机能,身陷于充满敌意的自然环境之中时,他失去了安全感和自我保护的本能,只剩下一丝明晰的意识,这提醒他疾病并不只是产生疼痛,也同样剥夺了痛觉本身。他麻木了。[60]这是整部小说中少有的情景,可以说在这一刻,卡斯托尔普转变了方向,他同自己进行无需媒介①赫尔曼·韦根观察到汉斯·卡斯托尔普如何在小说的进程中经过一系列危机,逐渐获得自我意识,呈现出一种教育式的体验。但是他同时认为卡斯托尔普的道德观念——这正是危机教给他的内容——是允许自己进入极限的,混杂的体验。很难说我是否完全同意他的理论,即使考虑到对于卡斯托尔普而言越来越重要的艺术实际上也一直在超越形式和身体的极限。但我肯定不能认同韦根的把卡斯托尔普看成是一个天才的观点。See WEIGAND, Hermann J[1933]. The Magic Mountain: A Study of Thomas Mann´s Novel Der Zauberberg.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5,p.21-24.在其他地方韦根也给出了同样有趣的讨论,基于这样的问题:卡斯托尔普如何在和他挚爱的克拉芙迪亚·肖夏的对话中产生了对自己人格的意识,以及他的人生轨迹。Cf. idem, p.135.的直接对话,身处茫茫白雪之中,与世隔绝,正如马勒的歌曲中描绘的那般。他此刻享受着自由,“他前面无路可通,后面也没有一条可以把他带回出发点的道路”。[61]
然而在小说的末尾,当汉斯·卡斯托尔普决定投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壕沟中时,死亡的威胁还是降临了。最后一章叙事者只用了几页向主角告别,在莫拉蒂的观念中叙事应该就此果断地结束,并且让主人公合理而突然地死去,而在《魔山》中主人公并未在叙事中死去,他的死亡应该发生在叙事结尾之后。在战场上他低吟着另一首歌:歌曲是威尔海姆·穆勒作的一首诗,由舒伯特弹奏的《冬之旅》中的《菩提树》。
汉斯·卡斯托尔普还在贝格霍夫疗养时,听到经理购买的留声机里播放了这首歌,并且立刻被它迷住了。从小就是音乐迷的卡斯托尔普享受着神奇的科技发明带来的快乐,从中获得了一种崭新而细致的美学体验,到了几乎负责管理疗养院唱片收藏(尤其是那些他最喜欢的曲目)的地步,这个时候艺术和技术、着迷与觉醒之间的界限被模糊了。在凌晨独处的时间里,他开始意识到死亡话题的意义和他对这个话题的热爱。[62]但这里的死亡不只是生理上的,而同时是表现为形式的消解,这在语义上与生命相对立,因为歌曲正是这样一种艺术,它从人体中只取用声音作为诗意的材料,②关于音乐形式对卡斯托尔普人格塑造的形式上的重要性的分析,参考REED, T.J. Thomas Mann: The Uses of Tradi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a.ed, 1996, pp.266-274; SERA, Manfred. Utopie und Parodie bei Musil, Broch und Thomas Mann: 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 - Die Schlafwandler - Der Zauberberg. Bonn: Bouvier, 1969.导致一种“自我征服”,最后到达“情爱的实质”。[63]
卢卡·克雷斯森其告诉汉斯·卡斯托尔普,人凭借视觉获取知识,目的在于“发现死亡在生命中潜伏的不同形式”。[64]他说得很正确:对于棺材之中死去祖父的回忆与画像中的形象混淆、X光片、基督的身体、《唐卡洛斯》中的场景这些都是死亡的表现。同样的,他敏锐地意识到音乐与其他艺术不同,因为“它超越形式之上”。[65]但笔者认为这一点还需要更多思考。“多么值得为它而死去啊,迷人的歌曲”,[66]叙事者通过汉斯·卡斯托尔普的意识说。但是为什么?因为正是在音乐中,世界、符号和爱被统一起来。[67]汉斯·卡斯托尔普最初的白纸一般的世界以及他的本质上的孤儿身份都压在他的肩上,尽管他感受不到重量,这仍然使他慢慢地麻痹。他像一张白纸是因为他能做任何事情,却没有界定自我的基准。这种麻痹感让他在X光机、药学书籍、业余绘画、中世纪圣母像、席勒的戏剧或者一部电影中寻找象征,这样一来他唯一的自我认识——对身体和形式的迷恋在疗养院的生活中缓慢地显露出来。他也喜欢聆听舒伯特的歌曲时形式消解的体验,仿佛灵魂脱壳,后来他重回低地的时候周围是炮声、泥土和尸体的碎块;如果说他走出了停滞,那么他回归的是一个正遭受毁灭的世界,这与那个他曾经毫无压力负担在肩上的世界截然不同。舒伯特的歌曲对于卡斯托尔普的象征意义显然与军服对于约阿希姆·齐姆森的意义不同,后者死去以后尸体在贝格霍夫停放期间依然穿着军服,相比之下汉斯·卡斯托尔普祖父在画像中永恒不变形象①卢卡·克雷斯森其:Melancolia occidentale: La montagna magica di Thomas Mann. Roma: Carocci, 2011, p.125. 尽管克雷斯森其认为汉斯·卡斯托尔普是一个忧郁的天才,因为他能够向世界传达出一个外部而短暂的信号,尽管我完全不同意这一点,他的看法仍然对我的解读产生了重要作用。的象征意味更强。从前形式以永恒死亡的面孔出现,而现在形式就源于身体之中,它发出的声音转变成一首稍纵即逝的歌曲。
如果汉斯·卡斯托尔普会找到一条自己的道路,那么这条道路无非是遵照他所受的训练罢了,这种训练的实质不是如何与世界达成一致且变得成熟,而是带着“良心的”、[68]“满怀预感的冥想”[69]以及表现为形式和成长的,他先是惊讶地发现这些感觉的存在,亲身体会它们,又最终超脱它们,直到能在战斗时轻声哼着歌曲。
一个战士在被各种形式的死亡所包围时,安静地哼着一首有些幼稚的浪漫歌曲,当笔者想象这个场面的美和震撼时,开始考虑小说的结尾如何将(歌声中的)魔法和(武器中的)科技结合在一起。整篇小说中艺术和科技可能靠得很近,但从未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一个将来注定要成为船舶工程师的小孩的帆船绘画中包含着魔法,就好像在播放着他喜爱的歌曲的留声机中包含着技术一样;卡斯托尔普并未接受提娜珀尔的教导,只是接受他的管教;他的冷淡折射出他对技术的冷淡,技术从不关心因何目的而被使用;但同时技术也让他意识到自己的有限,让他开始“期待尸体腐烂”。汉斯·卡斯托尔普加入战争并非因为美学的意识形态——在目前的解读中这常被理解为20世纪浪漫主义的负面影响②这种解读的一个例子是EKSTEINS, Modris. Rites of spring: The Great war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age. Boston; New York: Mariner Books, 2000.——而可能是因为卡斯托尔普与威尔曼。麦斯特、皮普这类听天由命的角色以及吕邦泼雷这类自我毁灭的角色不同,他的行动不全是为了快乐。③这个说法来自英格玛·博格曼主演电影Fanny and Alexander, 其中亚历山大的木偶剧团出场时的标语写着:“不只是为了快乐”。
[1][6][7][8][12][24]弗兰科·莫莱蒂:《如此世道:欧洲文学中的成长小说》,伦敦:沃索出版社,1987年,第8-10、5、5、5、163页。
[2][3][4][5][9][10][11][14][18][19][35][36][37][41][42][44][48][49][56][57][61][62][63][66][67][68][69]托马斯·曼:《魔山》,钱鸿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第1、1、2、2、42、4、4、26、40、46、20、20、20、379、300、766、355、356、406、436、681、927、928、778、776、928、929页。
[13][15]托马斯·曼 [1924]: Der Zauberberg: Roman. Grosse kommentierte Frankfurter Ausgabe.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2002, p.13,pp.46-47.
[16][46] Weigand, Hermann J [1933]. The Magic Mountain: A Study of Thomas Mann´s Novel Der Zauberberg.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5, p.33, p.33.
[17] WEBER, Max. Ciência como vocação. In: ______ Metodologia das ciências sociais. Vol.2. São Paulo: Cortez;Campinas: Editora da Unicamp, 2001, p.439.
[20][21] MANN, Thomas [1924]. Der Zauberberg.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2002, p.94,p.39.
[22]奥尔格·卢卡奇:A Teoria do Romance: Um ensaio histórico-flosófco sobre as grandes formas da épica. São Paulo: Ed.34, p.79.
[23][25][26][27][28][29][30][31][32][33][34][40][47][50][51][52][54][59][60] MANN, Thomas. Der Zauberberg.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2002, p.165,pp.276-277,p.159,p.226,pp.93-94,p.215,p.154,pp.305-306,pp.61-63,p.150,p.177, pp.810-811,pp.42-44,p.535,p.594,p.168,p.816,pp.717-718,p.730.
[38][43] MANN, Thomas. The Magic Mountain: A Novel. New York, London, Toronto: Alfred Knopf, 2005, p.331,pp.388-399.
[39]同上 p. 753; cf. WEIGAND, Hermann J [1933]. The Magic Mountain: A Study of Thomas Mann´s Novel Der Zauberberg.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5, p.53.
[45] HEFTRICH, Eckhard. Zauberbergmusik: Über Thomas Mann.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 1975, p.208.
[53] REED, T.J. Thomas Mann: The Uses of Tradi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a.ed, 1996, p. 254.
[55] SERA, Manfred. Utopie und Parodie bei Musil, Broch und Thomas Mann: 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ten - Die Schlafwandler - Der Zauberberg. Bonn: Bouvier, 1969, p. 190.
[58] MANN, Thomas. A Montanha Mágica. Tradução de Herbert Caro. Rio de Janeiro: Nova Fronteira, 2000,p.433.
[64][65]卢卡·克雷斯森其:Melancolia occidentale: La montagna magica di Thomas Mann. Roma: Carocci, 2011, p.143,p.228.
责任编辑:郭秀文
K203
A
1000-7326(2016)10-0109-11
*本文系CNPq创新基金资助下的研究项目成果。本文中文版由作者授权本刊首发。
佩德罗·卡尔德斯(Pedro Caldas),里约热内卢州联邦大学(UNIRIO)历史系教授/CNPq项目研究员;赵培玲,中南大学外语学院教授(湖南 长沙,41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