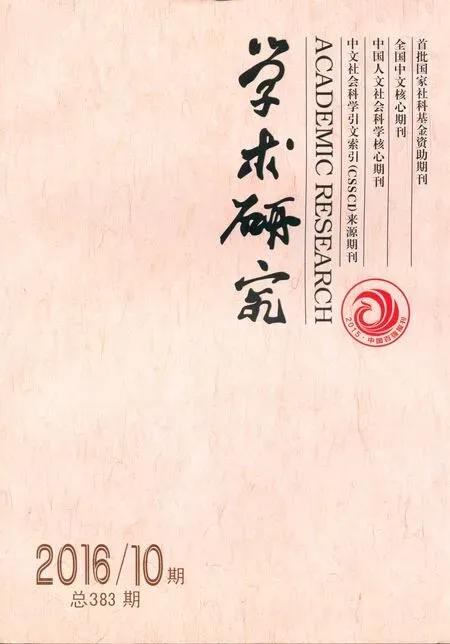重新理解马克思“两个伟大发现”之间的辩证关系——兼纪念柯尔施诞辰130周年*
孙乐强
哲 学
重新理解马克思“两个伟大发现”之间的辩证关系——兼纪念柯尔施诞辰130周年*
孙乐强
在正统马克思主义那里,剩余价值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往往被视为历史唯物主义在经济学领域中的具体运用,或是对它的一种理论证实。在批判这一观点的基础上,柯尔施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解读模式。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分别构成了马克思唯物主义和革命理论的哲学和科学阶段,并基于社会意识、形而上学批判和阶级斗争理论,系统阐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化和替代作用。然而,由于其方法论上的内在缺陷,导致他根本没有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最终陷入历史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窠臼,遮蔽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
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革命理论柯尔施
如何打破传统学科界限,基于整体范式,重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已成为当前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焦点话题,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两个伟大发现”即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之间的辩证关系。围绕这一问题,众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形成了几种极具特色的解读模式,柯尔施的研究尤为值得重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学界并没有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基于此,本文以柯尔施为对话语境,在客观评述他的理论得失的基础上,进一步诠释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内在关系,以期为国内学界系统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理解提供一点拙见。同时,也谨以此文纪念这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诞辰130周年。
一
恩格斯曾将马克思毕生的理论贡献概括为“两个伟大发现”:一是历史唯物主义,它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二是剩余价值理论,它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1]那么,它们之间到底存在何种关系呢?在正统马克思主义那里,较为流行的有两种模式。一是“运用论”。它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只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中的具体运用,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剩余价值理论则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经济学领域中的具体运用。二是“证实论”。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列宁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天才发现,在《资本论》之前,这一理论在本质上“还只是一个假设……是一个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以严格的科学态度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2]而《资本论》的发表,则从根本上证明“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证明了的原理”,[3]从而实现了对过去一切历史观和社会学说的革命性变革。
然而,到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这两种解读模式却遭到了质疑。面对正统理论家将马克思主义肢解为各种分支的做法,卢卡奇和柯尔施率先提出了一种整体性的解读范式,将其诠释为一种总体性的社会革命理论,认为这不仅是把握马克思思想精髓的关键,而且也是理解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根本原则。也是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对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二者关系的理解。他们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绝不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一般概括,而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认识”[4]或“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经验研究”。[5]因此,当恩格斯、第二国际理论家和列宁将这一理论放大为整个人类历史时,已经扭曲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内涵及其适应范围。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唯物史观绝不是辩证唯物主义或自然辩证法在历史领域中的具体运用,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剩余价值理论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经济学领域中的单纯运用,更不是对后者的简单证实,相反,是对后者的全面深化和替代。这一点在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卡尔·马克思》中得到了全面、系统的阐发。
柯尔施指出,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总体性的社会革命理论,这一点不论在前期还是后期都没有丝毫的改变,但在表现形式上,却出现了重大变化,即从前期的哲学批判转变为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6]也是以此为由,他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划分为两大阶段。
一是1843—1850年,这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的哲学阶段。柯尔施指出,截至20世纪早期,不论是资产阶级思想家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始终没有澄清一个核心问题,即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关系问题:前者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当做黑格尔哲学的余波不予考虑,否认马克思主义存在任何哲学内容;而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证科学,否认它与哲学之间存在任何联系;而其他理论家则主张用康德、狄慈根、马赫等人的思想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实际上,这也就等于否认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质。虽然他们的立场是根本对立的,但在这一问题上却是出奇地一致,即都否认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之间存在任何关系。在柯尔施看来,这些观点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主义早期形态的内在本质。他指出,从源头来看,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思想反映,而且也是资产阶级哲学的继承者,正是在黑格尔哲学的胎胞中,马克思主义才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因此,绝不能像资产阶级思想家或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那样,彻底否认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实际上,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到处都渗透着哲学。“仅仅因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具有不只是理论的,而且也是实践的和革命的目的,就说它不再是哲学,这是不正确的。相反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按其基本性质来说,是彻头彻尾的哲学……它是一种革命的哲学,它的任务是以一个特殊的领域——哲学——里的战斗来参加在社会的一切领域里进行的反对整个现存秩序的革命斗争。”[7]虽然此时他得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乃至革命意义的结论,但不得不承认,这一理论在总体上并没有真正超越资产阶级哲学,因而,“在内容、方法与用语方面仍然带有它所由产生的母体即旧黑格尔哲学的胎痣”。[8]就此而言,此时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本质上还不是一种科学,而是一种哲学。从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来看,虽然此时马克思在不同文本中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但这种批判还停留在哲学维度,并没有从根本上超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如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开始将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嫁接起来,对蒲鲁东的经济学形而上学和方法论做出了尖锐批判。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批判还只是一种哲学批判,在整个经济学水平上,它根本没有超越李嘉图,更不要说建立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了。[9]同样,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虽然马克思突破了前期对资本的理解,将其诠释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并力图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来揭示阶级斗争的经济基础,然而,不得不承认,他“在形式上并没有超越这样的口号……自由放任,听天由命。”[10]也是在此基础上,柯尔施指出,这充分表明,一方面,将《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等文本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视为马克思唯物主义和革命理论彻底成熟的标志,是站不住脚的;另一方面,也从侧面表明,“运用论”的解释模式是有问题的:按此逻辑,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在《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就应当建立起来了,而不应等到后来的《资本论》,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以此来看,“运用论”的解释模式显然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遮蔽了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丰富而又复杂的深层关系。
二是1850年之后,这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理论的科学阶段。柯尔施指出,进入50年代以后,通过系统的经济学研究,马克思最终建立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剩余价值理论,重新整合了各种资源,实现了对资产阶级哲学和经济学的全面超越。他不再像前期那样聚焦于哲学、宗教或法的批判,而是更多地集中于经济学批判,通过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系统解剖资本主义制度的生理机制及其运行规律,从而实现对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意识形式的总体批判。这时,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才最终摆脱哲学批判的形式,成为一门最充分、最成熟的科学。而《资本论》就是它的智慧结晶和完美体现,它不仅是古典经济学最后的伟大成果,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完美结合的历史产物,更是无产阶级革命科学的第一部伟大著作。[11]基于此,柯尔施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剩余价值理论绝不是前期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简单运用,更不是对它的一种线性证明,而是对它的全面超越和替代。
二
那么,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剩余价值理论,在何种意义上超越并替代了历史唯物主义呢?柯尔施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了分析。
第一,就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而言,柯尔施指出,在早期,马克思更多地关注意识形态(哲学、宗教、法等)与现实的关系问题,那么,到了后期,他的问题域则拓展为整个精神生活与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柯尔施强调,在1859年的“序言”中,马克思明确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意识:一是意识形态,包括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和哲学等多种形式;二是社会意识形式,包括商品拜物教、价值观念以及由它们所派生出来的其他范畴,它们的真实性完全不亚于法和国家,并同后者一起,共同构成了整个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到了这时,马克思意识到,要实现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体批判,单纯停留在哲学层面还是不够的,毕竟后者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只是社会意识的一部分。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将前期的哲学批判拓展为对整个社会及其意识形式的总体批判,而这恰恰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场语境。对此,柯尔施指出,以此来看,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本质上始终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及其全部意识形式的整体批判。因此,在后期,马克思的重心不再像前期那样集中于哲学批判,而是转化为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商品拜物教批判就是这一理论的集中体现。
柯尔施指出,与意识形态不同,商品拜物教并不是一种虚假意识,而是个人在资产阶级社会实践中生成的一种具有客观效力的社会意识形式,因此,拜物教绝不是观念错认的结果,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客观颠倒形式。因此,要扬弃拜物教,绝不能停留在单纯的意识层面,必须通过社会行动扬弃拜物教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理论批判与革命实践相统一的原则,构成了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本质区别,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精髓所在。基于此,柯尔施得出结论说,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研究,不仅构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全部理论的核心,而且也是他整个唯物主义理论最精辟的表达。[12]因此,就马克思整个思想发展历程来看,从前期的哲学批判转变为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绝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是他唯物主义理论的系统深化和发展。只有到了这时,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才彻底成熟。因此,与前期的哲学批判相比,政治经济学批判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始终是第一位的。[13]
第二,政治经济学批判彻底揭示了形而上学得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强调,费尔巴哈所做的工作只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14]柯尔施指出,在马克思看来,要彻底完成对哲学、宗教等意识形态的批判,单纯把它们归结于世俗基础,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事情是,还必须通过“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彻底瓦解世俗基础本身。就此而言,历史唯物主义只完成了第一步。就资产阶级哲学而言,历史唯物主义的确颠覆了观念的自主性,提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但近代唯心主义哲学家为什么会把观念视为新时代的统治力量?它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如何从根本上颠覆这种基础?对此,柯尔施认为,此时马克思根本无法给出科学的解答。就资产阶级经济学而言,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批判蒲鲁东式的经济形而上学以及古典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将资产阶级社会视为永恒的自然制度——无疑是有效的,但它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本身却无能为力,因为劳动价值论、拜物教、资本以及由它们所衍生出来的其他范畴,毕竟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虚构,而是有着客观效力的思维形式。因此,要真正扬弃古典经济学,单纯将这些范畴归结为它的世俗基础还是不够的,必须进一步深入到社会存在的内在矛盾之中,通过对资本运行机制的科学解剖,方能厘清并全面超越古典经济学。对此,柯尔施指出,要完成这一任务,单纯依靠前期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本行不通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就是典型例证。虽然此时马克思批判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蒲鲁东式的经济形而上学和古典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性,但他在经济学上并没有真正超越李嘉图,不论是劳动价值论、货币、资本理论还是劳动商品理论都深深打上了李嘉图的烙印,根本没有克服后者的缺陷。
在此基础上,柯尔施总结到,以此来看,历史唯物主义根本没有能力揭示并瓦解形而上学(包括资产阶级哲学和古典经济学)的世俗基础,而要做到这一点,还有待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而这恰恰是在《资本论》中完成的。他强调,一方面,通过剩余价值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意识到,黑格尔哲学之所以采取颠倒的观念形式,根本原因并不在于黑格尔,而是在于资本主义的现实世界本身。在这里,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以太”,成为统治一切的抽象力量,而它的生活过程则表现为假象丛生的颠倒过程,完全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内在本质,最终使资本主义成为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15]或者说,资本从“内部的有机生命,进入外部的生活关系”[16]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颠倒的辩证运动,而由此所生成的现实本身就是一种颠倒的形而上学。从这个角度而言,黑格尔哲学只不过是对这种颠倒现实的观念反映。因此,要彻底扬弃黑格尔哲学,单纯依靠所谓的“主谓颠倒”方法是行不通的,必须要深入到资本的矛盾运动之中,实现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及其意识形式的总体批判,才能从根本上剥离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外壳及其合理内核,完成对后者的彻底颠倒。另一方面,剩余价值理论的形成,不仅使马克思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现实本身的批判,而且也完成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史的批判,彻底超越了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使之成为一门真正的批判科学。也是在此基础上,柯尔施指出,如果说马克思的理论目标是要彻底扬弃资产阶级哲学和经济学,那么,前期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无法胜任的,唯有剩余价值理论的出场,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就此而言,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剩余价值理论,实现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替代。
第三,政治经济学批判全面深化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柯尔施指出,与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相对应,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包括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马克思虽然力图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论证资本主义灭亡的现实性,但由于此时他经济学水平的限制,导致他根本无法科学解剖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最终只能走向由分工和分配不公平引发的阶级斗争线索。柯尔施将这一模式称为“工人阶级主体的反叛”[17]之路,也即所谓的“主观表达方式”。[18]这一模式虽然体现了马克思鲜明的革命立场,但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条过分倚重阶级斗争和主体反叛的道路,是一种“狂热的、空想的、唯意志论的”[19]革命浪漫主义。然而1848年欧洲大革命的失败给了马克思一个惨痛教训,促使他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革命理论,从而使其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即与“热情的、幻想的第一阶段”相对的“冷静的‘第二’阶段”。[20]此时马克思不再过分强调主体力量,而是将重心集中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挖掘,以此来引出阶级斗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柯尔施将后一模式称为“生产力的反叛”[21]之路,也即所谓的“客观表达方式”。[22]他指出,如果说前一模式对应于历史唯物主义,那么后一模式则对应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就革命逻辑而言,从历史唯物主义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意味着“从直接的革命行动转到建立在客观经济发展基础上的、只是间接地针对革命目标的工人阶级运动形式”,[23]意味着“由工人阶级主体的反叛到客观的‘生产力的反叛’这种赋有特征的重点转移”。[24]
然而,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恰恰不理解这一点,径直将客观公式与主观公式对立了起来。在他们看来,这一转变意味着马克思已经放弃了前期的阶级斗争线索,“同他早先的革命倾向实行了全面的决裂”,[25]以此为由,他们将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诠释为完全依赖经济力量的社会进化论和机械决定论。对此,柯尔施做出了全面批判。他指出,后期马克思之所以强调客观公式,并不像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的那样,放弃了阶级斗争线索,转变为信奉经济力量的宿命论,相反,是为了强调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前提,即它必须建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之上,这一前提“不可能通过纯粹的良好领导、正确的理论或者富有战斗力的革命组织去取代”,[26]如果脱离了客观公式,抽象地谈论阶级斗争,那无疑是唯意志论的。另一方面,就物质生产力而言,它不仅包括“自然界、技术、科学……还有社会组织本身和在其中通过协作与产业分工所创造的、伊始就是社会的力量。”[27]就此而言,工人阶级的联合以及由此形成的“力量就是生产力”,[28]而且是“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29]因此,强调客观公式,绝不意味着抛弃阶级斗争,而是对后者更好地继承和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作为……整个历史发展和奠立其上的社会经济形态隐蔽的推动力,不过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其他著作里许多其他地方阐明为社会阶级的对立与斗争的同一事物的如实表达。”[30]二者是融合为一体的,脱离了前者,阶级斗争就会丧失内在的合法性。也是在此基础上,柯尔施指出,正是通过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才彻底克服了前期的革命浪漫主义,建立科学的、成熟的革命理论。
柯尔施认为,正是由于剩余价值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才彻底扬弃了“任何哲学的思维方法”,[31]实现了对资产阶级哲学和古典经济学的全面超越;也正是到了这时,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才“不再是一种‘哲学的’方法”,而是转化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经验科学的方法”,[32]从而使他的革命理论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在此基础上,柯尔施得出结论说:“构成新的马克思科学最后基础的,既不是黑格尔也不是李嘉图,既不是资产阶级的哲学,也不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33]而是对现实的革命运动以及资产阶级社会经验的具体研究,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发展并最终成为一门科学的决定性源泉。
三
我们应该如何评价柯尔施的观点呢?首先,必须承认柯尔施提供了一种整体性的研究范式。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总体性的社会革命理论,而历史唯物主义和后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只是这一理论的两个不同阶段,从而将二者共同统一于革命理论本身,这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传统三分天下的学科界限,抓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为当前学界进一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其次,与传统“运用论”和“证实论”相比,柯尔施提供了一个更为深入的解读路径。在他看来,剩余价值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既不是前期历史唯物主义的单纯运用,也不是对后者的简单证实,而是对它的进一步发展和替代,并从三个方面系统诠释了这种深化作用,这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线性思维,呈现了二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再次,如何理解客观公式与主观公式之间的辩证关系,不仅是贯穿整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个核心问题,也是衡量是否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试金石。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导致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形象:第二国际正统仅仅抓住客观公式,将其诠释为经济决定论,进而阉割了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而以卢卡奇为代表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仅仅抓住阶级斗争线索,陷入唯意志论的漩涡之中,忽视了客观公式的历史作用;以奈格里、克里弗、莱博维奇、巴迪欧等为代表的当代左翼思想家,更是乐此不疲地主张从主体出发,来重构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将后者诠释为一种纯主体性的活动,彻底否定了革命理论的客观前提。相较于这些观点,柯尔施无疑更为准确地诠释了客观公式和主观公式之间的辩证法,即使从当代来看,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柯尔施的解读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理论缺陷。
第一,从阶段划分来看,列宁曾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指出,在1843—1844年,马克思彻底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34]这也是后来苏联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哲学发展诠释为“一次转变论”的重要依据。当柯尔施把1843—1850年界定为唯物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时,他显然没有突破这一模式,没有看到哲学唯物主义(1843—1844年)与历史唯物主义(1845年之后)之间的本质区别。另一方面,就前后关系而言,“运用论”虽然存在一定的缺陷,但它毕竟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柯尔施却彻底否认了这一点。当他把政治经济学批判视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替代时,已经僵硬地把二者对立了起来。就此而言,所谓的“替代论”和“运用论”一样,只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没有真正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二,从革命理论来看,柯尔施将1850年之前的阶级斗争理论界定为一种狂热的革命浪漫主义,这一观点也是错误的。客观地讲,此时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确实存在不完善的地方,但与所谓的革命浪漫主义还存在天壤之别。马克思指出,革命唯意志论者“要做的事情恰恰是要超越革命发展的进程,人为地制造革命危机,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诗。”[35]真正的革命浪漫主义就是要彻底抛开历史进程,将革命变成人为制造的恐怖袭击活动。而此时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显然并非如此。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共产党宣言》,他都始终致力于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论证阶级斗争的现实性,虽然此时他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还不足以支撑整个阶级斗争理论,但这最起码反映了他此时的思路,即将主观公式奠基在客观公式之上,以此来寻求阶级斗争的客观依据。就此而言,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的发展,绝不是柯尔施所断言的那样,是革命浪漫主义与科学理论的断裂过程,更不是线性的取代过程,而是在整体思路完全一致的前提下,不断使革命理论走向深化的过程。
第三,在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关系的理解上,柯尔施的确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模式;不过,值得反思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真的能彻底代替前期的历史唯物主义吗?它真的不需要任何哲学的支撑了吗?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搞清楚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内涵。虽然柯尔施也认为,它可以“适当的扩展转用于其他历史时代”,[36]但在根本定位上,他始终与卢卡奇一样,将它诠释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认识。通过这种变形,柯尔施实际上也就把恩格斯所界定的“两大发现”,还原为“一个发现”了。那么,历史唯物主义真的只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反映吗?针对这一问题,国内学界已展开了充分研究,在此不再赘述,只强调两个结论。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不仅适应于资本主义社会,而且也适应于一切前资本主义社会。恩格斯将其界定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是非常准确的。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一种教条,而是一种方法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7]这就意味着,要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研究,仅仅停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层面上,是远远不够的,就像用“人”这个概念,永远理解不了任何一个“个体”一样。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超越一般层面,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而政治经济学批判恰恰就是马克思在这一方法论的指导下,从一般(人类发展规律)上升到特殊(资本主义社会)的展开过程。就此而言,作为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研究,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剩余价值理论绝不只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简单运用,而且也是对后者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从这个角度而言,柯尔施从社会意识、形而上学批判和革命理论三个方面所做的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我们决不能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将政治经济学批判视为对后者的彻底代替。作为一种特殊,政治经济学批判既不可能取消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性,也不可能彻底摆脱这一方法论前提。因此,当柯尔施断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彻底超越了一切哲学思维方法,不再需要任何哲学支撑时,恰恰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这方面,阿尔都塞的观点值得肯定:在《资本论》中,我们不仅能够发现马克思的科学,而且也能读到他的真正哲学。[38]
第四,虽然柯尔施诠释了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力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但这一理论努力还是不够的。恩格斯指出,正是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社会主义才实现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39]二者既紧密相关,又相互独立,共同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双重支柱。到了柯尔施这里,这一命题则失去了原有的内涵。在他看来,总体革命理论是本质,横贯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全过程,而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这一理论的两个不同阶段(哲学和科学阶段):前者并不足以使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成为一门科学,只有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后者才彻底摆脱哲学批判的形式,成为一门真正奠基在经验研究之上的社会科学。以此来看,柯尔施所理解的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代表的唯物主义,实际上不过是一种经验唯物主义,当他把后者视为马克思唯物主义和革命理论的最成熟形态时,无疑又重新退回到经验主义的老路上来。这一做法不仅彻底阉割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人类学基础,否认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价值,而且也从根本上曲解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内涵,歪曲了它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关系,根本无法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科学依据。[40]
最后,柯尔施之所以会做出这种解读,根本原因在于他的立场和方法。综观柯尔施的整个逻辑,可以发现,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他都预设了革命政治实践的优先性,在他的视域中,所谓的历史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物质生产的历史,而是革命实践的历史;所谓的理论、科学与实践的统一,归根到底是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的统一。因此,在政治立场上,柯尔施无疑是一位革命优先论者;在历史观上,是一个典型的历史主义者;而在方法论上,则是一个鲜明的经验主义者。[41]这构成了柯尔施理论建构中不可或缺的“三位一体”框架。当他从这一框架入手来分析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时,必然无法走向深入,最终只能陷入自己的偏见之中,无法自拔。
[1][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6、740页。
[2][3]《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0、161页。
[4][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12、315页。
[5][8][9][10][11][12][17][18][19][20][21][22][23][24][25][26][27][30][31][32][33][36][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熊子云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28、179、69-70、144-145、71、89、160、121、73、73、160、120、159、160、159、161、148、149、129、179、182、128页。
[6][7][13][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4、37-38、45页。
[14][28][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128、194页。
[15][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40、52页。
[34]《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9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21页。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42-743页。
[38][法]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4页。
[40]John Rundell,“Karl Korsch: Historicised Dialectics”,Thesis Eleven, 1981(3).
[41]James Watson,“Karl Korsch: Development and Dialectic”,Philosophy Social Criticism, 1981(8).
责任编辑:罗 苹
B089.1
A
1000-7326(2016)10-0016-07
*本文系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资本论》的哲学思想及其当代效应研究”(2014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再研究”(12CZX002)的阶段性成果。
孙乐强,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江苏 南京,21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