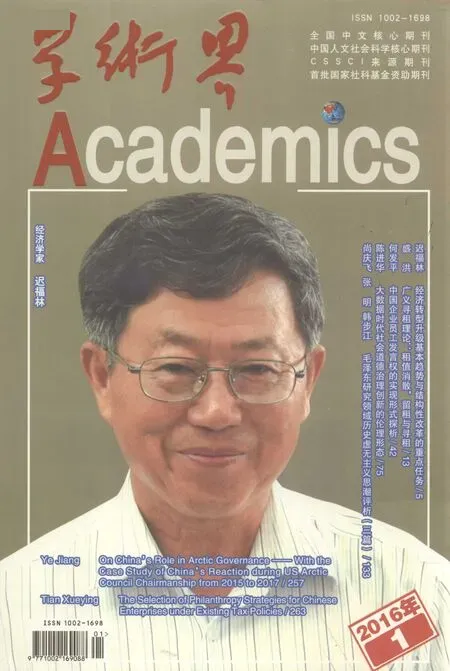从“有无互成”到“天人相合”〔*〕
——周汝登本体论思想考察
○ 田 探
(重庆大学 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哲学中心, 重庆 400044)
从“有无互成”到“天人相合”〔*〕
——周汝登本体论思想考察
○ 田探
(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哲学中心, 重庆400044)
周汝登的本体论思想建基于有无之间互缘互构的关系。这种关系投射于其心学领域中,表现在层层递进的三个方面:在良知与见闻关系上,两者互相缘构;在理、气、心关系上,呈现为以“理、气总之一心”为纲,以“即心即理”和“即理即气”为目之双层架构;在太极与物的关系中,指明了道德法则的自定自有。进而从“无善无恶”和“千圣所传一心”两个维度揭橥出良知心体实为通达古今的引导性场域,以及道德法则的历史性根源。由此可知,良知心体在更宏大的视域中是连接天人的场所,它决定了天道呈现的方式和天人互构关系建立的途径,同时也是对程朱理学“天理”观的祛魅。
有无;良知;无善无恶;天人
周汝登因发扬王龙溪“无善无恶”说,被时人目为“今之龙溪”,后学也多据此认定他为王龙溪的思想之余绪。目前学界对周汝登本体论的考察主要依据是他与许孚远进行的“九谛九解”辩论。他们认为,在实有层面上,周汝登虽然标榜“无善“,但其实只是超越了善、恶对待之分的“至善”;这种“至善”在作用层面上,是心体自然流行,毫无造作之迹,故可以“无”形容之。总之,周汝登的本体论思想依然属于儒学正脉。
学界对周汝登学脉渊源的分疏是大致妥当的。但是,统观文献,我们发现周汝登本体论是一个层层关联,上达天人的圆融体系,其所牵涉面众多,远非有、无关系所能涵盖。因此,他所指的“无善”不可视为实体意义上的至善。“无”确是形容良知流行无执无滞的品格,但它在根本义上是对“有”的统摄,是“有”之为“有”的根源,这才是周汝登以“无善无恶”述说良知的真实义。
一
周汝登本体论的核心是有、无之间的互构关系。他所提出的“有以成无,无以成有”的思想正是对此关系的提炼。在“剡中会语”中有人以《道德经》“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请教先生,周汝登答曰:
即如此屋居住,全是空处,明取牖,由取户,是空。如此桌上面铺设处,是空;此椅坐处亦是空。至如人身,目窍空,故能视;耳窍空,故能听;鼻窍空,故能嗅;口窍空,故能食,总只是受用得个空。然空亦离不得有,非有,空亦无。乃是有一种著空的,又要并去其有,辟如因住处是空,连屋也不用,如何使得?可见有以成无,无以成有,实处是空,空处是实,有、无、空实分不得,取舍不得。于此圆融,方称妙悟。〔1〕
此段中的“空”和“无”意指事物之用,例如耳、鼻、口等感官之用,牖、户之用。事物之用与物本身的实在不同,它虽“虚而无有,无可形容”,但也“决不断灭”〔2〕。所以“空”“无”概念所指的是不能为我们感官所感知的事物的功能作用。
而此段中的“有”则指可为感官所能感知到的实在,它为事物的功用提供了物质实在的基础,事物之功用也由此实在而得以实现。“有”指的是通达于感官,融摄于心体,进入了主体存在的事物,并非是指与人完全无关的客观之“有”。它以自身实在为基,标识着一个与之相关联的功用系统,故曰“有以成无”。此功用系统“不能并去其有”,须以“有”为基才得以可能,也只有通过“无”的功用系统,“有”才能获得自己的规定性,故曰“无以成有”。可见,“有”“无”之间既相互支撑,又互相指引。“无”因“有”得以实现,而“有”依于“无”也不断获得自身的意义,如此循环往复,达于圆融之境。因而,我们既不能执“有”忘“无”,也不能因“无”弃“有”。前者胶着于感官,后者流于偏颇,俱不能圆融。所以,周汝登“有、无、空实分不得,取舍不得”的断语实际揭示了它们之间不离不弃、互缘互成的关系。
有、无之间的互缘互构虽然表明两者的圆融一体性,但实则确有区别。从主体的角度看,“有”总是意味着外在条件的限制,我们不能完全主导;而“无”,即外在事物的功用和意义,却与主体的目的性、意向性相关。所以,在主体性的关照中,即在心学结构中,有与无的体用关系发生了翻转。“无”相对于“有”居于主体统摄性的地位,“有”依靠“无”而获得自身的规定性,因此,从心学的角度讲,“无”居于体的地位,而“有”作为意义的承载者则反居于用的地位。在周汝登的哲学体系中,体即是指心体,他明言:“天地万物无体,以吾之心为体。”此心即是能够统摄天地的“无”体,而天地万物作为“有”则是心体呈现自己的用。心为天地万物的根本,而天地万物为心之外显,此为因体而达用,溯用而通体,“体用一原,实不可分”〔3〕。通体达用,亦显体用圆融。如此,“有无互成”的关系就与“体用一原”的宗旨完美地融摄在一起。在这里,心学的视野是我们理解周汝登关于有无体用关系的关键。
二
“有无互成”的结构在周汝登的哲学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当这种结构作为思维背景进入周汝登心学领域时,就展现出了丰富的理论内涵。
1.良知与见闻
良知与见闻的关系实际源于孟子心物之分,是孟子心物之分的心学化表达,但也是对心物关系的深化和丰富。
王阳明曾在回答欧阳德“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时说:“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4〕阳明以此表达了良知与见闻不离不滞的关系。对此,周汝登在《王门宗旨序》中发挥说:
“心性有两名而无两体。知是知非之谓心,不识不知之谓性,似有分矣。然而不识不知非全无知识之谓,即知是知非不可以知识言也。……方其是非未萌,无是非而知则非无,及其是非既判,有是非而知亦非有。知而无知,无知而知,是谓良知。”〔5〕
周汝登首先从“心”“性”的角度表述“良知”,因为正是“良知”把“心”“性”连为一体,使“心”“性”之间“有两名而无两体”,这使我们必须把良知看作“体”。其次,周汝登明确了良知的含义:“知而无知,无知而知,是之谓良知。”其中,“知”是道德判断的能力,亦即“知是知非”之“知”,它表明此“知”乃是良知最根本的功能。“无知”是指良知心体的是非判断“反观既得”,非由外溯,所以“知是知非不可以知识言”,即良知心体与知识无涉,这就是“知而无知”。同理,知觉与知识也不可等同于良知心体,“有是非而知亦非有”是说是非随事而有,但当下的是非并非良知自身之能,故称“无知而知”。周汝登强调:“所谓心虽不离见在知觉,而未可便以知觉当之。”〔6〕知觉为良知心体所发,因当下所遇事物而显,受外界限制。故从本末来说:“洒扫应对,末也;精义入神,亦末也;能知洒扫应对,精义入神者,本也。”〔7〕洒扫应对为身体的履践,精义入神为良知的神用,两者皆为末,只有良知“知是知非”之能是根本。为了强调良知之能,他甚至说:“恐人以知识为知,故说一良字。若知体透彻,即良字亦多说了,其实只一知字而已矣。”〔8〕见闻知识无所谓“良”,若缺乏“知是知非”的判断能力,知识毫无意义。所以,见闻知识呈现出德性或德行的根源在良知之能。故此,周汝登又说:“仁本于知,知以成仁”〔9〕。
既然良知之“良”表现为统摄见闻知识,并使之转换为德性与德行。那么,良知就意味着一个始终运作着,且“不杂气质”“不落知见”的思之域。它的意义在于:首先,他将耳目所闻所视,心之所思均纳入个体的思域中,从而使见闻之知获得意义,也使良知心体拥有抵达自身的载体;其次,他是个体能够赢获自身德性的根基,离此无以成德。所以他说:“太虚之心,无一物可着,正是天下之大本”。也正因为良知是所有道德判断的根本,超出了随事而应的具体是非,故称为“无善无恶”。最后,良知所营构的思域通过转化个体经验为德性、德行而不断地获得自身。可以说,生活情境中的所有是非判断都是对良知心体的营构、补充和更新。质言之,良知与见闻的互缘互构关系充分表明了它们是有无关系在心学语境中的扩展和丰富。
2.理与气
良知“知是知非”的统摄作用是良知之能。之所以能够有是非之知,是因为良知心体有理,这就牵涉到理、气、心之间的关系。
在阳明心学的学理中,将理、气归纳于心是其区别于宋代理学的基本特征。杨国荣先生疏解阳明心学时认为,心与理的统一首先意味着普遍之理与个体意识的融合,一方面弱化了普遍之理的超验性;另一方面为个体意识赋予了普遍性的品格,是个体性与普遍性在心体上的统一。〔10〕周汝登作为阳明学的三代弟子,驳斥朱熹心外有理说,收纳理、气于一心,是其继承心学学脉的体现。而且,他更在三个层次上详细地分疏了三者的关系。
首先,周汝登接续心学道统,指出:“理、气虽有二名,总之一心。心不识不知处,便是理;才动念虑,起知识,便是气。虽至塞乎天地之间,皆不越一念。”〔11〕在这段话中,“至塞乎天地之间”的主语是气。这表明,不仅天地万物为气,而且心之“动念虑,起知识”也是气。换言之,凡可为我们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之事物,均是气而不是理。若以此为理,是“知识累之也”。〔12〕所以,当周汝登否认“心外有理,理外有心”时,实际是指凡是心之“已发”皆属于气,而只有“未发”的心体方是理之所在。
其次,周汝登在回答何为“学问窍要”时说:“知识忘,而视、听、聪、明,即心即理,岂更有理为之所循耶。”表面看来,“即心即理”似乎是在重申“理不外心”,实则不然。此处正体现了周汝登对良知心体认识的深化。我们知道,理不是气,而心之所发皆归为气。如果以心之所发来认识未发之理,就会导致以气来认知理的情况,此时的是非判断就是“落于知见”“杂于气质”,所形成的善恶观就是有对待的善和恶。因此,理只能在“忘却”知识后,方能呈现于视、听、聪、明之中。这就意味着,理自身的运行法则与气无涉,知识和见闻的多寡深浅(气)不能影响理的运行。由此,“即心即理”所表达的就是心和理对气的共同统摄。
心的作用是“知是知非”,气层面的见闻知识因心的判断和选择功能进入心体所营造的思之域,从而获得道德性。因此,心所突出的是“知”字,即拥有自我意识的功能。而理的作用在于,为心的判断和选择提供道德性的保障,理是见闻知识之气获得道德性的根本。理与心各司其职,它们各自对应“性”与“心”,故周汝登称“知是知非之谓心,不识不知之谓性”。两者“似有分”,却“有两名而无两体”,是良知心体的两个侧面。可见,“即心即理”之说是对良知“知而无知”的回应和深化。
心、理的运行法则虽然不因气而改变,但毕竟要由气来呈现。所以,周汝登最后分疏了理气关系。他说:“即理即气,孟子所谓‘浩然之气’是也。不识知之识知,孟子所谓‘赤子之心’是也。非槁木死灰之谓也。”〔13〕“即理即气”之“即”与“即心即理”之“即”含义相同,指理虽统摄气,而气之流行运转无不涵蕴理于其中。理与心是良知心体相辅相成的两个侧面,它们共同统摄气的流行,赋予气化流行以意义。从这个层面来理解,理就绝非抽象出的槁木死灰之概念。
综上所述,在心、理、气三者的关系中,心和理构成良知心体的两面,共同统摄气的运行;氤氲流荡之气因良知心体而脱离了纯粹的自然,成为进入主体生命的“浩然之气”。由此我们说,周汝登以“理、气总之一心”为纲,以“即心即理”和“即理即气”两个层面为目,疏解了三者的关系,可谓纲举而目张,彰显了周汝登思想的精微。
3.太极与物
理、气、心三者的论述虽有涉本体与现象的联系,但还未曾探究其本源,尤其是道德判断的根据——“理”从何而来的问题,这才是整个体系中最为关键的部分。
在宋明理学的语境中,理来源于天,故称“天理”。人类能够“知是知非”,源于心中有天理。朱熹解释周敦颐《通书》中言:“万物之中,各有一太极,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14〕朱熹将太极置放于天地万物之中,以示天地自有常,宇宙运化自有其理,此“太极”即为道德判断之源头。这种理解置道德源头于人之外,导致“形上之域与形下之域的对峙”〔15〕,无法避免思辨的构造。对此,周汝登指出:
各具一太极者,本来自具,非分而与之之谓也。统体一太极者,千灯一光,非还而合之之谓也。使太极而可以分合,可以与受,则太极亦不过一物,当必有妙于太极者,分之,合之,受之矣。其可通乎?太极生天地,非天地生太极也。天地、日月、四时、鬼神,皆太极中物。合则无间异,非以此合彼之谓也。〔16〕
天地万物之太极并非由一外在的太极实体所赋予,由此不可以分合、与受言之。“本来自具”意指太极是万物所自有的法则,天地万物都受它的约束,这个法则就是良知心体。因此他明言:“无极而太极,即吾心是也。”〔17〕可见,本来自具的太极并不指向物理意义的规律和法则,而是指良知心体的法则对天地万物的统摄。所谓“太极生天地”,实际是指太极的这种统摄性。据此,我们可以合理的推论,道德判断的根据和本源来自于我们自身,换言之,天地万物之意义与法则都统摄于我们自身。无论称之为“理”,还是“太极”,总之是我们内心自有的法则。于是,天地法则的探索,道德本源的追问就应回归于良知心体的内省与体证。基于此,周汝登提出“学问只在自反”的观点。他指责向外探寻天理之人是:“不务穷其本根,而徒于万上寻求,有处执着,伏羲之旨湮矣。”〔18〕
三
在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已经阐明,道德判断以及其依据来源于良知心体自身。心的功能是能知,它为道德判断提供智性的支持;而理作为道德之依据,依然内在于心体之中,这揭示了道德法则的自定自有。这可谓是周汝登思想的核心,他从以下两个层面深化了此命题。
1.道德法则自定自有的依据
既然道德法则是良知心体的自定自有,那么对它的寻求就是“闻者自闻,知者自知”。周汝登说:“学问头脑只在信得自己,自己一毫无所亏欠,……曰反身,曰自得,语语归根,是入门第一义谛。”〔19〕“圣圣相传,自见、自闻、自知,同归于宗”〔20〕。以“自见”“自闻”来诠释“真见”“真知”表明了良知心体所蕴含的天理并非是身心之外的超验之物。在周汝登看来,道德法则既不能求之于外界事物,也不能求之于心之所思,因为“心可思者,皆末也”。道德的法则不能以思辨来构造,心之所思所想是无法把握道德法则的,这是周汝登思想中的精髓,也是他所提倡的“无善无恶”说的理论根基。
周汝登在与许孚远有关良知有无的争论中,指出:“不虑为良,有善则虑而不良矣。”〔21〕虑即是思,是心之已发,正因道德法则不能用思维来把握,因此任何思虑所意之善都不是真善。所以,他说“有善丧善”“着善着恶,便作好作恶”,并直指其原因在于:“学问用力之人,患在有害而执著……不知本自无善,妄作善见”。〔22〕以思虑所着为善,病在固执己见,故此难免“舍彼取此,拈一放一”。在周汝登看来,如若以思虑所着之善为善,求善于思辨的构造中,则必然走向“诚意而意实不能诚,正心而心实不能正”的伪善。
伪善之为伪不仅在于个体为善的虚假性,更在于以私意求之反而会遮蔽真善。太虚之心所以为天下之大本,是因为它“不落知见”,不被具体的见闻知识和心意思虑所局限,故而能摄纳天地万物。因此,它是天地万物在此得以互相通达的场所,也是天地万物得以获得自身意义的源头。这种通达天地万物的能力才是人性之至善,这种善不能以具体的善来表述。相反,如果执著于思虑所因之善,“于心上寻个理”〔23〕,则是自限于“理障”,蔽于一曲。所以,真学问无他,只是要明白此身具有此通达天地的太虚之心。正如周汝登所指:“下手工夫,只是明善。明则诚,而格致诚正之功更无法。”“舍是而言正诚格致,头脑一差,则正亦是邪,诚亦是伪,致亦是迷,格亦是障。”〔24〕故此,为了避免着善着恶,周汝登提出“不以善为善,而以无善为善,不以去恶为究竟,而以无恶证本来”〔25〕的“无善无恶”之说。
实质上,心体只有“无善无恶”,道德法则才能够自定自有。思虑所着之善往往视善为一永恒超验的实在之物,表面看来是持守善念,实则顾此失彼,褫夺了心体虚灵不昧、通达万物的本性,自拘自限,最终“以人作天,认欲作理”〔26〕。由此可见,道德法则之所以自定自有,在于良知心体始终虚位以待,具有统摄性,不固执己之所见和己之所思。也只有不泥于己见己思,才能在每个与天地万物相往来的当下打开自己的善性。
2.千圣所传一心也
“自见”“自闻”“自知”表明道德法则的自定自有,而明此自定自有的良知心体就是对千圣所传道统的接续。
自古圣人未尝有一法与人,亦无一法受于人,前无辙迹可寻,后无典要可据,见者自见,闻者自闻,知者自知。自见者无所见,自闻者无所闻,自知者无所知。故曰:无有乎尔,则亦然有乎尔!〔27〕
这段材料蕴含着三层意思。首先,后人去古已远,圣人已逝,其言其行不可得而见,故此“无辙迹可寻”。其次,修身进德之业只能是自见自知。德性日修是个体生命全身心投入的事业,它体现为生命成长之流,是整全而不可分离的。每个当下都是身心全体的托付,它随时随事而变,神应无方,妙应无穷,任何的言行记录都只是片段性的截取。若拘泥于圣贤文字而无自我体悟,那么,圣人之德则沦落为可见可闻的对象化知识,而这势必导致知与行的分离,身与心的分离。因此,圣人的进德修业之法不仅无所闻、无所知,实则不能传授,故曰“无典要可据”。最后,圣人之法“无所见”“无所闻”并不意味着他们修身立德的活动失去了立教的意义。周汝登对此解释说“千圣相传只传此心而已。夫人生而有此心,这个心……一毫无欠,不必加添,见在运用,皆是此心。”〔28〕前贤传诸于后世的是他们广大精微之德,此德来源于内心仁德的扩充。每个人生来都先天具有此统摄仁德心体,都具有成德的可能。换言之,在成德的条件和可能性上,圣凡是相同的,所以“一毫无欠,不必加添”。在这个意义上,前贤通过扩充仁心成就德性的生命本身就是圣人所传之法。它的作用无非是提点众人觉悟那本来自具的良知心体。而众人继承千圣所传之心的实质是以圣贤的生命为引导,接纳自身所本具的良知并扩充到生命当中。所以当周汝登说“人人本同,人人本圣,知而信者谁?信则同,不信则异,圣凡之分也。”〔29〕时,意即圣凡之别就在于是否真正地接纳本来自具的良知,并将它施诸四体。
可见,千圣所传之法其实就是圣人立教所传之道。圣人所传之心不是思辨所抽象的道德实体,而实是引导我们觉悟自身具有自定自有道德法则的场域。这样的理解就彻底消解了对良知心体及其道德法则超验化、抽象化的理解方式,从而将众人的德性建立在“自见”“自闻”“自知”的生命活动中。由此我们说,圣人立教传道实则是开启了后人自得其性命之正的道路,换言之,圣人立身成德的活动始终意味着开放性的场所,其中,不仅圣人自得其位,自定其德,而且也将自身的进德修业作为一项礼物遗留给有志之士。后学在其引导下反省、接纳自己的良知心体时,不仅开显了自身的德性,也承继了圣人之道,千圣之心。
综上所论,圣人之心超越了具象化的道德法规,升华为通达古今的引导性场域。在这个层面上,良知心体的自反与自得拒绝了自我封闭,在向前接纳和向后传承两个维度上敞开自身。于是,与其说良知心体代表着道德法则,不如说它构建了道德法则的场域。此场域由道德主体在具体的修身活动中营构出来,而接纳前贤和传承后世都是在此场域中完成的事业。因此,良知心体不仅是个体的,也是历史的,这也是千圣所传之心的理论蕴涵。
四
良知心体所营构的场域不仅具有历史性,在更宏观的意义上,它是连接天、人的场所,换言之,它决定了天人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以及天道呈现的方式。这是对程朱理学系统中“天理”概念的祛魅,和对天人互构关系的回归。
程子曾这样描述天:“《诗》、《书》中凡有个主宰底意思,皆言帝。有一个包涵遍覆底意思,则言天。有一个公共无私的意思,则言王。上下千百岁若合符契。”〔30〕其中,天被释为无所不赅且绝对公正的主宰,其流行运化而赋于万物以理,所以“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己何与焉。……与则便是私意。”〔31〕天的周流运转过程完全是“自然当如此”,不能有丝毫的人欲参杂于其间。人之所为或束缚人欲,或皈依天理,均失去了其主体的能动性。如果浩浩之天的不可穷竭性被简化为抽象的“天理”,其后果就会是尽心知性的配天、参天活动实则成为向抽象天理观念的皈依,天人相互通达转变为由天向人的单向度统摄,两者被人为地悬隔。对此,周汝登诘问:“天之一字,自皋陶发之,实莫之为而为之意,至汤乃有上帝降衷之言,人遂执以为性真天降,若有所与受然者。夫性果可以与受之物哉?”〔32〕天之周遍流转本来是自然而然,无意志,无目的,人之自性亦非天所授予之物。故而他批判朱熹将天命解释为令,并质其“穷理尽性以至于令乎?”〔33〕
在周汝登看来,人之性是在与天地合德的过程中自知自成的。他说:“天合于人,人情乃畅;人合之天,天庆弥隆。以此为乐,一切势位名称,吾身外者,举无以尚,故命之曰一。”〔34〕天人之合不仅畅达人情,而且能够获得上天的赐福,以此为乐,则不为名利所诱,故称一。“一”不仅否认了天人的隔绝,而且揭橥着天道与人性的互融关系。周汝登在解释《中庸》首章时指出:“究而言之,天外无性,性外无道,道外无教。教即是道,道即是性,性即是天,一也。”〔35〕人性的生成始终是在天地的场所中完成,而人性的流行和充沛就是道。道的本义是人所行之道路〔36〕,周汝登也指出“人之率履处即是道”〔37〕,道意味着开辟和通达,君子修身以抵达人性的活动也就是开辟人生所行之道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君子不单日新其德,更重要的是以自身的修德为教,为后进学者开辟了一条进德修业的途径。所以,天、人、道、教四者的开显全部收摄于主体的修身活动中。天道和人性勾连为一体,天道为人性所打开,人性的完善就是天道的开展,人性的丧失也就意味着天道的遮蔽。因此,周汝登说:“道与性,名异而实同也。”〔38〕
由上述的分析看出,周汝登所指的天不是与主体无涉的自然之天,而是为主体所认知之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道出了乐道之真谛:“造化在我,何天非人;学虑不事,何人非天。凡言合者,犹歧之也。歧之不离,凑泊而不二,乃无始终一乐。悟此乐,斯为至。”〔39〕真正的乐之所由,正是天人互摄下主体的修身活动,以及伴随而来的德性成就。于是,我们可说,周汝登思想所建构的天人关系包含如下意蕴:天之合于人,即是主体纳天地万物于良知中,并在修德立身的事业中赋予天地万物以意义,同时也使自身德性在与天地相往来的过程中流行畅达;人之合于天,即人的修道活动不仅开显了人性,也是完成了配天,参天的活动,是对天之所命的承继和发扬。
注释:
〔1〕周汝登:《剡中会语》,《东越证学录》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一六五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502页。
〔2〕〔11〕〔12〕〔13〕〔17〕〔18〕〔32〕周汝登:《武林会语》,《东越证学录》,第452、454、454、454、454、455、455页。
〔3〕周汝登:《四书宗旨·大学》,第245页。
〔4〕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1页。
〔5〕周汝登:《王门宗旨序》,《东越证学录》卷六,第524页。
〔6〕周汝登:《圣学宗传》卷九,《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69页。
〔7〕〔37〕周汝登:《四书宗旨·论语》,第525、492页。
〔8〕孙奇逢:《理学宗传·附录》,光绪庚辰浙江书局版。
〔9〕周汝登:《四书宗旨》,第45页。
〔10〕〔15〕杨国荣:《心学之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9-60、70页。
〔14〕周敦颐:《周子全书》,《通书解》卷九,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69页。
〔16〕周汝登:《圣学宗传·周敦颐》,第106页。
〔19〕周汝登:《程门微旨序·在几篇》,《东越证学录》,第516页。
〔20〕〔27〕周汝登:《越中会语》,《东越证学录》,第479、478页。
〔21〕〔22〕〔24〕〔25〕〔26〕周汝登:《南都会语》,《东越证学录》,第434、432、432、433、435页。
〔23〕周汝登:《圣学宗传·王守仁》,第261页。
〔28〕周汝登:《新安会语》,《东越证学录》,第443页。
〔29〕周汝登:《重刻心斋王先生语录序》,《东越证学录》,第524页。
〔30〕〔31〕程颢、程颐:《二程遗书》(第二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0、30页。
〔33〕〔35〕〔38〕周汝登:《四书宗旨·中庸》,第253、257、254页。
〔34〕〔39〕周汝登:《题一乐堂册》,《东越证学录》,第584、584页。
〔36〕许慎:《说文解字注》,段玉裁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5页。
〔责任编辑:流金〕
田探,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哲学中心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明代儒学、儒家哲学。
〔*〕本文系重庆市社科规划办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博士项目“周汝登心学思想与晚明儒学本体论思想变迁研究”、中央高校重庆大学人文社科跨学科研究项目(106112015 CDJSK 47 XK 31)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