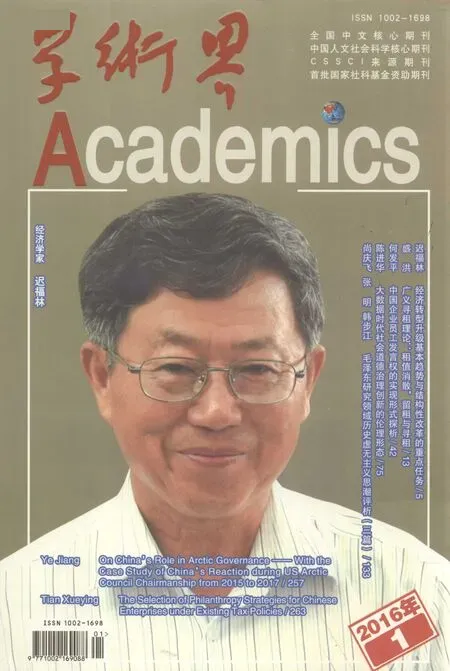迈向建制型国家:近代中日比较
○ 卢正涛
(贵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迈向建制型国家:近代中日比较
○ 卢正涛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贵州贵阳550025)
转向建制型国家,实现国家形态的更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新趋势。近代以前,中国是压制型国家,日本是竞争型国家,不同的国家形态使得中日在迈向建制型国家过程中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日本依靠私营企业发展制造业,推进工业化,市场成长起来;运用国家权力强制对社会进行改造,严厉镇压旧势力的反抗,为私营企业、市场创造良好环境,最终促成了一个工业化的新社会,顺利迈入了建制型国家。中国借助于国有企业发展制造业,国家的工业化努力与市场化冲突;不对旧社会进行改造以支持市场发展,也不压制旧势力的抗拒,未能跨进建制型国家的门槛。
建制型国家;近代;中国;日本
始于18世纪60年代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变革,它使人类步入了工业社会,从此告别了生产力低下,发展缓慢的农业社会,一种新型的国家——建制型国家横空出世。建制型国家是国家、市场和社会互动而形成的一种新国家形态,它与此前任何一种类型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国家、市场与社会各自相对自主是建制型国家的要求,在国家(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市场与社会三个方面构建基础性制度是建制型国家的特色;主动调整国家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将国家、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有效整合起来,实现快速、持续、协调发展。建制型国家的降临,并不意味着各国都能分享发展的红利,相反,它宣告了人类社会中各种“共同体”(民族的、亚民族的等等)竞争新时代的开始,任何一个共同体,倘若仍像以往那样只借助于国家,或者市场、社会中的一种力量推动发展,在竞争中难免一败涂地;任何一个共同体,如果不想在竞争中落下风,就必须转向建制型国家,整合国家、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实现赶超。近代中日两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开始迈向建制型国家的。迈向建制型国家意味着:首先,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从前建制型国家转变为建制型国家,实现国家形态的更新。其次,任何一个国家通过必要的改革,推动工业化,培育、发展新的市场主体,建立新的市场组织,造就出一个内涵不同于以往的新市场,使市场相对于国家(政府)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再次,依靠市场力量不断改造旧的社会,同时把握好改造的节奏,将改造过程中出现的冲突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从而催生出一个新的社会(相对于国家、市场有一定自主性的社会)。最后,在新市场、新社会形成过程中,建制型国家逐步推进基础性制度建设,以规范国家、市场、社会各自的行为,缓解国家(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从而有效整合国家、市场、社会三种力量。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能否顺利迈入建制型国家,关键取决于国家(政府)改变对市场的态度和控制市场在改造社会过程中出现的冲突。比较近代中日两国的历程,思考其得失,依然是学术界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不同的起点,相同的目标
70多年前,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在其名著《中国近代史》中说:“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1〕落后的农业国与先进的工业国之间的巨大差距决定了中国必然失败。不幸的是,鸦片战争并没有使中国从此警醒,不仅浪费了战后20年可以追赶的宝贵时光,而且20多年后接踵而来的新打击也未能使中国执政当局(包括推行“新政”的洋务派在内)摸清世界发展的方向,在前进的道路上始终举步维艰。与中国相邻的日本则不同,经历“黑船来航”的屈辱及其后与西方的接触后,迅速摸准了世界发展大势,追寻工业国家的足迹,踏上了崭新的发展之路。
对于近代中日两国在迈向建制型国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反差,学术界不乏精妙的见解。比较近代中日两国,需要回到“推动发展的力量是什么”这一基本点上来。如果这样做就不难发现,近代以前,中日两国在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互动所形成的结构,以及由此展现出来的国家形态等方面都是迥然不同的。众所周知,农业社会时代,土地是理解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互动和国家形态的关键,围绕土地的占有和利用衍生出王权、贵族两大势力,而两大势力之间又会形成不同的组合:强势王权与弱势贵族、强势王权与强势贵族、弱势王权与强势贵族。不同的组合与不同的国家—社会结构相关联。周代前期的中国是高度贵族化的社会,〔2〕以致国王行使权力时离不开贵族。从战国开始到秦国统一,随着郡县制推向全国,以及“为强迫人民之迁徙,使各本土原有之豪宗强族,皆失其所凭依”〔3〕的推行,贵族作为一支政治势力被拔除,不再对王权产生威胁,国家直接将统治建立在对“以纳税人自耕农、平民地主为主体的农民”〔4〕的控制和压榨之上。日本学者对这一统治形式作了恰如其分的概括,“帝国社会的各个领域(政治、社会乃至文化),都不存在早期族制般共同体性质的中间团体,也不存在通过中间团体构筑国家秩序的迹象。”〔5〕经过战国至秦的变革,中国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国家—社会结构:国家(专制王权)高居顶端,贵族从属于国家,国家通过赋税、劳役与官僚体系严密控制着农民,整个结构呈现出社会高度依附于国家的特征。在国家与市场关系方面,历朝历代的“抑商”或“抑末”政策执行得非常彻底,市场完全依附于国家。在商品生产领域,国家掌握大量资源,直接从事生产,对私营商品生产严加限制,有时甚至公开抢夺;在商品流通领域,国家经营商品买卖,依靠政治特权制造垄断价格,获取高额利润;阻碍私营商业的正常发展,商人兼业与兼业商人普遍化,更多的人参与到对商业利润的分割中,“导致商业经营在一定规模内低水平地重复发展”。〔6〕中国古代这种压制社会、市场,使之依附于国家(专制王权)的国家形态可以成为“压制型国家”。压制型国家致使社会、市场均无自主性,无须通过调整国家与社会、与市场的关系来缓解它们之间的张力,社会承受不了国家的重压而塌陷,随之而来的是国家崩溃,市场在社会大动荡中完全被摧毁,接着在与前朝开国时差不多的起点上重建国家、社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更糟糕的是,压制型国家扼杀了社会对近代以来的巨变自主作出判断和选择的能力。
近世以前的日本则根本不同于中国。在国家与社会底层之间,势力强大的贵族长期存在,因而形成了一个有别于中国的国家—社会结构。在江户时代,名义上统治国家的是京都的天皇和朝廷,但在德川幕府(将军)控制下政治影响力极其有限。“为了防止朝廷与大名密谋,幕府将朝廷官员与外界严厉隔绝,天皇也被禁足于皇宫之中。作为天皇首都京都行政长管的所司代,由德川家陪臣担任”。〔7〕真正掌控国家的是德川幕府的历任将军,他控制了全国1/4的土地,是全日本最大的地主,拥有数量最多的军队。幕府通过幕藩体制和“参觐交代制度”控制着各地的藩主(大名)。各藩藩主也有自己的土地,蓄养武士,建立自己的武装,“大名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真正的自主性,在他自己的藩国内行使着类似将军的权力,甚至到了迫使他势力较强的陪臣也实行参觐交代的地步”。〔8〕在国家权力分配的格局中,顶端是有名无实的天皇和朝廷,其下是握有实权的幕府,以及有一定自主权的藩主。显而易见,强大的中间集团的长期存在,既阻碍着国家权力直接深入社会底层,又相互竞争着国家的实际统治权。各中间集团拥有自主性,使得日本呈现出社会相对于国家拥有一定的自主性的特点,这为某些社会政治势力在社会大变革时期自主作出判断、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和道路奠定了基础。日本国家—社会结构决定了国家实际统治者无法建立起专制统治,也就不能系统运用国家权力压制市场,市场因而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第一,不同政治势力分享国家权力,决定了日本根本不可能出现国家进入商品生产和流通环节占用大量资源,压制市场发展的情况。第二,将军、大名和武士居住在城市中但不从事工商业,其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必须通过市场解决,围绕保障他们的生活出现了一批御用商人、特权商人。“很少有大名会冒疏远工商业界的风险,各藩的经济生活时常要依赖于这些工商业者的专业知识、良好信誉和协力合作”。〔9〕这些御用商人、特权商人积累起巨额财富,反而有利于推动市场规模的扩大。国家与市场保持一定距离,使市场相对于国家有一定的自主性,形成迥异于中国的国家—市场结构。日本国家、社会和市场之间的互动产生了一种极不同于中国的国家形态——“竞争型国家”:国家的实际统治权由不同社会政治集团来竞争,尽管获胜者力图限制竞争,但竞争的基因始终被保留下来,一遇合适的环境,各集团又会展开竞争,这就为在特定条件下转向新形态的国家提供了制度空间和可能性。不同的国家—社会—市场结构和国家形态,决定了近代中日两国迈向建制型国家时起点是不一样的,虽不存在水平高低之分,但在面对外来压力时却展现出不同的认知,由此采取了不同的应对路线,产生了截然相反的结果。
近代中日两国有着相同的目标,即迈向建制型国家,依靠国家力量调整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构,改变国家、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不相协调甚至互相冲突的状况,整合三种力量协同推动发展。如上所述,建制型国家最先在英国出现,西欧的法国、普鲁士—德国和北美的美国等迅即转向了建制型国家。对中日两国来说,需要认清并走好关键的几步路,恰恰在这几个方面,近代中日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第一,了解现有的建制型国家的情况,确定本国的发展方向。鸦片战争结束后,无论是最高统帅道光皇帝还是他的亲历战争的大臣们,谁也没有进行认真的反思,也没有谁想到要实地了解打败自己的对手。中国学者对鸦片战争中包括林则徐在内的12位负有重大责任的顶级人物战后的表现作了分析,得出没有一个想或能使国家真正有变化的结论。〔10〕主持洋务的首领,无论是中央的奕、桂良、文祥还是地方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大办洋务的19世纪70、80年代,均未出国考察(李鸿章出国已是1896年的事情了)。受制于有限的视野,洋务派把握不住世界大势和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当然不能把国家带上建制型国家的道路。日本则不同,德川幕府统治后期兰学的兴起使日本对西方并不陌生,幕末推行的改革特别是西南部诸藩的改革表明,日本已开始了主动应对西方的挑战。明治政府成立后日本立即派出了包括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在内的岩仓具视使团访问欧美18个国家,历时近两年,考察了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工厂、金融、教育、海陆军等等。“岩仓使团的作用,不仅在于其返国后有巨册的调查报告问世,向国内介绍和普及了有关西方国家的知识,而且还由于,使团的正副使节及理事官等,都是明治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他们根据耳闻目睹,迅速投身于改造旧日本和建设新日本的实践中去”。〔11〕得益于对现有建制型国家的观察和体认,明治政府更加坚定了选定的发展方向,推动国家迅速转向建制型国家。第二,对国家应发挥什么作用有清醒的认识。近代中日与西方之间的差距,表面上是“坚船利炮”对传统冷兵器的差距,实质上是国家在驾驭与市场、社会以及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保持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各自自主的前提下实现工业化、推动现代发展方面的差距。要缩小差距,不仅要消除表面上的差距,而且更重要的是解决实质上的差距,由此引出了国家应发挥什么作用的问题。对此,中日的认识可谓天壤之别。“日本的伊藤博文和李鸿章于1884年进行过一次谈判。伊藤博文说,李中堂,你应该改变一下中国的发展思路了,你们这种发展模式不可持续。这时日本的明治维新已经进行了十几年,他们的经验是允许自由经济的发展,而政府的责任就是允许自由经济的发展”。〔12〕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的对话清楚地表明了近代中日两国对国家作用的不同理解:国家是依靠私营企业推进工业化、支持市场成长还是国家取代私营企业主持工业化、压制市场发展?当然最后的结果也就大相径庭。第三,理清国家发挥作用的内在逻辑关系。建制型国家的出现是以国家改变对市场的态度为标志的。〔13〕国家从压制市场转而支持市场,市场不断对社会进行改造,促使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市场对农业社会的改造伴随着巨大的痛苦,必然引发社会的排斥与抗拒,因而需要国家强有力的支持,同时控制好改造的节奏,保证市场完成对社会的改造。这就是建制型国家兴起后国家发挥作用的逻辑关系。中国既不支持市场发展,也不通过打击社会中旧势力,引导社会转而支持市场;日本不仅运用国家力量直接支持市场发展,而且营造市场发展的社会氛围,对阻碍市场发展的旧势力毫不手软。
二、面对市场:支持还是压制
本文一开始就提出,顺利迈入建制型国家的起点是国家(政府)改变对市场的态度。具体到近代中日两国来说又有两点,即国家(政府)是否改变对私营企业的态度;在制造业勃兴的时代,国家(政府)依靠私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作为工业化的支柱。在一国的市场中,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从事商品生产,均是重要的市场主体,对一个国家来说必不可少。所不同的是,外资企业所占的比重不应过高,也不能掌控该国经济的关键部门,否则,就会导致该国经济主权的丧失,发展的希望化为泡影。国有企业是性质特殊的一类企业,除追求赢利外还具有政治功能,是国家(政府)直接占有市场部分资源的组织载体,国家(政府)正是藉此才对经济进行有效的控制和引导。不过,国有企业在一国经济中占有的比例也不能过高,过高表明国家(政府)占有的资源过多。众所周知,国家(政府)是按照国家需要或战略配置资源的,一旦国家(政府)占有的资源过多,那么,大量资源的配置就脱离了市场机制的支配,效益难免低下,从而在实际上对私营企业构成了抑制,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难于发挥出来。私营企业不同于国有企业,它以商品生产为唯一目的,所有活动都受市场机制的支配。一国私营企业的比例越大,表明该国中由市场来配置的资源越多,市场化的程度就越高。私营企业虽然同外资企业一样追逐利益,但其活动推动着国家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质量逐步提升,保障着国家的经济主权。正因为如此,私营企业的数量、规模、生产的技术装备水平等直接决定着一个国家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和市场的质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私营企业就等于市场。国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实包含着三类关系:国家(政府)与外资企业的关系、国家(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国家(政府)与私营企业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的关系。在人类社会开始工业革命后,依靠私营企业发展制造业,推进工业化,市场随私营企业的成长而扩大,内涵因新市场主体(从事机器生产的私营企业,不同于以前手工劳动的私营企业)的涌现也不断更新,建立在农业生产力基础上的市场转变为工业生产力支撑的市场。私营企业、工业化、市场是一体的,国家权力与市场权力合作,相互支持。如果依靠国有企业发展制造业,则表现为国家工业化努力与私营企业、市场的对立,国家权力与市场权力互相冲突,力量被耗费掉,国家的发展被大大延误。所谓国家(政府)改变对市场的态度,主要是指国家(政府)改变对私营企业的态度,即从以往的压制转变为支持,扶持民间发展制造业,推进工业化,创造出更多的从事机器生产的私营企业,将整个国家经济的基础逐步从传统的农业、手工业调整到制造业和现代农业之上,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同时,处理好国家(政府)与外资企业、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保证发展私营机器生产企业这一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
近代中日两国在迈向建制型国家时碰到了一样的难题,即市场中并不存在使用机器生产的私营企业。解决之道无非两条:一是国家(政府)支持民间创办机器生产企业。二是国家(政府)动用财政收入建立国有企业,引进机器生产。由于私人资本较少,采用机器生产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风险无法估计,开始时没有多少人愿意尝试。国家(政府)只得选择创办国有企业。尽管近代中日两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国家(政府)领办企业这一方式,但两国在对待民间创办机器生产企业和发挥国有企业作用上的不同态度和做法,使得中日在迈向建制型国家的道路上起步时就分道扬镳了:日本顺利踏入了建制型国家的门槛,而中国则始终在建制型国家的大门外徘徊。另外,两国对待外资企业的差异也是原因之一。
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府主导着现代化的努力。〔14〕这种主导是建立在日本政府对私营企业和国家作用的准确把握之上。1874年,出国考察归来不久的大久保利通,作为政府的实际负责人,提出了关于殖产兴业的建议书,指出“大凡国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物产之多寡,虽依赖于人民致力工业与否,但寻其根源,又无不依赖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力”。〔15〕在这份建议书中,有几点极为关键。第一,“致力工业”的是“人民”,即兴办、经营机器生产企业是私人而不是政府的事情。第二,政府的作用是“诱导奖励”而不是直接经营工业,将工业化中政府和民间各自的作用明确区分开来。第三,政府与民间合作,共同推动发展,实现工业化。明治政府成立之初,通过商法司和通商司,将大量的太政官纸币贷给民间,以达到“振兴产业,发展贸易”的目的。从1875年至1885年间,政府又以“公司补助金”的名义给予大资本家以总额达147万1千多日元的补助金。〔16〕日本政府对私营企业的扶植从三菱的成长历程即可窥全豹之一斑。1871年,土佐藩藩主把11艘船和一笔数量可观的现金送给岩崎弥太郎,给予他樟脑、茶叶、木材等藩营企业的控制权。1874年,明治政府将按虚报价格的13艘汽船卖给了他。第二年又把剩下的汽船都移交给他,还同意给予补助。岩崎弥太郎成立了三菱汽船会社,很快控制了日本沿海航线,并迫使大英轮船公司退出上海——横滨航线。〔17〕正是政府长期坚定的扶植,日本的私营企业才最终成长起来。尽管如此,明治初期的私营企业比较弱小,无法产生强大的动力推进整个国家的工业化。为此,日本政府在支持私营企业发展的同时由国家出面兴办实业,创建若干国有企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佐渡金矿、生野银矿、院内银矿、富冈缫丝厂、东京缫丝厂、品川玻璃、爱知纺织厂、新町纺织所、长崎造船所、兵库造船所、三池煤矿等。日本创办国有企业并不是单纯把机器生产引入到日本,或者是为了增加机器生产企业的数量及规模,而是让人们接触现代工业,改变观念,在工业化进程中培养人才。不可回避的是,国有企业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首先,国有企业官僚习气浓厚。作为政府兴办的企业,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是由政府安排的,与政府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他们关心自己的位置更胜于企业的赢利,也容易把盛行于政府的管理方式带到企业之中,因而官僚气息充斥着整个企业。其次,国有企业普遍出现亏损、腐败。官僚管理企业,必然造成企业经营方式的僵化,更严重的是管理层滥用权力,中饱私囊,以至于企业负债累累。1881年松方正义出任大藏卿后,日本大规模地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不到10年的时间,日本政府将兵工厂外的绝大部分国有企业处理给了私人,〔18〕价格之低,条件之优惠,几乎等于白送。对此,松方正义是这样说的:“政府不应在创办工商业上与人民竞争,因其永远不如受追逐私利的直接动机驱使的企业创办者精明和有远见。因此政府最好不要直接介入商业贸易,而是留给个人和企业去经营发展。”〔19〕日本政府将效益低下甚至亏损严重的国有企业甩出去,不仅减轻了政府的负担,而且意义更为深远,日本推进工业化的战略由此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扶植私营企业与创办国有企业并行转到主要依靠私营企业,市场也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而不断壮大。创办和处理国有企业作为推动发展的一种战略手段,如何使用将深刻影响着国家的发展道路。正如日本明治维新表明的那样,政府创办国有企业是在私人资本无力兴办机器生产企业情况下的暂时举措,其使命是为私营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创造前提性条件。换句话说,在没有私营机器生产企业时,政府通过创办国有企业,然后将国有企业处理给私人,从而造出私营机器生产企业来!当私营企业有所发展,需要政府增强其实力时果断、及时地处理国有企业。日本对外资的态度是严加限制,尽管明治初年财政困难,日本害怕损害主权,尽力避免借外债。支持本国企业将外资企业排挤出日本市场,为私营企业的成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私营企业、市场的成长,提出了构建政府与市场之间基础性制度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产权制度。从明治初年开始,日本即着手制定民法典,经过近30年的不懈努力,民法典于1899年正式施行。〔20〕总而言之,日本成功地转向了建制型国家。
中国清政府虽声称求强求富,但对国有企业作用以及私营企业发展的认识,从根本上说仍然停留在压制型国家阶段上。洋务派首领李鸿章认为,“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21〕“浚饷源”成为洋务派推行新政的指导思想。第一,发展机器工业,振兴商务,只是清政府获取收入的一种方式,而不是推动国家转型的战略举措。第二,国家对私营企业、市场进行压制,而不是扶持。第三,没有发挥市场和国家各自作用的必要,因而也不需要二者的合作。这与同期日本比较起来,差距实在是太大了。1871年,有人申请在镇江开办新式煤矿,被两江总督曾国藩阻止。1873年上海商人魏镛等3人拟自筹资本,聘请外国矿师在上元、句容等地勘探采掘,遭到金陵制造局的阻挠;不久,镇江商人王某禀请开发,因为“江〔宁〕镇〔江〕两府人情汹汹”,清政府不予疏导,被迫中止。〔22〕1882年还在筹建中的上海织布局获得了10年内不准华商“另行设局”的特权。〔23〕这足以说明清政府对待民间兴办新式企业的态度。“由于清政府财源竭蹶,对已有的新式军用工业已感难于维持,它尽管期望通过民用工业的创办来减轻军用工业的负担,却无力提供创办新式企业所必需的全部资金。又由于客观存在的大量社会资金引人注目,洋务派企图设法招徕作为新式企业的资本。”〔24〕洋务派兴办民用工业时普遍采用了官督商办这一形式。所谓官督商办企业,实际上是洋务派汲取民间资源的工具而已。1881年,李鸿章作出的规定再清楚不过了,官督商办企业“并非一缴公帑,官即不复过问,听其漫无矜制”。〔25〕这就是说,即使官督商办企业还清了政府的先期支付的垫款,企业的经营活动仍得听从官方的安排。开始时,由于资本主要由政府出具,官督商办企业具有明显的国有企业的色彩。随着民间资本的增加,商办色彩渐浓,但始终没能变成为私营企业。正因为如此,民间对官督商办企业集股极为冷淡,上海及其相邻城镇拥有资金的商人宁愿向外国在华企业投资。1872年轮船招商局集资无术,旗昌轮船公司(美资)则宣告增资到225万两,它所发售的股票竟成为当时华商追逐的主要对象,有人甚至愿意出价212两购买该公司面值100两的股票而不可得。〔26〕可见,洋务派禁止民间办厂和国有企业的无能,导致了本有一定资本的中国社会不支持本国的工业化事业,而是投资外国在华企业,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工业化努力。1883年上海发生金融危机,给中国的中小型企业以致命打击,大多数因此破产了。长期参与工矿企业活动的李金镛1887年谈到了当时企业负责人的困境,“中国自〔仿效〕泰西集股以来,就上海一隅而论,设公司者数十家,鲜克有终,而矿为犹甚。承办者往往倾家,犹有余累。‘公司’二字久为人所厌闻”。〔27〕洋务派官僚不仅不对私营企业施以援手,反而进一步打压官督商办企业中的商股,以至于这些企业的“商办”色彩迅速消退,实际上沦为其控制的私产。不同于日本的是,中国选择了逆向操作,不去处理手中的国有企业,以此增强私营企业的力量,借助于私营企业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构建起国家与市场之间的新关系,反而加紧进逼私人资本,牢牢主宰着市场。结果,国有企业亏损、腐败等顽疾无法克服,社会停滞不前;政府借国有企业占用社会大量资源,严重阻碍着私营企业、市场的成长,使扭曲了的政府与市场关系长期得不到矫正,中国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中国对待外资企业的态度也与日本形成强烈的反差。例如,轮船招商局与外资太古、怡和公司订立“齐价协议”,结果没能约束外资企业的活动,却限制了中国私人资本进入水运行业,最终轮船招商局也受到外资企业的排挤。外部环境的险恶是中国私营企业、市场得不到发展的原因之一。中日两国的差距到甲午战争前1893年已十分明显,日本10人以上工人的工厂有3019家,其中使用蒸汽动力的675家。工人人数38万人。铁路2039.6英里,使用蒸汽动力的轮船11万吨。而与此同时,中国官办工业企业24家,私人资本兴办的工业企业也只有100多家。〔28〕由于清政府限制、禁止私人开办机器生产企业,不准民间分享工业化成果,不保护私人的财产权,市场不能随私营企业的发展而成长壮大,也就不可能产生重新构建市场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动力,更谈不上主动地建构顺应市场发展需求的基础性制度了,近代中国未能走出压制型国家的藩篱而成为建制型国家。
三、直面社会:改造还是维系
英国著名学者波兰尼认为,市场在改造社会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引发社会的反向运动。〔29〕社会的反向运动实际上是社会对市场化的抗拒,抗拒包含着两种性质不同的运动。一是即将被市场化、工业化消灭的社会势力的反抗,尽管反对随市场化、工业化而来的痛苦有着合理性,但它们的反抗是要维持旧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秩序,本质上是反市场化、工业化。二是伴随市场化、工业化诞生的社会势力对因市场改造社会而产生的痛苦的反对。这种反向运动并不为了排斥市场化、工业化,而是要求减轻痛苦,消除灾难,本质上不是反对市场化、工业化,而是要求构建市场与社会的新关系。建制型国家对前者采取严厉压制、打击方式以保护市场,支持市场对社会的改造。对于后者,虽然也进行压制,但最终承认它们有权组织起来,争取必要的权利。迈向建制型国家,绝非仅仅是国家(政府)扶植私营企业发展制造业,推进工业化,促成市场的成长,还涉及调整与社会的关系,形成容许、支持私营企业发展的社会环境,进而对内涵不断变化的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规范,实现国家(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协调。在面对社会时,国家(政府)是对社会进行改造,将资源从旧社会势力手中转移出来以支持新社会势力的发展,还是维持旧的社会,继续使资源沉淀在旧势力手里阻碍新势力的成长?在面对社会的抗拒时,国家(政府)是压制旧势力的反抗还是纵容旧势力对抗市场对社会的改造?近代中日两国不同的态度导致了迈向建制型国家的不同结局。
日本政府在扶植私营企业发展制造业时,运用国家权力对旧社会强制进行改造以支持市场的发展,创造工业化、市场化所需要的社会环境。实施“版籍奉还”“废藩置县”,将原来各藩国的土地和人民收归政府,〔30〕铲除了横亘在国家与社会底层之间的中间势力,使国家权力能够直接调动社会的资源。废除身份等级制度,公卿、诸侯为华族,其臣属为士族,农、工、商统称平民,准许平民与华族通婚,四民平等,创造私营企业、市场发展的社会前提。发行公债,规定华族、士族的俸禄由公债支付。士族拿着俸禄公债转移到农、工、商等行业上去,少数人将公债转化为资本,促进了工业化,大多数人则变成为工业劳动力。〔31〕更重要的社会变革是推行地税改革,确认土地所有权,不管收成丰歉,土地税一律按地价的3%收取,以货币形式支付。地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也是建立国有企业,推动工业化的重要资金来源。通过对社会的改造,日本政府最大限度动员社会的资源,引导其从农业领域向制造业转移,促成社会的变迁。由工业化推动的市场对社会的改造也引发社会的抗拒,日本政府正确区分了不同种类的社会反抗运动,采取不同的应对方略,从而较好地把握了市场改造社会的节奏。对于旧势力的反抗,视其威胁的程度采取措施予以解决。农民的抗争针对的是过高的地税,对国家不具根本性威胁。1877年日本政府将地税税率由3%降为2.5%后,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农民的反抗。因特权被废除而反政府的旧武士则不同,他们的反抗对国家的发展方向构成了威胁。日本政府毫不留情,严厉镇压了佐贺之乱(1874年)、敬神党、秋月、荻的叛乱(1876年)、西南叛乱(1877-1788年)。对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工人罢工等,日本政府予以镇压,以保证工厂制度的顺利运行。当然,日本政府一定程度上默许工人组织工会,开展合法的斗争,以提高工资、改善工作环境、缩短工作时间等,社会与市场之间的新关系开始形成。日本政府在运用国家权力对社会进行强制改造的同时,大力发展教育,将其视为建立新社会的基础性工程,大约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结束时,日本普及了国民教育。〔32〕教育为工业化造就所需的人才和有一定文化的劳动者,有力支持了私营企业和市场的发展。概而言之,日本政府经过努力,创造了一个新的市场和一个新的社会,尽管这个市场还很不完善,这个社会还保留浓厚的旧社会残余,但为在市场与社会之间构建基础性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晚清中国屡遭外敌入侵,早已是千疮百孔,但在很长时间里拒绝变革。恰如李鸿章晚年抱怨的那样,他做了一辈子的事,不过一裱糊匠而已。〔33〕从最高执政当局到厉行新政的洋务派都坚持“中体西用”,声言不改变中国的根本,只是对在风雨中摇摆的破屋进行裱糊,作些修修补补。所谓“中国的根本”,除了纲常名教、君主专制统治等这些人们熟悉的内容外,从社会与市场关系的角度看还包括官僚特权支配社会一切,以及敌视商业、市场的社会意识等等。不改根本,其实就是维系旧的社会秩序。一是政府没有发动旨在推动工业化、市场化所必需的破除官僚特权的社会变革,致使洋务派官僚运用特权压制私营企业和市场,借助于兴办民用工业企业这一方式从民间、市场抽取资源,工业化成为洋务派阻碍私营企业、市场成长的工具。二是政府对守旧社会力量破坏机器生产不予惩罚,私营企业发展壮大缺乏相应的社会土壤。尽管清政府不支持民间发展现代工业,但完全商办的企业还是出现在中国大地上。这些企业的诞生,赋予市场新的内容,它们的存在与发展,必然引发与社会守旧势力之间的冲突,这不过是市场改造社会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急需政府的支持,清政府的表现恰恰相反。19世纪80年代初,广东南海一带丝织行会和缫丝工厂因争夺原料等等原因,发生了矛盾,致行会手工业者向新式缫丝厂发动破坏性的袭击。当时广东地方政府不仅不作疏导,反而迁就落后势力的要求,借口丝厂未经“立案”,粗暴地命令企业“永远勒停”,命令业主将“机器依限自行变价”出卖,具结“永不复开”。〔34〕事实上,旧习惯的阻碍、旧势力的破坏,是任何一个国家在转向建制型国家的时候都可能遇上的问题,能否解决,关键取决于政府的态度和行为。英国工业化初期,机器大生产导致不少手工业者破产,他们掀起反对机器生产的工人运动。同时,工厂工人开展旨在破坏机器的“卢德运动”。英国政府的反应是严厉镇压,保证工业化的顺利推进。显然,清政府纵容旧社会势力对抗新式生产,使得旧社会能够长期延续下来,中国社会的转型既漫长又异常艰难。三是由于没有变革现有社会的打算,清政府在提高民众的教育水平上乏善可陈,虽然开办了京师同文馆和一些学堂,主要服务政府而不是国家工业化、市场化的需要。正是清政府既不为私营企业、市场的发展创造前提性社会条件又不对旧势力对抗新生产力的行为给予打击,结果,新的市场无法生长出来,新的社会因素在充满敌意的旧社会中为生存艰难努力,无力推动旧社会转变为新社会,更说不上在新市场、新社会的基础上建构基础性制度了。
四、结 论
迈向建制型国家是国家形态的重大转换,是工业化启动以来人类社会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向。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并非每个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内都能顺利完成。从世界范围看,绝大多数的国家遭受到了曲折坎坷,至今仍在努力完成这一转换。比较近代中日两国迈向建制型国家的历程,我们从中或许能够发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一是原有的国家—市场—社会结构和国家形态对于一个国家在迈步走向建制型国家的时候能否选择正确的道路具有重大影响。在压制型国家,社会缺乏自主性势力,无法进行比较选择,迈向建制型国家的道路充满艰难曲折;在竞争型国家,彼此竞争的社会势力可以提出不同方案,进行比较选择,从而找到正确的道路,迈向建制型国家的道路相对顺利。二是迈入建制型国家的前提是国家(政府)创造出具有一定自主性的市场和社会。在人类社会已开始进入工业时代,创造自主性市场就是国家(政府)支持私营企业发展机器工业,使之成长为新的市场主体,以此支撑起自主性的市场;私营企业、市场、工业化是一体的,国家(政府)与市场同向发挥作用。如果依靠国有企业推进工业化,工业化与私营企业、市场成长相冲突,国家(政府)与市场相向发挥作用,缺少机器工业支撑的私营企业无法成长为实力强大的新市场主体,市场因而不能获得相对的自主性。三是工业化开始时市场面对着一个抵制它的旧社会,需要国家(政府)进行必要的改革,为市场化、工业化创造必要的社会环境;同时国家(政府)控制住市场改造社会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冲突,保证改造顺利推进,使新的社会势力随市场化、工业化成长壮大,成为具有相对自主性的新社会的支柱。四是国家(政府)在推动形成自主性市场和社会的过程中,逐步建构国家(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基础性制度,协调发挥国家、市场和社会三种基本力量。
注释:
〔1〕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武汉:武汉出版社,2012年,第17页。
〔2〕〔美〕费正清等:《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8页。
〔3〕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上·先秦两汉部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7页。
〔4〕冯尔康:《从农民、地主的构成观察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
〔5〕王德权:《东京与京都之外——渡辺信一郎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载〔日〕渡辺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中日比较史的视角出发》,徐冲译,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81页。
〔6〕冷鹏飞:《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形态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07页。
〔7〕〔8〕〔英〕威廉·G.比斯利:《明治维新》,张光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7页。
〔9〕〔美〕马里乌斯·B.詹森主编:《剑桥日本史(第5卷):19世纪》,王翔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31页。
〔10〕茅建海:《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560-677页。
〔11〕周启乾:《日本近现代经济简史》,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年,第83页。
〔12〕马勇:《重寻近代中国》,北京:线装书局,2014年,第27页。
〔13〕卢正涛:《中国建制型国家的兴起与演进——以民营经济的成长为视角》,《学术界》2015年第4期。
〔14〕Steven K. Vogel:Freer Markets, More Rules: Regulatory Reform in Advanced Industrial Countri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p.51.
〔15〕大久保利通:《近代史史料》,吉川弘文馆,1965年,第117页,转引自伊文成等主编:《明治维新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478页。
〔16〕伊文成等主编:《明治维新史》,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506页。
〔17〕〔19〕〔美〕詹姆斯·L.麦克莱恩:《日本史(1600-2000)》,王翔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9年,第192、179页。
〔18〕浜野吉等:《日本经济史:1600-2000》,彭曦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4页。
〔20〕何勤华等:《日本法律发达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0-134页。
〔21〕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39卷,第32页。
〔22〕〔27〕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第7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27-428、316页。
〔23〕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43卷,第44页。
〔24〕张国辉:《洋务运动与近代中国企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26页。
〔25〕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第6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61页。
〔26〕〔34〕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90、1501页。
〔28〕《重读甲午:清朝战败是工业化竞赛失败的结果》,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special/gongyehuajingsai/ ,2014年4月9日。
〔29〕〔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30〕〔日〕坂本太郎:《日本史》,汪向荣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64页。
〔31〕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92页。
〔32〕万峰:《日本近代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00页。
〔33〕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四。
〔责任编辑:力昭〕
卢正涛(1967—),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比较政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