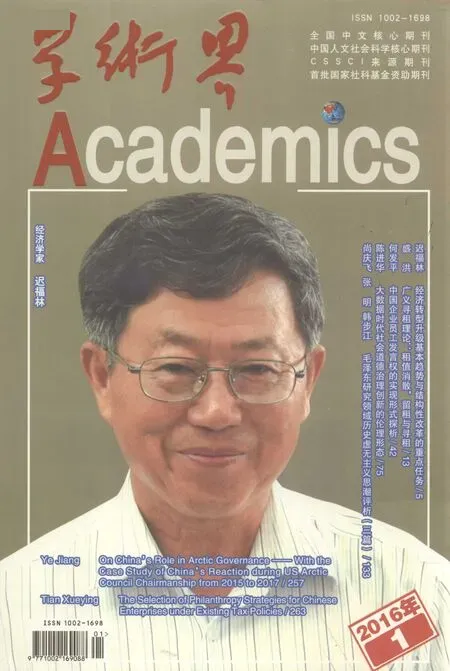从族类到气类:论朱熹的“异姓存祀”观〔*〕
○ 胡荣明
(上饶师范学院 朱子学研究所, 江西 上饶 334001)
·学术史谭·
从族类到气类:论朱熹的“异姓存祀”观〔*〕
○ 胡荣明
(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 江西上饶334001)
朱熹从其哲学体系的内在圆融性出发,依据分类与祭祀所具有的一般性原理,通过建立一种新的族类之间相属关系及其识别标志,对早期中国基于血缘或祖先之德的祭祀分类体系进行了一种创造性转化。他在“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祭祀原则的基础上,为“异姓存祀”的合法性提供一种学理支撑。这既是对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姓存祀”现象进行的学理解说,同时也是为其道统祭祀行为进行了理论道路的清理。
朱熹;存祀;祖先祭祀;道统祭祀
在生存时间的长河中,何为生者与逝者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如何形成、维系和保持这一最基本的关系?古代中国将其称之为“存祀”问题。所谓“存祀”,就是维系“家”内生者与逝者之间最基本的“祀—歆”关系。在此过程中,逝者通常以祖先的面貌出现。为了维系和保持这一关系,中国古代先民创制了一套严密甚至繁琐的祖先祭祀礼仪,其中包含了一系列的祭祀原则与祭祀程序。“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就是这样一项原则,〔1〕它在“莒人灭鄫”这一儒家“春秋大义”以及国家礼法制度的共同作用下,成为了华夏民族的集体思想而在祖先祭祀实践中被不断强调与遵行。但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收养异姓以存续祖先祭祀的情形却一直存在并引起普遍的争议,〔2〕笔者将此种现象称为“异姓存祀”。在众多讨论“异姓存祀”现象的理论陈述中,南宋理学家朱熹(1130-1200)最为系统的在自己的思想体系内部通过对社会分类体系的重构,解决了“民不祀非族”经义背景下“异姓存祀”现象的合理性及其意义转化的问题,从而为他自己以异姓的身份私下祭祀先圣先贤的行为提供了学理解说,表现了他深厚的学理素养和醇厚的经世情怀。
一、解释框架:分类与祭祀
分类,“是指人们把事物、事件以及有关世界的事实划分成类和种,使之各有归属,并确定它们的包含关系或排斥关系的过程”。〔3〕自从涂尔干与莫斯在《原始分类》一书中第一次对“分类”进行定义及学理研究之后,人类学者日益认识到分类研究的重要性。但是,分类的研究却没有给其他学科带来应有的雨露,其他研究也似乎从来没有给过分类应有的位置。〔4〕理解一个社会的分类方式、认同与差异不仅是人类学家在进行异域民族研究时的任务,当一个现代的历史学者着手对自己的历史进行清理的时候,他所面临的处境与人类学家相差无几,他们都是罗德尼·尼达姆所描述的手术复明后先天性盲人。〔5〕对于先人的生活世界,现代历史学者面对的可能是一堆陌生印象的混合,它们与自己熟知的(甚至可能也是貌似熟知)社会习俗格格不入。因此,现代历史学者在研究中应该做的或所能做的,就是要学会把先人的世界看成是先人为了自己而建构的生活世界,学会理解先人创造的别具一格的范畴。因此,他研究任务,“首先就是要理解分类的模式”。〔6〕
作为人类最基本的能力,分类可以说是人类采取行动所需要依靠的一个重要指针,如果没有分类的能力,人类将无法生存和采取行动。因为分类使人能够把握自己与别人的关系、自己与家庭的关系、自己与社团以及自己与祖先的关系,从而可以藉此采取相应的行动。分类为人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网,在这张网上人们把各种人、事物、现象、意义放在了特定的位置,由此我们会像格尔茨一样同意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人是悬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同意“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7〕文化这张“意义之网”依赖的正是分类的展开,如果没有分类,我们的意义将无从放置、意义之网也将无从编织。对于祭祀应作如是观,祭祀这张“意义之网”也需依赖分类体系的建构。
分类可以说是祭祀得以发生的前提,祭礼的形成过程正是分类的实现过程,它涉及的是一个范围极为广泛的对人的身份、人的行为方式的一种繁复的分类系统。只有符合这个分类系统的祭祀行为才是符合祭祀主体理想秩序的,或者说只有符合这个分类系统的祭祀行为才是合法的。对祭礼程序进行划分、对社会关系进行甄别、对祭祀主体予以确认、对祭品进行归类或排除、对仪式进行认定考量……这个分类的过程把祭祀者认为有必要由祭礼处理的事实、社会关系等等一切他们认为需要的要素安置在祭礼之内,祭礼对管辖范围内的所有事项的位置都进行了安排,表达了祭祀者心目中理想的祭祀秩序,这种秩序也在祭礼创制者的分类观念中得以实现。当然,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祭祀活动或祭祀原则及其相应的分类体系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在这过程中,要么创制新的祭祀活动或祭祀原则以适应新的社会分类体系,要么对分类体系作出调整以保持原有祭祀活动或祭祀原则。
就本文的研究主题而言,分类观念的梳理无疑是一条全面理解朱熹“异姓存祀”观的有效途径。当然,在这之前我们还是应该对早期中国“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这一祭祀原则所依赖的分类模式进行分析,因为这是朱熹建构“异姓存祀”观的渊源所在。
二、德性与“民不祀非族”
作为一项祭祀原则,“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观念的成立乃是依赖于这样一套分类体系,它将生存世界的居住者根据生命形态分为生者与逝者,他们分别以神(祖先)与民(子孙)的形象出现,并通过“祀—歆”这一祭祀活动形成了一种共存关系,不同世代的人经由此关系形成了一个以永远祭祀祖先为前提而存在的祖先祭祀集团。当然,由于祖先的不同,这一体系又将生存世界的居住者划分为不同的祖先祭祀集团,他们祭祀着各自的祖先,并通过姓氏制度对这些不同祭祀集团加以区别,同时用“不祀—不歆”的祭祀禁忌保持着他们之间的排斥关系。
(一)祖先之食
早期中国先民在祖先崇拜的基础上通过“血食”观念而将生者与逝者,祖先(神)与子孙(民)联系起来。所谓“血食”,就是祖先接受祭祀。依照何炳棣先生的说法,最早、最基本的原始人类相信死者和生者一样,都需要经常的饮食。而且随着祖先崇拜的升级,祭享之物标准越来越高,注重牲祭,于是便产生祖宗之灵必须“血食”的信念。〔8〕生者与逝者,祖先与子孙就在“血食”观念的指引下,通过“祀—歆”确定了他们之间的双向共存关系,这种关系的确立意味着早期中国先民的生存世界乃是一个以永远祭祀祖先为前提而存在的祖先祭祀集团。
各部族可以看成是由始祖与子孙后代所构成的一个大家庭,亦即人神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存续是以祖先神依赖于子孙的祭祀,而子孙的生存也依赖于祖先神的守护这种两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为前提。〔9〕祖先与子孙在祭祀与生命中相互找出自己存在的根据,达到共存。当时把不能祭祀祖先用“不血食”来表现,“不血食”就意味着共同体的灭亡。比如《国诸·齐语》记载桓公恐政治腐败国家灭亡时说:“恐宗庙之不扫除,社稷之不血食”。《国语·吴语》也有类似记载:“求残我社稷宗庙,以为平原,弗使血食”。“宗庙不血食,绝其后类”(《吕氏春秋·当染》)说的是共同体的灭亡。当时所有的家、世族、诸侯国都是一个以始于祖先的生命,通过祖先与子孙的相互依存关系永远继承延续的祭祀集团。《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曰:“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就明确了续祀和共同体繁衍间的依存关系。对这种以永远祭祀祖先为前提的人神共同体来说,“祀”就成为了国之大事。
不仅如此,在早期中国先民的宗教观念中,具体的祖先与特定的共同体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这种关系主张祖先需要的血食(祭祀)只能由自己的子孙奉献,相反的,子孙的生命也被祖先所左右。这种对应关系如此之强,以他们认为人们不应当祭祀非己族类之(祖先)神,即“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因此,这便涉及到通过何种分类,以求确立这种民神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祭礼创制者还需要设立另外一种分类体系,以便解决“非类”或“非族”识别判定问题,从而使祭祀得以顺利完成。出于这一需要,姓氏制度便被作为一张“意义之网”被编织出来,它将社会群体进行同姓与异姓的分类方式就成为理解早期中国延续祖先祭祀实践的一个关键点。
(二)祖先之德
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指出,作为一种分类,姓氏乃是起源于标准化和清晰化的国家工程。斯科特认为,中国是较早建立固定姓氏制度的国家,他在采纳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出于征税、征兵、征劳役的目的,秦朝就试图给它治下的人口强加姓氏。〔10〕斯科特揭示了中国姓氏制度所具有的社会认证方面的世俗性功能,但他这一富有想象力的分析并不足以说明中国姓氏制度所具有的诸多层面的功能。〔11〕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姓氏制度最主要的功能乃是区分血缘群体,是对同一血缘群体之血缘同一性的认知和表征。〔12〕也就是说,姓氏是代表一定的血缘遗传关系的种族记号,通常是指一个家族长期以来共用的一种表示同宗同族的代号,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以家族观念加以支撑的身份确认体系的一部分。〔13〕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相同的血缘是人群结合最自然、最原始的方式,早期中国的社会群体也是以血缘因素为原始群聚的前提,但姓氏一开始并没有特别标识血缘成分的功能,正如杜正胜所指出的,“姓氏皆缘政治要求而生,血缘意义反而是后起的”。〔14〕所以,要理解姓氏制度对于先秦时期“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观念中“类”与“族”的真正含义,还应该从“政治要求”上探寻早期中国姓氏制度建立的标准。
现代学者在经过梳理解读早期中国文献后发现,姓氏制度是在“赐姓”“命氏”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其基础乃是根源于血缘的“德”或曰“祖先之德”。〔15〕作为族群划分的标识,早期中国姓氏乃是一个“建德”的过程。郑开就指出,早期中国凡涉及“姓”“氏”远源的记叙,都不能不诉诸始祖神话传说,以及“祖先之德”,他指出祖先祟拜乃是“姓”“氏”制度的深刻背景。〔16〕这个“德”是特属于某一族群的共同属性,而不是道德善行之义。〔17〕它的原始语意是指“族群禀性”,萧延中称其为“德性”,他指出,所谓“姓”即“性”(性格、性质),“性”即“德”。因此,导源于“祖先之德”的“德性”就成为一种文化界标,具有了区别族群边界的分类功能。〔18〕因此,对外族而言,“德性”具有独占性的特征;对本族而言,“德性”在族内具有开放性特征,族人都具有同样的“德性”。所谓“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就是这种族群划分的结果。
“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就是基于同姓与异姓的这种区分所衍生出来的集体祭祀观。
这一祭祀原则要求祭祀者必须与所祭祀的祖先不仅有生物性的血缘关系,同时要求两者之间文化性的“德性”关联。而不论是生物性的血缘关系还是文化性的“德性”关联,其最简便经济的识别标志就是姓氏制度。
三、理气与“异姓存祀”
春秋战国以降,虽然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两三代的血缘团体(家庭)作为政治社会的基本单位取得了日益独立的地位,姓氏制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作为一种集体思想,延续祖先祭祀仍是人们最大的愿望。只不过小家庭的脆弱性使得他们在延续祖先祭祀方面面临更大的风险。所以无后家庭无视“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祭祀原则与国家礼法的禁止性规定,收养异姓以延续祖先祭祀便成为一种普遍现象。〔19〕至刘宋时,庾蔚之曾提出立异姓为后较有说服力的见解,他说:“神不歆非类”,盖舍己族而取他族为后。若己族无所取后而养他子者,生得养己之老,死得奉其先祀,神有灵化,岂不嘉其功乎!〔20〕庾蔚之站在实用主义的立场对“神不歆非类”的原则进行修正,他并没能从社会分类体系的标准方面为“异姓存祀”给出整体性的哲学解答,朱熹所从事的就是这样一项工作。
(一)祖先之气
祖先祭祀在朱熹的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不仅亲定祭礼,而且还努力将之整合进一个庞大而严整的哲学体系中以求作出一个通融性的解释。朱熹是以“理”“气”两个范畴来解释天地万物的生成的,他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21〕在朱熹看来,理与气是天地之间的两个基本要素,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本源。从这一宇宙生成论的观念出发,朱熹通过对气之聚散的状态分类对生存世界的生、死以及与此相关的祖先祭祀问题做出了解释。
在朱熹看来,“只是这个天地阴阳之气,人与万物皆得之。气聚则为人,散则为鬼。然其气虽已散,这个天地阴阳之理生生而不穷。祖考之精神魂魄虽已散,而子孙之精神魂魄自有些小相属”。〔22〕祖先祭祀行为的对象是死者,死者的灵魂化为气,但两者之间有着从属的关系,因此祖先之气能通过祭祀者的行为而得以与生者之气发生“感—应”。朱熹说:“自天地言之,只是一个气。自一身言之,我之气即祖先之气,亦只是一个气,所以才感必应”。〔23〕可见,气乃是祭祀者与其对象之间发生“感应”(又可称“感格”或“感通”)的依据。对此,朱熹进一步解释道:“然人死,虽终归于散,然亦未便散尽,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远者,气之有无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孙,毕竟只是一气,所以有感通之理”。〔24〕可见,气的延续是使祖先接受祭祀的因素。因此,这种双向共存的“感—应”关系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就敬奉的祖先而言,祖先之气本来就在子孙身体中传承运行;就子孙自身而言,“我之气即祖先之气”,因而这样的沟通是极其自然而且有效的,能够“有感必应”。〔25〕当然,在这种“感—应”关系中,朱熹固然强调从祖先继承下来的特殊之气的重要,但朱熹同时也强调:“但有子孙之气在,他便在。然不是祭祀时,如何得他聚!”〔26〕可见,朱熹以为祖先之气之所以能够在祭祀的时候为其子孙触动,需要有“子孙之气”的在场,子孙之气及子孙的祭祀活动乃是重聚祖先之气的机关。
另外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就是朱熹也强调祖先之鬼神也有独立于血缘关系而存在的特点,祖先的精神魂魄作为气,可能浩然长存,不断转化。朱熹说:“若说有子孙底引得他气来,则不成无子孙底他气便绝无了。他血气虽不流传,他那个亦是浩然日生无穷。”“不成说有子孙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无子孙,其气亦未尝亡也。”〔27〕可见,朱熹认为就算没有子孙,祖先之气亦“浩然日生无穷”,亦有“感格之理”,可以通过适当的祭祀活动“引得他气来”。这就为“异姓存祀”行为留下了空间。
可见,朱熹通过气尤其是子孙之气,在其哲学体系内部建立起一座沟通生者与逝者、祖先与子孙的桥梁。他成功的将气之“感—应”作为祖先祭祀得以发生的基础,从而在血食之“祀—歆”之外建立了一种新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还超越了祖先之德,而更加着眼于子孙之诚。
(二)子孙之诚
祭祀者必须与所祭祀的祖先有气属关系,但是仅仅气属关系不足以确保“感—应”关系的发生。“诚”作为礼仪的一个基本的因素,对于促成子孙之气与祖先之气的“感—应”具有重要的作用,朱熹就特别从祭祀者的角度探讨了诚的重要性。朱熹说:“毕竟子孙是祖先之气。他气虽散,他根却在这里;尽其诚敬,则亦能呼召得他气聚在此。”〔28〕这里的“根”,可以解释为祖先之间的血缘关系,因为祖先和后代拥有父子代代相传的“气”。〔29〕朱熹说:祖宗气只存在子孙身上,祭祀时只是这气,便自然又伸。自家极其诚敬,肃然如在其上,是甚物?那得不是伸?此便是神之著也。所以古人燎以求诸阳,灌以求诸阴。谢氏谓“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已说得是。〔30〕这里所谓的“感格”显然与“气”有关,但仅仅说“气”还不够,在具体的祭祀行为中,朱熹认为还要讲求行为者的内心诚敬,所以说“能尽其诚敬,便有感格”。朱熹说:“故祭祀之礼尽其诚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这个自是难说。看既散后,一似都无了。能尽其诚敬,便有感格,亦缘是理常只在这里也”。〔31〕由于祖先之气与子孙之气一脉相承,因而诚敬即能感格。
对于子孙之诚在祖先祭祀中的作用,还有一个事例值得特别提出。徐居甫曾就异姓收养过程中的异姓子孙主祭的困惑咨询朱熹。徐居甫说:后世礼教不明,人家多以异姓为后,寓所见乡里,有一人家兄弟二人,其兄早亡无后,遂立异姓为后,后来弟却有子,及举行祭礼,异姓子既为嫡主,与凡题主及祝版皆用其名,若论宗法,祭惟宗子主之,其他支子但得预其祭而已,今异姓为后者,既非祖宗气血所传,乃欲以为宗子而专主其祭乎?寓意欲以从弟之长者共主其祭事,亦同著名行礼,庶几祖先之灵,或歆享之,不知可以义起否?伏乞裁教。〔32〕
在这种情况下由谁来主持祭礼呢?徐居甫认为按照规定祭祀不应由弟弟的继承人承担,而应由长兄之子承担。但在这一事例中,长兄之子是异姓养子。针对这种特殊情况,徐居甫主张由弟弟的儿子与哥哥的养子共同承担祭祀职责。朱熹答道:“立异姓为后,此固今人之失,今亦难以追正。但预祭之时,尽吾孝敬之诚心可也”。〔33〕结合前文的研究,我们认为朱熹主张就算没有子孙,祖先之气亦浩然长存并有“感格之理”。鉴于子孙之诚在祖先祭祀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朱熹同样从“诚”的角度明确了“异姓存祀”的合理性。
四、道统与圣贤祭祀
朱熹试图通过子孙之诚来建构起子孙之气与祖先之气的感格,为“异姓存祀”提供了一个哲学的解说,但“异姓存祀”也毕竟还是一个拟制的血缘关系。朱熹面临的最大挑战乃是他如何能够解释他以异姓的身份在私下场合供奉祭祀与他自己没有血缘关系(拟制)的先圣先贤。为了克服这一困境,朱熹在道统祭祀体系中从两个方面克服了“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祭祀禁忌,建立起了他更具社会实践意味的“异姓存祀”观。
(一)公共之气
前文已经提到,朱熹认为“理”“气”是天地之间的两个基本要素,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本源。在朱熹看来,存在于天地之间的理是“公共之理”,气则是“公共之气”,他说:“这理是天下公共之理,人人都一般,初无物我之分”“天地公共之气,人不得擅而有之”。〔34〕这里所谓的“公共”,是不为任何个体所私有之意,公共的理气是尚未生成个体之前的弥漫于天地之间的理气。朱熹就是从气的公共性出发,为他自己的道统祭祀提供了哲学根据。
曾有门人根据祭祀对象的分类,向朱熹询问天地山川之祭祀,自己祖先之祭祀,上古圣贤之祭祀与理气问题有何关联?朱熹就明确的指出,“有是理,必有是气”“都是理,都是气”,认为理气在祭祀对象中自是不可分的,因为不仅理是天地公共之理,气亦是“天地公共之气”,在朱熹看来,天地山川、祖考、圣贤皆是“此公共之气”。在此基础上,朱熹强调指出,人的三种祭祀行为:祭天地、祭圣贤、祭祖先,都在“气”的前提下,祭祀者与祭祀对象可以彼此“相通”(亦即“感通”或“感格”)。〔35〕
虽然天地、圣贤、祖先都是“天地间公共之气”,但并不意味着“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祭祀原则失效,朱熹从公共之气的哲学立场出发,提出了一种关于“类”与“非类”“族”与“非族”的新认知,即看祭祀者与祭祀对象的“气”类是否相关。对此,田浩曾在其有关朱熹鬼神观与道统观的杰出研究中就注意到,朱熹在界定何谓适当的祭祀活动时,就特别强调当适当的人员进行祭祀活动时,有一种身份联结或所属关系。如朱熹就曾指出,“若不属我,则气便不属我,则气便不与之相感,如何祭得他”。〔36〕朱熹还以天子祭天、诸侯祭社稷为例,突出了祭祀者与接受恰当祭祀的神灵之间的“属”和“气类”的联结关系。他说:“如天子则祭天,是其当祭,亦有气类,乌得而不来歆乎。诸侯祭社稷,故今祭社亦是从气类而祭,乌得而不来歆乎。今祭孔子必于学,其气类亦可想”。〔37〕对于祖先祭祀,朱熹也是以子孙之气与祖先之气“有小相属”为前提的。
(二)圣贤之道
那么如何判断气类之间是否相属呢?同时,他如何判断他自己与他所祭祀的异姓先圣先贤的气是相属的呢?对此,朱熹从一种社会实践视角,提出了判断各种气类是否相属的标准。
这种标准不仅是一个“义理”性的话题,而是充满了实践意味,用他的话说就是要“负荷”。他说:“天子统摄天地,负荷天地间事,与天地相关,此心便与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虚气,与我不相干。如诸侯不当祭天地,与天地不相关,便不能相通。圣贤道在万世,功在万世。今行圣贤之道,传圣贤之心,便是负荷这物事,此气便与他相通。如释奠列许多笾豆,设许多礼仪,不成是无此姑谩为之!人家子孙负荷祖宗许多基业,此心便与祖考之心相通。”〔38〕
在朱熹看来,天子因为“负荷”天地间事,所以能与天地之气相属,诸侯不“负荷”天地间事所以不当祭天地,否则就违背了“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原则而不能相通,对于子孙祭祀祖先也是这样,因为子孙负荷了祖宗许多基业,所以两者之心气能够感通。在此基础上,朱熹指出,“圣贤道在万世,功在万世。今行圣贤之道,传圣贤之心,便是负荷这物事,此气便与他相通”,这句话的含义是非常明显的。在朱熹看来,学者承担的使命和任务就是传圣贤之统绪,继圣贤之心志,行未尽之王道,做到这些,就是“负荷这物事”,就能与作为异姓的圣贤之气相同而不违背“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原则。就这样,朱熹将哲学性的气类相属的问题转化为了事业负荷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将宗教性的祭祀创造性的转化为一种充满人文精神的道统传续问题。
通过这种改造,朱熹成功的消除自己私下祭祀异姓圣贤之间所可能面临的指责,他所要做的就是进一步寻求一种技术分类能够顺利的建立起自己与圣贤之间的联系,证明自己是“行圣贤之道,传圣贤之心”,负荷圣贤事业的人选。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着力描摹的道统传承的谱系就是这样一种技术性分类,它表明朱熹在道统接续中的地位。
对此,朱熹在沧州精舍祭祀孔子及其他儒家先贤的行为说明他已成功的建立起了自己与古今圣贤的相属问题,朱熹在祝文中说:“恭惟道统,远自羲轩。集厥大成,允属元圣。述古垂训,万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时雨。维颜曾氏,传得其宗。逮思及舆,益以光大。自时厥后,口耳失真。千有余年,乃曰有继。周程授受,万理一原。曰邵曰张,爰及司马。学虽殊辙,道则同归。俾我后人,如夜复旦”。〔39〕这表明朱熹一方面将在《大学章句序》和《中庸章句序》中关于道学传授的谱系结合起来,认为道统可以追溯至伏羲和黄帝,尔后孔颜曾孟得以发扬光大。就宋代而言,继承道统的有周敦颐、二程、邵雍、司马光、李侗等,朱熹认为这些均是道统的继承者。同时朱熹将自己的老师李侗作为从祀对象,将其与孔颜、周、二程相比。〔40〕
总之,朱熹成功克服了“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祭祀原则,并通过“异姓存祀”的形式彰显了自己作为道统继承人的合法性。〔41〕在这些祭祀中,先圣始终作为“道”的象征而存在。〔42〕而朱熹则以一种“祀其道”“祀其教”而非“祀其人”方式,在心志以及信念上达到与圣贤志同道合、心心相契的境界。〔43〕
四、结 语
综上所述,朱熹的“异姓存祀”观不是对早期中国“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观的否定或取代,他只是对其基于血缘或祖先之德的祭祀分类体系进行了一种创造性转化。朱熹对传统的祖先祭祀观是遵守的,他所做的只是从其哲学体系的内在圆融性出发,为“异姓存祀”的合法性提供一种学理支撑。这既是对社会普遍存在的异姓存祀现象进行的学理解说,同时也是为其道统祭祀行为进行理论道路的清理。而不论是通过气之感应以及心之诚敬为民间社会收养异姓以存续祖先祭祀提供哲学性的解说,还是通过气之相属以及事业之“负荷”为自己祭祀异姓圣贤提供实践性的根据。朱熹都只是在对“类”“族”进行重新界定,他所作的仅仅是依据分类与祭祀所具有的一般性原理建立了一种新的族类之间相属关系及其识别标志。在这过程中,与早期中国祖先祭祀“祀—歆”关系中充满浓厚原始宗教意味的血食观念相比,虽然朱熹将祖先祭祀建立在气之“感—格”的基础上的做法更具理性,但两者都是一种人文精神的体现,早期中国祖先祭祀是讲求祖先之德注重的氏族文化的存续,而朱熹的祖先祭祀及道统祭祀也是讲求祖先基业以及圣贤之道的“负荷”与传承。其间所蕴含的使命感不是一人、一家、一族或一党之私,不论是“同姓存祀”抑或是“异姓存祀”,它们都是希望通过世代间的生命连结,实现一种突破自然之“私”而通向文化生命的“公”域。
注释:
〔1〕关于先秦“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观念,参见陈戍国:《中国礼制史》(先秦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1页。
〔2〕〔19〕〔美〕沃特纳:《烟火接续:明清的收继与亲族关系》,曹南来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7-76页。
〔3〕〔法〕法爱弥尔·涂尔干、马塞尔·莫斯:《原始分类》,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页。
〔4〕〔7〕王启梁:《法律是什么?——一个安排秩序的分类体系》,《现代法学》2008年第4期,第96-104页。
〔5〕〔6〕〔英〕罗德尼·尼达姆:《原始分类英译文导言》,〔法〕法爱弥尔·涂尔干,马塞尔·莫斯:《原始分类》,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05、106页。
〔8〕何炳棣:《何炳棣思想制度试论》,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4年,第20-21页。
〔9〕〔日〕高木智见:《先秦社会与思想:试论中国文化的核心》,何晓毅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71-129页。
〔10〕〔美〕詹姆斯·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修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76、78页。
〔11〕纳日碧力戈:《姓名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36-37页。
〔12〕袁雪石:《姓名权本质变革论》,《法律科学》2005年第2期。
〔13〕郭明瑞等:《民商法原理》(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80页。
〔14〕徐复观:《中国姓氏的演变与社会形式的形成》,收入《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台北:学生书局,1975年,第379页。
〔15〕杜正胜:《传统家族试论》,载黄宽重、刘增贵主编:《家族与社会》,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1-5页;郑开:《德礼之间: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88-234页。
〔16〕郑开:《德礼之间:前诸子时期的思想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88-234页。
〔17〕王健文:《奉天承运》,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第71页。
〔18〕萧延中:《德性:群族禀赋的精神象征》,《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20〕杜佑:《通典》礼二十九,《异姓为后议》。
〔21〕朱熹:《答黄道夫》,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755页。
〔22〕〔23〕〔24〕〔25〕〔26〕〔27〕〔28〕〔29〕〔30〕〔31〕〔34〕〔35〕〔36〕〔37〕〔38〕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086年,第46、47、47、170、50、173、47、1546、2084、46、76、46、612、177、46-47页。
〔32〕陈淳:《北溪字义》,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59-60页。
〔33〕朱熹:《答徐居甫》,《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790页。
〔39〕朱熹:《沧州精舍告先圣文》,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050页。
〔40〕朱熹:《挽延平李先生三首》,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08页。
〔41〕〔美〕田浩:《朱熹的鬼神观与道统观》,载《21世纪的朱子学──纪念朱熹诞辰870周年逝世800周年论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1-183页;肖永明:《书院祭祀中的道统意识》,《哲学与文化》2008年第9期,第31页。
〔42〕李继祥:《宋明理学与东亚儒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页。
〔43〕张清江:《书写、聆听与超越:论朱熹“祝告先圣”行为中的意识体验及其意义》,《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第11-16页。
〔责任编辑:黎虹〕
胡荣明(1981—),历史学硕士,上饶师范学院朱子学研究所讲师、江西省2011朱子文化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
〔*〕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朱子学学术史”(项目编号:13ZX0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