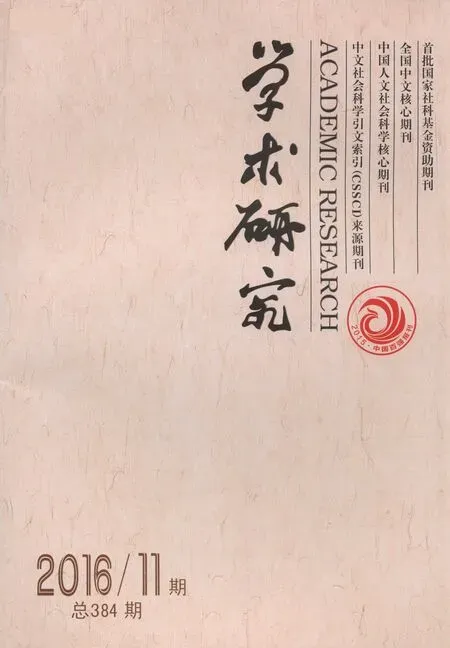阿列克西耶维奇的纪实小说叙事艺术*
侯海荣 胡铁生
阿列克西耶维奇的纪实小说叙事艺术*
侯海荣 胡铁生
白俄罗斯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西耶维奇以倾听者角色用“第三只眼”完成了关于历史题材的宏大叙事,其口述纪实小说毫无刻意雕饰藻绘,通过声音纪实原生态的方式呈现了俄罗斯政权现当代不同史程中的恶之花。小说文本诸多对比元素铸就了超强的审美震撼力,作品中审美客体通过各种对立关系相互抗衡、映衬和阐释,接受主体在多重声音、观念、画面的刺激下形成了复杂的立体式审美感受。从审美经验构成的审美感知、想象、情感、理解四要素观之,阿列克西耶维奇口述小说的审美张力具体体现为:场景反差与审美感知、比拟反差与审美想象、人性反差与审美情感、时空反差与审美理解四重审美效果。
阿列克西耶维奇 诺贝尔文学奖 口述小说 声音纪实 审美张力
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Светлана Алексиевич,1948—,以下简称阿氏)2015年登上“文学奥运”的最高领奖台。德国出版商与书商协会于2013年为其授予德国书业和平奖时曾称她“创造了一个将在全世界得到回响的文学门类,必将掀起证人与证词涌现的浪潮”。[1]将自己的作品定性为纪实文学时,阿氏更加倾向于使用“文学—文献小说”(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документальныйстиль)一词。貌似毫无铅华的口述纪实小说,虽具有显见的文献性,但其文学性体现在阿氏对声音复调的审美学加工以及反差叙事带来的语言质感,在一定程度上趋近于受众的尚实与求新心理,给阅读者期待视野带来意外的审美收获。
一、非虚构的“声音纪实”
阿列克西耶维奇是第14位女性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总共108次评奖中,这是诺奖第二次颁奖给非虚构作品,①第一次颁给英国温斯顿·丘吉尔(Winstоn Сhurсhill),代表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英语民族史》。体现了“诺奖评委在文体方面一个特意为之的新关注”。[2]“非虚构叙事”是基于想象与虚构退场后的新现实主义重构,昭示出作家面对历史真相缺失而做出的反拨,是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对纪实书写的共同渴望。然而,阿氏的口述纪实又并非等同于现在进行时的场面纪实,而是通过回溯的方式将读者带回苏德战争、阿富汗战争、核反应堆爆炸以及苏联解体的历史进行时。这种纪实方式通常被界定为“声音纪实”。
阿氏之所以采取声音纪实的写作范式,首先是由于作家本人对声音的职业敏感性与深刻理解。历史文牍通常为一些所谓的主流声音进行存档,而社会底层民众和弱势群体在官方记录中常常处于话语缺失状态中,只有伟大的作家才敢于钩沉一个时代的多声部。诚然,阿氏并非口述小说的开创者,从比较文学的视阈来看,口述实录文学乃世界文坛的一种共时性现象。譬如,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美国作家斯·特克尔(Studs Tеrkеl)的《好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口述历史》,中国作家张辛欣的《北京人》等。前苏联文学中,斯米尔诺夫(С.С.Смирнов)的《布列斯特要塞》、索尔仁尼琴(А.И.Солженицын)的《古拉格群岛》、格拉宁(Д.Rеранин)的《奇特的一生》等作品皆属此类,尤其是阿达莫维奇(А.Адамович)的《围困纪事》和《我来自火光熊熊的村庄》等作品的采访实录创作方式得到阿氏的高度赞赏:“故事就在大街小巷里,就在芸芸众生中”。[3]阿氏毕业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新闻系,曾在多家报社任职记者。口述实录小说被其文体性所规定,必然注重对事实客观性乃至新闻性的耦合。因此,她以资深记者的身份收集资料,以文学的方式进行写作。阿氏的纪实作品,可被视作新新闻主义在当下的回归,此乃“纪实文学与新闻学的联姻成就了作者的荣光”。[4]从听觉叙事的起源来看,声音作为个体情感与诉求的具体表达,更利于较大范围的“全天候”式沟通,因此出现了视觉符号(手势)向听觉符号(语言)的演化。“重返听觉,强调的是人类的多元感知平衡,重回到被遮蔽的艺术现实、创作现实和批评现实”。[5]阿氏坦承自己俨然“变成一只越来越巨大的耳朵,自己所阅读的,是声音”。[6]由此可见,阿氏对声音的笃信就是对现实的尊重,对声音的情有独钟是其创作观、价值观、文学观的反映。生活乃创作不朽的源头活水,藉此成为作者观察世界、洞察历史的一种方法,因此导致其文本厚重的历史自觉意识并构成作家深邃的文学情结:现实感、真实感、忧患感、关切感、使命感。正是由于阿氏作品声音的纪实性,其作品被选入教材的相关内容被删除也在情理之中。政府指控她是美国中央情报局(СIА)间谍,作家被迫侨居意大利、法国、德国和瑞典等地。作家本人在获奖演说中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类知道的真相,要远远多于文学的记录。所以我在做什么?我收集日常所感所想,我收集每一寸光阴”,“在我的书中,这些人述说着他们自己的小历史,使得大历史在无形中也得以窥见。”[7]据此,我们可以看出阿氏深谙真实声音所具有点对面的特质,读者对声音的远程接收使其共享功能得以现实化,因此阿氏通过声音来谛听尘世万象,声音振聋发聩的作用令读者沉迷陶醉。获奖后她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我的声音从此获得了新的意义。至少,当权者不能再轻易地回避我,他们不得不倾听我的话语。而且有很多人本来已经没有力量去相信什么,我的获奖也许能给予他们些许力量。”[8]
阿氏小说文本并非各种粗粝声音的嘈杂外放,而是体现出声音复调的艺术风貌。正如托尔罗夫(Tsvеtаn Tоdоrоv)所言:“从两个不同的视点观察同一个事实,就会写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实。”[9]一方面,阿氏作品大面积以“我”的称谓出现,这种“内聚焦叙事”①内聚焦叙事是热拉尔·热奈特(Gеrаrd Gеnеttе)在《论叙事话语》中提出来的,指叙述者只说出某人物所知道的情况。自传体、日记体、意识流小说经常使用此法。从聚焦效果来说,除了内聚焦叙事,还有零聚焦叙事和外聚焦叙事。参见张寅德:《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43页。拉近了叙述者和读者的心理距离。同是卫国战争这一史实,《我还是想你,妈妈》采取的是儿童视界,作品贯以儿童的叙述姿态,将儿童叙事无忌的语言品格发挥得淋漓尽致;《我是女人,也是女兵》则以女性心灵深处的缠绵曲折来对抗男性战争叙事的巾帼话语呈现。作品信息传达的这种策略类似绘画中散点透视的技法。于是,在一个核心事件的统摄下,其作品形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威势,聚集成一股强劲的话语力量。正是这种声音的多样性统一,文本在丰富多彩的叙述中彰显内在血脉的一致性。按照福柯的观点,话语本身构成权力,它与社会文化实践(sосiо-сulturаl рrасtiсе)相联。[10]通常,女人与儿童处于社会的边缘,据此,叙述者高度个性化的声音所负载的大量历史信息与情感信息,使读者获得了强大的同情能力。因此,阿氏的系列战争作品被苏联作家维·康德拉季耶夫(Bячеслав Kондратьев)誉为在战争文学领域开发了“深深的岩层”;[11]另一方面,阿氏作品由声音群体组成的复调和弦使文本的意义内涵衍生不断扩大。黑格尔(G. W. F. Hеgеl)曾指出:“在音乐里,孤立的单音是无意义的,只有在它和其他的声音发生关系时才在对立、协调、转变和融合之中产生效果。”[12]该论断对于阿氏小说具有同样意义。声音在纪实中的作用是创造性的,阿氏多部作品并不全是“我”的直接叙述,而是插入了解密档案、往来信札、报纸通讯、文学片段、作者笔记、采访电话等,显示出叙述路径的多样性与开放性,这就规避了因个人视野限囿带来文本叙述的片面性,同时也给文本解读提供了互文性。譬如,《二手时间》在前言中引用德国俄罗斯问题专家费德勒·斯特潘(Stераn Fеdеrеr )的话:“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记住,若恶势力在全世界获胜,要被追究的首先不是恶方的驯服执行者,而是善方的清醒执行者”;[13]《锌皮娃娃兵》引用萧伯纳(Gеоrgе Bеrnаrd Shаw)的名言:“历史会说谎”;[14]《我还是想你,妈妈》中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Фёдор Mихáйлович Достоéвский)的提问:“无辜的孩子哪怕流下一滴泪水,我们是否能为此找到一个充分的理由?”[15]等等。从叙事学理论观之,阿氏作品的叙事视点(роint оf viеw) 出现并置、交叉、补位等多重方式,属于限制叙事视点基础上自然的视点转换,各种声音的相互抵牾、相互阐释、相互佐证,更加逼近了历史原貌。
阿氏在文本中既对大量的声音保持了原汁原味的特色,同时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审美处理,主要体现在由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共同完成的叙述互动中,作者对叙事频率、叙事速度以及叙述节奏等方面的有机把握。对于叙述者心路历程的呈露,小说文本常常以揣测、探问、反诘的形式表现出来。譬如,“许多年过去了……现在我想问:上帝是不是看到了这些?他是怎么想的……”[16]《锌皮娃娃兵》中每一部分的开头都是作者的话,“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上帝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我在《圣经》寻找什么?问题还是答案?”等等。[17]这样,作者饱含哲理色彩的点睛之笔与被采访者的问语相映成趣,凝聚成警句般的经典和睿智。文本在叙述过程中还备注了哭泣、流泪、思索、沉默等面部表情与抬头、点烟、画十字等肢体语言,从而发挥了声音的造型能力,其言外之意留给读者去填充,进而引发读者对生命本体意义的追寻和对人的生存价值的追问。正如《日瓦戈医生》中对拉拉的赞美:“时代的所有主题,它的全部眼泪和怨恨,它的任何觉醒和它所积蓄的全部仇恨和骄傲,都刻画在她的脸和她的姿态上。”[18]亦如伊凡·布宁(И.А.Бунин)《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中的主人公一样,他们不连贯的感觉和思考占据了作品的主要篇幅,充溢着“关于过去的杂乱回忆和对未来的模糊猜测的不停顿的流淌”。[19]随着人物意识代替人物性格在作品中成为主角,“意识流”这一叙事策略瓦解了小说以故事情节为轴心的写作传统。阿氏的作品正是借鉴了这样的书写模式,有时作家全然不顾及起承转合的行文逻辑,故意在文中出现凌乱、断裂、不完整的絮叨式叙事方式。作家在作品中虽并未对叙述者内心世界展开剖析和挖掘,但作品侧重表现的恰恰是人物的思想、情感、心理和精神生活。因此,正如阿氏认为自己的记录犹如一台黑匣子一样,其作品堪称俄罗斯民族命运的备忘录,同时也是特殊时期民族文化心理的艺术长卷和社会精神生活史。
二、文本的反差艺术
聂珍钊把储存在大脑中的文本称之为“脑文本”(brаin tехt),[20]对于口述小说而言,相当于被采访者的原始文本。张荣翼认为,文字文本可以物化为一种记忆方式,当新的社会需求与该文本有较多关联时就会重新焕发出其力量。[21]当被采访者将自己的记忆信息通过话语输出,就形成了以声音为载体的第一文本,将被采访者的脑文本则固化为物质文本。如何将第一文本转变为第二文本而完美面世并形成文学在公共空间内的公共性,这需要写作者醇厚的艺术功力。在声音纪实的基础上,提升语言魅力乃不二之途,因为语言是文学永在的栖身之所与身份标识。把聒噪喧哗、声泪控诉以及“厨房里的谈话”①“赫鲁晓夫小厨房”是俄罗斯十分简陋的厨房,它不仅是做饭的地方,也是饭厅、客厅、办公室和讲坛,又是可以进行集体心理辅导的地方。这是20世纪60年代苏联精英阶层的生活方式,即厨房的生活方式。参见S·阿列克谢耶维奇:《二手时间》,吕宁思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4页。赋予文学语言的表现功能,既是对作家“带着镣铐舞蹈”的创作挑战,也是非虚构写作与虚构写作的明显差异。按照阅读理论的相关观点来看,诗歌阅读也好,小说阅读也罢,经由诗学(роеtiсs)阅读抵达阐释学(hеrmеnеutiсs)阅读的关键是对语言的高度关注;当文学的话语疏离了或异化了普通言语时,就能使读者更加充分和深入地占有经验。纵观阿氏的口述小说,反差叙事尤为典型,这是作品艺术感染力产生的渊薮,其基本特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场景反差。阿氏小说中大量的声色对比具有漫画般的意蕴,因而抒怀的某些文字就突破了口述的藩篱。对于旷日持久的惨烈战争,作品复现了自然时序中非常态的场景,尤其是春秋与清晨的特殊景观。譬如,“春天冰雪消融,冰块在河上移动。村庄后面的河流上全是尸体,赤裸着,通体黑色,只有皮带扣闪着亮光”,[22]“从地平线可以看到冰雪皑皑的天山峰顶,春天整个草原因为盛开的郁金香而一片红艳,秋天葡萄香瓜都已成熟。但拿什么买呢?还在打仗!”[23]“大清早我们就看见阳光下闪烁的修道院,镀了一层金色的森林,这就是索洛维茨基群岛,在这里开办了我国第一家海军少年水兵训练学校,我们需要参加学校的建设,确切地说——是挖窑洞”。[24]诸如此类的场景反差俯拾即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当大自然生机蓬勃之时,人类却在生灵涂炭,互相毁灭。在一个句群中,前后两部分的内容有意形成了不和谐性,作者就是以这种方式将美好与暴虐、温情与血腥的对立面以看似和风细雨的笔触同步呈现出来。在这里,自然不仅是反衬战争的幕布,也成为深掘作品意义的利器。再如,白桦树作为俄罗斯的国树,已然成为这个国家民族精神的象征。俄罗斯人举办婚礼的时候,通常用白桦树进行装扮。但第一批德国人来到村子开始他们的屠戮壮举时,汽车上也以白桦树作为饰物。此种言说方式正所谓“以哀景写乐,倍增其乐;以乐景写哀,倍增其哀”(王夫之《姜斋诗话》)。当同一个描写对象从通常的感知领域转移到一个新的感知领域,即会产生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导致语义极大变化;文中充斥的各种音符在形式上极不协调,却在更高层次形成了辩证统一。
第二,比拟反差。从认知语言学角度观之,无论是拟人为物、拟物为人还是拟甲物为乙物,都属于积极修辞。阿氏作品强烈的比拟反差进一步折射出时代悲剧与人伦之殇:山河破碎,草木同悲。“我看见过,邻居家的狗在哭泣。它蹲在邻居家房子的灰烬里,孤零零的。它有一双老年人的眼睛”。[25]“第一批法西斯敌人穿着钉有铁掌的皮靴,咚咚地踏过我们的小桥,我甚至觉得,当他们经过的时候,就连大地都会疼痛”。[26]诸如此类的主观体认,直似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传达出战争时期人们直觉的原初本能体验,视觉意象的变形,给读者极强的声势移情与审美刺激。例如,敌兵从高处看到白色的水桶,以为是蒙着白头巾的人,就开枪猛射;被逮住的猫吊死在绳子上远处看像个小孩;落水后浮在水面的孩子们像是皮球一样;骨头破碎的声音啪啪作响就像熟透的南瓜等,意象极为新颖。这些描写既出乎常人的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摹写出一副儿童眼里的战争景象;看似轻松的笔调,实际传达的却是当年孩子们的痛苦经历与感受。尽管文中陈述的情绪十分克制,但法西斯分子却被描写得如此丧心病狂而不忍卒读。再如,“妈妈——就是我的整个世界,我的星球”。[27]“战争对某些人来说如同后娘,对另外一些人则是亲妈”;[28]“人民就是一群羚羊,权力是一头母狮”;[29]“俄罗斯是个伟大的国家,不是一个单开关的燃气管道”。[30]个人与家庭的关系、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人民与国家的关系、政府与专制的关系,通过比拟判断的话语方式一针见血地表现出来。作品的暗喻修辞与无意夸张,极大地拓展了作品涵盖的深度与力度。
第三,人性反差。人性历来是战争文学的永恒母题。作为人学的文学,在揭示人本质的同时,总是力图探讨人际关系的伦理价值观。阿氏作品中的人性反差颠覆了苍白的道德训诫,成为关于战争与人性二元悖论的感性回答。文中出现叙述者对保育院教导员的幸福回忆、陌生人馈赠一块面包的温暖回忆、父母罹难被邻居收留的感恩回忆等,民族浩劫中的同仇敌忾、休戚与共跃然可感。“我透过篱笆悄悄地偷看他们,看起来,他们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我想看看,他们长着什么样的脑袋,为什么我有这样的预感,他们都长着不是人类的脑袋……已经有传言,他们会杀人,会放火。可他们坐在汽车上,谈笑着,心满意足的样子。”[31]妈妈漂亮的脸上遭到枪击,喜欢重复“这世间——让人百看不厌”诗句的爸爸阵亡,我们埋葬了开朗智慧、热爱德国音乐与德国文学的奶奶,等等。所有杀人狂魔人性的分裂、畸变与无辜者的文化心理、民族性格反差式描写,是对脸谱化、格式化、抽象化的人性解构。事实上,人性书写在众多体裁、题材中司空见惯,只不过阿氏作品的人性言说,由于依赖叙述主体的在场而更加鲜活真切。
第四,时空反差。过去是不可逆的,对于阿氏这类回忆性口述小说而言,时间与空间是最活跃的两个因素,因为涉及叙述者的物理时空与心理时空两个维度。阿氏在时空维度上,重在后者,从而使得文本保持了一种既持续又跳动的轨迹,在时空变换中充满了动感。譬如,作品有意识地出现叙述停顿、中断、延宕、缺省等,从侧面上反映出那些不幸的人们历经岁月洗礼而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我还是想你,妈妈》中写道:“我已经五十一岁了,有了自己的孩子,可我还是想妈妈”,[32]“在埋葬爷爷的地方,长起来一棵苹果树,代替十字架立在那里。现在它已经是一棵老大的苹果树了”。[33]叙述者恍若隔世又清晰如昨的慨叹,使得光阴暌隔的历史沧桑之感格外凝重。对于阿富汗战争的实质,士兵们意识到这是一场肮脏的战争,他们对人民代表大会颁发的“国际主义军人”纪念章感到羞愧;核反应堆爆炸后曾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的医护人员,若干年后明白了政府当年的欺骗;那些曾经血拼疆场的女兵们认为史上是否有斯大林存在都无所谓。她们经历的痛苦不能改写,历史真相就这样在时空跨越的陈述中渐渐浮出水面,它调节、提升、更新了读者的心理图式(sсhеmе),克服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霸权同化。显然,对于卫国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这样重大的军事事件和政治事件,此在的叙述自我与昔日的经验自我伴随时间的推移会产生新质,作者将叙说者劫后余生的心理时间予以压缩,不仅成为作品的有机构成,也成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理解方式,帮助读者探赜隐含的诗化寓意并引发共鸣。文中出现语言风格与意识判断两个层面明显的“二我差”①“二我差”指的是当一个叙述者“此我”,在讲述自己的往昔,既可以用“昔我”,也可以用此我的语言,既可以表现“昔我”也可以表现“此我”的意识、经验、判断。参见赵毅衡:《论“二我差”:“自我叙述”的共同特征》,《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14年第4期。现象,依据赵毅衡的观点,该种现象在所有的自我叙述(hоmоdiеgеsis)中普遍存在,但其反思意义更加凸显。显然,直觉与幻觉相结合,对现实加以形象化和神话式的改编,是永恒与其时空的结合,触及的则是人类生存的本质状态。
鉴于文化的本质是一种意义结构,因此,听觉互动对社会文化情感的构建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阿氏小说声音纪实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此种纪实性的倾听文学给作家的才思驰骋似乎带来一定的桎梏,也给文体创新带来极大的困难,阿氏作品由于内容的政治倾向性与形式的陈旧性在俄罗斯屡遇诟病,处于二三线作家之列,但阿氏能够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对于声音纪实既顺从其制约又叛逆其羁束,其艺术匠心可以从反差叙事中捕捉到并得以确证。
三、审美张力的生成
从表现形式上来看,声音纪实类小说采取的是类似一种口头叙说的方式。不过,这“叙说”不同于“叙述”,前者是一种口头语言的表达方式,后者是一种书面语现象。阿氏的口述实录小说已经成功地从其发生学胎盘——口头文学中剥离出来并实现了二者的恰切相融,使得该类文本具有了独特的审美内质。譬如,《二手时间》中的某些标题体现出浓郁的唯美色彩:“专政之美和水泥中的蝴蝶之谜、残酷的火焰与高尚的救赎、苦难中的甜味和俄罗斯精神的焦点、难以污名的死者和寂静无声的尘土”等,就是很好的例证。还有小说的一些段落更如美文节选:“当我们火烧麦田时,我回忆起过去在农村的生活。我想起自己躺在风铃花和野菊花的花丛里,想起我们怎样在篝火边烤麦穗。天太热了,麦田一下子就燃了起来,火势熊熊,到处散发出粮食的味道。火苗把童年记忆中粮食的香气扬起来了……那边的夜不是慢慢降临,而是突然砸落到你身上,白天转眼成了黑夜,就像你原本是个娃娃,瞬时成了男子汉。”[34]如此绮旎的文字,甚至丝毫不逊于“顿河草原的写生画家”肖洛霍夫的手笔。尽管在阿氏作品中,自然风光的描绘没有取得独立地位,也不似《静静的顿河》那样浓墨重彩,而只是如同马赛克般的艺术镶嵌或零散点缀,但它始终与叙述者的战争记忆共同律动,别具一番审美韵味。
文学鉴赏作为高级的、能动的审美实践,在审美过程中,人以应然的存在方式出现,人的本质力量得到充分、自由地展开。阿氏口述小说中声音纪实与反差叙事的艺术技巧,令阅读者在与文本的精神交流中大大提高了“符号的可感性”,从而获取了增值的审美愉悦感,因为“凡是存在着对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力量,冲动或有意义的地方,都存在张力”。[35]若从审美经验构成的四要素,即审美感知、审美想象、审美情感、审美理解观之,阿氏口述小说文本内生的审美张力具体体现为:场景反差与审美感知、比拟反差与审美想象、人性反差与审美情感、时空反差与审美理解四重效果。第一,场景反差全方位调动起阅读者的各种感觉官能,不协调的情境氛围激发起读者的极大审美注意力。这一点对处于艺术感觉被磨钝或已自动化的读者而言,场景反差巨大的审美弹性带给读者特殊的审美反馈,它不是侧重告诉读者什么,而是设置审美悬念迫使读者继续赏读什么。这种迥异于日常体验的审美惊异驱策审美主体去进一步感受审美客体的兴致,从而引发审美主体动力机制的积极参与,并使审美经验的动态过程得以完成。第二,比拟反差中本体与喻体之间颇大的异质性,一方面高度契合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同角度叙述者的生理特征与认知逻辑;另一方面,正如储泽祥指出的那样:“两个事物的相似程度越低,比喻就越典型”。[36]从接受美学理论来看,接受过程中读者一定时间单位的停留驻足与欣赏流连十分重要。比拟反差的表意策略旨在以复杂化的形式增加读者感知的难度,消耗心灵更多的能量,延长审美想象的时长。想象作为创造性思维的表象过程,经验想象力是“通过改造主体在审美经验的呈现阶段所获得的原初材料,形成关于审美对象的格式塔”。[37]从比拟反差作用于审美想象的关系来看,受众就是在比拟修辞这种陌生化、个性化、不相容、不匹配的语义错置中突破了思维定势,在审美位差带来的骇异状态中获得了意外的审美快感与审美想象。因此,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不仅不加强我们的既成认识,反而侵犯或僭越这些规范的认识方式,从而教给我们新的理解密码”。[38]第三,审美情感与日常情感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绝非由于本能需要的满足而引发,而是包含更多的理性因素和社会色彩。人性反差叙事使原有的审美效果正向延伸,赋予有限的能指以无限的所指,潜在的人伦召唤深化了审美深度,增强了审美意蕴,指向了审美哲思,升华了故事的语义学内涵。第四,审美经验从感觉始,以感悟终。时空反差叙事既把过去与当下自然链接,又将显性的此在视角与隐性的彼在视角叠合运用,“两个世界”①“两个世界”原指端木蕻良《初吻》这类回忆小说的叙事视角,即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对立。作品主人公回忆时,在过去的童年世界与现在的成年世界之间出入。阿列克西耶维奇的《我还是想你,妈妈》等作品也具有这样的叙述特点。参见钱理群:《文体与风格的多种实验》,载《文学评论》1997年第3期。补充互生,作品辐射给读者的审美共振进一步增强。质言之,所谓美就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在审美相互作用中所生成的一种特殊价值。阿氏作品中审美客体各种对立关系相互抗衡、相互映衬、相互诠释,接受主体在多重声音、观念、画面的刺激下产生了复杂、立体的审美感受,进而形成了作品的审美张力。诚如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Mаriо Vаrgаs Llоsа)对阿氏的评价:“阿列克西耶维奇在反抗三伪文学的过程中把每一行文字安排得如此透明,不知不觉就深入到人内心最深最柔软的地方去了。”[39]
综上,“奖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40]是诺贝尔文学奖一贯秉持的评奖原则。诺贝尔文学奖全部作品无不在关注作家所处社会制度下人的生存困境并力图寻找一条出路。“为了占有文化的世界我们必须不断地靠历史的回忆来夺回它,但是回忆并不意味单纯的复制活动,而是一种新的理智的综合——一种构造活动。”[41]正是因为听觉作家(Писатель-ухо)阿氏作品里所有的故事既是声音纪实的艺术化展示,也是“多声部的”创作。阿氏作品的纪实语言,在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以及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之间摇摆、移动、杂糅,其幅度之大,形成了该口述小说的美学风貌,这也正是阿氏作品文献价值之外蕴涵的文学品格。作为女性作家,阿氏没有像英国女作家莱辛(Dоris Lеssing)那样通过社会环境和社会问题分析和探讨造成女性当前处境的关键,也没有像法国女作家波波娃(Simоnе dе Bеаuvоir)那样,从人的本体存在和意识存在来剖析父权制文化而成功地将女性囿于他者处境的根本,[42]而是从文艺美学的角度出发,在新的历史时期文学创作中完成了对历史题材的宏大构想,表现出这位女性作家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
[1]田洪敏:《倾听心灵的声音——斯·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非虚构文学》,《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5年第6期。
[2]常江、杨奇光:《在新闻与文学之间:聚焦白俄罗斯女记者获诺贝尔文学奖》,《新闻界》2015年第22期。
[3][7]S·阿列克谢耶维奇:《我是女兵,也是女人》, 吕宁思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年,第413、410页。
[4]龙锋、方建移:《口述实录: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新闻学启示》,《传媒评论》2015年第11期。
[5][20]曾斌、易丽君:《重返“听觉”:听觉研究中的众声协奏——“听觉与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6][8][39]新华社:《白俄女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新浪新闻网:httр://nеws.sinа.соm.сn/о/2015-10-08/dосifхirmqz9564439。
[9]张寅德:《叙述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65页。
[10]李勇忠:《叙事视角与性别意识建构》,《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11]高莽:《阿列克西耶维奇和她的纪实文学》,《俄语学习》2000年第1期。
[12]黑格尔:《美学》第2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71页。
[13][22][28][29][30] S· 阿列克谢耶维奇:《二手时间》,吕宁思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前言、85、512、556、512页。
[14][17][34] S· 阿列克谢耶维奇:《锌皮娃娃兵》,高莽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年,前言、200、114-115页。
[15][16][23][24][25][26][27][31][32][33] S· 阿列克谢耶维奇:《我还是想你,妈妈》,晴朗李寒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年,前言、252、257、92、59、15、252、108、258、162页。
[18]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蓝英年等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629页。
[19]汪介之:《20世纪俄罗斯文学经典的重新认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21]张荣翼:《媒体传播与文学史书写》,《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35]陈大柔:《美的张力》,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页。
[36]储泽祥:《相似性的“N1似的N2”格式》,《语言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4期。
[37]朱立元:《美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70页。
[38]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伍晓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99页。
[40]阿尔弗雷德·伯哈德·诺贝尔:《诺贝尔遗嘱》,贾文丰:《诺贝尔文学奖百年百影》,珠海:珠海出版社,2002年,第354页。
[41]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235页。
[42]王丽丽、林凌:《女权战士与推石者——从〈第二性〉和〈金色笔记〉看波波娃和莱辛的女权主义思想》,《华侨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责任编辑:陶原珂
I106.5
А
1000-7326(2016)11-0163-07
*本文系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资助项目“美国文学研究”(СSС97822032)、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十八大”重点项目“文学的文化软实力研究”(2013А04)、吉林省高教学会2016年重点课题“诺贝尔文学视域下的高校文学教学发展研究”(JGJX2016B30)的阶段性成果。
侯海荣,文学博士,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科研处处长(吉林 四平,136000);胡铁生,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教授,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吉林 长春,13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