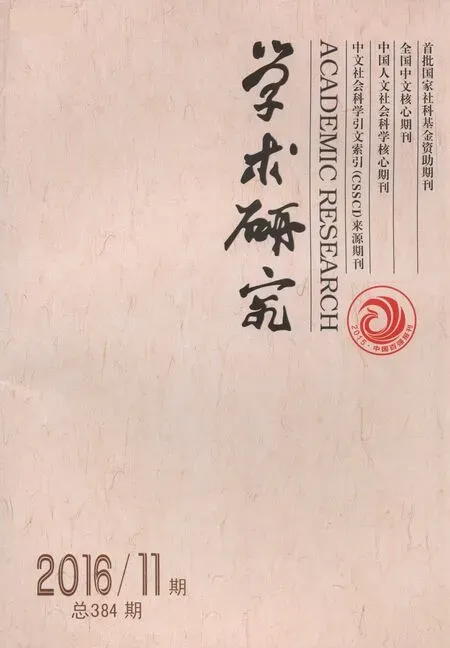商人雇主制:方显廷论乡村工业的一体化模式*
傅春晖
商人雇主制:方显廷论乡村工业的一体化模式*
傅春晖
本文围绕方显廷在南开经济研究所所做的对华北地区乡村工业——特别是对高阳织布业的调查,分析了商人雇主制作为一种乡村工业的一体化模式在生产、销售和资金流通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商人雇主依靠中间人和散处工人组织生产,依靠布线庄销售其产品,并依靠钱庄进行资金融通。在地方金融体系中,他们创造性地运用了“拨条”制度,并利用“跑街”减少因“贴水”而造成的资金损失。但是,商人雇主制也有其固有的缺陷,需要用合作制度加以解决。对商人雇主制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商人雇主制 乡村工业 商业资本 乡村金融
一、导言
乡村工业的发展是经济史和社会科学经久不衰的话题,这不仅因为它是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重要经济现象,也因为由它而引申出了乡土伦理[1]、社会保护[2]等经济现象背后的重要的学术和现实问题。随着各学科研究的深入,乡村工业这个组织学意义上的“黑箱”也已经逐渐明晰起来。当然,与之伴随的,也浮现出各种各样困扰其发展的问题。例如,资金短缺就是素来困扰乡村工业发展的一大难题,针对这个问题,今天,中国各地的乡村企业家们仍然在想尽一切办法予以解决。组建“合会”[3]、逐级“欠账”[4]等方法都是企业家们重要的金融制度发明。而类似的情况其实早在中国工业化之初就已经出现过,并且,当时的社会科学家们对此也做出过出色的研究,方显廷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方显廷被称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四大经济学家之一。①其他三位是刘大钧、马寅初和何廉,其中何廉不仅是方显廷在耶鲁大学求学时的学长,也是他在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合作者。就这个时期的成就来说,他为人所知的主要贡献,是和何廉一起编辑出版了著名的南开物价和生活指数系列研究。②为提高当时统计资料的质量,何廉和方显廷等学者开始着手于通过调查而搜集数据资料,这是经济学“中国化”最早的努力之一。“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愿望是:通过统计数字的收集、编纂和分析,以数量来表示国内的经济情况。”另外,在南开经济研究所工作的这个期间,他还进行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研究,特别是运用实地调查的方法对华北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乡村工业做出了重要的分析。[5]
但是,学界目前对于方显廷本身的研究仍然非常局限,要不就是仅限于一般性的论述,例如概括其学术生涯和主要贡献,[6]要不就是仅仅把他看做经济学“中国化”的先驱,[7]而以现在经济学的量化研究标准来衡量,这些先驱的研究早已被超越而不用再受到重视,或者就只在经济史的范围内对他的研究进行讨论,而缺乏交叉学科的广阔视野。相反,对于他的一些重要的分析性概念——例如本文提到的“商人雇主制”(mеrсhаnt еmрlоуеr sуstеm)等,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围绕着商人雇主制而建立的生产、销售和资金流通的一体化模式,极大地缓解了乡村工业对于资金的需求,这种独特的制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今天仍然能给予我们极大的启示。
“商人雇主制”这个概念是方显廷在耶鲁大学写作的博士论文《英格兰工厂制度的胜利》中的独创。方显廷批评性地结合了当时的经济史学界对于工业组织的诸种分类方法,①在这之前,被学界广为接受的是Büсhеr关于工业组织的分类,他将十九世纪中后期的英国工厂组织区分为家庭生产(hоusеwоrk)、有偿工作(wаgе wоrk)、手工艺人(hаndiсrаft)、授权经营(соmmissiоn)和工厂制度(fасtоrу)。方显廷认为,这种分类方法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例如,在Büсhеr的定义当中,手工艺人是一种局限于提供其产品给当地消费者的生产形态,但事实并非如此,诸多经济史资料给我们描绘的图景当中,手工艺人实际上更为广泛地和“市场”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再比如,在Büсhеr关于授权经营的分析当中,忽略了中间人(middlеmаn)在商人雇主(mеrсhаnt еmрlоуеr)和散处工人(оutwоrkеrs)之间起到的周旋和协调的必要作用。Büсhеr显然是从一种历史演化(еvоlutiоn)的角度看待这几种不同生产形态的产生和发展。同时期的其他学者们,也有从其他不同的角度对工业组织做出过分类学意义上的研究。例如德国著名学者桑巴特,他把工业组织区分为个体的(或者小的)、过渡的(或者中等的)和社会的(或者大的),这是从劳动合作(lаbоr со-ореrаtiоn)的角度做出的区分。另外,生产规模、技术种类、报酬性质等也都在诸多研究当中被看做是进行工业组织类型区分的不同角度。建立了自己的工业组织分类体系。他将其区分为:工匠制度(сrаftsmаn sуstеm),商人雇主制和工厂制度。虽然方显廷并没有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明确提出他做出这种分类所依据的角度,但我们可以体会到,这种区分并不仅仅是出于对Büсhеr的工业史理论的简化,以及对其他学者论述的简单综合。在这种区分中,方显廷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区分工业组织类型的视角,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注重商品“流通性”的视角,以区别于那些更强调“生产性”的视角。或者可以这样说,方显廷显然更倾向于把现代工业体系看做是商品流通的体系而不单纯是商品生产的体系。由此,我们才能理解商人雇主制这种独特的制度在方显廷工业组织理论中的重要性。
方显廷是这样对商人雇主制进行定义的:
“在商人雇主制之下,商人雇主自己购买原料,在自己办事所内,发给散处工人;或由自己及其所雇之散活员(sаlаriеd аgеnt),将原料送至散处工人之家中。散处工人,将此项原料,造成制成品或半制成品后,或径自送至商人雇主之办事所,或由商人雇主及其散活员亲往收集。收集之后,于是售之于消费者或其他商人。然商人雇主依契约法,可以任用中间人,收其原料交与之,而约定交货日期。届时商人雇主,即向中间人取货。中间人自商人雇主处取得原料后,再分付之于散处工人,约期交货。届期由中间人收集散处工人所造之制成品或半制成品,交之商人雇主。依商人雇主与中间人之工作契约论,中间人事实上为商人雇主之官员;但有再与其他代理中间人(sub-middlеmаn)或散处工人订立工作契约之自由。有时亦可招集散处工人于其所设之作坊,从事制造。”
如图1所示:

图1 商人雇主制
对这样一种生产组织形态,学者们曾进行过各种各样的描述和概念分析,诸如“家内生产”(dоmеstiс)、授权经营、“血汗制度”(swеаting)、“外包制度”(рutting оut)等概念都被尝试用来概括和解释这种生产现象,但它们都只强调了其中的某一方面而有失偏颇。商人雇主制却是一个综合的概念,扎根型生产、委托—代理关系、雇佣劳动和任务分配等生产特点都被包含在其中。[8]在方显廷后来的研究当中,对于工业组织的分类虽然有过一些小的调整,②在对中国乡村工业的研究当中,方显廷把工业组织区分为家庭制、匠人制、商人雇主制和工厂制四种类型。在方显廷看来,“家庭制为工业组织进化之最初制度,无交易之必需”。所以,家庭制是一种不具有“流通性”的生产组织形态,其产品甚至不能被称之为是商品。传统中国小农经济中的男耕女织,应该可以被看做为家庭制生产的典型形式。但商人雇主制一直是其理论的核心,并且,他也将这个经济史的一般概念应用在对中国乡村工业的讨论当中。
二、工业化与乡村工业
不同于当时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应该“以农立国”,①钱穆先生曾写作《农业国防刍议》一文,方显廷的学生滕维藻随即撰写《工业化与农业——与钱穆先生论“农业国防”》予以反驳。方显廷倡导工业化的主张可见一斑。方显廷及其南开同仁坚持认为,工业化才是近代中国的大势所趋,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经济指数研究即由此而来。[9]这种研究方法的意义主要在于强调各行各业经济变化指数之间的相互联系,并且认为工业化的程度与其他产业的经济蜕变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南开经济研究所从事的华北地区经济发展研究当中,这种方法首先被用来研究天津的各种工业组织。②研究成果包括《天津地毯工业》、《天津织布工业》、《天津针织工业》和《天津之粮食业及磨房业》等一系列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著作。但是,这种运用“典型提问”和“普遍调查”的手段、依靠“未严格训练的助手”的研究方法,从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因为不论调查者或者调查对象,都“一样缺乏统计数字的概念”。并且他们也逐渐认识到,从当时来看,“工厂工业在整个中国经济的画面上是无足轻重的”。因此,他们就把实际考察的重点转移到了“乡村经济情况”上面。并且,他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进了研究方法,例如采用“广泛研究与典型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建立“实地工作站”并配备训练有素的研究助手以进行文献查阅和“会晤个别典型人物”,有时候“甚至与农民一起干活”以进行参与观察,等等。运用改进后的方法,他们做出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华北地区的农业经济、乡村工业以及地方行政与财政。[10]方显廷在其中参与最多的就是对于乡村工业的调查研究。
方显廷认为乡村工业是中国乡村建设最重要的内容,这是出于两方面的思考。其一,参照英德法美等先进国家的工业发展史来看,工业革命固然使制造业逐渐从乡村移到了城市,但是,“大工业中心附近所兴起各种小工业为数众多”,且已经随着电气事业的发展而推及至乡村,也是不争的事实。一些过分工业化的国家——如英国——甚至已经开始重新认识乡村工业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其他各国——如瑞士、瑞典、挪威、丹麦、芬兰等国——也开始对乡村工业加以特别的注意。[11]可以说,在当时的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有一种“乡村化”的趋势。而中国工业的特点是,其“根本就是乡村化的”。其二,从乡村工业本身的特点来看,它不但具有小规模工业的诸多优势,例如:需要的资本较少,无需固定成本的支出,不要求太高的技术,工作比较有弹性,等等。而且,就它与城市工业相比较而言,优势也是明显的。首先是劳动力价格低廉,其次是因为交通闭塞而形成的地方市场优势。[12]所以,利用、发展乡村工业在乡村建设的意义上就显得尤为重要。
乡村工业的重要作用,从经济功能上来看,首先是对农民闲暇时间的利用,③时任金陵大学教授的卜凯(J.L. Buсk)在其著作《中国农家经济》中指出,华北及华东地区农民全年的实际工作量,只需要全年时长的四分之一,而剩余的时间,如果完全闲暇,就是一种严重的劳动力浪费。从而避免了大量人口的隐性失业。其次,乡村工业往往依托于当地原料进行生产,所以能使本地的土产和副产得到更好地利用。最后,乡村工业最终能够有效地增加农民收入。从社会功能上来看,乡村工业的作用也是不容小觑的,首先可以使农民增加对机器的认识,其次,乡村工业还具有启发民智的教育作用,④方显廷认为,这种教育的价值,尤其体现在合作组织当中,因为合作运动可以启发个人的责任心和合作的美德。最后,乡村工业较之大工业来说,对乡村社会的破坏较少。乡土社会的传统观念,如果能够再加上工业上的“新组合”,就“更能促进大规模之社会合作”。[13]同时期的其他学者也纷纷在强调乡村工业的重要性,比如写作了《江村经济》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14]因此可以说,对乡村工业的重视几乎成为了当时社会科学界学者们的共识。而从时间上来看,方显廷显然走在了更前面。
按照方显廷的分类方法,可把乡村工业分为纺织、食品、化学及杂项四种类型。其中,纺织业包括棉、丝、苎麻的织造,扩展来说,还包括花边、发网、草帽辫、芦席等物品的生产;食品业则包括舂米、磨面、酿酒、榨油、制茶以及制造出售粉丝、通心粉、罐头等;化学工业包括造纸、陶器、玻璃、爆竹等;最后,制胶、毛笔、艺术品等产品的生产销售则都归属于杂项工业。可以说,乡村工业的种类是包罗万象的。总体上来说,它们都具有“就地制造”的特点,有非常浓厚的地方性色彩,如江苏吴江县盛泽镇的丝绸、山东龙口的粉丝、浙江的绍兴酒、江苏宜兴的陶器、天津杨柳青的彩画等,都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产业聚集。促成这种地方性生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乡民之企业性”(现在通常称之为“企业家精神”),西洋教士的传导,资本家的商业动机,以及当地农民对农副产品和闲暇的利用。[15]
就方显廷及其同仁们集中调查的华北地区特别是河北一省来说,棉布及人造丝布的制造,是乡村工业中最为重要的。1928年其产出为7000多万元,占当年河北省44种家庭工业总产值的73.9%。所以,南开经济研究所特别选定了可以看做河北省织布业代表的高阳县,作为他们调查研究的对象。[16]
三、高阳织布业的发展
精确地说,历史上的高阳织布区域,并不止于高阳一县,“其所包括的地带除高阳全境外,有蠡县、清苑、安新和任丘的一部分,最兴盛时会兼及河间、肃宁县的边境各村”。[17]就南开经济研究所对于这整个区域织布业的研究来说,吴知的《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固然是一个大的综合,但其中最精练的思想,则体现在方显廷的《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当中。高阳及其邻近乡村织布业的兴起和发展,受到地区经济、生产制度、国内外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在20世纪之前,高阳农民织造的布匹,大部分留作家用,只有剩余部分才在集市中出售。这个时候的生产组织,以家庭制和工匠制度为主导。
20世纪初,高阳农民用改良后的铁机替代了原来的木机,并且开始用洋纱进行织造,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布匹的产量。而产量的提高又反过来促使农民求购更多的棉纱,但以当地农户一家之积蓄,尚不能够负担因此而产生的资金问题。这时候,就出现了一种商人资本家,他们提供给农民洋纱和铁机,并且把以此而生产出的布匹向外埠进行销售。这样就建立了农民织户和商人之间一种类似于雇工和雇主的关系。农民不再需要在市场上自己出售布匹,而是从商人那里领取织布的工资。而商人则因此而具备了“商人”和“雇主”的“双重资格”,逐渐取代了集市中布商和布贩的地位。商人雇主由此而取得了对农户生产的控制,农户之所产,都出于商人雇主的“旨意”。
1914年以后,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造成洋布来源断绝,促使全国对于土布的需求,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高阳的织布业也因此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生产需求的扩大,使得商人雇主必须招揽更多的农户为之生产,因此就把触角从中心的市镇拓展到了更为边远的乡村。但因为距离太远而从业人数太多的缘故,生产监督便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从而激发了一种“中间人商号”的出现,作为商人雇主和农户之间联系的桥梁。中间人商号很多都是高阳布商的分店,其中也有完全独立的。但无论如何,中间过了一道手,留给农户的利益就更少了。因此,有点积蓄的农户,也常常自购棉纱,自产自销。其他还有向布商赊购棉纱进行生产销售的,以及由布匹和棉纱之间重量的差别而赚取差价的。以上种种,就是后来经济史家总结的高阳织布业在商人雇主制下发展出来的“撒机制”、“赊线制”和“换布制”等不同的生产方式。
1920年以后,高阳织布业经历了一个衰落期。首先是因为停战以后外商重新加入了竞争的行列,其次也因为国内各大纱厂增加了机械生产的规模,最后还由于潍县布业的异军突起造成的冲击。在这几重压力之下,高阳织布业的规模开始缩减,中间人商号也间有倒闭,以及由此而引起了“边际织户”(mаrginаl wеаvеrs)的大量流失。
1926年以后,高阳织布业来到了第二个繁荣时期。一方面是因为全国物价高涨,并伴随老百姓购买力的增强,布匹作为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也大大增加。另一方面是因为高阳率先从天津引入了人造丝的发明,农户相率购置机器进行人造丝布的生产。正因为技术改良的缘故,出于织造繁杂布匹的需要,于是就出现一种被称为“领机”的人,负责指导其他农户的生产,这是商人雇主制在这一阶段的新的发展。
但是好景不长,1930年以后,高阳织布业又产生了严重的危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内忧外患而引起的。首先是因为“九一八事变”以及淞沪会战等战事的影响所及,其次由于长江和西北地区相继产生了水旱灾害,再次则因为币制改革造成了人造丝成本的增加,最后潍县织布业仍然持续对高阳产区施加影响。多种因素叠加,到南开经济研究所展开调查的时候,高阳织布业已经又趋于衰落了。[18]
总之,从高阳织布业的发展历史来看,商人雇主制正是其生产组织的典型形态。
四、商业资本在其中的表现
关于商人雇主制下的生产体系、营销渠道等,以往学者根据方显廷等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们搜集的资料已经做出过很多的二手研究。但是从一手资料到二手资料的转换来看,在他们的研究当中付之阙如的是对商人雇主制下金融组织的介绍。[19]但实际上,从高阳织布业的具体运作来看,金融流通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方显廷在《中国工业资本问题》中指出,中国的工业投资,基本上被外资所把持,以1928年上海的工业投资为例,外资约占投资总额的65%。而国内的金融界,当时分为新旧两大类:新者为银行,旧者为钱庄。银行和钱庄的投资取向有着显著的差别,银行倾向于投资通商大埠的工厂,而钱庄则更专注于内地工业。高阳的织布业,就十分倚赖于天津的钱庄(或称之为“银号”)。[20]但是,天津的钱庄想要发挥作用,也得倚靠高阳当地的商人雇主。商人雇主所聚集的商业资本,因此也成为了织布业中金融流通的一个重要部分。
高阳与全国其他各县的金融周转,大部分借重天津及内地各县的钱庄,兹以天津为例说明。高阳商人为运销高阳布匹,曾于68个县市设置分庄。天津分庄从钱庄借得款项购入棉纱,棉纱从天津运往高阳,在高阳当地织成棉布。然后棉布从高阳运往各县市分庄进行销售,以换取现金。而在各县市出售布匹所得的现金,则又通过各县市钱庄运送到天津钱庄以归还之前所借之款项。汇兑在各县市和天津钱庄之间进行,在整个过程中,并不需要有大量现金的流通,从而对所涉及过程中的资本需求是一种缓解,并且也可以免除运载现金的费用与危险。①民国以前,商户也有雇用镖局汇解现银的情况。“镖汇清算,每年分为4期,称为镖期。”一届镖期,舟车并至,输抵现银“可达五六十万两”。这种现金运送方式不但费钱费力,而且有较大的风险。自从各商户在各地开设分庄之后,该种办法即弃之不用。各县市分庄并且可以将归还款项之后剩余的现金通过各地钱庄存入天津钱庄,以备将来购置棉纱的需要。由此,棉纱、棉布和现金之间就形成了一个三角运行的关系。
以上是高阳织布业所涉及的县际金融制度。高阳的本地金融,则向来盛行所谓的“拨条”制度。高阳本地大宗的布线交易,都使用拨条作为支付工具,例如:
“甲商向乙商购入棉纱10包,价250元,共值2500元,如甲商信用素著,乙商即将款暂存甲商处,双方各落账记数,备他日用款时,乙商可向甲商开拨条支款。倘乙商须付款与丙商,即对甲商开一拨条与丙商,丙商如持拨条向甲商取款,甲商收妥乙商开出之拨条,并不支付现金,亦开一拨条交丙商向甲商有存款之丁商处支取,丁商收妥甲商开来之拨条后,亦开一拨条交丙商向丁商有存款之戊商取款。倘丙商认戊商为可靠,拨条即交戊商,款存戊商处,以为他日付款时向其开拨条之用。”
所以高阳本地的交易,全都使用拨条支付,市面上只能见到拨条,现金极为少见甚至于无。因为这种债务缠绕的关系,各商户间的账目常常拖延不结。如果要用拨条兑换现金,必须付出若干贴水,称之为“贴现”。贴现每天都有行市,其涨落和天津汇市相似,“每千元自数元至数十元不等”。于是,那些存有大量拨条的商户,为了减少这种损失,就有了所谓的“跑街”。
跑街是一种特定情况下的结算方式。即某一商户向有其存款的其他商户,猝不及防地开出拨条,派若干人等到各个商户请求兑换,各商户也当即开出拨条用以支付,于是该商户派出人等又持有各商户当即开出的拨条,向下家请求兑换,直到用这种方法把拨条全部结除之后,就可以找到最后那个欠款的商户,并向其请求兑换,如果这个最后的商户没有现金,则只能用天津钱庄中的存款抵作现款进行汇兑,但是贴水也因此而免除。于是,但凡每次跑街,市面上所有的拨条就可以清除一次。一年之中发生跑街的次数并不多,“多不过五六次,少则一二次,亦有全年无‘跑街’者”。[21]
总之,相比于城市大工业所可能获得的金融支持,乡村工业获得资本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银行等现代金融机构没有动力涉入其中,即便是钱庄和银号,其流通也只限于县际之间的结算,真正流入到乡村的工业资本是很少的。这就逼迫乡村工业必须发展出一套自己的金融体系,在现金缺乏的状态下,处理好资金流通、使用的问题。在高阳织布业中我们可以看到,商人雇主已经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制度创造,围绕“拨条”、“贴水”和“跑街”而构成的地方金融流通,给当地织布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五、弊端与改革
如前所述,商人雇主制的兴起和演变,反映了商业资本逐渐从生产、销售和金融流通上控制乡村工业的过程。商人雇主制固然给华北地区乡村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制度动力,但是其弊端也是不容忽视的。最主要的是,农户的利益在其中无法给予有效的保障,商人雇主因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而压低农户的工资,无端刁难、吹毛求疵以克扣农户应得款项,以及雇佣周期不定等等,都对农户收入的增加造成了影响。而这种农户和商人雇主之间的不平等状况,主要是由农户之间缺乏组织造成的。农户因为过于分散,无从得知同行所得工资的多少,商人雇主便借以压低不知情的农户的工资。所以,往往同一项工作,不同农户的工资相差甚巨。当然,从客观上来说,低工资也是乡村工业相对于城市工业的比较优势。而农户之所以欣然接受这种“榨取”,也是因为除此之外,很难有其他可以利用农闲而从事副业的机会。由于这种相对的弱势,商人雇主就更能够在质量控制等方面对农户提出更苛刻的要求,甚至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随时可以结束这种“不规则”的雇佣关系。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正因为生产过于分散,质量监督几乎是不可能的。劳动情况随农户而异,织成的布匹在规格和品质上都没有统一的标准。农户、商人雇主和顾客之间形成了环环相扣的欺骗,织布业几乎成为了一个劣等布匹取代上等布匹的“柠檬市场”。更有甚者,农户盗用棉纱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粗制滥造更是不可避免。
另外,乡村金融组织付之阙如,仅仅依靠民间信用作为担保,也潜藏着巨大的风险。就以“跑街”为例,跑街时全城各商号开出的拨条,总计往往能够达到百万元以上。携带大量拨条进行来往抵换,都是跑街人的责任,跑街人如果疏忽而失落拨条,商号概不负责,跑街人如果取款潜逃,商号既已开条,也不用负责。所以跑街商号对于跑街人的选择是非常谨慎的。跑街自然是那些实力雄厚的商号的行为,而底子空虚的小商号因为害怕被一时挤倒,“竟有不顾信用居心作弊的”,这种作弊的行为被叫做“推磨”。所谓推磨,指的是小商号因现款不足,所以“集合相约,各开假码,轮流交兑”,使得跑街人无处寻觅最终能够兑换现款的商号,只得“出人说项,定期缓交”,从而造成跑街的失败。如此等等问题,都亟需加以解决。
方显廷认为,中国乡村工业的诸多问题,非以“合作”不能解决。[22]从当时来看,工业组织中合作制度代替资本制度之崛起方兴未艾。环顾世界,德国、苏联、印度等国已经纷纷创立合作事业。对于消除商人雇主制的弊端来说,合作制度具有保障非正规就业、庇护乡村工业的作用,对于克服商人雇主制“无组织、不合作”的问题,有极大的裨益。①虽然商人雇主制中也有所谓的“合作经营”,有生产合作、销售合作、“机房”合伙和劳资合伙等形式,但是“数目极少,寥若晨星”。
方显廷对于高阳织布业合作社的设计,共分为三层组织。首先是村织户合作社,其针对社员的活动,包括棉纱的分配、布匹的收集以及工艺标准的维持等等。其次由村合作社可以进而组成区合作社,主要负责织布的预备工作,例如摇纱、上经、穿经、浆经、上纬等手续,如果能设立一个“中心工厂”进行生产就更好。区合作社的存在,可以有效调节生产“过分集中化”和“过分分散化”的两个极端。最上面一级则是县合作社,主要负责原料的购买和布匹的销售,以及天津、高阳等地之间款项的汇兑,并且也承担一部分织布的预备工作。
方显廷等认为,由此而建立的合作组织可以有效地解决乡村工业的组织、机器及科学的利用、资金的筹措等诸多问题,在生产和分配两端都对农户起到积极的保护作用。但因为后来持续的战乱和政治形势的剧烈变革,这种合作制度并没有得到应当的推行,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六、总结和讨论
首先,围绕商人雇主制的产生和发展,我们得以窥见乡村工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本文主要分析了商业资本在其生产、销售和资金流通当中所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它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资金短缺的问题。可以说,商人雇主制正是维持这个乡村工业一体化模式顺利运转的关键。诚然,乡村工业是商人雇主制发生的最典型的场所,但在城市手工业中,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其实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方显廷对于当时天津工业的调查中可见一斑。甚至可以说,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历程,每一种工业的发展,都与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从工业发展史的角度来讲,对于商人雇主制的研究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总而言之,“商人雇主制”既是经济史中的重要经济形态,也可以被看做社会学研究意义上的“理想类型”,因而是一个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分析性概念,也正是方显廷乡村工业研究的核心概念。
其次,就研究的现实意义来讲,目前中国乡村工业的发展,仍然带有商人雇主制的痕迹,沿海地区来料加工产业的发展,就是这种扎根型生产组织方式的现实证明。来料加工当中的经纪人就相当于是商人雇主,其组织生产的方式同样是发散性的。总体上,我们可以把这两者都归入到“包买制”的普遍范畴当中。[23]当然,在特定的经济、社会和制度环境下,这种生产形态也遇到了新的问题和挑战,但它至今仍然是工厂制度的重要补充,在全球化订单工业的生产体系中,尤其显得重要。[24]
再次,从商人雇主制出发,我们也可以扩展开很多理论上的思考。例如本文提到的乡村工业中的合作问题,其重要性已经超出了商人雇主制的范围,进而成为一个理论和现实的普遍问题。对比当时的其他学者来看,例如,费孝通也关注过农民合作的问题,被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是《江村经济》中最成功的一章的“蚕丝业”,描写的就是“家庭企业如何有计划地变革成为合作工厂”。[25]费孝通认为,以合作的方式来组织乡村工业,是对抗“作坊工业”①费孝通认为,乡村工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农闲的基础上用来解决生计困难的家庭手工业,另一种是作坊工业。作坊工业是一个累积资金的机构,并且这些资金最终还是用来购买土地,更加造成了乡村中的土地集中和贫富对立。这里的作坊工业可以看做是商人雇主制的一种变型。并阻止土地进一步集中的有效手段。②费孝通在这里所说的“合作”是家庭手工业和作坊工业的合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技术上的合作,例如可以把制造过程“拆断”,分配到用电力推动的小型工厂或用体力的家庭工场中去(他甚至还注意到日本的自行车制造,就是“把各部分零件分散到乡村家庭中,用简单的电力机器制造,然后到总厂去装配”,实际上这也是包买制的一种形式);另一个方面是组织上的合作,即生产工具的所有权要分散到所有参加生产的农民手上,而不是集中在少数有资本的人手里。机械化对于乡村工业的影响,在费孝通看来是一种外生变量,新式乡村工业能否健康发展,关键在于家庭手工业能否以合作的方式组织起来。并且,对合作问题的讨论,甚至于被上升到了国民性的高度。费孝通很不留情面地总结道:“中国乡下最大的毛病是‘私’。”差序格局中自我主义式的一己之私,和团体格局中作为“实在”的“公”,两者之间有着难以跨越的障碍。[26]而梁漱溟则认为,中国人与西洋人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即没有范围超越于家族的组织,其后果便是组织能力的缺乏。[27]这些判断,和方显廷批评商人雇主制的剥削性和“个人主义”是一脉相承的。[28]这些思考,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当下的农民合作问题,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最后,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方显廷的研究也构成了我们反思目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一种“史前史”。其研究虽然也属于当时盛行的“统计型调查”,[29]但是从理论背景和前提假设来看,既不同于更早期的一些经济调查研究成果,例如托尼立足于基督教社会主义而写作的《中国的土地和劳动》和卜凯对照美国大农场传统而写作的《中国农家经济》,也不同于当时社会学研究中流行的Bооth式调查[30]和吴文藻的社会研究法,[31]而不如说他受到了在耶鲁大学求学期间主导美国经济学研究的历史学派的影响。[32]当然,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论述的范围,不过,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也将会有非常重要的学术史价值和指导当前学术研究的意义。
[1]周飞舟:《回归乡土与现实:乡镇企业研究路径的反思》,《社会》2013年第3期。
[2]闻翔:《劳工问题与社会治理:民国社会学的视角》,《学术研究》2015年第4期。
[3]张翔:《合会的信息汇聚机制——来自温州和台州等地区的初步证据》,《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4]李英飞:《资金短缺下市场如何运作——浦镇轻纺产业资金链中的社会时间机制》,《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2期。
[5]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经济学(季刊)》2001年第1期。
[6]孙智君:《民国经济学家方显廷的农业经济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7]易仲芳:《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研究(1927-1949年)》,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8] H. D. Fоng,Triumph of Factory System in England,Nаnkаi:thе Сhinli Prеss,1930,рр.6-16.
[9]滕维藻:《工业化与农业——与钱穆先生论“农业国防”》,《贵州企业季刊》1944年第1期。
[10]何廉:《何廉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第68-74页。
[11][13][15][16]方显廷、吴知:《中国之乡村工业》,《方显廷文集》第4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93-358页。
[12]方显廷:《中国之工业化与乡村工业》,《方显廷文集》第4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71-393页。
[14][25]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4-166、11页。
[17]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经济卷(中)》,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25-328页。
[18][21][28]方显廷:《华北乡村织布工业与商人雇主制度》,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经济卷(中)》,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93-497、511-513、515页。
[19]史建云:《手工业与乡村经济》,从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35-434页。
[20]方显廷:《中国工业资本问题》,《方显廷文集》第4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33-292页。
[22]方显廷:《乡村工业与中国经济建设》,《方显廷文集》第4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59-370页。
[23]傅春晖:《包买制:历史沿革及其理论意义》,《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2期。
[24]田志鹏:《社会关系与订单获得——以浙江省丽水市来料加工业为例》,《社会发展研究》2014年第2期。
[26]费孝通:《费孝通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8-19页。
[27]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4-75页。
[29]黄兴涛、李章鹏:《现代统计学的传入与清末民国社会调查的兴起》,黄兴涛、夏明方主编:《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5页。
[30][31]李章鹏:《社会调查与社会学中国化——以1922-1937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例的研究》,黄兴涛、夏明方主编:《清末民国社会调查与现代社会科学兴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7-91页。
[32]熊性美、关永强:《本卷序言——方显廷中国工业化思想研究述略》,《方显廷文集》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хiii-хiv页。
责任编辑:王雨磊
С91-09
А
1000-7326(2016)11-0067-08
*本文系北京市教委“科研水平提升项目经费”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5年提高定额——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的阶段性成果。
傅春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社会工作系讲师(北京,100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