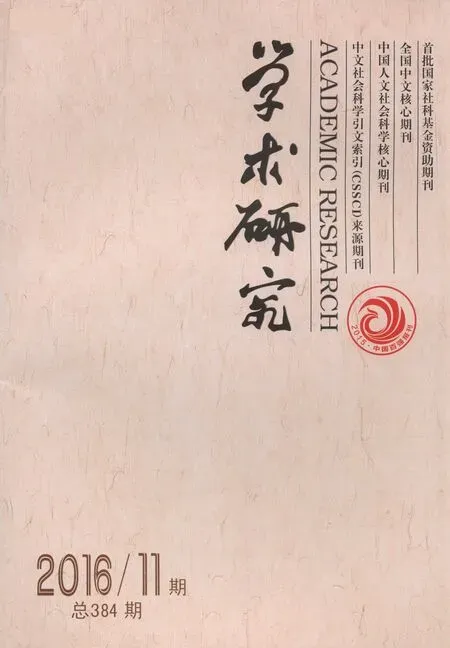以职业团体为基础的劳动力组织化动员
——以抗战时期民生公司的成功动员为例
杨 可
以职业团体为基础的劳动力组织化动员
——以抗战时期民生公司的成功动员为例
杨 可
抗战时期劳动力的组织化动员需要一个国家与社会“合意”、“合力”的过程,作为“社会”领域中劳动力组织化动员的成功案例,民生公司利用自己高效的公司行政结构优势,灵活地采用法令为经、福利为纬的动员策略,辅之以职业团体的情感动员,协调了劳工、企业和国家利益,在完成政府下达的劳动力动员任务的同时,兼顾了劳工和企业的需求。这条以职业团体为基础进行劳动力组织化动员的路径,对动员力不足的政府形成了有效补充。
组织化动员 劳动力动员 职业团体群
一、问题的提出
抗战爆发之后,蒋介石多次强调,“现代战争是三分军事七分经济”。[1]为了在比拼经济实力的现代战争中确保后方物资生产,尤其是军需品的生产,参战各国的劳工①按学界共识,本文所言“劳工”包括工人、雇员和职工,即除农民之外,所有以劳动换取工钱者。都走上了历史的前台。同样,中国也需充分调动和合理配置劳动力,最大限度地发挥劳动力的效率,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对劳动力的动员提出了要求。劳动力动员的对象既包括一般人力,也包括后方各工矿企业技术员工。有学者指出,国民政府的劳工政策因此也从战前的劳资协调逐渐走向了劳工统制。[2]按已有研究的总结,国民政府的劳工措施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设立劳动力管制的行政机构,即社会部劳动局以专门负责此项工作;二是对劳动力情况,尤其是技术员工的情况进行大规模摸底调查;三是出台一系列法规来为劳动力动员提供政策基础和法律依据,如1938年4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日建国纲领》提出“一切建设以军事为中心”,“使第一国民之劳力,以最经济之运用,尽瘁于军事建设之完成,而不致虚耗”,为劳动力的动员提供了政策依据。[3]此后1943年行政院、国民政府分别推出了《非常时期厂矿工人受雇解雇限制办法》与《战时全国技术员工管制条例》,直接对特殊劳工群体的动员和管理提出明确规定。根据学者的评估,这些针对劳工的管制性法规的效果应该是很显著的,可称维护了大后方的生产秩序、保障了军需生产、推动了后方工业发展,“具有不可否定之价值”,[4]尤其是在1943年控制劳工转移率的过程中可谓功不可没。
不过,正如学者们已经指出的,学界对整个国民政府抗战动员体制的研究有重决策中枢而忽视基层实践的倾向。[5]同样,纵观有关抗战时期劳动力动员的既有研究,研究的重点大多在国民政府身上,无论是全国性政策法规的出台,还是针对具体人群的劳动力动员统制措施,突出的都是国家这个宏观的层面,强调官方政策对劳动力动员的作用,而劳资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方——组织劳动力进行生产的企业在这一时期劳动力动员中的角色却被忽略了。本来,任何国家层面法令政策的有效推行都离不开实践层面负责机构的认同与执行,这两者缺一不可,也无法互相替代。尤其对于1928年才统一全国、中日战火初起便被迫几次迁都的国民政府而言,[6]其行政系统的结构设置尚不完善(前述社会部劳动局直到抗战中后期1942年9月才得以设立),如何保证完成战时高效劳力动员的目标?既有研究并没有回答。本文尝试以民生公司①民生公司全名为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25年由卢作孚等创办于合川,以经营长江中上游航运为主,后来逐渐发展成为民国时期最大的民族资本航运企业。至1949年,其投资兼涉冶炼、机器、造船、煤炭、纺织、食品、建筑、保险等行业,跻身民国时期最大的资本集团的行列。抗战期间,因民生公司在承担军用物资和人员抢运中的突出贡献和巨大牺牲,曾受到国民政府多次嘉奖。在战时对其员工群体的动员为例,提出一条以职业团体为基础进行劳动力组织化动员的路径。民国时期,以民生公司为代表的一些模范企业不单纯是在经济领域追求资本收益的企业,还主动承担了经济事务之外的社会功能。民生公司本已在战前的管理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建设职业团体、打造群体团结的经验,在战时的劳动力组织化动员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二、以企业为基础的组织化动员
众所周知,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战爆发,战争态势急剧发展。被迫迎战的国民政府直到1937年底才开始在全国各省设置“动员委员会”,办理战时人力、物力、财力征调及指导生产统制,[7]但未有专门针对劳工,尤其是特殊技术员工动员的机构。此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国民政府经济行政部门发动和组织的沿海工矿企业内迁运动,国民政府此时之重点是工业动员、统制资源,随着600余家国营、民营企业的内迁,数万名依附于企业的熟练技工也跟随企业进入大后方。尽管这个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后方诸多企业对熟练技术工人的需求,[8]在整个后方的劳动力中所占比例也很小,但我们可以从厂矿内迁动员的过程中看到一种以企业为单位各个击破、进而统制员工的动员思路。
根据1942年大后方的工业统计,大后方所有3758家工业企业中民营企业占到了3102家,工人数量为164445人,占68.05%。[9]本文要重点讨论的民生公司也是一个重庆本地发展起来的民营航运企业,但由于抗战初期整个航业损失惨重,运力大大受损,[10]随着战事发展和战线的西移,军事运输、物资抢运和人口疏散对交通运输提出了巨大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川江特殊的航行条件和下游航运公司的损失,这些任务只可能靠民生公司来完成。危机时刻,尽管并非国营企业,素有公共责任担当的民生公司呼应国民政府的要求,进行了航运力量的动员。40年代的劳工研究者曾提出,“人力动员以法令为经,以劳工福利为纬,则相辅相形,使其安定生活,乐于从业”,[11]下面即从法令和福利两方面来考察民生公司对劳工的动员是如何开展的。
(一)以法令为经
1937年8月31日,为掌握残存的航运力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1515号公函,对所有船员实行统制管理。
凡在轮船服务之船员,如非重病大故,一律不得请假离船。其未在船之船员,一奉征调命令,应即赴指定轮船服务。如有擅自离船或故意违抗规避者,均按军法治罪。至在非常时期各级船员因公致死伤者,得依照海军抚恤例办理。
这一份公函直指所有船员,形成了国家对劳动力个体实施统制的制度压力;同时,尽管并未言明,它也对各级船员所在的航运企业提出了执行人员统制的要求。民生公司也立即制定了《非常时期船员离船办法》,于9月通函全公司,具体办法如下:
1.船泊码头,不得自由上岸,应随时留船待命。
2.除父母妻子子女死亡,本人婚配,家庭直接受水火灾害及本人重大疾病经医生证明不能执行职务得请假外,其他事故,一律停止给假。
3.因公上岸,必须填具公出单。如私人临时有重大事件,或疾病治疗,得请临时假。
4.高级船员离船,必须有代理人,并须说明所到之地点及回船之时间。
5.如离船不返,耽误航行及公务,无故漏船,不假离船及逾假不归者,严重处分或停职。这份《非常时期离船办法》是对前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管制船员公函的一个细化,前述公函里的非“重病大故”不得离船,在实际操作中如何明确?从这份《离船办法》中可以看到,其实民生公司基本认定即使在非常时期,离船也是可以允许的,但是需要细化可接受的离船理由,因此需要具体的“离船办法”:船员因家庭重大事件和个人身体原因是可被接受的离船理由;离船需履行一定的组织手续;高级船员因其可替代性小,必须在有代理人的情况尚可离船。仔细比较这份《离船办法》与前述的政府管制公函,可以看到《离船办法》中这些细节的安排既有行政强制性,也较具操作性与合理性,而且将政府公函的管制意味加以微妙反转,变成对准假条件的一个细化。这样一来,提出限制要求的是国家,而给予准假优待的是公司,这反映出实际面对职工群体的企业的管理经验,同时也使得这份本意仅在响应政府号召管制员工的文件带上了一些表达其态度和利益的色彩。
民生公司1936年职工人数已近4000人,[12]其中约七成以上是船上人员,对全公司船员进行统制管理难度非常之大。幸而民生公司素以科学管理闻名,30年代初已完成公司组织结构调整,废除买办制,各船人权、物权、财权全部上收到公司,实现了“从对人的依附到对公司的依附”的转变。作为一个大规模航运企业,它同时是一个部门高度分化、分工明确又高度协作的现代企业。[13]在赏罚分明的人事管理制度下,民生公司的行政系统表现出高效率、强约束的特征,这也是发动员工组织化动员的基础。
马明洁曾总结“组织化动员”的特征如下:“每一个被动员者都和动员者密切相关,更确切地说,动员者与被动员者之间存在一种隶属性的组织纽带。其基础是,动员者往往掌握了对被动员者而言至关重要的稀缺资源”。[14]在民生公司的案例中,职工可从企业获得的稀缺资源有二:一是相对的人身安全和经济安全,因民生公司负有“后方交通运输重责”,因此政府特许各轮现任职工可以缓服兵役,这甚至引发了地方壮丁涌入民生机器厂充当艺徒试图规避兵役的事件,同时,劳动力市场的管制使得他们选择其他就业机会的成本上升、难度加大,一旦落入“与抗战无关各业”,甚至有工作被取缔之虞;①这里涉及国民政府的一般人力管制政策。自1937年底开始,国民政府开始清查限制及取缔与抗战无关各业。国民政府社会部拟定的《重庆市人力车轿夫及与抗战业务无关各业及其从业员工清查限制及取缔办法》由行政院会议通过,该办法主要目的是清查限制及取缔重庆市内劳动力浪费,以充实兵源,并使转就生产各业,有利于抗战。参见周勇主编:《重庆通史第三卷近代史(下)》,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年,第1181页;秦孝仪等主编:《革命文献抗战建国史料——社会建设(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3年,第6页。二是在百物紧俏、物价腾贵的大后方,民生公司相对优厚的劳工福利极具吸引力,下文将详述。
(二)以福利为纬
民生公司主张以工作、学问、娱乐等各种集团生活将员工聚集成一个生活的共同体,“职工的问题由公司解决”,在战前即有较为完善的劳工福利,不仅膳宿免费,还有包括红酬(职工可持股)、双薪、医药津贴、文娱津贴、服装津贴、粮食补贴、死亡抚恤、退休和养老金、假期优待与乘船优待等一系列福利待遇。举例来说,早在1934年,民生公司就曾尝试从宜昌等地运廉价米、炭入川,不仅供应员工食堂,还发放给员工家庭,以期减少员工家庭的支出。这一供应员工生活日用品的传统抗战时期一直在持续,根据老民生职工的讲述,公司有时候发米,有时候发棉纱。公司附属的消费合作社对民生公司职员九折供应货物,偶尔还能供应乌花布等紧俏物资,一时名声在外,引得很多民生职工的亲朋也来找他们借职工消费合作社的手册去买东西。[15]1944年3月11日消费合作社发放家属食米时,甚至因为领米人数过多,“致将楼板压塌,受伤者共计三十三人”。[16]战时物资供应的局面之紧张,由此可见一斑。相比战前而言,由于战时各种资源供应日趋紧张,职工们在获取日用品时面临的是更少的市场选择,民生公司这顶大伞给予职工的不仅是作为工资收入补贴的福利待遇,更是雪中送炭式的日用必需品供给。对比战前和战时民生公司福利政策,战时员工福利甚至有增无减(参见下表)。

民生公司战前、战时福利制度比较表
劳工福利待遇不同于货币化工资,它建立在正式职工资格之上,使职工在经济上更紧地依附于公司,这是执行劳动力组织化动员的有利条件。事实上,仅仅是踏踏实实执行免费膳宿制度这一条,已经赢得了许多员工的认同。正如曾在民生公司机器厂和煤站工作过的罗英杰老人所言,“第一个给你安排住好,第二个安排你吃好……卢作孚就是这一点,他把职工的心买到了”(罗英杰访谈记录,2009110801)。
战争爆发后,由于民生公司不得不执行危险的军运任务,频繁往来于日机轰炸不断的川江前线,民生员工中也发生了不少脱离岗位的情况,出现了人心不稳的问题。在民生公司的人事档案中可以看到,请长假、不假离船和逾假不归的下级船员不在少数。[17]在公司1938年底发布的《简讯》里也承认,“有少数船员不明大义,借故请假者有之,不待准假擅自离船者有之”。也许正因为民生公司的员工身份来之不易,也很少有人直接辞职,而是采取请假的办法以期名义上不脱离公司,保留住公司成员的身份。面对安全难以保障、职工人心动摇的局面,公司采取了多种办法来对员工进行再次动员。首先是根据航段的风险程度大幅提高工资待遇。1940年6月宜昌沦陷后,民生公司紧接着开辟了重庆至三斗坪的航线,这段短短的航程被分作了三部分,从上游往下游依次是重庆至万县、万县至巴东、巴东至三斗坪,因为越往下游风险越大,员工的报酬也是递增的:“巴东以下,拿三级,万县以下,拿两级。就是万县到巴东,拿两块,巴东以下,拿三块。万县以上,拿原工资”。在船上员工看来,这种奖励办法“有鼓励性。有些人不怕,长期走下面都要得,我工资高”(邹鸿俊访谈记录,2010050601)。其次,在工资报酬之外,民生公司于1938年5月特别拟定了《为职工保障计特有新拟订战时兵险救济办法》,增设战时兵险救助,以为坚守岗位的职工安全增加保障:“在抗战期中,本公司直接任用之各部职工,已取得互助保险资格,完备投保手续,并未请假离开职务,而于实际工作时,遭受兵灾身故,因超出职工互助保险章程范围,未能领受该项保险金额者,即由本公司照其所保金额,分行拨款,如数发给其受益人承领,以资救济”。从实际发生的抚恤情况来看,1941年9月公司在第433次人事会议上议决通过《战时职工死亡救助金及遗族生活费标准案》,决定当日起“战时死亡职工救助金遗族生活费改照原条例第五章第十六条及第十七条规定金额之六倍核给(即照战前加五倍)”。[18]
可以看到,无论是公司行政管理还是劳工福利方面,民生公司在进行战时劳力动员时都表现出了高度的制度创新性,这种个体企业因应环境变化和自身特点进行变通的灵活性和适切度显然是宏观层面的动员机构无法比拟的。把具体组织生产劳动的企业所做的工作纳入到战时劳动力动员的考察视野中,我们进一步理解了抗战时期劳动力动员的效率从何而来。
三、以群的情感为基础的组织化动员
上文在行政制度管制、福利刺激和安全庇护的层面分析了民生公司开展战时劳工动员采取的办法,如果仅仅是这样,那充其量这只是一个以企业为基础的劳动力动员,而单纯依靠法令管制或物质刺激的动员手段不可靠,也不长久。史国衡先生在《昆厂劳工》中就曾指出,工人不能安定,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找不到他自己的适当地位”,而“在这个大混乱当中,物质的凭借既不雄厚,更不能单靠工资来吸引工人,也不必把工人当作唯利是图的小人看待。应该从各方面来激发工人的热情,安定他们的生活”。[19]民生公司一直不止把自己视为“纯为赚钱”的企业,它努力的方向是“造成现代的社会生活”,它还利用员工在多年集团生活中积累起来的群的情感和群的道德,以积极的职业认同推动集体行动热情,用“以身许友”的情感动员来代替硬性制度规定。
如前所述,随着1938年战火逐渐波及到长江中游,员工请假多有发生。1938年2月,公司发布了一份题为《临难勿苟免》的通函,言辞恳切、慷慨激昂,一方面以报效国家之崇高精神激励人,一方面诉诸职工多年的组织生活休戚与共积累起来的同伴情感,希望能唤起大家“以身许友”、“甘苦共尝”:“吾辈多系壮年,正是献身国家之日,应凭群策群力,共御外侮,使敌寇不能深入,则根据不失,复兴可期。若人人俱畏缩畏惧,敌一乘我,则灭亡立至,彼时吾辈宁有生理?加之近代战争,无分前方后方,皆有危险。我公司职工素尚组织,与其单独逃避,安危难卜,何若团体行动,尚易共筹良策,免除危险……我全体职工,共事公司,多者十余年,少者亦一二年,平昔甘苦共尝,休戚与共,古人以身许友临难不图苟免之精神,此时正宜表现”。[20]
民生公司内部刊物《新世界》上同期还刊发了另一文章《非常时期的修养》,文字更浅显,说理更直接,对前述通函精神再加以直白的阐释和更为人格化的理解,文章以“我们”来称呼职工,以一种“我群”的亲切口吻号召大家追随卢总经理,与国家、公司,更重要的是与同舟的兄弟共患难。不难发现,这里谈的修养很多来自于传统的道德资源,各种道德话语只要能唤起共同的情感,统统都被调动起来:
责任既如此之重大,我们平时都是患难与共的朋友,难道国家至于今日,我们能不相共患难么?我们的卢总经理,从战事发生后,随时都是置身前线,我们怎好意思退后?古语说,“同舟共济”。公司事业大半在水上,此时正好适用这句话,大家勉力来共济时艰,借这非常时期来磨练自己……
非常时期是磨练人的。受此磨练者,至少要有下列几组修养,才能处之裕如。不然,一定会感觉苦闷,意冷心灰,终成为一个准亡国奴,或间接的汉奸。一、不思家庭。我国人素重家庭观念,尤其在乱离时候,慈母娇妻,巴不得儿子或丈夫,成天在一块儿。这虽是人情之常,但我们这群既已献身国家的朋友,不应该受家庭的拖累或束缚。昔人说:“匈奴未灭,男儿何以家为!”我们个个应当有此气概……强寇当前,应该同仇敌忾,共御外侮;不应该英雄气短,儿女情长,随时那样的思家………四、要能合群。常人之情,一遇困难或危险,便不能抑制感情,或发烦恼,或现忿怒,或示消极,对于周围的人,往往不能合作,这不但危害团体,而且危害自己。俗语说:“三个臭皮匠,当得诸葛亮。”假若处非常时期,人们合拢来各显其能,各竭其智,无形有形两方面,要销[消]除许多困难合[和]危险。若在抵挡强暴时,要需要群策群力,不能单独行动,所谓“分则易折,合则难摧”,再进一层讲,处非常时期,正是人类发挥群性的最好机会。有些人平时对人非常亲切,一到有危险时,便立刻拆伙,足以证明平时之亲切皆是假的。而且有些见义勇为,临难不苟免之人,又非在处变时不易表现其特色。西谚有云:“需要中之朋友,乃为真友。”我们这群朋友中,谁是真友,谁非真友现刻正是在试验中啊![21]
仔细分析上面两份文献所使用的话语,我们发现它将国家政治的高度诉诸于日常生活中“群”的生活所建立起来的感情,这是与共同生活的集团中其他个体相互间的横向联系,对于底层员工来说,更有实感,因而更有凝聚力,更能发挥团结的作用。这时候所谓的“发挥群性”,不再以抽象的公司为边界,而是落实为日常的集团生活共同体中建立的、一趟趟同舟共济的走水生活中稳固下来的兄弟之情,抽象的爱社会爱国家被还原为切身的情感体验。在一个紧密团结的群体里,“怯者不得独退”,“苟活”是不为群体接受的苟且行为。1941年8月民俗轮被炸,全船船员不负众望,表现出了高度的同生共死的群的意识。虽然机舱机器已被炸停,全体机舱值班人员均不离去;当船即将倾覆沉没时,船长催水手长龙海云逃生,龙慨然回答:“船长不走,我怎能离开!”最后腹部中弹牺牲。[22]这种生死与共的情感只存在于高度整合的群体之中。涂尔干曾在《自杀论》中论及高度整合的团体——军队中士兵的利他型自杀,[23]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同生共死的群的情感也正来自于军事环境中的船队。高风险的环境激发了高度的整合,“在一个船嘛,同生死共患难!”(邹鸿俊访谈记录,2010050601)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民生公司16艘轮船被炸,其中9艘被炸沉,牺牲船员117人,76人伤残。[24]民生公司的职工们以血的代价证明了他们没有愧对兄弟,见证了职业团结的力量。正是通过对职业团体“群”的情感的挖掘,民生公司赋予了劳工职业的自豪感和归属感,完成了职业团体的建设。在一个以情感和认同紧密维系的职业团体中,组织化的动员有了最根本的基础。
四、小结与讨论
本文关注抗战时期的劳动力动员在实践层面是如何实现的。如前所述,此前有关抗战动员体制的相关研究重视国民政府行政中枢的政策法令而忽视基层具体实践,事实上,即使是国家设于各省的基层动员机构也被视为“层级繁叠,纵横扦格,权责不清,效率低下”,并未很好地发挥动员作用。[25]而劳动力动员不可能只是由国家发文、颁布政策就自行完成,而是需要一个国家与社会“合意”、“合力”的过程。吊诡的是,现有研究对社会力量如何参与劳动力动员着墨甚少,因此,本文把关注重点放在了一直未得到足够关注的“社会领域”,也即劳动力组织的具体企业之中,尝试以民生公司在战时对其员工群体的动员为例,在中观层面提出一条以职业团体为基础进行劳动力组织化动员的路径。
从与国家的关系来看,民生公司并非国营企业,更不是国家行政体系内的基层机构,作为民营企业,它更好地代表了抗战时期后方的大多数企业。选择民生公司这样的民营企业作为案例也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劳动力的组织化动员与其说是国家经济行政部门对下属企业的强制要求,不如说是动员力不足的国家借重了公司高效率的行政结构和凝聚于行业之中的职业情感。而且从逻辑上而言,民生公司能实现成功的组织化动员,更多一层行政强制力的公有企业和政府机构的组织化动员亦能成功。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民生公司不是一个被动执行政府劳动力动员政策的机构,相反,它利用自己的高效的行政结构优势,灵活地采用法令为经、福利为纬的动员策略,辅之以职业团体的情感动员,协调了劳工、企业和国家利益,在完成政府下达的劳动力动员任务的同时,兼顾了劳工和企业的需求。就战时劳工动员而言,若无视作为动员对象的企业劳工的实际需求,没有民生公司这样的企业居中推动,劳动力动员不可能只靠来自政府的顶层制度设计取得成功。
在有关“组织化动员”的社会条件的讨论中,马明洁曾指出,“组织化动员是以再分配制度和单位制为基础的”,[26]但通过本文对抗战时期民生公司劳力动员的案例分析,我们看到,即便在并不存在典型意义的“单位”、并非单位社会的抗战时期,只要存在相对的资源紧张,只要人们通过对职业团体的组织化依赖能获得稀缺资源,组织化动员就可能借由职业团体来展开。本研究努力还原抗战时期职业团体在劳动力动员中的历史角色,也希望有助于我们思考后单位制社会中发挥动员作用的组织路径。
[1][11]潘洵主编:《抗战时期西南后方社会变迁研究》,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1年,第103、117页。
[2]衡芳珍:《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劳工统制”与劳工立法》,《中州学刊》2014年第5期。
[3]江红英:《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劳动力管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824-848页。
[4]秦孝仪等主编:《革命文献第一〇一辑 抗战建国史料——社会建设(六)》,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
[5][7][25]吕晓勇:《国民政府抗战动员体制若干问题辨析》,《军事历史研究》2013年第4期。
[6]唐润明:《衣冠西渡:抗战时期政府机构大迁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8]张守广:《筚路蓝缕:抗战时期厂矿企业大迁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9]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合编:《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工业》,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年,第129-130页。
[10][12][22][24]凌耀伦:《民生公司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第172-173,121,184,184、187页。
[13]杨可:《民生公司的现代集团生活建设——一个社会学的视角》,《开放时代》2013年第4期。
[14][26]马明洁:《权力经营与经营式动员——一个“逼民致富”的案例分析》,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厦门:鹭江出版社,2000年。
[15]冉云飞:《民生公司职员六十年前的日记(三)》,《书屋》2007年第3期。
[16]重庆市警察局:《关于报送民生公司消费合作社发售职员家属食米跌伤人数经过情形上重庆市政府的呈》,1944年3月11日,重庆市档案馆,档案号:1002187847-8。
[17][18]赵晓铃:《炮火下的人事管理》,《卢作孚研究》2012年第2期。
[19]史国衡:《昆厂劳工》,重庆: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136页。
[20]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通函临难勿苟免》,《新世界》1938年第12卷第2期。
[21]刘子周:《非常时期的修养》,《新世界》1938年第12卷第2期。
[23]埃米尔·迪尔凯姆:《自杀论》,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39-252页。
责任编辑:王雨磊
С912.2
А
1000-7326(2016)11-0075-07
杨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