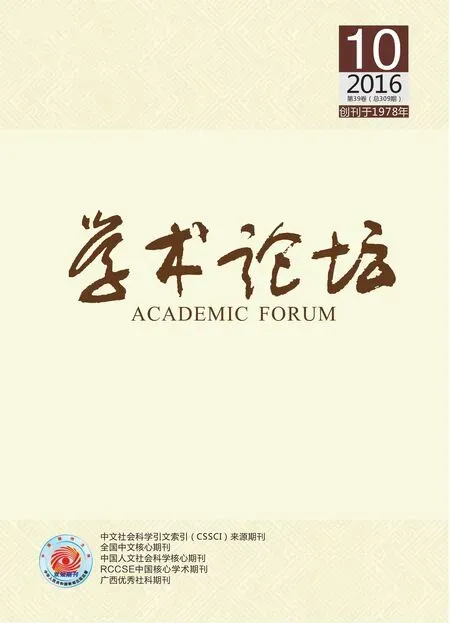德国一般人格权中的隐私保护
杨芳
德国一般人格权中的隐私保护
杨芳
由于个人隐私不具有典型的社会公开性,在德国一般人格权案件中,法官往往通过在个案中具体化其保护领域以及进行利益衡量,来判断是否存在隐私权侵权行为:并不是所有的个人信息都受到保护,是否受到保护取决于当事人的保密意志是否可为外界识别,且为法律秩序所认可;违反当事人外界可识别的保密意志获取或者传播个人信息的行为,并不当然具有违法性,对于违法性判断而言,对立利益和隐私利益之间的衡量必不可少。
一般人格权;隐私权;领域理论;利益衡量
一、一般人格权判决中的隐私保护
一般人格权从诞生到发展,在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和联邦宪法法院的表述中,它的宪法基础总是被表述为德国《基本法》第1条规定的“人格尊严必须受到尊重”以及第2条第1款规定的“每个人有权自由发展人格”。这种回溯《基本法》之规定的“法官造法”,正是具体部门法缺乏贯彻基本法确立的基本价值的相应规定,从而存在法律漏洞时,创造性地填补法律漏洞和发展法律的一种方式。
如下的判决可称为一般人格权确立之路上最富意义的里程碑,这些案件中的法官在谈到这种“新的法律诉求”时,都不约而同地将这一诉求的正当性建立在“自决”的基础上。
(一)读者来信案(BGHZ 13,334)
被告在其周刊上刊登了一篇关于前帝国银行行长沙赫特(Schacht)的文章。文章的部分内容分析了沙赫特在第三帝国时代所发挥的政治作用。沙赫特的律师为此给被告写了一封信,要求报纸对这篇文章予以更正。被告将这封律师函删改后,发表在报纸的“读者来信”一栏。这种发表形式有可能使读者产生误解,认为这并不是基于律师职务的信函,而是该作者本人对沙赫特事件的个人意见。因此,该律师起诉该周刊,要求撤回这一不符合实际的言论。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原告胜诉。该案的判决主旨可归纳为如下两点:第一,原则上,未经当事人同意,不得擅自公开其私人的信件或者其他手稿,不仅如此,原则上,以何种方式公开该信件或者手稿也必须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第二,当事人的上述权利源自于德国《基本法》第1条和第2条,因此,即使系争的信件或者手稿并没有达到著作权保护的要求,结果亦然。
(二)骑士案(BGHZ 26 349.)
在本案中,被告是一家制造壮阳药的企业。它在为其名为“Okasa”的壮阳药做广告时,擅自使用了原告着骑士装束的照片。原告请求停止损害,并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原告胜诉。判决要旨可总结为:既然自由决定人格发展的权利已经被《基本法》第1条与第2条所承认为法秩序中的基本价值,那么,如下的推理就是正当的:在本案中,即便原告并没有因自己的肖像被非法公开而遭受财产上的损失,法院也能类推适用民法典第847条的规定判予精神抚慰金。本案中的关于自决权的表述是,“基本法直接保护每个人的内在的个人领域,在这个个人领域中原则上仅由个人自我负责地自我决定”[1](P349)。
(三)录音案(BGHZ 27,284.)
本案双方当事人因税捐、房屋经营发生纠纷,在谈判的时候一方当事人私下录音作为证据。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主旨表现为如下三点:第一,原则上,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录音其谈话内容,侵害了该当事人的一般人格权;第二,在例外情形下,比如,正当防卫或者存在其他更加重要的利益,上面所称的侵害一般人格权的行为则不具有违法性;第三,本案中被告仅仅为了保存证据而对私人谈话内容做了录音,这种私人利益并不能正当化对一般人格权的侵犯。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本案中,将一般人格权表述为:“个人自主决定其话语是否仅为其对谈话对象,或特定圈子的人,或为公众所知悉的权利;个人更有权自主决定是否允许他人用录音机录下自己的声音。 ”[2](P284)
(四)索拉雅案(BGH NJW 1965,685)
原告索拉雅是波斯国王的前妻,被告为出版社及其编辑。被告在其刊物上刊载了一篇有关她的访问稿,但事后却发现该访问稿纯属捏造。该出版社发现后立即以一篇新报道及索拉雅的更正启事并列刊登的方式作了更正。索拉雅认为此举侵犯了其人格权。
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同意了原告的诉求,认为将一个杜撰的、内容涉及他人私事的访问稿公之于众,侵犯了他人的一般人格权,并且加害人须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和上述案件一样,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再次将本案意义上的一般人格权定义为“自己决定是否向公众发表有关其私人领域的言论,以及如果她有此愿望,以何种形式发表”[3]。
二、寻找隐私的客体表现形式
隐私诉求实际上是一种保持隐秘,免受打扰的意志,这种意志并没有建立在外在可识别的有形的客体上,而且,哪些意志应该得到尊重也并不总是能获得广泛的共识,亦即,隐私权诉求缺少客体上的表现形式(gegenständliche Verköperung)以及“社会典型公示性”,人们无法藉以判断出哪些行为可能侵害他人的隐私诉求。所以,如何判断当事人已经将自己的隐私诉求以一种外界可识别的方式公之于众,如何判断特定隐私诉求受到了法秩序的肯认,是问题的核心。当然,并不是只有明确表示出来的保持隐秘的意愿才能获得法律的保护。毋宁,道德、习俗、日常生活中的习惯以及法律本身对于判断是否存在保持隐秘的意愿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该个人信息处于个人生活的私密领域(Intimsphäre),那么根据事物之性质,即可推知出当事人不愿他人刺探和传播的意愿,例如,健康信息、性生活等则属于这样的信息。如果该个人信息的公开或者传播将对个人的声望造成重大影响,我们也能从中推知出当事人的保密意志,例如犯罪前科。如果那些旨在保护隐私的法律规则规定了某些明显具有私密性质的生活事实或情形,那么,从中也能推知出当事人对于这些领域的保密意志,例如,德国《基本法》第4条关于信仰秘密、第6条关于婚姻家庭秘密、第10条关于通讯秘密以及第13条关于住宅领域不受侵害的保护规定。如果个人的保持私密的意愿并不能从上述情形中推知,为了获得法律上的隐私保护,个人就必须就要让其保密意愿具有外在的可识别性,因为,相对人有义务尊重那些外在清晰可见的保密意愿[4](P406)。
(一)个人信息获取与收集领域中隐私的客体表现形式
判断获取信息的行为是否侵害了隐私权时,首先必须考察仍然是该隐私利益是否具有外界可识别的具体表现形式。亦即,那些想要远离好奇的眼光的人是否已经以恰当的方式向公众宣称:这是我的私密空间,请勿打扰;是否已经为自己的秘密构筑了一道“保护墙”[5](P25)。不仅如此,阻止他人获取信息的意志还必须得到法秩序的认可,其要么被明确规定于法律中,要么被约定于契约中,要么被社会一般观念所接受。
1.私人领域的判断。私人领域可以分为空间意义上的私人领域和非空间意义上的私人领域。
(1)空间上的私人领域。典型的空间意义上的私人领域系存在于个人家居的范围内。在“自家的四壁之内”,每个人都有权自由决定自己的行为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他人知晓[6]。所以,对于家居内的一切活动,当事人原则上得要求免于刺探。无论是在他人的家居中安装秘密摄像头,或者仅仅是隔墙偷听,都侵犯了他人的隐私。
个人的私人空间不仅限于个人家居范围,一定情形下的具有私人特点的领域,即使处于家居之外,也可视作私人空间,人们在此领域中的活动也应免于外界好奇眼光的干扰。问题是,在特定案件中如何判断是否存在此种类型的私人空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仍然是当事人是否将“免遭打扰”的意志以一种恰当的方式公之于众,亦即,当事人是否营造出了一种气氛,这种气氛使得当事人能够合理地认为自己已经避开了他人的眼光——通常是
将行动的范围和公共领域隔离开来——而且,他人能够识别出这种气氛。
(2)非空间意义上的私人领域。受到法律承认的私人领域不仅限于空间意义的私人场所,某些个人信息,即使并非来自于私人场所,他人也不得任意获取或者收集。至于哪些个人信息属于此列,则是价值判断的问题[7](P40)。在价值判断中,社会一般观念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而且,当事人是否为该信息建立了外界可识别的保护墙,将该信息的秘密性公之于众,以致于他人能够知晓自己行为的禁区,也是该信息是否受法律保护的重要因素。此类信息中,较为常见的是,密封的信件、被锁起来或者藏起来的日记、不欲为他人所知晓的秘密谈话、私人性质的电话谈话。如果当事人并没有将自己免遭干扰、免遭窥探、免遭倾听的意愿明确地表示出来,而根据周遭的情势,也无法推知当事人是否有此意愿,则当事人的隐私利益不受保护。
2.对客观的“保护墙”的逾越。只有以不正当的方式,违背了他人客观的、同时也为特定法秩序承认的“保持信息隐秘”“排除干扰”的意志,获取他人的秘密,亦即逾越了客观上的“保护墙”才构成违法行为。不当的方式包括,欺骗、暴力以及胁迫等等[8](P504-507)。只要在一般的道德观念中,逾越保护墙的行为是不地道的、令人反感的或者令人感到恐惧的,都可能构成对他人一般人格权的侵犯。例如,未经同意开启信封、未经同意开启他人加锁的日记、使用电子设备窃听他人房间中的谈话等。
(二)个人信息传播领域中隐私的客体表现形式
在该领域的隐私保护上,德国法奉行的仍然是“真相是自由的”这样的原则[9](Rn.200)。原则上,传播他人的个人信息并不当然属于侵权法意义上的违法行为。当事人要么应该和特定的人约定不得传播自己的个人信息,要么应该谨慎地选取谈话伙伴,在一般情形下,保护个人免于上当并不是一般人格权以及德国民法典第826条所提及的善良风俗的任务[10]。和前述获取个人信息行为的违法性取决于“打破保护墙”类似,传播个人信息的行为的违法性的前提也在于开启了“保持缄默的印章”,亦即,阻止他人传播自己的个人信息的意志必须以一种外界可识别的方式体现出来,这些方式较为常见的是,通过契约约定他人保守秘密的义务,但不限于此,略述如下:
1.契约中的保密义务。在违反保密义务的案件中,明确约定保密义务,以及如何惩罚违反保密义务的合同是比较少见的,较为常见的保密义务来自合同双方默示的附随义务。例如,医生对于患者病情负有保密义务;律师对于客户负有保密义务等等。违反这些保密义务自然构成违约,同时也可能构成一般人格权侵权行为。
2.契约之外的保密义务。如果不存在契约中的保密义务,那么如何判断特定情形下是否存在上文所说的“保持缄默的印章”则成为此类隐私权案件中的关键点。如果涉及的是当事人的私密领域,倾听者明确地意识到对话伙伴所透露的个人信息具有私密性,则可认为存在保持缄默的印章。例如,如果起诉书的内容包含了他人的生活细节,则接收者不得向第三人公开该起诉书;未经同意,报道他人家庭生活的细节,则构成违法。如果信息的传播可能给当事人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则可以推定当事人已经为这些信息加上了保持缄默的印章,传播行为具有违法性[11]。
三、隐私保护中的利益衡量
如果系争的隐私利益具有客体式的外在表现形式,亦即,在个人信息收集领域,当事人已经为自己的信息筑起了可为外界可识别的“保护墙”,在个人信息传播领域,该个人信息是如此的隐秘或者关系重大,以至于可推知出当事人已经为其加上了“保持缄默的印章”,那么,突破保护墙的行为以及打破缄默的印章的行为也就被推定为具有违法性。但是,系争的侵害行为是否最终被确定为违法行为,仍须取决于该行为本身具有的利益与当事人的隐私诉求之间利益衡量的结果。
(一)确定行为违法性的“领域理论”及其相对化
德国司法实践将受保护的人格领域分为个人领域(Individualsphäre)、隐私领域(Privatsphäre)和私密领域(Intimsphäre),这三个领域的受保护强度不同,依次增强。个人领域保护的是个人能够在社会生活和工作中展现自我,这个领域的隐私保护被最大程度地限制,有时候并不受保护。私密领域涉及的是个人内在思想或者内在感受的外在表现以及根据事物本质应该处于保密状态的行为或者信息,例如,私人信件、日记、健康信息、性生活等受到法律的绝对保护,是“绝对不得触及的核心领域”,对之的任何侵犯行为都当然具有违法性,无需进行利益衡量[12](P87)。人格保护涉及的多数情形是处于个人领域和私密领域之间的隐私领域。这个领域涉及的是根据社会一般观念,只有得到当事人的同意,第三人或者公众才能进入的生活领域,
特别是个人在家居范围内、家庭生活中的行为。隐私领域的受保护强度居于上述两个领域之间,对其的侵害行为本身不能推导出违法性,因此利益衡量是确定违法性的必要途径。上述根据个人事务所处的不同领域来确定其保护程度的主张被称为领域理论(Sphärentheorie)。
领域理论正确地指出了并非所有的隐私诉求都能获得法律的支持,并非所有的侵害行为都应该受到同等程度的禁止,对他人私人领域的侵犯程度越深,需要的正当化理由在程度上也就更高,偷听“小酒馆内邻桌的谈话”和“在别人家中安装窃听设备”的侵害行为在违法性上不可能被同等对待。领域理论也有助于阻止隐私保护的范围无所不
包[13]。
但是,领域理论容易导向这样的主张:侵害行为的违法性仅仅或者首先取决于对人格领域的侵害程度。由此,判断系争的隐私诉求属于上述的哪一个领域就是必要的前提。只是,恰当地作出这样判断首先是困难和不无争议的,其次,是否存在受到绝对保护的私密领域,也是不无疑问的。德国法院对个人日记的不同保护态度即可说明,通常被归属于领域理论中的“私密领域”的个人信息,对其的侵害行为并非一定具有违法性,在某些情形下,利益衡量仍是不可避免的。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64年所做的判决中,否定私人日记可作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理由在于,调查和惩戒犯罪的利益没有高于日记本身蕴含的人格利益,即使在该案中,日记作者曾经让第三人阅读自己的日记,从而引发了日记内容被继续传播的危险[14]。与这个案件的处理结果完全相反的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1989年所做的判决。在该判决中,法院认为本案中的日记可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15]。理由是,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即使是人格的核心领域,也仍具有社会关联性。所以在判断哪些生活事件可被归入该核心领域,不能仅仅通过是否具有社会关联性而为判断,毋宁应该考虑该生活事件的性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和公共利益相关。这并不是可以抽象地给予回答的问题,而是需要结合个案考察。本案的日记在内容上和被指控的罪行之间具有密切关系,这就已经证明了该日记不应被归入核心领域,因此本案的日记并不具有绝对不可侵犯的性质。此案的重大意义在于将领域理论中绝对不可侵犯的核心领域相对化了,强调并没有绝对受保护的人格核心领域。
因此,对领域理论的理解和适用不能绝对化,而是应当结合个案的特殊情况。对领域理论的正确理解毋宁为,并不是对人格领域的所有侵害行为都具有违法性;并不存在绝对受到保护的、无需利益衡量即可推定出侵害行为违法性的核心领域,在隐私保护中进行利益衡量对于判断侵害行为的违法性是不可或缺的步骤。
(二)利益衡量
在利益衡量中,侵害行为的目的或动机及其与侵害行为本身是否具有恰当的关系具有决定性作用。至于侵害行为必须具有怎样的目的才足以正当化对隐私利益的侵犯,无法概而言之。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原则上,源自人格保护的隐私保护和宪法上的其他基本权之间并没有位阶上的高低之分,对隐私的侵害行为是否受到禁止,毋宁必须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形而为判断。如果侵害行为的目的是追求公共利益、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讨论公共事务等,那么可能因符合德国《基本法》第5条中所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艺术自由、科学自由、研究自由与教学自由而获得正当化。如果侵害行为仅仅为了追求经济上的利益,例如,传播一些能够吸引公众眼光的新闻噱头,则不能获得正当化;保全民事诉讼证据的目的并不能正当化秘密录制电话通话行为;在网络论坛上对老师进行客观评价的行为在价值上高于被评价人的隐私利益。即使系争侵害行为服务于合理的目的,侵害行为的性质和方式也必须和该目的之间具有恰当的关系才能获得正当化,亦即,侵害行为对于目的的达成是合适的及合理的[12](P1310)。例如,在新闻报道中提及罪犯的名字不具有违法性,只要对该名字作了处理,以致于被提及人的曝光程度只限制在那些无论如何都能识别出他的人们中间。
四、结 语
上述法律推理可归纳为如下五点:第一,并不是所有的个人信息都受到保护,是否受到保护取决于当事人的保密意志是否可为外界识别,且为法律秩序所认可。第二,并不是所有的个人信息都受到同等程度的保护,一些和人格利益关系较为疏远的个人信息受到的保护较弱,或者不受保护。第三,并不是所有的同类信息都能获得同等的保护,例如,名人的和非名人的家居生活在受保护程度上有所不同。第四,违反当事人外界可识别的保密意志获取或者传播个人信息的行为,并不当然具有违法性,对于违法性判断而言,对立利益和隐私利益之
间的衡量必不可少。第五,系争的个人信息是否受到保护,并不是一个能抽象地回答的问题,毋宁只能结合个案中的具体情形予以判断。
[1]BGH.Entscheidungen des Bundesgerichtshofes in Zivilsachen[M].Berlin,Carl Heymanns,1954.
[2]BGH.Entscheidungen des Bundesgerichtshofes in Zivilsachen[M].Berlin,Carl Heymanns,1958.
[3]BGH.Entscheidungen des Bundesgerichtshofes[J].NJW,1965(685).
[4]Baston-Vogt.Der sachliche Schutzbereich des zivilrechtlichen allgemeinen Persönlichkeitsrechts[M].Berlin, Mohr Siebeck,1997.
[5]Zöller.Informationsordnung und Recht[M].Berlin,De Gruyter,1990.
[6]BGH.Entscheidungen des Bundesgerichtshofes[J].NJW,1981(1366).
[7]Fuchs.Deliktsrecht[M].Berlin,Springer,2009.
[8]Larenz/Canaris.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Band II, Besonderer Teil,2.Halbband[M].München,C.H.Beck,1994.
[9]Erman-Ehmann.BGB[M].Berlin,Dr.O tto Schm idt,2009.
[10]BGH.Entscheidungen des Bundesgerichtshofes[J].NJW,1987(2668).
[11]BGH.Entscheidungen des Bundesgerichtshofes[J].NJW,1987(2667).
[12]Palandt/Sprau.BGB[M].München,C.H.Beck,2010.
[13]Hubmann.Persönlichkeitsschutz ohne Grenzen?[J].U fita, 1974(70).
[14]BGH.Entscheidungen des Bundesgerichtshofes[J].NJW,1964(1139).
[15]BVerfG.Entscheidungen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hofes[J].NJW,1990(563).
[责任编辑:刘烜显]
杨芳,海南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海南 海口 570228
D912.7
A
1004-4434(2016)10-016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