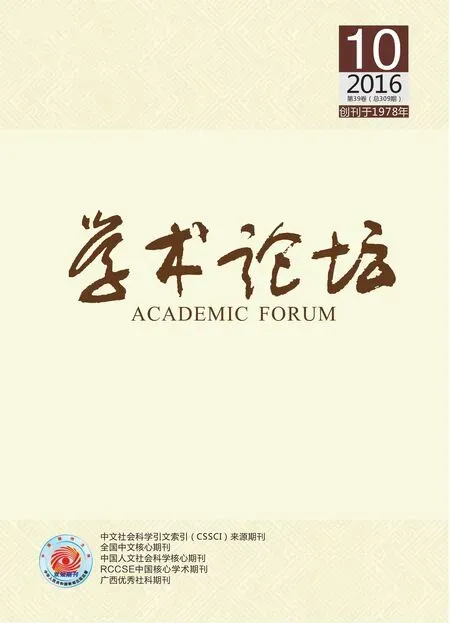历史嬗变中文学南京自我身份的认同与建构
——以民国时期文学书写的南京为中心
许永宁
历史嬗变中文学南京自我身份的认同与建构
——以民国时期文学书写的南京为中心
许永宁
文学南京在民国时期获得了空前的可阐释性。借助于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其延续着作为地域中心强有力的文化和精神的向心力,同时也突破了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城市形象。文学南京的文化意味与现实遭遇恰恰显现出:民国成立之后,在整个文化的框架内面对北京传统古都的教育文化和上海新型都市的经济,它所表现出来的独特魅力,因而展现出整个中国在世界之林中的国家民族形象。文学南京的丰富和建构,不仅仅来自于城市实体形态的物质建设,更重要的是文学赋予实体形态以更多的文化内涵,反映出民国时期文学南京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自我”身份的认同与建构兼具流动性与独特性。
民国;文学书写;文学南京;他者;自我
自古以来,文学对城市的书写从未缺席。有汉以来,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开始了对城市的极尽夸张和铺排的描述,西晋文学家左思的《三都赋》有过之而无不及。继之而起的唐传奇,宋元话本以及明清小说中对于城市的书写和记载不胜枚举。近代以来随着现代都市的崛起,文学对于城市的描写更加的繁复和喧哗,手法也更多变灵活。城市作为一个地域的核心,往往也是其地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代表了一个地域的整体风貌和文化特性,因此在对其不厌其烦的书写过程中,文学与城市的互动影响,共同丰富和发展了城市的形象和城市的文学。千百年来世人追求政治上的抱负屡见不鲜,尤其是作为政治中心的南京,在民国时期获得了很大程度上的政治地位的认可,“中国的城市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它首先是政治的中心,士人到都城来追寻自己的政治前途,即选择了或者说无奈地卷入了城市中的政治漩涡和斗争”[1]。文学也就或多或少地参与到政治意识形态等活动中,而基于如此认识之上的民国时期的南京则具有了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文学风貌,同时也在历史的流变中不断丰富和建构着自身的精神特质。
一、“他者”的存在与“自我”身份的认同
一个城市的独特存在是在与其他城市的比较中产生的,萨义德认为,“每一种文化的发展都需要有一个与其相异质或者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2](P426)。所以,在文学南京自我身份的建构过程中,时时处处需要有“他者”的存在以作为“自我”存在的价值判断。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中为我们提供了“观察者”这样一个“他者”视角,“他们居住于城,分享着甚至也陶醉于这城市文化的一份和谐,同时又保有知识者、作家的清明意识,把城以及其他人一并纳入视野。他们是定居者——观察者。后一种身份决定了他们有限的归宿。以城作为审美关照的对象,使他们在其中犹在其外”[3](P11)。这样一种说法,隐隐地有一个“他者”的存在,这个“他者”在赵园看来是一个“观察者”,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定居者在城市中显然有了作为城市主体的角色,影响和改造着城市的景观。正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对城市的定义而言,城市就是一个以人为主体的区域系统[4](P42),那么作为主体的人
构成了城市文学言说的主要对象,而中国现代城市的兴起与这种言说是密不可分的。
作为现代城市的个体,南京在整个民国城市文学版图中有怎样的地位或者特性,同样离不开这种“观察者”的角色,而从民国时期城市文学的本土特性来看,北京和上海无疑最具成为南京的“他者”代表。梁实秋在游历了南京之后写道:“(东南大学)这里的学生没有上海学生的浮华气,没有北京学生的官僚气,很似清华学生之活泼质朴。”[5](P39)叶文心以“中式长袍”“西装”“党的制服”分别象征北京大学的新文人、圣约翰大学的资产阶级子弟、中央大学的未来国民党干部[6](P152-155),这几所学校分别对应着北京、上海及南京的校园文化。中央大学未来国民党干部的“党的制服”很好地显示出政治在民国时期的南京的重要特点。在这里,校园中的学生成为大学文化特点的体现,而大学文化特点正是城市文学精神风貌的一种表露。与这种校园文化一致的是新闻出版、传播等新兴文化发展状况,正如荆有麟在《南京的颜面》中所言及的:“南京报纸也不少,新闻自然是千篇一律,连编辑的形式,好像都不敢有所独创,一味墨守旧法……闹得在南京长住的人,反都去订阅上海或天津北平的报纸。”“南京杂志本就少,然而,少之中,能维持到一年以上的,还没有几个,多半是‘昙花一现’,就夭折了的。闹得想看杂志的,还得搜寻上海北平一带的刊物。”“图书馆,这更可怜,夫子庙民教图书馆,已经就觉得笑话了,但公开的图书馆,据说这还是第一家呢?”“我不懂,南京有人花钱办电影院,开大饭店,却没人花钱愿意筑图书馆。”[7]在文化更新和诉求方面南京远远落后于作为“观察者”的“他者”。同样从烙印在文人内心的城市想象来看,“他者”的身影更是无处不在。张恨水坐在重庆怀念北京和南京时自有一番认识,“北平以人为胜,金陵以天然胜;北平以壮丽胜,金陵以阡秀胜,各有千秋”[8]。同时这里更隐藏了“重庆”这样一个“他者”,在重庆大轰炸的情形下,不免会怀念南京悠闲自得的生活,使得张恨水回忆起来显得那么的从容与安定。日常生活比较更是随处可见,“十几年前我在上海居住的时候,乘坐马车的人们虽然已经不多了,但仍然可以有机会看到……但在今日之南京,马车的用途却变得非常的广大了”[9],十几年间的变化,南京与上海在交通方面的差距如此巨大,恐怕作者的言说并不仅仅停留在对交通的抱怨上。
在整个民国时期,将南京与其他中心城市放入一个平面化的现实中进行比较,政治的南京是其最核心的部分,在政治作为其重要影响因子的前提下,文学等各方面有了作为南京独特性的标示。随着民国政府1927年再次定都南京,对于南京而言,意味渐浓的政治文化中心,与北京传统的教育文化中心和上海现代经济文化中心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与此同时南京的经济和教育文化的劣势也得到大大的改善,并逐步发展壮大起来。
直接跳出“定居者”范畴,从外国人这一“观察者”眼光来看,南京又是另一番味道。1840年代,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西方人眼中,南京大概也因1842年那份不光彩的《南京条约》而闻名”[10](P7)。外国人开始频频关注、游历中国,这里面尤以日本为盛。1871年中日建交,由于距离较短,日本人游历较多,一方面处于“对中国文化的乡愁”情结①在《对中国文化的乡愁》一书的前言中,借用吉川幸次郎在日文本的《对中国的乡愁》中贝塚茂树的《解说》:吉川幸次郎氏为这个随笔集取名《对中国的乡愁》,乡愁一词,在他的意识中,我想这时是与一般人理解的乡愁完全不同的。它与学子对于偶然邂逅的巴黎、瑞士怀有的那种乡愁,或许有同样的内涵。它指的是在法国留学的人回忆起巴黎的留学时代,在瑞士的旅行者回忆起攀登阿尔卑斯山时的情景,在那时表现出的一种感情。这个乡愁,不过是借用来说明终归为异邦之人的日本留学生、旅行者对待异乡的情感,超出了这个词的本义。参见(日)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对中国文化的乡愁》,戴燕、贺圣遂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多次造访考察,这里面更多的带有对中国想象的成分。早在1920年还未到过中国的芥川龙之介根据1918年游历南京的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秦淮之夜》写成《南京的基督》一文,小说中借秦淮妓女的形象展现出在当时历史和社会环境下南京陈旧、没落的形象。这也促成了芥川龙之介1921年的中国游历,在其游历中国以后写成的《中国游记》中有对于秦淮河的描述,“所谓今日之秦淮,无非是俗臭纷纷之柳桥”[11]。借用朋友之口吻暗讽“在南京最可怕的就是生病了。自古以来在南京生了病,如果不回日本治疗的话,从来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11]。“病”在芥川龙之介从《南京的基督》到《中国游记》中深刻地隐喻着中国在日本观念中的变化,文化的精神故乡已经一病不起,病态的妓女无论是身体上抑或是精神上沾染了疾病,更多的是反映着以中华民国首都南京为代表的中国落后和愚昧。另一方面,“当时日本人的中国之行,总体上与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有关,因此这就决定了他们所写的游记大多不同于纯粹以访古探胜、欣赏大自然为目的而做的‘观光记’,而是以调查和探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风土、人情等为目的的‘勘察记’
或‘踏勘记’”[12](P9)。而南京作为中国南方的重镇和民国政府的首都,这一游历的“记录”显得更加重要。1899年踏上中国国土的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游历南京写下《中国问题和南京北京》,在文中他谈到“中国问题的研究家们,近来突然把注意力集中在南京,委实是一需要留意的事”,尤其在谈到对于学校位置的设立上,他认为“在学校以外的事业,我倒不赞成在南京用力过多。因而我不得不怀疑是否有轻视北京、天津的不当倾向”。“我不知道除了研究语言以外驻留在南京还有什么意义。”[13]这种情况在中华民国奠都南京之后有过之而无不及,南京成为日本研究中国的一个重要的窗口和途径。南京的陈旧和没落不再是南京作为一个城市的形象,而成为整个中国的代言。
相较于日本作家文人又爱又恨的南京印象,西方人则稍显客观,更接近于国人自我的认识。1912-1913年先后游历印度、中国和日本的英国作家狄更生在南京短暂的停留写下了他眼中的南京,“南京是个值得观光的地方,虽然它的名胜多少有些悲剧色彩。一条20至40英尺厚、40至90英尺高、周长22英里的城墙围绕着一块比任何其他中国都市都大的区域。但这一区域大部分都是旷野和废墟。你乘坐火车经过城门,却发现自己身处乡间。你下了车,却依旧身处乡间”[14]。这与中国作家陈西滢“可是我爱南京就在它的城野不分”[15]有着相似的境遇。张英进曾指出:“北京是位于乡村——城市连续带中间地段的一个传统城市,位于小镇(如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边城、师陀的果园城)和现代大都市(如上海和后来的香港之间)。”[16](P12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南京也是一个“位于乡村——城市连续带中间地段的一个传统城市”,这就决定了南京在作家文人的笔下也会是一个摇摆不定的,既有传统文化长期熏陶的历史遗迹,又有欧风美雨浸润而来的现代气息,南京具有了多种因素合力浇灌之下的城市特性。对于生活、工作在中国很多年的记者柯乐文来说,“多年前,南京还是一座沉睡中的省会城市,还沉浸在它过去辉煌的梦境中,那时的南京是一个更适合休闲遐思和学习的好地方。多年后,如果现在所有的发展计划都得以实现,南京将成为一座宏伟的、生机勃勃的城市”[17]。在南京依然旧迹斑驳的城市中,他对于未来的南京充满了希望,这与奠都南京后大多中国人对于南京的希望与梦想暗合。可以说南京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南京的城市印象不仅存在于古旧建筑遗迹以及中国文人“定居者”的文学形象的塑造上,还有那来自于作为“观察者”的外国人“他者”的记录与叙述。
民国时期南京在本土“他者”的镜像中,始终处于弱势的地位,在具有了政治中心的功能之后,略显丰富。也正是由于政治的功用,其从江南重镇一跃为全国的中心,引起国外关注,然而在异域的“他者”镜像中又一次落败。可以说南京在“自我”身份认同的确立中一直处于流变状态,这也是文学南京形象不断变换和丰富的一种结果。
二、文本内涵的丰富与“自我”身份的建构
清末民初,中国经历了一场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方面的变革,古老的封建帝制覆灭,代之而起的是民主共和的新政权的建立。曾为六朝古都的南京,在这一时期也从偏安一隅的江南重镇一跃而成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在这个巨大的变革中,社会各个层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生活于斯、游历于斯的文人墨客,在他们的笔下,南京开始发生了从其固有之印象到新兴之观念的嬗变。
如何表现这一嬗变的历程,文本无疑是最好的表现方式。对于一个城市而言,文本首先就是其客观存在的实体,凯文·林奇认为,“城市如同建筑,是一种空间结构,只是尺度更巨大,需要用更长的时间去感知”[18](P1),对于南京而言,它的文本自然就是它的建筑、道路、古迹和自然风光。张英进在论述如何表现1930年代文学中的上海时谈到,“我认为现代城市的文本创作其实也许是20世纪初中国城市现代性的一种特殊的经验,也就是现代城市的感觉和认识的创新”[19]。虽然张英进强调“制作”城市文本的过程,但不可否认,这个过程的原初动因和最终体现却是由城市文本搭建的。同时,他的论述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推而广之颇有价值的经验,那就是“20世纪初中国城市现代性的一种特殊经验”,并且这种经验是一种“现代城市的感觉和认识的创新”。具体到对于南京城市的书写,无论是传统的士大夫还是新文学家,在他们的笔下,南京印象的初步建立依然靠的是实体的建筑、道路、古迹名胜与自然风景带给的感受。凯文·林奇同时也认为,任何城市都有一种或一系列的公共印象,而这种公共印象与物质形式有着密切关系。他进一步把这种物质形式分为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五类,其中标志物“常被用作确定身份或结构的线索”[18](P36)。例如朱自清《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的秦淮河,秦淮河是南京的母亲河,“自南唐和明初筑城后,秦淮
河流人古城通济门外的九龙桥时始分为两支。未人城的一支叫外秦淮,是南京城的护城河;流人城内长约十里的叫内秦淮,是其正流。它自东关头人城,经夫子庙和中华门内的正淮桥,水波宛转向西北,然后从水西门的西水关出城,与城外淮水汇合,这就是素有‘十里珠帘’的秦淮”[20](P436)。梁实秋、俞平伯、张恨水等文人留下珍贵的文字来书写秦淮河对于“自我”的南京体验,秦淮河可以说成了古旧南京城最初的印象和最为明显的标记。同为游览,那么对于文人雅集来说,最好的去处莫过于鸡鸣寺上豁蒙楼。豁蒙楼是两江总督张之洞为了纪念其门生“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而修建的建筑,而“豁蒙”二字则取自杨锐时常吟诵的杜甫《八哀诗》“忧来豁蒙蔽”句,其地位于有“南朝四百八十寺之首”赞誉的古鸡鸣寺最高处、风景集散地鸡笼山的东北端。尤其是梁启超所题“江山重叠争供眼,风雨纵横乱入楼”,使得流连于此的文人忆及时局的动荡,颇深感唏嘘。由于其毗邻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也成为学生时时畅谈游历之地。这样一来,“豁蒙楼”成了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对于城市的精神和内涵的一个新的体现。南京不仅仅是“六朝古都”的金粉之地,对于世事的关注,对于国家的关心,南京城市的印象逐步发生变化。随着中华民国奠都南京,新的建筑之于城市印象的建立有了新的变化,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对“新名胜之中,自然首推中山陵墓”[21]的推崇。朱自清在1934年游历南京之后对于南京印象发生大的变化与袁昌英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那就是陈述了种种古旧名胜之后说道,“南京的新名胜,不用说,首推中山陵”[22],更是从政治话语的空间延伸将中山陵比作是“南京的基督”①曹聚仁在《南京印象》一文中写道:“一条又宽又长的大路,从这条大路走向孙中山先生的坟墓。哎,南京的基督。”参见丁帆编选:《江城子——名人笔下的老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袁昌英在游历了南京之后欣喜地感到“只有人——万物灵长的人——却另呈一番新气象”,[21]可以说他对于“新都”的赞美是由外而内的,这种新的建筑带来的认识上的变化是与政治的南京密不可分的。
如果仅是城市主体建筑、古迹等风物的书写,还不足以体现南京在奠都以后的从固有之印象到新兴之观念的嬗变,隐匿在这建筑、古迹背后的文化蕴含则将这一嬗变表达得入木三分。通过风物所体现隐隐体现出的城市精神,更具文本内涵。李书磊在谈到城市与文学的关系的时候指出:“中国现代文人是一个城市阶层,而现代文学创作是一种城市活动。事实上可以说现代文学就是现代城市中的一种‘无烟工业’。中国现代文学就存在于中国二十世纪城市的环境、氛围乃至于区域之中,它本身就是城市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23](P4)浸淫于此的现代文人作家始终摆脱不了这种痕迹在创作中的影响。城市进入到文学的方式是以提供作家生存和生活的话语空间为载体,在对于载体的论述中,城市明显的将文学作为其城市特性的一部分,这不仅是因为“都市建筑从外在形态来看呈现为物质存在和物质形态”,更重要的是“它们同样也以其所反映和承载的文化心理演化为精神形态”。从城市形成的机制来说,“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是这些礼俗中所包含,并随传统而流转的那些统一思想和情感所构成的整体”[24](P7),从这一点上来说,城市又是一种文化心理状态的衍化。
南京从1912年孙中山定都到袁世凯废都再到1927年再次奠都,这中间莫不是经历了太大的变化,对于长久以来偏安一隅的南京来说,或许早已习惯了这种存在的方式。众多文人笔下的南京也呈现出一派安静祥和的景象,这或许是由于遭受传统的文化浸淫太深,以至于面对新的时代的到来显得迟缓和滞后。那些古老建筑所传递出的讯息与传统士大夫的游历怀古情绪默契一致,“不详其‘旧’,无辨其‘新’;未明其‘常’,不识其‘变’”[24](P4)。有感于所受传统文化影响太深的南京在文学上的表达方式,1927年4月奠都以后的南京明显表现出一种紧迫感。袁昌英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两次相同的游历,得到大大的不同感受,那种对于新政权建立伊始的想象和期许,在6年之后发出了愤怒的呼喊:“新都,你的旧名胜困于沈愁之中,你的新名胜尽量发挥广大着。可是你此刻的本身咧,却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城池罢了”,“新都,你只须举目一望,在这浑圆大好的地球上面,你能发见多少像你这般空虚的都城”。“你这种只有躯壳而不顾精神生活的存在,实在是一种莫大的没面子。”[25]这与6年前“只有人——万物之灵的人——却呈现出另一番新气象”形成了截然相反的对比。此刻古都已换“新都”,除了新修的中山陵以及中山大道两旁修建的政府机关之外,“新”体现在哪呢?胡适曾指出“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大多数人心的倾向是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26],这种“新”是建立在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建立的国民政府并且因其形式上统一了全国所带来的对于和平和发达的期望上,与胡适有着同样感受的时任南开大学教授何廉也表示:“我们住在北方,我却真心实意地拥护南
京政权,例如1928年,我、蒋廷黻和几个朋友从天津到南京。我们在南京见到新国旗时是多么激动呵——对我们来说,那或许是一个伟大新时代的象征。”[27](P11)这个新建都市完全成了当时国民的一种精神的向往和寄托,尤其是历经多年战乱灾祸的中国,急需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结束战乱,维护安定和统一,无疑在这一点上,“新都”的象征意义已经大于其实际的城市建设的实体意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相对于群体而独立的个体知识分子,在亲赴其地的感受中生发出不同的声音。高长虹目睹南京奠都之后的状况质疑道:“南京也是文物之邦,交通便利的地方,何以看不见青年办的什么刊物呢?”[28]白克带有揶揄意味的讽刺:我们在伟大的图书馆里就找不到一本可读的新杂志,像《永生文学》《世界知识》都没有[29]。如果说前面重点论述的是城市外在的形态对于“新都”的“新气象”的意义,那么高长虹、袁昌英、白克、荆有麟等人则深刻意识到文化之于“新都”内涵建设上的意义,可以说在这一点上两者形成了同构的关系,并没有因为新都建设所表现出的“新”而掩盖住隐藏在背后的缺陷和污点,就连《中央公园》等民国政府主办刊物也批判道,目前首都存在的“六朝的风度”,“那就是,名士的清谈,有闲的趣味,享乐的追逐,醉生的梦死”[30]。从这一点上来说,新都不仅在外在物质形态的构建方面树立了新的形象,而且无论从正面的宣传还是侧面的纳谏上都呈现出一种积极的心态,这应是前所未有的“新气象”的表现,显示出作为“新都”的精神风貌和文化心态。
南京沦陷之后,“新都”景象一转而为“陷都”,面对日本的侵略,南京作为民族国家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对于南京的认识逐渐从描述古旧风物的形态上演变为由此而生发出来的家国情感,古旧风物成了寄托这一情感的想象性的载体,并一直持续到抗战的结束。除却对于抗战的惨烈描述所激起的家国之恨之外,张恨水更多的是怀念南京这一象征家园的精神依托。他的《白门之杨柳》《日暮过秦淮》《秋意侵城北》《顽萝幽古巷》等一系列的情感随笔,将这一思恋之情延伸得绵远而又深长,南京的古旧风物完全成为其怀念故国的精神象征,那是秋风起也思,杨柳动也想,日暮乡关怀念,江冷楼前怅惘,可以说他乡的一草一木都可以牵连起作家的“乡愁”情绪。然而这并不完全能概括这种情感的表达,从某个侧面来说,“张恨水与其说是在怀念一个地理意义上的记忆空间,不如说是在怀念一个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城市知识分子空间,这是一种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生存方式”[31](P144)。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大多是经过城市的浸染与熏陶,无一不染上“都市病”,正如离开家乡之后的“怀乡病”一样,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的迁徙,身上自然地带有这种“怀乡病”所遗留下的传统,虽然在很多时候对于都市是抱着一种“敌意”的态度,在城市中怀念自己的家乡,但是一旦离开城市却又念起城市的好来,在这一点上鲁迅的“离开—归去—再离开”的模式表现得最为典型。当然这也不为鲁迅所独有,曾卓曾深切地歌吟道:“当离开你回到故乡时,我欢跳若向你告别,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又荫生着对你的思念,因为,在你的怀中,留下了多少青春的回忆。因为,是你的,既有圣火又有毒焰的熔炉,锻炼了我,陶冶了我,给了我结实的身体和火焰的心!”[32](P109)就张恨水而言,南京是其人生最为辉煌的阶段,在南京创办了《南京人报》,并且在这之前自费考察西北经济状况,可以说,张恨水已经完全脱离传统文人吟咏畅谈的文学表达模式,而是身体力行地实践,以一个个体的力量来促进家国的繁荣,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张恨水赋予了南京这座城市独有的记忆,文学的南京因为有了张恨水的存在而变得更加丰富和迷人,南京与文人形成了一种良好的互动形态,共同应对着新的时代对于文化的诉求。
作为实体建筑的文本构筑了民国时期南京最基本的雏形和框架,而动荡不堪的历史赋予南京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多的色调,可以说,民国时期的南京是与整个中华民国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其政治的更迭而引起文学观念变化,也由于文学观念的嬗变,不断地丰富和建构着“自我”的身份认同,形成了一种互文的关系。
上述的言说中,文学南京在民国时期获得了空前的可阐释性,借助于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其延续着作为地域中心强有力的文化和精神的向心力,同时也突破了传统根深蒂固的城市形象。可以说,近代以来的历史将地理意义上的南京在政治方面的功能激发得更为显著。但是,不可遗忘的,也正是这些复杂因素所具有的现实遭遇与自南朝以降的潜移默化的文化移植和转化,使其成为一个显著的特征。有学者指出:“文化作为一种联动整体和历史存在,并不能按它自身的结构形态去孤立地进行所谓内在的认知和把握,它既以一种‘社会’化的方式生存和运行,就必须以一种‘社会’化的方式来加以考察和探讨。因此,文化史研究要揭示的,就不仅仅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态,它
还包括文化内部各门类、各领域之间通过何种社会机制互相影响的过程与内容。”[33](P3)作为包含在文化之中的文学南京,它的文化意味与现实遭遇恰恰显现出在民国成立之后,在整个文化的框架内面对北京传统古都的教育文化和上海新型都市的经济,文学南京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性,也显示出在整个世界中中国文化的异质性和独特性。也就是说,民国时期的文学南京在新的历史状况下“自我”身份的认同与建构兼具流动性与独特性。
[1]孙逊,刘方.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及其现代阐释[J].中国社会科学,2007(5).
[2]萨义德.东方学·后记[M].北京:三联书店,2007.
[3]赵园.北京:城与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
[5]梁实秋.南游杂感(五)[A].丁帆.江城子——名人笔下的老南京[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6]叶文心.长袍、西装和制服[A].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7]荆有麟.南京的颜面[A].丁帆.江城子——名人笔下的老南京[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8]张恨水.窥窗山是画[N].新民报(重庆),1944-02-05.
[9]柳雨生.南京的马[A].丁帆.江城子——名人笔下的老南京[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0]衛周安.西方人眼中的南京(代序)[A].卢海鸣,邓攀.金陵物语[C].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
[11]芥川龙之介.南京[A].中国游记[C].北京:中华书局,2007.
[12]张明杰.近代日本人游历中国总序[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3]内藤湖南.中国问题和南京北京[A].卢海鸣,邓攀.金陵物语[C].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
[14]狄更生.南京[A].卢海鸣,邓攀.金陵物语[C].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
[15]陈西滢.南京[A].丁帆.江城子——名人笔下的老南京[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6]张英进.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M].秦立彦,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17]柯乐文.今日南京[A].卢海鸣,邓攀.金陵物语[C].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
[18]凯文,林奇.城市意象[M].方益萍,何晓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19]张英进.都市的线条: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派笔下的上海[J].冯洁音,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3).
[20]叶楚伧,柳诒征主编.首都志[M].南京:正中书局,1935.
[21]袁昌英.游新都后的感想[A].丁帆.江城子——名人笔下的老南京[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2]朱自清.南京[A].丁帆.江城子——名人笔下的老南京[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3]李书磊.都市的迁徙[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
[24]陈继会.新都市小说与都市文化精神[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
[25]袁昌英.再游新都的感想[A].丁帆.江城子——名人笔下的老南京[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6]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N].独立评论,第18号,1932-09-18.
[27]自易劳逸.流产的革命——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M].陈谦平,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
[28]高长虹.南京的青年朋友们起来吧[A].丁帆.江城子——名人笔下的老南京[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9]白克.一天的生活和回忆[A].丁帆.江城子——名人笔下的老南京[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30]庸.六朝的风度[N].中央公园,1933-01-22.
[31]朱周斌.张恨水作品中的乡村与城市[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5.
[32]曾卓.重庆,我又来到你身边[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
[33]黄兴涛.新史学·序言: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M].北京:中华书局,2009.
[责任编辑:戴庆瑄]
许永宁,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江苏 南京 210023
I206.6
A
1004-4434(2016)10-0119-06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民国社会历史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框架”(12AZW 010)的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