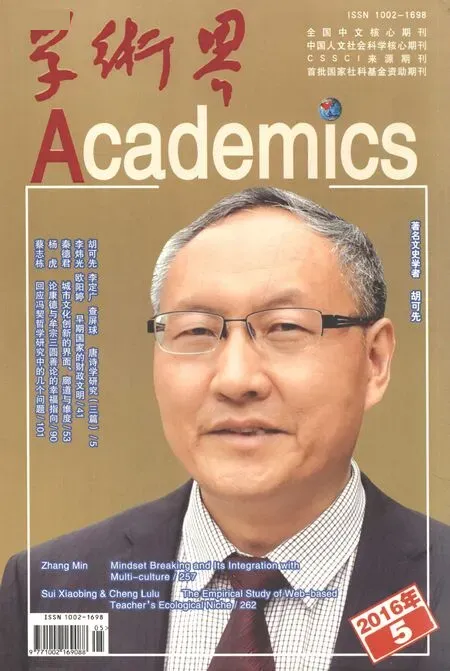论《乐记》对宋代理学家乐论的塑形
○ 康 勤
(合肥师范学院 音乐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论《乐记》对宋代理学家乐论的塑形
○ 康勤
(合肥师范学院音乐学院, 安徽合肥230601)
音乐在中国古典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乐记》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音乐理论著作,它对宋代理学家的乐论影响巨大。宋代理学家的主要乐论带有明显照搬《乐记》的痕迹,《乐记》对其具有“塑形”之功。这种影响除表现在基本母题、美学范畴、指导思想等方面的一致性之外,在音乐接受心理层面亦有明显的表现。与此同时,宋代理学家乐论又对《乐记》思想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归纳和提升,使其经过理学化的定型之后,对宋代以后的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乐记》;音乐;理学;乐论;塑形
宋代理学以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乐论,与《乐记》〔1〕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乐记》是先秦音乐美学、音乐理论的突出代表,它“不仅是第一部最有系统的著作,而且还是最有生命力、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2〕对于《乐记》,以往的研究者更多地围绕其自身体系进行探究,集中对《乐记》中的礼乐关系、礼乐本质、以及音乐功能等层面展开讨论。诚然,此类研究固然重要,但往往偏重于共时性,致使很多成果陈陈相因,往往忽视了《乐记》对中国哲学史和音乐史的深刻而具体的影响。本文认为《乐记》不仅是宋代理学的重要理论来源,同时也是其乐论思想的渊薮,在理学家眼中《乐记》是与道学关系最为密切的儒家经典之一,二程、朱熹等理学家都认为“唯《乐记》为最近道学者”〔3〕。因此笔者不揣浅陋,试从音乐理论层面探讨《乐记》对宋代理学家乐论、乃至整个理学体系的意义。
一、《乐记》创生理学家乐论基本范畴
要梳理《乐记》与宋代理学家乐论及理学整体思想的关系,首先需要明确《乐记》自身的定位问题。目前来看,对《乐记》的研究还存在许多不够明朗的地方,比如作者问题、产生年代以及版本传承问题等。李学勤先生在《周易溯源》一书中认为《乐记》的作者是公孙尼子,当为七十子的弟子,为战国初期人物,其年代应在子思之后,孟子、荀子之前。〔4〕这一观点目前在学界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因此本文从此说。另一个争论的焦点是《乐记》版本问题,笔者同意著名音乐理论家吕骥的观点,〔5〕他认为《乐记》当存在两个版本,一个为河间献王刘德所撰,经王定、王禹的传授,最终献于汉成帝,在《艺文志》中有《王禹记》(已亡佚),应该便是刘德所撰《乐记》;另一个当为《公孙尼子》二十八篇,后经刘向校定为二十三篇,而收入戴圣《礼记》中的为前十一篇,后十二篇在刘向《别录》中只存其目。
对《乐记》的作者、成书年代、版本问题有了基本的定位之后,下面具体讨论它与宋代理学家乐论基本范畴之间的关系。《乐记》作为早期儒家艺术理论著作,其中已经广泛涉及“天理”“性”“静”“情”“欲”等重要范畴,并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定位,这些观念经过历史的洗礼,到了宋代便成了宋代理学家建构理学体系的宝贵资源。
宋代理学的整个理论体系及其主要理学家的乐论,实际上恰是围绕上述几个范畴来展开的。某种程度上这些范畴也是构建理学家乐论的思想基石,厘清它们的含义及相互关系,对于把握理学家的理学思想和乐论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性意义。这些范畴中,“理”“性”无疑是最具本体性的,二程认为“性即理”,朱熹在《二程遗书》中专列此条,并有非常翔实的记述,朱熹亦认为“天即理”“性即理”。可以说,这种观念最早开始于《乐记》,后经郑玄的进一步解释,始得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延展开来,郑玄在解释《乐记》时称:“理犹性也。”以郑玄为代表,汉儒的这种观念被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接受并加以系统化,从而形成了构建学说的重要基石。
《乐记》除了认为“民有血气心知之性”之外,还有两段涉及“性”的文字:《乐本》篇言“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乐论》篇言“乐由中出故静”。对于《乐记》而言,“人性本静”是最基本的出发点。这些认识深刻地影响了宋代理学及其乐论思想,比如张载说:“赤子之心,人皆不可知也,惟以一静言之。”〔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理学家也并非亦步亦趋地机械搬用《乐记》思想,而是以此为起点,进行了创造性地加工改造,程颢在《颜子所好何学论》中对“静”的认识是“真而静,其未发也五性具焉,曰仁义礼智信”〔7〕,对此,朱熹的解释是“五性便是真,未发时便是静”〔8〕,由此可以看出,在程颢、朱熹等宋代主流理学家的乐论中,“性”的本质特征仍是“静”,但却并非像《乐记》一样将“性”或“静”的本体归为“血气”,而是认为“仁义礼智信”为其根本。这一转变就很有意思,“五常”肇始于先秦儒家的伦理道德,虽然在儒家音乐体系中十分重要,但与人的本性并无必然联系。但是在理学家看来则并非如此,或者说他们人为地将“五常”与“性”“理”加以勾连,从而使其在理学乐论中具备了更为充分的合理性。由此,可以说宋代理学家的乐论,一方面继承了《乐记》中“性”与“静”这样两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另一方面也同样认同两者之间的关系,只不过将“静”的内容定义成了具有鲜明伦理性的“五常”,并以“五性”视之。这一点恰是宋代理学家有意对《乐记》思想进行修正的地方。
“静”是内心尚未萌动的原初状态,与“静”之本性相对的则是人的情欲。故《乐记·乐本》言:“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这段文字认为人受到外物触动从而心性产生激荡这是正常的现象,关键要对由此产生的“好恶”之心加以节制,如果人被外物诱惑而无法节制,便会有“灭天理而穷人欲”的结果发生。由此可见,宋代理学家乐论中对“性”“天理”“人欲”之间关系的认识,在《乐记》中已经初具雏形了。事实上,宋代理学家对《乐记》的这一思想恰恰是进行了非常自觉地接受的,据南宋黄震《黄氏日抄》所载:“明道尝曰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愚按《乐记》已有‘灭天理而穷人欲’之语,至明道先生始发越大明于天下。”〔9〕黄震为宋代著名学者,晚于朱熹,而崇朱子之学,受理学影响非常深,所以其上述观点应该不是空穴来风。综合来看,在“天理”与“人欲”问题上我们便有了大致的线索,尽管在对待“人欲”的问题上,《乐记》主张以“节”(节制)为主,理学家乐论主张以“去”为主,但两者并无本质的不同,正如蔡仲德先生所言:“就‘人欲’的‘去’、‘节’而言,二者确有程度上的不同;就将‘理’与‘欲’对立起来,主张‘反躬’以保存先天固有的‘天理’而言,却不能否认它们在唯心论的本质上并无二致。”〔10〕到了宋代,《乐记》中“灭天理而穷人欲”的观念一变为二程的“灭私欲则天理明”,而在朱熹那里,更是将这种观念发扬光大,甚至在他看来整个儒家经典都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11〕
由此不难看出,从《乐记》到二程,再到朱熹实现了对“天理”和“人欲”问题的系统化和哲学化,在《乐记》中“天理”与“人欲”这两个概念毕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而且两者的内涵也与理学家乐论中的含义不尽相同,《乐记》中所言“天理”当更接近“天性”,郑玄便释“理”为“犹性也”,因此可以讲此处之“理”可以视为“性”带有形而上特点的另一种称呼,而在宋代理学乐论中,“理”的内涵则要丰富很多,它不仅是“性”的母体,也是对传统“礼”的哲学化。就是说,理学家乐论将先秦儒家所推崇的“礼”进行了哲学化的升华,使原来仅停留在日常道德领域的伦理化的“礼”,变成了一种既兼具等级性,同时更具统摄力的“理”,从而完成了“天理”对“人性”“情欲”乃至社会人生的全面掌控,从作用于外在的“礼”,变成了干涉人灵魂的“理”。这不能不说是儒家乐论思想的完善过程,尽管其中对“人欲”的禁止,后来成了禁锢人性的糟粕,但理学家乐论对儒家核心思想的创造性重构则是值得肯定的。重构的过程尽管意义非常,但却少不了固有资源的贡献,《乐记》恰是这种固有资源中值得重视者。
严格意义上讲,《乐记》对于宋代理学及其乐论基本范畴的意义,丝毫不亚于《大学》和《中庸》。或者说《大学》《中庸》是朱熹在北宋既有的理学框架下,从义理层面对儒家典籍的再发掘,重在进一步强化新儒家的指导思想和行为规范,相比之下,《乐记》则参与了北宋理学及其乐论的最初构建,因此它更具有本体性意义,宋人卫湜在《礼记集说·统说》中曾指出:“河南程氏曰……《礼记》除《中庸》《大学》,唯《乐记》为最近道学者,深思自得之。”〔12〕同样的记载亦可在朱熹辑录的《二程遗书》之《畅濳道录》篇中见到。应该说,朱熹肯定是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的,只不过元代以后“四书”在逐渐被官方经典化的过程中,地位愈发固定,从而遮蔽了《乐记》本应有的光芒。
二、《乐记》规约理学家乐论基本母题
在谈完《乐记》对宋代理学及其乐论的整体贡献之后,下面谈谈其对宋代理学家乐论的具体影响。概而言之,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乐与政的关系、音乐美学范畴,以及淫声雅乐之界限三个方面。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一直以来便是儒家音乐理论关注的对象,事实上周代典礼仪式便开始大量用乐,自此乐便与礼仪、政治纠缠在了一起,较典型的例子如春秋时代吴公子季札出使鲁国,观周乐而知政治得失(《左转·襄公二十九年》)。乐与政的关系,在《乐记》中获得了最充分的表达,《乐记·乐本》言:“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懘之音矣。……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尽管后来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提到了与之不同的观点,但不管怎么说,以《乐记》为代表的儒家乐论在整个中国音乐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是占据主导优势的,而“声音之道与政通”的思想也构成了宋代乐论尤其是理学家乐论的重要内涵,并表现出直接的继承性。其中较突出者就是理学的开山之祖周敦颐。
周敦颐的乐论思想主要集中在《通书》中,该书专门辟有《礼乐》《乐》(上)、《乐》(中)、《乐》(下)四篇讨论音乐问题。其在《乐》(中)篇开篇即说“乐者,本乎政也”,认为音乐的根本来源是社会政治,只不过在周敦颐看来政治、人心、天地之气、万物之间是存在相互和合的关系的,即“政善民安,则天下之心和,故圣人作乐以宣畅其和心,达乎天地,天地之气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则万物顺,故神祗格鸟兽驯”。〔13〕政治的良善,带来人心的和谐,人心的和谐会感染天地,进而又使得万物和顺。需要说明的是,政治、人心、天地、万物这些范畴在《乐记》中都已经出现,而且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做了一定的说明,只不过与周敦颐较为周延的理论言说相比,尚显得稚嫩。比如,《乐记》在谈到乐的起源问题时,提出了著名“感物说”,《乐本》篇开篇即言“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承认人心与外物之间的感应关系。同时,《乐论》篇亦提出“大乐与天地同和”的观点,指出乐是符合“天地—自然”的规律的,某种意义上乐是天地间万物和谐的体现,《乐礼》篇言:“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但需要指出的是,《乐记》在提出“感物说”和“大乐与天地同和”的观点之后,却缺乏必要的理论勾连,所以在理论体系的圆融性方面尚显不足。相较而言,周敦颐的乐论体系可以用“俗变—心变—乐变—气变—俗变”这一模式来概括,在这一体系中各单元之间的关系又并非是单向度的,而是具有回溯性的,比如一方面“心变”可以带来“乐变”,但反之亦然,故其在《乐下》篇中又称:“乐声淡则听心平,乐辞善则歌者慕,故风移而俗易矣”〔14〕这便又构成了“乐变—心变—俗变”的模式。
而且,周敦颐除了在体系上对以《乐记》为代表的传统乐论进行改造之外,亦对传统儒家音乐美学的范畴进行了处理,他最为著名的“淡和”观便是对《尚书·尧典》《乐记》中“和”这一范畴再加工的产物。《周子通书·礼乐》言:“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15〕这段话不仅将“礼”纳入到了“理”的范畴,而且仍将“乐”的本质定义为“和”。在此基础上,其“淡和”思想主要在《乐》(上)和《乐》(下)两篇中有所体现。周敦颐在《乐》(上)中指出:“故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16〕很明显,他将传统儒家艺术观中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改为“淡而不伤、和而不淫”,认为只有将“淡”与“和”充分配合才能发挥乐的最大作用,消除人的躁动之心。
周敦颐作为宋代理学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不仅改变了孔孟以来儒家道统中绝的困境,而且“对尔后七百年的学术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7〕这种评价同样适用于音乐美学层面。仍以“和”这一美学范畴为例,周敦颐对这一概念的继承,在张载、朱熹、真德秀等人的乐论中亦得以延续。首先来看张载,他言:“古乐所以养人德性中和之气。……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则入于噍杀,太下则入于啴缓,盖穷本知变,乐之情也。”〔18〕很显然,此处的“古乐所以养人德性中和之气”思想与周敦颐思想中由“乐变”而“气变”的“淡和”观念是有联系的,从中我们亦可看到,周敦颐在张载思想中仅是起到了中介的作用,其思想的本源当是《乐记》。张载上面的这段话在《乐记》中亦可寻到踪迹,《乐记·乐本》载“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乐记·乐情》称“是故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啴缓、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除此之外,张载在《礼乐》篇的开篇就指出:“礼,反其所自生;乐,乐其所自成。礼别异,不忘本,而后能推本为之节文;乐统同,乐吾分而已。”很显然,这完全是由《乐记》中的“乐统同,礼辨异”的观念演化而来,只不过张载将礼与乐的这种差异性纳入到了自己的理学体系中而已,从而使礼乐和合思想更加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
“和”这一音乐美学范畴,经过北宋周敦颐、张载的接受、利用,在南宋朱熹的乐论中仍有充分体现。朱熹认为音乐乃至乐器的最高境界便是对人的“中和”品性的培养,他将这种品性称为“正性”,其在《紫阳琴铭》中便直言“养君中和之正性,禁尔忿欲之邪心”,〔19〕这成了衡量音乐乃至乐器好坏的重要标准。而且,他也对周敦颐“淡和”思想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古圣贤之论乐,曰和而已。此所谓淡,盖以今乐形之,而见其本于庄正斋肃之意……古今之异,淡与不淡,和与不和而已。”〔20〕在朱熹看来,“和”与“淡”都是古乐具有的特质,但时过境迁,今天音乐所追求的平和,很有可能与“和”的最初形态不尽一致,所以面对这种实际音乐情况,“淡”似乎更容易达到,朱熹认为这恰是周敦颐提出“淡和”思想的深层动机,《答廖子晦》之十四篇称:“古乐以和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盖今之所谓宽者,乃纵弛;所谓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谓宽与和者,故必以是矫之,乃得其平耳。”〔21〕由此可见,朱熹是对周敦颐的思想持肯定态度的,某种程度上朱熹的乐论是带有辩证性的,与当时时代实际音乐状况结合相当紧密的。
宋代理学家乐论除了在对待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在音乐美学范畴层面直接沿袭《乐记》传统之外,在对待郑卫之音的态度上也存在同样的因袭。实际上,对郑卫之音的否定源自孔子,但却是在《乐记》《毛诗序》等文献中将之发挥到极致的,而《毛诗序》的思想又来自《乐记》,所以严格意义上说,《乐记》对后世艺术思想尤其是乐论的影响更为根本。《乐记》在其第一部分即《乐本》篇中便指出:“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对于“慢”,用《乐本》篇中的原话解释便是宫商角徵羽“五者皆乱,迭相陵,谓之‘慢’”,如果一个国家充斥这种“慢”音,那么“国之灭亡无日矣”。同时,《乐记》中对这种音乐还有另外一个称呼:“溺音”。《乐记·魏文侯》篇记载了魏文侯与子夏的对话,魏文侯问子夏说“敢问溺音何从出也?”子夏的回答是:“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综合来看,《乐记》认为作为“慢”音或“溺音”的郑卫之音危害极大,就小处而言,可祸乱人心,使人们“皆淫于色而害于德”,就大处来说,则会导致社稷易主、江山变色。事实上,在宋代理学家中这种倾向是一以贯之的,张载便说:“移人者莫甚于郑卫,未成性者皆能移之,所以夫子戒颜回也。”〔22〕同时,“郑卫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连,又生怠惰之意,从而致骄淫之心”。〔23〕张载对郑卫之声的否定是从人性角度进行的,这也代表了理学家乐论思想的总体倾向,在他们看来郑卫之声是对“性”的扰乱,很容易激发人不适度的情欲,所以理学家绝不称呼郑卫的音乐为“乐”,而只是以“音”称呼之。其实,这种情况肇始于先秦,《乐记》最开始便对“声”“音”“乐”这三个概念进行了区分,其中“乐”与前两者的区别不仅是形式层面更为多元,最主要的是要表现出“德”的内涵,所谓“德音之谓乐”是也。郑卫之“音”相较于“乐”缺少的不仅是形式层面的合适,更是内容方面的道德质素,前者只能祸乱人心,后者才可“养心”“治心”,所以真德秀便说:“今世所用大抵郑卫之音,杂以夷狄之声而已,适足以荡人心、坏风俗,何能有补乎?故程子慨然发叹也。然礼乐之制虽亡,而乐之理则在。故《乐记》又谓‘致礼以治身,致乐以治心。’”〔24〕由此,足见《乐记》思想对宋代理学家音乐雅俗观的深刻影响。
综上,宋代理学家的乐论各有侧重,而且由于他们的乐论是整体理学思想的组成部分,所以相较于先秦《乐记》,往往表现出更具体系性的一面。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基本母题、美学范畴、指导思想等方面还可以看到它们明显因袭《乐记》的痕迹,而且除了周敦颐将“淡”引入乐论体系之外,理学家的乐论也并无多少新意,并未脱离《乐记》中的既定讨论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乐记》对宋代理学家乐论起到了最为基础的“塑形作用”。
三、《乐记》孕育理学家音乐接受观
音乐心理学是现代音乐研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学科,音乐对人的影响往往是带有潜移默化性质的,考察这种影响的发生机制是现代心理学的重要研究维度。诚然,这一视角属于现代学科范畴,但早在《乐记》中便已经有了非常充分的相关论述,并得到了宋明理学家的呼应。
上文已有所涉及,《乐记》中有一篇讲到魏文侯与子夏的一段对话,子夏向魏文侯比较系统地解释雅乐与俗乐之间的内在区别。这段对话在音乐美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它从十分理性的角度剖析了两者在精神实质上的不同。但我们往往忽略这段对话的起因。魏文侯对子夏说,他听“古乐”唯恐自己会睡着,但听“新声”则会不知疲惫。由此,两人才展开了对雅俗问题的讨论。实际上,魏文侯向我们展示的恰恰是接受者在欣赏音乐时的复杂心理现象。作为一个城邦的君主,魏文侯的道德素养和知识水平不可谓不高,按理说,乐于欣赏高雅的古乐应该合情合理,而事实上,他则对节奏欢快的俗乐情有独钟。可以说,魏文侯的内心矛盾,恰代表了一种普遍的音乐接受心理,比如在宋代初期的太宗、真宗、仁宗这里,按照《宋史·乐志》的记载,他们私下里都曾钟情俗乐,甚至亲自制作教坊乐曲并加以演奏歌唱,但对外则要营造一种高雅的品味,不承认自己喜欢俗乐。〔25〕这种矛盾就其实质而言,乃是音乐接受心理层面理性与情感的冲突,它往往具有普遍性。
理学家是承认这种复杂的心理现象的。这似乎与我们一贯的认知不尽相同,较突出的例子就是朱熹。朱熹尽管仍然没有摆脱北宋理学家的正统观念,但其难能可贵之处是,能以一种辨证的眼光来审视古与新的问题,他反对机械刻板地复兴古乐、古礼,他说“况今去孔、孟之时千有余年,古乐散亡,无复可考,而欲以声求诗,则未知古乐之遗声,今皆以推而得之乎?……则今之所讲,得无有画饼之讥乎?”〔26〕认为一味地推崇所谓的上古雅乐,无异于画饼充饥,其结果只能是越来越僵化。正因如此,朱熹有时也不免会陷入《乐记》中魏文侯的困境之中,即在理性的接受层面他对古乐或雅乐仍充分肯定,但在感性的接受心理上,他则对俗乐犹抱琵琶半遮面,在《朱子语类》卷92中有这样的记载:“胡问:‘今俗妓乐不可用否?’曰:‘今州县都用,自家如何用不得?’亦在人斟酌。”〔27〕就是说只要稍加节制,甚至是最为道学家所反对的“妓乐”都是可以承认的,只不过欣赏这样的音乐时要有一定的条件,即以不放纵情欲,达到理与欲的平衡为标准。因此,与其说朱熹的乐论带有向现实妥协的倾向,毋宁说他的这种做法,恰是他洞悉音乐接受心理之奥秘的明证。
《乐记》除了在雅俗问题上触及音乐接受心理之外,其“德育”思想也属于这一维度。以《乐记》为代表的先秦音乐理论认为,音乐是与人的内心以及内在情感相联系的,内心的感情最初通过语言表达出来,但当这种感情达到一定浓度的时候,便会以歌咏之,甚至是手舞足蹈。正因如此,中国古代乐论一方面重视通过音乐反观人的内心是否和谐,另一方面,也异常重视音乐对人心的熏陶,试图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实现对人心的干预,在润物细无声之中培养优良的德行。这种对接受心理的重视,在理学家的乐论思想中仍在延续。比如上文提到的周敦颐,便认为欣赏音乐会使人的内心平静,达到“欲心平”“燥心释”的效果,就是说通过音乐的作用,会使接受者消除纷杂的欲望,释放烦躁的情绪。与周敦颐的倾向相一致,张载借助对郑卫之音的心理学剖析,从另一个层面强调了音乐对接受者内心的影响,他说:“郑卫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连,又生怠惰之意,从而致骄淫之心,虽珍玩奇货,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从而生无限嗜好。”〔28〕就是说在张载看来,郑声的最大问题是促使产生“怠惰之意”“骄淫之心”以及“无限嗜好”,这些都是对“心”的扰乱。如果说周敦颐是从积极层面解读音乐对人内心的影响的话,那么张载则是从消极层面强调恶俗之音对人心的戕害。但不管怎样,以周敦颐和张载为代表的早期理学家是非常重视音乐对欣赏者接受心理的影响的,这种倾向在二程、朱熹乃至陆九渊的乐论中都有所承续,限于篇幅,不赘述。
因此,无论在处理雅俗问题上出现的理性与情感的冲突,还是对音乐的“德育”效果的强调。理学家的乐论都沾染着明显的《乐记》气息,虽然中国古代没有所谓的音乐心理学这样的称呼,但无疑地,这些发现都是具有普遍性的,哪怕在现代音乐教育体系中也仍然熠熠发光。这就使得无论《乐记》还是受其影响的理学家的乐论,都具有了某种现代意味,甚至在强调素质教育的今天,也可为当下的教育实践者提供某种参考。
行文至此,笔者认为中国思想史在发展过程中总体上有两个黄金时期,第一个时期当然是先秦,作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也作为后世思想的武库,提供了思想文化向前推进的潜能。第二个时期则是宋代,原因在于这一时期不仅实现了儒释道思想在理论层面的融合,而且也形成了相对周延的哲学体系。理学产生于宋代,但却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先秦时期的天道观、人性论都为其产生埋下了古老的种子。一直以来,我们由于受到朱熹“四书”说法的影响,往往认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对理学贡献巨大,这种认识固然不错,但并不完全。《乐记》不仅“是我国古代一部比较系统的音乐美学著作”,〔29〕而且也是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美学著作,它对宋代理学体系的建构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同时正是由于宋代理学家对《乐记》思想的接受,客观上又使其思想获得了系统性的归纳和提升,使其经过理学化的定型之后,在宋代以后的乐论发展中继续发挥作用。
《乐记》对理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这种影响不仅表现为其在哲学领域对理学整体建构的重要作用,也表现为其在狭义的音乐思想层面对理学家乐论的影响。但也正是由于这两个方面的整体性影响,《乐记》对理学乐论的意义也就优劣杂陈了。具体来说,《乐记》对理学体系建构的影响是积极的,是值得肯定的,甚至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乐记》便没有理学的健全和完善,但另一层面,《乐记》对理学家乐论的影响则带有消极的味道,由于在理学家眼中“道统”思想异常严重,所以他们的乐论多停留在陈陈相因的层面,并无多少创新,其讨论的主要内容、美学范畴、接受心理等基本上还局限在《乐记》早已设定的固有藩篱之中,这种情况到了明代,随着心学的崛起以及民间文艺的繁荣才有所好转。
注释:
〔1〕本文所引《乐记》文字,悉据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一书,下文不赘。
〔2〕蒋孔阳:《评〈礼记·乐记〉的音乐美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第117-137页。
〔3〕〔7〕〔宋〕程颢、程颐:《二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23、577页。
〔4〕李学勤:《周易溯源》,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109-120页。
〔5〕吕骥:《关于公孙尼子和〈乐记〉作者考》,《中国音乐学》1988年第3期,第4-12页。
〔6〕〔18〕〔22〕〔23〕〔宋〕张载:《张载集之经学理窟·诗书》,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255、262、263、378页。
〔8〕〔11〕〔27〕〔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三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75、207、2349页。
〔9〕〔宋〕黄震:《黄氏日抄》(卷三十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页。
〔10〕蔡仲德:《评吕著〈乐记理论新探〉》,《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第73-81页。
〔12〕〔宋〕卫湜:《礼记集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页。
〔13〕〔14〕〔15〕〔16〕〔宋〕周敦颐:《周元公集》(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29上、429上、427上、428下页。
〔17〕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3页。
〔19〕〔21〕〔26〕〔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五),朱杰人等:《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994、2100、1653页。
〔20〕〔明〕邱浚:《大学衍义补(卷四十四)·乐律之制下》,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年,第385页。
〔24〕〔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公文集·问兴立成》,明正德刻本,第287页。
〔25〕〔元〕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356-3357页。
〔28〕〔宋〕朱熹、吕祖谦:《近思录集释》(下),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924页。
〔29〕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48页。
〔责任编辑:钟和〕
康勤(1980—),合肥师范学院音乐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音乐理论、钢琴演奏与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