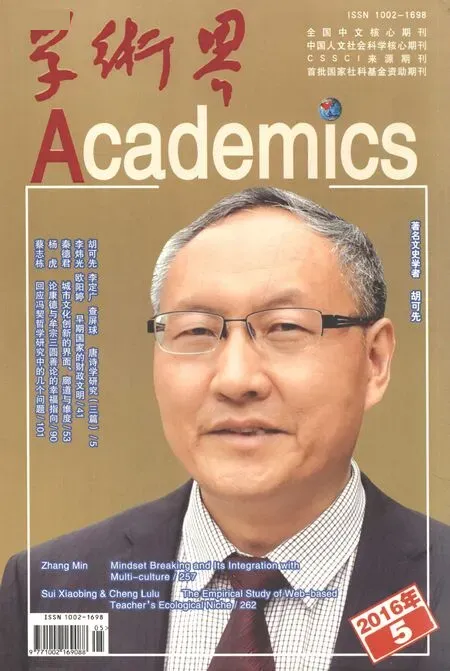早期国家的财政文明
——三星堆文化遗存的启示
○ 李炜光, 欧阳婷
(天津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天津 300222)
早期国家的财政文明
——三星堆文化遗存的启示
○ 李炜光, 欧阳婷
(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天津300222)
应用历史学研究中的早期国家理论、经济学研究中的新制度经济学国家理论和财政社会学理论的基本方法,根据三星堆古文化遗存中的青铜器、祭祀土台、古城墙遗址和治水遗迹的考古文献资料并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可以认为三星堆古国的财政是一种早期国家财政,其基本特征是财政资源凝聚于祭祀活动和常备军支出方面,同时亦承担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治水等社会公共需要的费用,并且财政文明中财政先于国家产生而存在。另依据古代文献,三星堆青铜器及其财政文明可能来自于中原夏代王朝,这是个需要考古学和财政史学的进一步研究才能加以证明的观点。
三星堆;古蜀国;青铜器;早期国家;财政起源
三星堆古文化遗址,地处四川盆地的成都平原,位于广汉南兴镇的月亮湾一带。作为早期国家形成和发展阶段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它的财政文明也富有魅力和启迪价值,合于财政与国家“紧紧捆在一起”的关系定位和作为连接政治、经济与社会三大子系统纽带〔1〕的基本特征,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印证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值得今天的学者认真面对和探求。我本人曾经两次去三星堆博物馆详加参观考察,感觉是震撼的和极富启发性的,引发的思考不断地困扰着我,遂撰成此文,就教于学界同行。
一、与现代财政理论的衔接:早期国家和早期国家财政
三星堆文化和以其为代表的古代巴蜀文化,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失踪已久的古代文明。它有着十分辉煌且极具个性特色的文化色彩,作为区别野蛮社会和文明社会界限的四项基本标志——城市、文字、金属器和礼仪性建筑都已具备。但今天的我们对这一古文明依然十分陌生,既不知道它来自哪里,如何发展,也不知道它因何种原因突然自杀式地走向灭亡。正如《三星堆文化》序言中所说的:“当它正处于隆盛状态时,却于商末周初戛然而止,给人们留下一连串扑朔迷离的难解之谜,凸显出一大片需要填补的巴蜀古史研究的空白。”〔2〕我们只能通过对出土的大量造型奇特的青铜器、规模宏大的古城墙和祭祀中心的残迹的考证,大略知晓这是个距离现在四千年左右的古代文明。
从现已发现的文化遗存看,三星堆古国国家机制的发展并不十分充分,疆域观念并不明确,世俗意义上的王权并不十分巩固,这从它依然较多地依靠神权强化统治就可以看出来,也没有迹象表明,它对所属邦国有较为严密的控制,这些特点,使得三星堆古国很可能处于由前国家形态向国家形态的过渡时期,即早期国家形态。所谓“早期国家”,是指以血缘组织为基础的邦国在公共权力、行政管理、财产分配及占有方式乃至意识形态等方面已经具有较为鲜明的国家性质,但在“以血缘组织而非地缘组织为基础划分居民等方面依然遗存着氏族社会的特征”,即还未演化到成熟国家的某个特殊历史阶段。早期国家是近二、三十年来国际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概念。在我国史学界,使用这个概念的学者还不很多,尚属一个“比较新的提法”。〔3〕李学勤先生也曾指出:“由于国家的兴起是一个相当长久的过程。国家的萌芽形态以及其早期面貌,必然和后世人们习惯理解的国家有很大的、甚至是带有根本性的差异。为了凸现这种差异,对萌芽形态的国家、早期阶段的国家赋以特殊的名称,借示区别,或许是必要的。”〔4〕
国内外学者对早期国家的基本特征大体有以下几点认识:第一,政治集权(political centralization,或“权力集中于少数人”)和行政管理专业化(specialization of administration),这两个特征在通常情况下是国家理论的主干。〔5〕只有在集权的国家中,才能组织起大规模的社会劳动,有效地抵御自然灾害的袭击和外来侵略。所以,早期国家都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最高政治权力中心,而中央集权的最一般的表现,如基辛(R.M.Keesing)所说,是“既有政治权威又具神圣性,……国王授权给头目管理各地方。”〔6〕三星堆文明大体符合这一特征,是一种集神权与王权于一身的政治统治。
第二,依据第一点,早期国家一般都已经拥有与其中央权力相适应的行政管理和政治机构,包括官僚系统、军队、监狱等,赋税的征收就属于这一类问题,它是辨别一个社会是否存在正式的行政和政治机构的主要标志,所以恩格斯曾说:“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捐税是以前的氏族社会完全没有的。”〔7〕今天的我们无法还原三星堆古国征收赋税的情景,但它的结果还是以青铜器和古城遗址的物质形态十分清晰地留给了3500年以后的我们。
第三,早期国家是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的社会,这是个与我们所熟悉的“阶级分化”十分近似的概念。它与“阶级”的差别在于它还不十分确定社会分化已导致真正的阶级的定型,而财政资源的筹集和配置就是在既定的社会分层格局下进行的。三星堆已是分层社会,国家建立后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设定和提供产权保护,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不同等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以换取持久征税的可能性。这从三星堆古城遗址上的文化遗存可以得到证明,当时已经是一个等级鲜明的社会,财富的支配权和占有权归于少数统治集团手中。
第四,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国家意识形态,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两个加起来共36立方米容积的祭祀器物坑、满满盛装着的800多件青铜、金、玉、陶等古代文物可以证明,神权和王权威严的脸谱和可以想见的庞大祭祀活动场面就是它的表象。〔8〕
伴随着早期国家的产生,由政权机构自存和发挥社会公共职能的需要而产生的财政行为、财政思想和制度也同时出现了。我们姑且将其称为“早期国家财政”。在我国财政史学界,一直存在着财政分配现象的产生早于国家出现的观点,〔9〕并有《史记·夏本纪》中“自虞夏时,贡赋备矣”的说法为依据,而三星堆早期国家财政实践又为这一认识提供了进一步的实物证据。当然,既然是“早期”草创阶段的财政,就很难避免不够成熟和完善。实际上,当时国家也处于开创期,也谈不上成熟完善的问题。虽然三星堆王国早亡,但作为一种制度演化和文化现象,其财政活动对于后世的国家治理和财政实践仍具有很高的价值。
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和财政社会学,国家政权建立后,需约法天下,声明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及基本的社会正义,以此换取提供这种保护的报酬——税收。税收是国家与人民之间签订的一种隐性契约,征税是国家缔造者所能获取的最大福利。税收具有独享性,国家必须是国内的第一暴力集团,因为第二集团就无法获得征收赋税的合法性。为了持久地获得税收来源,国家必须兼顾另外两个问题,即设计和提供财产权利的形式,通过调整产权格局,激励产权持有人的经济行为,使国家税收最大化。同时国家要努力降低施政成本,目的是防范政治对手的竞争。事实上,这种竞争对手总是存在的。所有这些问题,三星堆古国都会面对和致力于解决。它的竞争对手,既来自于内部的政治角逐,也来自于外部中原王朝的压力和征讨。至于为什么这样,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将试图给出一个答案。
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是一个被财政学界有所忽视的有关财政税收起源的重要思想,是由道格拉斯·诺斯提出的,对我们理解三星堆文明有很大帮助。诺斯阐述的国家形成的三个基本要素是:
第一,国家用一组被称之为“保护和正义”的服务,来交换税收;
第二,国家将公民分成团体和阶级,为每个团体和阶级设计和制定产权,以最大限度地增加生产、增加国家税收;
第三,国家永远存在着提供类似服务的竞争敌手,譬如其他的国家,或者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因而国家受公民的机会成本的制约,也就是受公民接纳第二个竞争者可能性的制约。〔10〕
显然,一方是国家征税获取的利益,一方是人民依法获得财产支配权和在此基础上所获得的税后利益,它们之间必须保持一个大体的均衡关系。如果国家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发生背离,国家横征暴敛而人民陷于重税盘剥的贫困之中,这就是著名的“诺斯悖论”所描述的情形。“诺斯悖论”出现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它预示着潜在的政治危机已经发生。
现代财政理论认为,税收是政治权力的一部分,是作为联结政治、经济和社会各子系统的媒介而存在的,为社会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才是它恒久不变的职能。所以,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公共权力首先给人们提供的是一种向心力和凝聚力,暴力则是次后发生的,这是人类社会需要一个政府存在的最恰当的理由。如赫尔佐克所说,如果国家征了税却不提供公共服务,“那么世界上的国家都不过是一些巨大的盗匪团伙而已。”〔11〕这是个有待证明的和存在争议的观点,但作为最早的国家形态,三星堆古国的统治者已经尝试着履行国家的职能,通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大规模治水活动为社会提供一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却可以得到比较确定的证明。三星堆古文化遗存让他们有机会作了一个自我证明,他们做的还算不错。
二、“祀”与“戎”:早期国家财政资源的凝聚点
青铜器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中原文明如此,三星堆文明也是如此。正如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所说的:“青铜器既是中国文明的象征,又是产生这种文明的因素。”〔12〕三星堆遗址的两个神奇的祭祀器物坑,坑中的青铜器、玉器、金器等出土物,仿佛是高度浓缩的古蜀文化的信息库,一经发现立即在整个世界引起轰动。而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人想到在中国的西南内陆一隅,会有如此辉煌发达的古代青铜文化遗存。而且,这种文化在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中原商周文化相比较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有些“另类”的文化面貌,被考古学家称为“三代以外”的早期文明。〔13〕
青铜是以铜、锡或再加入铅为主要原料熔炼而成的合金,具有良好的延展性、硬度和强度等优点,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颇受青睐。张光直先生认为,中国青铜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作为巫术法器的中国古代艺术品在造成或促进政权集中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因政权的集中在中国历史上一向是与财富的集中紧密结合的,而财富的集中又是文明产生的基础,中国古代的艺术在文明起源的程序上就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里所讲的“中国古代艺术”,主要指的就是青铜器,其对文明起源、国家起源、阶级社会起源的原则性、法则性问题上,“有世界一般性的意义”〔14〕。
在古蜀人看来,青铜器由于它的特殊造型和纹饰,具有连接人与天地相通的功能,占有青铜器便是握有权力,便是合法的统治者,所以青铜器是政治性的物品,青铜冶炼以及青铜制品几乎全部被用于与政治相关的领域。正如张光直先生所指出的:“中国青铜时代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青铜器的使用,不是在生产技术方面,而是在另一个方面。”〔15〕这里所说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政治权力的工具。青铜硬度高,是先进生产力的表现,却不被用于生产领域,这是中国青铜文明迥异于世界其他国家的现象。
王权采取神权的形式,是政治权力宗教化的表现,意味着古蜀国实行的是一种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王权与神权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国家元首同时也是宗教领袖,“既为政治领袖,又为群巫之长。”〔16〕世界上单件最大的青铜器——高2.6米的“青铜大立人”,考古学家普遍认为它是蜀人的大巫师,也有学者认为它是古蜀国的最高统治者——蜀王的造型。如果真是这样,他应当经常在祭祀大典上主持仪式和发表演说,深谙占卜和天象知识,同时也懂得如何治理洪水和领导农业生产。他依靠宗教和军队作为统治工具,以贡赋的形式获取和支配王国的资源。
显然,在中国古代文明中,青铜是神权和王权的象征。祭器和兵器皆为青铜所制,祭器和神联系在一起,是以神的法则立国的宣示,而军人身上的铠甲和手中的兵器是护卫神权和王权的利器,它们无一不是青铜文明的产物。这就是“国之大事”为什么“在祀与戎”的原因。〔17〕两者之中,“祀”又是第一位的。这是中国早期国家财政的最初特征。三星堆王国财政的这个特点尤为突出。
青铜器是为祭祀这种当时最重要的公共活动所制造,必然有大批专门技术人员、工匠参与其中。他们需要掌握勘探和熔矿技术,使用较有效率的生产工具,兴师动众地进行采矿、伐木、运输、冶炼过程。三星堆青铜器物群所用铜材总量估计有8到10吨。根据地质学知识,天然铜矿的含铜量一般在10%至14%左右,也就是说,要得到10吨纯铜,至少需要100吨铜矿。铸造过程中,需要数十座坩埚同时点火,场面一定十分壮观,而这一切的背后是资源的征集与调配问题。当时一定有一个高效率的国家指挥中心在发挥作用。本文所关注的,正是青铜器这种物质在“文明起源程序”中的组织形式中所起的至关重要作用。这实际上是一种财政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值得作进一步的探讨。
祭祀活动总要有场所进行。华夏先祖遗传下来的一个极其古老的风俗,就是祭祀天神和祖先。祭祀高于一切,感谢神灵赐给人生命和生活技能,祈求后代繁衍和免除灾难。人们构筑高台,在台上搭建草木建筑,将精心制作的木、石以至三星堆时代的青铜雕像置于祭坛之上,人们对之顶礼膜拜。所谓三星堆之“三星台”,就是三座长约数十米至百米,高5米至8米,连结成一线的土堆,分布在马牧河西岸东、南、西三面的台地上,这里就应该是古老祭坛的所在地。
在成都北门外,有一座巨大的正方形土台——羊子山土台,高10米,分三层,底座面积超过19000平方米。人们开始以为这是一座大墓,并开挖了数年,后来发现它是一座大型祭祀台。分层构筑是土台屹立数千年而不倒的原因,说明古蜀人已经掌握了十分先进的建筑施工技术。目前多数考古学家认为羊子山土台是三星堆文明的一部分,因为从成都出发到广汉城西鸭子河畔不过30公里。四川学者段渝在《四川通史》中提出了一个羊子山土台的建筑工程问题,认为该土台“总面积约10733平方米,估计用泥砖130多万块,用土总量在7万平方米以上。若征发两万人修建,至少要3年或4年才能建成。”〔18〕这个观点曾引起考古界对古蜀国国力问题的一场大讨论。不管怎样,该工程浩大无比的规模说明古蜀国已经具有十分强大的国力,背后必定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进行统一调度指挥,并提供充分的物力支持。这便是财政问题了。
在早期国家,战争的功利目的,包括对土地和财产的占有,对人力资源的吞并等变得日益重要。如斯宾塞指出的,战争所要求的组织能力,它的等级制和中央统帅机制,最终从军事领域扩大到整个社会。〔19〕这是他对战争在国家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的一个概括性的说明。战争改变着社会运作的机制,对人类政治组织的集权化和复杂化起了催化的作用,产生出原始部落社会所没有的新的机制,比如“打败的村落就被迫纳税和献贡”等。〔20〕这些显然都是通往国家制度的重要因素。
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齿形上下援青铜戈、全身披挂戎装的青铜站立甲士雕像,以及大批明显是由实战兵器演化而来的戈、矛、剑等形制的玉石兵器,还在二号祭祀坑出土了20件三角形锯齿援直内无胡戈。此外,在古蜀国腹心地带成都发现了大量属于商末的青铜兵器,以及在王国边疆地区陕南汉中城固发现有80多件商代中晚期的三角形援蜀式青铜戈。〔21〕种种迹象表明,三星堆古国存在着一支相当规模的常备军,这需要消耗大量物质资源,即相当规模的养兵费用,包括武器装备、组织管理、军事训练、指挥系统、后勤供给等在内,都需有充分的资源配置。这也从军事的角度证明,王国的核心政治集团已经建立起一个垄断和支配其所需要的资源的集权性质的国家机器。
三、城市建设和治水:早期国家的基本公共职能
关于国家起源,恩格斯的说法是:“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22〕“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23〕但研究中国历史发现还有问题存在。在国家职能中,暴力当然是存在的,但这只是它的一个方面。国家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为了压迫人而存在的,是为了保证统治者过上既奢侈又有权势的生活而发明出来的。如果没有一个对共同体至少是大多数成员都有好处的目的,统治秩序是不可能稳定和长久维系的。所以研究国家起源问题,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它最初的时候是以何种德性和手段聚集了民众,然后才是军队、警察、监狱等专政工具的问题。这个初步的判断来自于历史,而不是教科书。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王朝收税之后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之一。考古资料表明,公元2000年前左右,至迟夏代晚期或商代早期的时候,三星堆古城的城墙就已然伫立起来了。日本学者堀敏一也指出:三星堆“遗址中的大规模城墙,一般认为已经建造于青铜器时代初期(大约在商朝早期)”。〔24〕三星堆遗址上残存着一堵巨大的城墙,东西长1600—2100米,南北宽1400米,总面积3.5—3.6平方公里,其规模超过了作为商代早期统治中心的郑州商城。据考古学家的勘定,该城墙横断面呈梯形,下部墙基宽约40米,顶部残宽约20米,可谓一项艰巨浩大的工程。由于取土量非常大,在墙体外侧竟挖出了一道深深的壕沟。修建如此规模的城墙,需要开掘数量巨大的土方,需要建立一个包括运输、工具、设计、施工组织、食物供应、劳动力和相关资源的征集在内的调度指挥中心,说明王国的财政系统已经形成,并且是十分富有效率的。
三星堆古城绝非一般意义上的聚落城址,而是一座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不是一个建筑物的稠密聚合体,而是一个由诸多专门确定的区域所构成的网络。”〔25〕在三星堆古城,宫殿、祭坛、广场、街道、大型房屋、地下排水设施等各种大型公共建筑已经出现,构成了早期国家的特征。这类建筑工程只有在社会剩余财富总量达到可观的数量时才可能组织进行,在部落社会中,这类建筑是见不到的。这说明,当社会逼近国家形成和它形成的初期阶段,它的生产力水平有了飞跃性的提高。没有一定规模的生产力,任何社会都无法凭空“发明”出国家来。
三星堆古城的城墙面积超过了中原商王朝的都城——郑州商城,也超过了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美索不达米亚早期城市乌鲁克和乌尔等城市。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古城的设计合于中国传统,以中轴线为核心加以规划、展开布局。在中轴线上,分布着古蜀国的宫殿区、宗教区、作坊区和生活区,构成了王国首都平面规划的四个基本要素。出土了数百件青铜器和黄金制品的两个大型祭祀坑就是在宗教圣区发现的,其中有著名的青铜大立人、青铜人头像、青铜神树、青铜兽面具、黄金面罩、黄金权杖等。生活区遗址可见密集的房屋群,其中有疑似公共建筑的面积达200平方米的超大型房屋。铺设有纵横交错的排水通道,透露出寻常巷陌间的市民生活气息。应该说,世界古代早期城市大都设有上述功能区,如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公元前5500年前就有人类聚居,公元前4000年前城市就已清晰地划分为各种功能区域。但以中轴线为核心加以规划,则是中原城市的基本特征。从城市规划布局来看,三星堆古城是中国古城的风格,而非外来文明。
治水是王朝提供的另一项公共服务。成都平原系大河冲击扇形平原,虽然沃土千里,却常常遭受洪水的侵害。每当夏秋之季,岷山雪融时,上游江水暴涨,一泻千里,冲毁平原上的村庄和庄稼。在三星堆遗址,至今仍能看到河流冲毁城墙,从城市中穿流而过的痕迹。所以从很早的时候起,蜀人就注重治水,不断总结经验,最终制服了洪水。按照常规,城墙的主要功能是军事防御,但三星堆城墙的构筑却有所不同,它的顶部宽度几乎相当于其底部宽度的二分之一。也就是说,它的墙面不是垂直或接近于垂直的,而是形成了一定的坡度,而这种坡度对于军事防御而言,恰恰是相当不利的。所以考古学家认为,“根据三星堆现有地形地势、河流分布以及文献所透露的点滴信息来看,三星堆城墙应当兼有‘防洪大堤’的功能。”〔26〕
总之,部落战争的压力、大型祭祀活动的需要、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治水等公共产品和服务,都需要动员大量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才能完成,这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力中心从事组织管理,财政指挥机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而这些工程完成之后,国家的政治权力也就得到了加强,例如治水的需要和控制当地居民的生活命脉(如水利工程)等。还应当看到,神权和王权合一的政治体对人民的制裁力和威慑力是极其强大的。无论是城墙、大型礼仪广场、宗教性建筑物的修筑,还是水患的治理,都是公共活动,它们只能在一定的强制力下进行,最后定型为现代税收的基本形式特征。
四、社会分层和等级制:财政起源的要素
国家税收是以暴力为依托的,但是国家诞生后并不需要经常使用这种暴力,而是倚仗暴力的威慑作用,尽量以和平、文明的方式与人民作交易,而人民也会在税赋大体合理的情况下尽量服从国家的税率。这一方面是因为不得不屈从于暴力的原因,同时也有“人民也需要税收”的含义,因为由国家出面提供的秩序和安全保护具有“规模效应”,相对说是最“经济”和“合算”的。但是,“当天灾人祸降临时,国家就负有不可逃脱的救济义务,这也是国家正义的一部分。”〔27〕所以,在强调税收强制性的同时,适当关照一下统治者与纳税者之间“各取所需”的合作关系也是有必要的,但这却是税收学理论的薄弱环节。
任何文明的出现,都要求建立社会财富分配的等级体制,这一点从三星堆青铜器上也可以看出来。正如张光直先生所指出的:“就中国来说,这些要素主要存在于政治领域:财富的积累,通过资源分配的日益不平衡而实现;反过来,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又是极强大的王权出现所带来的结果。在这里,极强大的王权的出现首先是与青铜器相联系的。对于中国文明的出现来说,青铜器是关键,因为青铜器被用于铸造礼器和兵器”。〔28〕
史学研究表明,社会分层是以社会的一部分人占有和攫取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为前提的,这需要某种机制来保障资源向特定的一部分人流动。在较低发展程度的社会中,由社会来供养一个非生产性的机构是难以做到的,而在社会分层的条件下,这一点就可以做到了。“在一个由少数人组成的集团范围内,较多财富的集中已经是可能的了,而社会对此只能容忍。于是新形成的国家机构便大肆搜刮民财民力,以此来建设一个对古代社会来说是极为庞大的‘上层建筑’。”〔29〕
在这个过程中,暴力的威慑力发生着作用,享有大部分资源的人逐渐成为统治阶级,并且这种资源流动方式也在国家体制的名义下逐渐合法化。“给中央仓库提供粮食,已不是个人的自愿行动,而是征税。”〔30〕这时候包括实物和劳役形式在内的经常性的赋税征收便开始出现了,一些大的基础设施工程由官员组织实施,通过强制性的劳动进行,并且逐步法典化。显而易见,在社会分层的基础上,早期国家获得了保证自身生存与运转的物质条件,它不仅来自于社会生产力总水平的提高,也是社会分层与阶级分化的结果。这便是对国家财政起源过程的一个粗线条的描述。
在三星堆时代,古蜀国便是一个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分层社会,其“统治阶级由国王、王室子弟、姻亲、贵族、臣僚和武士等构成,也包括分布在各地的大大小小的地方性族群之长。”在政治上实行的是王位和贵族的世袭制度。段渝先生说:“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和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各式青铜人像、人头像,其间的时代相距达百年以上,可是它们却在若干基本形制方面,比如面像、表情和衣式、冠式、发式等方面颇为一致,具有明显的继承性,意味着它们所象征的历代统治者集团完全是一脉相承、世代相袭的。”〔31〕在三星堆城内遗址还发现了大量形制不同、制作精美的青铜和陶质酒器,展示了当年权贵和官宦的生活场景。
在三星堆古国,由国家权力的运行所带来的庞大政治性消费是社会的沉重负担,社会生产发展成果的很大一部分用于这种消费,表现出其对生产力发展的依赖性和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双重作用。大批最先进的生产力(青铜资源和技术)被用于祭祀活动这类单纯性的物质耗费上,却极少用于制作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上,这是那个时代的局限,三代中原王朝也都是如此。
五、三星堆早期国家及其财政文明或来自中原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批眼部突出的青铜面具、人头像、大立人像和青铜扶桑树等特有文物,令今天的人们喜出望外,但同时又大惑不解,因为这些青铜器物大都是被人为砸坏或被火烧损后就地掩埋的。那时的三星堆人不知中了什么“魔法”,他们在做了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之后就集体撤离,辉煌的三星堆文化就此完全消失。他们给后世的人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谜团,至今难以解开。这就是史学界常说的“失忆”现象。
考古学者认为,三星堆文化属于该文化层的“三期文化”时期,但它并非二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甚至可以说毫无相似之处。因为一、二期文化十分原始落后,连一块金属片都没有,而三期文化突然涌现出大量制作精美的青铜器和陶器,技术含量高出一、二期太多。这不像是一种正常的过渡。〔32〕既没有任何过渡,也没有传递和继承。
成都平原基本没有铜矿资源,缺乏制作铜器的原料,而三星堆器物坑却出土了大批青铜器,就像在没有水的地方突然出现了大批鱼群,令人不可思议。四川境内的铜矿集中在石棉县境内以及更南的西昌一带,与三星堆的直线距离在700公里以上,中间隔着高山河谷,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三星堆人从那里获得铜矿的可能性不大。另外,三星堆遗址内也没有发现大的金属冶炼和铸造作坊,〔33〕也没有发现应该堆积如山的矿渣,只发现有规模不大的手工作坊。这样规模的作坊只适于金属器物的修复和小规模生产铸造。
两坑器物埋藏的情况都有些“不正常”:青铜大立人出土时从腰部斩断并被分置两处,青铜神树也被无情地砸烂,部分人头像和人面具也被故意砸坏,而且大多数器物有明显的火烧痕迹。现在我们看到的完美的青铜像是经过考古工作者精心修复的。可以想象,这种“不正常”的埋藏方式,一定是在某种紧急而特殊的情况下发生的。当时的情景一定令人深感不安,事态万分火急,它可能牵涉到古蜀国历史上的一个隐秘的重大事件。但那是什么样的事件呢?是外敌兵临城下,还是大水冲进了城市,抑或整个族群要自我毁灭、另谋生存?对这些问题,我们一无所知。
三星堆文明之奇,在于它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出现了,又毅然决然地自我毁灭。仿佛从天而降,又不明不白地突然消失,所以让人有不知所措之感。是不是可以说,三星堆的青铜器是来自于外部?那么,它们又是来自外部世界的哪个方向、哪个地域呢?
考古学界和史学界对于三星堆青铜文明来源,有出于当地土著、出于西域、出于外星人等多种说法,亦有学者认为古蜀文明出于夏桀时期,由有缗氏部族从山东携带入蜀而开创的。这个说法引起了我的注意,并且在三星堆遗址考查中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认识。
考古学界早已证实,我国夏代社会已经进入了青铜器时代。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器铸造技术已经走向成熟,出现了作为礼器的斛、爵、鼎、斝等;兵器有戈、器、镞等。铜器等制作工艺已相当进步。〔34〕《左传》宣公三年记:“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此处所说的“金”即铜;“贡金九牧”就是夏王朝各地方诸侯向中央王朝贡纳青铜。《史记·封禅书》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九鼎之说,史学认可其为信史,说明这个王朝社会已经有较高的社会分工和劳动专业化程度系,以及财政资源的调度能力和控制手段了,较复杂的政治制度已然出现。
夏王朝早期国家已建立起较为完备的贡赋制度。据《尚书·禹贡》载:“禹别九州,随山濬川,任土作贡。”《史记·夏本纪》载:“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推行以贡纳和山林川泽之利为主要形式的早期国家财政征收制。所以司马迁说:“自虞夏时,贡赋备矣”;“众土交正,致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另据《国语·周语下》引《夏书》:“关石和钧,王府则有”。韦昭注:“关,门关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赋调钧,则王之府藏常有也。”
奇怪的只有一点:商朝遗址中一直没有出土前朝的青铜器。常识告诉我们,商朝是不会损毁夏代青铜器的,因为他们是战胜者,以之炫耀自己的功绩才是理智的选择。那么,夏朝的青铜器到哪里去了呢?这里面有个起伏跌宕的故事。据史载,夏朝中康之子帝相时爆发寒浞之乱,帝相被寒浞之子浇所杀。相的正在怀孕的妻子缗侥幸逃脱,至其母家有仍国(河北任县,一说山东济宁地区)避难,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少康。待少康长大,做了有仍国的牧正,其母向其讲述身世,说你不该在这里,你应该是国王。少康牢记母训,联合友好邦国攻灭寒浞集团,光复故国,夏作为众邦之首的地位重新得到确认,史称“少康中兴”。〔35〕
这段历史精彩绝伦,可称之为中国版的“王子复仇记”。《左传》哀公元年是这样记载的:浇“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四川学者白剑依据古本《竹书纪年》进而认为,有缗氏是夏后氏帝相妻的母族,帝少康的“姥姥家”,因完成“少康复国”壮举而在族群中德高望重,所以承担起保护夏王国祖庙重器的职责。〔36〕此为推论,缺乏足够的证据,但不失为一个合乎逻辑的假设。
孔甲之后,夏王朝由盛转衰,在诸侯国中威信下降。其子履癸即位,是为夏桀。这是个历史上出名的暴君,《夏本纪》称其“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尚书·汤誓》载:“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说明夏统治者与人民的离心离德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桀为了扬威于诸侯,曾“为仍之会”,有缗氏是舜的后裔,地位高贵且在少康复国中有功,不愿服从桀的暴政,史载其被夏桀攻灭,但是也有另外的说法。《左传》昭公四年:“夏桀为有仍之会,有缗叛之。”《竹书纪年·帝癸(夏后桀)》载:“帝桀十一年,桀在仍地会见诸侯,有缗氏首领逃离。”同书又载:“帝桀十四年,扁率军队征伐岷山,桀命扁讨伐有缗氏。”
蜀族逃离祖地,长途跋涉进入四川平原,定居于蜀中腹地,将中原文明融入当地,建立起蜀族统治中心。宣公十八年载:“楚于是乎有蜀之役。”杜注:“蜀,鲁地,泰山博县西北有蜀亭。”《中国历史地图集·战国》亦标注,泰安名下有“蜀”名。所以后世泛称有缗氏为“蜀族”,地名则有位于四川省北部的“岷山”和中部的“岷江”等。此“岷”与“缗”,两字相通。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孙华先生也认为,三星堆青铜文明的产生与当时的夏代文明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夏代的晚期,与夏王朝有着姻亲关系的有缗氏背叛夏王,遭到围剿,他们的一支辗转湖南、湖北,顺江而上,来到成都平原,与当地部落结成联盟,给三星堆带来了先进得多的青铜文明,并最终取得古蜀国的统治权。〔37〕孙华教授曾指出,三星堆文明源于中原的一个有力证明,是在一件青铜器上镌刻着的“眼睛”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件陶器上的“眼睛”完全相同,而不同文明遗存物的标志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38〕
距今3200年,蜀族军队加入周武王伐纣的“八国联军”,放弃三星堆圣城,掩埋祖器,自毁圣庙。妇女老弱和一支留守部队撤出三星堆进入岷山,逃避可能的战败后商纣王追杀。这段历史至今仍是一个说不清楚的谜,但一支联军中有一支蜀军能征善战,英勇无敌,消灭了大量商纣王的有生力量,却是史有记载的。《尚书·牧誓》记载了参加征讨商纣的“八国联军”的诸侯国有“庸、蜀、羌、鬃、徽、卢、彭、濮”。
如果三星堆文明果真是有缗氏部族从中原带出来的,那么他们带出来的就不会只是青铜器,也会连带将夏朝的诸般赋税财政制度一并移植于三星堆古国的制度体系之中了。我们在此所关注的问题是,财政的出现决不会晚于国家,因为它本身就是国家政治权力的一部分,而且是核心的部分。说“国家产生之后为了维持国家机器的存在而征收赋税”的观点值得重新思考斟酌,因为“之后”的说法太不确定,而且三星堆等古文化遗存表明,财政的产生是早于国家而出现的,至少是同步演进的。
三星堆古城的坐落方位并非中国传统的坐北朝南,而是呈东北、西南方向。古城的城墙并非四面合围,鸭子河方向即北面无墙,如果我们将这一面视为古城的开口方向,会吃惊地发现,整座古城也是朝着东北方向的。而城中心的三星堆排列,竟然也是朝着东北方向的!“如果我们将三星堆和月亮湾构成的直线向东北方向延伸开去,会看到什么呢?正是有缗氏祖居地山东济宁一带”!〔39〕三星堆人以这种虔诚的和独特的方式,祭奠着自己的祖先之地,表达着永世不忘先祖恩典的情意。
注释:
〔1〕李炜光:《权力的边界——税、革命与改革》,九州出版社,2015年,第75页。
〔2〕〔3〕王和:《历史的轨迹——基于夏商周三代的考察》,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88、97-98页。
〔4〕李学勤为谢维扬著作《中国早期国家》所作序言,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5〕P.B.Roscoe, Practice and Political Centralisation, Vol.34,Current Anthropology,1993,p.113.
〔6〕基辛:《现代文化人类学概论》,巨流图书公司,1981年,第525页。
〔7〕〔2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9、167页。
〔8〕以上四个要点的表述参见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51页。
〔9〕杨华、段君峰:《中国财政通史·先秦财政史》,叶振鹏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页。
〔10〕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9页。
〔11〕周书灿:《中国早期国家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序二,第13页。
〔12〕〔14〕〔15〕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5、488页。
〔13〕〔25〕〔28〕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自序,第13、384、387页。
〔16〕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宗教》,《燕京学报》1936年第20期。
〔17〕《左传·成公十三年》。
〔18〕〔37〕萧易:《古蜀国旁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5年,第90、13页。
〔19〕H.J.M.Claessen & P.Skalnik,ed.,The Early State ,p.45.
〔20〕〔30〕马文·哈里斯:《文化人类学》,李培茱、高地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240、239页。
〔21〕唐金裕等:《陕西省城固县出土殷商铜器整理简报》,《考古》1980年第3期。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6页。
〔24〕〔日〕堀敏一:《中国通史——问题史试探》,邹双双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1页。
〔26〕肖平:《三星堆:青铜之光照耀世界》,成都时代出版社,2005年,第22页。
〔27〕于阳:《中国政治时钟:三千年来国家治理的周期运动》,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第23页。
〔29〕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页。
〔31〕〔33〕段渝:《酋邦与国家形成的两种机制——古代中国西蜀地区的研究实例》,袁林主编:《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研究》,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61、54页。
〔32〕白剑:《文明的母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11页。
〔34〕张之恒、周裕兴:《夏商周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页。
〔35〕《左传》哀公元年;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7页。
〔36〕〔39〕白剑:《无字天书——来自三星堆的天启与神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16页。
〔38〕见中央电视台电视纪录片《三星堆·消失与复活》,第4集。
〔责任编辑:陶然〕
李炜光(1954—),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财政学、财政史;欧阳婷(1975—),河北经贸大学财税学院讲师,天津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财政税收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