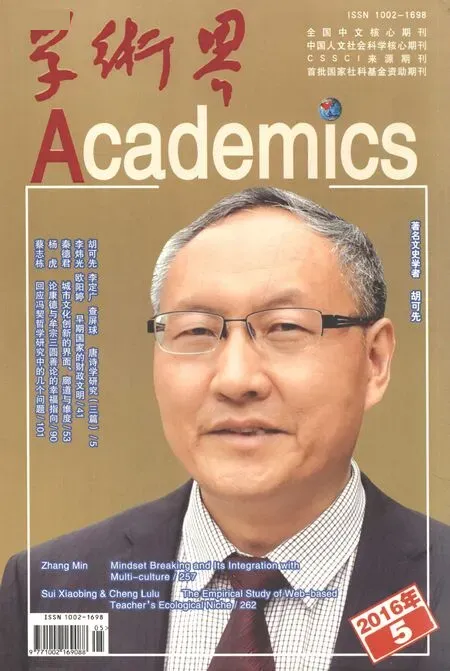生命彼岸世界的追寻与想象〔*〕
——红柯长篇小说的诗性建构
○ 李小红
(1.兰州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20;2.西北民族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30)
生命彼岸世界的追寻与想象〔*〕
——红柯长篇小说的诗性建构
○ 李小红1,2
(1.兰州大学文学院, 甘肃兰州730020;2.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 甘肃兰州730030)
新疆是红柯生命中洋溢着浓郁诗意的彼岸世界,他在五部长篇小说中完成了对彼岸世界的构筑。红柯侧重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书写,将“追寻”视作是一种重要的艺术手段完成他对精神原乡的返归。其次,在小说文本世界的历史和现实两级维度上,红柯完成了小说人物理想人格的建构,生命神性的塑造因此更富有人的主体性,也就更富有人文性和现实感。而这一诗性世界建构,同样也得益于神话、历史故事、歌谣的文本介入。
彼岸世界;诗性建构;长篇小说;红柯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工业化、城市化强势推进的背景下,乡土家园日趋沦丧,人类因此面临“失根”的威胁。在“危机寻根”浪潮的推动下,涌现出一批以精神寻根、文化寻根为主要写作诉求的“边地小说”。在怀旧力量的牵引下,以寻根方式完成了对边地历史与文化的追溯,从而在“神秘、纯洁、博大、涵藏着生命终极意义的性灵之地”,“救赎在现代生活中迷失了的灵魂”。〔1〕红柯的小说无疑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十年之前,红柯从关中平原走向新疆大野,十年之后,红柯回归故乡。然而,天山的长河落日,戈壁绿洲,大漠雄风,马背上民族的英雄神话、史诗、歌谣,成为红柯挥之不去的生命印记。于是,他执笔纵情书写,《西去的旗手》《大河》《乌尔禾》《生命树》《喀拉布风暴》五个长篇小说相继问世。对红柯而言,天山或新疆是他生命中洋溢着浓郁诗意的彼岸世界〔2〕。红柯对彼岸世界的构建,一方面,他侧重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书写,将“追寻”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手段完成对精神原乡的返归。另一方面,他从小说文本世界的历史和现实两级维度,完成了小说人物理想人格的建构,因此,生命神性的塑造更具人的主体性,也更富有人文性和现实感。而对这一诗性世界的建构,同样也得益于神话、历史故事和歌谣的文本介入。
一
“西域有大美”〔3〕,红柯如是说。红柯对“大美”精神原乡的呈现,首先通过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表述来传达,以“追寻”为其重要的艺术手段。追寻起因于人类对于自身生活现状的不满或对理想生活的期待,人类通过想象来构建种种理想境界,并将其作为一种寻找和探求的动力。2004年出版的《大河》,是“红柯对人类理想‘黄金时代’的追寻与凭吊。”〔4〕在并不恢宏的叙述格局中,小说讲述了白熊与女人的故事,呈现出自然与人和谐相融的美妙世界。在红柯始终濡染着温暖诗意的笔端,一个充满神性与诗意的美好世界跃然纸上,诗意中同时传递出些许神秘。《大河》中执拗的小女兵,为了逝去的情人,甘愿葬生于熊腹。然而,白熊却不愿伤她,将她置于山洞。她在山洞里与逃亡的土匪一起生活,后来由于怀孕离开山洞,最后嫁给了炊事兵老金。仅从文本层面看,红柯讲述的是一个温婉的人生故事,而故事的更深层面却是表达一种自由、和谐、美好的自然生命状态。女兵与老金结婚后,将房子建在森林边上,夜晚伴着满天星星入眠,吃的是从森林里采摘的鲜嫩可口的蘑菇,喝的是自家牛身上挤出来的牛奶。他们相信万物有灵,他们热爱自然、敬畏自然,认为自然是他们唯一的家园。《大河》中的小女兵认为情人死后变成了白桦树,她之所以能够嫁给老金,是白熊做了他们的媒人。女兵的孩子从小就是大力士,还能和树、老鹰等说话。白熊能够与河里的鱼聊天,鱼甘愿被白熊吃。世间万物间原本的分界线在《大河》中不再存在,物与物、人与物之间的阻隔被神奇的想象力所打通,生命之门洞开,自由流淌。于是,人与万物诗意栖居在小说营造的文本世界里。沈从文曾经提出“自然即神”的观点:“神的意义在我们这里只是‘自然’,一切生成的现象,不是人为的,由于他来处置。他常常是合理的,宽容的,美的”。〔5〕“一个人过于爱有生一切时,必因为在有生一切中发现了美,亦即发现了‘神’”,〔6〕“生命之最高意义,即此种‘神在生命中’的认识”。〔7〕由此看来,神性和诗性是不可分割的双子座,相辅相成、共生共灭。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柯与沈从文关于自然的认识不谋而合。
《大河》中,红柯“在山川、河流、大地以及动物之间”追寻,“到人真正找到了生命的根基”。〔8〕正是在对生命神性的敬畏中,“物”获得了与人等齐的灵性,自然不再是人的附庸或叙事的背景工具,而是推动人向善向真的拯救力量。红柯认为,“在人与物之间,不再把大自然作为背景作为风景,动植物应该成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从背景走向前台。”〔9〕《生命树》中他将物的灵性发挥至极致,对人与物的关系重新定位,书写物对人心灵的抚慰及对悲剧人生的化解。《生命树》全文的中心意象是生命树,这是一棵神奇的树,它长于地心,每片叶子都闪耀着灵魂。围绕着生命树,作者还描写了洋芋、牛粪及和田玉,每一种不同的物体都对应着相应的人物,都体现着物与人之间奇妙而神秘的关系。小说中高材生马燕红人生遭遇重创,精神崩溃,终日恍惚,父亲将她送到老战友的村子里静养。她在村子里偶遇一个挖洋芋的小伙子,被其挖到的洋芋深深吸引。后来她沐浴阳光,穿越田野,洞穿了天地万物的秘密,身心都得到了自然的抚慰,终于抚平了内心的悲伤,与种洋芋的小伙子成家,生下儿子王星火。马燕红一家就靠种洋芋卖洋芋为生。后来,她家那头通人性的老牛,在因吃灵芝草死亡后,丈夫将它与洋芋一起葬在沙漠里,长出一棵巨大的生命树。 海德格尔说:“拯救不仅是使某物摆脱危险;拯救的真正意思是把某物释放到他的本己的本质中。”〔10〕洋芋不仅拯救了马燕红,而且将她的命运与生命树紧密联系在一起。生命树支撑着地球,大地荡涤了人内心的创伤,荒漠变成花园,人在花园中诗意的栖居。这是红柯的期许,也是他的写作理想。
红柯说:“我的那些西部小说就是梦中惊醒后的回忆,《奔马》《美丽奴羊》《阿力麻里》《太阳发芽》《鹰影》《靴子》,这些群山草原的日常生活用品——闪射出一种神性的光芒。”〔11〕事实上,不仅在中短篇小说,红柯在其长篇小说中对新疆大野的想象和构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完成了一次灵魂对记忆中诗意家园的追寻。红柯用合于自然性情韵味的文字,构建出一种理想的诗学镜像,对“诗意栖居”时代内在的精神诉求予以响应。同时,表达他对原生态文化自然神性的尊崇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悲悯伤怀。他对乡土家园的追怀,传达着浓郁的精神乡愁和原乡意识,渗透着深刻的人文情怀,使之为现代人精神栖息的缺失疗伤。
二
红柯说:“在西域,即使一个乞丐也是从容大气的行乞,穷乡僻壤家徒四壁,主人一定是干净整洁神情自若。内地人所谓的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仓廪实而知礼节在西域是行不通的。大戈壁、大沙漠、大草原,必然产生生命的大气象。”〔12〕正是对这种生命气象的敬畏和尊重,使他超越了阶级、民族和政治的历史沟壑,将生命还原为具有永恒光泽的艺术形象。红柯笔下的人物兼具神性、血性和雄性的特征,散发着迷人的人格魅力,对理想生命的倾心表达,成为红柯小说诗性建构的表征之一。
《西去的骑手》是一部充满英雄主义神性气质的作品,在苍凉而厚重的历史和浪漫而旖旎的情怀中,红柯塑造了20世纪20、30年代驰骋于大西北战场上中外闻名的骑手“尕司令”马仲英的传奇形象。红柯说:“英雄关乎人类进步,是对他者的肯定。”〔13〕为了彰显马仲英身上的英雄主义特质,红柯进行了净化处理。一方面,红柯回避了民间传说中关于马仲英与不同女性的情感纠葛,荡涤其所有现代意义上的英雄美人儿女情长。对马仲英娶妻的情节和后来其妻隐姓埋名蛰居大漠的情节,也进行诗化处理。另一方面,红柯有意剥离史料记述中马仲英杀人如麻的匪性色彩,刻画出一位在金戈铁马、碧血黄沙的战争场景中铁骨铮铮的英雄。在辽阔苍凉的大地上,是战争成就了神采奕奕的生命——“自然生命的力量在这些野性十足的汉子们的狂喊咆哮和刺杀战斗中挥洒得淋漓尽致,如鲲鹏之翅击水三千,又像黄河之水飞泻九天。这些充满血性的骑手跃马天上如一股强烈的冲击波,读来使人不禁血脉贲张,卑琐、柔弱和犹疑不决被一荡而尽,只想长啸九霄,横行天下。”〔14〕这是属于红柯的马仲英,一个“古典游牧民族的英雄”形象,寄托着红柯对英雄的向往和渴慕。
作为一个古典的理想主义者,红柯在马仲英形象塑造中放纵着自己的诗意激情,同时,也在这一形象塑造中注入了神性元素。《西去的骑手》中,红柯用富有音乐感的语言、绚烂纷呈的色调和奇谲瑰异的语境,让我们明显感受到马仲英传奇人生释放出的奇诡与浪漫。诚然,红柯对马仲英的性格弱点未有遮掩,在马仲英背井离乡,征战南北,穿越瀚海沙漠,直到最后投身于黑海的过程中,爱与恨、正义与邪恶、勇敢与懦弱、善良与残暴,在两个极点的对抗中,一个单纯、勇往直前、闪耀着诗意的血性男儿的光辉形象出现。在《西去的骑手》的文本阅读中,读者为之所震撼的,不是那些正义战胜邪恶的无数重复的寻常故事,而是在一种不同寻常的阅读体验中跟随马仲英一起开启精神远征。因此,马仲英不仅仅是一个英雄,更是一个能够不断反思、不断超越的精神领袖,这也是文本中最动人心魄的力量,为当今陷落在精神真空时代的人们,燃起了一缕充满诗意光辉的希望。
如果说红柯在《西去的骑手》中演绎了一段古典英雄主义的浪漫传奇,那么他在《喀拉布风暴》中是将小说的故事背景从民国拉回到了当代,主人公也由不同类型的骑士英雄变成了当代新疆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迥异于《西去的骑手》中洋溢着阳刚之气的男性的叙事,《喀拉布风暴》中的红柯变得深情,他讲述了三个青年的成长故事,借助主人公的爱情成长经历,寻求一种本真的生存状态,解放或拯救被压抑的人性。
《喀拉布风暴》中,红柯为一号男主人公张子鱼设置了两个不同的生存空间,少年时期的张子鱼生长于“关陕空间”,而青年时期的张子鱼为寻求救赎来到了“新疆空间。”小说中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张子鱼,是在叶海亚的望远镜下由远而“拉近”“放大”的一个在沙漠戈壁游荡的“幽灵”形象,这个脸被风沙打磨得毫无血色、眼睛空洞而焦灼的“沙漠幽灵”让叶海亚想到了阿拉山口。张子鱼后来以一曲苍凉粗粝的情歌——哈萨克民歌《燕子》,俘获了少女叶海亚的心,两人闪电结婚,而后遁入沙漠深处度蜜月。然后,顺着叶海亚前恋人孟凯的视角,徐徐展开了张子鱼在“关陕空间”的前世今生:从小在郊区生活,体验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虽然通过发奋读书走出原来的生存之地,但却成为他心灵上挥之不去的创伤和阴影。中学至大学时期的张子鱼,不乏漂亮优秀的女性追求者,他凭着自身的魅力赢得了画画少女叶小兰、医生女儿姚慧敏及省城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大学同学李芸等人的好感,然而苦难造就的自卑心理使他没有勇气和信心面对爱情。于是,结局或是女性黯然离去,或是他在紧要关头下意识地采取“保护自己的姿势”而惯性退缩,心里这种“让人不寒而栗的阴影”让他不堪重负。于是,张子鱼来到精河沙漠空间里的“今生”寻求救赎。在遮天蔽日的喀拉布风暴中,他与天地融为一体,变成了真正的“沙漠之子”。他勇敢地收获了“沙漠女儿”叶海亚的爱情,完成了他身心的第一次成长。在叶海亚的精心呵护下,尤其是在情敌孟凯报复似地追溯他的家族渊源、追踪他的少年苦难、回溯他的情感“前史”的历程中,张子鱼终于卸下了身上的重重盔甲。
在叶海亚“快绷不住了”的夜晚,在历经了又一次昏天黑地的喀拉布风暴后,张子鱼向叶海亚完全敞开了他那颗深沉的心,完成了他身心的第二次成长。同样是从“关陕空间”中走出,西去大漠的农家子弟,张子鱼的身上有着红柯自身的投影。《喀拉布风暴》对张子鱼理想人格的构建,是以张子鱼对爱情完全敞开心扉和重获爱的能力为基础。在红柯看来,生命只有经历黑色的、席卷一切的喀拉布风暴,才能获得真正的成长。作为小说中以配角出现的两个人物形象,孟凯的成长归功于因失恋而重新补回人生苦难的一课,并由此重获生命的激情;武明生的成长焦点落在克服童年的创伤性体验,消解人生过于精明和功利的一面,以及弥补人生的厚重博深。他们成长的人格化过程表现出共性的一面,那就是逃离现代人的生存困境,重拾遗失的自然精神,选择一种“可能成为自己”的生存方式,抵达本真的生命状态。这既是成长的救赎,也是被压抑人性的拯救。
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消费型社会的渐趋成型,中国大地上,特别是经济文化的中心发展地带,躲避崇高、信仰失落、英雄隐退、道德沦丧,共同构筑了一个精神贬值的文化景观。正因为如此,红柯浓墨重彩塑造的理想人物,都是奔涌着血性力量和生命激情的西部汉子,都成长或脱胎于西部游牧民族的文化氛围中,显示出一种异于中原文化的生命意识。而表现人的神性、血性及其无所畏惧的生命意识和精神气质,正是红柯的审美理想之所在。“理想之为理想就因为它并不现实存在,而只是作为人的一种精神目标来引导,完善和改进人生,使之趋于完美。”〔15〕红柯将自己的理想人格投射于小说人物身上,使他们绽放出无限的激情、华丽和庄严。红柯的写作,是将血性和雄性的血液注入萎顿的大地之上,让生命恢复应有的高贵与尊严。
三
红柯文本世界的诗性建构,就审美品格而言,得益于他在小说中对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史诗、歌谣的文本介入。而注重意象的选择与意境的营造,将叙事与诗意并重,则可看成是红柯对古典美学神韵的内在追求。
在红柯的小说世界里,新疆乃至整个中亚细亚地区的蒙古族、藏族、回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汉族等不同民族在不同时代关于神马谷、北极熊、放生羊、大公牛、神龟以及生命树的种种神话传说,成吉思汗、努尔哈赤、左宗棠、斯文·赫定等不同国家的英雄、探险家的故事,哈萨克的《燕子歌》、伊斯兰古文献《热什哈尔》的经文、蒙古族的歌谣《波茹来》、维吾尔族的《劝奶歌》等都笼罩着一层神秘梦幻般的诗意色彩,它们或担当起小说的叙事母题和故事原形,或作为人物行动的叙事背景,有时还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小说故事情节的叙述过程之中,成为小说文本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西去的骑手》中,回族伊斯兰古文献《热什哈尔》的第一句经文穿行于整部小说,成为支配主人公命运的一种话语仪式。年幼的马仲英,在与哥哥们比试刀法胜利后,跟随大阿訇来到祁连山深处的神马谷。神马谷里无数骏马的灵骨化为一片沃土,长出如血的玫瑰。马仲英打开大阿訇送给他的生命之书,读到了那句与他生命历程形影相随的神秘经文:“当古老的大海朝我们涌动迸溅时,我采撷了爱慕的露珠。”大漠就是西部骑手心灵深处的大海,马仲英率领他的骑手们奔赴新疆,骑手们手中的河州短刀如同船桨,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掀起层层波浪。在手刃骑兵师师长的辉煌后,与随之而来的苏联大部队交锋,但以失利告终,马仲英便从大漠来到了辽阔的黑海。当他在苏联被人暗算服毒后,他和他的大灰马一起跃入黑海之中。生命如同西部高原上烁亮的露珠,虽然短暂,却辉煌绚烂。红柯用苍凉的文笔,将马仲英的传奇人生勾勒得荡气回肠。神秘的经文是贯穿全文的核心线索,冥冥之中支配着主人公的命运,让马仲英的身上笼罩上一层宿命般的迷雾。作为一种“好奇中冒险”的写作,红柯在“单纯中隐含丰富和神秘”〔16〕的马仲英形象的塑造中,折射出其丰富的神性魅力。
在《大河》中,红柯让白熊和像熊一样的男人交替出现在小说文本中。从北冰洋沿着额尔齐斯河顺流而上,在阿尔泰山完成神奇之旅的白熊与棕熊的奇妙情缘,与小女兵的奇遇,最后葬生于猎枪之下,魂归大地的悲怆结局,与老金、与土匪托海的命运相互辉映。作为一种神话动物的原型,白熊成为小说中象征着男性和雄性的一种图腾,它的出现使《大河》呈现出童话般的诗意色彩。《乌尔禾》中,草原古老的放生羊的传说成为贯穿全篇的核心意象和主题成分,以失实而得“意”的象征成为提示作品意义和经验的标志符号。全书七章中有四章的题目与羊直接相关——《放生羊》《黑眼睛》《刀子》《永生羊》,为了避免长篇写作中容易出现的主题游离和结构松散,红柯自觉以羊为核心线索和母题,将基于宗教层面对羊的放生/永生与主人公围绕着羊展开的感情故事娓娓道来。参加过朝鲜战争的退伍军人刘大壮,与王卫疆母亲在夜晚的一次尴尬际遇,使刘大壮与王卫疆一家结下了不解之缘。刘大壮替代王卫疆一家去最偏僻的连队牧羊,羊进入刘大壮的生命,汉人刘大壮从此变成了能听懂兽语的蒙古人海力布。王卫疆在海力布的抚养下长大,在懵懂的少年时期,他放生了两只羊。而长大后他的爱情,也都为这两只羊所牵引。收养了他放生的羊的燕子,与王卫疆、朱瑞以及像羊一样的白娃娃之间的恋情,都在冥冥之中与羊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小说的最后,为了化解王卫疆失恋的忧伤,海力布讲了属于自己的“三秒钟的幸福”和西域的古老神话。至此,以永生羊和草原石人等现代神话的原型意象的小说主调渐次清晰,而承载这一主调的乐符(燕子、王卫疆、朱瑞、刘大壮等)个个鲜活清亮,他们共同成就了《乌尔禾》的诗意存在。
红柯认为:“艺术家首先是个手艺人,手艺人面对材料,不会那么‘立体性’,也依物性而动。”〔17〕在新作《喀拉布风暴》中,红柯突破以往英雄与历史题材的书写,开始关注爱情和成长。他接续了中国传统的艺术智慧,用不同的意象结构全文,呈现出小说的诗性意境。《喀拉布风暴》中出现的“冬带冰雪,夏带沙石,所到之处,大地成为雅丹,鸟儿折翅而亡,幸存者衔泥垒窝,胡杨和雅丹成为奔走的骆驼”的黑色沙尘暴,与勇敢地飞翔于沙漠瀚海之间的“黑色精灵”燕子相映成趣。两个意象在文中频繁出现,前者凸显了西域自然的荒凉、粗犷和狂暴,折射出伟力和重生等意蕴;后者则成为水与女性的象征,“大西北干旱荒凉,燕子那种湿漉漉的影子与河流湖泊泉水有关,很容易成为一种永恒的集体意象与神话原型。”〔18〕哈萨克民间认为:“每个男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燕子”。只有经历人生和爱情的“喀拉布风暴”,男性才能真正成长起来,才能获得沙漠女儿燕子的爱情。而贯穿小说文本的哈萨克民歌《燕子》,也成为主人公爱情的一种媒介和隐喻。
在追寻彼岸世界的过程中,红柯运用的神话、史诗、歌谣书写,成为其回返自然、接近灵魂的有效途径。在一个个未被现代狼烟污浊的文学世界中,颂赞自然、祈祷神佑、书写英雄、礼赞爱情都离不开这些艺术元素。而作为诗歌修辞特征意象和意境的文本介入,为小说叙述注入了极富个性化色彩的抒情风格,带有苍凉绚烂的美感特征。红柯说,文章写作中最愉快的时候在于结尾:“如同秋天的大地,落叶缤纷,果实归仓,宁静中的丰收的喜悦,即便是泪水,也是一种满足。”〔19〕他的彼岸文学世界的诗性建构,何尝不是如此?
注释:
〔1〕费勇:《零度出走》,广东旅游出版社,2003年,第157页。
〔2〕〔3〕〔12〕红柯:《自序》,《西去的骑手》,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4、4页。
〔4〕李遇春:《新神话写作的四种叙述结构——论红柯的“天山系列”长篇小说》,《南方文坛》2011年第4期。
〔5〕沈从文:《凤子》,《沈从文全集》第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23页。
〔6〕〔7〕沈从文:《美与爱》,《沈从文全集》第17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59、360页。
〔8〕陈晓明:《童话里的后现代与现代》,《中华读书报》2004年9月29日。
〔9〕红柯:《在希腊书展会上的演讲》,http://www.chinawriter.com.cn/。
〔10〕海德格尔:《筑·居·思》,《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1193页。
〔11〕红柯:《我的西部》,《敬畏苍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0页。
〔13〕〔17〕〔19〕张雪艳:《自然与神性的诗意追寻——红柯访谈录》,《延河》2009年第11期。
〔14〕朱向前:《黄金草原——心灵的牧场》,《小说评论》2003年第4期。
〔15〕张汝伦:《理想就是理想》,《读书》1993年第6期。
〔16〕叶开、钟红鸣、红柯:《访谈录》,《西去的骑手》,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3页。
〔18〕红柯:《喀拉布风暴》,重庆出版社,2013年,第159页。
〔责任编辑:弘亭〕
李小红(1978—),兰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
〔*〕本文受2015年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甘肃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本土化书写研究”(项目编号:YB019)资助。
——《丝路骑手:红柯评传》自序(节选)
——“红柯中短篇小说集品读会”会议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