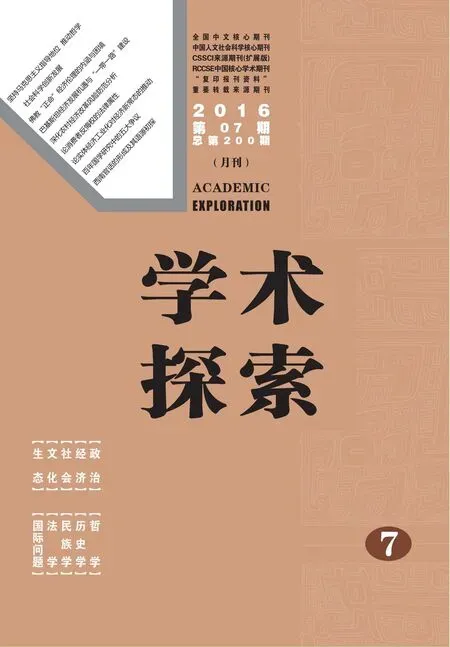论儒学社会主义
杨柳新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论儒学社会主义
杨柳新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既需要“与资本共舞”而又需要“超越资本”,这使得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与孔子儒学的融合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议题。儒学社会主义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孔子儒学人文主义与马克思的人文主义高度契合,这主要体现在两者对人的社会性本质或共同体性的洞察,两者对人的主体创造性的肯定,以及关于人的自由个性成长的过程哲学等方面。孔子与马克思以人文主义为主题的对话,昭示了一种以社会个人的“自我意识”和儒学传统道德价值观为内核的儒学社会主义精神。
儒学社会主义;孔子;马克思;人文主义
一、“儒学社会主义”何以可能
当代中国社会生活中有许多现象,指向一种正在兴起的“儒学社会主义”。最典型的征兆也许是孔子的“复活”:孔子像,孔子学院、孔子研究、孔子影视剧、孔子祭祀典礼等等。孔子所象征性地代表的儒家文化,及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正在通过经典、礼仪、话语、学术、教育、风俗、文艺等载体和途径全方位地复苏。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系辞下》)。审视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可以看出,在经济基础层面,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资本和市场经济共舞;在上层建筑层面,马克思主义与正在复苏的儒学对话与交融。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相遇需要历史的契机,然而,作为两种对人类的命运,尤其是出于深沉的忧患意识,对人类文明进程所面临的危机及其化解之道,有着高度契合的共同关注焦点的思想及其现实运动,两者交汇与合流的必然性是由两者的内在特质决定的,两者注定要通过某种机缘走到一起。当今中国具备合适的环境和社会载体,能够提供这种“机缘”。全球资本主义的种种问题在这个儒学曾长期主导的古老的文化国度最为广泛、显著、深刻、突出、尖锐地凸显出来。由于在经济上采用了资本和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所面临的道路上与价值上的挑战和考验,无疑是人类生活中前所未有和最为艰险的。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孔子与马克思的相遇成为一种必然的思想事件。孔子和马克思都是那种“天下”意义上的圣哲,他们都有一颗为天下和万世而思想的心灵。他们绝非局限于其民族、时代和国度的思想家。他们之间思想的衔接,具有某种跨越文化界限的传承性。马克思并非完全是西方的,而是兼具西方和东方的“气质”。更直白点说,马克思在思想上可以视为是孔子儒学与西方文化联姻而生的“后代”。不可以将儒学仅仅视为一种古典和中古的东方传统而已,也不可以将马克思主义仅仅视为一种现代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反对之物。它们本是不受其产生之时代与地域局限的,普遍性的人类精神成就。然而,狭隘化地理解两者而形成的种种误解,从来就屡见不鲜。
儒学从人的德性和伦理文化的角度,阐明了“天人合一”的“天下共同体”形成与永续发展的内在必然性、现实可能性,以及历史演进的路径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则聚焦于理解、批判和超越人类现代性的历史中产生的破坏“人道”共同体的物化力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直面现实的“危机”。现代生产方式的奥秘与危险在马克思主义中得以揭秘。而关于如何建设一种至为广大的文明共同体的理想、自我意识、基本观念、伦理、价值和方法,儒学提供了思想和实践的典范。马克思主义也有理想,但其理论的重心在对“现实”的批判。儒学内在具有批判现实的功能和价值,它本质上不是一种只为“现实”辩护的“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具有批判意识的人文理想。不可否认,两者都有其盲点,但是,两者恰可互补而构成完整的视野。两者在今天的融合,适逢其时,为超越“资本”的天下共同体的建设所必需,为生态文明的诞生所必需。
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历史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愈来愈彰显出一种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这一中国文化传统的主体相结合的精神气质。或者说,中国正在兴起一种可以称之为“儒学社会主义”的现实运动。这事实上表明,马克思与孔子关于人文主义的对话已经在现实中“实践地”展开了。因此,从理论上把握这一对话的实质,已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课题。
二、孔子与马克思的人文主义
儒学和马克思主义有着对于人的共同的关切,这是它们彼此能够穿透历史和空间的距离,展开人文主义对话的基础。孔子与马克思都是典型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者,他们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人的本质是怎样的,以及人应该怎样生活才能实现人的尊严、创造、自由,以及人类共同体和个体的福祉。如果一种思想正视人类自身的尊严和幸福,并以此作为其思想和与之相关的生活实践的核心。那么,这种思想就是人文主义。所谓人文主义,其基本特征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将人的生命和价值置于思想的核心位置,相信人的性情、理性、道德是人类自主创造的领域,人类社会的文化和历史是人类自主创造的成就,人类生活的意义在于获得幸福,而人类的理想是实现人类的自我完善。“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论语·微子》),“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是孔子的人文主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P294)这是马克思的人文主义。
也许在马克思和孔子之间存在某种古典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差异,但他们共同秉持的人文主义是高度一致的。若人们乐于考据,应该不难辨识出一条隐秘的脉络:中国思想,尤其是孔子的儒学通过传教士的“贩运”而传到西方——西方启蒙运动的先驱们从中汲取营养和灵感——马克思主义作为启蒙之子的诞生。至少在启蒙思想的语境中,从孔子到马克思之间隐秘的“桥梁”,通过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伏尔泰、魁奈等人与孔子的关联是隐约可见的。于是,我们若说马克思主义具有孔子儒学的“基因”,就并非完全无根据的猜想。这个根据的存在,也是马克思与孔子人文主义对话的历史和思想根据。
有一种观点,将马克思视为一个为阶级斗争服务的社会“革命”理论家,一个“政治经济学”家,一个“唯物主义”的哲学家,甚至是这些形象的某种“合集”。不能说,马克思的思想,或者从马克思思想源头引申而出的马克思主义中没有导致人们形成这些印象的依据,但是,马克思有比“革命”的狂热更为冷静和深沉的历史哲学思维。而就他针对人类经济生活的思考而言,由于《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及其所依托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所以,准确地说,马克思不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家,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家。从哲学上讲,马克思的哲学并非简单地就是“唯物”的,而是强调人类生活世界的客观性与人的主体对象化的过程,是一种统一的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是表达人的主体创造能动性的唯物主义,而不是机械的、无生命、无精神气息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
马克思作为一个“改造世界”的思想家与实践家,他的思想和实践包含密切相关,有机统一的内外两面。前面提到的这个马克思的“通常”的形象,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外在化的一面。与着眼于现实的社会状态而改造外部世界的维度密切相关,而又不同于这一面的是,马克思的思想还有一种内在化的维度,这涉及一些运用外在的经济与政治手段不可能直接解决的问题:人基于一种什么样的世界观来理解人是什么?人应该相信什么或不相信什么?什么是值得或不值得追求的价值?人类生活的伦理、道德、习俗、制度和行为的法则如何生成而又如何变革?而人如何适应这些变革以获得自由和幸福?这些问题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人文主义维度。很大程度上这是关于人的自我意识、精神内涵、文化传统、道德品质、教育、劳动和生活艺术的视域。马克思思想这个视域,无疑与孔子儒学思想的视域是高度重合的。马克思与孔子关于人文主义的对话就此可以展开。
三、人的创造性与共同体性
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在“大写的人”的自觉立场上,理解人本身及其生活的意义。如果说马克思是一个无神论者,他要帮助人民戒除宗教这种精神的“鸦片”,那么,孔子或许是无神论的一个先驱。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又曰:“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马克思思想的人文主义特质,在于恢复人的尊严。这是马克思浸润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精神:很多先生将对这样从自身必然产生的结论大吃一惊,人们仰望着把人抬举得这样高的全部哲学的顶峰感到头晕目眩。为什么,到这样晚的时候,人的自由禀赋才得到承认?这种禀赋把他和一切大人物置于同一行列之中。我认为,人类自身像这样地被尊重就是时代的最好标志,它证明压迫者和人间上帝们头上的灵光消失了。哲学家们论证了这种尊严,人们学会感到这种尊严,并且把他们被践踏的权利夺回来,不是去祈求,而是把它牢牢地夺到自己手里。”[2](P46~47)在相似的意义上,孔子认为,人是生于天地之中,参赞天地之化育的大人。
马克思主义批判和否定了神秘主义,无论是宗教的还是理念论的,然而,它并没有因此而否定人本身及其生活的神圣性,而是将这种神圣性和人的创造本性的对象化关联起来:真正的神圣在于,不是通过“神创”或者理念的启示,而是通过人的实践的创造过程,人在自然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作为社会性主体的人本身、人的社会、历史、文化,以及人化了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说,人创造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作为人的对象化的整个生活世界。“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3](P88)孔子也肯定人的创造性本性。《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天赋的创造本性是开辟人类生命之道的原动力;在人类社会文明的传承中,这种天赋创造性能力及其成果得以累积性地延续和拓展。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人类生活之道,既是自然之道又是人文之道,需要以人的创造性作为其持续发展的条件。并不存在固定不变的“道”可以支撑只是无所作为的生存着的“人”。孔子的儒学把改善的权能交到每一个人手中,但并不把自满的权力赋予任何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止于至善”就是没有止境,这个方向是确定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大学》)“知”乃是知人道之本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子与庶人皆有与焉,“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因此,致知也就是在生命实践中,每个人对自己如何实现其道德价值的自我觉悟或自我认识。以这种实践性的自我认识为基础,依靠人类自身,创造人类的自我、社群、国家和天下的幸福,以及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这是人类生活的价值目标。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明确了,“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乃是人类生活的意义。这也是马克思本人终身未改的志向。
实践活动,尤其是生产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生产劳动,是体现人的创造性的最基本形式。在作为生产劳动的实践基础上,人同时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所依托的社会关系,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以及精神文化的世界。马克思通过人的感性的外在对象,理解人的对象化,但是人并不等同于人的对象化的客体,而是作为对象化客体的源泉和主体。在马克思关于人的自我理解中,人的精神性和物质性并不是分裂的二元,而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甚至,“对象”和“客体”也正是作为含有人的“精神”的可感性把握的载体,才能作为人的对象和客体而存在于人的生活世界之中。
马克思主义肯定人是灵肉一体、主观客观统一的,肯定人具有“合外内之道”的主体创造本性,或主体精神能动性。在实践的能动的唯物主义看来,被人自己创造出来的成果中也包括了人的个体性,即每个人的独特的个性和自我。这种自我并不是预先存在的人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人与人在共同体中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4](P136)“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人的个人生活和类生活并不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个人生活的存在方式必然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方式,而类生活必然是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个人生活。”[3](P79)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彻底洞悉了人的社会性本质,或人的共同体属性。“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4](P135)
四、人的发展之“道”
马克思与孔子的人文主义都建基于一种“过程哲学”。这突出地体现于儒学范畴“道”和马克思的“自然历史过程”范畴之上。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孔子在过程论的意义上,通过反思自己的生命历程而典范性地展现了他对个人生命成长的理解。个人的道德人格与自由个性的成长,本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和主要特色。
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思想,也以自由个性为其目标,但是,马克思主义不像儒学那样侧重于道德和心性养成问题,而是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关注人的能力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生产力,不仅是物质生产力,而且包括精神生产力;不仅是物的生产力,而且也包括人本身的生产力(种的繁衍)。这是理解马克思人的发展观的关键。正是在人自己生活的生产中,人的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和发展起来。
人的发展的终极目标在儒学看来,是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儒家关于圣人或大人的描述甚多,如《易传》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而况于鬼神乎!”(《易·乾·文言》)大人与小人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是否“知天命”。子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论语·季氏》)又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儒学诉诸人的道德修养与生命觉悟,来追求天人合一。从一种后现代的视角来看,儒学的天人合一,具有突出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伦理意蕴。例如孔子在《易传》中,基于天地万物共生的世界观,主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序卦》)《易》弥纶天地人三才之道,三才之道,象以六爻。“《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系辞下》)三才之道,虽有分理,不碍统合于一:“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卦》)总而言之,无非“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明乎此,可以顺性命之理,可以见太和之义。《易·乾·文言》曰:“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说将人的发展的境界提到了“天人合一”的高度。“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4](P66)马克思认为,未来人类理想的社会状况是:“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5](P760)但是,马克思侧重于强调人的生产能力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孔子关注人的发展,以“天命之性”或“性命”为核心,直指人心,以每个人的自身修养为本,强调天人和谐和人伦和谐。这是孔子所看到的关于人的发展的永恒的主题,正如孟子所言:“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这一主题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可以认同的。与孔子形成鲜明的对照:马克思在微观的个体生命历程之外另辟蹊径,从一种宏观的人类历史视角,描述了人类发展的历程: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个阶段;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6](P107~108)马克思的视野似乎更为宽广,在“个人全面发展”这个主体性和个体性的方面之外,马克思还强调了人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的发展,这个客体性的和整体性的方面。人们的“社会财富”和“个人全面发展”一同构成人的“自由个性”形成的基础。
五、马克思与孔子融合:超越资本
关于资本的本质,以及人类历史的发展如何超越资本的“辩证法”,是儒家所不可能设想和涉及的现代社会特有的话题。
“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6](P112)马克思将资本理解为人类所经历的一个现代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虽然这种关系是异化的”,“但是,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由此可见,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只有当资本成了这种生产力本身发展的限制时,资本才不再是这样的关系”。[6](P286)很显然,资本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之内是不能退出中国和世界的历史舞台的,因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正需要利用资本这种生产性的关系来发展社会生产力,并为人的个性的丰富和自由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然而,资本的“副作用”也是非常突出的,马克思称之为“异化”或“人的物化”。其典型症状可以简要列举如下: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拜物教、价值与伦理秩序的颠覆、社会分裂和社会排斥、史无前例的战争与仇恨、文明与野蛮混淆的相对主义的“泥潭”、资源环境和生态危机……这一切都是资本的逻辑的必然产物。马克思洞悉了资本的本质和资本的逻辑,指明了超越资本的方向,甚至隐约勾勒了一条通过资本的发展而超越资本的路径:起初是物质性资本的发展,后来是人本身作为资本,即现代经济学称之为“人力资本”的发展,然后,必然会突破平衡点,人力资本在经济的重要性上终于超过物质资本而居于主导地位。于是资本就会开始它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尽管如此,马克思并没有提供医治资本发展的“解毒剂”,也就是说,马克思未能充分关注“与资本共舞”的文化传统对于社会共同体的建设,伦理价值的维护和个体道德人格养成的重要作用。于是,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事实上向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向作为主流的儒学传统发出了一种召唤,要求马克思与孔子“联手”,共同来超越资本。或许可以借用马克思的术语: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基础”出发,超越资本的经济和政治逻辑;儒学将从“上层建筑”出发,来超越资本主义的道德、文化和精神。
人类的文明如何不断向“止于至善”的方向更新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具体说来,这个问题在当下表现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生活中,人的“物化”和“异化”是如何发生和演化的,人的“物化”和“异化”将如何克服?也就是说,在现实的世界中,德性文明遭受到了怎样的挑战,以及现代社会将如何复兴德性文明?面对这个问题,儒学从道德的传统延续的角度,马克思主义从科学的现实批判的角度,可以携起手来,构成道德与科学,传统与现代的互补,从而做出完整而有创造性的回应。
六、儒学社会主义精神
儒学“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贲·彖》)马克思主义寻求在与资本共舞的过程中超越资本,从而为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开辟道路。将马克思与孔子的思想结合起来,运用于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发展,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之中,所产生的运动可以称之为儒学社会主义。儒学社会主义首先是作为观念、价值、伦理和文化而凸显出来的,其次,才是在此基础上尝试建立的各种可以不断修改和完善的制度和器用之物。
儒学社会主义的内核是“意识形态性”的,或者说是一种作为文化和价值观的“精神”特质,它的根本属性是“反资本主义精神”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突出地体现为融化在资本主义道德教条中的价值悖论:“你的存在越微不足道,你表现的生命越少,你的财产就越多,你的外化的生命就越大,你的异化本质也积累得越多。……把从你那里夺去的那一部分生命和人性,全部用货币和财富补偿给你,你自己办不到的一切,你的货币都能办到……它是真正的能力。……因此,一切激情和一切活动都必然湮没在发财欲之中。”这正如马克思之后的另一位德国哲人所说:现代道德价值序列最为深刻的颠倒是生命价值隶属于有用价值。[7](P141)资本主义依托个人主义和拜物教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关于人的社会性本质和共同体本位人文价值体系根本冲突。
儒学社会主义精神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或共同体本位的个人观,也可以称之为一种社会人的“自我意识”;二是儒学传统的仁义价值准则和价值体系。前者保证了儒学社会主义现实的而非抽象的人性,后者从价值准则上将儒学社会主义的文明,与现代资本主义的野蛮区分开来。
儒家的“华夷之辨”曾经用于区别文明与野蛮,其核心价值准则就是“仁义”。仁是君子出于人性对人和天地万物的关怀,亲亲仁民而爱物。义是伦理上的合宜与道德上的公正。“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礼记·礼运》)中国大众社会生活中的儒家传统文明,在家庭和社区中仍有深厚的根柢留存,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野蛮的个人主义自我意识和拜物教价值观的持续而日益加剧的冲击下,已是岌岌可危。“金钱确定人的价值:这个人值一万英镑(he is worth ten thousand pounds),就是说,他拥有这一笔钱。谁有钱,谁就‘值得尊敬’,就属‘上等人’,就‘有势力’,而且在他那个圈子里在各方面都是领头的。”[8](P566)恩格斯所描述的主导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拜物教价值观,今天已然盘踞在了许多中国人的心中。儒学与马克思主义需要携手恢复共同体本位的仁义之人的自我理解,恢复“以义为利”的价值准则和伦理。儒家经典《大学》在两千多年前的义利之辨,在今天依然渊默而雷声:“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当今新的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异化”问题,并没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消解,而是愈演愈烈,资本主义不断上演的危机—修复—危机的循环,已逐渐将资本主义推向前所未有的,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与人伦危机的极端,仿佛是吞噬道德文明的一个巨大的“漩涡”,而处在“漩涡”中心处的正是中华民族。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华民族依托民族文化优秀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所做出的反应,将不只是一种关乎中国人命运的反应,它也将是为全人类做出的一种具有全球普遍意义和深远历史影响的文化创造。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黑格尔书信百封[M].苗力田,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斯·舍勒.价值的颠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On Confucian-Socialism:Dialogue between Kongzi and Marx
YANG Liu-xin
(School of Marxism,Peking University,Beijing,100871,China)
The practice of today's Chinese socialism needs not only to“play with capital”,but also to“surpass”it.In this context,to integrate Confucianism and Marxism in theory is a topic that cannot be avoided.The reason why a way of Confucian -socialism is possible is that Kongzi's humanism and Marx's humanism fit highly with each other.Thi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ir common insights of human social nature or human's essence of community,creativity of human subject,as well as a process philosophy about development of free personality.The humanist dialogue between Kongzi and Marx leads to a Confucian-socialism spirit,the core of which is composed by a kind of social individual“self-consciousness”and traditional moral values of Confucianism.
Confucian-socialism;Kongzi;Marx;humanism
〔责任编辑:左安嵩〕
D614
A
1006-723X(2016)07-0006-06
杨柳新(1967—),男,湖北天门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传统道德哲学与道德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