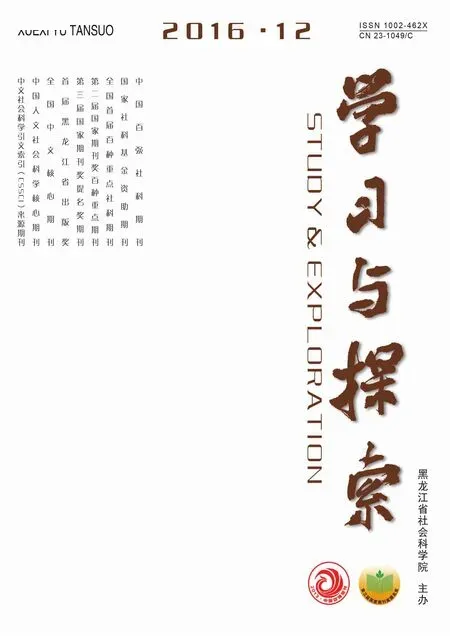林肯与美国法治观念的变迁
——以林肯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讲为例
蔡 乐 钊
(西南大学 a.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b.法学院,重庆 400715)
·政治发展研究·
林肯与美国法治观念的变迁
——以林肯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讲为例
蔡 乐 钊a,b
(西南大学 a.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b.法学院,重庆 400715)
林肯的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讲是他对内战问题的一次深入思考和总结,堪称美国政治宗教的奠基性文献。随着内战的发展,林肯愈来愈意识到植根于异教传统的古典自然正义理论的困境及实证主义“法治”的不足,因而逐渐转向一种富有基督教色彩的高级法之治,并提出一种补救正义秩序的爱的秩序。
亚伯拉罕·林肯;美国法治观念;美国内战;高级法;正义秩序;爱的秩序;就职演讲
在美国历任总统中,林肯占据着一个特殊的、无可替代的地位。这种地位不仅是因为他在内战生死攸关的时刻坚定地捍卫了联邦制,颁布了影响深远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还因为他以总统的身份,通过一系列的演说和行动对美国宪法进行了深入诠释,在塑造美国法治观念的进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宪法学界领军人物之一保尔森(Michael Stokes Paulsen)就认为,林肯的几篇演讲对理解美国宪法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最高法院那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两者同样“具有最重大的历史后果和经久不衰的意义”。在这些演讲中,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讲可以说是林肯对美国法治精神的最后总结陈词,并永久地奠定了美国政治宗教的高级法基础。
一、“国家牧师”林肯的“布道”
提起林肯最伟大的演讲,大多数人可能会想起大名鼎鼎的“葛底斯堡演讲”,罗纳德·怀特(Ronald C. White)却认为,林肯最伟大的演讲是他的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讲。“葛底斯堡演讲”发表于1863年11月19日,是那场决定性战役的四个半月之后;第二次就职演讲发表于1865年3月4日,那时战争的帷幕正在缓缓落下。两篇演讲都篇幅不大,却同样影响深远。
美国Simon & Schuster出版的“林肯文丛”中,有两本书分别对这两篇短小精悍的演讲进行了精心研究,它们分别是加里·威尔斯(Garry Wills)的《林肯在葛底斯堡——重塑美国的那些话》和罗纳德·怀特的《林肯最伟大的演讲——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葛底斯堡演讲”中的“民有、民治、民享”国人已经耳熟能详,其重要性亦无须赘言;与“葛底斯堡演讲”一起构成林肯演讲词双璧的第二次就职演讲带给我们的启示,却仍有待于我们深入发掘。在发表演讲的6天前,林肯曾对他的一位朋友说,这份文件中有“许多智慧”在里面,现在就锁在他的抽屉里。如今,这份文件已经公之于世,每个人都可以随时花几分钟阅读它,学习其中蕴含的林肯式智慧。
怀特用一本200多页的书来分析这篇只有区区703个单词的演讲,自然有足够的空间来做庖丁解牛式的细致剖析。全书由九章和一个尾声构成,掐头去尾,中间八章是对演讲的逐段解释,有时甚至是逐字逐句的推敲,因此我们有机会看到许多为一般论者所忽略的细节。比如,他统计出演讲所用的703个单词中,有505个单词是单音节词,并且推测林肯在演讲中所用的语速应该是比较缓慢的,整个演讲过程可能用了6~7分钟;比较了演讲的初稿和定稿之间措辞的微妙变化,以及林肯在演讲中对他所偏爱的头韵的使用,等等。然而,与这些细枝末节相比,更重要的是,正如詹姆斯·麦克弗森指出的,他的这项研究把第二次就职演讲研究置于“一个广阔的历史和神学背景”之中,其中,神学背景尤其引人注目。
在该书的卷首题词中,怀特引用了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在演讲当日对这次演讲的一句精到的评论:“这次演讲听起来更像是一篇布道而不是一篇国家公文。”确实,尽管美国政治从殖民地时期开始就与宗教问题牵扯甚深,但只有到了林肯这里,美国的“政治宗教”才可谓瓜熟蒂落,而他的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讲则是这个宗教的奠基文献。不少人认为美国真正的国父实乃林肯,而非建国一代的元勋们,这种说法不无道理。美国内战实际上可视为对美国高级法传统的一次史无前例的挑战,而林肯对高级法的捍卫则显得至为关键,这也是新世界在战火中对旧世界的正义秩序的一次重新阐释。
二、“人”的创造
林肯的政治宗教是从创造人开始的。在此之前,尽管有联邦党人可敬的努力,但美国人民的身份依然未能完全摆脱那种混沌状态,多少显得有点模糊不清,他们更像是“州民”而非“国民”。正如詹姆斯·布赖斯日后所观察到的那样,这里存在着“双重的政府,双重的效忠,双重的爱国主义”。地方政府由于更亲近它的居民,因而是他们更加自然的崇奉对象。这种对地方的感情如此强烈,以致约翰·亚当斯说它“弄瞎了我们的双眼,遮蔽了我们的理解力”(亚当斯1775年10月29日致其妻书)。当南方各州宣布脱离联邦时,南方人并不觉得那是一场叛乱,而是在重申其古老的自然权利——我们也可以确切地称其为古典自然权利。各州拥有与生俱来的自决的绝对权力,这是自然正义的要求,其他团体无权干涉。州权的鼓吹者亚历山大·斯蒂芬斯如是说。
但是古典自然权利有一个无法解决的两难问题,自古典时代以来这个问题就令西塞罗这样优秀的异教哲学家异常为难:两个人遭遇船难同时掉到水里,某人抓住水里一块木板以求自保,而另一个人为了自救也向这块木板游来,而木板仅能承受一个人的重量,这时候该怎么办呢?某人为了自保而把另一个同样为了自保的人推进水里是否符合正义?自保,无疑是第一项自然权利,优于其他各种自然权利。但如果双方都是为了自保呢,这岂不是两个平等的自然权利?这便是古典自然权利理论的终极困境。新学园派奠基人卡涅阿徳斯(Carneades)于公元前2世纪出使罗马时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抛出的这个问题,令现场的听众不知所措。以维护风纪著称的监察官老加图敦促元老院尽快遣返这批使节,以免他们的理论腐化青年的心灵。异教哲学家从未能对此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在美国,打破“自然平等”这层坚冰的一个著名尝试是《独立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这一点很可能连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杰斐逊本人都未曾意识到,而林肯却敏锐地捕捉到其中隐含的讯息。可以肯定的是,林肯在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讲结尾提到的“记忆的神秘琴弦”中,《独立宣言》及其所代表的76年的爱国者精神,连同美国宪法,一起占据着一个近乎宗教的神圣地位。在林肯看来,美国作为一个国家(nation),是从宣布“自创造时起人人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开始的,这里的“人”也包括黑人、外国人和天主教徒,他说,如果这些人被排除在外,那么他宁愿移居到俄罗斯忍受纯粹的专制统治,也不愿忍受这种虚伪的自由。
但是并非人人都像林肯这样来理解《独立宣言》的平等条款。塔尼(Roger Taney)大法官在德雷德·斯科特案的判决意见书中宣称黑人并不在《宣言》作者的考虑之内。卡尔霍恩把“人人生而自由和平等”视为“巨大和危险的错误”。他说,人人平等只存在于自然状态中,而自然状态不过是理论家的假设,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相反,人一出生就处于政治社会之中,因此生来就要屈从于国家的权威、法律和制度。显而易见,卡尔霍恩依然把《宣言》里的平等理解为自然平等,他在攻击人人平等这一思想时,始终使用的是born(出生)而不是《宣言》中使用的created(创造)一词,因此,他自始至终地把平等理解为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自然平等。
但是《独立宣言》并未停留在自然层面,它一开始就同时诉诸“自然法和自然的上帝”,这里,最终规定这种平等的并不是自然法,而是自然的上帝,即造物主。因此,我们发现这份一开始似乎充满自然权利气息的“宣言”,最终落脚点却是最末一段的“世界的最高审判者”和“神意”。把平等与创世联系起来并非没有先例。一个引人瞩目的例子即比《独立宣言》早几个月发表的一部当时在北美非常流行的小册子,即托马斯·潘恩的《常识》。潘恩在书中更加明确地写道:“人类最初在创世的秩序中是平等的(Mandkind being originally equals in the order of creation)。”生而平等属于自然的平等,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和今人耳熟能详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都是“拟制”的平等,如果说法律面前的平等是“人为”的,那么上帝面前的平等就是“神为”的。换言之,支撑着平等条款的,是一种终极意义上的高级法,是神法而非古典意义上的自然法。
林肯看到了这点,因而他比卡尔霍恩、塔尼和一切州权的拥护者站得更高。州权的拥护者把《宣言》看成自然权利的证书,它过去曾是美洲人脱离英帝国统治的宣传工具,现在当然也可以用来为南部各州脱离联邦辩护:州权和个体权利一样,都是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林肯则认为《宣言》的平等条款并不是为了实现眼前如此实用的目的,而是着眼于更长远的未来,即自由社会的建立,它指引人们只要有可能就不断地朝着这个理想努力,哪怕暂时未能完全实现——一个永恒的目的取代自然的目的。林肯仍秉承温斯罗普和国父一代“山巅之城”的信念,深信美国人作为“近乎被拣选的民族”,肩负着建立一个模范的自由社会的天命,而他和他的同胞一样,都是上帝实现这一计划的一个“卑微的工具”。从他于1861年2月21日在新泽西州参议院发表的演讲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点。在那次演讲中,他先是动情地回忆起独立战争时期在新泽西州发生的英勇斗争,之后说道:
虽然那时我还只是个小男孩,却也想到,那些人为之奋斗的必定是某种非同寻常的东西,这种东西不仅仅是民族独立,这种东西为全世界人民和未来所有的岁月提供了一个伟大的允诺。我极其渴望这个联邦、这部宪法和这些人民的自由能够永远延续下去,并符合人们为之奋斗的那个原初理念。我确实会成为最幸福的人,如果我将成为全能者和他的近乎被拣选的民族手中的一个卑微的工具,以使那场伟大的斗争的目标永远延续下去[1]。
林肯不是一个喜欢谈论抽象概念的人,即便如此,在这里,他不得不诉诸一个“原初理念”,他只知道这个理念“非同寻常”并且高于民族独立,并且它才是当年独立战争的真正目标。显然,这时候林肯已经预感到内战风暴的临近。他也将进行一场战争,而这场战争的目标是延续国父一代为之献身的那个“原初理念”,它不仅仅关乎奴隶制的存亡,更为重要的是,关涉联邦、宪法和自由的存续,甚至关涉全人类的未来。而美利坚民族将在实现这个理想的进程中扮演类似于以色列人的“上帝选民”的角色。
三、从“法治”到“高级法之治”
从19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林肯思想的一个重要转变可以概括为从实证主义的“法治”发展为超验主义的“高级法之治”。诚如考文所言,美国宪政体制中正因为保留了高级法这一赋予它青春活力的源泉,才有可能开创一个“从查士丁尼时代以来法学上最富有成果的时代”[2]。因此,林肯这一观念上的转变尤其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作为一名从业律师,早年的林肯也难免倾向于守法主义。在斯普林菲尔德青年学会的演说中(1838),林肯认为美国这座孤独地屹立于美洲大陆之上的“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政治大厦”,不会遭受来自外部的危险。如果有一天它注定要毁灭的话,那必定是毁于自杀。他不安地看到一种漠视法律的情绪在日益滋长,这种无法无天的精神最终可能导致暴民的统治。因此,他呼吁每个美国人“凭着革命的鲜血起誓”绝不违反法律,并且也不允许别人去违反。对宪法和法律的尊崇应该成为这个国家的“政治宗教”,无论男女老幼,不分肤色贵贱,所有的人都要在这个祭坛上献祭。令人惊奇的是,这时候的林肯强调美洲革命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不再是人们汲取力量的源泉。这段历史曾经是“自由圣殿的柱石”,但是将失去支撑的作用,因为构成这种柱石的材料是激情,而时间一长,激情就会冷却,因此必须用理性的柱石代替激情的柱石,才能维持这座圣殿不倒,而法律就是这种理性的化身。像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一样,林肯对激情异常警惕,而对理性无限推崇。激情曾经帮助美洲人摆脱了英国的统治,但是在未来,这种激情却可能导向暴民统治。因此,如古代哲学家教导的那样,激情必须接受理性的引导,而理性的统治就意味着法律的统治。“理智,无往不胜的理智将作为世界的主宰而生存和行动。功德圆满!万岁,愤怒垮台!理性称王,万万岁!”(《斯普林菲尔德戒酒协会演说》,1842)
但是法律——无论是实证主义的法律,还是源自自然理性的法律——很快证明并不配得到那么高的赞扬。自威尔莫特附件以来,人们一直盼望着能够从法律上一劳永逸地解决准州是否允许蓄奴的问题。由塔尼大法官主导的德雷德·斯科特案判决是从法律上进行裁决的最臭名昭著也是最后一次流产的尝试。在洛克那里,自由奠定在财产之上。然而,在这份判决意见书中,财产却成为反对自由的理由。“一个邪恶、欺诈的裁决”“一种残暴的主张”“共和国司法史上最大罪恶”,便是共和党人对这次裁决的评论。房子上的裂痕更大了,即使是“伟大的调和者”亨利·克莱这样巧妙的工匠再世,也无法再次修补裂痕。在人们对法律手段彻底幻灭之后,诉诸超法律手段已然是唯一出路[3]。因此,在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讲(1861)中,林肯不得不放弃早年那种严格的守法主义,诉诸那些他曾认为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渐失去感召力的历史。为了证明联邦比宪法古老得多,他回顾了联邦的发展史,把联邦(Union)的形成追溯到1774年的《联合条例》,1776年的《独立宣言》和1778年的《邦联条例》是其发展成熟的阶段,1787年制定的宪法则是为了“建设一个更为完美的联邦”。联邦的目的在于要用宪法的手段来保护和维持自身的存在。林肯甚至已不再满足于停留在美国宪法与法律的层面,而提出了国家与宪法的自保是“普世的法”和“一切国家政府的基本法”的观点。 林肯非常清楚,把宪法的自保确立为宪法的最高原则对他来说意味着总统权力的扩张,为了履行“维持、保护和捍卫”宪法这一誓言,他可以在非常时刻行使某些超越宪法的权力。在这方面,《独立宣言》的执笔者仍然堪称林肯的精神导师。杰斐逊在1810年9月20日给科尔文(John B. Colvin)的信中写道:
你提出的问题,即是否环境有时会使身居要职者有义务僭取超越法律的权威,在原则上很容易解决,但在实践上有时则令人犯难。严格遵守成文法无疑是好公民的崇高义务之一,但不是最高的义务。必然的法则、自保的法则、在危难时刻拯救我们的国家的法则,是更高的职责。由于谨小慎微地死守成文法而失去了我们的国家,也就失去了法律本身,也失去了生命、自由、财产和所有与我们一同享有它的人,因而也荒谬地为了手段而牺牲了目的[4]。
林肯在为自己内战期间的违宪行为辩护时也遵循同样的自然权利逻辑,这和他早年的观点截然对立。波尔克总统未经国会授权而发动墨西哥战争时,当时还是伊利诺伊州参议员的林肯就指责波尔克创下一个很坏的先例,使总统像国王一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动战争。然而单是内战中越过国会中止人身保护令这一举动,就使林肯这位自诩的宪法守护者拥有了比英国国王还大的权力。但是,宪法的最高原则是宪法和宪法所赖以存在的国家的自保,为此,在非常必要的情况下,总统作为宪法的首要保护者可以越过特定的宪法条文。林肯辩称,不可为了维护一条法律(人身保护令)而让其他所有法律都陷于瘫痪。总之,有一个可以推断为经宪法认可的超越于宪法之上的最高原则,宪法条文的解释必须服从这一原则。通过诉诸自保这一自然权利,林肯抛弃了早年的守法主义,大胆地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法律并不是理性的当然化身,如果这种法律违反了自然理性。这是林肯通往高级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高级法还主要体现为自然法,而不是“自然的上帝”颁布的神法。然而,随着战争的发展,自然法和自然理性被证明同样无法令人满意,于是神法出场了。
一句古老的拉丁谚语说,“法律在战争期间变得沉默”(Inter arma silent leges)。这在林肯看来只是部分正确。在战争中,双方实际上都把自己托付给了神意这一更高级的法律。在第一次总统就职演讲中,林肯起初表示自己不想干涉各州的自主权,他尊重“每个州完全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安排和掌控自己内部体制的权力”。这看起来似乎是对个体主义和自然权利的一种让步,但是我们发现,在演讲的末尾,决定权最终不在州那里,而在“美国人民”这个“伟大的法庭”手里,他呼吁人们要对人民的最终正义抱有耐心和信心,并且把人民的裁决等同于上帝的“永恒真理和正义”。
研究者指出,林肯晚年在公开的讲话中愈来愈频繁地引用《圣经》,其次数之多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统。事实上,在内战中,圣经是参战双方士兵必不可少的读物,其出版量十分惊人。怀特在书中意味深长地写道,“随着敌对状态的开始,生产圣经几乎就像生产子弹一样快”[5]102。美国内战史权威麦克弗森亦尝言,内战期间的军队或许是美国历史上最具有宗教精神的军队,因为他们都是第二次大觉醒运动的产物。在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讲中,林肯说“双方都阅读同一本圣经,向同一个上帝祈祷,每一方都吁求上帝帮助自己来反对另一方”。可是,“全能者自有其意图”,不管战争的结果如何,他相信上帝的裁判绝对是公正的。克劳塞维茨把战争视为一场大规模的决斗,但是他只看到两者的共通处在于以暴力迫使敌人服从自己的意志。事实上两者有更深的关联,它们都是一种司法形式,而不仅仅是暴力冲突。在历史上,现代司法程序兴起之前,决斗曾长期作为神裁的一种方式。司法决斗是最原始、最野蛮的司法形式,从这个角度说它也是最低级的司法形式;但它同时又是最高级的司法形式,因为它本质上是一种神意的裁判,属于高级法范畴。在战争状态中,也就是敌对的自然状态中,只有上帝才能充当仲裁者,这也是洛克在《政府论》中的一个重要教诲。
在那个大多数人还笃信宗教的年代,誓言依然是很有威力的。美国宪法规定,总统就职时必须宣誓“维持、保护和捍卫合众国的宪法”。林肯一再提醒人们注意他这一不可推卸的宪法责任。尽管主持宣誓仪式的是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但是誓言的监督者并不是这个尘世的法官,而是上帝。在第一次就职演讲中,林肯告诉听众,这个誓言是记录在天上的,是一个最庄重的誓言。
林肯最终将会发现,真正值得人们为之奉献的“政治宗教”不是实证主义意义上的“法治”,而是一种高级法之治,体现为国父一代的那个“原初理念”,“葛底斯堡演讲”(1863)正式确立了这一宗教精神。在第一次就职演讲中频繁出现的“联邦”(union)这个字眼在这次演讲中没有再出现,林肯反复使用的词是“国家”(nation):一个“新国家”在87年前诞生了,这个国家孕育于自由,献身于“自创造时起人人平等”这一信条。《独立宣言》的发表不再是作为联邦发展史的一个环节,而是作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诞生的标志。与“国家”出现频率同样高的另一个词是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奉献”(dedicate)。内战的牺牲,是为这个新国家和它的政治宗教做出的奉献。
意大利法学家贞提利的《论战争法权》中有一个段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奉献”的意义,在那里,贞提利解释了为何以虔敬与怜悯闻名的罗马先祖埃涅阿斯竟然残忍地杀死了向他求饶的敌人图尔努斯。贞提利辩护说,这是雅典娜根据希腊宗教用图尔努斯来祭神。换言之,这是一场献祭,是雅典娜借埃涅阿斯之手做成的,在希腊宗教中是允许的,他的杀人之举恰恰是他虔敬的体现。林肯的“奉献”修辞起着同样的作用,舍此他无法为内战中的同胞相戮找到更好的辩护。区别在于,美国人民不是献身于希腊或罗马的宗教,而是通过《独立宣言》的发表而确立的那个“政治宗教”。
林肯可能没有想到的是,和那些战死沙场的同胞一样,他最终将也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完成这一奉献,成为 “第一位伟大的殉教者领袖”。虽然他被暗杀了,但他的国家和宗教则不朽。没有人比惠特曼更理解林肯之死的意义,诗人惠特曼在《亚伯拉罕·林肯之死》中指出,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伟大的死,无论是恺撒、拿破仑还是苏格拉底之死。林肯之死使他和全体人民牢牢地黏合起来,比“成文宪法、法庭或军队”所起的黏合作用更加持久和强大。“战斗、殉难、鲜血,甚至暗杀”合在一起,把这个国家永久地巩固下来。
自内战爆发以来,林肯愈来愈频繁地思考上帝的意志问题。但是,尽管他急切地想探求神意,但是他知道这已经不是奇迹的时代。他不太可能得到直接的启示。《对上帝意志的沉思》(1862/1864?)就是他在这方面思考的集中体现:
上帝的意志胜过一切。在大规模的斗争中,每一方都自称遵照上帝的意志行事。双方都可能是错的,有一方必然是错的。上帝不能在同一个时候对同一件事既表示赞成又表示反对。在目前这场内战中,上帝的意图很可能和任何一方的意图都有所不同;但是,人类的手段实行起来,最适合于实现他的意图……上帝愿意有这场斗争,而且眼前还不愿它结束……既然已经开始,他可以在任何一天给任何一方以最后的胜利。但斗争还是继续进行下去[6]。
尽管神意是那样地晦暗不明,但是林肯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焦虑或慌乱,他把自己置于一种超然的地位,仿佛自己不是参战的一方,而是一位旁观者,像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不带感情地、镇静地打量着目前这场战争。这场战争犹如一场上帝监察下的司法决斗。在裂痕已无法弥合的情况下,正如古罗马人所说,“用言辞争战是愚蠢”。林肯也坦承“别无选择,唯有呼唤战争权”(依《元照英美法词典》的说法,“战争权”这个词有可能是林肯首创),战胜者即得到上帝垂顾的一方。这是那些怀着虔诚信仰的古人的逻辑,无论是异教徒还是基督徒。当一切人类的智巧都用尽时,我们只能返回这类最朴素的思想才能摆脱困境,这也是亚历山大大帝毅然选择斩断“戈尔迪之结”的缘由。
战争是验证上帝正义的手段,而谁是执行上帝正义的工具?是人民。在第一次就职演讲中,林肯宣称由美国人民组成的“伟大的法庭”将作为上帝的代言人做出最后的正义裁决,这也是在美国宪法序言中提到的“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宪法中的“我们人民”和《独立宣言》中的“人人平等”构成了林肯心目中的民主政府的两大理论支柱,分别代表了人民的权威与人的权利。恰恰是这两个表述,林肯留意到,在邦联的宪法和宣言中被删去了。内战,在林肯看来,“本质上是一场人民的斗争”,通过这场战争,他们将寻回失去的自由,寻回属于国家的人民,并且把这个政府重新交到他们手里。在林肯的思绪中,经过内战的“火的考验”——一种典型的中世纪神裁方式,也是麦克弗森一本关于美国内战的著作的书名——得到新生的人民将再次出场:“我们要使这个国家在上帝福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葛底斯堡演讲》)
四、正义秩序与爱的秩序
回到前述“卡涅阿徳斯的木板”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无法在充满诸神争吵的异教世界中得到解决。直到基督教出现后,人们才找到一个摆脱这一两难困境的办法。16世纪经院哲学家苏亚雷兹(Francisco Suárez)给出的答案异常简单,但也异常深刻。他说,在这种情形下,正义的秩序(ordo justitiae )终止了,爱的秩序(ordo caritatis)接管了这个案件[7]。林肯最后回归的正是这一发端于中世纪的基督教政治传统。无怪乎有人说林肯的神学和教皇庇护九世的政治一样,可以嗅到中世纪黑暗时代的浓厚气息。
林肯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讲临近结尾的地方那句表达对同胞基督之爱的话:“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对一切人都怀着爱(With malice toward none; with charity for all)”。在异教时代,正义意味着复仇(nemesis),而复仇又意味着新的复仇,秩序由此卷入到一种无休止的自然循环中。对于基督教而言,正义却意味着纠正和拯救,而基督教关于末世的构想则让人看到终极正义实现的前景。正义与基督之爱(charity)之间的关系是中世纪教会法著作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经典命题[8]。因此,我们看到,阿奎那和苏亚雷兹等经院哲学家以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古怪方式,把对正义战争的论述放到基督教“爱”的总纲之下,以此完成对正义战争理论的一次革命——正义不再是自然的正义,而是神的正义。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美国内战始于异教的自然正义的诉求,终于基督教上帝的裁决。无疑,林肯比任何人更清楚这点。在胜利即将到来之际,林肯再次使用他非常喜欢的charity一词(怀特提到他对这个词的使用有半数时候会说“christian charity”,基督的爱),试图抚平这场空前的内战必然留下的巨大创伤。怀特写道:
这些字句立刻成为第二次就职演讲中最令人难忘的表述。很快,在林肯被暗杀前所剩的短短数周内,“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对一切人都怀着爱”成为写在报纸上、刻在徽章上的标语。而在他被暗杀后,它们成为林肯留给这个民族的遗产的象征。它们将成为我们的某些神圣的言辞。他的其他言词,出自葛底斯堡演讲的“民有,民治,民享”,之所以经久长存,是因为它们一劳永逸地界定了美国。“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对一切人都怀着仁爱”界定了林肯对内战后美国的远见(vision) [5]164。
正是凭这种洞悉“异象”、预见未来的能力,林肯成为美国政治宗教的先知。我们说他为了拯救联邦践踏了联邦的法律,毋宁说他超越或扬弃了人为法:从实证法过渡到自然法,又从自然法跃进到神法。最终,我们发现林肯像一个典型的中世纪的人那样,把这场战争理解为上帝的一次司法,一次彰显神的正义的裁判。“双方都可能是错的,有一方必然是错的。上帝不能在同一个时候对同一件事既表示赞成又表示反对。在目前这场内战中,上帝的意图很可能和任何一方的意图都有所不同。”这种对人类经验的局限性的深刻体验,使林肯变得更为宽容大度。在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讲中,我们看不到半点胜利者的骄傲或喜悦,唯有怜悯和谦卑。奠定在古典自然法也可以说是古典战争法之上的正义秩序终结了,一种面向和平的救赎的秩序——爱的秩序——得以恢复。这也是17世纪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清教垦殖者们意欲建立的“山巅之城”的理想:一个理论上的以中世纪城镇为模型、依靠基督之爱统一起来的城市[9]。
[1] LINCOLN A. Speeches and Writings, 1859-1865[M].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89:209.
[2] 考文. 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M].北京: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96:93.
[3] 麦克弗森 詹.火的考验:美国南北战争及重建南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137-138.
[4] JEFFERSON T. Political Writings[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375.
[5] WHITE J. Lincoln’s Greatest Speech: The Second Inaugural[M].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2.
[6] BURT J. Lincoln’s Tragic Pragmatism[M].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2013:673.
[7] ROMMEN H. Natural Law[M].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98:18.
[8] 彭小瑜. 教会法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64.
[9] CARROLL P. Puritanism and the Wilderness[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3.
[责任编辑:巩村磊]
2016-05-21
蔡乐钊(1984—),男,博士后研究人员,从事法哲学与政治哲学研究。
D097
A
1002-462X(2016)12-007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