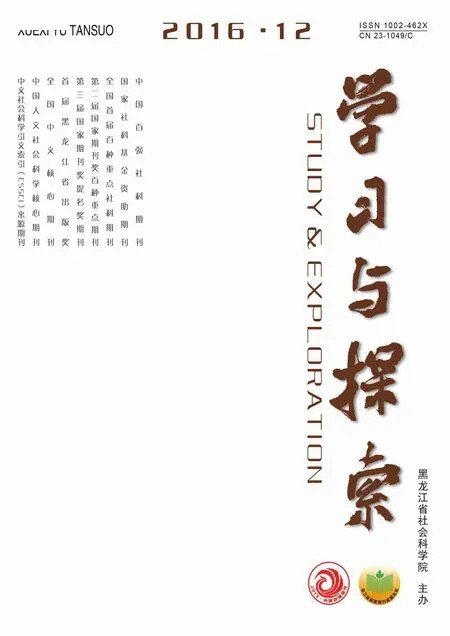《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贫困问题探讨
张 文 喜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当代哲学问题探索·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贫困问题探讨
张 文 喜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贫困问题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展开分析的主要背景。对马克思来说,贫困一词所具有的只是社会意义。如果按照马克思的思路去解决贫困问题,除了改造社会以外,根本就没有其他解决问题的出路。国民经济学的基本性质不是对抗贫困,而是对抗穷人。即便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慈善”却不是行善,所谓的经济发展既没有改变贫富对立,反而更毒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共产主义是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消灭贫困的基本逻辑。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贫困问题的深刻揭示能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定启示。
贫困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
一、一个批判性回顾
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贫困化和日益富有的资产阶级在日益缩小,这是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一个关键论断。但对事态的进程,可以说是预言,而不是事实判断。因为我们今天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头再看一遍,将感到马克思要通过自己的理论写作揭露两大阶级矛盾的尖锐程度而使问题明朗化。马克思告诉我们,为了使问题得到最尖锐的表现,他必须将世界历史归结为两大阶级对立。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好地深入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内在机制。他的理论创作是以对无产阶级有利为标准。
人们通常会说,他预设了立场,这下马克思自己授人以柄了。攻击马克思的人就有了借口,好像马克思在学理上的研究水准不够。因为不幸的是,随着历史的变迁,很久以来围绕它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如人们所知,马克思的论断强调日益贫困化究竟是客观存在,还是他追随一种倾向性立场。大家今天都熟悉这些争论,所以大家也知道这种争论毫无结果。因为它没有摆脱那种无聊的所谓经验问题:贫困只是相对的。言外之意,贫困在各个国家和各个时期既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我们的真正问题是:日益增长的贫困化的事实必须是对工人阶级来说可感的客观事实,还是马克思实际上说的是相对贫困化,而相对贫困化肯定更有说服力吗?
碰巧的是,这里真的到了该说出我们关于这场争论的批判性看法的时候了。无论从何种角度,我们对这些争论不持赞成态度,它们无疑都是因为解释马克思文本的困难而胡编出来的。可是,我们的确看到了我们没有足够的理论修养和悟性,或者说,我们曾经向往当一个战士,但如今是一个物质主义时代。客观直白一点说,今天的很多人稍微有点钱,他们就吃着喝着,完全沉浸在物质享乐之中,为所欲为。或者我们还可以说,时代条件尚未成熟,听上去更无伤大雅。笔者想在这里首先表明的是,我们的真正问题——贫困问题——属于人与人的关系问题。问题要害就在这里。
二、穷人是如何陷入贫困的
贫困问题构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马克思的问题的背景。谁也不会否认共产主义问题是和贫困问题联系着的。在资产阶级时代,马克思研究贫困问题,“就像”国民经济学家制定各种不同的发财政策一样。至少可以说,马克思试图解释一个完全贪婪的私有制是怎么样和贫困问题不可避免地联系起来的。笔者认为,马克思充分揭示了工人阶级的贫困。他以此承担了无产者的理论家最紧迫的任务:认识到工人阶级是多么贫困和它怎么样贫困,以便能够走向自身反面,以及对制约现实社会关系的普遍原则进行揭示。也就是说,问题的要害所在,不是马克思有一个关于工人阶级日益贫困化的看法,而是这个关于工人阶级贫困化的看法把马克思塑造成一个完成一场哲学革命的人。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关于工人阶级贫困化的看法对于人类历史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如果不能把坚持这个想法的人理解成为改变世界的人,那么它就只能降格为某种类似于“体系创新”之类的小小举动。
因为,一方面,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日益贫困化的观点体现着他力举的实践意义。马克思新世界观的核心正是“实践”,因而对它的误解必定连带着对这个世界观及其整体的误解。因此,不难看出,这个关于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看法,关乎的是“事情”,而非“事实”。马克思说,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这件“事情发生了”,但是他不会说这个关于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事实发生了”,这个区别里面包含很多值得深入思考的原则理解。另一方面,在理论的展开上,更精确地说,马克思的贫困化问题研究的展开常常依赖于各种引证,因为它可以算是论战性的东西。贫困问题在当时那个时代还是新涌现出来的问题。因此,它跟当时占压倒优势的“发财致富”意见往往背道而驰;而我们如今往往认为贫困问题将退处于卑微地位,我们的心力将用来或重新用来,对付我们的真正问题——生活问题。因此,如果只是单纯看这种贫困理论研究的话,或许其意义会削弱许多。
但是,这里说“贫困”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贫困和财富是二元分裂的。马克思说:“分工提高劳动的生产力,增加社会的财富,促使社会精美完善,同时却使工人陷于贫困直到变为机器。劳动促进资本的积累,从而也促进社会福利的增长,同时却使工人越来越依附于资本家,引起工人间更剧烈的竞争,使工人卷入生产过剩的追猎活动。”[1]231也就是说,在这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也是社会的财富增加,但“增加社会的财富”怎样变成“使工人陷于贫困”了,“资本的积累”怎样变成“资本的统治”,也就是说,为何不是像资产阶级理论家奉为教条的那种两种势力相互作用,直到两者合而为一,而是规定的差别之两极分化?资产阶级理论家要想了解这一切是不难的。问题只是他必须知道,工人怎样为自己买得自由,国家机器怎样为资本家服务,社会财富怎样变成富人的财富;房地产商一方面怎样利用国家在国家所有的土地里攫取金钱,而另一方面又怎样帮助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而为自己买得种种特权;伦敦的地下室住所为什么能够“给房产主带来的收入比宫殿带来的更多,就是说,这种住所对房产主来说是更大的财富”[1]345,等等。所以,马克思这里讲的显然是“有事情发生了”。
而一开始那些不同的说法提示出相对贫困的说法,乃是对相对贫困的误解。威·舒尔茨在其著作《生产运动。从历史统计学方面论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新科学的基础的建立》中这样写道:“即使所谓社会一切阶级的平均收入都增长这种不真实的情况属实,收入的区别和相对的差距仍然可能扩大,从而贫富间的对立也可能更加尖锐。因为正是由于生产总量的增长,并且随着生产总量的增长,需要、欲望和要求也提高了,于是绝对的贫困减少了,而相对的贫困可能增加。靠鲸油和腐鱼为生的萨莫耶特人并不穷,因为在他们那种封闭的社会里一切人都有同样的需要。但是,在一个前进着的国家,生产总量在大约十年内与社会相比增加了三分之一,而工人挣得工资仍和十年前一样多,他们不但不能保持过去的福利水平,而且比过去穷三分之一。”[1]233舒尔茨这样定义贫困:封闭的社会里的穷人并不穷,而“前进着的国家”里的工人才算真正的穷人,但是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的趋势会消失。所以,什么时候我觉得穷等于真实的穷,什么时候不等于,这要看平均收入。看起来,这对于澄清有关贫穷与否的理论(感觉)大有帮助。但是,很显然,它变得只是把理解贫困的质的条件化约为量上的规定。这是现代科学的趋势。“例如,像我们感知到的质的区别,如光和声的区别,都要通过量的区别来确定。人们还可以针对更普遍的趋势来说,想要把人与人之间的必要性、社会事件都归因于统计学的、和数字相关的关系上等。”[2]在这里,贫困这个具有社会事件之质的规定性的范畴被国民经济学之量的范畴所排斥。因此,这个概念并没有被清楚地领会。经济研究所里面的人和具有知性思维方式的人才会这样思考问题。例如,对于萨莫耶特人,鲸油和腐鱼就是丰厚并能够知足的财富了,而英国的工人有一百万元还是贫穷的。所以,贫穷和富有是完全相对的东西。因此,舒尔茨或许会这样定义并责怪那些贫穷的人:这个人不知道如何来感受幸福。也许,他还会认为,这最清楚地表现了内在富有和外在的不足这种心理情感的两面性。可以说,这又是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基督教把穷人当作有正确信仰和敬畏上帝的人。但是国民经济学家把穷人当作有物质追求的、世俗的、乐天的人。
这样我们就直接正面地领会了国民经济学的矛盾。因为在这里国民经济学不只是一门发财致富的科学,它本身变成了“关于惊人的勤劳的科学,同时也是关于禁欲的科学”:一方面,是“世俗的纵欲的外表”,另一方面却是“真正道德的科学,最最道德的科学”[1]342。它把尽可能的贫乏的生活当作统计学标准,是因为它适用于算出“社会一切阶级的平均收入”。
这种对相对贫困的领会,在马克思看来,都意味着对工人阶级的生活充满蔑视。相对贫困,听上去无关紧要。好像是说,工人并不是真穷,而只是不富,尤其是相对于世界各国在大街上乞讨的人而言。这样一来,归根结底“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1]233。作为一个证人,马克思深刻揭示其原因,即在于我们的时代,比起人,动物离我们更近。我们不得不通过对占有欲的依附来生活。我们俗称的经济问题,也就是欲望与贫困的问题。这是一种循环,即我们不得不通过新的占有物、通过新的依附关系保护我们的占有物不至于丧失。因此,贫困问题在这种特定条件下只能通过数字来理解。譬如,“绝对的贫困”这个说法,是指缺乏生存必需品,如衣服、食品、住宅。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每人每日少于1.5美元可支配花费,就属于绝对贫困。据世界卫生组织和经合组织的标准,每个月可以支配收入低于其所在国国民中等收入一半的人,属于相对贫困。
问题仍然是,贫困这个概念可以被清楚定义吗?相对贫穷一定等于相对于前进的国家吗?当然不是!如同相对贫穷不是相对非洲,而是与社会结构相联系。在结构方面,在性质方面,《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贫困问题并非仅仅由物质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还在于对人的本质的承认。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困可能比封建社会的贫困更悲惨,如今消费社会中的贫穷可能比生产社会的贫困更严重。
三、如何消灭贫困
致力于消灭贫困问题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前面谈及穷人是如何陷入贫困时就得出了这个结论。但是,有人说,这个世界已经告别了贫困。贫困一词应该换成“无用”“疾病”“犯罪”“不卫生”等词汇;也有如今的大学教授说,贫困不是底层社会的主要问题,而是大量消费快餐和微信。那么,我们纠结的问题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该如何回应这一论战。
1.贫困问题是社会问题
对马克思来说,贫困一词所具有的只是社会意义。因此,马克思认为,当国民经济学家说“你必须把你的一切变成可以出卖的,就是说,变成有用的”[1]343,谈到的也只是一种社会意识,即对象或者资本,是被使用的社会意识。资本主义私有制只知道一种方式,即我们与对象发生关系,就是拥有和买卖关系。这样一种社会意识是深入今天每个人的生活的。在一个所谓民主的国家里,实际上依然严重地存在着隐形的等级制。它属于人类创造上的贫困问题。哈特曼说:“在像德国这样富裕的国家里,穷人同样被轻视。当他们为了领取超市捐赠的食物排队时,他们至少穿上体面的衣服,这是他们保持尊严的方式,而即便如此也会遭到责怪”。哈特曼问:“在德国,难道穷人得先有饿瘪的肚皮,才相信他们的贫困?穷人为了得到我们的同情,非得衣衫褴褛?”[3]9
马克思同样会问:为什么社会上会有“无用的人”?这种“传说”为什么会顽固地延续?为什么“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却把这种考察交给刑事司法、医生、宗教、统计表、政治和乞丐管理人去做”[1]232?回答依然是,资本和使用意义上的有用性原则。资本主义的定数就是有用性。正因为如此,“小偷、骗子、乞丐,失业的、快饿死的、贫穷的和犯罪的劳动人,都是些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并不存在,而只在其他人眼中,在医生、法官、掘墓者、乞丐管理人等等的眼中才存在的人物。”[4]66
马克思的这一视角非常全面。因为,通过诋毁让穷人为自己服务,资产阶级社会早已深谙此道。穷人被贬值,穷人被犯罪,这些都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了。回顾起来,其开始正值资产阶级上升期。在中古时代,穷人还在“上帝”拯救计划中占据了一定的位置。穷人还是“上帝的孩子”。富人给穷人“募捐”具有行义的象征意义。行义是基督徒在世上生活的重要部分。在《新约》中贫穷受到了颂扬。至此,我们可以很快想到那一句话,“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针眼还难”,“这是基督教教义对此问题的主要看法”[5]。在基督和基督徒那里,贫穷被神秘化了,“有着完全不同于社会意义的意义”[6]。其要害在于,抽去贫穷的社会意义,也就掩盖了剥削。避免因此看上去人与人有任何差别。在资产阶级社会,对贫穷的看法已经改变,区分了“有教养的穷人”和“没有教养的穷人”。所谓“有教养的穷人”,就是那些眼睛瞎的、瘸腿的或孤儿或寡妇,即那些无辜陷入贫穷困境并需要帮助的人。“没有教养的穷人”,指小偷、骗子、在街上打架斗殴的流氓、妓女、无力还贷款的人,等等。总而言之,是那些得不到社会承认的人。
在今天,几乎没有人相信这种划分了。但是问题是,这种“有教养的穷人”与“没有教养的穷人”之间的根本差别,可以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加以解释吗?断乎不能!把穷人分为“有教养的穷人”与“没有教养的穷人”,实际上是把穷人设计为“有用的穷人”与“没有用的穷人”。前者创造经济利益,他们组成了一支廉价劳动大军,后者则是所谓社会福利的消耗者或者“罪犯”。我们知道,自从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理论以来,许多著作家不断为它辩护。
例如,巴枯宁说:“在我看来,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首先是广大群众——亿万没有教养的、被剥夺了权利的、悲惨的、目不识丁的百姓。恩格斯先生和马克思先生也许会把他们交给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实行家长式统治。在我看来,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恰恰是一切政府的这种无穷无尽的炮灰——广大乌合之众几乎没有受到资产阶级文明的玷污;在他们的体内,在他们的激情和本能中,正孕育着未来社会主义的一切种子。”[7]这段话表达了“有教养的无产阶级”与“没有教养的无产阶级”之间的根本差别。巴枯宁煞费苦心地认为,马克思把“有教养的无产阶级”看成未来社会的创造者。我们知道,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概念无论是在19世纪还是在今天看来,实际上可以看成一个征象,因为它与许多不同的价值内涵混淆在一起。他们是受凌辱、受伤害的人,但面对世界,他们绝不是无力的人。相反,他们是有历史创造力的人。所以,巴枯宁从马克思的看法中引申出他自己的无政府主义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么,回到我们的主题。如果按照马克思的思路去解决贫困问题,除了改造社会以外,根本就没有解决社会问题的出路。
而国民经济学面对工人的贫困问题,通常就是发明一些权宜之计。譬如,为穷人搞一个食品银行。专门把超市里剩余的食品运送到食品银行。目前在欧美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组织。但现在问题来了,食品银行应该怎样运转?有人穿着“公益”这件外衣,总还是想方设法要靠穷人发财。譬如,他们说,应该让那些在食品银行里领取食品的穷人做公益劳动,否则,会带来懒惰、浪费等问题。一言以蔽之,“公益”既要商业化,也要私有化。在这些方面的举措已经获得的成效足以验证亚当·斯密所谓的“社会是一个商业社会。它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商人”[4]171。马克思为此说,这样一来,“我们每个人实际上把自己变成了另一个人心目中的东西;你为了攫取我的物品实际上把自己变成了手段、工具、你自己的物品的生产者”[4]183。既然如此,他们就不会质疑一个让富人越来越富的社会制度安排,反而更愿意与富有的统治阶级勾结在一起。例如,在国家信贷中,国家地位同“单个人的地位完全一样”,“在公债券的买卖中暴露出国家怎样变成了商人的玩物”,“银行家所建立的银行在国家中的统治,财产在银行家——国家的国民经济学的阿雷奥帕格——手中的集中,可以称得上是货币的完成”[4]170。在城市中,穷人除了住在地下室,还被富人(房地产商)排挤到贫民窟里,政府则从经济可利用的角度对此起推波助澜的作用。至于固有的偏见是:“人民和政府的粗陋的国民经济学的盲目信仰紧紧抓住感觉得到的、摸得着、看得见的钱袋不放。”[4]166诸如此类的事实,不仅使得富人越来越富,而且使穷人越来越穷。可以说,对于国民经济学家来讲,解决两极分化,最多只能从抑制经济增长,调节一下福利,再加上不要贪得无厌追逐利润之类的忠告着手;而对于马克思来讲,这还只是一个模糊事实性质的概念。对将来来说,不改变私有制社会结构,就难以遏制这种两极分化的事情。因此我们愿意遵循马克思的思路提醒说:“把剩余食品分发给贫穷的食品银行用户,归根结底帮助的是生产过剩以及把盈利建立在生产过剩上的连锁商业的经济模式。”“在德国,连垃圾都是财产,偷盗垃圾可能受到法律惩罚。”如果穷人从垃圾箱里设法捡几个剩面包和过期酸奶之类的食品,就是犯法。眼前的矛盾就是,“从垃圾中贡献食品”恰恰是食品银行反复宣传的“可持续发展精神”的一部分[3]36-40。
从马克思的立场来看,人类是善于改变环境的。就整个关系来说,即使大家都是买卖关系,这种资本主义社会买卖关系中,穷人往往比富人付出更多。马克思认识到,被国民经济学大加赞赏的商业社会掠夺并欺压了一个阶级。但是,对于国民经济学来说,大家都有生意做,既不是非法的,也不是不道德的。但很少有人能够真正觉察到这一点,即它最终却是剥削性的。这不是做生意是否诚信、老少无欺、明码标价的问题,而是人的生存意义问题,属于创造、行为与自由的问题。因此,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富有的人和富有的人的需要代替了国民经济学上的富有和贫困。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总体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自己的实现作为内在的必然性、作为需要而存在。不仅人的富有,而且人的贫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同样具有人的因而是社会的意义。”[4]90因此,我们认为,在这个世界上,迄今为止还没有哪种主张是在这种意义上关心穷人的。
2.国民经济学与对抗贫穷的主要目标渐行渐远
在国民经济学看来,生产的真正目的是赢利,而不是一笔资本能够养活多少个工人。因此,资本家获得的经济地位和利益,实际上是极端特殊化,极端自私化的;但是国民经济学却把它看成是恒久的和理所当然的。马克思讥讽说:“如果把强制的情况除外——我怎么会非把我的私有财产转让给另一个人不可呢?国民经济学回答得很正确:由于贫困,由于需要。另一个人也是私有者,然而是另一种物的私有者,这种物是我需要的,我没有它就不行或者我不愿意没有它,在我看来,它是补足我的存在和实现我的本质所必需的。”“物的为我的存在、对它的占有,就是我的本质的属性和特点。这样,两个所有者都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私有财产,不过,是在确认私有权的同时放弃的,或者是在私有权关系的范围内放弃的。因此,每一个人转让给别人的是自己的私有财产的一部分。”[4]172-173
有两点理解在这里非常非常重要。首先,如果思考解决贫困问题的一条道路,如果一场社会运动必须有一个目标的话,那么,私有财产制度消除贫困这个目标必须设法消除私有财产制度自身。但是私有财产制度并不认为自己是应当消除的,相反它致力于自身的兴盛和发展。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把制造贫困当作自己的“事业”。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特点是扩大再生产,在这一过程中,资本积累得越多,生产越扩大,就越能更多地积累,这样,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就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在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生产者对自己的劳动产品拥有所有权,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所有权对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他人无酬劳动的权力。”[8]就这样,由于穷人没有所有权,也就没有财产;这样资本家则会用自己的经济地位来剥削那些在财力上不如他的人,而且是变本加厉,想按照原有的规模大大扩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每一项创造出来的“经济奇迹”都掩盖了贫困的真相。例如,食品银行的成功,首先让人们关注到的是它的经济奇迹、慷慨的捐助、新创造的就业岗位,诸如此类。每一次食品银行的贡献都使社会和政治对“慈善资本主义”有进一步肯定。所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许多捐助机构都为己所用,贫穷不再是它们关注的问题。
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通常就会用“失业者”“福利享受者”“政治冷漠者”之类的词汇替换“穷人”这一称谓。如果一个“穷人”,由于过生日而置办了一场酒席,他就会失去他从救济所领取穷人补助金的资格。而富人想的是,多消费些。可见,一方面,资本主义救济经济的真实面目乃是抽离公民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生产对富人所具有的意义,明显地显示在生产对穷人所具有的意义中”。“工人粗陋的需要是比富人的讲究的需要大得多的赢利来源。”[1]345这样一来,我们就像霍克海默看到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设下的诡计:“只有对这个体制感兴趣的人才有资格对它进行批评。至于其他那些有机会从下层社会认识这个体制的人,他们的反抗斗志被轻蔑的评语——易怒、嫉妒、报复心重,消灭殆尽”[3]101。
看来,首先,在如何消除贫困这个问题上意识形态的雾障也必须消除。当然,从私有财产制度的角度看,穷人和富人,即是私有者同私有者的关系。在这里,如果国民经济学要关注财产问题,那么国民经济学就认为,穷人就是那种只剩下没有权利或资格使用私有财产的人,但是,国民经济学家同时也想到穷人也必须使用一定的物品。他也有需要。那就搞一个济贫法。从法律上规定穷人的合法需要。只不过,穷人的需要是维持穷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的需要,而且只限于保持穷人的后代不致死绝的程度。所以,满足穷人的需要,就像“为了保持车轮运转而加的润滑油,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4]66。看来只有国民经济学家能够这样麻木不仁。只有他们才会声称:这不是穷人获得了使用权,这只是一种没有权利的使用。这正是国民经济学虚伪及矛盾的地方。
其次,对于马克思来说,这种想法确实让人们看到富人与穷人,两个私有者之间对立的社会关系。为了生存,每一个人生来都需要仅仅凭自己一己之力不可能获得的事物,由此他就需要群体,其中每一个人都为他提供某种他所需要的事物。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与其他的人都处于此种关系中。由此,各种人类共同体在其中产生了。有完满的共同体,也有异化的共同体。资本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异化的共同体。一方面,正如今天我们所见,高盛集团这种规模的私有银行可以对西方国家政府产生极大的影响力。它曾多次因欺诈行为而被告上法庭,但它依旧是个不倒翁。然而再看看政治领域,就会感到无比惊讶。共济会是世界上最有钱和最有权势的人物结成的“兄弟”同盟,美国是一个完全被共济会控制的国家,总统的政治见解必须与共济会的需要保持一致,否则,就是尼克松或肯尼迪的下场。
就在这一点上,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中,社会交往和人在私有权范围内的联合只是表现为“物物交换”,“它同时也是同社会关系的对立”[4]173。因此,我们满眼看到的,满耳听到的,是利用穷人赚钱,是假借服务社会名义而开拓市场,是非政府组织充当资本的帮凶,是政治如何为了经济利益损害就业;一句话,劳动和资本对立一达到这样的极端,贫穷和社会对立就是同一回事。这时,人们感到极深刻印象的就是,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者的“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里所描写的那种景象——“吸烟、饮酒、吃饭等等在那里已经不再是联合的手段,不再是联系的手段。交往、联合以及仍然以交往为目的的叙谈,对他们来说是充分的;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并且他们那由于劳动而变得坚实的形象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精神之光”[1]348。要言之,共产主义是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消灭贫困的基本逻辑。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2] 陈奇佳.卢卡奇论戏剧[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68.
[3] 哈特曼.富国的贫困[M].李明瑶,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
[4]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5] 桑巴.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M].安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04-205.
[6] 黄凤祝,等.伯尔文论[M].袁志英,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63.
[7] 施米特.政治的概念[M].刘宗坤,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92.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
[责任编辑:高云涌]
2016-03-3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MEGA2的马克思早期文本研究”(15ZDB001)
张文喜(1961—),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B1
A
1002-462X(2016)12-002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