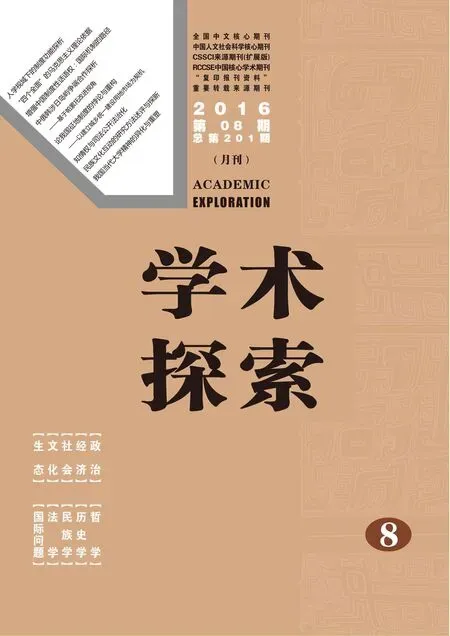论推动民族艺术重构的决定要素
——名誉资本、国家在场与权力
张 晨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论推动民族艺术重构的决定要素
——名誉资本、国家在场与权力
张晨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少数民族文化事项表演者名誉资本的提升与权力的获得依赖国家力量。国家以观众的形式介入艺术场,在观众和分配者双重身份间转换,逐步掌握艺术场控制权。表演者通过吸引带有国家缩影的优位观众并获得推荐权,升入更高层次的艺术场角逐,以优异的人际交往能力胜出并获得国家力量的塑造,使其在高阶名誉资本下获得民族艺术重构的权力,进而获得在国家管控限制下的垄断权力。
民族艺术;名誉资本;权力;国家在场
国家是一种抽象的政治实体,国家力量是其行政范围内的主导力量,将权力延伸至国家行政范围内的所有场域关系中,通过场域网络发挥作用。艺术场作为场域关系中的一种,既受国家力量的权力支配,又分享国家力量的支配权力。艺术场内所有人均可以通过竞争获取国家力量赋予的权力。当下,很多少数民族文化事项被人们称为“艺术”,并被重新整合、改编为舞台艺术,扩大该文化事项的名气,从而吸引来自国家不同层面的关注。文化事项是文化的一部分,其非物质部分需由承载体来承载,因此该文化事项的表演者便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同一文化事项的表演者数量可能会很多,甚至对该文化事项所能演绎的水平不相上下,在这种情况下,表演者需要不自觉地进行竞争,以获取相当的名誉资本,以吸引国家不同层面的注意,进而成为该文化事项的代表人物。
名誉资本的获取、提升与塑造是少数民族文化事项表演者成为该文化事项代表人物的关键要素。“名誉资本即名望信誉”,是象征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象征资本的展示是导致资本带来资本的机制之一”,资本以象征资本的形式转换为可使用的权力。[1]表演者通过不同层面艺术场斗争,获得来自国家不同层面对名誉资本的塑造,使名誉资本不断提升,表演者将自身名誉资本转化为可使用的权力。民族艺术作为一种民族文化事项,从审美惯例到演绎法则等方方面面均具有被重新构建的可能。民族艺术的重新构建需依托表演者或者国家力量的支配。民族艺术表演者凭借国家塑造的名誉资本转化而来的支配权可推动民族艺术多方面的重新构建。表演者将该文化事项由地方传统转变为国家传统过程中,他以形象代表的身份借助国家力量推动该文化事项的审美惯例重构和“再地方化”。
一、观众的评价是获取名誉资本的重要影响因素
名誉资本是一种象征资本,布迪厄称之为“物质和象征保证人的一种信用”。名誉资本为持有者提供了可靠的、持续的、可转化的象征性利益,并为持有者提供了将“信用”转化为一定支配权力的资本,因此拥有名誉资本等同于拥有支配权。文化事项表演者想要获得支配权,需通过名誉资本的获取。普通观众的评价为某文化事项的表演者的名誉资本获取提供初步参考。表演者在展演文化事项的过程中,他所演绎的角色和内容能否使生活在该文化中的观众在其阐释中产生共鸣,是观众对其演绎水平的评价标准。[2]本土观众对本土文化事项极其熟悉,他们可根据自身文化经验对演绎者进行较为客观的评判,并给出详细的参考值。但本土观众不一定是评价的决定者。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尽管旅游业不断发展,但本土民众与外界社会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并不多,使本土观众内部对某位表演者的评价并不能得到更大范围的认同。即使身处在同一种文化当中,物理距离也决定了相同文化中相互交流的机遇同样有限。除此之外,即使本土观众对某位表演者的评价较高,他的评价并不能得到“合法”的认可,即评价者缺少名誉资本,使其评价缺乏可信度。
观众的位置决定评价参考值的分量。观众既是消费者,又是评价权力的持有者,有充足的理由对某位表演者给予相应的评价。本土观众给予表演者初始名誉资本,当具有优位的观众进入艺术场之后,他们在艺术场中观摩的行为已经使其成为该表演者的观众,并对该表演者给予评价。成为观众的优位持有者给予的评价具有不同分量,将该分量附加在表演者身上,决定了表演者获得的名誉资本的大小。“齐美尔指出,在任何社会互动的情势之中,人与人之间都可能有优位之势与劣位之势这类不同境地的区别。”[3]相对劣位观众而言,具有优位的观众给予表演者的名誉资本明显较大,并且优位观众掌握实际评判权力。尽管在《艺术社会学》当中提及“文化客体受到创造和分配它们的人和体系的过滤和影响”,[4]但在实际消费过程中,优位观众作为表演的接受者,其评价几乎作为该表演者的唯一评判标准,并决定表演者的初始名誉资本。
同时,处于优位的观众对权力场的推动与重组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贝克尔提出艺术品符合被分配的标准,否则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被分配。[5](P87)优位观众以分配者的身份,在艺术场中逐步掌握控制权。若优位观众介入表演者的表演,该观众可能会影响表演者的演出,进而打破艺术场内的权力平衡,从而由外界推动艺术场的权力重组。优位观众是权力的持有者,也是权力的执行者。他所持有的不同层次的权力使表演者可能为投其所好而调整表演的内容,这种调整本身已经形成了推动艺术场权力重组的初始力量。优位观众在进一步介入艺术创作当中,甚至成为艺术创作的主导力量时,观众的身份也随之发生转变,即由观众角色向分配者角色转换。比如文化部门工作者以观众的身份观摩表演并给予初步评判,该工作者拥有使表演者与文化部门进行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决定权,他俨然成为被国家选派具有初步推荐权力的国家代表,他掌握表演者获取更高层面艺术场入场券的推荐权力。表演者为获取该工作者掌握的权力,需根据该工作者的要求对自身的演绎进行调整,以期从该工作者处获得更高的名誉资本。这使该工作者的身份在观众和分配者之间转换。
二、表演者的人际关系是获取名誉资本的基础
人际关系是在权力场斗争中胜出的重要的环节。拥有同一类文化资本且水平相当的人有很多,但终究只有其中极少部分人能够成为该文化的代表,这类极少数的人拥有了充足的名誉资本与其他人或事物进行周旋。如上文所述,获取名誉资本需存在几个便利条件,即较为便利的地理环境、较为恰当的推荐人甚至包括运气因素等等。除此之外,名誉资本的获取还需要某人具备较为优秀的沟通活动能力,使其能够在人际关系中胜出。大型艺术场的入场券是表演者角逐的第一步。在入场券的获取过程中,初始名誉资本的获得是表演者的立足之本。但并不是拥有了来自民间的名誉资本,就能进入艺术场,表演者还需与其他艺术场的权力持有者之间进行周旋,以期获得其他人的认可。他需要动用所有的资源,为其做好铺垫,比如很多表演者进入艺术场时依靠部分观众的优位得以获得入场券。想要获得优位观众的支持,除了拥有卓越的表演水平,还需要获得优位观众对其人品进行初步的判断。虽然表演者的实际品行与其所表演人物之间的品行存在一定的差距,但表演者凭借自身优异的表演能力,尽量将自己演绎为品行高尚的人。除了以品行、表演水平来迎合优位观众的心理需要,他还需要与其他表演者之间展开竞争。
表演者需要通过组建团队提升名誉资本。表演者在民间获取的初始名誉资本是其组建团队的基础。表演团队需要依赖人际关系得以建立,不同表演者可能会选择不同的团队,提高自身的演绎实力。与表演者的单独演绎比较,组建小型艺术团体能够获得更大的名誉资本。每个团队都有可能获得优位观众的支持,因此不同团队之间存在着竞争。表演者名誉资本的提升有助于其依靠人际关系与其他团队进行博弈。表演者从表演个体开始组建团队,当团队到达一定规模时实现与其他团队的联盟,通过两个甚至多个团队的联盟的方式扩大名誉资本。当表演者尝试接触其他团队时,可能会通过人品、演绎水平等多方面因素,使部分团队愿意与该表演者组成联盟,成为他的助力。部分与其他艺术团队无法协调的表演者参与进该表演者的团队,补充团队演出力量,表演者也有可能利用其自身团队人员,与其他团队进行接触,通过熟人引荐,使其实现与其他团队的联盟。对于两方团队来说,形成联盟意味着两方最具魅力的表演者团队形成,多位较知名的表演者组成团体提高其名誉资本,团队联盟协作意味着两个团队都获得了更强大的表演阵容,这为获得艺术场入场券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但联盟也有失效的可能,一旦发生失效,双方表演团队在两方代理人的领导下,既可能进行良性竞争,也可能出现恶性竞争。当恶性竞争形成时,双方会动用各自的资源,阻碍对方获取更大名誉资本,资源较多的一方容易获胜。恶性竞争对双方而言会在内耗的过程中导致双方名誉资本均受到损失,这就会为其他团队名誉资本的提升提供了机遇。当双方胶着于演出权力斗争时,双方均无暇抵抗其他团队的运作,其他团队利用其斗争的间隙,不断通过与斗争双方早期积累名誉资本相同的方式迅速提高自身的名誉资本,使其他团队具有获取艺术场入场券的可能。
艺术场由众多权力体共同组成,表演者需依靠人际关系获取不同层面权力机构的支持以进入大型艺术场。艺术团体的组建为表演者提供了获取大型艺术场入场券的机会。他所组建的艺术团体通过不断巡演,与不同权力机构以及更广泛的观众进行交流,使其拥有获得更大名誉资本的可能。艺术团体的演出需获得由权力机构颁发的各类表演许可证,在办理许可证的过程当中,与权力机构的交涉,使该团体的代理人能够进一步了解权力机构的实际需求,这使其掌握了迎合权力机构以期获得其支持的技巧。表演者在与观众的交流过程中已经习得充足的迎合技巧,这使表演者将权力机构作为潜在的观众,吸引潜在观众观看其表演成为表演者的重要任务。不同层面的权力机构对于观看表演的需求可能存在差异,表演者通过揣摩,设定不同版本的演出,以期获得权力机构对他的赞许。权力机构的许可为表演者提供了一定发言权,他以“彰显传统”为名,尝试向权力机构提出扶持保护传统的要求,并以此获得替国家行使权力的机构为其提供的名誉资本塑造机遇。
三、国家力量的介入是名誉资本获得塑造的根本途径
国家以权力符号的形式介入文化生活方方面面,并定义文化事项的“合法”和“非法”。国家力量对某事项是否合法的评判,是该事项能否获得生存空间的法定基础。当国家有通过对某事项的评判促进对国家认同的需求时,国家力量除了给予该事项“合法”地位,还可能会在恰当的时机给予该事项攀附的机遇。该事项本身攀附国家力量,未必会引起共享该事项的所有人对国家产生认同,若使共享该事项的人以事项代理人的名义获得攀附的机遇,则可使事项代理人凭借自身的名誉资本优势为国家认同提供号召条件。国家在形塑文化事项的同时,文化事项也打破了被动的局面,其代理人主动将国家符号引入自己的生产生活当中,使自身与国家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强化自身的合法性。
名誉资本需攀附国家力量获得塑造并得以扩大。在以往的仪式展演或者舞台表演中,表演者不一定具有合法地位,甚至可能会被评判为“非法”。在这样的情况下,变成“合法”成为其追求的目标,甚至借助加入国家认证的某些机构,以期获得“合法”地位。获得“合法”的地位需要获得较高名誉资本,通过较高名誉资本以换取权力机构的注意,并寻求其颁发证明其“合法”的证书,“权力机构颁发的关于能力的证明,就是对证书持有者的技术能力和社会能力进行担保和认证的社会委任书,是以对发证机构的集体信仰为基础的信誉称号”。[6](P204)但表演者加入国家认证机构的申请不一定会被接受,比如会被认为表演者所展演的文化事项不在该机构所涉及的管理范围内(如民间巫师申请加入佛教协会),因此拒绝了表演者的申请。部分表演者拥有充足的网络资源,在互联网空间中活跃存在,但仍旧没有获得“正式名号”。在这种情况下,表演者只能借助观众的引荐,以“彰显传统”为名,向不同层面的国家政府申请证明其“合法”的“证书”。国家力量的介入使其拥有了法律保护下的“名正言顺”的称号,但获得称号并不能满足名誉资本的进一步提升。因此,名誉资本需要在获取国家赋予其相应称号的前提下,获得国家力量的塑造,表演者才能使名誉资本进一步提升。
国家有保护传统、营造认同、增强团结的需求。国家力量塑造该表演者,使该表演者在高层次艺术场中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的民间文化代表,在低层次艺术场中是国家文化精英的代表。表演者在低层次艺术场或民间仪式中的演绎,营造少数民族地区良好文化氛围,使少数民族文化需求得到满足。“政府可能会认为,一些艺术或全部艺术都是民族身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政府资助它们,因为它们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特征”。[5](P165)通过国家授权表演者在民间的演绎,表演者将国家带给少数民族地区民众的优惠政策通过表演实现传达,民众的文化心理得到满足,最终实现民众对族群的认同、对国家的认同,提供了维护国家统一、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稳定发展的条件。“彰显传统”是表演者在国家政策扶持的情况下获得的最佳塑造,并以“传统”为名展示其演绎的内容。“文化世代传延形成传统,传统之‘统’体现着古往今来人类文化的根脉与连续性,同时又在‘传’中必然地历经各种变迁与考验,并与不断成长的现代性在相互借鉴中表现自身和熔铸新生。”[7]表演者所塑造的“传统”必定是在其所生活的文化圈中正在展演的部分文化事项,或距离目前并不久远的某些文化事项。表演者通过引用口述史、地方志以及优位观众为该文化事项撰写的历史内涵等多种方式,证明其自身演绎的内容与“传统”相同或相近。表演者以“传统演绎满足民间需要”为名,争取国家力量保障其拥有固定的表演空间。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部分表演者在舞台上演绎的内容均取自民间,有些直接取材自部分民间仪式。这些来自民间的演绎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很多表演者身兼民间仪式专家和舞台演员两种职能,这为表演者提供了以“传统演绎满足民间需要”为名争取国家力量塑造的理由。国家出于满足普通民众需求的考虑会提供支持,这就促使表演者不但提升名誉资本,同时也获得了由国家授权其民间演出的“合法”条件。因此,“彰显传统”为表演者提供了名誉资本获得塑造的条件,国家也获得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稳定和发展的条件。
不同层面国家缩影的优位者的关注为表演者带来更广泛的观众,表演者充分地利用“传统绝活”,通过不断借势宣传以展现特色。这些优位者兼有观众与分配者两重身份,使表演者继续获得优位者为其争取的更广泛舞台,使“传统绝活”以保护和发展为名,获得国家提供的更高层面艺术场,使其从自身所处文化圈中的艺术场逐步胜出,使名誉资本在自身文化圈的艺术场中逐步提升到极致。“彰显传统”需要依靠表演者的“绝活”,并使之成为吸引国家力量塑造名誉资本的关键要素。表演者拥有了向所有人展现“绝”的资本,这为表演者区别于其他表演者提供了有力的参考和证据。“彰显传统”中强调“传统”,表演者将“绝活”与“传统”绑定,不断强调“面临失传”的危机,这使包括优位观众在内的众多不同层面国家缩影的优位者为如何保护甚至发展以“失传”为名的“传统绝活”展开研究和规划,使表演者以“传统绝活”的名义获得更多的关注。表演者进入国家层面的艺术场,这使其转入来自不同文化圈的“传统绝活”权力者组成的更加庞大复杂的艺术场中角逐。这些权力者所掌握的名誉资本与表演者相差不多,所有的权力者都在设法使自身掌握的“传统绝活”由地方传统象征提升为国家传统象征,以期在国家层面艺术场中将名誉资本提升至极限值。表演者想获得名誉资本的极限值,必须在国家艺术场中胜出。这促使表演者根据国家需要,在演绎过程中不断融入国家符号、营造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若获得国家的认可,这将为该表演者提供了推动同类表演的艺术重构和“再地方化”的权力。
四、民族艺术重构受被塑造名誉资本的决定性作用
文化是人创造的,由于文化始终处在变迁之中,因此文化本身并不是一个完全完整的整体。“文化变迁就是碎片化到重构的过程。”[8]民族艺术作为一种文化事项,在其原有的文化语境中不一定被称为“艺术”,当被剥离出原文化语境,强调其艺术的形式,它本身便成为一种碎片,因此在一定外在条件下可以被重新构建。
表演者的名誉资本被国家力量塑造到一定程度时可推动表演审美惯例的重构。艺术场的范围可根据其所处时空位置发生变化。如在国家层面,没有获得许可证的表演者不得入场;转换至地方或更小范围内,所有表演者都可以成为艺术场内的权力斗争成员。虽然处在较低层面的艺术场内斗争仍然激烈,但与国家层面的艺术场相比,其影响有限。国家力量介入高层面艺术场,并在成员获取不同等级权力的基础上,给予不同等级的塑造,使表演者获得更多观众。获得“证书”的表演者被处在非自身文化圈观众观摩,获得该群体的高度评价,除名誉资本不断积累和扩大外,他的表演也很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在本文化中推行的范本。尽管本土观众可能会对持有更高层面艺术场入场券的表演者不满,但获取国家“证书”的优位表演者仍旧在更大范围内树立起更具实力的名誉资本,并获得不同程度的塑造。来自国家颁发的“证书”已经认可表演者代表最高表演水平,并通过国家力量介入塑造,使越来越多的本土观众通过媒介接触到他的表演。随着媒介的不断推广,本土观众对同类表演的审美逐步由原本获得其认可的其他表演者转变为该表演者,进而由优位观众的审美意识变迁推动地方艺术场内审美惯例的重构。
审美惯例的重构为与该表演者演绎的同类表演提供了“再地方化”的可能。该表演者生活的文化圈内,即使演绎相同的文化事项,不同表演者的演绎细节甚至框架均存在差异。审美惯例的重构,使不同层面的艺术场逐步改用新的惯例对全体表演者进行审美评判。即使观众不足以撼动其他表演者主动修改自身的演绎,但新惯例的产生迫使越来越多的表演者主动迎合,以避免失去入场权力。沿用先前惯例的表演者,逐步失去了融入以新审美惯例为衡量标准的入场券。其他表演者主动迎合新审美惯例,使处在先前惯例中的表演者表演范围逐步缩小甚至消失。手握不同层面艺术场入场券的表演者,有一部分人兼任艺术场内的表演和文化事项展演的双重职责。艺术场的审美惯例被重构,使兼职双重职责的表演者调整自身表演以达到艺术场的审美要求,即使他回归原文化圈当中,多少携带有在艺术场内为获取名誉资本而迎合新审美标准并改造的表演内容。“在我们的直觉和思维过程中存在着很强的保守倾向。”[9]该表演者主动迎合并适应新审美惯例,使其在思维逻辑惯性的驱使下,将新审美惯例带入自身展演的文化事项中,使文化事项由审美惯例的变迁引发变迁。这使新生成的审美惯例引发了该表演的“再地方化”,这更加使得先前的审美惯例失去了生存之地。前文提及的塑造新审美惯例的表演者俨然成为其演绎文化事项“再地方化”的发起者和受益者。这为其在本土文化中再次收获名誉资本提供了更广泛的观众基础。国家力量为其提供了便利的发起条件和丰厚的收获条件。
英国人类学家托马斯认为“再地方化”使不少“传统”被激活,以此来打造和强调“地方性”,为拥有该“传统”的社区谋取利益。[10]表演者作为“传统”的代理人,以自身演绎作为“传统”被激活的“偶然因素”,使他的演绎成为该“传统”的表演范本。他通过“再地方化”在本土文化圈中成为表演范本,使其收获了充足的名誉资本,在艺术场中握有充足的权力。其中较好的结果是获得该资本的人能够将其所拥有的文化资本进一步推广以扩大其社会影响力,负面的影响可能是由于某人获取了相应的名誉资本,并阻止了更多适宜参与进该文化资本的人,形成权力的垄断。获取名誉资本需要以文化资本为依托。想要获取名誉资本,处在某种文化当中的表演者需懂得其所处文化的特征,有能力对该文化所蕴含的某种文化事项进行简易的塑造,或有较突出演绎该文化事项的能力。表演者在自身演绎的基础上,重新吸收整合本土或外界社会对该文化事项的评价之后,对该文化事项的某些外在进行解说,以吸引其期待的观众。“拥有称号的人是稀有位置的合法拥有者,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杰出技能的掌握者,这一切便构成了他们垄断的基础。”[6](P214)这导致该表演者使用其权力对艺术场内的表演进行“垄断”,其他表演团队逐渐失去在艺术场中的话语权,随之逐步失去艺术场的入场券。其他表演者或表演团队预想进入艺术场,只能通过加入该表演者的团队获取艺术场的入场券。该表演者作为其团队的唯一代理人,除了决定谁能获得表演资格外,还有权力决定表演的内容,以及评价其他表演者的表演水平。这种“代理人”式的制度,不利于发挥团体的创新能力,导致文化事项由活态转变为非活态。国家在这种情形下可能会随时介入该表演团体,从逐步取缔代理人的“证书”开始,逐步剥夺代理人的名誉资本,逐步将权力转交给艺术场内外的其他表演者。国家作为观众和分配者,通过调配艺术场中的权力,避免了表演者由于艺术垄断造成艺术停滞发展的后果。
国家、名誉资本与权力是驱动民族艺术重构的决定要素。“由于国家控制力量的强大,民间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更多表现为民间社会向国家的主动靠拢,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在场时的‘国家姿态’:国家是主导者、施惠者。”[11]优位观众可能会被表演者认为是国家的缩影。文化部门工作者以观众的身份进入地方艺术场,尽管他不足以代表国家,但他所掌握的地方艺术场与文化部门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决定权,使他在表演者眼中显然带有国家的缩影。这类优位观众有权力将表演者引荐至不同层面文化部门,表演者只有通过这些优位观众,才能够获取进入大型艺术场的入场券。至此,国家以观众的形式介入地方艺术场,并通过观众和分配者双重身份的转变,使国家逐步掌握艺术场的控制权。表演者想要提升名誉资本需要攀附国家力量。表演者通过人际交往,获得不同层面权力机构的支持,使其进入更高层面的艺术场,并通过组建团队和结盟等方式提高自身演绎实力,在高层面艺术场中获得一定的发言权。他以“彰显传统”为名获得国家颁发的“证书”后,进入国家层面艺术场与来自不同文化圈的“传统绝活”权力者的角逐,通过营造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以获得国家支持,最终实现将地方传统象征提升为国家传统象征,使名誉资本提升为极限值,进而获得推动艺术重构的权力。
[1]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M]. 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2]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M].杨利慧,安德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邓正来.中国法律哲学当下基本使命的前提性分析[J].法学研究,2006,(05).
[4]维多利亚·D·亚历山大.艺术社会学[M].章浩,沈杨.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3.
[5]霍华德·S.贝克尔.艺术界[M].卢文超.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6]皮埃尔·布迪厄.国家精英[M].杨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7]郑杭生.论“传统”的现代性变迁——一种社会学视野[J].学习与实践,2012,(01).
[8]严墨.文化变迁的规律[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04).
[9]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10]冯广圣.“去地方化”与“再地方化”:乡村旅游传播对村庄社区文化的影响[J].新闻界,2014,(23).
[11]陆群.民间仪式中的国家在场——以湘西花垣县大龙洞村苗族接龙仪式为例[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06).
〔责任编辑:李官〕
The Determinants of Promot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Ethnic Arts:Reputation Capital, Power and the State in the Artistic Field
ZHENG Chen
(College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Wuhan, 430074, Hubei, China)
Ethnic cultural performers enhance their reputation capital and get power dependent on state power. In the artistic field, state intervention begins as an audience, transforms between audience and distributors, and gradually controls the art of field. Performers who have been recommended by attracting the privilege audience with the epitome of state power are promoted to a higher level of artistic field competition, win and get the shape of national power with excellent interpersonal skills. Then, supported by the high-order reputation capital, they obtain the power of reconstructing ethic arts, and finally the monopoly power under national control restrictions.
reputation capital; power; the state in the artistic field
张晨(1987—),男,黑龙江大庆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
J0-02
A
1006-723X(2016)08-0135-06